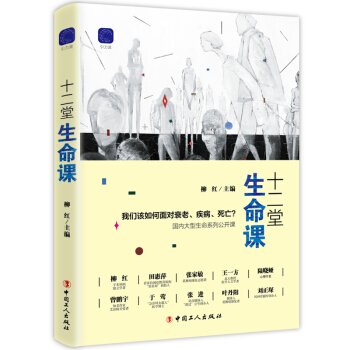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l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疾病、死亡;l国内首次系列生命公开课;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
l本书邀请了有过特别生命体验或专门进行研究实践的学者亲身讲授他们的经历;
l子尤妈妈、独立学者柳红,自闭症教育机构“星星雨”创始人田惠萍,乳腺癌康复志愿者张家敏,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心理学者陆晓娅,艾滋病关爱者曾鹏宇,“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渡过”公号创办人张进,乳腺癌康复者叶丹阳,民间骨髓库创办人刘正琛;
l流动的生命之河,开放的精神空间
内容简介
如今,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老和病”主体被边缘化,很多人从心理上视其为“失败”“无望”的人生。所以“十二堂生命课”邀请了十位具有特别生命体验的讲者,把老、病、死的话题作为公共话题谈出来,希望人们开放地、有准备地面对,重新规划自己的有生之年,让老后和病后的生活成为人生美好的时光。作者简介
柳红,子尤妈妈,独立学者。2004年进入疾病与死亡的世界,在癌症患儿的精神关怀和失丧关怀上做过一些努力。十年来,除了对于病、老、死、医患关系等有思考,也在身体和健康的认知与实践上着力,成为马拉松跑者和百公里毅行者。目录
第一讲 残缺之美:当我与乳腺癌遭遇 / 001第二讲 那些逝去的生命教给我们的事 / 001
第三讲 宿命之问:我们为什么害怕死亡 / 025
第四讲 失丧十年:我的路 / 077
第五讲 生如夏花:78岁抗癌勇士的生命感悟/ 099
第六讲 永远的陪伴:我和我的自闭症儿子弢弢 / 113
......
精彩书摘
第五讲失丧十年:我的路当我想讲这个题目时,却发现不知怎么准备,那些化在生命里的心路历程,岂是语言可以表达?首先特别要说感谢的话。是很多人的帮助使我走到今天;除了感谢还有缅怀。这十年,有很多故人离去。我们生病后,就经历了周围病友相继死去,意识到死亡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离去,我都痛惜得不得了,尤其会想到他们的家人。
关于“失丧”和“哀伤”
第一次知道“哀伤研究”是在三年前,北师大心理系研究生何丽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哀伤研究。她访问了一批丧失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也找到了我。
实际上,所有人都要经历“失丧”。人类世世代代就是在这样的生生死死中发展、演变的。但总有一些死亡,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哀伤指数的话,它的哀伤程度要高一些。死亡,有正常和异常之分。经历异常死亡的哀伤要深于经历正常死亡。比如,失去孩子----本应承续父母血脉的,却亡故在先,这就属于异常死亡。即便如此,在多子女时代,失去孩子也是常有的事。对于那些父母来说,他们还要哺育这个,拉扯那个,得以将哀伤转化成对其他孩子的养育责任上。然而,失去“唯一的孩子”;更为甚者,失去“不得不”是唯一孩子的情形,是中国1980年后推行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有现象,确实是人类不曾有过的极端情形。而我,就不幸落在了其中。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丧子爸爸妈妈,我知道有一些父母难以承受如此丧子之痛而病、而亡,身心饱受折磨。对于我,在那个时刻,怎么样才能够活下来,是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什么是对孩子最好的爱?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是我的大学同学夫妇。前不久,他们的孩子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孩子在世时,成绩等各方面极为优异,令父母引以为骄傲。她非常急切地大声问: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活下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说是“爱!”
她问:“为什么?”她的意思是说,儿子是我们的希望,当希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我要随着这个破灭的希望而去了。
但我却觉得它可能就是一转念的事:我们爱孩子,什么是对他的爱?怎么体现这个爱?孩子一定希望爸爸妈妈在他不在之后,还能健康,还能过一个好的生活,还能有他们生命价值的体现。而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亡故,爸爸妈妈也倒下去。所以我说,对孩子最大的爱是,我们过得好。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次我们的通话。我当时还说,我想跟她先生谈谈,因为她先生相对封闭一点。她告诉我,用的是免提,先生正在一旁听着。而她的问题是很多丧失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首先追问的。
建立什么样的观念固然重要,但是,毕竟日子是要一天一天过的,而且是在每分每秒地承受着心灵煎熬之下过,这绝非易事。
子尤是2006年10月22日去世的,马上就进入冬天了。往年我们都买冬储大白菜。到了时候,大卡车又拉着白菜来我们小区卖。那天,我就站在车边上看着那堆白菜,和热热闹闹地抱菜上称的欢喜人家。而我独自一人,确实没什么吃的能力和必要。但是,这个时候买不买冬储大白菜的含义,好像超过了餐桌的需要,而是个心气儿。事关日子过不过,怎么过?最终,我还是下决心买了,搬到楼上去,用报纸包好,码在阳台上。
社会网络支持与偏见
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最难过是曲终人散时。朋友们可以救急,在危难之时伸手帮助,但是,曲终人散时,只能自己面对。虽然街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孤岛上,是心灵的孤岛,无处话凄凉。那时的信息手段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还是博客时代。多亏有很多远方的不相识的网友依旧访问子尤博客,在上面留言。每天看留言,对我的心理是一个安慰。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作用。我们处在一个较为中心的节点上,得到了更多的精神支持。
人们在面对丧子之痛时,有不一样的应对。这与她/他本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都有关系,并没有一个药方可以医治,只能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一个良善的社会和文化,有助于失丧者的康复;反之,则会加剧人的痛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感到至少有这样几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一是,要求失丧者快速封上哀伤的口子。
有一位妈妈孩子去世后,请了一段时间假,出去“散心”。回来上班后依然难忍悲伤。这是多么自然的情形,本应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关爱。可是她的领导却埋怨她:“你怎么还走不出来啊?”,给她增添了很大压力。这位妈妈通过博客找到我。我邀她到家里来。她一进门,就说:“哟,这儿真好。”因为在我家几面墙上都挂着儿子大幅彩色照片,孩子的骨灰就摆在条案上。而她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先生某次趁她外出,把所有孩子的东西全部用车运走。这是不想让她睹物思人,减少一些刺激。这位妈妈只有一张很小的孩子照片放在钱包里。她拿出来给我看,讲述女儿病中的故事。她先生潜在的意图是想封上这个痛苦的口子,堵住哀伤。结果,适得其反。而此时此刻,这位妈妈也不愿跟先生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毕竟孩子的爸爸心情也很难过。那天,她和我敞开谈,谈到伤痛处,我们一起哭;谈到美好处,一起笑。记得那天她离开我家时的最后一句话是说她一定能行。这位妈妈后来练书法。我知道,她父亲是一个擅长书法的老先生。多年未见了,想必她现在已经写得很好了。
2006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出来?”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当即的反应大概是,没有计划,也不可能计划什么时间走出来。这种痛苦会伴随我一生;我会一直流着眼泪往前走。两者并不矛盾。
二是,阴森恐怖的“哀伤”文化。
朋友们帮助我为孩子办了一个彩色的葬礼,每一位来宾手里拿一朵红玫瑰。我穿着新旗袍,换了新发型。我们还举着蜡烛,守着他,唱歌念诗。我觉得,这个样子符合儿子的心意。
子尤是10月22日去世,我们计划在24日举行告别式。有一位发小,23日来家。她带我出去买了旗袍和剪了短发。其实,当时我心里很不安。家里有一大堆事儿要做啊!虽然忘年交许医农先生在家里守电话,还有分工细致,进进出出忙碌的朋友。是朋友好意,专门带我出去。剪短发,是因为在孩子的最后阶段,我姐姐对他说:“你妈妈留短发可好看了。”子尤说:“我妈妈留短发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说:“那好,我哪天剪给你看。”然而,已经没时间了。所以,剪个短发给儿子看就成了一个心愿。
有人在网上说:这个时候他妈妈还打扮,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不够哀伤。
什么是哀伤?外人有什么资格凭着衣服和形象来评论我的哀伤?难道我蓬头垢面,哭晕过去、死过去才是表达哀伤?还有,“你”是谁?我凭什么要向“你”表达我的哀伤?这种非议里潜藏着这个社会和文化里一些很阴暗的东西。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而事实上,我眼看着那么多哀伤致死,哀伤致病、致残的人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关怀。哭还不容易吗?躺倒还不容易吗?死还不容易吗?难得是不哭,不倒,是活出来,活下去。
我研究生时代最好的朋友,她80年代去了美国,女儿患白血病去世。在葬礼上,所有的朋友都伤心痛哭。而她衣着得体,从头到尾没有让自己失态。只是眼泪从眼角悄悄流。每一个人过来跟她握手都说:“你真棒”。她就跟别人说:“如果是你,你也行。”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是此前我唯一一次受到的关于死亡的教育。
我不会按“习俗”行事,只会想怎么样最让孩子满意。记得2004年6月25日,那天是是他接受纵隔肿瘤切除术的日子。那时他14岁,很早就起来做各种术前准备,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在一个小本子上随手记下来。其中的一段说的是:“妈妈,你应该是高贵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举止文雅的,说话端庄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驮着背从外面走进来,给我丢脸。”这就是儿子对我的要求和嘱咐。我了解子尤的心思,是不可以给他丢脸的。所以,最后送别时刻,他躺在那里,我要尽量体面,这样一种精神之爱和连接,我能够领会,有所表达,是我的幸福所在。
偶然一个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果丹皮的网友说:“有一天我走了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但我希望离开苦难的那一天,我的母亲能够像子尤的妈妈一样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为我送行!”他这么清晰地表达自己希望什么样的送别。这是一位患肝癌的青年。我去医院看过他,与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后来,他的电话和博客都停掉了,想必他真的走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不知他的妈妈是不是了解他的心意,满足了他的心意,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为儿子送行?
三是,标签化,歧视。
人们倾向于给失丧者贴上“失败”、“悲惨”的人生标签,想象她/他的行为轨迹一定是怎么样的。而当事人害怕旁人异样的目光,或是尽力摆脱这种标签,迎合,在人前人后反差很大,在压抑和掩盖痛苦中难免成疾。另一种表现是,自己也接受这样的标签,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将“失丧者”与“健全人”分成两个世界。
也有给我贴标签的。我岂能被一个标签锁住?事实证明贴标签者是错的。因为我的跨界身份,更加理解丧子父母的处境。十年前,我曾接触过上海的丧子爸爸妈妈群体--“星星港”。他们是中国最早组织起来的,自助助人。这使很多丧子父母找到了家园。但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聚会时虽然高兴地说笑,回到家,就又陷了自己的痛苦难以自拔。近年来,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支持团体建立起来,在内抱团取暖,在外与社会隔绝的现象较多。他们遭受着各种各样地被歧视,难以回归和融入正常的社会网络。
……
用户评价
《十二堂生命课》对我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自我探索之旅。它没有提供标准答案,而是激发我不断地去提问,去思考。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关于“勇气”的章节。它不是鼓励我们去鲁莽冲动,而是教导我们在认识到风险和恐惧的同时,依然能够勇敢地迈出一步。这种审慎而坚定的勇气,让我觉得它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也更加具有实践的意义。 书中有很多令人回味的金句,它们如同种子一般,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逐渐改变着我对事物的看法。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希望”时,那种不带一丝矫揉造作的真诚。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洞察,以及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本书让我更加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会有微弱的光芒指引我们前行。它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并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能从中获得启发的宝藏。
评分《十二堂生命课》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里面装满了智慧和温柔。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独特,它不像传统的说教类书籍,而是通过一个个生活化的故事,将深刻的道理融入其中。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成长”的探讨,它没有强调一夜之间的蜕变,而是细致地描绘了成长的过程,包括那些不易察觉的微小进步,以及偶尔出现的退步和迷茫。这让我感到非常安慰,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成长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而这本书恰恰印证了我的感受,并给予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 书中的语言风格非常朴实,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力量。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击人心。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人物内心情感时所展现出的细腻和真实。它让我看到了,即使是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不平凡的意义。这本书不仅仅是在讲述道理,更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态度。它鼓励我们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去珍惜身边的人,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内心更加充盈,对生活也充满了更多的热爱和期待。
评分当我捧读《十二堂生命课》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所有的焦虑和不安都在这里慢慢消融。作者在书中关于“平静”的论述,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平静,并非来自于外界的宁静,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安宁。它不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过去总是试图通过改变外界来寻求内心的平静,但这本书让我明白,这一切都源于内心的转化。 书中的笔触非常细腻,能够捕捉到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情绪和感悟。我尤其喜欢它在探讨“自我成长”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循序渐进的节奏。它没有要求我一夜之间变成另一个人,而是鼓励我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积累。这让我感到非常放松,也更加有信心去面对自己的不足。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更加懂得如何去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评分初读《十二堂生命课》,我被它朴实无华的叙事所吸引。作者没有刻意制造悬念或华丽的辞藻,而是以一种真诚而温暖的笔触,娓娓道来。我尤其被它在探讨“学习”这一主题时的深刻洞察所打动。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是将学习视为一种不断探索、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我过去常常觉得学习是枯燥的,是应试的工具,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学习的真正乐趣,以及它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书中对“坚持”的论述,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者没有回避坚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败,而是强调了那种即使跌倒,也要爬起来继续前进的韧性。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它让我更加懂得,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保持耐心和毅力是多么重要。这本书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引导我更深刻地理解生活,并以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面对未来。
评分这是一本让我爱不释手、反复品读的书。《十二堂生命课》给我带来的最大感受,是一种久违的平静和豁然开朗。作者没有试图去定义什么是“完美”的人生,而是引导读者去探索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我尤其被其中关于“意义”的章节所吸引。它不是给你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让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这个过程充满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更加珍视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因为每一个决定,都在为我的人生增添属于我自己的独特意义。 书中的许多观点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它让我重新审视了很多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比如,它关于“放下执念”的论述,就彻底改变了我以往看待困难的视角。我常常会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而耿耿于怀,但这本书教会我,有时候,真正的解脱,并非来自于解决问题,而是来自于放下对问题的执着。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自由。我非常感激这本书,它让我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烦恼,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制造出来的,而解开这些烦恼的钥匙,也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评分《十二堂生命课》是一本能够触及灵魂的书籍。我非常欣赏作者在处理“爱”这一议题时的深度和广度。它不仅仅局限于男女之爱,而是将爱延伸到对家人、朋友,甚至是对自己的爱。这让我意识到,爱是一种连接,是一种滋养,是一种让生命更加丰盈的力量。我过去常常因为害怕受伤而不敢去爱,但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爱,是包含着接纳和理解,它能够让我们在付出中成长,在连接中获得力量。 书中的语言风格非常优美,却又充满了力量。它能够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和体会。我尤其喜欢它在描述“放下”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从容和智慧。它不是让我们遗忘,而是让我们懂得,有些过往,终究要学会放手,才能为新的开始腾出空间。这本书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也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段经历。它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并能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漫长旅途的佳作。
评分读完《十二堂生命课》,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洗礼。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钥匙”,它更像是为你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内在的门,让你有机会与自己更深层次地对话。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关于“接纳”的章节。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我们总是被鼓励去追求更好,去超越,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如何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作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方式,展现了接纳的力量,它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的开始,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但依旧热爱生活,并从中汲取前行的勇气。 书中的许多案例都非常贴近生活,没有那些遥不可及的“人生导师”式的论调,更多的是普通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境时,内心的挣扎与成长。我尤其记得一个关于“放下”的故事,主人公经历了巨大的失落,却最终通过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明白,有时候,我们执着于某些东西,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害怕改变。这本书教会我,真正的强大,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能够放下多少,不被过去的包袱所累,勇敢地走向前方。
评分刚拿到《十二堂生命课》的时候,我被它朴实无华的书名吸引了。没有华丽辞藻的包装,没有故弄玄虚的悬念,就像一位老友,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你的倾听。翻开第一页,我便被一种温和而有力的叙事节奏所包裹。作者的笔触细腻,如同在描绘一幅幅生活的写意画,没有激烈的冲突,却有深刻的触动。我尤其欣赏它在探讨一些看似宏大的生命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接地气的方式。它不是高高在上地给你灌输道理,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一个个 relatable 的场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与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甚至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其中有一段关于“选择”的论述,让我久久不能忘怀。作者没有直接告诉你什么选择是“对”的,而是引导你去审视每一次选择背后的动机、考量以及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它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于选择,并非因为选项本身有多么复杂,而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恐惧、期望以及对未知的抵触。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思考的框架,帮助我理清思路,更加理性地评估风险与收益,并且最终,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像是一次内在的梳理与疗愈,让我对过往的一些遗憾,有了新的理解和释怀。
评分《十二堂生命课》给我带来的震撼,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我发现自己开始更加关注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仅仅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是对“自我认知”的深入探讨。作者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引导我去审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并学会以一种更加客观和包容的态度来接纳真实的自己。我过去常常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潭,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但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和他人比较,而在于不断超越过去的自己。 书中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却又不失亲切感。它没有那些晦涩难懂的术语,而是用最朴实、最真诚的语言,与读者进行心灵的交流。我尤其喜欢它在讲述关于“感恩”的章节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深情。它让我意识到,我们常常会忽略身边最平凡的幸福,而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忽略的角落,让我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美好。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人生更加饱满,也更加懂得如何去爱自己,去爱身边的人。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是一本心灵的指南针。《十二堂生命课》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打开了全新的生命理解维度。我不得不说,作者在处理“关系”这一主题时,简直是大师级的。它没有简单地告诉你如何“维系”一段关系,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关系背后的本质,包括理解、尊重、以及边界感的重要性。这让我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在关系中感到痛苦,并非因为对方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对关系的期待,或者说,对“如何处理”关系的认知存在偏差。 书中的例子非常生动,让我仿佛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我尤其记得一个关于“冲突”的章节,作者没有将冲突描绘成洪水猛兽,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成长的契机,一种深入了解彼此的机会。这种积极的态度,彻底颠覆了我过去对冲突的负面看法。它教会我,与其回避冲突,不如学习如何建设性地处理冲突,从而让关系更加稳固和健康。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知识,更在于它能够引导我们去改变行为模式,去提升生活的品质。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评分正版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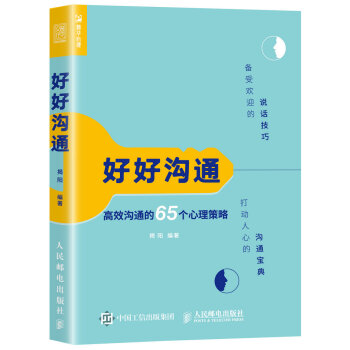






![中学生心理辅导 [Psychological Guidanc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1971/5a74348eNd75a2e0e.jpg)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185/5a338dcbN8e651500.jpg)






![健全的社会(弗洛姆作品系列) [The Sane Socie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681/5a5d9f49N0c842bd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