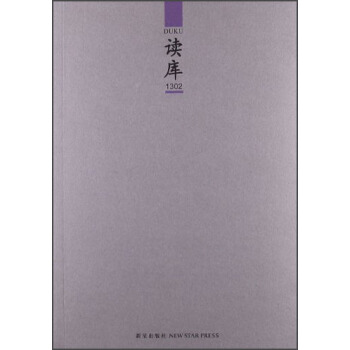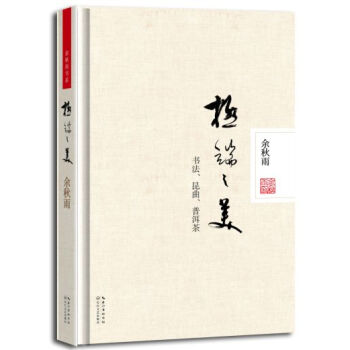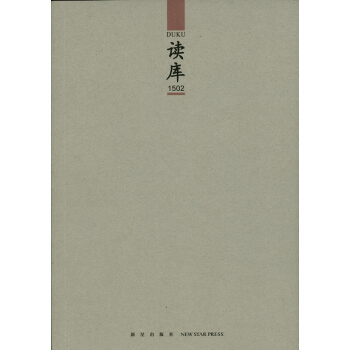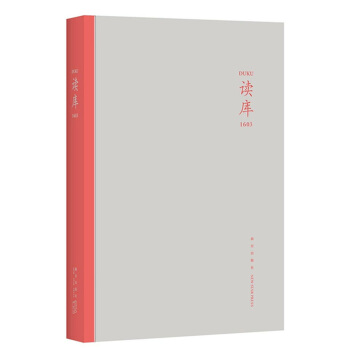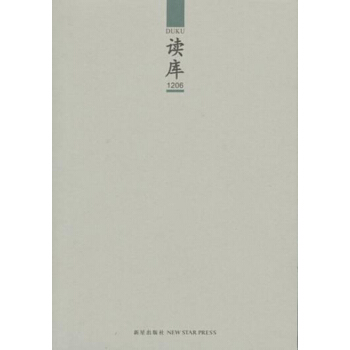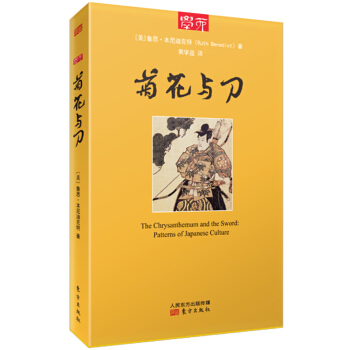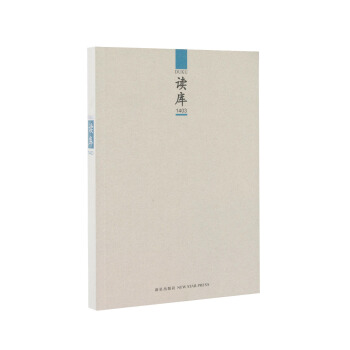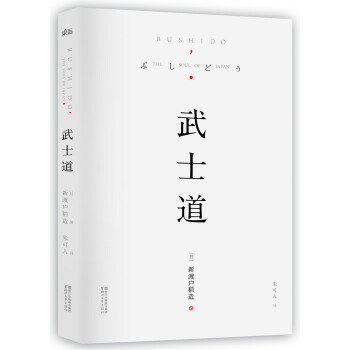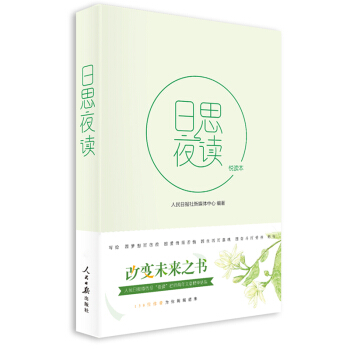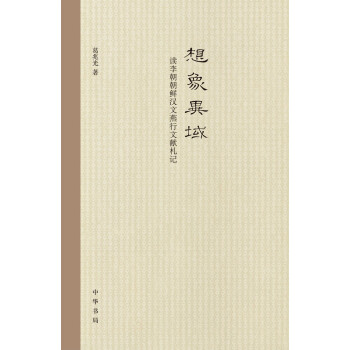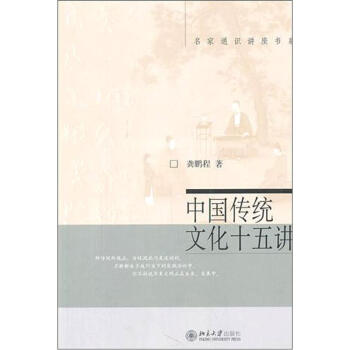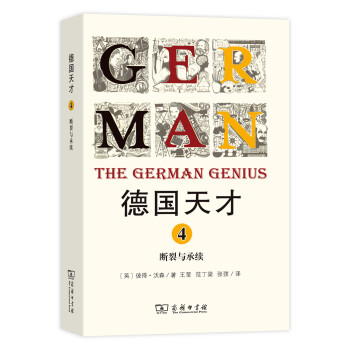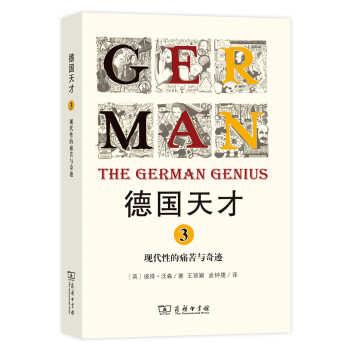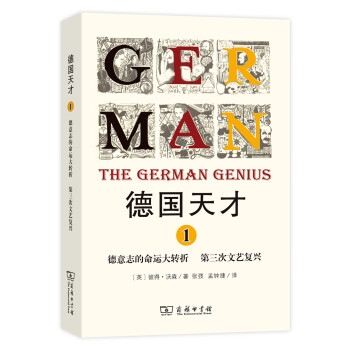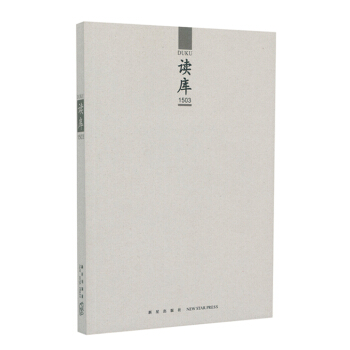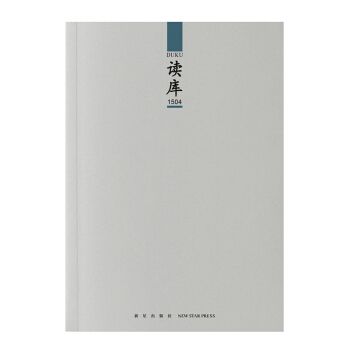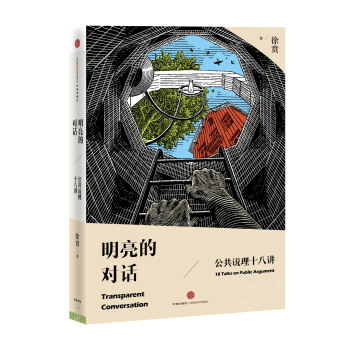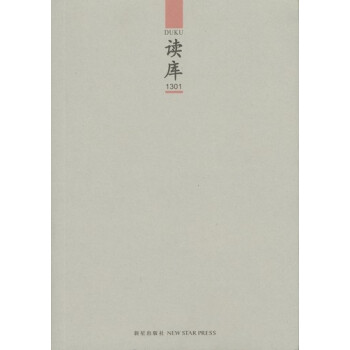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读库1301》一共有八篇文章,《第五次迁徙》、《两败俱伤》、《支边去》、《求学奇遇记》、《童书的黎明》、《谁论金角复银边》、《皇帝梦》和《声音》。
2008年3月,高屯子回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地,把手中的镜头,从阳光与风雪中的藏族牧人身上,移向了山林与田野里的羌族农民。在山路和田野间行走之余,他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破坏最惨重的区域,正是羌族聚居地。他和他的摄影团队常年穿梭在这一带高山深谷之中,有了了解熟悉路线和地形的救援优势,做了很多救援工作。重灾区灾民散落安置到各地,今后羌文化还如何延续?如何传承?仍是个很大的问题。他和助理去了不通公路的夕格羌寨和其他有羌人居住的深谷高山,了解羌文化,延续拍摄羌人的行程。《第五次迁徙》一文选了二十八幅图片,展示羌人离开故土的惜别之情。
《两败俱伤》讲的是一起由阑尾炎手术引起的医疗纠纷。医学并非尽善尽美,法律亦非滴水不漏,当医学迷局遭遇法学困境,我们能否收获期待中的正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许多十几岁的年轻人揣着户口本去报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要“支援边疆”,当时他们觉得离开上海,就像是一次秋游。而在遥远的新疆,团场领导说要派人到上海动员十万知识青年,接他们到新疆来,到兵团来,一起参加生产建设。《支边去》讲的是这些年轻人怀揣梦想到新疆“磨炼自己,改造地球”过程中经历的事情。
张五常的《求学奇遇记》是他自己的一段自述,从跟在哥哥后面上学到出国拿下博士学位,他说,他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求学一般求成见,是创作的大忌。
自格林威和凯迪克这两位童书艺术的先驱开始,童书不再是成年读物的简化本与配图本,主要供儿童欣赏的图画书,也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童书的黎明》一文,是作者姬炤华对“童书”发展史进行的梳理,包括了创作手法技巧材料以及印刷的变迁的介绍。优秀的童书正是通过用图画说故事的方式,将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路流淌而来的宝藏传递给儿童。
在《谁论金角复银边》中,作者余昌民回顾了1964年到1983年发生在清华发生的围棋往事。
张宏杰挖掘太平天国起义的另一面,在《皇帝梦》里,列举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各色人等在追逐“皇帝梦”过程中的起因和结果。
《声音》是每年年底《读库》的保留栏目,是对2012年的表达与记录。
作者简介
张立宪,出版人,曾策划《共和国教科书》《传家》《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等书,他策划主编的《读库》系列丛书成为近几年书业亮点,本人获选《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中国经营报》“中国思想力人物”。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五次迁徙 高屯子
两败俱伤 潘 悦 李清晨
支边去 大 力
求学奇遇记 张五常
童书的黎明 姬炤华
谁论金角复银边 余昌民
皇帝梦 张宏杰
声音 苗 炜 辑录
精彩书摘
第五次迁徙高屯子
大地震之后的中国羌人。
1995年5月,在成都举办了“高原风.朝圣之路”影展之后,我的拍摄对象在不经意间转向了青藏高原和西域大地那些美丽的风景,并把许多的时光消费在了与“旅游”、“文化”相关的“打造”中去。这十年间,虽然时时提醒自己要尽快回归初时的状态,但遍地泛起的物欲风潮,己汹涌摇晃着整个世道人心。及至2003年前后,内心对“打造”、“策划”之类的营生已十分倦怠,而对回归“以影像代替文字发言”的冲动与渴望,在心底日渐强烈起来;在晨光暮色中拍摄奇山丽水的激情,也随之减退。
2008年3月,结束了三年的居家阅读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业之后,在又一个春雪飘飞的季节,我重新回到青藏高原的东部山地。
这一次,我没有翻越尕里台,走向我熟悉的松潘草地,而是中途拐进了岷江上游的幽深山谷.
我把手中的镜头,从阳光与风雪中的藏族牧人身上,移向了山林与田野里的羌族农民。
在山路和田野间行走之余,我开始更系统地翻阅一些关于“羌”的文字。
通过对甲骨文的辨析,我们发现,“羌”,是三千多年前,殷商人对其以西大约今天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边缘人群的称谓;通过对《史记》,《国语》等古籍的阅读,我们了解到,“羌”,是秦汉时期由秦陇向西大规模扇形迁徙的那些族群;通过对《华阳国志》、《明史》,以及后来顾颉刚、费孝通等历代史家著作的浏览,我们又看到,两汉、魏晋之际,在整个华夏西部形成了广阔的“羌人地带”,从西北天山南麓的姥羌,河湟流域的西羌,陇南蜀西一带的白狼羌、参狼羌、白马羌、白狗羌等八羌,再到川西滇北一带的青衣羌、牦牛羌.及至唐宋,吐蕃势力与藏传佛教由IH称“发-羌”的地域迅速向东扩展,与中原势力和文化在这片广阔的羌人地带上全面相遇。之后数百年间,甘、青、河湟h川西北广大区域的羌人,分别融人汉、藏、蒙古等民族之中,到了明、清,只剩下岷江上游和湔江上游,一些高山深谷间有少量羌民了。这部分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区分之际,被认定为“羌族”。
这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所书写的羌族历史。但当我们从这些历史书本中回到岷江上游深谷高山之间的古老羌寨,来到农人耕种的田野细心体察,并将其与周边文化形态进行I:I~N时,便会禁不住思考:随着中原文化向西扩展,而随之向西迁徙的“羌”,果真是数千年来的同一个民族,并不断迁徙吗?眼前这些自称“尔玛”,却在八九十年前从未听说过“羌”这一称谓的人群,与活跃在历代文献典籍中的
“羌”、“羌戎”、“氏羌”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并非想要加入到“羌学”专家的行列里,对羌族历史做出考证。但是,以汉字书写,或以羌语传说的种种“羌”的历史,又是表现今天这些羌人,无法不去面对的苍茫背景。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大地震破坏最惨重的区域,正是羌族聚居地。
地震发生时,我们这个常年穿梭在这一带高山深谷之中的摄影团队,便有了熟悉路线和地形的救援优势。5月14日晚,我们将四辆越野车的后排座椅拆下,装满急救药物,从成都出发,经康定、丹巴、金川、马尔康、理县,一路穿越飞沙走石,为成为孤岛的汶川县城送去了第一批急救药品。之后的十多天时间里,这几辆越野车,又引领着六辆大货车,将山西、陕西、深圳等地朋友捐赠,和我们自筹的救援物资,沿这条线,送往理县、汶川、茂县、松潘灾区。
二十多天之后,大家渐渐停下了在废墟中抢救生命、向灾区抢运药物的步履,开始抽空与亲人、同学和朋友联系和相聚。六月初的一天,一位羌族好友从水磨打来电话,我们相约在成都见面。
他脚上的胶鞋被泥土厚厚包裹,脸上的皮肤被太阳层层剥落。言及大灾中的羌人,他神色凝重,黯然神伤:“曾几何时,我们羌人纵横在那样广阔的西部大地,在那里游牧耕种,繁衍生息。无数次战乱迁徙之后,如今仅残留在岷江上游汶)ll、茂县、理县、松潘和绵阳的北川这些高山僻壤。这样的历史变迁,这样的历史遭遇,已让我这样的羌族文人常生感伤。而这次千年不遇的大地震,重灾区又正好落在我们羌人的聚居地。”
他连饮两杯之后接着说:“目前重灾区灾民散落安置到各地,今后羌文化还如何延续?如何传承?”
离别相拥吋,我感到满脸潮润。
深夜回到家里,我对妻子颜俊辉说:“看来我们还要做点事情才行。”她说:“羌寨妇女不是都会绣花嘛,我们来设计一些现代人喜欢的刺绣产品,让灾区妇女回到家里去绣,再想办法卖出去,这样既可解决灾后的生计,让她们找回自信,又有助于羌文化的传承。”.
2008年7月21日,“羌绣帮扶计划”启动。颜俊辉带领着与她共事多年的年轻设计师们,把自己的目光从现代都市的时尚空间,向古老羌寨的田间地头转移。而我,却在大地震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在羌族诗人羊子陪伴下,和旺甲、严木初两位摄影师一道,来到了大山深处的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羌寨,来到了释比贵生的家里。
大地震发生之后的前半月,我没有拍下一张图片.此时尘嚣已悄然落定,我带着助理和器材,人背马驮,来到不通公路的夕格羌寨,延续拍摄羌人的行程。
从腊月二十七到正月初十,我们与释比贵生,贵生的大儿子永顺以及许多村民,依次祭拜了屋顶的白石神、巨石拱卫下的羊神、山坡上的神树林……正月初八,全村在崴孤山顶祭天,一盏满绘古老图案的天灯,高悬在一根三丈三尺高的杉木杆之上,在远村夕格苍茫的夜空中,闪烁着温暖而灵动的光芒。
同夕格村民相处半月回到成都,我无心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许多年前,在松潘埃溪羌寨过年时聆听“力莎”的情形;地震前夕,在北川乌龙寨景区观看释比为游客表演的场景;震后,在萝!、寨废墟中面对茫然伫立的灾民身影,以及那些新旧书本上对羌人的种种描绘,如一帧帧黑白图片,在我脑海竞相呈现。
我必须马上回到羌寨,不仅是夕格,不仅是汶川,还有岷江上游、湔江上游,所有有羌人居住的深谷高山。
2009年4月18曰,我坐在永顺家的火塘边,用手机向远在都市的朋友发出这样一则短信:
山寨通讯社消息:岷江上游高山之上的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直台两个羌寨的七百多位村民,在“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到来之前,将尽数迁往成都以西约一百公里的邛崃南宝山原劳改农场。男女老幼一同前往,牛马牲畜不得内迁。今日,两寨青年人已开始变卖家畜、耕牛、粮食,老人们则纷纷陷入即将永远离别旧居、祖坟、家神的伤痛,三位老年释比注视着世代相传的释比法器,沉默不语。
从垮坡到夕格,在陡峭的山路上爬行两个多小时,到永顺家的火塘边坐下,我便觉双腿隐隐作痛。永顺的父亲贵生,将长长的烟杆伸向“噼啪”燃烧的火塘,点燃他自种的兰花烟。兰花烟浓烈的气味,与松枝燃烧的清香,以及烟火薰烤下的腊肉气息,在火塘四周弥散开来。
看见暖色的火苗在贵生不断鼓腮抽烟的脸上跳动闪烁,不禁想起两个多月前的除夕之夜,也是在这个火塘边,也是这样静静地注视着闪烁的火苗,轻舔在贵生沧桑的脸上,听他娓娓讲述关于夕格,关于夕格羌人的故事一
“听说我们的祖先,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西北草原。后来由于战争,迁到了岷江上游的深山峡谷。我们夕格这支人来到龙溪沟,就在崴孤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在这里居住了几辈人。战争渐渐少了,雀鸟乌鸦又多了起来,比人还多。我们每年辛苦劳作的庄稼地,都被那些雀鸟乌鸦糟践得不成样子。吃不饱肚子,我们就迁到了东路的石泉、油溪、白岩,就是现在的北川,土门这些地方。但这些地方的猴子又很凶,比崴孤的乌鸦还多还凶。后来有人回夕格打猎,子弹袋里的青稞籽掉在了野猪拱过的地里,下半年再来时,发现青稞长出了一拃长的吊吊(穗)。夕格的土地变得肥沃,乌鸦也少了,我们就又迁回夕格,大家分散居住在崴孤、大寨子、牛场这几个地方。在这里生活了两代人后,靠近树林的崴孤、牛场这两个地方的野猪、老熊又凶起来,每年的庄稼不等你去收,那些野猪、老熊早帮你收得差不多了。所以你看崴孤和牛场现在是个空寨子,都迁到现在的乱石窖、麻地头、新寨子了。我们家是几年前才从牛场迁到现在这个乱石窖的。
“总共迁了四次:第一次是战争,第二次是雀鸟乌鸦,第三次是猴子,第四次是野猪老熊。
“经历这么大一场地震,才过半年,我们就又可以在家安安心心过年了。这要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那么多的好心人,我们也不忘我们的神。昨天,我们到崴孤神树林去敬了神,你看这次这么大的地震我们夕格只死了一个人,就是我的大女婿,他是在山下的路上……今天,我们又在楼顶纳萨敬了天神,到房前房后去敬了水神、羊神,在家里敬了家神,家里十二尊神都敬了。正月初八全寨子人一起敬天神点天灯。天灯点在一根三丈三尺高的杉木杆上。
“春天你们再来吧!那时整个山沟都是歌声,春耕时犁地的,牵牛的人一起给耕牛唱歌。你看这里的地都就巴掌那么大,又陡.要给它唱歌它才会好好给你耕啊,用心唱,耕牛会听得泪流满面的。春分这天大家在家休息,都不上山,不进树林。这天是所有雀鸟、野兽恋爱交配的日子,不能去打扰的。”
两个月之后,春天依旧来临,整个龙溪山谷的山花依然如期绽放,但高山之上的夕格、直台两个寨子,耕者唱给耕牛的歌声,却在2009年4月18曰这一天戛然而止。弥漫在鲜花与歌声中的春播景象,现在只能在想象中一次次绽放。
夕格不通公路,但几年前已有了电视。通过被村民们称为“锅盖”的卫星信号接收器,夕格村民在电视屏幕上目睹并感受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纷争、灾难、便捷与享乐。对于大多数夕格人来说,满世界都是汽车、火车、高速公路,而夕格至今连机耕道都没有一条,日常所需的一切,卖出买进都得靠人背马驮。但现在要永远离开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山寨,所有夕格人,特别是老年人,都面色凝重,沉默不语。
2009年5月6日,离“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还有六天,汶川县龙溪乡夕格羌寨的杨永顺全家,就要和世代居住的羌寨,和这座长年相守的房屋告离了。现在,全家人将去山下的东门口,与夕格、直台两寨的七百多名男女老幼会合,再一同乘车前往他们新的居住地:邛崃南宝山。
前排右二就是永顺,身边是他的弟弟杨永学。永学腿有残疾,先前在家放羊,地震后经人介绍,去了郫县一家工厂打工,现在请假回来帮助家里收拾东西。后排是永顺六十一岁的父亲杨贵生,和比父亲大十六岁的大伯杨德才,两位老人背上的麻袋里装的,是杨家世代相传的各种释比法器。前排左边是永顺的母亲余秋珍,和永顺的妻子王彩文。永顺母亲脚下和手中口袋里装的,是他家那只每日准时打鸣的公鸡,和终日蜷伏在火塘边的那只小猫。永顺七岁的儿子杨有理,已经跑下山看汽车去了。他右手牵着的,是五岁的女儿杨群星。在小姑娘稚嫩的脸上,我们还读不出关于迁徙、离别的滋味。
大地震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夕格羌人对自从有人把麻将、电视机背上山以后便被疏远了的一些传统风俗,渐渐亲近起来。这么大一场地震,夕格只死了一个人,老人们说,这得益于夕格人并没有对天地神灵过分地冒犯。
自打有人把电视机、“锅盖”背上山以后,高山之上的夕格羌寨,便再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闭塞了:武打片、宫廷片、选秀节目、征婚节目、猪饲料广告、丰乳霜广告……开始在古老羌寨每一座昏暗的石屋里,轮番播放。
虽然,电视机一上山,村民们就对其赞叹不已,但电视在山民生活中的地位,始终还是达不到城里人那么重要的地位。高山村民没条件像城里人那样终日蜷缩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把自己的七情六欲融人方寸之间的影像世界里。他们耕种地里的庄稼,需要跟随春夏秋冬、月圆月缺的脚步;他们放牧家里的牛羊,需要倾听绿草清溪、飞鸟走兽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一家老小坐在一起刚打开电视,那些男女的亲热动作,儿子儿媳也坐在身边,总让人感到别扭,觉得不如围着火塘,七嘴八舌说一些山上的野兽啊、家里的牛羊啊、地里的庄稼啊,那么自由自在。
大地震刚发生的那段时间,电视画面一下子由吃喝玩乐的享乐天地,变成了灾难伤痛的悲惨世界。龙溪乡的村民被安排到汶川县城附近的河谷避难,一个月后回到山寨,大家再也不愿浸泡在让人伤心的电视画面之中了。村民们纷纷关掉电视,给电视机罩上布套。没有合适的布套,就找一条毯子、一张羊皮或一件衣服。
村民们又喜欢抽烟沉思,或串门聊天了。大家闲来往地边一块草坪,或家里火塘边一坐,每个人都能发表一套自己关于生死祸福、善恶因果的高论。每个人论点的背后,都有地震中发生的种种事例来作为支撑。永顺父亲贵生,是有名的“释比”。释比是能通过自己的身体、舞蹈、唱辞,来完成对神的邀请、鬼的驱使的。经常和鬼神交流,贵生的论点自然分量不轻。我把他在腊月底那次火塘论坛上,用羌语和汉语杂糅着发表的论点,整理如下:“你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哪一样不依靠这块上地?哪一样不是土地给的?这地和人是一样的哦!草木就是他的毛,上地就是他的肉,那些金矿煤矿就是他的骨他的髓,我们开山打洞修电站的那些河里水,美国人到处去争去抢的石油,就是他的血!现在你看山底下,你看电视里,到处都在拔他的毛,割他的肉,挖他的髓,吸他的血啊。他实在受不了了,当然要蹬个腿,翻个身哦。他一蹬腿,一翻身,你就惨了,花那么多钱修建的楼房,用来吃饭、睡觉、办公、享受的楼房,就成了埋人的坟堆……”
羌寨的地边论坛、火塘论坛与外面的论坛可不同,比如“今年过年昨个过”这个议题,大家在腊月间的一次地边论坛上,十分钟,达成共识:按传统风俗过;二十分钟,形成决议:敬神、舞狮、点天灯,三十分钟,落实到位;每家出资五十元,公积金支出五百元,手巧的负责扎狮灯,力大的负责砍天灯杉杆。
大家立即行动,找出了尘封几年的狮头竹架,开始抹灰固节,糊纸画彩。一天王夫,一只彩狮就在高山夕格转世再生,并在“咚咚呛呛”的锣鼓声中,在遍地涌动的春雾里,跳跃欢腾。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甸甸的质感,拿在手里就觉得分量十足。封面选用的纸张纹理非常细腻,触感上乘,不同于现在很多追求轻薄的出版物,它带着一种老派的匠人精神。内页的排版也极其考究,字体的选择和行距的控制,都透露出编辑团队的用心良苦,读起来非常舒适,长时间盯着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尤其是那些大段的文字,在没有过多花哨装饰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沉静和有力,让人更能专注于文字本身所传达的思想深度。我常常在傍晚时分,泡一杯热茶,翻开它,享受那种被书籍的实体感包裹的阅读体验。这种对物理形态的尊重,在这个电子书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和难得,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可以被细细品味和收藏的艺术品。每一次翻阅,都能在指尖感受到纸张与油墨交织出的美感,这种仪式感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愉悦度。
评分这本书的后期处理,尤其是注释和索引部分,简直是业界典范。对于如此信息密度巨大的作品,详尽的参考资料是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我特别欣赏它在引用和延伸阅读上的严谨态度。每一个关键论点,几乎都能追溯到其源头,这对于做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来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可靠性。而且,那些看似是“补充材料”的部分,其质量丝毫不亚于正文,很多都是独立的精彩片段,单独成章也毫无逊色。这说明作者和出版方在“信息附录”这个环节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们明白,对于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严谨的佐证和延伸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对细节的近乎偏执的追求,是这本书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关键所在。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成功地在严肃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很多探究深层次议题的作品,往往会陷入故作高深的泥潭,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然而,这本书的叙事脉络却异常清晰,即便涉及复杂的概念或跨越时间线的跳跃,作者总能用一种近乎对话的方式将读者拉入情境之中。它没有预设读者必须拥有某种专业背景,而是耐心地引导我们一同构建理解的阶梯。这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能够将宏大的命题拆解成一个个可以被消化的单元。这使得我能够带着好奇心一路前行,没有产生任何“想跳页略过”的冲动,全程都保持着一种被引导的、探索的乐趣,非常适合希望在轻松氛围中获取知识深度的读者。
评分坦白说,初次翻阅时,我有点被它那种近乎冷峻的叙事风格给震慑住了。作者的笔触极其克制,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辞藻去渲染情绪,一切都以一种近乎客观记录的姿态铺陈开来。这种冷静反而产生了一种更强大的冲击力,仿佛是冰冷的解剖刀,精准地剖开了某个社会现象或历史侧面,毫不留情地暴露其内在的肌理。它要求读者必须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解读那些看似平淡的描述背后蕴含的巨大信息量。我必须承认,阅读过程需要一定的“体力”和心智上的投入,它不是那种可以让人放松地消磨时间的读物,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马拉松。但正是这种挑战性,让最终的领悟变得格外透彻和深刻,一旦你跟上了作者的节奏,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简直无与伦比,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
评分从主题的广度来看,这本书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博学和跨界整合能力。我注意到其中穿插了许多不同领域之间的参照和联系,从古典哲学到当代科技,从地域风俗到个体心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却被作者巧妙地编织进同一个宏大的思维网络中。这种网状的知识结构,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它不像传统书籍那样按部就班地沿着一条直线铺陈,而是像一张细密的蜘蛛网,每一个接触点都能引发出新的思考方向。这种结构迫使我必须不断地进行联想和类比,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表面信息之下的结构性相似性。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塑,不再满足于线性的、单一视角的观察。
评分书很好,质量高,可读性强,这次趁着活动买了一大箱书。或许从此就开始收藏书籍了。哈哈。
评分一共13本:读库1301
评分当钻石巨人戴比尔斯集团把注意力放到日本时,眼中所见的还只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1966年,di一则广告展开攻击时,收到钻戒的日本新娘人数还不到1%。到了1981年,这个数目飙升到60%。再经过十年持续的广告宣传促销,钻戒在将近90%日本新娘的婚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前完全没有人注意的东西,忽然成了必需品。
评分封面有点脏,还有点破损,送货快。。。
评分凑单买的,挺好的。不错的一套书
评分包罗万象,值得收藏!可惜书背污迹斑斑。。。
评分自从知道读库开始,一直想买几套回来看,终于等到活动,感觉很划算,就相信京东自营,五星好评!!!
评分活动买的很划算,感谢京东!
评分挺好的,促销活动时候买的。很久之前就想看的一套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