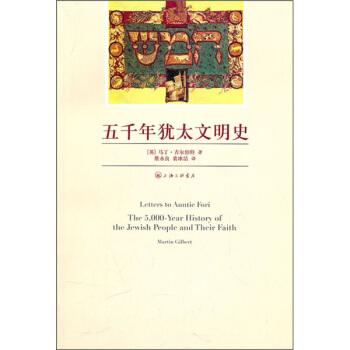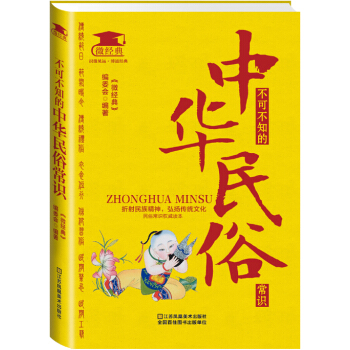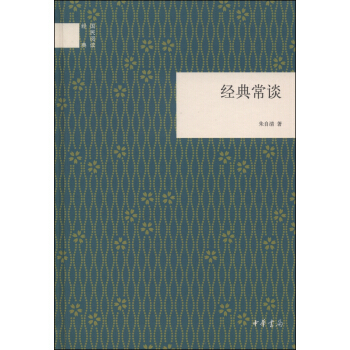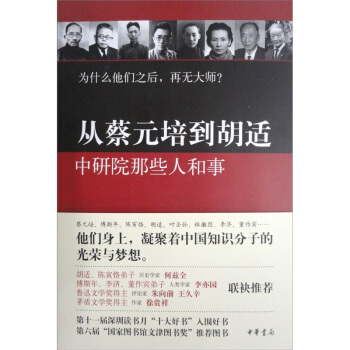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本商品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一代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家国命运。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考古学家王世民、人类学家李亦园!
著名作家徐贵祥、评论家王久辛、诗人何三坡联袂推荐!
本书是全国一本关于民国年间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学者群体传记。
作者岳南为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文笔细腻,挖掘了不少著名学人的当年隐事,令人回味无穷,可读性极强。
内容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以中研院从组建到迁往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进取精神。《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再度以鲜活的形象,凸现于世人眼前,令人在对前辈们敬仰感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作者简介
岳南,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理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着力对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思想脉络、道德精神与学术成就进行调查研究,有《李庄往事》、《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作品问世,同时著有《风雪定陵》(合撰,获1996年《中国时报》开卷版好书奖)、《复活的军团》、《天赐王国》等“考古文学系列作品”十部。已有数部作品被译为日、韩、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现居北京。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部著作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大的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读之令人回味无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家 何兹全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其继承者,连同各所所长与专家,对青年学者的培育特别重视。后来留在大陆对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优异贡献的夏鼐,就是这一时期青年学者的杰出代表。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描述皆
目录
蔡元培生前身后事跨过时代的门槛
病逝港岛
群英会陪都
行都灯火春寒夕
最后的博弈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世间已无梁启超
梁思永东北之行
殷墟发掘的光芒
醉别清溪阁
苦难的李庄岁月
傅斯年与梁家兄弟
林徽因的感恩信
梁思永之死
花落春仍在
陶孟和的尴尬人生
北大校园与毛泽东结缘
自立山头的甘苦
山行复悠悠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进军西北”之梦
决裂
一代名嫒沈性仁
多情最数金岳霖
张家祠言和
满目山河空念远
落花风雨更伤春
考古星河中的两只“大鼎”
吴金鼎的清华时代
城子崖遗址横空出世
夏鼐与吴金鼎的交往
发掘彭山汉墓
打开前蜀皇帝陵墓
吴金鼎参军内幕
盟军招待所的悲苦日子
夏鼐的西北之行
夏鼐为郭沫若斗胆进言
吴金鼎之死
书剑飘零一介眉
闽东才女游寿
走进山门
反出“忠义堂”
遥知北国有姮娥
叶企孙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雾都遥念陈寅恪
重返清华
离奇的C.C.特务案
日夕凉风至
旧业已随征战尽
“抢救”学人计划
傅斯年夜赴台湾
在台大校长任上
“归骨于田横之岛”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身死演讲台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李济的旧梦新愁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精彩书摘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作为中国学界领袖的蔡元培,身体状况已现衰老的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在此情形下,他仍以身垂范,为国家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蔡的学生、曾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与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蔡元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未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拉开了高潮大幕。硝烟炮火中,蔡元培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三个研究所向内地撤退。
11月1日,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上败象已现,各路大军奉命撤退或正在转移途中,蒋介石紧急召集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情报和意见,九国公约联盟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的命运关系甚大,只要中国军队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有可能出面联手制裁日本,断其战略资源的通道。为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历史性契机,蒋介石决定收回撤退成命,各部重返前线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为配合政府这一战略决策,11月2日,蔡元培带头与上海交通、同济、暨南等大学校长黎照寰、翁之龙、何炳松,以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等著名教育界、科学界人士,联名致电比利时九国公约会议,强烈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对华侵略,严惩日本违反国际公法、肆意摧毁中华民族文教机关之暴行。但历史让人们看到的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蔡元培,都只是一厢情愿,结果是公理未能战胜强权,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回上海再战的中国军队,于混乱中遭到日军精锐重创,两个星期的时日未到,中国军队开始大规模溃败。12日,上海沦陷。
就在上海沦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总干事朱家骅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准备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汇合。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香港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在港岛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翌年2月,蔡元培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平时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并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关注着中研院的命运,同时为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计谋筹划。据蒋梦麟回忆说:“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正是具有这样一个人格,隐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划组织,于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显现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部颇为欣慰,精神为之大振。此次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对未来作了前瞻性筹划,与会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当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利用电炉制钢的现代化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撤出人员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昆明。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辅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100亩地大小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最新兴起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种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著名建筑,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向同胞和国际友人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衰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港岛。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人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流亡昆明的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作为一位留法归国的杰出美术家,自和法国归来的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杭州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于抗战流亡途中撒手人寰。蔡威廉一家在昆明生活得极其艰难,而她本人则死得更加悲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寻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殒落,举国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各界人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以“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来烘托蔡元培高山仰止的人格光辉与民族气节。国民党在重庆举行公祭,由党总裁蒋介石亲自主持,接着举行追悼大会,以表达对死者的追念与哀思。远在延安窑洞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闻讯,也向这位对自己当年进北京大学谋到图书管理员差事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长发表了“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唁电,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一代名流许崇智、廖承志分别受国共两党委托,亲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之执绋者5000多人。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港岛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后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长眠于香江之岸。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经国之大业,自由之思想,科学、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作为一座屹立在岚烟雾海中不灭的灯塔,指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读书治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将真理发扬光大。
……
前言/序言
前言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
因我与中央研究院有过一段缘分,岳南在写作本书时,对我进行过几次访问,对一些旧事作过探讨。现在他把这本书的校样送来,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看过稿子,顺便写下一点文字,谈一点感受,算是对读者作一个简单推介,也借此机会,对曾经教导、关怀、帮助过我的师友们献上一份缅怀纪念吧。
大家知道,中央研究院是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级学术研究机关,原北大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任院长。因国力有限,经费困难,开始的时候,中研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几个研究所。以后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9年间,又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包括物理、化学、工程研究、历史语言在内的共十个研究所。据说按当初蔡元培先生的计划,中研院要建立十四个研究所,但随着抗战爆发,各研究所被迫向西南大后方迁移,虽有筹备扩张的打算,但实际上的建制也就到此为止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除一个较完整的史语所和数学所部分图书、人员随蒋介石政权迁台外,其他的都留在了大陆,并陆续归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我与他见过几次面,因辈分差异太大,说不上深交,但我心中却非常景仰这位“北大之父”、中央研究院元勋硕老。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蔡先生由上海乘船到香港,未能回到重庆就得病去世了,伤哉!
岳南书中提到的另外几位师友,我不但与其熟悉,还从他们身上受到了不少教益,得到了他们许多帮助,至今感念不已。
1931年暑假之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1935年毕业,这时期正是胡适先生在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我听过他的课,如他讲的淮南王书、禅宗和尚、神秀、慧能等等,但学到的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没有学到他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受他影响最深的倒是《红楼梦》考证。我喜爱《红楼梦》,赞成他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材料,考订《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自传。我没有研究红学,但我一直坚持此说。这是胡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
在校期间,有两回事胡先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年北大所在的沙滩周围,住着很多不是北大学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中,一部分是考学落第准备明年再考的学生;一部分是北伐革命战场上退下来的青年。这些青年和北大学生一样挎起书包走进北大课堂,找个座位就坐下听课。教师不问,学校也不问。一天,胡先生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胡先生的高明和胸怀使在课堂上的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那些偷听生,都是真念书的。当时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可见偷听生确实是用功用心想学习的青年。胡先生的话改变了偷听者的身份,偷听成了正大光明的听。胡先生是用亲身示范,教育了所有在座的青年,要做胸怀开阔的人,做纯厚、高尚的人。
另一回事是,胡先生每星期拿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在家接见青年学生,解答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可以谈,他尽力解答。那时他住在地安门里米粮库(解放后,这座房子五十年代是画家陈半丁先生住,后来是邓小平同志住)。我到胡先生家去过一次,问什么问题已回忆不起来了,大约主要是好奇,要去看看。只见“高朋满座”,都是青年学生,有问有答,有讨论,有辩论,气氛热烈,高兴和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书育人的办法,后来我在大学教书,很想学胡先生每星期找出一个固定时间接见学生,借以亲近学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但始终没有做到,现在想来仍感惭愧,也由此更加佩服胡先生的精神和毅力,了不起。
北大毕业后我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在重庆编了几年杂志,那时已是抗战时期了。1944年我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邀请,进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主持的史学组工作。当时史语所为躲避日机轰炸,已由抗战早期的南京、长沙、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县与叙府(宜宾)之间的李庄镇一个叫板栗坳的山中。这个地方确实是偏僻隐蔽,从李庄镇到板栗坳需要沿长江岸边走好几里地,再爬一个大约五百级石阶的山坡才能到达,其环境就跟《水浒》描述的我的家乡、山东西南部的水泊梁山差不多。傅斯年先生是这个山寨的“头领”,只是他多数时间在重庆,实际上在这个山头“聚义厅”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是董作宾先生,他是代理所长。
尽管我们居住的板栗坳上下山辛苦,但避免了日机轰炸的麻烦和无谓的牺牲。关于李庄的风土人情与迁到这里后的中研院史语所,以及由陶孟和主持的社会学所、李济主持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外加同济大学等等情况,岳南在这部著作中已有较为详尽的披露,并且比较到位,这里就不多说了。
要说的一点是,我在史语所工作期间,由于当时一些报告、电文我没有机会看到,而事隔六十多年由岳南从多种资料、特别是从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查考得来,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许多事,我看了岳南的这部书稿后才知道。特别是当年心中已有所感觉,但事实仍模模糊糊的同事们生活间的内幕,甚至矛盾纠葛,通过“傅斯年档案”中留存的一批书信的披露,外加岳南的考证,理出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才恍然大悟。比如傅斯年在李庄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到教育部、中研院总办事处要钱以救济病中的梁思永、林徽因的事;傅斯年与陶孟和发生矛盾,后来又握手言和的事;傅斯年为何对吴金鼎与夏鼐产生不同的看法,吴金鼎负气出走当兵的事;号称“闽东才女”的游寿与傅斯年、董作宾之间暗中较劲等等,在当时我的脑子里是模糊的。比如女才子游寿,我只知道她不是傅斯年亲自选拔的人,好像是南京一个什么官推荐的。但傅斯年先生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凡不是他亲自选拔的人,在史语所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后来游寿果然在史语所不长时间就走了,她走的真正原因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岳南在书中有理有据地把尘封的材料摆出来,我才认识到,呵,原来是这么回事。惜哉,游寿!
如果说岳南这部著作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认为除了具有文学家文笔的优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史料的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发掘探幽,将鳞爪缀成珠串,使湮没于历史泥沙中的真相层层剥出,使今天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独特性格和风范的鲜活的生命,读之令人亲切感动,回味无穷。
当然,因篇幅与选材上的关系,有些我以为很好的材料,岳南并没有纳入书中。比如,当时史语所有个好制度,就是不定期的作学术报告。我印象中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还有劳干、董同龢、逯钦立等先生都作过。傅先生讲的“性命古训”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逯钦立那时还年轻,与我年纪仿佛,是山东菏泽地区同乡,他所作的陶渊明诗演讲,很为大家喜欢。董作宾先生说话有河南口头语“老天爷”,说不三句话就出来一个“老天爷”,或“我的老天爷!”时间久了,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们背后就送给他一个“老天爷”的雅号。只要一说“老天爷”如何,大家都知道是指董先生,后来竟连年轻的家属们也跟着叫起“老天爷”来了。因了这个雅号,现在想起来,董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并觉得特别亲切。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史语所开创的这个学术交流活动,对每个人的研究都是个督促。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当主任的时候,就定期让同仁作学术研究报告,一直维持了好几年,大家反映都说这办法很好。
岳南书中提到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都是我的师辈人物,梁思永先生于李庄后期身体不好,在病床上的时候较多,但还是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特别是他一手发掘的安阳殷墟那批东西,可谓倾尽了心血。因为在李庄板栗坳山上没有娱乐活动,星期日,我们年青人有时就到社会学所去,顺便认识了陶孟和先生与梁方仲、罗尔纲等研究人员。陶先生话较少,是个老实人,也是个真正的学人,可惜解放后不太得志,也受了一些凌辱,最后抑郁而终。这一切,从岳南书中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不赘。
除了社会学所,我们也到山下的中国营造学社听梁思成先生夫人林徽因师母的“训话”。当时林师母已病在床上了,看到我们去她特别高兴,“训”起话来也格外起劲。我说的“训话”完全是真诚善意的。梁、林都是我的长辈,待人热情,林夫人长得漂亮,又极健谈,和她在一起,话总是她说的多,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围在她身旁,听着她的话,如沐春风中。
至于岳南书中所述及的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等年轻一辈学者,都是我的学长,说起话来就更随便一些,要讲关系的话可谓亲如兄弟姐妹。我认为,这几个人皆属于胡适、陶孟和、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第一代学者之后又一批天才式人物,也都是了不起的学问大家,是很值得纪念的。岳南在书中对他们的理想、事业与人生追求有不同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那段历史史实,让后人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已渐被历史风尘埋没的人与事,同时也见识了他们在事业上不懈追求努力的人格风范。所谓薪火相传,血脉不绝,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不灭等等,不是靠泛泛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作为后世知识分子,特别是年青一代,了解一下前辈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术历程和业绩,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而岳南在书中所给予大家的正是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本书赋予当今社会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抗战胜利后,流亡于西南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陆续复原回到南京。大约是1946年秋冬,胡适先生从北平到南京来,傅斯年先生叫我到机场接他。第二天晚上,史语所召开了一个欢迎胡先生的茶话会,家属小孩都参加了,小孩子钻来钻去,乱哄哄,场面很热闹。胡先生很高兴,会上谈了些学术教育问题,又说了一些如何“怕老婆”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傅斯年先生讲话时说,适之先生是娘家人,大家不必见外等等。又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傅先生这个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但从抗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做过汉奸的伪北大教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之”(傅斯年语)等等棘手的事务上来看,也真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的“斗士”。
1948年之后,由于国共内战的原因,中央研究院的这一批学者各奔东西,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归骨于田横之岛”。政治的阻隔使得原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的师友,只能遥天对望而不能相聚一堂,甚至父子家人都永远不能相见了。胡适、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前辈最终客死他乡,这真是人间少有的历史性悲剧。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了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和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在史语所黄宽重所长的陪同下,先后拜谒了傅斯年、胡适之、董作宾、李济之、董同龢等先生的墓,并一一鞠躬致哀。先生们远离故乡,飘零海外,魂魄而有知,一定会感到寂寞凄楚的吧。愿台湾、大陆早日统一,使先生们的学术精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续学术香火于天下。
何兹全
2009.11.22
时年九十九岁
用户评价
这本厚重的文集,仿佛一扇通往民国精英世界的时光之门。我尤其被其中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细致勾勒所吸引。作者似乎对人物命运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将这些历史人物标签化,而是将他们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与个人生活细节的交织之中。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种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探索、最终做出选择的沉重与不易。比如,对于某个学者的学术道路选择与政治态度的微妙变化,描述得极其细腻,没有那种事后诸葛亮的轻松,而是充满了对“当时情境”的体贴入微。这种对历史的“在场感”,让枯燥的史料变得鲜活起来,让人不禁思考,在相似的岔路口,自己会如何抉择。那种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入挖掘,远超一般的传记写作,更像是一部关于“何以为士”的探讨史。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度,而非仅仅是历史的片段。
评分从整体结构上看,这本书的编排布局非常精妙,它并非简单的线性时间轴梳理,而是通过若干个交叉的主题线索,将不同领域、不同资历的学者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知识网络图谱。这种网状的叙事策略,避免了人物传记容易产生的孤立感,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思想是如何通过师承、论辩、合作与竞争,在这个知识共同体内传播和演变的。每一次话题的转换,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核心始终是那个时代的学术精神的流动与汇聚。这种结构上的匠心独运,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层次感,使得读者在合上书本时,脑海中留下的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学术生态系统”的印象。
评分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史料搜集工作简直是令人惊叹的。它不是那种依靠二手资料拼凑起来的肤浅论述,而是建立在对大量档案、私人信件乃至边缘性文献的精细梳理之上的。这种扎实的根基,使得作者在叙述那些关键历史事件时,拥有了令人信服的权威性。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在处理不同派系学人之间的观点冲突时所采用的平衡术。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清晰地梳理了思想交锋的脉络和逻辑起点。这种近乎“学术考古”的严谨态度,对于我们这些希望深入了解特定历史阶段学术生态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它提供了一个极为可靠的基准线,让我们得以避免被过度简化的历史叙事所误导。读完之后,我对那个时代知识生产和学术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认知。
评分最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对特定历史语境下“学术自由”与“外部干预”之间博弈的呈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讨论,而是通过具体人物在具体情境下的决策点来展现的。例如,当某种政治力量试图影响大学的课程设置或研究方向时,那些学者们是如何运用他们的知识、声望乃至个人关系网进行周旋、抵抗或妥协的。这种“技术性”的抗争描写,远比直接的口号式反抗来得震撼人心。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真正的独立,往往体现在无数个微小、隐蔽的日常选择之中。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维护学术的纯粹性,需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以及这种代价是如何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雕刻着一个时代的知识面貌。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古典韵味,但又不是那种故作高深的陈词滥调。作者的文字如同精心打磨的玉器,温润而有光泽,尤其擅长在叙事中嵌入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但这些议论从不喧宾夺主,而是如同水流一样自然地融入到人物的故事线之中。我非常享受那种在阅读情节高潮时,被作者一句精妙的总结所点醒的感觉。这使得阅读体验从被动接受信息,转变为一种主动的思考对话。它不像某些严肃历史著作那样让人望而生畏,反而有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即便是对相关历史背景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被其叙事的节奏感所吸引。这种平衡了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的写作技巧,是许多同类著作难以企及的。
评分包装不错,书是正版无疑,还没读。。。。
评分不带学究气的高手 文章漂亮 叙事清晰
评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对清末明初的那些人比较感兴趣,真正大师辈出的年代,或许是乱世造英雄吧,个个都是国士风范,宗师造诣,读他们,能洗去自己很多张狂。
评分了解历史,正视历史,思考历史.
评分看了南渡北归,让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提起了兴趣。喜欢岳先生的书。
评分朋友推荐的~~还没有开始看
评分从蔡元培到胡适,对于希望了解那段历史的有些帮助!
评分观民国大师爱恨情仇,叹今世小丑贪腐弄权
评分民国之后无大师,看看大师的风采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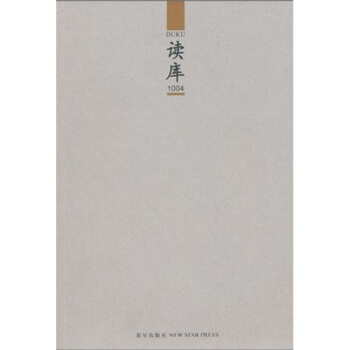


![希腊精神 [The Greek Wa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20043/rBEhWVMpULIIAAAAAACJ6SklGsUAAKWHwE9ZJQAAIoB70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