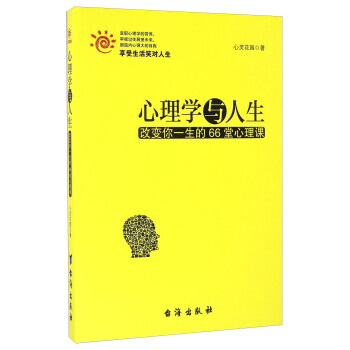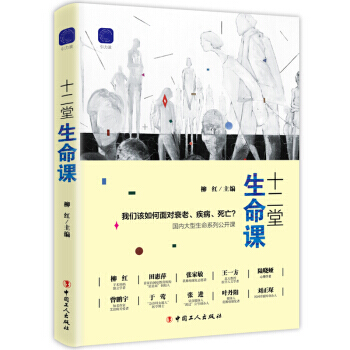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十二堂生命课
定价:49.80元
作者:柳红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11-01
ISBN:9787500867883
字数:
页码:308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l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疾病、死亡;
l系列生命公开课;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
l本书邀请了有过特别生命体验或专门进行研究实践的学者亲身讲授他们的经历;
l子尤妈妈、独立学者柳红,自闭症教育机构“星星雨”创始人田惠萍,癌康复志愿者张家敏,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心理学者陆晓娅,关爱者曾鹏宇,“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渡过”公号创办人张进,癌康复者叶丹阳,民间骨髓库创办人刘正琛;
l流动的生命之河,开放的精神空间
内容提要
如今,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老和病”主体被边缘化,很多人从心理上视其为“失败”“无望”的人生。所以“十二堂生命课”邀请了十位具有特别生命体验的讲者,把老、病、死的话题作为公共话题谈出来,希望人们开放地、有准备地面对,重新规划自己的有生之年,让老后和病后的生活成为人生美好的时光。
目录
讲 残缺之美:当我与癌遭遇 / 001
第二讲 那些逝去的生命教给我们的事 / 001
第三讲 宿命之问:我们为什么害怕死亡 / 025
第四讲 失丧十年:我的路 / 077
第五讲 生如夏花:78岁抗癌勇士的生命感悟/ 099
第六讲 永远的陪伴:我和我的自闭症儿子弢弢 / 113
......
作者介绍
柳红,子尤妈妈,独立学者。2004年进入疾病与死亡的世界,在癌症患儿的精神关怀和失丧关怀上做过一些努力。十年来,除了对于病、老、死、医患关系等有思考,也在身体和健康的认知与实践上着力,成为马拉松跑者和百公里毅行者。
文摘
第五讲失丧十年:我的路
当我想讲这个题目时,却发现不知怎么准备,那些化在生命里的心路历程,岂是语言可以表达?首先特别要说感谢的话。是很多人的帮助使我走到今天;除了感谢还有缅怀。这十年,有很多故人离去。我们生病后,就经历了周围病友相继死去,意识到死亡原来离我们这么近。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离去,我都痛惜得不得了,尤其会想到他们的家人。
关于“失丧”和“哀伤”
次知道“哀伤研究”是在三年前,北师大心理系研究生何丽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哀伤研究。她访问了一批丧失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也找到了我。
实际上,所有人都要经历“失丧”。人类世世代代就是在这样的生生死死中发展、演变的。但总有一些死亡,如果我们给它一个哀伤指数的话,它的哀伤程度要高一些。死亡,有正常和异常之分。经历异常死亡的哀伤要深于经历正常死亡。比如,失去孩子----本应承续父母血脉的,却亡故在先,这就属于异常死亡。即便如此,在多子女时代,失去孩子也是常有的事。对于那些父母来说,他们还要哺育这个,拉扯那个,得以将哀伤转化成对其他孩子的养育责任上。然而,失去“的孩子”;更为甚者,失去“不得不”是孩子的情形,是中国1980年后推行三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现象,确实是人类不曾有过的情形。而我,就不幸落在了其中。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丧子爸爸妈妈,我知道有一些父母难以承受如此丧子之痛而病、而亡,身心饱受折磨。对于我,在那个时刻,怎么样才能够活下来,是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什么是对孩子好的爱?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是我的大学同学夫妇。前不久,他们的孩子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孩子在世时,成绩等各方面极为优异,令父母引以为骄傲。她非常急切地大声问: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活下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说是“爱!”
她问:“为什么”她的意思是说,儿子是我们的希望,当希望没有了,那么我们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我要随着这个破灭的希望而去了。
但我却觉得它可能就是一转念的事:我们爱孩子,什么是对他的爱?怎么体现这个爱?孩子希望爸爸妈妈在他不在之后,还能健康,还能过一个好的生活,还能有他们生命价值的体现。而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亡故,爸爸妈妈也倒下去。所以我说,对孩子大的爱是,我们过得好。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次我们的通话。我当时还说,我想跟她先生谈谈,因为她先生相对封闭一点。她告诉我,用的是免提,先生正在一旁听着。而她的问题是很多丧失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首先追问的。
建立什么样的观念固然重要,但是,毕竟日子是要一天一天过的,而且是在每分每秒地承受着心灵煎熬之下过,这绝非易事。
子尤是2006年10月22日去世的,马上就进入冬天了。往年我们都买冬储大白菜。到了时候,大卡车又拉着白菜来我们小区卖。那天,我就站在车边上看着那堆白菜,和热热闹闹地抱菜上称的欢喜人家。而我独自一人,确实没什么吃的能力和必要。但是,这个时候买不买冬储大白菜的含义,好像超过了餐桌的需要,而是个心气儿。事关日子过不过,怎么过?终,我还是下决心买了,搬到楼上去,用报纸包好,码在阳台上。
社会网络支持与偏见
凡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难过是曲终人散时。朋友们可以救急,在危难之时伸手帮助,但是,曲终人散时,只能自己面对。虽然街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孤岛上,是心灵的孤岛,无处话凄凉。那时的信息手段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还是时代。多亏有很多远方的不相识的网友依旧访问子尤,在上面留言。每天看留言,对我的心理是一个安慰。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作用。我们处在一个较为中心的节点上,得到了更多的精神支持。
人们在面对丧子之痛时,有不一样的应对。这与她/他本人的性格,受教育程度,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等都有关系,并没有一个药方可以医治,只能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式。而一个良善的社会和文化,有助于失丧者的康复;反之,则会加剧人的痛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感到至少有这样几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一是,要求失丧者快速封上哀伤的口子。
有一位妈妈孩子去世后,请了一段时间假,出去“散心”。回来上班后依然难忍悲伤。这是多么自然的情形,本应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关爱。可是她的领导却埋怨她:“你怎么还走不出来啊?”,给她增添了很大压力。这位妈妈通过找到我。我邀她到家里来。她一进门,就说:“哟,这儿真好。”因为在我家几面墙上都挂着儿子大幅彩色照片,孩子的骨灰就摆在条案上。而她是什么情况呢?他的先生某次趁她外出,把所有孩子的东西用车运走。这是不想让她睹物思人,减少一些刺激。这位妈妈只有一张很小的孩子照片放在钱包里。她拿出来给我看,讲述女儿病中的故事。她先生潜在的意图是想封上这个痛苦的口子,堵住哀伤。结果,适得其反。而此时此刻,这位妈妈也不愿跟先生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毕竟孩子的爸爸心情也很难过。那天,她和我敞开谈,谈到伤痛处,我们一起哭;谈到美好处,一起笑。记得那天她离开我家时的后一句话是说她能行。这位妈妈后来练书法。我知道,她父亲是一个擅长书法的老先生。多年未见了,想必她现在已经写得很好了。
2006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出来?”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当即的反应大概是,没有计划,也不可能计划什么时间走出来。这种痛苦会伴随我一生;我会一直流着眼泪往前走。两者并不矛盾。
二是,阴森恐怖的“哀伤”文化。
朋友们帮助我为孩子办了一个彩色的葬礼,每一位来宾手里拿一朵红玫瑰。我穿着新旗袍,换了新发型。我们还举着蜡烛,守着他,唱歌念诗。我觉得,这个样子符合儿子的心意。
子尤是10月22日去世,我们计划在24日举行告别式。有一位发小,23日来家。她带我出去买了旗袍和剪了短发。其实,当时我心里很不安。家里有一大堆事儿要做啊!虽然忘年交许医农先生在家里守电话,还有分工细致,进进出出忙碌的朋友。是朋友好意,专门带我出去。剪短发,是因为在孩子的后阶段,我姐姐对他说:“你妈妈留短发可好看了。”子尤说:“我妈妈留短发的样子我不记得了。”我说:“那好,我哪天剪给你看。”然而,已经没时间了。所以,剪个短发给儿子看就成了一个心愿。
有人在网上说:这个时候他妈妈还打扮,隐含的意思是说我不够哀伤。
什么是哀伤?外人有什么资格凭着衣服和形象来评论我的哀伤?难道我蓬头垢面,哭晕过去、死过去才是表达哀伤?还有,“你”是谁?我凭什么要向“你”表达我的哀伤?这种非议里潜藏着这个社会和文化里一些很阴暗的东西。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而事实上,我眼看着那么多哀伤致死,哀伤致病、致残的人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关怀。哭还不容易吗?躺倒还不容易吗?死还不容易吗?难得是不哭,不倒,是活出来,活下去。
我研究生时代好的朋友,她80年代去了美国,女儿患白血病去世。在葬礼上,所有的朋友都伤心痛哭。而她衣着得体,从头到尾没有让自己失态。只是眼泪从眼角悄悄流。每一个人过来跟她握手都说:“你真棒”。她就跟别人说:“如果是你,你也行。”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是此前我一次受到的关于死亡的教育。
我不会按“习俗”行事,只会想怎么样让孩子满意。记得2004年6月25日,那天是是他接受纵隔肿瘤切除术的日子。那时他14岁,很早就起来做各种术前准备,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在一个小本子上随手记下来。其中的一段说的是:“妈妈,你应该是高贵的,井井有条的,忙而不乱的,举止文雅的,说话端庄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驮着背从外面走进来,给我丢脸。”这就是儿子对我的要求和嘱咐。我了解子尤的心思,是不可以给他丢脸的。所以,后送别时刻,他躺在那里,我要尽量体面,这样一种精神之爱和连接,我能够领会,有所表达,是我的幸福所在。
偶然一个机会,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果丹皮的网友说:“有一天我走了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但我希望离开苦难的那一天,我的母亲能够像子尤的妈妈一样穿上漂亮的衣服为我送行!”他这么清晰地表达自己希望什么样的送别。这是一位患肝癌的青年。我去医院看过他,与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后来,他的电话和都停掉了,想必他真的走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不知他的妈妈是不是了解他的心意,满足了他的心意,穿着漂亮的衣服为儿子送行
三是,标签化,歧视。
人们倾向于给失丧者贴上“失败”、“悲惨”的人生标签,想象她/他的行为轨迹是怎么样的。而当事人害怕旁人异样的目光,或是尽力摆脱这种标签,迎合,在人前人后反差很大,在压抑和掩盖痛苦中难免成疾。另一种表现是,自己也接受这样的标签,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将“失丧者”与“健全人”分成两个世界。
也有给我贴标签的。我岂能被一个标签锁住?事实证明贴标签者是错的。因为我的跨界身份,更加理解丧子父母的处境。十年前,我曾接触过上海的丧子爸爸妈妈群体--“星星港”。他们是中国早组织起来的,自助助人。这使很多丧子父母找到了家园。但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聚会时虽然高兴地说笑,回到家,就又陷了自己的痛苦难以自拔。近年来,各地有越来越多的支持团体建立起来,在内抱团取暖,在外与社会隔绝的现象较多。他们遭受着各种各样地被歧视,难以回归和融入正常的社会网络。
……
序言
用户评价
拿到“十二堂生命课”这本书,我首先被它独特的包装所吸引。不是那种华丽的、堆砌的封面,而是透露着一种沉静而有力量的美感。中国工人出版社,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踏实的底蕴,让我相信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那种空泛的说教,而是真正源于生活、扎根于实践的道理。翻开书页,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扑鼻而来,这大概是书籍最原始的魅力吧。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十二堂”课到底会讲些什么。是关于人生的选择,还是关于情感的经营?抑或是关于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每一个“生命课”的标题都像一个未解之谜,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去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有时候,我们太容易被眼前的琐事蒙蔽,忘记了生活的本质,忘记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东西。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面镜子,照出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并且提供一把钥匙,帮助我开启通往更美好未来的大门。
评分看到“十二堂生命课”的书名,再了解到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我内心涌起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在中国,工人出版社的书籍往往以其朴实、深刻、贴近现实而著称,这让我对这本书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总觉得,生活中的很多道理,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去阐述,而是可以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真实的经历来展现。我希望这“十二堂课”,能够带领我走进一个个别样的人生,去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去领悟其中的酸甜苦辣。或许,这本书会告诉我,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又或许,它会教我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真诚和善良。我期待着,它能像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最深刻的道理,让我能够从中汲取力量,更好地前行。
评分“十二堂生命课”这个书名,听起来就充满了哲思和启发性。作为一本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我预感它会带着一种务实的精神,不会像一些理论性的著作那样晦涩难懂,而是更侧重于实际的应用和生活中的感悟。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日常的平凡之中,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挖掘。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宝藏地图,指引我发现那些被我忽略的生命真谛。我很好奇,这十二堂课会涵盖哪些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面对挫折?还是如何培养积极的心态?每一个关键词都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让我能够将书中的道理融会贯通,并在我的生活中加以实践,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充实。
评分对于“十二堂生命课”,我充满了期待,尤其是知道它出自中国工人出版社。这意味着它可能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更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悟。我一直觉得,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师,但有时候,我们缺乏一双发现的眼睛,或者一个能够点拨的引路人。“十二堂生命课”这个名字,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它仿佛在向我招手,邀请我进入一个由智慧构建的殿堂,去学习、去成长。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系列关于人生哲理的启示,也许是关于如何保持初心,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又或是如何在逆境中找到力量。我不求它能一语道破所有的人生秘密,但只要它能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一丝光亮,在我失落的时候,给我一份安慰,我就已经心满意足。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十二堂生命课”,出版社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无所适从,找不到方向,更别提什么“生命课”了。但正是这种迷茫,让我迫切地想要寻找一些能够指引我、启发我的东西。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简洁,但“生命课”这三个字却有着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仿佛预示着里面蕴含着深刻的智慧。我尤其喜欢它字体设计,既有力量又不失温度,让人忍不住想要翻开它,一探究竟。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更从容地面对挑战。也许,它能告诉我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或者,如何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拥抱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名字也让我感到一丝亲切,仿佛这是一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朴实智慧,接地气,不空洞。我期待着,它能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朋友,娓娓道来,点亮我心中的迷茫。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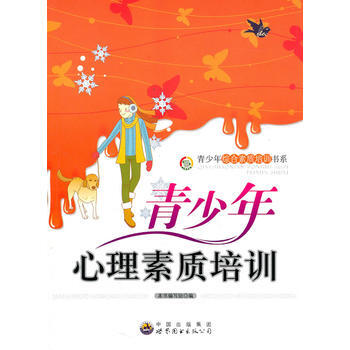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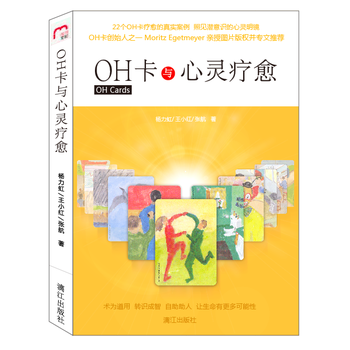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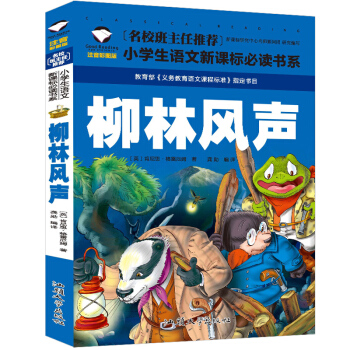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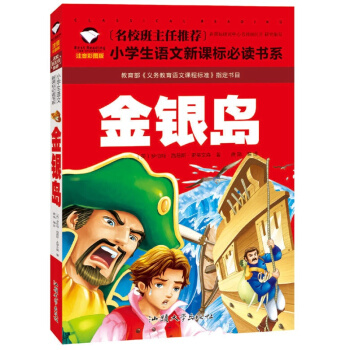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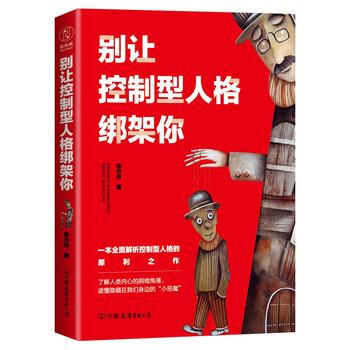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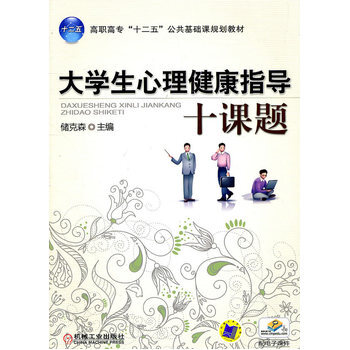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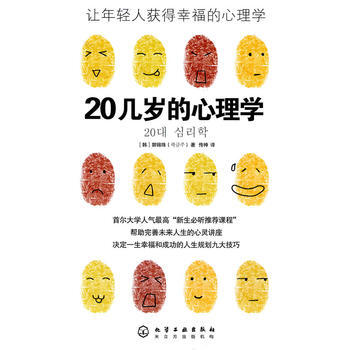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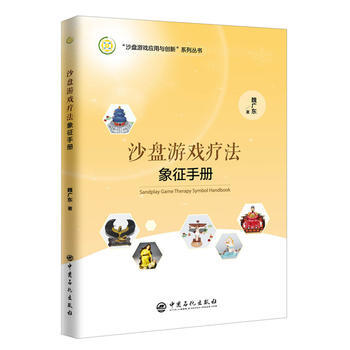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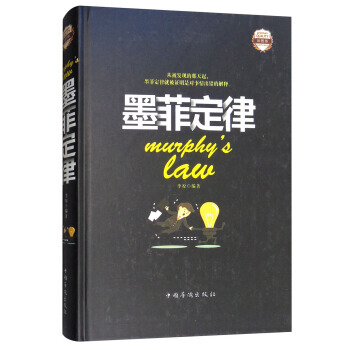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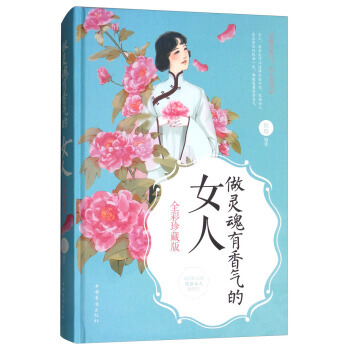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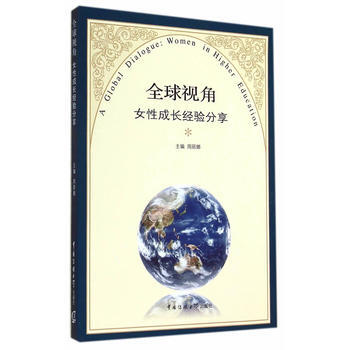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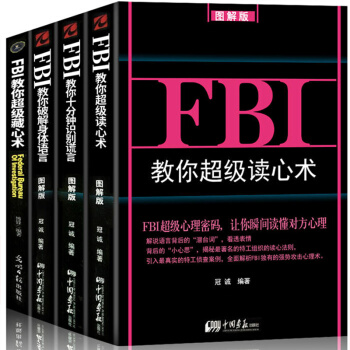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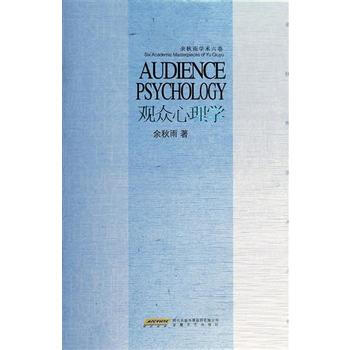
![正版新书--青少年电子游戏与网络成瘾 [法]卢西亚.罗莫,斯蒂芬妮.比乌拉克,劳伦斯 上海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29677666771/5b320852N194b2f3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