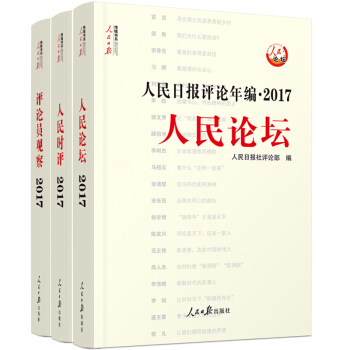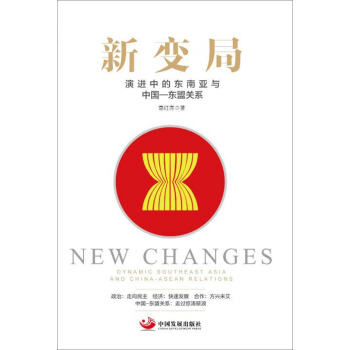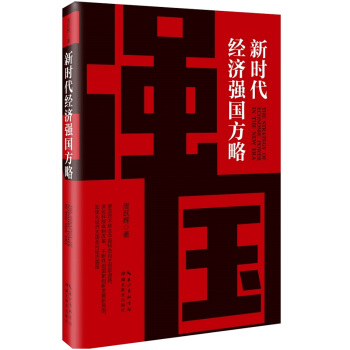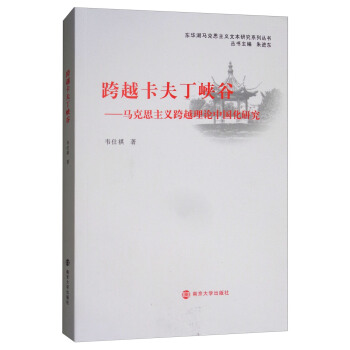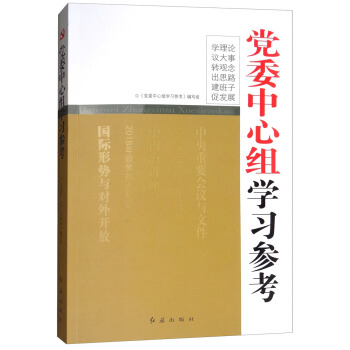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本书是政治传播、舆论、民主理论、美国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必读书。可读性强,理论叙述与历史叙事相结合。
有助于了解美国历史和政治。
内容简介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涉及两个主题:一是民主与理性的关系。二是民意调查的数据具有工具的和象征的两个功能。本书既有对民意调查的技术、历史方面的探讨,还有对它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辨。作者简介
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美国知名政治学家,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校长,是该校1881年建校以来首位女性校长。译者张健,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目录导语/00
第一章 定量与理性
第二章 数字与符号政治
第三章 舆论表达与统计方法
第四章 党派政治与模拟调查的符号运用(1856—1936)
第五章 国会议员、记者与意见评估(1930—1950)
第六章 当代公众舆论研究
第七章 群众估算与公众舆论
第八章 意见量化与民主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民调与大众传媒本书不少篇幅讨论记者所进行的民调以及调查研究,因而对当代民调业的讨论也从新闻组织开始。正如詹姆斯·布赖斯在《美国联邦》中所指出的,记者有助于塑造公众舆论,但他们也会尽其所能来尝试评估大众情绪。记者们一直对评估公众舆论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公众舆论很重要——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对公众舆论的严密评估可以帮助编辑考量公众想要听到或读到什么,并因此而形塑新闻内容。另外,人们喜欢阅读或者听到关于公众舆论的新闻,意见调查也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比较成为可能。
记者早就发现他人所提供的民调数据非常有用。在19世纪,他们报道由志同道合的党派读者所寄送给他们的民调。到了20世纪,新闻组织经常订阅民调服务,并且持续地刊登或者播报由他人收集的关于公众情绪的数字。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一些新闻组织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内部民调机构。两位新闻学教授——戴维·韦弗(David Weaver)与麦克斯·麦库姆斯(Max McCombs)提出:记者最早开始对社会科学方法感兴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社会科学下设置了首个新闻学培训项目后,很多大学创办了新闻学的研究生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者接受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据研究者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的调查,到70年代晚期,77个新闻学硕士项目中,61%的项目规定了一门量化研究方法的课程。
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以前是记者,现在教授新闻学,他普及了“精确新闻学”这个术语,用于描述记者、编辑如何能够运用社会科学技巧的方法。他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这本书影响深远,在新闻学院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在书中,他认为记者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发展,量化工具在报道新闻中非常有用: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帮助我们……社会科学在许多领域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智慧的持续审核。仅仅密切关注和查明社会科学家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为自己省去不少麻烦,省去不确定性和错失的良机。更为重要也更为直接的实用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去追随他们这样的榜样,同时丢掉哲学家的扶手椅,放弃这样的观念,即某些事实与常识就能使任何问题迎刃而解,把黏性的、高性能的研究技巧变成我们手中的技巧。
像新闻学课程一样,新闻机构以调查研究和民意调查的形式,持续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日报、电视新闻节目涵盖了形形色色的有关民调与调查研究的报道。1980年,戴维·帕尔兹(David Paletz)与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一次内容分析,目的是探究媒体如何使用民调。他们发现,在3个非选举年期间,《纽约时报》刊载了380个民调;在同样的时间里,NBC和CBS的夜间新闻节目也一直在报道大量的民调——数量分别是83和40。迈克尔·特劳戈特(Michael Traugott)与罗伯特·鲁希(Robrta Rusch)研究媒介中民调的扩张,他们分析了由《纽约时报》在1980年、1984年、1988年总统大选年中报道的大量民意调查,发现在每次竞选期间被报道的民调的绝对数量都增加了;引用民调一般是报道文章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强调竞选策略和“赛马”。
尽管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政治民调的数量没有明确报告,但是媒体要负责生产和推广许多数据。一些全国媒体联合起来进行民调(比如,《纽约时报》/CBS新闻民调或者是ABC新闻/《华盛顿邮报》民调),还有很多民调是由地方新闻机构来完成的。艾伯特·坎特里尔(Albert Cantril)认为,尽管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民调数量不断增加,但1988年的大选期间民调似乎“无处不在”。许多媒介渠道都用到了一本名叫《热线》(Hotline)的出版物——选战的每日报告,是一本州和地方民调的汇编。实际上,州和地方民调一般被全国性新闻机构所忽视;1988年之所以获得关注,也是因为这份《热线》。但全国性新闻机构对《热线》的依赖是有问题的,因为《热线》省略了许多方法上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恰恰能够帮助消费者评估民调的可靠性。
媒体中数量庞大的民调塑造了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特征。尽管我会在结论章节中探讨民调与量化对民主交流的影响,但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有很多记者担心民调在媒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菲利普·迈耶报告说,许多依赖民调的新闻机构,让他感到“不安”。有时候,记者、编辑因为他们可能在大选中造成公众舆论的“乐队花车效应”而感到内疚,尝试减少这些感觉到的民调影响。报纸以及电视新闻广播在报道民调结果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他们“试图隐瞒”数据的精确性:
比方说,当《纽约时报》去年11月报道盖洛普公司最终的民调结果时,它删去了盖洛普机构的基本预测——布什会在两党投票中获得56%的选票而获胜,只是报道了能够显示“尚未决定(如何投票)”的那部分不太精确的数字。《今日美国报》采用了高登·布莱克(Gordon Black)的直接预测,在头版用一张图表显示55%的人支持布什,但没有在与图表一起的报道中提及预测结果,而是强调选民中的“倾向者”与“尚未决定者”。这三家网络化的民意调查都没有尝试给出“尚未决定”的选民的发布情况。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分部的编辑。他认为,民调对记者来说很有用处,但在很多方面上也是有问题的。民调造成了“赛马”式的报道,这过早地在选战中将候选人从竞争中排除出去。此外,许多媒体机构在它们内部的民调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经常会无视其他民调人员的结果。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那些其他的民调结果可能会与报纸自己的民调结果不同。科瓦奇想知道,是否媒体与他们的民调一起为公共辩论创造了议题:“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危险?”他问道,“其他的观点、议题以及办法都被排挤出去了,然后采用了一个不完整的议程?”事实上,大量来自记者与其他人士对媒体运用数据的批评声音,集中于媒体如何报道数据上。传播复杂的调查结果的困难、记者们缺乏恰当的量化方法培训、没有批评性地报道民调数据,所有这些都受到相当大的关注。10记者可能有时候会符号性地使用民调数据,像19世纪那样,但是当代民调报道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对数据的错误解读。在结论一章笔者会按照民主理论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用户评价
我一直在思考,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民意调查是否还保有它原有的力量?这本书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答案。作者不仅分析了传统的民意调查方式,还探讨了新兴的数字技术,如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如何被用来“量化”民意。他讨论了这些新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新的挑战。我尤其对关于“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的讨论感到着迷,这些概念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民意”可能并不代表真实的情况。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民意调查的演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政治力量也在不断地适应和利用这些变化。它让我对未来的政治格局充满了好奇,也让我对如何更准确地理解“民意”有了更深的思考。
评分这本书带来的最深刻的触动,是关于“沉默的大多数”与“发声的少数”之间的张力。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生动地展示了民意调查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某些声音,而又可能“忽略”了另一些声音。这种对民意复杂性的深刻揭示,让我对民主的运作机制有了更全面、更辩证的理解。它让我反思,在追求民主和公平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确保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而不是被统计学上的偏差或政治上的操纵所淹没。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评论。它引导我思考,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如何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如何才能真正地让“数字”反映“民意”,而不是被“民意”所裹挟。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每天接触到的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民意调查数据,竟然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甚至能够深刻地改变政治的走向。作者以一种极其详实且富有条理的方式,将复杂的统计学原理和政治学分析相结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我特别喜欢他剖析不同民意调查方法时所使用的案例,那些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作者的笔下变得更加鲜活,也让我对那些“数字”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例如,在某个历史性的选举中,某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民意调查结果,是如何被解读、被利用,最终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倾向,甚至左右了选举结果。这种层层递进的分析,让我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政治漩涡之中,深刻体会到民意调查作为一种“工具”,其背后所蕴含的策略和博弈。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获取信息的方式,也让我对所谓的“民意”有了更审慎的看法。
评分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它没有停留在简单地描述民意调查的结果,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数据是如何被“生产”、“传播”和“使用”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力量是如何巧妙地介入和操纵的。作者对媒体在其中的角色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分析了媒体是如何选择性地报道民意调查,如何通过放大某些数据来制造舆论,从而影响公众认知。这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被大量的碎片化信息所淹没,而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辨别信息真伪、理解信息背后意图的有效方法。它提醒我们,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故事,一个想要说服你的故事,而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对于做出明智的判断至关重要。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人了,那种冷静的蓝色调,搭配着简洁有力的字体,隐约透出一股严谨和思考的意味。光看书名,就让人产生了无限的联想。“用数字说话”,这四个字本身就充满了力量感,仿佛每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都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相,而“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更是直接点明了核心议题,将“数字”与“民意”、“政治”这三个看似遥远却又息息相关的概念巧妙地联系起来。我一直对民意调查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感到好奇,它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一个如此复杂且充满变数的政治环境中?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的窗口,让我期待着能跟随作者的脚步,去揭示那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逻辑和力量。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更像是一本关于理解社会运行机制的指南,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第一页,开始这场数字与政治的探索之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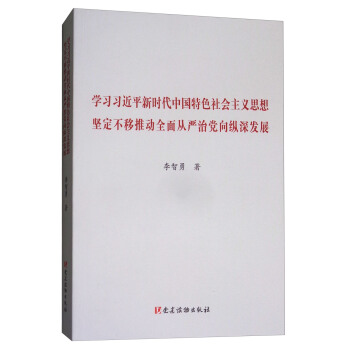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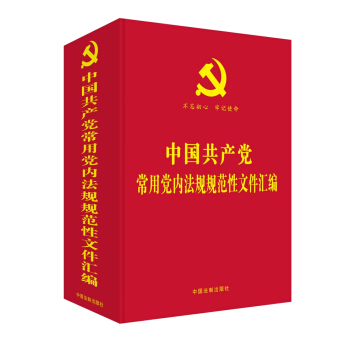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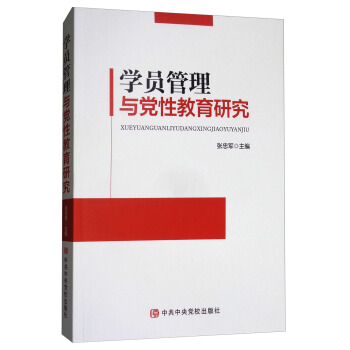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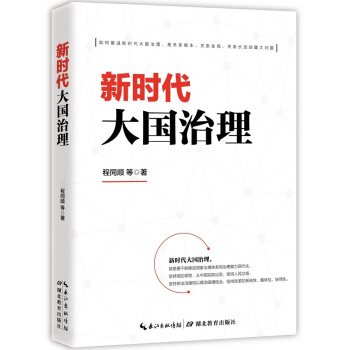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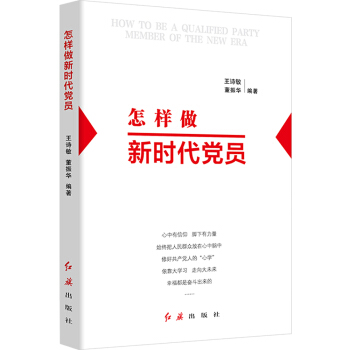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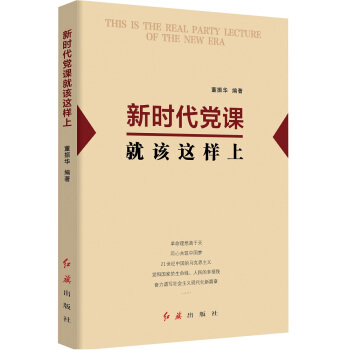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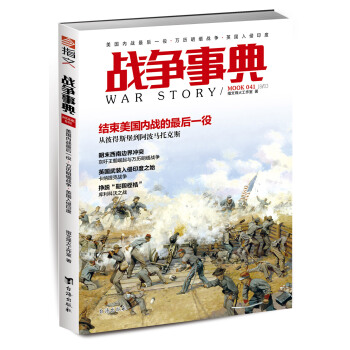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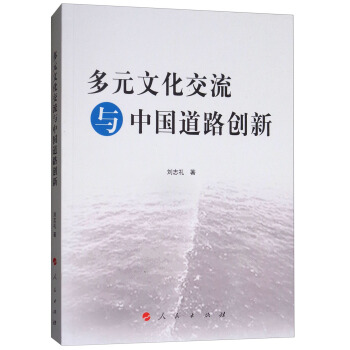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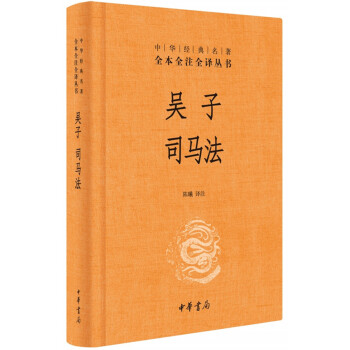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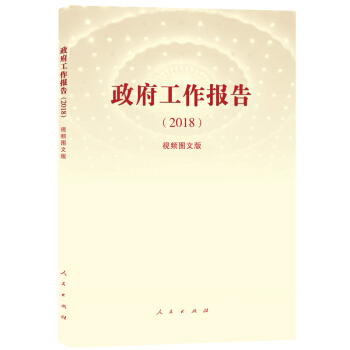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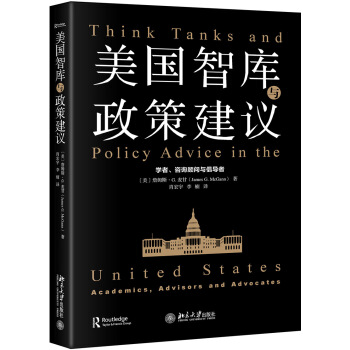
![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8) [ Annual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entral Asia(2018)]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24961/5ac48024Na81be1e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