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3.周作人的散文,平淡如水、自然如风,展现出平和、空灵的人生境界,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鲁迅晚年向斯诺夫人推荐周作人,认为他是中国优秀的散文家。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一生著译传世约一千二百余万字,其中翻译作品居一半有余。
3.周译特色有三:一是选目,二是译文,三是注释。所译多为世界文学经典之作,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古事记》,《枕草子》,日本 狂言和“滑稽本”等,取舍精当自不待言。周氏精通古希腊文、日文、英文等多种外文,追求直译风格,自家又是散文大师,所译总能很完美也很自如地传达原著的意味。周氏为译文所加注释向为其所重视,在译作中占很大比例,不妨看作是对相关外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他一生置身于主流话语体系和正统思维方式之外,保证了这些注释不受时代局限,价值历久不衰。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一个巨大复杂的存在,他站在血腥飞舞、风雨迷茫的时代,亲历学术间的起落,深感历史的残酷。颇受争议,却难掩夺目风采。
2.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要高于鲁迅。
3.周作人的杂文平和冲淡、趣味横生、博通古今、优雅慢调。
内容简介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苦雨》《乌篷船》等多篇经典散文、随笔,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通过民国翻译大家周作人经典译本,重温日本文学、希腊文学的闲雅之美。
周作人的文章属于耐看的一类,声名远远高于同代的作家,学问力度毫不逊于鲁迅。他将思想家的意绪和艺术家的灵感汇于一身,以小品文的面目出现,叙天下经纬,议红尘旧事,形成了独立的文风。本书收入周作人《荣光之手》《日本管窥》《在女子学院被囚记》等多篇经典杂文、小品文、杂谈,篇篇精到,让读书观字之你我,随其恬淡之语感其情调之线,在枯燥的文学和历史中,找寻一点点光亮。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精彩书摘
(二)虾油黄瓜
我从朝鲜经由满洲到北京去的路上,想起来是在山海关左近的一站。有一种什么东西装在小小的篓子或是罐里,大家都在那里买。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想来总是北方名物吧,我也是好奇,便也买了一个。木刻印刷的标签上,看不很清楚的写着“虾油玉爪”。虾的油是什么东西呢?至于“玉爪”,更加猜不出是什么了,心想或者是一种盐煮的小虾米吧。便朝着篓子看,同车的日本人也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什么呀。答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说是不知道就买了么,便大笑一通。
到了北京之后,打开盖来看时,这却很是珍奇。是一种盐渍的没有像小手指头那么粗的黄瓜,满满装着,像翡翠的碧绿。要得这样一篓——说是篓却是内外都贴着纸,涂过防水的什么东西——小黄瓜,以我们日本人的常识来说,不知要从几百株的藤上去采摘,而且这样小的黄瓜除了饭馆里用作鱼生什么陪衬,才很是珍重的来加上一两个,算是了不得。于是才知道,从前认作“玉爪”的原来是“王瓜”之误,便是日本所谓黄瓜。虾油者似乎就是盐腌细虾腐烂溶解的卤汁。后来留心着看,此物往往用作一种调味料,譬如我们叫作成吉思汗料理的烤羊肉,就必须用此,但是因为有一种异样的气味,所以对于日本人是不大相宜的。用了这种卤汁浸的黄瓜,味道很咸,不能多吃,但是当作下酒的菜却是极妙的。回国后过了十多年,偶然有一个在上海的友人,托人带了两瓶这东西给我,我很高兴能够再尝珍味,赶紧拿来下酒,可是比起从前在路上所买的,却没有那新鲜的风味,不觉大为失望。现今想起来,觉得那时胡乱买得一篓,真是天赐口福了。
在女子学院被囚记
刊一九二九年四月《华北日报副刊》
署名岂明
收入《永日集》
四月十九日下午三时我到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上课,到三点四十五分时分忽然听见楼下一片叫打声,同学们都惊慌起来,说法学院学生打进来了。我夹起书包(书包外面还有一本新从邮局取出来的Lawall 的《四千年药学史》),到楼下来一看,只见满院都是法学院学生,两张大白旗(后来看见上书“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进来之后又拿往大门外去插,一群男生扭打着一个校警,另外有一个本院女生上去打钟,也被一群男生所打。
大约在这时候,校内电话线被剪断,大门也已关闭了,另外有一个法学院学生在门的东偏架了梯子,爬在墙上瞭望,干江湖上所谓“把风”的勾当。我见课已上不成,便预备出校去,走到门口,被几个法学院男生挡住,说不准出去。我问为什么,他们答说没有什么不什么,总之是不准走。
我对他们说,我同诸君辩论,要求放出,乃是看得起诸君的缘故,因为诸君是法学院的学生,是懂法律的。他们愈聚愈多,总有三四十人左右,都嚷说不准走,乱推乱拉,说你不用多说废话,我们不同你讲什么法,说什么理。我听了倒安了心,对他们说道,那么我就不走,既然你们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我就是被拘被打,也决不说第二句话。于是我便从这班法学院学生丛中挤了出来,退回院内。
我坐在院子里东北方面的铁栅边上,心里纳闷,推求法学院学生不准我出去的缘故。在我凡庸迟钝的脑子里,费了二三十分钟的思索,才得到一线光明:我将关门,剪电话,“把风”这几件事连起来想,觉得这很有普通抢劫时的神气,因此推想法学院学生拘禁我们,为的是怕我们出去到区上去报案。是的,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假如一面把风,剪电话,一面又放事主方面的人出去,这岂不是天下第一等笨汉的行为么?
但是他们的“战略”似乎不久又改变了。大约法学院学生在打进女子学院来之后,已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都备了案,不必再怕人去告诉,于是我们教员由事主一变而为证人,其义务是在于签名证明法学院学生之打进来得非常文明了,被拘禁的教员就我所认识,连我在内就有十一人,其中有一位唐太太,因家有婴孩须得喂奶,到了五时半还不能出去,很是着急,便去找法学院学生要求放出。
他们答说,留你们在这里,是要你们会同大学办公处人员签字证明我们文明接收,故须等办公处有人来共同证明后才得出去。我真诧异,我有什么能够证明,除了我自己同了十位同事被拘禁这一件事以外?自然,法学院男生打校警,打女子学院学生,也是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喔,几乎忘记,还有一个法学院男生被打,这我也可以证明,因为我是在场亲见的。
我亲见有一个身穿马褂,头戴瓜皮小帽,左手挟一大堆讲义之类的法学院男生,嘴里咕噜的,向关着的大门走去,许多法学院男生追去,叫骂喊打,结果是那一个人陷入重围,见西边一个拳头落在瓜皮帽的上头,东边一只手落在瓜皮帽的旁边,未几乃见此君已无瓜皮帽在头上,仍穿马褂挟讲义,飞奔地逃往办公的楼下,后面追着许多人,走近台阶而马褂已为一人所扯住,遂蜂拥入北边的楼下,截至我被放免为止,不复见此君的踪影。
后来阅报知系法学院三年级生,因事自相冲突,“几至动武”云。我在这里可以负责声明,“几至”二字绝对错误,事实是大动其武,我系亲见,愿为证明,即签名,盖印,或再画押,加盖指纹,均可,如必要时须举手宣誓,亦无不可也。
且说法学院学生不准唐太太出去,不久却又有人来说,如有特别事故,亦可放出,但必须在证明书上签名,否则不准。唐太太不肯签名,该事遂又停顿。随后法学院学生又来劝谕我们,如肯签字即可出去,据我所知,沈士远先生和我都接到这种劝谕,但是我们也不答应。法学院学生很生了气,
大声说他们不愿出去便让他们在这里,连笑带骂,不过这都不足计较,无须详记。
那时已是六时,大风忽起,灰土飞扬,天气骤冷,我们立在院中西偏树下,直至六时半以后始得法学院学生命令放免,最初说只许单身出去,车仍扣留,过了好久才准洋车同去,但这只以教员为限,至于职员仍一律拘禁不放。其时一同出来者为沈士远、陈逵、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浚济、王仁辅和我一共八人,此外尚有唐赵丽莲、郝高梓二女士及溥侗君当时未见,或者出来较迟一步,女子学院全体学生则均鹄立东边讲堂外廊下,我临走时所见情形如此。
我回家时已是七点半左右。我这回在女子学院被法学院学生所拘禁,历时两点多钟之久,在我并不十分觉得诧异,恐慌,或是愤慨。我在北京住了十三年,所经的危险已不止一次,这回至少已经要算是第五次,差不多有点习惯了。
第一次是民国六年张勋复辟,在内城大放枪炮,我颇恐慌,第二次民国八年六三事件,我在警察厅前几乎被马队所踏死,我很愤慨,在《前门遇马队记》中大发牢骚,虽马是无知畜生,但马上还有人,不知为甚这样胡为之语。
以后遇见章土钊、林素园两回的驱逐,我简直看惯了,刘哲林修竹时代我便学了乖,做了隐逸,和京师大学的学生殊途同归地服从了,得免了好些危险。现在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手里吃了亏,算来是第五次了,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我于法学院学生毫无责难的意思。他们在门口对我声明是不讲法不讲理的,这岂不是比郑重道歉还要切实,此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学校当局,却不能就这样轻轻地放过,结果由我与陈沈俞三君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质问有无办法,能否保障教员以后不被拘禁,不过我知道这也只是这边的一种表示罢了,当局理不理又谁能知道,就是覆也还不是一句空话么?
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回我的被囚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大能怪别人。诚如大名鼎鼎的毛校长所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女子学院去,报上早已发表,难道你们不知道么?是的,知道原是知道的,而且报上也不止登过一二回了,但是说来惭愧,我虽有世故老人之称,(但章士钊又称我是胆智俱全,未知
孰是,)实在有许多地方还是太老实,换一句话就是太蠢笨。
我听说法学院学生要打进来,而还要到女子学院去上课,以致自投罗网,这就因为是我太老实,错信托了教育与法律。当初我也踌躇,有点不大敢去,怕被打在里边,可是转侧一想,真可笑,怕什么?法学院学生不是大学生而又是学法律的吗?怕他们真会打进来,这简直是侮辱他们!即使是房客不付租金,房东要收回住屋,也只好请法院派法警去勒令迁让,房东自己断不能率领子侄加雇棒手直打进去的,这在我们不懂法律的人也还知道,何况他们现学法律,将来要做法官的法学院学生,哪里会做出这样勾当来呢?即使退一百步说,他们说不一定真会打进来,但是在北平不是还有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军警当局么?不要说现今是在暗地戒严,即在平时,如有人被私人拘禁或是被打了,军警当局必定出来干涉,决不会坐视不救的。那么,去上课有什么危险,谁要怕是谁自己糊涂。
前言/序言
北京的茶食
刊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署名陶然
收《雨天的书》《泽泻集》和《知堂文集》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
我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
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十三年二月
用户评价
《夜的草木》,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静谧和诗意,读起来,果然如其名,充满了夜晚的幽深和草木的芬芳。作者的文字,像是在夜色中缓缓流淌的溪水,没有激烈的起伏,却有着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他擅长于捕捉那些细微的光影变化,那些夜晚的虫鸣鸟叫,以及在月光下摇曳的草木姿态。 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充满了诗情画意,却又不会显得过于矫揉造作。他将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仿佛与草木共呼吸,与夜色同沉醉。读他的文字,你能感受到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之美,那种宁静、安详,能够瞬间治愈都市生活的疲惫。 《夜的草木》中最让我动容的,是他对生命短暂的感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他看到草木在夜晚的生长与凋零,联想到人生的起伏与无常。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反而在这种无常之中,体悟到生命的珍贵。他鼓励我们去感受每一个瞬间,去珍惜眼前的拥有。 书中,他对于孤独的描写,也与众不同。他并没有将孤独视为一种痛苦,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机会。在夜深人静之时,与草木为伴,与星月对话,在孤独中,寻求内心的平静与成长。这种对孤独的积极解读,让他的文字,充满了积极的力量。 这本书,就像在寂静的夜晚,为你点亮一盏温暖的灯。它用轻柔的笔触,带你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世界。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感到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它让你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你更加懂得如何去面对生活的起伏。这是一本能够让你在喧嚣中找到内心宁静的佳作。
评分《花前月下,青丝白发》,仅仅是书名,就足以勾勒出一幅跨越时空的画面,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岁月的沉淀。这本书的文字,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山水画,淡雅而不失意境,写意而不失神韵。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婉,能够捕捉到生活中那些转瞬即逝的情感,并将它们定格在纸页之上。 他对于爱情的描绘,并非是轰轰烈烈的激情,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平淡的日常之中。他写男女之间的情愫,写相思的愁绪,写岁月的变迁对感情的影响。这些描写,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却又饱含着对真挚情感的赞美。他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脆弱,也看到了爱情的坚韧。 《花前月下,青丝白发》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作者对于“时间”的独特理解。他似乎总能游走于不同的时间维度,将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感受巧妙地融合。他写“青丝”,也写“白发”,这两个词语,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变化,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他让我们看到了,时间是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一切。 他对“花前月下”的意境,更是描绘得入木三分。那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承载着无数情感的载体。他将个人的情感,融入到自然景物之中,让读者在品读文字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浪漫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 这本书,就像一位知心的朋友,在你耳边低语,讲述着关于情感、关于岁月的故事。他的话语,或许并不宏大,但却能触动人心最深处的情感。读《花前月下,青丝白发》,你会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去感受那份属于青春的浪漫,也去体味那份属于岁月的沉淀。它让我们懂得,在时光的流转中,珍惜那些美好的瞬间,也懂得,在生命的旅途中,去追寻那份永恒的情感。
评分读《寂寞的散步者》,我仿佛置身于一条长长的、蜿蜒的小巷,阳光斑驳地洒在青石板路上,空气中弥漫着老旧书本和尘埃混合的味道。这本书的文字,就如同那条小巷,带着一种复古的、慵懒的气息,一点点地在你眼前展开,让你沉浸其中,不愿离去。作者的叙述方式,并非直奔主题,而是像一位老者,慢悠悠地跟你拉家常,从一件小事引出另一件小事,再从这些小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生活、对人生的思考。 他的笔触极其细腻,能够捕捉到那些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细节。比如,描写一个人物的眼神,就能勾勒出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描绘一个场景的色彩,就能传达出作者当时的心情。这种细腻,并非堆砌辞藻,而是源于他对人情世故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日常生活细微之处的敏感。我常常在读到某些段落时,会停下来,反复咀嚼,因为那里面的话,总能让我联想到自己曾经的经历,或者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豁然开朗。 《寂寞的散步者》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寂寞”的解读。他并没有将寂寞描绘成一种负面的情绪,而是将其看作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富足。他笔下的寂寞,不是孤独的、绝望的,而是一种内省的、宁静的、甚至是带有某种优越感的。这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寂寞,是在喧嚣尘世中,为心灵寻觅一片安宁之地的寂寞。 他对于“散步”的描绘,也同样富有哲理。散步,对他而言,不仅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漫游。在散步的过程中,他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思考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让思绪在自然的流动中,逐渐清晰。这种“散步”式的写作,也反映在他的文字风格上,没有生硬的逻辑,没有刻意的结构,而是如同随风飘散的叶子,自由而舒展。 这本书,就像一个老朋友在午后的阳光下,缓缓地向你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平淡的叙述,深沉的思考,以及一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温情。它让我重新审视了生活中的许多“小确幸”,也让我对“寂寞”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本能够安抚心灵的书,能够让你在纷繁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
评分翻开《灯下漫笔》,一股浓郁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回到了那个似乎已经模糊了的年代。这本书的语言,带着一种古朴的韵味,没有如今网络流行语的浮躁,也没有过度的情感渲染,只是用一种平实、真诚的笔触,娓娓道来。读起来,你会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就像在品尝一道精心烹制的家常菜,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暖的味道。 作者在书中,对许多旧事、旧物,都流露出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描写儿时的回忆,童年的趣事,以及那些已经消逝的旧景。这些描写,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饱含着作者对逝去岁月的眷恋,以及对那些美好时光的怀念。他通过这些片段,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展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 《灯下漫笔》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作者对“人情”的深刻体察。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邻居、朋友,还是偶遇的路人,都被他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绘,没有虚假的客套,也没有刻意的疏离,而是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理解。他懂得人性的复杂,也懂得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系。 书中,他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也并非是冰冷的事实堆砌,而是带着一种温情的旁观者的视角,去审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不会去评判对错,而是试图去理解,去感受。这种视角,使得他的文字,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历史的意义。 这本书,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坐在灯下,向你讲述他的人生故事,讲述他眼中的世界。他的话语,可能并不惊天动地,但却蕴含着深邃的人生智慧。读《灯下漫笔》,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在平淡中感悟生活的真谛,在温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好。它让我们停下脚步,去回味那些曾经的时光,去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
评分周作人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像一杯温吞的茶,初入口时或许平淡,细品之下,却能品出甘醇与悠长。我最近读了他的《雨天的书》,那里面关于雨的描写,每一个字都仿佛被湿润过的空气包裹着,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宁静和淡雅。他写雨丝,“如柳絮,如烟,如雾”,又写雨声,“淅淅沥沥,如窃窃私语,又如低吟浅唱”。读来,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湿润的江南雨季,窗外是迷蒙的景致,屋内是温热的茶香,而心中,则被一种淡淡的惆怅所填满。 这种惆怅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源于他对生命,对世事的深刻体悟。他笔下的寻常事物,比如一只猫,一扇窗,一棵树,都能被他赋予灵性,引出一段段哲思。他观察细致入微,情感真挚朴素,没有过多的雕饰,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最细腻的感受,娓娓道来。这使得他的文字,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感,仿佛是和一位老友在静静地交谈,倾听着他的人生感悟。 《雨天的书》中,我尤其喜欢他写“过时”二字。他对于“过时”的理解,并非是物质上的陈旧,而是精神上的某种失落,某种与时代脱节的无奈。这让我想到了许多人,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是否也曾有过被时代抛下的感觉?这种怀旧的情绪,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让文字充满了厚重感。 周作人的文字,还有一种“闲”的味道。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闲,而是经过沉淀、历练后,对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从而获得的一种从容和淡定。在《雨天的书》里,他写到“静观”,写到“闲适”,这些词语在他笔下,仿佛拥有了生命,散发出一种宁静的力量。读着读着,我感到自己的心也慢了下来,开始审视生活中的许多匆忙,开始体会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总的来说,《雨天的书》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激昂澎湃的宣言,只是用一种平和、淡远的笔调,描绘了作者的生活片段和思想碎片。然而,正是这份平和与淡远,却蕴含着深邃的智慧和动人的情感,能够触动人心最柔软的角落。它像一首舒缓的乐曲,在喧嚣的世界里,给予我片刻的宁静与慰藉。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配送快速,包装紧凑,书籍清洁整齐!
评分商品很好,物流快
评分看着还不错,应该是正版
评分商品很好,物流快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看着还不错,应该是正版
评分配送快速,包装紧凑,书籍清洁整齐!
评分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写小说如何打草稿 [Ready,Set,Novel!:Writer’s Workbook]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1647/5b0def27N640732dd.jpg)
![龙与猫之国(套装1-6册)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1978/5b223726N87ea807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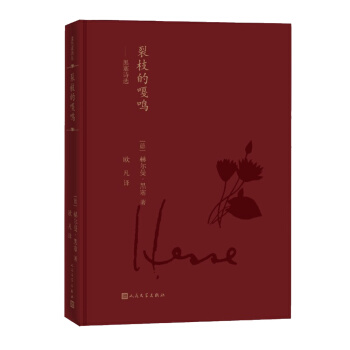


![拼音王国· 名家经典书系(曹文轩/彭懿/汤素兰/彭学军/冰波/保冬妮/张之路/周锐/常新港/孙幼军套装共10册) [6-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347/5b10a858N36686688.jpg)


![紫雾心谜4:孑然妒火/儿童文学淘乐酷 [9-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687/5b28a1d0N1fd64bef.jpg)
![花海与沼泽/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青春飞扬”系列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691/5b28a1d0N0f5e5624.jpg)

![百千大阅读·一年级上册 为天量身高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807/5b34872dN7ad66fa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