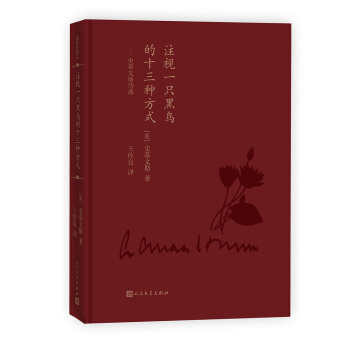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浮出历史地表:现在妇女文学研究》: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经典著作;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苏青、张爱玲等九位现代重要女作家。内容简介
《浮出历史地表》是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经典著作。借助精神分析、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本书以作家论形式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重要女作家,同时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理论切入、文本分析和历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女性书写在不同时段、不同面向上的主要特征,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本书自1989年问世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作者简介
孟悦,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5年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2000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专著有《历史与叙述》《本文的策略》《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等。戴锦华,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目录
目录绪 论 1
一、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 2
女性的(反)真理 2
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 4
“人伦之始” 7
“妻与己齐”——话语权 10
女性形象——空洞能指 13
二、一百年:走到了哪里 22
女性与民族主体 24
从“我是我自己的”与“女子没有真相” 29
“祥林嫂系列”与“新女性群” 34
第一部分 (1917—1927)
第一章 “五四”十年:悬浮的历史舞台 43
一、弑父时代 43
弑父——历史坐标上的零点 43
魅力与匮乏 46
两个死者,一个镜像 48
二、从女儿到女人——“五四”女作家创作概览 53
“父亲的女儿” 53
塑造母亲 56
爱——反侵犯性话语 58
经验与话语互逆 60
写女人 63
第二章 庐隐:“人生歧路上的怯者” 66
庐隐的世界 66
狭隙间的两扇门 71
悬浮舞台与文化死结 76
第三章 沅君:反叛与眷恋 83
爱情作为女性反抗途径 83
性爱道德观 88
母女纽带 91
第四章 冰心:天之骄女 95
得天独厚 95
神圣的母子同体——极乐的一瞬 97
“心外的湖山”、身外的面具 101
长不大的女儿 103
第五章 凌叔华:角隅中的女性世界 108
闺房中的风云变幻 109
“太太”阶层 112
新女性与新妻子 119
第二部分(1927—1937)
第六章 三十年代:文明夹缝中的神话 129
一、轮回 129
进退维谷的历史步履 129
大众之神与政父 131
双刃匕首 134
二、黑暗、阴影与白天的分割 137
陷入孤独的女性 137
他人的女性之躯 140
“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 144
第七章 丁玲:脆弱的“女神” 146
异化与孤独 146
“韦护”的两面 153
复苏与泯灭 159
第八章 走向战场与底层 166
血写的革命与墨写的革命 166
放弃小我,走向大众 170
第九章 都市的女性:辉煌之页的边缘 175
唯美意识形态 175
履着“新文化”碎片徘徊 179
第十章 白薇:未死方生 183
“弑父”场面中的女性 184
“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命运——《炸弹与征鸟》 187
十年孤独——《悲剧生涯》 190
第十一章 萧红:大智勇者的探寻 196
命运 196
女性的历史洞察力 205
彻悟与悲悯 214
第三部分(1937—1949)
第十二章 四十年代:分立的世界 223
一、主导话语阵地与解放区 224
民族新生抑或寒夜 224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善 229
无性之性 232
女性与个人共谋 234
二、女性、女人、女性话语 236
牢狱与自由 236
结束弱者阶段 239
女性话语的初始 241
第十三章 苏青:女人——“占领区的平民” 244
灾难的畸存与历史的残片 245
女性:空间性的生存 248
女人、母亲、做母亲 251
新女性:一部荒诞戏剧 255
第十四章 张爱玲:苍凉的莞尔一笑 260
一个正在逝去的“国度” 261
绣在屏风上的鸟 264
文明·历史·女人 270
结 语 性别与精神性别——关于中国妇女解放 276
2003年再版后记 282
赘言其后 288
精彩书摘
第十三章?苏青:女人——“占领区的平民”(节选)
似乎是民间传说之中在背后解开异国千结百扣的红罗包裹的少女,苏青出现在一个时代的背后,在一个血水浸染、烈火升腾的时代的阴影里,解开了庐隐们至死无奈的历史与文化的新女性之结。苏青的“结婚十年”是对“庐隐十年”的历史延续。似乎是在时代鲜血的润滑之下,五四之女的历史狭隙尽头的第二扇门终于艰涩地裂开了一道缝,从那里传来了苏青的清朗的语流。然而,苏青并不是那个背解红罗包裹的美丽、神秘、无名无姓的少女,她的出现既不可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也不可能解脱女性于历史的重轭之下。她只是在女人——这个空洞的能指,这扇供男人通过的空明的门中,填充了一个不是所指的实存,填充了一张真实的面孔,一个女人裸露的、也许并不美丽的面孔。她只是在一种素朴而大胆的女性的自陈之中,完成了对男性世界与男性的女性虚构的重述。
在苏青的世界中已不复冰心的春水繁星式的温婉,亦不复庐隐荒坟独吊式的悲怆。她不是丁玲,她的作品不是那不羁而狂放的女性的第二乐章;她亦不是白薇,有着那种在血和泪的深壑之中“打出幽灵塔”的决绝,苏青只是在极度苦闷与极度窒息的时代的低压槽中涌出的低低而辛辣的女性的述说;只是在一种男性象征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而一个女人自毁性的讲述行为,正是男性社会所必需的女性表象的轰毁。这是历史地表之上的女性对其历史地表之下的生存的陈述。
灾难的畸存与历史的残片
作为解开庐隐之结的第一人,苏青出现在沦陷区的上海,并非偶然。异族入侵者赤裸裸的血腥统治,“大东亚文化”如同一个密闭的毒气室的天顶虐杀了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男性主题与文化使命遭受了野蛮的阉割式。在正统民族文化、主流的男性文学面临着废退、解体与死亡的时候,始终在民族危亡、社会危机的常规命题下遭受着灭顶之灾的女性却获得一种畸存与苟活式的生机。如同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广岛,焦土之上竟怪异地开出一层层、一片片花朵。对于苏青来说,这并不是一片“水土特别不相宜”(傅雷语)的土地。
沦陷区,由于侵略者死亡与暴虐的占领,而隔绝了直接战祸,由此而成了一座加缪式的鼠疫猖獗的孤城,成了一片没有时间、没有历史、没有名称的荒地。在沦陷区的中心监视塔式的辐射状牢狱中,自由意味着死亡,生存意味着一种符号性的苟活。实存与权力的主体是作为异族入侵者的“他人”,而沦陷区的国民却成了物样的客体,遭受着被蹂躏、被无视、被践踏又被使用的命运。而这一切,却以民族劫难的形式外化并显影了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女性始终遭受着的历史判决与历史命运。“占领区的平民”,正是女性/新女性/解放了的女性的生存境况。这是一种和平的居民,一种规定应“安居乐业”的居民。对于他(她)们,战争已结束。他们享有自由,享有“和占领国的国民一样的尊严与权力”,但是,不言而喻的是,他们却“当然”是一批“劣种”,一批“二等公民”,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的权力与自由来自占领者的恩赐,他们应该在感激涕零之中心满意足,心安理得,不复生出任何无妄之想。占领区的平民在王道乐土上的遭遇正类似于女人作为永远的“第二性”,在男权的民主社会、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的表象下的历史遭遇。
于是,女性文学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以无害的外表在沦陷区开始了她悄然的生长。在男性主流文化废退、消失的缝隙间,在异族统治所造成的民族、男权的历史压抑力被阉割、被削弱的时间的停滞处,苏青获得了直白地讲述一个女人的真实的故事的可能。而对女人生存的真实而非想象的状况的陈述,不仅成为历史无意识的释放,而且在新的政治无意识中成了沦陷区平民生存状况的隐喻与发露,或许这正是苏青之出现、之成功、《浣锦集》《结婚十年》等行销十数版的谜底所在。而苏青也以她的女性生存的直面式,与女性话语的平实为人们所“激赏”,呈现出女性的历史解构力。而沦陷区日伪机构四面楚歌的累卵之危,也决定他们无暇也不可能识别出这种女性文学作为秩序内的反叛者,作为社会内的反社会力量的隐晦的力量与意义。而这也不是以男性主人/胜利者文化自居的刘心皇以“春秋大义”为准绳,《叛臣传》《贰臣传》式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所能定论的。而这也正是日寇一经驱逐,始终龟缩后方的国民党政权堂而皇之地前来“光复”、并重建、恢复他们的政父统治与文化压抑之后,苏青便成了以“落水作家”“性贩子”“比鸳鸯蝴蝶派有过无不及”的名义大兴讨伐之底蕴。殊不知苏青的女性的直陈,非但与鸳鸯蝴蝶无涉,而且正是对鸳蝴派将女性表象作为关于女人的神话式虚构、作为将女人作为男人欲望的空洞的能指的悖反与解构。但是,苏青终于被淹没了,她和张爱玲等沦陷区的女作家一起被投入了历史的忘怀洞,被历史的压抑力淹没在无意识的黑海之中,从墨写的文学史中消失了踪影。而当中国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消费文化以它特有的侵蚀力与瓦解力削弱了主流文化的覆盖与压抑的时候,苏青诸人才能再次而仍然是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但今日之苏青竟已是难于复原的残片,如同对文学上的解构主张的一个滑稽模仿式的例证。
但是,由子君而亚侠,而莎菲,而怀青,历史的绞盘毕竟松开了它锈死链条上的一扣,这不是一个女性“人物”的画廊,而是一个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进程,一个女性由死者而为必须死去的生者,而为屈辱、挣扎着要活下去的女性的进程;一个由男性的五四之子的历史献祭与话语存在而为活人与历史主体的进程。由“象牙戒指”——一个“枯骨似的牢圈”,一个洁白的〇,而为《蛾》——一个焚身自毁也要触摸现实,并在现实中涂上一片墨迹的“疯狂”,苏青的低语与锐叫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奇观,成了“现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一个高音区。
尽管苏青以重新标点/重写圣人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冒犯常识”,成了一个时代的大勇者。但几乎从任何意义上说,苏青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与谢冰莹等高喊“男女平等,大家从军去”的塑造新女性/强者的女作家相比,苏青笔下更多的却是“新旧合璧”的女性/弱者的生存。然而,与冰心、冯沅君等人以“爱”为旗帜的弱者话语相比,苏青的叙事文本却充满了强者的话语。她以一种“灯蛾扑火”式的勇气,揭去了女人隐秘性的历史屏障,将20年代女作家放逐到文本之下的边缘化的女性经验再度中心化。她描述而不辩解,叙说而不思辨。她的女性的自觉表现为一种文本的肌理,而不是一声空洞的战叫。这是一个无需长发蔽体,也敢裸身驰马的女人。她说:“女作家写文章有一个最大困难的地方,便是她所写的东西,容易给人们猜到她自己身上去。关于这一点,当然对于男作家也如此,只不过女作家们常更加脸嫩,更加不敢放大胆量来描写便是了。我自己是不大顾到这层的,所以有很多给人家说着的地方。”然而,苏青之女性的裸露,并不是作为一种代价或一种诱惑。惊世骇俗,与其说是她的刻意追求,不如说是文本中女性真实境况本身的惊骇力量。即被五四主流文化编码定义为死者与盲点处的生之显现。
女性:空间性的生存
如果说,沦陷区如同一片时间、文化、历史断裂的空间,那么苏青笔下的新旧参半的女性正是中国历史中这样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如果说作为五四之女的庐隐们,正是在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过剩的思辨中成了行动的瘫痪者;那么苏青则更像一个大胆行动而不及其他的女性的唐·吉诃德。苏青的世界,不是以女性的自省、自辩、自证、自许而取胜,也不是以外形式的几何晶体式的排列与精美而夺人,苏青的世界似乎是透明的,似乎是女性生活的自行呈现。而她的“真实”,并非一种事件内具的真实,而是一种讲叙行为的基调,她并未讲述人们闻所未闻的奇观或罕事,她只是以一种平实、素朴的叙事语调讲述了男人也曾讲述的地表之下的女性生存的琐屑之事——只是一味地重复,一味地庸常,一味地琐碎,如同一道永远走不尽、走不出的鬼打墙的迷障。那是一个没有时间向量的国度,那是永远“楼台高锁”“帘幕低垂”的闭锁的荒原。而苏青正是以这种女性空间——颓败、痛苦的空间性生存重述了男人们的关于女人的故事。
如同一个历史的偶句,《结婚十年》的第一幕便是一场“新旧合璧的婚礼”,那是由女儿而为女人、而为人妻的一幕,是庐隐放逐到文本外的一幕,是五四所允诺的关于女人的多幕剧中的第二幕。在苏青的世界中,婚姻既不像对男性那样是女性的成人礼,命名式,也不是新女性之梦的实现,甚至不是“性的引入”;这只是一次空间性的位移,一种列维-施特劳斯意义上的“交换”——一次摒除了女人参与的、两个家庭间的对女人的交换。经由一个“漆黑、闷气煞人”的狭小的密闭空间——花轿,女儿将由父亲之家转移给她的夫家,而不是丈夫;以便成为一个监视得更加森严、闭锁得更加严密的空间的一件陈设。从此开始她作为一件容器——孕育家族子嗣的容器的生存。
苏青以一种辛辣、自虐的语调叙说了这种婚姻事实。当怀青经由花轿的过渡,由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中去的时候,仅意味着女儿时代(=求学时代)那短暂的时间性存在的结束,意味着两扇门之间的“粉面朱唇,白盔白甲”式的梦想的破灭与隐没。当怀青奉献出她的女儿之身的时候,她并没有变成一个“妻子”,而只变成了一个“媳妇”,一位少奶奶,一个大家族——一个女性陈设其间、而男人来去匆匆的空间中的“第十一等B”式的存在。是婆婆(同为等外公民的“第十一等A”)的仆从,是小姑(身份未明的女人)的天敌,是真正的女佣们的准主子。
《结婚十年》的最初几幕讲述了一个老中国之女的故事,一个死者之生存的故事。她撕裂了一道重重低垂的帷幕,揭示了隐秘的女人的隐秘的生存。在觉慧们(巴金《家》)眼中,一个封建家族是一个恶魔统治的狭的笼,是永远的为“子”为“孙”的身份。那么苏青则揭示了这一闭锁空间中为“子媳”的命运。这甚至在巴金的《家》中,也是一个隐藏在好女人(瑞珏、母亲、三婶)与坏女人(姨太、四婶、五婶)类型背后的无名的存在。那不一定是悲剧,不一定是“坏狱卒”式的婆婆=封建家长)手下的凄惨的监禁,不一定是一场赤裸裸的吃人、献祭的仪式。而只是永远的周而复始,永远的期待与失落,永远的监视与无视。其中的“洞房花烛”“三日下厨”“姑嫂之间”“产房生女”,都如同一场恶俗的木偶戏,一场已遗忘了原初含义的礼仪,永远重复的台步,永远重复的位移。永远作为一个将包容宝物的容器被人们珍爱,而又永远如同一个用过即弃的容器般地被人无视与遗弃于寂寞之中。所谓少奶奶/媳妇的唯一功能是“生儿”——制造家族的男性继承人,而“育女”却只是一个语词性的点缀与无可奈何的容忍。
苏青的《结婚十年》以“个中人”的女性视点揭示了一个中国式的非核心家庭——封建大家族“内庭”中的空间性存在——女人们。除非发生了非礼式的灾变,这似乎是一个男性罕至的“地域”,这是一个由女人组成的,由女性家长——婆婆控制的,由女人间的琐屑、无聊的明争暗斗构成的世界。甚至在婚礼上怀青听到的第一个语音,看到的第一个形象也是“银色的高跟皮鞋”“银色的长旗袍”“银色的双峰”“一只怪娇艳的红菱似的嘴巴”——那是一位“嫂子”,继而则是一个“粗黄头发、高颧骨、歪头顶的姑娘”——那是小姑,未来的人家的“媳妇”,今日之媳妇命定的灾星。在这之上便是婆婆,一位说不上慈爱,但也宽容,说不上凶狠,但也严格的准家长;在这之下则是女佣、奶妈等算不上女人的仆佣。这个女人的世界除了全无意义的诸如“奉早茶”、听候呼唤之类的礼仪之外,只有对男人(丈夫们)的期待,只有为保有丈夫而互相猜忌、争斗,只有对最终从媳妇——这个珍贵的容器中取出一个男婴(男人)的期待与失落。这是一个由女人对女人的苛求,女人对女人的虐待,女人对女人的轻蔑组成的世界。苏青笔下的“生了一个女儿”几乎成了这个女性世界中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成了媳妇/产妇对这女性世界的恶意的促狭与嘲弄。女婴,似乎算不得一个婴孩,至少算不得一个“完整”的婴儿,只是一场空欢喜,“一个哑爆竹!”(《生男与育女》)于是,“好吧,先开花,后结子!”“明年定生个小弟弟!”“先产姑娘倒可安心养大,女的总贱一些。”“好清秀的娃娃,大来抱弟弟。”女婴,在这个女人的世界里也只是天生的“贱货”——“赔钱货”,只是介乎于乌有与有之希望之间的一种无名物。甚至拥挤异常的产房也成了充满不祥禁忌的“红房”,成了遗弃了产妇(还算不上母亲)的禁地。媳妇/产妇将独自留在“红房”里吞咽她的辛酸、不平、愤懑,追悔她的“无能”“失误”,藏起她的“无颜”与“耻辱”。甚至母亲的全部抚慰也只是:“拉住我的手呜咽道:‘儿呀,委屈些吧,做女人总是受委屈的,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于是乎重新开始的是再一次受孕的恐惧与期待,是再一轮的希望、痛苦、失落。在从媳妇这具容器中取出一个男婴之前,时间是空无的,有的只是如同空洞无声的“红房”一样的空间,与充不满这空间的寂寞、诅咒与淡薄的希望。直到产下一子——一个未来的男人,这空间才获得了男婴所带来的时间维度,才有了“望子成龙”,日后做婆婆,升为“十一等A”的可能。如果借用时下一个流行的短语,那么苏青的世界中便充满了“丑陋的女人”,自轻自贱的女人,自相虐待,自相残杀的女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操刀人,执行者。然而,这世界的循环往复,无名无常,隐秘丑陋都是由通常缺席的男人所规定的。男权社会将女人定义为永恒的客体、一个永远的负面、一个永恒的匮乏。于是真正的全子/家长(候补家长)才是这块空间中真正的期待/争夺/保有的对象,是这块空间的真正的能指,只有父亲/丈夫/儿子的出现才能结束女人世界的无尽而虚无的循环,才能赋予这片空间以名称和时间。苏青在她的作品序列中将隐秘的女人呈现为“丑陋的女人”,这不仅是对女性真实生存的裸露,也不仅是在新旧女性生存中挣扎的女人的自省,而是对男性话语中或“神圣”或“邪恶”或“低贱”的女性表象的亵渎、嘲弄与解构。这便使苏青超出了同时代的女作家,超出了斯托夫人式家庭女权主义——以女性/弱者的道义、人格力量去否定男权社会——传统。
用户评价
我对于“浮出历史地表”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好奇。它意味着曾经被忽视、被淹没的东西,开始重新显现。而“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则精准地指明了研究的对象和领域。这让我非常期待,这本书将会如何运用文学这个载体,去发掘那些可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被遮蔽的女性个体经验。我猜测,作者很可能会选取一些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女性文学作品,然后深入剖析其创作背景、艺术特色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我尤其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现代”的开端和范围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文学是如何从传统的束缚中逐渐走向解放和独立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让我能够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作家是如何通过她们的作品,来表达她们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的认知和思考。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来新的启发,让我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给我一种强烈的画面感:历史的厚重地表下,涌动着无数被掩埋的女性生命和思想,它们挣扎着,渴望被看见。这让我联想到很多历史事件中女性角色的模糊和被简化。我猜想,这本书会聚焦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但它的“研究”二字又暗示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读到对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动机、思想根源的深入剖析,以及她们的作品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限制、文化压力,以及她们如何以文学为武器,进行自我表达和反抗。我尤其关注那些在不同历史节点上,女性文学所呈现出的转折和变化,比如从早期对家庭、婚姻的描绘,到后期对独立人格、社会参与的追求。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女性文学是如何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自我革新,并对当时的社会观念产生影响的。它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堆砌,更是一次对女性意识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深度探索。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非常有吸引力,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中透着一股女性特有的韧性和力量。拿到手里,纸张的质感也很好,翻阅时有一种沉静而愉悦的体验。我平时就对历史题材的作品很感兴趣,特别是那些能够展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成长的故事。最近读了一些关于近代女性生活史的书籍,发现她们的生活和思想往往被忽略了,或者被简单化了。所以,当我在书店看到这本书时,立刻被它的副标题“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所吸引。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去挖掘和呈现那些可能被历史遗忘的女性的声音和经历。我期待能够在这本书中读到那些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家们的作品,以及她们是如何通过文字来表达她们的观察、感受、反思和抗争的。我希望这本书不仅能让我了解到更多关于文学本身的内容,更能让我对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思想演变以及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成就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对那些能够颠覆刻板印象、展现女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研究尤为期待,希望作者能够带领我走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那些与“现代”这个词息息相关的女性群体。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期待,更多地源于它所暗示的“研究”二字。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系统性的、深入的视角,来审视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现代”这个时期的?是以某个历史事件为开端,还是以文学思潮的转变来划分? Furthermore, 我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研究非常感兴趣。比如,西方现代女性文学和东方现代女性文学在表现形式、主题侧重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上,会有怎样的异同?这本书是否会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另外,我非常想了解,作者将如何处理“文学”与“研究”的关系。是侧重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还是更侧重于其背后的社会学、历史学、性别研究等层面的探讨?我希望它不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论著,而是能够用清晰、引人入胜的语言,带领读者去发现女性文学的魅力,去理解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闪耀的女性智慧和情感。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认识和欣赏现代女性文学。
评分我一直觉得,要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女性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她们的生活体验、情感世界,以及她们如何与社会结构互动,往往能折射出更深层、更细腻的社会肌理。这本书的题目《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光是听着就有一种挖掘和揭示的意味,仿佛要将那些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女性身影和思想,重新带到我们眼前。我尤其关注的是“现代”这个时间坐标,它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转型期,传统观念的瓦解与新思想的萌芽交织,女性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解放、困惑、挣扎与觉醒,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文学印记。我很好奇,这本书会选取哪些代表性的女性作家或作品?她们的创作背景又是怎样的?她们的作品在当时社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否也如同书名所暗示的,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声音,通过文学的载体,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关注和解读?我渴望通过这本书,了解现代女性文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以及它如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中获得对历史和人性的更全面理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百千大阅读·一年级上册 为天量身高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807/5b34872dN7ad66fa7.jpg)
![百千大阅读二年级上册风的握手 [7-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809/5b34863aN1eecfda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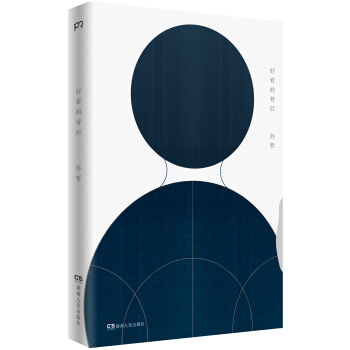





![沃尔夫金色童书·儿童睡前故事:最动人的神话传说+最欢快的动物故事(套装全2册)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3895/5b20cfabN7b94da93.jpg)



![侏罗纪世界2 [8-1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5353/5b14e261Ne8fa75f2.jpg)
![侏罗纪世界1+2(套装共2册) [8-1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5383/5b14e281N9fbe6d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