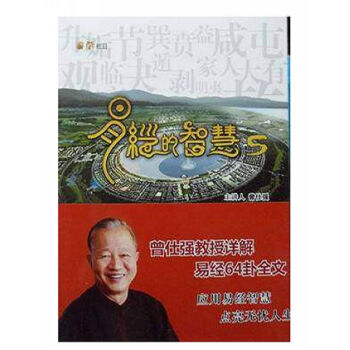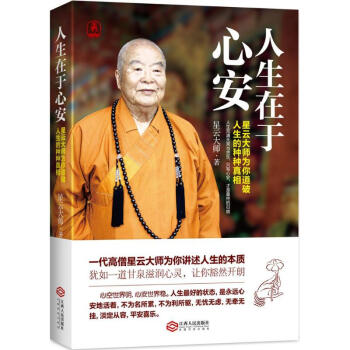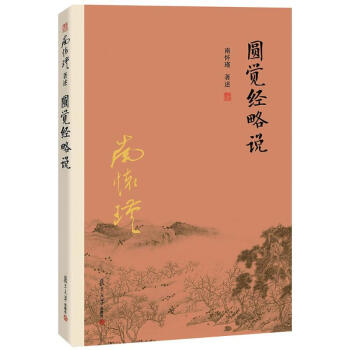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本书仍旧延续了格尔茨著作所具有的才华横溢的特征,体现了文化解释学的研究路径。该书稿零散地探讨了格尔茨在一生中所感兴趣的政治哲学、心理学和宗教问题。这些论述直接关系到后现代主义和当代多文化主义的“微光”(即书名《烛幽之光》之意),通过这些微光,读者可以了解格尔茨的思想历程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录了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11篇文章,探讨了11个主题。所这些探讨的主题,既体现了格尔茨的个人研究兴趣,同时又是可以与读者共通的。涵盖面包括从维特根斯坦到雅加达的宗教,从艺术到政治,从文化战争到今天夏威夷、斯里兰卡、巴尔干的种族冲突,从道德相对主义到文化差异、心理差异和认知差异之间的关联。作者简介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1956年,他以《爪哇宗教》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博士称号。格尔茨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代表作有《文化的解释》等。目录
序…… 0011 转向和机遇:我的学术生活…… 001
序曲…… 001
泡沫…… 001
改变主题…… 010
等待时间…… 019
2 思想是一种道德行为:新兴国家中田野工作的伦理层面…… 020
3 反“反相对主义”…… 040
4 多样性的用途…… 069
5 最新动态的评论…… 092
蹒跚而入…… 092
文化战争…… 101
深度游荡…… 112
历史学与人类学…… 126
“地方性知识”及其限度:一点附带意见…… 144
6 奇怪的疏离:查尔斯?泰勒与自然科学…… 152
7 托马斯?库恩的遗产:适当时机的适当文本…… 170
8命运的困厄:作为经验、意义、认同和权力的宗教…… 178
9 失衡的行为:杰罗姆?布鲁纳的文化心理学…… 200
10 文化,心灵,大脑/ 大脑,心灵,文化…… 217
11 破碎的世界:世纪末的文化与政治…… 233
破碎的世界…… 233
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一个民族,那它是什么?…… 247
一种文化如果不是共识,那它是什么?…… 265
索引…… 281
前言/序言
序如果有两门学科,它们的范围都界画不明,又都自诩要穷究全部人类生活和思想,那它们的彼此猜疑可就不止一星半点。人类学和哲学恰是这种情形。一种散乱冗杂的学术认同,与将几乎一切事物与别的一切联系起来并直探事物根底的一种抱负相结合,这让它们二者都忧心忡忡,拿不准谁该做什么。并非是它们界线重叠,而是没人能够稍有把握地绘出它们的界线。也并非是它们旨趣殊途,而是没有东西明显见斥于它们之一。
这两个领域通常为了最终定论和最先创见,婉转地、暗暗地较着劲,但除此之外,它们共享了其他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困扰着它们的相互关系,给它们之间的合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特别是它们都容易被渗透而陷入险境,虚弱而遭到围攻。眼下它们就发现自己不断受到不速之客的侵入和纠缠,后者宣称可以比它们自己更有效地从事它们的工作,因为它们落入陈陈相因的窠臼不能自拔。
对哲学而言这不是新鲜事了。哲学史充塞着这样的事情:它的保护领地和封邑,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后来甚至逻辑学和知识论,都相继脱离它,成为独立自主的特殊科学。对人类学来说,因分离主义压力而收缩统治权,这是较近的事情,也不那么秩序井然,但同样严重。自19世纪中叶以来,它给自己划了一块x特别的地盘,就是研究文化“那个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一员的人所习得的——信仰、道德、法律、习俗”。而今它却发现,各种临时拼凑、坐享其成的新兴学科、半学科和发展中的学会(性别研究、科学研究、酷儿研究、媒体研究、族群研究、后殖民研究,它们被松散地归类为“文化研究”,这是人类学的最后羞辱),群集到它曾千辛万苦、勇猛无畏地开荒拓土的这片空间上来,着手工作了。不管是像一家古老而名高誉隆的控股公司,它的股份和名誉正在慢慢溜走,还是像一桩智识的高冒险事业,遭到偷猎者、暴发户和食客们的明抢暗夺,总之分散和分裂感以及“终结”感是与日俱增了。这不是大度地互动和联手的特别恰当的局面。
不过,这样互动与联合的努力依然颇值一试。忧惧被夸大其辞了,猜疑也无根无据(哪个领域都还没打算各走各道,它们在风格或脾性上的敌对程度,也不像它们大嗓门的捍卫者喜欢设想的那么严重),不仅如此,它们如今其实同样穿流在后现代海洋之中,这片海域波涌浪翻,不见航道,使它们越来越需要相互扶助。无论对哪种事业而言,目标并非举目可望,或在附近什么地方;丧失目标,为寻找方向和根由而折腾乱窜,才是近在眼前。我本人有志于拉起或加固一条连线,或者——想想蒙田或孟德斯鸠——也许是复兴一条连线。这种志趣既不是源于我动了改换专业认同的什么心思,五十年来我拼命建立起我的专业认同,今天我对它要多惬意有多惬意了;也不是源于有心要拓宽这种认同,成为某种高级的无专长思想家。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民族志学者,是个讨论民族志的作家,我不制造理论体系。但是这种志趣可能以某种方式牵连到这一事实:如我在开头一章所解释的,我起初动手“搞哲学”,但过了短得丢人的一段时间后,我放弃了,想让我的思想更直接地,像我过去认为的一样,扎根于世界的多变性上。那时我关心的、也是我想从经验上而不仅从概念上追索的种种议题——观念对行为的影响,“意义”的意义,对“判断”的判断等——萦回在我论爪哇宗教、巴厘国家和摩洛哥市场的作品中,也在论现代化、伊斯兰教、亲属关系、法律、艺术及族群的作品中被延展和重新表述过了,而且我相信被充实、具体了。这里汇集的“省思”,正是这些关怀和议题稍微明白一点的表达。
悖反的是,我所做的那种工作,即查明他族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与哲学家们——或者至少是打动我的那类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即通盘研索人类经验的范围和结构及其特征,这二者今天要加以联系,比我憧憬自己朝着哲学家生涯进发的20世纪40年代末,在许多方面都更容易。就鄙见看来,这主要是因为自那时以来,哲学家们——或者起码他们的绝大多数——构想他们职业的方式有了较大转变,那种转变的方向与像我这样的一些人特别投缘,我们都相信,我们的大部分普遍问题——为何?如何?什么?何方?——如果有答案的话,答案要到鲜活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去寻找。
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如果不是促成它的话——的主要人物,再次就鄙见看来,是身后令人头脑一新的造反者,“晚期维特根斯坦”。1953年——他去世两年之后——《哲学研究》出版了,在牛津剑桥以外一度不过是耳闻的东西,转换成了明显具有无尽生成潜力的文本,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对自己想干什么、希望实现什么的看法,随后几十年间,“评论”、“大事记”、“笔记”和“纸条集”等从维氏未发表的遗著中纷纷整理出版,也让我深受影响。在耕耘于人文科学领域、试图从他们那被堵塞的捕蝇瓶里找到出路的人们中间,像这种遭遇并非唯我一人。但是我的确算是对接受这一讯息预先准备得较为充分的人之一。人们常说,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师的那些作家,就是这样的人:有些话早在我们舌尖打转,我们自己却难以表达,而他们似乎终于说出来了;我们心智的动作、趋向和冲动刚刚起步,他们已经形诸言语了。如果此话当真,那么我非常高兴承认维特根斯坦就是我的大师,或者说无论怎样也是大师之一。
当然他以德报德,承认我是他的门人,这太不可能了;他可不大喜欢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赞同或理解。不管怎样,他对私人语言这种观念的抨击,将思想从它的头脑洞穴中带到了人们可以看见它的公共广场上;一旦它作为一套实践来到那里,他的语言游戏观又提供了看待它的新方式;他建议将“生活形式”当作——引用一位注释者的话说——“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复合体,对世界的任何一种特定理解,都是以那些环境为先决条件的”。所有这一切,简直就像是为促成我和跟我同好的其他人所从事的那种人类学研究量身定做的。这些观念当然有种种伴奏和推论追随左右:“依据一种规则”,“别寻找意义,寻找用法”,“哲学的整片云浓缩成语法的一滴雨”,“说话和表现”,“家族相似”,“图像俘虏了我们”,“看作”,“大致站在那里”,“回到粗糙的地面”,“面相盲”,“我的铁锹挖不动了”,等等,它们不是那么有为而发,却是对哲学发动的一场无情的颠覆性批判的组成部分。然而恰是这场批判,或多或少缩小了哲学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距,极力去发现人们——一群群的人,单个的人,作为整体的人民——如何在谈话当中,将个别的、斑驳的声音聚而为一。缩小——或者也许仅仅是探明和描述——这种差距的途径,由上述警句中对一线人类学家而言最具诱惑力的那一句提示出来:“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维特根斯坦写道:“我们站立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那么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去吧!”《哲学研究》(,第107则)人类学——虽然当然不止人类学——是在探索这粗糙的地面,在那上面维特根斯坦或别的其他人的思想才可能获得附着摩擦力:对我来说,这种看法不仅本质上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观念,而且正是这个观念,虽然目标未定,阐述不明,引导我自始即迁移到人类学这个“领域”和“田野”。我厌倦了在康德式、黑格尔式或笛卡尔式冰流上乱滑,我想行走。或四处游逛。穿越各种地方和人民而游走,就他们可能提供的对可能出现的任何难解之谜的不管什么见识,没完没了地找出差异性和恒定性,在这过程中,我们所生产的,与其说是一种立场,对一组固定议题的一种稳步积累的观点,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立场确定——形形色色目标的形形色色论证。这就留下大量的(也许是大多数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但在这点上,我们也在追随维特根斯坦:他写道,有人会问:“‘一个模糊的概念究竟是不是一个概念?’——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是否仍是某人的肖像?用一张清晰的照片替换一张模糊的照片,是否总是有好处?难道模糊的照片不会刚好是我们需要的吗?”(《哲学研究》,第71则)不管是抑或不是,也不管“我们”可能是谁,后面诸篇是各色各样不过略加编排的一组评注、实例、批评、反思、评估和探究,它们牵涉起码还算得上“哲学的”问题和人物——“相对主义”,“心灵”,“知识”,“自我”,泰勒,罗蒂,库恩,詹姆士。差不多是介绍性的首章评论了我的专业生涯飘忽不定的发展,那是为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学术人生”系列讲座准备的;此后接下来的三章谈到了开展田野工作当中升腾起来的道德焦虑,人类学中最近流行的某种所谓反相对主义主张,以及对道德哲学中捍卫文化地方主义的某些论调的批评。第5章“最新动态评论”,汇集了五篇即兴短论,它们论及目前人类学内部和周边发生的道德和知识论争讼。随后四章,是对查尔斯?泰勒、托马斯?库恩、杰罗姆?布鲁纳和威廉?詹姆士著作的较为系统的思考,这是为纪念他们的专题论文集而作的。第十章“文化、心灵、大脑……”,仍是要再次思考(据称是)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显然是)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可能)关系。最后是“破碎的世界”,涉及最近“族群冲突”高涨给政治理论出的那些难题。通常大概这个时候就该志谢了。关于志谢,迄今我有那么多人要感谢,我可不愿冒因列出名单而漏人的风险。反正他们大多数人以前都已谢过了。作为替代,我只将本书题献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我的那些合作者们,书里几乎一切东西最先都是在那里写出来讨论,改写后再讨论,也是在那里,我们同心协力创造出了一个值得守护的地点和态度。为了防止他们或别的什么人多想,他们的名字,是以沿着走廊距离我的办公室的远近为序,排列出来的。
普林斯顿1999年8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是震撼与回味并存。它不是一本读完就能立刻总结出三点论的快餐读物,它更像是一段漫长的、需要沉淀的旅程。每一章似乎都在为下一章铺设更坚实的基础,最终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关于人类认知建构的立体模型。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启示”,即如何用跨文化、跨历史的视野来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读到最后,我甚至开始对那些在哲学史中被反复讨论的公理产生怀疑——这些“公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究竟是多么短暂的现象?这本书成功地将人类学中对“差异”的尊重,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用以解构哲学中对“普遍性”的迷恋。它促使我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框架,去真正地“看见”那些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生存智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智力探险。
评分不得不提这本书的文风,它有一种沉静而有力的力量感。与其他探讨人类心智与文化的书籍相比,这本书的叙述节奏显得更为舒缓,但绝非拖沓。作者似乎深谙“少即是多”的哲学,很多关键的转折点都是在看似不经意的观察中完成的。比如,在讨论某种边缘社会对“梦境”的理解时,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了当地人如何处理梦境中的信息,但这种处理方式,却间接地挑战了笛卡尔以来对“清醒意识”的绝对权威性。我喜欢这种不动声色地瓦解既有框架的方式,它不咄咄逼人,而是通过展示替代性的、同样有效的世界模型,来邀请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整本书读下来,就像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深度清洁,那些平日里被我们奉为圭臬的观念,在这些异质文化的映照下,开始显露出它们偶然性和历史性的面貌。这种阅读体验,远比直接的哲学说教来得深刻和持久。
评分从专业角度看,这本书的资料引用非常扎实,但处理得极为高明。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堆砌大量的脚注和引文来展示博学,而是将人类学的田野资料内化为论证的血肉。阅读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不同文化人类学家的思想脉络的掌握程度,从早期的结构主义到后来的后殖民批判,都有所涉猎,但所有的引用都服务于“烛幽之光”这个核心目标——即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照亮哲学深处的幽暗角落。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工具理性”的剖析,作者没有像许多批判理论那样陷入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而是展示了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那些看似“非理性”的实践,如何构建了比现代工具理性更为稳定和适切的生存秩序。这让我意识到,评价一个知识体系的好坏,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具体生存场域来空谈。这本书真正做到了跨越学科的壁垒,提供了一种更具韧性和适应性的思考工具。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倒是很别致,那种深邃的靛青色调和边缘泛着微光的排版,让人一眼就觉得里面藏着不少引人入胜的思辨。我最初翻开它,是抱着一种探寻人类文明根源的好奇心。我一直觉得,我们讨论的那些宏大叙事,比如道德、真理、时间观,最终都得落脚到那些最朴素的群体生活方式上。这本书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没有陷入纯粹的形而上学泥潭,而是试图用一种更贴近“人”的视角去解构那些高悬的哲学命题。那种将抽象理论还原到具体仪式、神话结构乃至日常行为模式中的尝试,读起来非常过瘾。尤其是作者在描述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存在”的不同理解时,那种细腻的笔触,仿佛带我穿梭于不同的时空部落,亲身体验他们的世界观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我特别欣赏它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没有牺牲掉文字本身的魅力,读起来有一种在广袤的田野上考察,又同时沉浸在古老智慧中的奇妙感受。它像一面镜子,让我开始反思,我所坚信的“理性”,是否只是特定文化演化出的一种优势策略,而非宇宙的必然真理。
评分这本书的论证脉络非常清晰,简直是一次逻辑上的马拉松。我通常对这类跨学科的作品持保留态度,因为很多时候它们要么偏重哲学,让社会学的部分显得单薄,要么就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描述过于冗长,冲淡了理论的锋芒。但《烛幽之光》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平衡。它像一个技艺高超的织工,将来自不同文化人类学的案例——比如关于时间感知的差异,或者特定图腾崇拜背后的权力结构——精心地编织进对传统西方哲学核心概念的批判之中。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关于“他者性”的章节,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文化相对主义上,而是深入挖掘了部落社会中“我群”与“彼群”边界是如何在仪式和禁忌中被动态地确立和维护的。这不仅仅是对理论的补充,更像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次温柔而坚定的“降维打击”。读完这一部分,我感觉自己对“何为人”这个古老命题的理解,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它不再是书斋里的思辨,而是活生生的、充满张力的社会互动产物。
评分书脊都烂了,居然还好意思封包皮。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凑单买的。
评分看看,了解……哈哈
评分书脊都烂了,居然还好意思封包皮。
评分看看,了解……哈哈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凑单买的。
评分一个儿子的足球之光,一直想买的一本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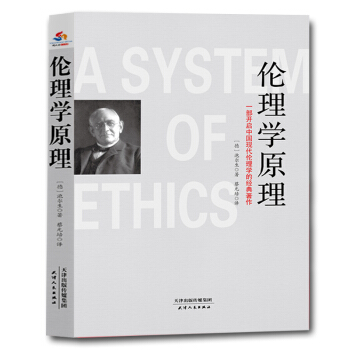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信仰十讲: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Ten Lectures on Marxism Belief]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2130/5b0bbbf0N8ea0f2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