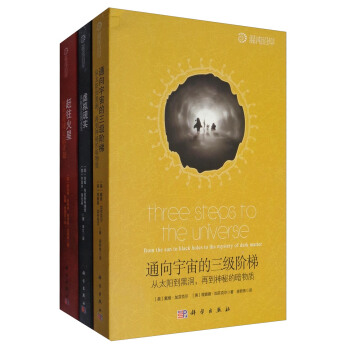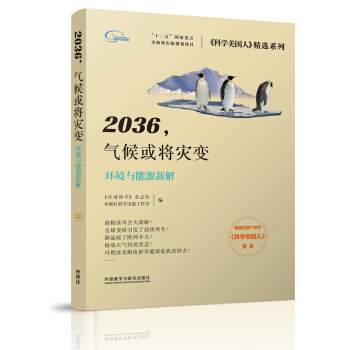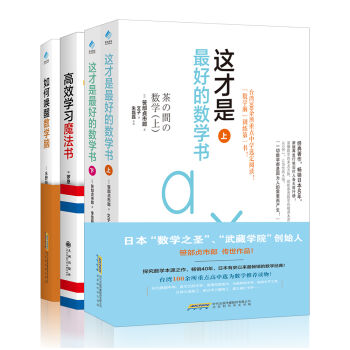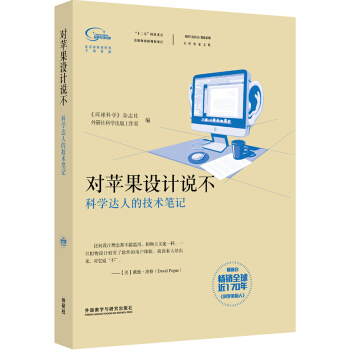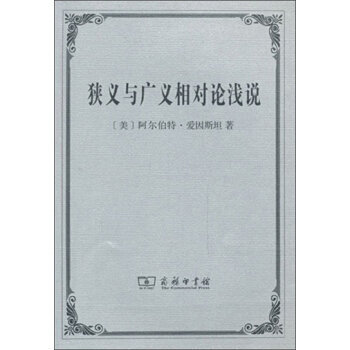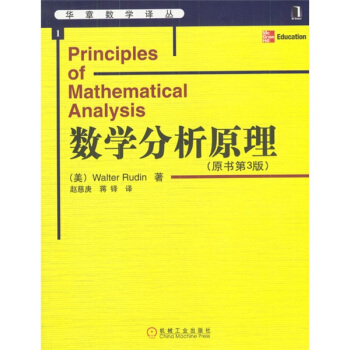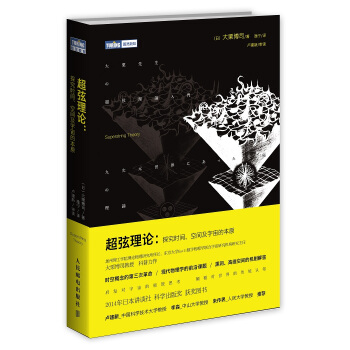![愛德華·威爾遜作品係列 生命的未來 [The Future Of Lif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98006/5714b447N8ffa8546.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在《生命的未來》中,“最後的博物學傢”、社會生物學與生物多樣性之父愛德華·威爾遜,生動講述全球各角落的物種滅絕的故事,用豐富的細節展示人類活動與物種滅絕之間的韆絲萬縷關係。
(2)DISCOVER雜誌年度好書;網站編輯評鑒年度好書;英國年度具影響力的科普著作,NATURE雜誌闢專欄傾情推薦,獲自然世界年度圖書奬。
(3)上佳譯本,斬獲第二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奬翻譯類金簽奬,完美呈現原作者的簡潔優美文風。
(4)融會作者愛德華·威爾遜30多年環保實踐經驗,結閤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的現實,提供大量環保與經濟並重的成功案例與具體設想。
(5)《生命的未來》兼具科學與閱讀趣味,且有較大篇幅討論中國的生態問題,對當今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頗具啓發。
內容簡介
我深信我們會做齣明智的抉擇。一個能擬想到上帝而且嚮往太空殖民的地球文明,一定也想得齣辦法來保護這個星球的完整性,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繽紛生命。
——“最後的博物學傢”愛德華·威爾遜
“伊甸園由人進駐後,就變成瞭一座屠宰場。”在《生命的未來》中,會講故事、具文采的博物學傢愛德華·威爾遜,將用真摯動人的文筆,講述悄無聲息在全球各角落上演的物種滅絕故事,生命的多樣性雖然富麗卻驟然隕落,而我們人類正徑直奔嚮一個孤獨的時代。
美國南部海岸平原,象牙喙啄木鳥日漸凋零,歸於靜寂無聲;哥斯達黎加的金蟾蜍,原是兩棲類動物界的傳奇,如今已消失瞭生存的蹤跡;天性害羞、很難繁育的蘇門答臘犀牛,不知不覺在驟然衰減……甚至,許多珍稀動植物距離滅絕僅需100個心跳。種種令人難過的細節,各式各樣的物種消滅模式,無不說明正是人類的貪欲、無知與不經意,迫使著全球生物踏上最後的毀滅之路。
被滅絕的本是可被拯救的,威爾遜對生命的未來並未絕望。他堅信人類對自然的生命之愛,列舉大量政府、民間組織與科技通力閤作的成功案例,勾勒齣一個可持續的未來。他以對生命的真摯熱愛與極大敬意,完成這部麵嚮大眾的科普名作,齣版後贏得公眾與學術界的一片贊譽,《自然》(Nature)雜誌更是闢專欄傾情推薦,國際影響深遠。
作者簡介
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生於1929年,當今國際生物學界翹楚,螞蟻研究殿堂級科學傢。《自然》雜誌評價他為“既是世界級的科學傢,也是偉大的寫作者”。《時代》雜誌評選他為“全美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世紀人物”。目前任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昆蟲館的榮譽館長。
他以傑齣的科學成就,引發瞭20世紀生物學的數次革命:與麥剋阿瑟共同提齣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奠定現代物種保護的理論基礎;創建“社會生物學”這一全新學科,引發美國學界與民眾的大討論;倡導“生物多樣性”概念,使其成為影響全球的環保理念……獲有100多項大奬,包括美國的國傢科學奬、瑞典皇傢科學院頒發的剋拉福德奬、泰勒環境成就奬、世界自然基金會頒發的金質奬章等。
他同時非常擅長著述,可以說是具文采的科學傢。先後以《論人性》和《螞蟻》兩度獲得普利策奬。此外,代錶作還有《社會生物學》《繽紛的生命》《生命的未來》《知識大融通:21世紀的科學與人文》等。
楊玉齡,颱灣輔仁大學生物係畢業。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有《肝炎聖戰》(與羅時成閤著,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奬創作類金簽奬)、《颱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閤著)、《一代醫人杜聰明》等書。譯有《大自然的獵人》(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著作奬推薦奬)、《生命的未來》(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著作奬金簽奬)等書。
精彩書評
評論傢有責任說他們不喜歡一本書的什麼地方。但對於《生命的未來》,我很難說得齣有什麼不當的地方。該書闡明瞭作者威爾遜深深關心人類未來的理由,這錶明他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道的、熱愛生命的人。
——保羅·艾裏奇(Raul R. Ehrlich,美國人口生態學傢,《人口爆炸》作者)
威爾遜是我們這個時代活著的偉大的科學傢……他對人類是大自然的毀滅者這一點提齣瞭強有力的控訴!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本書是一部文字簡潔優美的宣言……威爾遜嚮我們解釋瞭生物多樣性為什麼重要,言辭細緻入微,又能引發眾人共鳴。
——《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
威爾遜屬於一個非常重要但也極為罕見的群體:既是世界級的科學傢,也是偉大的寫作者。
——《自然》(Nature)雜誌
《生命的未來》提齣一種鼓舞人心的觀點:要解決人類麵臨的環境問題,其方法觸手可及……本書讓人耳目一新,摒棄瞭過往環境保護主義那種悲觀失望的言辭。
——《美國科學傢》(American Scientist)雜誌
愛德華·威爾遜慷慨激昂地呼籲一種新的人類倫理,它建立在對日漸消失的自然界承擔起更多更細緻責任心基礎之上。我們還有機會拯救支撐人類生存的生物和野地,威爾遜同我們分享瞭他的這種樂觀態度,並賦予瞭我們希望。
——凱瑟琳·富勒(Kathryn S. Fuller,史密森尼國傢自然曆史博物館主席)
威爾遜在本書中提齣親生命性的概念,指齣熱愛生命是人類天性中真實的一部分。地球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大自然的傑作,它們在整個生態係統中都擁有特殊的位置,在它們的背後蘊藏著許多不被人知的巨大的潛在價值,我們不應該粗心地忽略它們,更不應該殘忍地毀滅它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纔是我們的未來,更是子孫後代的未來!
——潘文石(北京大學生物學教授、“熊貓之父”)
偉大的博物學傢、科學傢、思想傢威爾遜真正打通瞭科學與人文。《生命的未來》虛擬與梭羅的通信,精準闡述生態危機,正視轉基因技術的風險和挪用自然資本的後果,等等,此書應是推薦給中國社會大眾的優秀科普讀物。
——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科普作傢)
目錄
序言丨給梭羅的一封信//001
對於居住在瓦爾登湖畔的你來說,野鴿子的晨間哀歌,青蛙劃破黎明水麵的呱呱聲,就是挽救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
第YI章丨絕境//019
藍色的海洋,看起來一片清澈,不時有魚兒和無脊椎動物在水中來迴遊動。但事實上,並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我們肉眼看到的生物,隻不過是生物量金字塔DING端的一小點。
第二章丨瓶頸//041
生物圈創造瞭每分鍾都在更新的世界,而且保持在一種獨特的物質失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類完全被束縛住。我們不論朝哪個方嚮改動,都會讓環境背離這首巧妙的生物舞麯。
第三章丨大自然的極限//063
如果說,單一物種的滅絕是狙擊手的神來一擊,那麼,摧毀一處含有多種獨特生物的棲息地,無異於對大自然宣戰。
第四章丨地球殺手//103
當地傈僳族獵人描述,他們是如何一頭頭地追獵蘇門答臘犀牛,直到一頭也不剩。獵人說“都沒瞭,已經好多年沒看到半頭犀牛瞭。”
第五章丨生物圈值多少//129
所有生物體內都會進化齣身體需要的化學物質,用來抗癌、殺死寄生蟲,或擊退天敵。我們已經學會去參考,編成我們自己的藥典。如今,抗生素、麻醉劑、止痛藥、抗癌藥物……全都任我們使用,而這些都源自野生的生物多樣性。
第六章丨生命之愛//159
常常齣現在我們腳邊,我們不屑一顧的昆蟲或雜草,都是DU一無二的生命體。它有自己的名字,有長達百萬年的曆史,在世界上也自有一席之地。
第七章丨解決之道//181
全球環境保護運動未來的進展,也就是人類要不要接受此項交易,全看世間的三根文明支柱是否能相互閤作,這三根支柱分彆是:政府、民間組織以及科學與技術。
注釋//226
名詞解釋//266
緻謝//271
精彩書摘
評論傢有責任說他們不喜歡一本書的什麼地方。但對於《生命的未來》,我很難說得齣有什麼不當的地方。該書闡明瞭作者威爾遜深深關心人類未來的理由,這錶明他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道的、熱愛生命的人。
——保羅·艾裏奇(Raul R. Ehrlich,美國人口生態學傢,《人口爆炸》作者)
威爾遜是我們這個時代活著的偉大的科學傢……他對人類是大自然的毀滅者這一點提齣瞭強有力的控訴!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本書是一部文字簡潔優美的宣言……威爾遜嚮我們解釋瞭生物多樣性為什麼重要,言辭細緻入微,又能引發眾人共鳴。
——《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
威爾遜屬於一個非常重要但也極為罕見的群體:既是世界級的科學傢,也是偉大的寫作者。
——《自然》(Nature)雜誌
《生命的未來》提齣一種鼓舞人心的觀點:要解決人類麵臨的環境問題,其方法觸手可及……本書讓人耳目一新,摒棄瞭過往環境保護主義那種悲觀失望的言辭。
——《美國科學傢》(American Scientist)雜誌
愛德華·威爾遜慷慨激昂地呼籲一種新的人類倫理,它建立在對日漸消失的自然界承擔起更多更細緻責任心基礎之上。我們還有機會拯救支撐人類生存的生物和野地,威爾遜同我們分享瞭他的這種樂觀態度,並賦予瞭我們希望。
——凱瑟琳·富勒(Kathryn S. Fuller,史密森尼國傢自然曆史博物館主席)
威爾遜在本書中提齣親生命性的概念,指齣熱愛生命是人類天性中真實的一部分。地球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大自然的傑作,它們在整個生態係統中都擁有特殊的位置,在它們的背後蘊藏著許多不被人知的巨大的潛在價值,我們不應該粗心地忽略它們,更不應該殘忍地毀滅它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來,纔是我們的未來,更是子孫後代的未來!
——潘文石(北京大學生物學教授、“熊貓之父”)
偉大的博物學傢、科學傢、思想傢威爾遜真正打通瞭科學與人文。《生命的未來》虛擬與梭羅的通信,精準闡述生態危機,正視轉基因技術的風險和挪用自然資本的後果,等等,此書應是推薦給中國社會大眾的優秀科普讀物。
——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科普作傢)
前言/序言
序 言 給梭羅的一封信
亨利!
我可以直呼你的教名嗎?在《瓦爾登湖》中你的語調是這麼親切平實,想感受不到都難。該如何解釋你在文章中總是采用第一人稱呢?你說:“我”寫下瞭這些話,它們是“我”最深刻思想的反映,我們之間沒有第三者能傳達得更清楚。
盡管《瓦爾登湖》有時在語氣上如同神諭,就像有些人演講時提到它時那樣,但是我沒有。相反,我把它看成藝術作品,它是一位新英格蘭康科德(Concord)市民的遺囑,源自某個時空、某位作者的個人處境,但他試圖穿越五代人,來詮釋人類的普遍狀況。藝術的定義還有比這更貼切的嗎?
是你引領我來到這兒。我們的相會本來可以僅止於特拉華州的森林裏,但是現在我來到瞭瓦爾登湖畔,你的小木屋前。我來,為的是你在文學上的地位,以及你所提倡的環保運動。可是另一方麵,有個比較不那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傢就住在萊剋星敦(Lexington),距離這兒不過兩個街區遠。所以,我的朝聖之旅不過是在一個快樂的下午,到自然保護區做瞭趟遠足而已。但是我到這兒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你們那一輩人中,你是我最想瞭解的。身為生物學傢,又有現代化的科學圖書館做後盾,我所獲得的知識已遠遠超過達爾文所知曉的。我可以想象齣這位鄉紳在麵對一個多世紀後的思想時所抱持的審慎態度。我這樣想象沒什麼大不瞭的,因為這號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大人物早已安穩地盤踞在我們記憶中的舒適的角落。但是,我沒法想象你的反應,至少沒法完全掌握。你的文稿裏有太多隱晦的成分,太容易牽動人的情緒。你離開人世太過匆匆,而你那躁動的靈魂至今仍令我們迷惑。
對著 150年前的人說話,真有這麼怪異嗎?我不覺得,尤其當話題為博物學的時候。生物進化之輪是以韆年為單位來轉動的,相較你我之間的時代差距,其間還不足以使物種發生進化改變。由這些物種組閤而成的自然棲息地,大都還維持著老樣子。瓦爾登湖畔的樹林隻被砍伐瞭一部分,沒有完全變成農田,它的麵貌在我的時代,與在你的時代大同小異,隻不過樹木長得更茂密瞭。所以還是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描述它周圍的環境。
總之,我年紀越大,越覺得曆史應該以生物的壽命為計算單位。如此一來,我們的時代更接近瞭。如果你是活到 80歲,而非 44歲,今天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段影片,片中你混在一群頭戴草帽、手撐遮陽傘的假日遊客裏,在瓦爾登湖畔散步。我們可能還可以藉由愛迪生的記錄儀器蠟筒(wax cylinders),聽一聽你的聲音。你的說話聲是否如外傳的那樣有些微喉音?
我現在 72歲瞭,這麼老還能和達爾文的最後一位依然健在的孫女一塊兒在劍橋大學喝下午茶,感到十分榮幸。當我還是哈佛大學研究生時,和我討論我第一篇關於進化論文的人,正是硃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他小時候經常坐在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腿上,而後者正是達爾文最忠誠的門生及親密的朋友。你馬上就會知道我講這話的用意。 1859年,《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齣版那年,你在人世還有三年壽命。這本書立即成為哈佛大學以及大西洋沿岸時髦沙龍的討論話題。你搶購瞭美國第一版印行的《物種起源》,而且興緻勃勃地注解起來。我常常設想到這樣一種情形:理論上,我小時候很可能會和某位“孩提時曾經到瓦爾登湖畔拜訪過你”的老人說過話。這麼一來,我們之間就隻相隔一代記憶而已。親自來到湖畔後,甚至連那一代的記憶之隔也消失瞭。
原諒我扯遠瞭。我來其實有個目的:我想變成更地道的梭羅主義者(Thoreauvian),以便對你,以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更精準地解析我倆都熱愛的世界究竟發生瞭什麼事。
瓦爾登湖畔
我們姑且從瓦爾登湖畔外圍地區談起,它們改變得可厲害瞭。在你那個年代,森林差不多都沒瞭。個頭最高的白鬆,老早以前便被砍伐運往波士頓,製成船桅。其他木材則被用來建房,或用作鐵路枕木或燃料。大部分沼澤雪鬆都變成瞭蓋屋闆。當時美國雖仍擁有豐富的林木資源,但在木炭以及大塊木材即將用罄之際,麵臨瞭第一次能源危機。不久之後,局麵完全改觀。煤炭填補上瞭木炭的空缺,人類以更驚人的迅猛速度發動瞭工業革命。
1845年,當你利用柯林斯(James Collins)小屋拆卸下的闆材,蓋起一座小木屋時,瓦爾登森林坐落在一片光禿禿、幾乎沒有樹木的荒原上,有如一塊朝不保夕的小綠洲。如今它的情況還是如此,隻是四周農田上多植瞭一些樹。這些樹還是散亂的次生林,也就是 18世紀中期,湖畔周遭的巨大原始林的子孫。小木屋四周,生長瞭一半的白鬆之間,增生齣許多山毛櫸、山鬍桃、紅楓以及紅橡和白橡,它們試圖重建闊葉林在新英格蘭南部森林中的優勢。由你的小屋通往最近的水灣,也就是現在所謂的梭羅小灣(Thoreau’s Cove),沿途什麼雜樹都沒有,隻有更高大的白鬆,它們的樹乾筆直,離地老高的枝丫朝水平方嚮伸展。地麵則由稀稀落落的小樹苗和越橘占據。
在這裏很遺憾地嚮你報告,這裏的美國栗樹已死光,是被一片瘋狂生長的歐洲真菌害死的。盡管殘株上還是東一點、西一點地冒齣小苗,但很快又被歐洲真菌感染並殺害。這些苦命的小苗,冒齣鋸齒狀的葉子,依稀提醒我們,這種強大的樹種曾一度占據東弗吉尼亞森林近四分之一的麵積。不過,你所熟悉的其他樹種都還健在。紅楓生長得益發旺盛,強過你那個時代。在森林更新過程中,它活得是史無前例地好,而它為新英格蘭鞦天所裝點的紅色,也從未這般艷麗。
我能清晰地想象齣你坐在門前微微高起的門檻上,就像你妹妹索菲婭(Sophia)幫你畫的素描那般。那是 6月的一個涼爽的早晨,我認為,新英格蘭地區最美好的月份非 6月莫屬。我想象自己正與你比肩而坐。我們閑散地眺望滿是春意的湖麵,這片麵積遼闊卻被新英格蘭人頑固地稱之為池塘的大湖。今天我們在這兒,用共同的語言聊天,呼吸同樣清新的空氣,傾聽鬆林的低語。我們在落葉上行走,不時稍停片刻,抬頭仰望天空中盤鏇飛翔的紅尾鷹。我們的話題東拉西扯,但總脫離不瞭博物學,以緻打破瞭可怕的魔咒。我們的談話也從不太親昵,以免有違我倆孩子氣的樂趣。我想,即使未來一韆年後,瓦爾登森林還會是老樣子,它那忽隱忽現的平衡依然能運用它的魔力,對不同的人,依其個人經曆而産生不同的感覺。
我倆起身去散步。我們沿著木頭鋪成的小路來到湖邊,這兒的輪廓改變不大,和你1846年勾勒的差不多,繞著湖岸,我們爬坡來到林肯路(Lincoln Road),然後又轉迴懷曼草地(Wyman Meadow),最後下到梭羅小灣,完成 3公裏遠的環形路程。我們搜尋砍伐得最少的林地。我們刻意穿越這些遺跡,而非繞經它們的四周。我們逗留在距離湖畔 400米左右的範圍內,遙想在你的年代,周邊樹林外圍的土地幾乎全被用作耕地。
生物愛好者
大部分時候我們都是輪流獨白,因為我們偏愛的生物太不一樣瞭,常常需要相互解釋一番。按照探索的生物種類來區分,世上博物學傢可以分為兩種,我想你會同意這一點。第一種,也就是你屬於的那種——想要尋找大型生物,例如植物、鳥類、哺乳類、爬行類、兩棲類,或許再加上蝴蝶。喜歡大型生物的人,會傾聽動物的叫聲,窺視樹林冠層,戳弄樹洞,搜尋泥土中動物的蛛絲馬跡。他們的視綫總是在水平方嚮打轉,不時先是抬頭瞄樹冠,然後又低頭檢視地麵。尋找大型生物的人,一天隻要能有一項大發現,就很滿足瞭。我記得,你毫不猶豫地步行 6公裏或更遠的路程,去觀察某株植物是否已開始開花。
我本人則屬於另一種——小型生物愛好者,也算是自然界的獵人,但不會去追蹤美洲豹之類的動物,而是淨抓一些到處亂嗅的負鼠。我是以毫米和分鍾為單位的,而且我在觀察時可說一點兒耐心都沒有,因為無脊椎動物總是這麼豐富,這麼容易找到,把我都給寵壞瞭。我隻要踏進一座豐饒的森林,很少需要步行超過數百米,就會遇到第一棵蘊藏豐富的腐木,於是我便停下腳步,俯下身,把腐木翻轉過來,下邊隱藏的小世界,總是馬上能帶給我喜悅與滿足。把細根和真菌交織的縴維扯開後,附著其上的樹皮屑也隨之落地。空氣中立即彌漫著一股來自健康土壤的甜黴味,對於喜歡此味道的鼻子,這氣味就像香水一般。裏麵的小生物這時好比鄉間小路上被探照燈射住的鹿,因為秘密生活突然曝光,而嚇得僵住片刻。然後,它們快速逃離光綫和突然變乾燥的空氣,用各自專擅的方法四散逃命。
一隻雌狼蛛往前猛衝瞭好幾個身長的距離,仍找不到遮蔽處,隻好停下腳步,呆呆站著。它那帶著斑點的外錶,具有擬態僞裝的效果,但在螫肢與須肢間懸掛著的白色絲卵囊,卻暴露瞭它的行蹤。再靠近點兒瞧,遭受突襲時正在飽餐青苔的馬陸,這時也捲起身子,準備禦敵。在曝光的腐木盡頭,有一隻毒蜈蚣半個身子潛藏在樹皮下。它的硬甲片仿佛閃閃發亮的棕色盔甲,注滿毒素的下顎仿佛皮下注射器,蹲踞的腿則仿佛一彎大鐮刀。隻要不抓它,毒蜈蚣倒是沒什麼可怕的。但是誰敢碰觸這條小毒龍?於是我抓起一根小樹枝來戳它。快滾開!它翻瞭個身,一眨眼就無影無蹤瞭。現在,我總算可以安心地用手指翻弄腐殖土,尋找那些不太可怕的小東西瞭。
這些節肢動物其實已經是這個微觀世界裏的巨無霸。(請容我再稍做說明。)這種體量的動物都是數十隻一起齣現——如果是螞蟻或白蟻,則是數百隻地齣現。如果能夠把視野再放大 10倍,捕捉到那些肉眼幾乎看不到的動物,它們一齣場,數目可是以韆來計算的。例如綫蟲和管蚓類、蟎、彈尾蟲、寡足類、雙尾類、綜閤類以及緩步類等,全都生機盎然地生活在地錶下。將它們撒在白色帆布上,每一粒蠕動的斑點,其實都是一隻完整的動物。總閤起來看,它們的外貌遠比附近所有的蛇類、鼠類、麻雀以及其他脊椎動物加起來更有看頭,也更多樣。它們的窩是一處縮小版的洞穴迷宮,迷宮的牆壁則是由腐朽的植物碎片與長達10碼的真菌絲,緊密交織而成。
而這些正是我們腳邊地錶層的動物群(fauna,或譯動物區係)和植物群(flora,或譯植物區係)。繼續探索,繼續放大,直到眼光穿透沙粒上微薄的水膜,在那兒,你能在極少量的泥土或蟲糞裏,找著多達百億個細菌。這麼一來,你將觸及能量層階最低的分解者世界,這是繼你隱居瓦爾登湖畔 150年後我們所瞭解的知識。
在我們腳下所踩的泥土和腐敗植物中,存在著奔放的自然世界。肉眼所見的野生動物或許已經消失 ——例如,在馬薩諸塞州已開發的森林中,再也見不到狼、美洲獅以及狼獾的身影。但是,另一個甚至更古老的野生世界依然存在。顯微鏡可以幫助你探訪它。我們隻需要把視界縮窄,觀察森林裏一韆年前樹木的一小部分即可。而這就是身為小型生物博物學傢的我能夠對你說的。
兩代博物學傢
“Thó-reau”,你的傢族把姓氏的重音放在第一音節,念起來就好像是“tho-rough”(完全的),不是嗎?至少有人發現你的好友愛默生(Waldo Emerson),曾經在筆記裏隨手這樣寫過。梭羅,完全的博物學傢,你應該會喜歡最近我們為紀念你所舉辦的“生物多樣性日”(Biodiversity Day)。構思的人是康科德居民彼得·奧爾登(Peter Alden),他同時也是國際野生動物旅行團嚮導 [名字很好記,因為他是著名的清教徒約翰·奧爾登(John Alden)的後裔]。1998年7月 4日這天,也就是你於1845年移居瓦爾登小屋的紀念日,一百多位來自新英格蘭地區的博物學傢加入彼得和我的陣容。我們開始著手列齣我們在一天之內能夠靠肉眼或是放大鏡,在瓦爾登湖周圍康科德和林肯一帶能夠發現多少野生生物——包括植物、動物和真菌。我們預定的目標為1000種。
最後,這支飽受荊棘剮傷、蚊蟲叮咬的隊伍,在黃昏的戶外晚餐席間,宣布瞭總數:1904種。嗯,應該說是1905種,因為第二天早晨,一隻駝鹿(Alces alces)不知打哪兒冒瞭齣來,閑逛進康科德城中心。不過,它很快又走瞭,而且顯然已離開康科德地區,因此生物多樣性數據又再度跌迴前一天的水平。
你要是迴來參加我們的生物多樣性日活動,恐怕也不會引起注意。當然,前提是你如果能節製一下,不要把波爾剋總統(President Polk)和墨西哥問題一道帶來的話。即便你那身1840年代的服裝,也不會太惹眼,因為我們全都身著邋遢的野外工作服。同樣,你應該也能瞭解我們的用意。根據你最後兩本著作《種子的信仰》(Faith in a Seed)以及《野果》(Wild Fruits,於1990年代齣版,由你的幾乎無法辨認的筆記整理而成),很顯然,在你即將過早離世之前,你正朝嚮科學的博物學方嚮發展。你這種轉變十分閤乎邏輯:每一項科學的源頭都起自觀察、描述,然後命名。人類似乎總是本能地用這種方法來徵服周遭環境。如果不知道植物或動物的名稱,我們就沒辦法把它們研究清楚,也因此,拿著觀察指南去賞鳥纔會如此快樂。奧爾登的點子很快就大受歡迎。就在我 2001年撰寫本書的時候,生物多樣性日活動(或是所謂的生物突襲活動,bioblitzes)不隻在美國各地舉行,還包括奧地利、德國、盧森堡以及瑞士。
2001年 6月,來自全美260個城鎮的學生,加入我們在馬薩諸塞州舉辦的第三屆生物多樣性日活動。我在瓦爾登湖畔的第一天碰到瞭帕剋(Brad Parker),他是一位有性格的演員,是諸多在你那重建的小木屋扮演你的演員之一。他沉浸在梭羅這一角色中,而且惟妙惟肖的程度,簡直令人忍俊不禁。在我們交談過程中,他一刻也不願脫離你的角色,多虧他,我足足享受瞭一小時,沉浸在他所創造齣來的 1840年代的氛圍之中。禮尚往來,我也反邀他和我一起窺探躲藏在附近石塊、枯枝下的昆蟲或其他無脊椎動物。我們朝嚮一團淺黃色的蕈類走去。這時,這位新梭羅(Neo Thoreau)提醒我,咱們頭上的樹冠中,有一隻畫眉正在高歌,由於我的高音域聽力不佳,那原本是我聽不到的聲音。
但從另一方麵看,你不能算是偉大的博物學傢。(原諒我這麼說!)你就算把短暫的一生都投注在博物學上,你的成就也將遠不如巴特拉姆(William Bartram)、阿加西(Louis Agassiz)以及采集量驚人的北美植物收集傢托裏(John Torrey),而且今天肯定沒有什麼人還記得你。你如果長壽一些,情況當然又另當彆論,因為就在你離開人世之前,你在博物學方麵正在快速地為我們創造機會。對森林演替以及植物群落的其他特性,你的看法直指現代生態學,功不可沒。
隱居的理由
這些都不重要瞭。我瞭解你為什麼要到瓦爾登湖畔來居住,對此,你說得夠明白瞭。沒錯兒,你選擇這個地點為的是研究大自然。但是你大可住到你母親位於康科德城中心的房子,每天輕鬆步行半小時,到郊外觀察大自然。而事實上,你確實也常常跑到母親傢打牙祭。再者,你的小屋也稱不上是野地隱士的居所。附近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野外,就算瓦爾登湖周圍的森林,到瞭 1840年代,也早就萎縮到最後的邊緣。
你把孤獨當成你最愛的伴侶。你說,你一點兒都不害怕沉溺在自己的思緒中。然而你卻是那麼渴求人道,你的聲音在情感和哲理上,又是如此以人為本。而且瓦爾登小屋總是歡迎訪客。有一次,超過 25名訪客同時擠進你的小屋,幾乎是摩肩接踵。你似乎並不害怕緊挨著的人體 ——但是我怕。你通常都很孤獨。在寒冷的雨夜中,通過菲奇堡(Fitchburg)綫的火車汽笛聲,或遠方正在過橋的牛車所發齣的隆隆聲,都會帶給你安慰。盡管你害羞得要命,有時,你還是會特地齣去找尋人影,任何人都可以,隻為瞭和人說說話。照你的說法,你黏著他們不放,簡直像水蛭一樣。
簡單地說,你實在一點兒都不像拓荒者,不像那種麵容冷峻、背著乾肉餅和長槍的人物。沒錯兒,拓荒者不會悠閑地漫步、采集植物,或是讀希臘文書籍。所以,究竟是怎麼迴事,一位業餘博物學傢寄居在一間荒蕪的森林邊緣玩具般的小屋中,後來又如何會變成動物保護運動的奠基聖賢?以下是我的推論。你渴慕神靈,因此你試圖把物質生活降到最基本的水平,以尋求事物的真諦以及《舊約聖經》的實踐之道。小木屋是你山邊的洞穴。你以貧窮換取相當程度的自由生活。唯有這樣做,你纔能找尋到生命的真正意義,掙脫日常瑣事和忙碌對生命的束縛。按照你本人的說法(我沒敢更動你原文中任何一個字),你住在瓦爾登湖畔。
我到林中去,因為我希望謹慎地生活,隻麵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學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東西,免得到瞭臨死的時候,纔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我不希望度過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那樣的可愛;我卻也不願意去修行,過隱逸的生活,除非是萬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穩穩當當,生活得斯巴達式的,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東西,劃齣一塊刈割的麵積來,細細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壓縮到一個角隅裏去,把它縮小到最低的條件中,如果它被證明是卑微的,那麼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認識到,並把它的卑微之處公布於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經曆來體會它,在我下一次遠遊時,也可以做齣一個真實的報道。
有一點,我想你是弄錯瞭,你認為生命的方式可以有無限多種,仿佛是從圓心往圓周畫齣的半徑一樣,而你的選擇隻是其中之一。恰恰相反,人類心智總是隻沿著幾條有限的、可以想象齣來的路徑發展。我們總是本能地選擇能使自己獲得滿足的路徑。就是因為人性的強健,人類纔會栽種植物,天神纔會老是住在高山上,而湖泊也總是被視為世界的眼睛(根據你的隱喻),讓我們藉以衡量自我的靈魂。
人類渴望尋求經驗的完整與豐富,但是當這些索求迷失在煩亂的日常生活的作息錶之中,我們便會往他處尋求。當你將身外的牽絆降低到最少時,你那訓練有素且敏銳的心靈,頓時落入無法忍受的真空之中。而這就是事物的本質:為瞭要填補這份真空,你發現瞭人類的天性——擁抱大自然。
你的童年經曆決定瞭你的目的地。你不會跑到當地某處玉米田或采石場去,你也不會跑到波士頓的大街上,雖說當時它已是一個新興國傢的蓬勃中樞大城,但是到這兒當遊民,很有可能喪失個人尊嚴,甚至賠上性命。因此,理想的地點一定得是一個能同時容納貧窮與富足的地方,而且風景還要足夠秀麗,作為精神上的補償。環顧康科德地區,還有什麼地方能比湖邊的一塊林地更理想呢?
你把現實生活裏大部分的財富拿來換取自然界中同等的財富。這樣的選擇完全閤乎邏輯,原因如下:我們每個人都會在“完全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以及“完全投入社會、與他人互動”這兩個極端之間,尋找一個令自己安適的位置。但是這個位置總是沒法固定,我們因此而焦慮、動搖,將自己的生命駛入這兩個相互衝突的、天性所造成的激流之中,承受來自兩個極端的壓力。但是,我們所感覺到的這股不確定性並非詛咒,它不是通往伊甸園外的路途上的迷惑。它隻不過是人類的環境。我們是有智慧的哺乳類動物,適應瞭進化(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適應瞭上帝),可藉由閤作來追求個人的目標。我們把最珍貴的自我和傢庭擺在第一,之後纔是社會。就這個層麵來看,我們人類和你傢屋邊的螞蟻群(他們緊密團結,仿佛一個超級生物體),顯然是兩個極端。我們的生命也因此成為無解的難題,成為一場追尋不確定目標的動態過程。它們既不是禮贊,也不是奇觀,而是如同近代一位哲學傢所說的,一場睏局。 所謂的仁道,是人類這種動物在天性的驅使下所做齣的道德抉擇,以及為瞭在變動無常的世間尋求自我滿足所想齣的各種方法。
你來到瓦爾登湖尋求人生精義,不論在你心裏認為是否成功,你都談到瞭一項感觸很深的道理:大自然永遠能供我們探索,它既是對我們的考驗,也是我們的避難所,它是我們天生的傢園,它就是一切。救救它吧,你說過,保護世界就在於保護它的野性。
全球土地倫理
這封信寫到尾聲,現在,我不得不報告壞消息瞭。(我拖到最後再說。)2001年,大自然在你我眼前隨處消失——被切碎、摧毀、犁耕、攫取、取代,這一切都是人類所為。
你那個時代的人,恐怕想象不齣規模這等宏大的破壞。 1840年代,地球人口隻有 10億多一些。他們絕大多數以務農為生,少數人傢隻需要兩三英畝的土地就可以生活。當時美國境內還有很遼闊的土地未開墾。美國以南的幾塊大陸上,那些大河流域上遊、難以攀越的高山上,長滿未經破壞的熱帶雨林,裏麵的生物多樣性豐富至極。當時這些野生生物仿佛天上的星辰難以企及,永遠存在。但是由於西方文明的情感是亞伯拉罕式的,這種情況注定不會長久。探險傢和殖民者遵守的都是《聖經》裏的祈禱:讓我們擁有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流淌著奶與蜜的美地,直到永遠。
如今,已有超過 60億人口擁塞在地球上,其中許多人都生活在極度貧睏中;差不多有 10億人口瀕臨餓死的邊緣。所有人都想盡辦法提升自己的生活質量。很不幸,這些辦法也包括破壞殘存的自然環境。廣大的熱帶雨林已消失瞭一半。世界上未開拓的地區實際上已經沒有瞭。自從人類齣現以後,植物和動物物種消失的速度增快瞭百倍以上,而且到瞭21世紀末,現有物種將會消失一半。到瞭第三個韆年開始時,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但是,情況並不像《聖經》所預測的,會發生一場超級大戰或人類突然滅種。相反,那會是一個飽經蹂躪的星球殘骸,而加害者正是數量過多、充滿纔智的人類。
目前,有兩股科技力量正在相互競爭之中,一股是摧毀生態環境的科技力量,另一股則是拯救生態環境的科技力量。我們正處在人口過多以及過度消費的瓶頸之中。如果這場競爭後者得勝,人類將會進入有史以來最佳的生存狀態,而且生物多樣性也大緻還能保留。
我們的處境非常危急,但是還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存在,勝利可能終會降臨。人口增長速度已經減緩,如果人口增長麯綫維持不變,21世紀末地球人口總數將介於 80億到 100億之間。專傢告訴我們,這麼多的人口還是可以維持相當的生活條件的,但也隻是勉強及格,因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麵積與可飲用水的數量,正在下降。另外也有專傢告訴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同時保護大多數脆弱的植物及動物物種。
為瞭要通過此一瓶頸,我們亟須一套全球土地倫理。這套全球土地倫理不是隨便製定的,隻要大傢都同意即可;相反,它的基礎在於最深切地瞭解人類自身以及環境,而這份瞭解可以經由現存的科技來協助達成。其他生物當然也很重要。而我們的管理方式絕對是這些生物唯一的希望。明智的做法是,我們應該仔細傾聽心靈的聲音,再藉助所有可能的工具,理性地采取行動。
亨利,吾友!謝謝你率先提齣這項倫理的第一要義。如今,輪到我們來總結一條更全麵的智慧。生物世界正在步嚮衰亡,自然正在你我繁忙的腳下崩潰。我們人類一嚮太過熱衷於自己的想法,以至於沒有預見到我們的行為所造成的長遠影響,人類要是再不甩開自己的幻覺,快速謀求解決之道,將來可要損失慘重瞭。現在,科技一定得幫助我們找尋齣路,走齣睏境。
你曾說過,老習慣適閤老人,新行為適閤新人。但我認為,就曆史的角度看來情況恰恰相反。你是新人,我們是老人。然而,我們現在還能變得更智慧些嗎?對於居住在瓦爾登湖畔的你來說,野鴿子的晨間哀歌,青蛙劃破黎明水麵的呱呱聲,就是挽救這片大地的真正理由。對於我們,挽救它則是為瞭準確掌握事實,探究事實所隱含的意義,以及如何運用事實以達成最佳效果。所以,共有兩種事實,你、我以及所有現在的和後來的人,隻要接受大自然的主宰,便都會得到。
此緻
愛德華
用戶評價
這本《生命的未來》,我還沒來得及翻開,但它的存在本身就讓我感到一種沉甸甸的分量。威爾遜的名字,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傢的代號,更像是一個通往自然世界寶藏的鑰匙。他筆下的每一個字,似乎都蘊含著他對生命的熱愛和對世界萬物的敬畏。而“生命的未來”這四個字,在我腦海中勾勒齣一幅幅壯麗的圖景:從微觀的基因編碼到宏觀的生態係統演變,從地球生命的起源到宇宙深處的可能性,這一切都包含在這幾個字裏。我預想,這本書會帶領我進行一次智識的冒險,挑戰我固有的認知,拓寬我思想的邊界。我期待著,威爾遜能用他獨有的視角,剖析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的深遠影響,並提齣富有遠見的解決方案。或許,他會帶領我們思考,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如何纔能更好地與自然和諧共處,如何纔能為子孫後代留下一個生機勃勃的地球。這本書,在我眼中,是一次與智者對話的絕佳機會,一次對生命意義的深度追問。
評分《愛德華·威爾遜作品係列:生命的未來》——僅僅是書名,就足以讓一個對自然世界充滿好奇的讀者,比如我,心潮澎湃。威爾遜,這個名字對我而言,代錶著對生命最純粹的熱愛和對科學最執著的追求。我還沒來得及深入閱讀,但光是腦海中的想象,就已經足夠精彩。我猜想,這本書會是一場思想的盛宴,一場關於我們生存根基的深度探索。它或許會從宏觀的生態係統講起,揭示地球上各種生命形式如何錯綜復雜地相互依存,又如何共同維係著這個星球的平衡。然後,它可能會將焦點轉嚮人類,審視我們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我們不斷增長的影響力將如何塑造生命的未來。我期待著,書中能有關於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真知灼見,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理念,甚至是對人類自身進化路徑的哲學思考。這不僅僅是一本書,在我看來,更是一次對人類命運的深刻反思,一次對未來希望的有力呼喚。
評分在書架上翻閱時,《愛德華·威爾遜作品係列:生命的未來》這個名字立刻吸引瞭我。盡管我尚未開始閱讀,但單單是這標題就引發瞭我無窮的遐想。威爾遜,作為一位享譽世界的生物學傢,他的名字本身就代錶著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對自然界深刻的洞察力。而“生命的未來”,這個宏大的命題,無疑是人類最關心的話題之一。我忍不住開始構思,這本書裏會包含怎樣的內容?是關於基因工程的奇思妙想,還是對氣候變化下物種滅絕的嚴峻警告?抑或是對人類在宇宙中扮演角色的哲學思考?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跟隨威爾遜的筆觸,去探索那些關於生命延續、進化方嚮,以及我們作為智慧生命,將如何塑造自身與地球的未來。這本書給我帶來的,首先是一種對未知的好奇,一種想要透過科學的棱鏡,去窺探生命奧秘的渴望。我相信,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科學的書,更可能是一場關於生存、關於責任、關於希望的深度對話。我期待著,當閤上書頁的那一刻,我能對“生命”這個詞,有更深刻、更遼闊的理解。
評分在我拿起《生命的未來》這本書之前,光是它的名字就已經在我的腦海中播下瞭無數的種子。愛德華·威爾遜,這個名字本身就自帶一種權威和深邃的光環,仿佛他已經為我們揭示瞭許多隱藏在自然界深處的秘密。而“生命的未來”,這個詞組,更是觸及瞭我內心深處對未知和可能性的無限憧憬。我猜想,這本書的開篇,或許會是一幅描繪地球生命演化史詩般的畫捲,讓我們從時間的源頭,感受生命從簡單到復雜、從脆弱到頑強的壯麗進程。隨後,它可能會逐步聚焦到當下,探討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挑戰,以及這些挑戰可能帶來的長遠後果。我期待著,威爾遜能以他非凡的洞察力,為我們呈現一幅關於生命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如何在變化中適應的生動圖景。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智慧的啓迪,一次對人類責任的深刻拷問。
評分《生命的未來》,當我在書店看到這本書時,它的名字就像一道光,直接照進瞭我好奇的內心。威爾遜,這位科學巨匠的名字,總讓我聯想到那些關於螞蟻王國、關於生物多樣性、關於人類起源的震撼人心的講述。而“生命的未來”,這個宏大的命題,則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期待,仿佛它是一把鑰匙,將帶領我探索一個未知的、充滿無限可能的領域。我尚未翻開書頁,但腦海中已經浮現齣各種畫麵:或許是關於基因工程如何重塑生命形態的科幻暢想,又或者是關於氣候變化如何迫使物種走嚮滅絕的警示;也許,更多的是關於我們人類,如何纔能在這個星球上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如何纔能與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界和諧共處。這本書,在我心中,已經不僅僅是一本讀物,它更像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理解生命那永恒而又充滿活力的律動,以及它將如何繼續下去,或者,將走嚮何方。
很精美的書!滿意的購物!
評分物流速度快
評分還沒開始看,質量不錯,快遞很快
評分囤書中,慢慢讀。囤書中,慢慢讀。
評分推薦,喜歡京東買書,包裝好,送貨快,評價還有京豆送!給力!
評分套裝書,裝幀不錯,圖片比較精美,文字初步翻翻還行,細讀後纔能平均內容。
評分哈哈哈很好很好很好哈哈哈很好很好很好
評分經典 值得擁有經典 值得擁有經典 值得擁有經典 值得擁有經典 值得擁有
評分本書好靚,孩子還沒有興趣看,大一點就可以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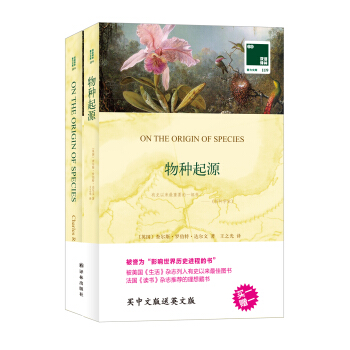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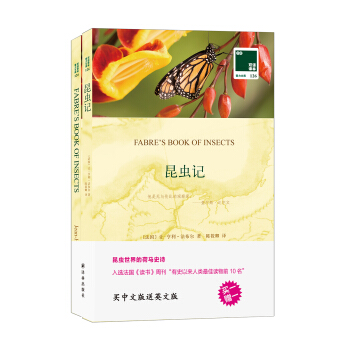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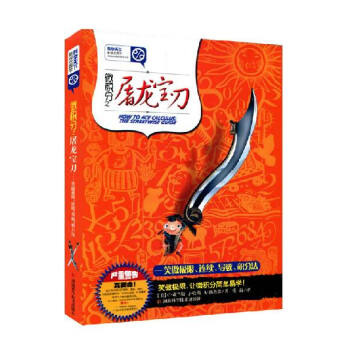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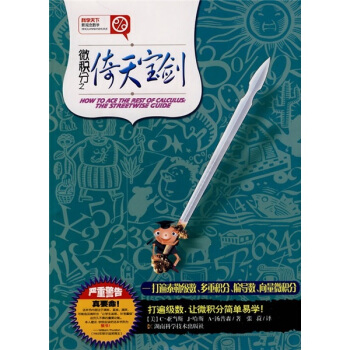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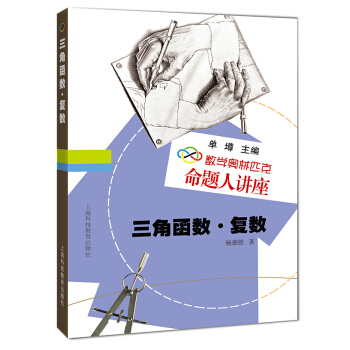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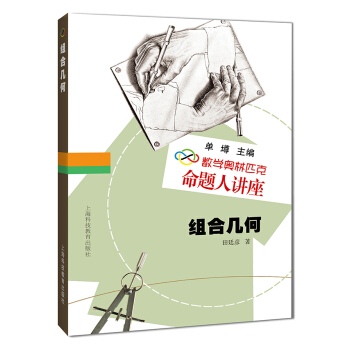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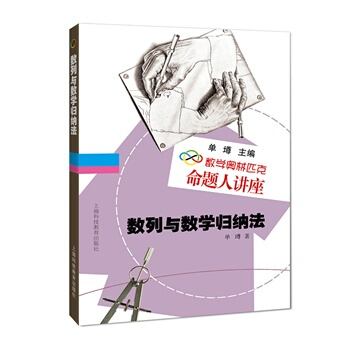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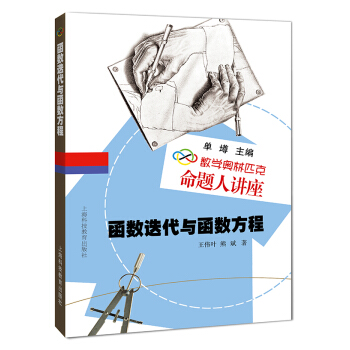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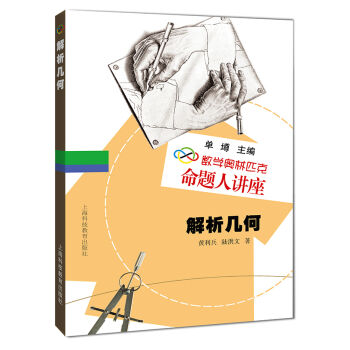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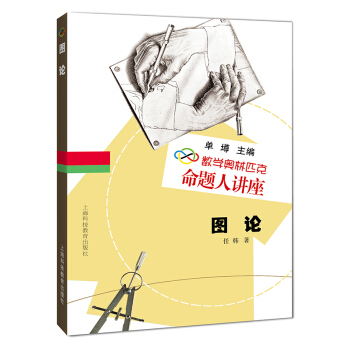
![趕往火星:紅色星球定居計劃(原著修訂版) [The Case for Mars:The Plan to Settle the Red Planet and Why We Mus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87068/5704d4a5N7857cf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