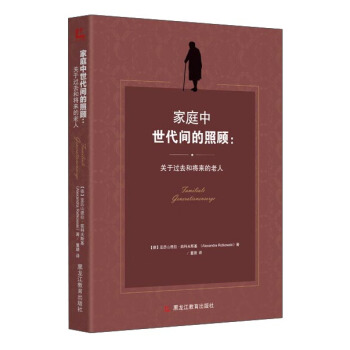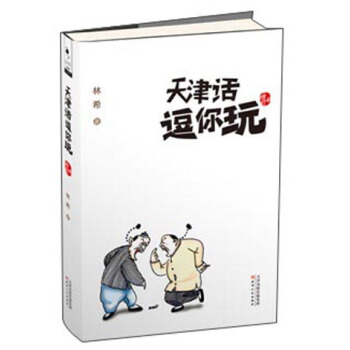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代,国际传播(信息的跨国界传播)业已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一种基本形态,同时也发展成为传播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国际传播/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传播学系列》从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学科内涵出发,对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发展历程、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及传播效果和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透视和深入系统的阐释,从而确立了国际传播学的学科自主性和学科完备性。本书内容丰富、观点独到、体例新颖,是一部时新的国际传播学教材,适合新闻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学等相关专业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学习参考之用。作者简介
李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任教;2003年至2005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年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工作,后转入传播研究院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出版有《文化外交》、《国际政治传播》、《全球传播学引论》和《中国国家形象》等著作。目录
第一章 国际传播的学科概说第一节 国际传播的学科界定
一、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内涵和外延
第二节 国际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一、从古代到现代的国际传播研究
二、国际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
三、中国(大陆)国际传播研究
第二章 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
第一节 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概述
一、从理论范式到国际传播的理论范式
二、国际传播理论范式的适用度
第二节 技术主义范式
一、传播技术决定论
二、发展传播理论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范式
一、信息自由流通理论
二、传媒依附理论
三、媒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四、传播世界化理论
五、数字(网络)神话理论
六、跨国公共领域理论
第四节 文化研究范式
一、文化研究理论:文化的再定义
二、从文本研究理论到受众研究理论
三、文化研究范式:对全球文化传播的解读
第三章 国际传播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 古代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的发生
二、国际传播的早期发展
第二节 近现代国际传播(上)
一、书籍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二、报刊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三、印刷媒介时代国际传播体系的萌发
第三节 近现代国际传播(中)
一、电报、电话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二、广播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三、电子媒介时代前期国际传播体系的形成
第四节 近现代国际传播(下)
一、电视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二、电子媒介时代后期国际传播体系的拓展
第五节 当代国际传播
一、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出现后的国际传播
二、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体系的扩散
第四章 国际传播的主体
第一节 国际传播主体的概说
一、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
二、国际传播主体的发展过程
第二节 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国家
一、国家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职能
二、国家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特点
三、国家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差异和变化
第三节 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发展历程
二、跨国公司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特点
三、跨国公司参与国际传播的形式
四、跨国传媒公司
第四节 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国际组织
一、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二、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第五节 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个人
一、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产生与发展
二、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特点
第五章 国际传播的控制
第一节 国家对国际传播的控制
一、国家对越境信息控制的手段
二、国家对越境信息控制的模式
三、国家对越境信息控制的趋势
第二节 国际组织对国际传播的控制
一、作为国际传播控制主体的国际组织
二、国际组织对国际传播控制的手段
三、国际组织对国际传播控制的实施及其效果
第六章 国际传播的渠道
第一节 语言媒介的转换
一、语言媒介转换的国际传播意义
二、语言媒介转换的文化对接实质
第二节 技术媒介的融合
一、传播媒介的技术融合
二、传播媒介的产业融合
第七章 国际传播的内容
第一节 国际传播信息的种类
一、新闻类信息
二、广告类信息
三、娱乐类信息
四、知识类信息
第二节 国际传播信息的性质
一、各种信息形态的糅合
二、本土性内容与异域性内容的混杂
第八章 国际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受众
一、国际传播受众的特点
二、国际传播受众的分类
第二节 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受众
一、国际受众地位的主体化
二、国际受众身份的多重化
第九章 国际传播的效果
第一节 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效果
一、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
二、国际传播效果的测评方法
第二节 国际传播的宏观效果
一、传播态势不均衡化的表现
二、传播态势不均衡化的成因
三、传播态势不均衡化的前景
第十章 国际传播的效应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主权的弱化
一、国际传播冲击国家主权的地缘逻辑
二、国际传播瓦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建构
第二节 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
一、全球公民社会的建构
二、全球治理和全球民主政治的实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国际传播的学科概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内涵和学科发展史。本章是国 际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纲要性说明,它阐述了国际传播学的研究 对象和内容、学科内涵及其发展历程。
国际传播的学科界定
面对一门学科,首要的是厘清其研究界限,划定其所属范围, 从而明确它的学科内涵。研究国际传播学,首先要明确国际传播研 究的对象和内容,由此确定其作为一门传播学的学科内涵。
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传递活动从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无论是古代的外交活动 (如各国互派使节、首领会盟),还是古老的民间往来(如远洋贸易、海外传教、跨境移民、长途旅行、对外战争、航海探险),都是信息跨国交流、流动的形式。到后来,随着各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不断深入,信息跨国界交流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
从一般意义上讲,上述信息的跨国传递或跨国交流就是信息的国际传播。在国内外学 术界,关于“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普遍地存在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在广义上,国际传播就是指人类信息跨越国家边界的交流和流动,即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国际传播是“一个国家以上的个人、群体或政府官员的跨越被承认的地理性政治边界的各种传播”。或者说,国际传播是“通过政府、组织、个人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递过程”。由此,广义的国际传播涉及政府、组织、群体和个人等各种主体的跨国传播活动,囊括了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等诸多传播形态。可以说,一切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都是国际传播。正是从广义上说,国际传播即为国际交往或国际互动,它包括世界各国政府之间、人民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切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一切跨国间的相互关系———国际关系(广义上的)。概而言之,国际传播的首要特性是跨国性,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人类传播的特殊形态。
在狭义上,国际传播是指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而不涉及跨 国间的人际传播或人际交流。 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或者说,国际传播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 主”。国际传播是“特定的国家或社会集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受众所进行的跨国传播或全球范围传播”。也就是说,狭义的国际传播就是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即国际大众传播,其传播主体往往局限于国家政府。正是从狭义上说,国际传播主要表现为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狭义上的国际关系)。
在国际传播学界,鉴于对国际传播概念持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学者们分别从 广义或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广义论者如国际传 播学者哈米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他把国际传播学定义为“包括通过个人、群体、政府和技术在两国、两种文化或多国、多种文化间传递价值观、态度、看法和信息的学术探索领域,同时也是对促进或抑制这类信息体系结构的研究”。基于此,他把人际间的跨国信息交流如国际旅游、国际会议、海外留学等都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统统纳入到国际传播研究对象内。与之相对,狭义论者如国际传播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Fortner),他把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的人际交流如国际信件往来和国际长途电话交谈都排除在国际传播研究的范畴之外,只保留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大众传播。
与世界国际传播学界相呼应,国内的国际传播学者同样或宽泛或严格地看待国际传播 研究的对象。有学者认为,现今交通发达,各国开放度增大,以旅游、移民、留学、访问、会议等形式过境人员日益增多,加之因特网的发展使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日益融为一体,国际传播的信息发送者中,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性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作用日益增强。无论其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为何者,所有这些跨国信息传播形式都属于国际传播研究的范畴。与之相对,另外有(甚至更多)学者认为,“只有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以及国际互联网等能量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国际传播才是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因为以人际传播方式进行的跨国交流活动涉及面过于广泛,而大众传播活动才是国际传播的主要部分和主要表现形式,将人际传播囊括于国际传播研究之中,势必会造成研究主题的泛化、研究重心的偏离和研究成果的弱化。基于此,应该把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限定在以主权国家政府为根本的传播主体、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方面,即限定在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方面,或者说,大众传播中跨越国界的那一部分传播现象。国际传播学所研究的正是大众传播中这种特殊的传播现象与活动。
在人类信息传播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近年来在互联网络和个人媒体(媒介)的数字媒介技术支持下,信息跨国界传播的多主体、多渠道、多受众等多维度、多层面性日益显著,人际间、群际间的跨国信息传播现象日益普遍。由此,“在用数字化连接的全球中,穿越国界的数据流量其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向我们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国际传播空间———超越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传播,而在全球范围之内融入了商业与商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本书倾向于从广义的角度定义国际传播概念,认定国际传播即为跨国传播(同时包含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并以此来界定国际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即: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是人类所有的跨国信息传播现象,包括其传播要素(环节)、结构、过程、特征、规律及其作用等诸多方面。鉴于国际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国际传播学可以传播学研究为基础,借用传播学的分析框架确定其研究内容。但与此同时,基于国际传播不是人类一般性的传播活动,其传播主体自身复杂多样,加之从宏观上看,整体性(非一次性)的国际传播活动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效应(非效果),因此,在考察国际传播现象时,除了一般传播学所规定的经典“5W”模式即五种研究(或分析)外,我们还要对国际传播主体和国际传播效应进行专门的研究。这就形成了国际传播学七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即主体研究、控制研究、内容研究、渠道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和效应研究。这七种研究构成了国际传播学的本体部分。
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内涵和外延
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旦明确,接下来就可以确定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传播学 的内涵和外延。
国际传播学首先应当属于传播学的学科范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现象的一门 社会科学。可以从不同研究角度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分类。依据传播的方式,可分为自我(人内、内向)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群体传播学、组织传播学与大众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内容,可分为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宗教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科技传播学、军事传播学等;依据传播的渠道,可分为传统传播学与网络传播学;依据传播的范围,可分为国内(域内或境内)传播学与跨国传播学(包括国际传播学和全球传播学);还可以依据传播的文化属性,分为文化内(同文化)传播学与跨文化(文化间)传播学。在传播学的知识版图上,各学科支系(分支学科)纵横交错,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交叉和关联,共同构成传播学的整个学科体系。
从最基本的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国际传播学是传播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支系,是 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际传播学同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人际传播 学、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不是相互并立,它并不完全独立于其他分支学科,而是与其他分支学科相互渗透。国际传播学几乎介入到其他所有的分支学科界域内,而其他的分支学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触及国际传播学。譬如,国际传播学中往往包含人际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要素,而人际传播学、政治传播学、网络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中也可能涉及国际传播学的成分。其中,跨文化传播学与国际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亲缘度最高。虽然两者分别从语言文化边界与政治地理边界来立论,但从现实经验的层面上讲,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一般具有各自的语言、文化背景,而语言和文化又往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载体,即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共同体)一般构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构关系,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国际传播活动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解。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因素,是不现实的;而国际传播研究如果不考虑文化和语言背景,也是难以理喻的。由此,国际传播学与跨文化传播学之间相互靠拢和重合的情形尤为明显。最终,就学科内涵而言,无论与传播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处于何种关系,国际传播学总归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传播学科。
如果进一步从细分的学科分类上看,国际传播学则属于传播学中的跨国传播学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相对于国内传播学),是跨国传播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者说,它是一门特殊形态的跨国传播学。在跨国传播学中,有两个学科分支即国际传播学和全球传播学(global communication),两者分别从主权政治(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物理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信息跨国界传播现象,前者视国界为政治边界,后者视国界为地理边界。由此,前者强化跨国信息传播的政治色彩,强调国内外传播的界限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概念。在前者看来,在信息跨越国界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发送者还是信息的接收者,都是有国籍的主权国家国民。跨国界的传播行为是一个穿越国家政治因素的传播行为。而后者淡化跨国信息传播的政治色彩,模糊国家主权概念和国内外传播的界限,国内传播与国外传播、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融为一体。在后者看来,跨国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都是世界公民。跨国界的传播行为纯粹是一个穿越地理意义上的边界的传播行为。因此,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政治性,“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全球传播的首要特征则是地缘性,全球传播首先关乎的是人类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不受国家主权和政治边界的限制而自由地流动。由此,国“内”“外”传播融为一体而以整个地球为范围进行传播。“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称谓的‘国际传播’,其语义中已含有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全球传播’则友好地涵盖了环绕地球的所有信息通道。”如果说,国际传播所指的信息跨国界传播是建立在确认和承认国家政治边界或国际界线的基础之上,它受国界的限制,那么,全球传播所指的信息跨国界传播则是建立在对国界的否认之上,它不以国界为界,没有国界限制,或者说,它超越了国界。换言之,国际传播“承认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而全球传播“并不承认”。因而,更为准确地说,“国际”传播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跨国界”传播,狭义上的跨国传播就是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则超越了跨国界传播的范畴,实质上是一种“超国界”传播(supranational communication)或“无国界”传播。正是从这种严格的意义上说,跨国传播只包含国际传播,而国际传播就是跨国传播,两者完全重合而可互换。概而言之,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学就是跨国传播学;全球传播学则不属于跨国传播学的范畴。与此同时,鉴于国际传播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传播概念,国际传播学主要属于政治传播学范畴,近似于“国际政治传播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全球传播则更多的是一个空间传播概念,全球传播学主要属于地理传播学范畴,可谓“全球地理传播学”(global geographical communication)。当然,如前所述,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讲,“国际 传播学”与“全球传播学”都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跨国传播学范畴,同为跨国传播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两者相互映照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所指的都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线的信息流”,差别只在于各自观照对象的角度不同(前者从政治的角度,后者从地理的角度)。由此观之,彼此分离、并立的两者可以重叠和重合,构成一体两面(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关系。
作为一门特殊形态的传播学科即跨国传播学,国际传播学无疑属于传播学的学科范 畴。但是,如果跳出传播学的视域,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国际传播学实际上同一门特殊形态的政治学科——国际关系学——有着天然的学缘关系。鉴于对传播的社会学理解——传播即为交往(互动),国际传播即为国际交往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的本质是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的表现是国际传播。在现实世界,两者本是一体,是一体两面的同一关系。同一种跨国界行为或国际行为,从信息流动的角度看,是国际传播活动,归属于国际传播学范畴;从社会结构或关系的角度看,则是国际交往活动(国际关系现象),要归属于国际关系学范畴。换而言之,国际传播是信息化的国际交往(国际关系),国际交往(国际关系)则是社会化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关系”、“国际信息体系”和“媒体外交”等国际现象就是两者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体现。“国际传播关系实际上是国家关系在传播领域的体现。”由此可见,“国际传播”与“国际交往(关系)”两个概念是相通的,既可以从国际传播的角度看待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现象,也可以从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待国际传播现象。一部国际传播史就是一部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广义上的)史。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分属于不同学科范畴的国际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实际上相互沟通、相互趋近,国际传播学是国际关系的信息化分析,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传播的社会学分析。因而可以说,国际传播学是被一门被重写(改铸)的国际关系学。
第二节 国际传播学的发展历程
像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而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受到了 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影响。国际传播学是国际传播研究进入到成熟阶段,能够利用自身特 有的核心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深入、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
一、从古代到现代的国际传播研究
从现实层面上讲,人类信息跨国界流动的国际传播现象古已有之,几乎同国家的历史 一样古老。国家赖以持续存在的国际社会便是建立在各国人民利用符号和技术等各种媒介进行跨国界交流的基础上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信息跨国流动现象,人类就开始关注和思考这种特殊的传播活动,由此开启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历程。
最早的国际传播研究始于人类早期对跨国界传播现象的认识、反思和记载,在西方可 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在东方,可追溯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关人类早期的国际传播活动,尤其是关于同一地域内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非常时期的交战和平常时期的交往如使节交换、货物交易、文化交流(如传教)及旅行探险等方面的信息流动,东西方的古代文献中均有大量的记载和论述。譬如,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古代中国的《战国策》等历史文献中,都有相当多的对跨国信息传播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其中还不乏精辟的论断和严密的论证。
在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肇始于15、16世纪,当时,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流行开来,于是就有了《土耳其侵犯欧洲新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记》、《卡尔五世侵犯里昂记》、《巴西探险记》等涉及国际传播活动的新闻传单(news-sheet)和记事性小册子(pamphlet)的问世。而后,又有了“新闻书”(news-book)和“新闻纸”(报纸,newspaper)对国际传播活动的记载和反观。无疑,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介技术的出现有 力地助推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
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兴起于17、18世纪世界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殖民主义运动时期以及关于全球化的早期探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及大规模殖民化运动期间信息跨地域、跨国界流通的盛况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到19世纪,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实体的出现和跨国传播系统的发展,现代跨国传播首次明确地被“国际的”来修饰,形成了“国际传播”的模糊概念。在19世纪,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众多西方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从交往尤其是文化信息交流即精神交往的角度揭示世界的相互依存和高度相关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相当于文化,‘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 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编者注)形成了一种世界的 文学(文化)。”在此,共产主义先驱们实际上揭示了国际传播造就人类共同体——共产 主义社会——的历史真相。
现代国际传播研究兴盛于20世纪世界战争的爆发时期。自19世纪以来,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大众传播技术相继问世,为跨国界、远距离、高速度和广覆盖面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传播技术在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广泛运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度开始了以大众传播为形式的较大规模的国际传播活动。战后,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形成高潮,心理战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对外宣传的效力等问题成为早期传播学者关注的焦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被称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于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该书对大战中各参战国媒体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为后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框架。因此,现代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的发展是以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为支撑和表现形式的。现代国际传播研究无疑是早期传播学的重要内容。甚至有学者认为,从出身论或者说从学科发展脉络而言,国际传播学是孕育传播学的元学科(meta-discipline),传播学显然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支流,而不可以说国际传播是传播学的子领域(sub-field)。
现代国际传播研究主要探讨战争期间主权国家之间的对外宣传(战时宣传)策略,操纵性、劝服性的心理战,国际传播流通的信息控制及国际传播系统的建构与瓦解,从而形成了一种国际宣传研究范式。这一阶段正是国际宣传的辉煌期(1933—1945年),其间最突出的是30年代的“广播大战”。现代国际传播研究的中心在美国。这是因为,出于国际战略的考虑,在战争中迅速崛起的美国尤为重视对外宣传(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宣传转向冷战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和关注对外宣传的研究。在战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对外宣传研究的资助。借助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等非政府组织之手,美国军方、外交和情报部门资助了几乎所有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的研究项目,譬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传播研究重镇———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IS)就是由政府出资成立的。1952年夏,中央情报局(CIA)和美国空军(Air Force)通过福特基金会一次性拨给这个研究中心87万多美元专门用于国际传播研究。该研究中心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如何控制大规模人群的态度和行为,尤其是如何运用大众传媒去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在美国国家战略需求和国家权力的倾力支持之下,配合着对外传播实践的开展,聚焦于冷战宣传和文化殖民的国际传播研究成果急剧增长,呈井喷之势。据统计,国际传播研究在战后十年(1945—1955年)所做的比前30年还要多。1850—1970年120年间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一半以上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国际传播研究,其突出特点是高度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它从属于政治,服务于国家,与国家的国际战略、外交决策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密切相关。从价值取向上讲,其研究框架或范式(paradigm of study)完全是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中心论 (nationalism, statism)——或者说,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alism)或国家本位主义 (state-departmentalism)的,即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中心、为本位(本体、基础或出发点)展开研究,其研究对象局限于主权国家政府的跨国界大众传播活动。在此,国际传播研究被“窄化”为国际政治传播研究。这种狭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即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极易演变为体现国家意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实现国家战略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工具,乃至于自身就沦为一种国家行动。美国在此一阶段的国际传播研究就是以心理战、国际劝服和美国对外政策(“国际一体化”)的名义进行的,其宗旨在于说服国外特定的受众群,从而以较低的成本去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一时期美国国际传播研究所关注的国际区域,恰好也是美国军事、政治和文化介入最深的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由于受到二战后和冷战时期政治气候和环境的影响,美国学者领导的早期国际传播研究为未来的研究和教学指明了方向,为美国的国际传播政策确定了基调。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际传播研究,西方有学者总结道:(1)研究重点在于强调国际传播在国家对外战略方面的巨大作用,而很少触及如何利用国际传播来促进世界和平;(2)极少学者关心如何改进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运作中的信息流通过程;(3)完全没有学者研究非政府主导的传播方式(如电影、书籍)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二、国际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
在人类历史逐渐步入全球化的时代,信息跨国界流动日益成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最为突 出的表现形式,人类信息的跨国界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在信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现象不断被主题化或专题化,国际传播研究日益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在传播研究中逐渐形成一门获得学科自主性的独立学科———国际传播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传播在美国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被正式提出来。在此期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专门给“国际传播”下了一个定义:“国际传播,不是指用机械、电子和其他物理的手段来向国外传送信息,而是指言词(words)、印象(impressions)和观念(ideas)的交换,去影响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说,国际传播不仅仅涉及跨国传播的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关涉跨国传播的内容、受众和效果方面。对“国际传播”概念的界定,为国际传播走向学科独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后,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行为科学家)、阿奇博尔德·克罗斯利(Archibald M.Crossley,舆论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社会学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传播学家)、塞缪尔·斯托夫(Samuel Stouffer,社会统计学家)、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政治学家)、埃尔莫·威尔逊(Elmo C.Wilson,心理学家)等一大批知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集结到国际传播这一研究领域之下,其研究工作深刻地影响乃至规范了后来国际传播学者的研究取向。其中,施拉姆等人于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最有影响力,它对世界范围内跨国信息传播的控制模式进行了国别间和地区间的整体性把握和分析。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也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关于国际传播的著述。1952年,美国的《民意研究季刊》(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冬季号)开辟了“国际传播”专刊,在该专刊中,有学者声称,国际传播研究虽然尚在起步阶段,在概念、方法和数据方面均有待完善,但它“终将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之林”。1956年,《民意研究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政治传播”专刊,其中划分为五个专题:(1)对决策者的传播——吁求与施压;(2)国际传播——媒体及其流向;(3)国际传播中的意象(images)、定义(definitions)及受众反应;(4)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政治;(5)传播与全球冲突。五大主题都涉及国际传播,并且基本上框定了国际传播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大致廓清了国际传播的学科内涵。
此后,伴随着国际传播核心概念的逐渐确定,研究范围的日益明晰,到20世纪60年代末,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学术领域进而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合法性在美国最终获得承认。首先,美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AEJMC)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并且在1969年举办了国际传播专题研讨会,次年出版了题为《国际传播:一个研究领域》(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的论文集,内容涉及国际传播课程设置方案、教学方法、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探讨。之后,美国两大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和国际问题研究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分别在它们的年会上开设了国际传播专题。1970年,由海因茨蒂里希·费希尔(Heinz-Dierich Fisher)等学者共同主编的另一本题为《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专题论文集面世。1974年,全美传播学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NCA)出版了国际传播专题研究成果——《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年鉴》(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1978年,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设立国际传播分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这标志着国际传播在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的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国际传播,从一个研究领域(a field of inquiry and research)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discipline)或科学(science),其中的关键除了核心概念的确立,就是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二十多年以美国为主体的国际传播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注重传播控制和效果、以效率为导向、“(国家)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研究范式。从方法论上讲,该国际传播研究范式是一般传播学研究中的经验功能主义或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范式在跨国传播研究领域的延伸和贯彻,它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色彩,同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这是因为,传播学正统学派——传统经验学派(由美国所奠基)持有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立场(取向),其客观、中立、中性、实证、量化的信息论路径及其所表征的“媒介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看似“科学”、“去政治化”和“权力缺席”,实际上却身陷于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沦为一种政治服务工具论。正是这种派生于传统经验学派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从美国蔓延开来,迅速流行于当时整个西方国际传播学界。在这种研究范式的支配下,极少或根本就不去关注国际传播中媒体的所有权、媒介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问题,大量的国际传播研究都是依据传播学的“5W”(who say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模式和“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元素,聚焦于对外传播活动中的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关系,并最终把研究落实到传播效果上。很自然地,这种以传播(信息)控制为核心、以传播效率为导向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主张,理想的国际传播模式应该是信息跨国界自由流通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传播美国式的民主,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显然,国际传播的学科发生和发展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发展的国际战略。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传播学从美国传播和扩展到全世界。在此学科扩散的过程中,首先在欧美地区,出现了一群属于批判学派的国际传播学者,包括美国的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英国的西斯·哈梅林克(Cees J.Hamelink)、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和芬兰的卡尔·诺登斯特朗(Kaarle Nordenstreng)等。他们采用了一种与经验功能主义相对立的批判主义研究方法,对国际传播现状持反思和批判立场,质疑国家间不均衡、不对等的信息传播秩序,强烈反对所谓的跨国“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并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文化霸权”(cultural domination)和“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等概念。他们致力于在批判中构建一个人类传播的理想家园,并在信息自由而均衡的跨国传播中确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聚焦于西方(以美国为首)政治经济霸权主导下的跨国信息传播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尤其是文化自主权所带来的冲击。
西方批判学派的国际传播研究契合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和发展态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广大的亚非拉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谓“第三世界”)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成为一股新兴的国际政治力量。正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国际传播不平衡的问题被提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上,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围绕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论战成为“面对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现状发出的第一声惊呼”(阿芒·马特拉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讨论国际传播秩序问题的主要讲坛。1969年,该组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就大众传播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召开专家会议,高度关注跨国“信息自由流通”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由北向南的信息单向流动(one-way flow)现象及其国际效应,即“信息穷国”(information-poor)对“信息富国”(information-rich)的依赖不断加剧。1976年,在第1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世界不结盟国家提交了旨在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的议案,正式提出争取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媒介接近权或近用权(right of access to media)问题。由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观成为国际信息自由流通理论的反命题。大会结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家的各方人士所组成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负责提出国际传播问题的研究报告。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乎每年都通过关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决议或声明,要求发达国家更多地重视跨国媒体的国际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传播基础设施,同时尊重所有民族在平等、正义、互利基础上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和参与国际信息流通的权利,以促进国际新闻和其他信息的更加公正和平衡的流动。正是在此期间,包括诺登斯特朗、哈梅林克在内的不少欧美批判学派的国际传播学者,都曾直接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研究项目(“传播研究国际项目”),投身于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事业中。
进入80年代,随着美国、英国先后于1985年、1986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组织作为国际传播论坛的作用逐渐淡化,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随之被边缘化,新秩序运动也日渐式微。由此,批判学派的国际传播研究陷入低潮。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新媒体的涌现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跨国界、去行政规制化的商业化和社会化浪潮风起云涌,在国际传播领域出现了一股各种传播主体蓬勃兴起、信息全球扩散的新动向。这使得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国际传播研究越来越无法全面地涵盖和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于是,一些国际传播学者纷纷调整他们的研究视角,从全球和平和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跨国信息传播现象和国际传播秩序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以全球为中心(本位)的全球主义(globalism)范式或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范式。作为新的分析框架或解释模式,全球主义范式意味着一场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方法论革命,它试图超越国家主义或国家中心论取向,不再以主权国家作为唯一的分析单位(“单元”)和出发点,而把囊括了各种超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全球传播网络体系纳入观照、分析和解释的视域之内。在方法论上,全球主义范式一般以批判学派作为理论支撑,以传播(信息)共享为核心,以传播公平为研究导向,注重对传播体制、秩序及其效应的反思,讲究传播的公正性。相对于国家主义范式,全球主义范式更多地带有思辨、诠释乃至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其价值立场是相对中性、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的,或者说,力求不带有价值偏向(当然,价值介入和参与实际上也是难免的,对国际传播现实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表达)。国际传播学者哈米德·莫拉纳于1996年出版的《变迁中的全球传播:多样性的终结?》(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Diversity?)是全球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作。该书主张在认识论层面上调整取向,在政治、经济等传统领域之外,更多地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文化关系,从使国际传播学者能够以开阔的视阈、开放的心态,努力超越本土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个体利益的局限,真正从“人的维度”(human dimension)以“全球主义的方式”(global approach)来研究国际传播问题。基于此,该书用了大量篇幅探讨了全球信息传播对本土社区、民族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与此同时,另一位批判学派的学者西斯·哈梅林克也从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中抽拔出来,更为普遍地从人的角度来进行国际传播研究,因为“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all people matter),而世界上现存的、规范信息跨国传播活动的种种国家政治机构并不都符合尊重和回归到人性和人本身的人本主义原则。因此,在他看来,人(而非主权国家)及人权(而非国家主权)应该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关切点。自由派学者、国际传播学家罗伯特· 福特纳则从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角度提出了国际传播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他指出,国际传播中存在着另一个中心方面——人(除了国家)。“首先是人的作用:人使用传播设备,人构成国际传播内容的受众。”作为国际传播的受众,人不仅仅是国际政治和商业宣传的对象,而且是拥有传播权利的主体——世界公民。与此同时,人权即人的传播权(right to communicate,寻求信息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也是国际关系中主宰信息流通的基本原则(除了国家政治主权)。基于传播主体和渠道的日益多元化,其他许多的批判 学派学者大都力图矫正传统的国家主义方法论,超越单一国家和国家主权,从更广阔、更多维的视角超拔地看待国际传播现象及其中的不平衡不公正问题,并提出各种理想的国际传播(更准确地说,全球传播或世界传播)图景及诸多替代性的国际传播策略。正是从“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立场上说,全球主义(姑且称之为“球本主义”)范式同时也是一种人本主义范式,它具有强烈的人文或人道主义倾向。
进入21世纪,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和跨国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 colonialism)、“数字帝国主义”(cyber imperialism)、全球媒介文化及认同等跨国信息传播现象持续成为在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中追求传播公正性的批判学者们权力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伴随跨国新社会运动或全球公民行动的兴起,各种社会性力量与传统的国家力量在国际体系内展开了激烈的符号竞争和信息博弈,“跨国公共领域”(transnational public sphere)、“全球公民网络”(global civic network)和“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等全球性媒介新景观成为了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新的关注焦点。由此,国际传播的公正性开始以传播的公共性的名义来主张。
纵观西方国际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科化发展历程,这是一个从国际传播研究 向国际传播学转化的过程。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明确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系统性等方面来看,这个转化的过程尚未终结。但无疑,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的国际传播学在传播学科体系内业已确立,而不再如某些国际传播学者所认为的,仅仅是一个“仍在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
三、中国(大陆)国际传播研究
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传播国际化和传播全球化不仅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同时也是一种自觉选择、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中国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到国际社会和全球化浪潮中,成为世界的中国。在中国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传播学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转道台湾、香港地区),首先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等北京高校启动,并迅速向全国推广开来。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较为系统的国际传播研究要晚得多,但迄今也有近二十年的历史。
在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之初,除了从事对外传播(对外宣传)部门的个别专家有自创性研究成果面世,大多数的国际传播学者都侧重于将国外有关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引介到国内,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展自主性的研究,并发表和出版学术成果。其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是北京广播学院自1999年起推出的国际传播研究书系,它标志着中国大陆国际传播研究的兴起。该书系包括刘继南主编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1999)、《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2000)和《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2002),蔡帼芬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2000)、《国际传媒与媒体研究》(2002)和《国际新闻与跨文化传播》(2003),张桂珍主编的《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2000),杨伟芬主编的《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2000),陈卫星主编的《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2003)等著作,当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国际传播研究的热潮。此后,在进一步总结和提炼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部国际传播教材相继面世,譬如,关世杰所著的《国际传播学》(2004)、郭可所著的《国际传播学导论》(2004)、程曼丽所著的《国际传播学教程》(2006)等。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对外传播的网络化、全球化新语境之下,不断有国际传播研究的专著问世,譬如《软力量与全球传播》(李希光、周安庆等,2005)、《中国政府形象传播》(刘小燕,2005)、《国家形象传播》(张昆,2005)、《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刘继南、何辉等, 2006)、《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李智,2007)、《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刘明,2007)、《新传媒环境下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何辉、刘朋等,2008)、《权力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周宇豪,2008)、《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龙小农,2009)、《国际传播——探索与构建》(王庚年,2009)、《全球传播》(陈阳,2009)、《新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田智辉,2010)、《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李智,2011)、《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程曼丽、王维佳,2011)和《新媒体国际传播研究》(王庚年主编,2012)等。
从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建制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国际传播的研究机构(非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1999年,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TICC);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ICSC);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CICS);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AICCC);2012年,中国传媒大学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合作创办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CIICS)。这些研究机构从事国际传播理论和学科体系研究,承担各级各类的国际传播课题;开展国际舆情跨国调查、分析、监测及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为政府、媒介机构和企业提供智力支持;举办国际传播全球论坛及各种规格的研讨会,为传媒业界、学界与政界搭建三方良性互动的交流平台;面向社会开设国际传播、对外报道等方面的课程,实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和培训项目。这些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共同建构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研究和应用体系。目前,在中国大陆,国际传播的学科建制业已完成,“国际传播”已经独立成为一个专门的专业方向。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及其对外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学术资源投入到国际传播研究领域。
反观中国近二十年来国际传播研究的历程,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大多数学者基本上遵循“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研究框架,即用西方的理论或话语来解释中国的传媒实践。显然,这种研究套路尚且缺乏对国际传播现象的知识化把握和对中国传播实践提出问题和回应的理论自觉。其次,从研究主题上看,通过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文献调查发现,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主题:媒介帝国主义批判、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建构。所有这些研究遵循着这样一套共同的逻辑,即:在批判媒介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对外传播的战略策略,从而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显然,在学缘上本来就脱胎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大多数中国国际传播学者,其学术旨趣基本上投注、聚焦于政府决策参考及政策建议和解读,而不在于纯粹的学理探究和知识生产。正如多数学者所认可的,国际传播的主要功能在于“服务本国意识形态”,是“主权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
迄今,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实践所贯彻并折射出的是一套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国家主义的规范下,这些国际传播研究“把国家当作核心的乃至唯一的分析单位,把政府的对外传播行为当作主要的乃至唯一的研究对象,进而专注于或最终归结、落实于国家信息控制、国家传播力的提升和国家形象的建构”。无疑,中国国际传播学者更多地承袭了美国前期国家主义的国际传播研究立场和范式,从而拘囿于国际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从总体上说,中国迄今为止的国际传播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狭义的国际传播研究。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尤其是在学科研究的初期,目前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经验功能主义取向,这在所难免。随着国际传播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国际传播研究的逐渐深入,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正从国家主义范式向全球主义范式过渡。事实上,今天中国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国家以外的传播主体(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组织、公司企业和个人等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全球效应,以及以非大众传媒(即手机、网络等个人媒体)为传播渠道的国际传播现象。与此同时,在方法论上,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正从经验功能主义的单一范式走向技术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思辨、诠释性的多元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把握国际传播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信息博弈提供更有效力的理论参照框架。这种实践反思与理论创新能力的提高既是捍卫中国主体性学术立场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学科化(科学化)发展的需要。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系统地整合了不同学派对国际传播现象的理解,提供了一个相当全面的知识框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上,我感觉它给出的指导性意见比较模糊。例如,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策略时,它强调了“敏感性”和“适应性”,但对于一个实际操作者来说,如何量化这种敏感性,或者在具体商业谈判中如何运用这些原则,书中的落脚点还是偏软。我希望看到更多具体的工具箱式的介绍,比如内容本地化的具体步骤、跨国媒体合作的法律边界分析,甚至是对不同国际组织传播规范的详细解读。它更像是一本描述“是什么”和“为什么”的书,而在“怎么做”这一点上,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这使得它在职业技能培养方面的效用略显不足,更偏向于理论研究者的参考用书。
评分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研读了其中关于“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章节,这部分内容处理得相当到位,作者没有简单地抛出定论,而是将历史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从早期的媒介技术扩散到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张力,论述层次分明。特别是引用的案例,选取得非常具有代表性,能够立刻帮助读者将抽象的理论概念与现实世界中的传播现象联系起来。然而,在论及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时,我感觉深度不够,很多地方只是泛泛而谈,缺乏对具体研究方法论的深入介绍,对于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如果能增加一章专门探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与局限性,并辅以具体的论文分析范例,这本书的实用价值无疑会大大提升。目前的处理方式更像是对现有成果的概括性总结,而非引导读者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实战手册”。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编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知识点的推进逻辑非常清晰,从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到微观的受众接受机制,层层递进,让人感觉每一步都踏在坚实的地面上。但让我有些困惑的是,在讲解媒介素养和信息安全这一块,所使用的语料和数据似乎略显陈旧,这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显得有些滞后。我们都知道,如今的网络信息战、深度伪造(Deepfake)已经成为国际传播中的核心议题,但书中对这些前沿挑战的分析还停留在传统的新闻真实性讨论阶段,缺乏对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驱动力如何重塑国际信息流的深刻洞察。这种“慢了半拍”的感觉,在涉及技术变革的章节尤为明显,让人不禁怀疑其内容更新的频率是否跟得上时代的速度。对于一本面向“21世纪”的教材来说,这种对前沿技术影响的捕捉能力至关重要。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严谨、规范,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挑剔的语病,充满了学术殿堂的味道。它成功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国际传播图景,尤其在介绍不同国家和地区(如发展中国家视角)的传播困境时,体现了很强的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然而,这种过度的“严谨”似乎也牺牲了一定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很多论述都倾向于使用长句和复杂的从句,对于刚刚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晦涩难懂,需要反复咀嚼才能领会其深意。我个人认为,在不牺牲学术精确性的前提下,适当穿插一些生动活泼的案例分析,或者用更具对话性的方式来引导论点,或许能更好地激发年轻读者的学习热情。它更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做学术报告,精准有力,但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点燃听众激情的火花。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确实很吸引人,拿到手里就感觉分量十足,封面设计简洁又不失专业感,光是看着就觉得内容会非常扎实。我特别喜欢这种纸质和排版,阅读起来眼睛很舒服,长时间盯着看也不会觉得累。不过,我发现它在理论框架的梳理上,似乎更偏向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式,对于当前新兴的媒介环境,比如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现象的深入剖析略显不足。当然,作为一本教材,其对基础概念的界定和经典理论的回顾是无可挑剔的,每一个术语的解释都清晰明了,可以说是为初学者构建了一套坚实的知识基石。只是,我个人更期待能在章节之间看到更多跨学科的视角,比如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前沿研究来拓宽传播学的边界,让整本书读起来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能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批判性视野。总的来说,它是一本非常可靠的入门读物,但在如何应对瞬息万变的数字传播浪潮方面,似乎还有提升的空间,也许这需要后续的增补或进阶读物来弥补。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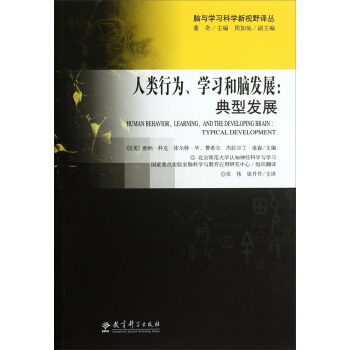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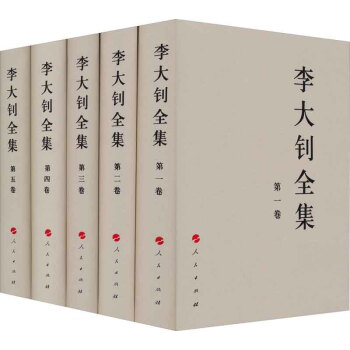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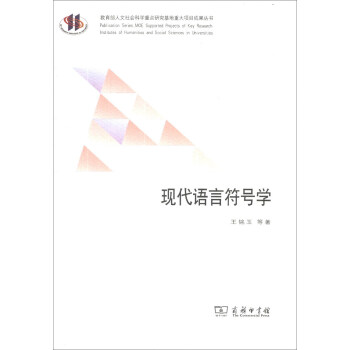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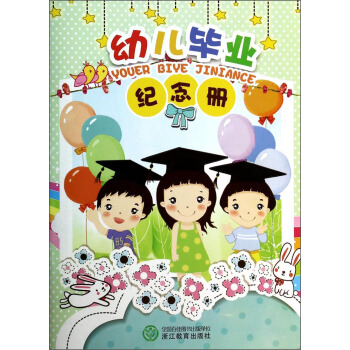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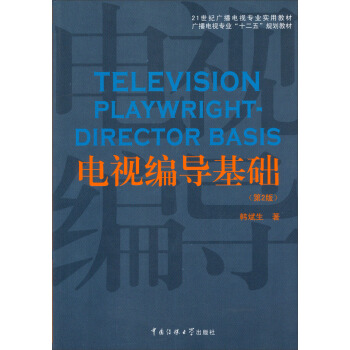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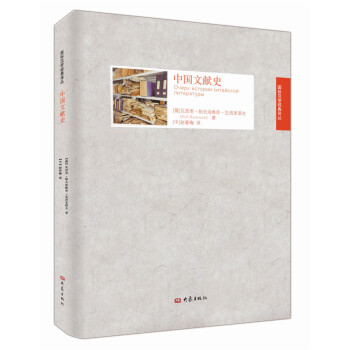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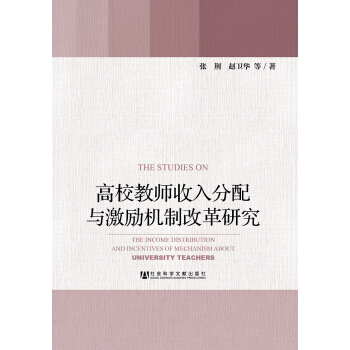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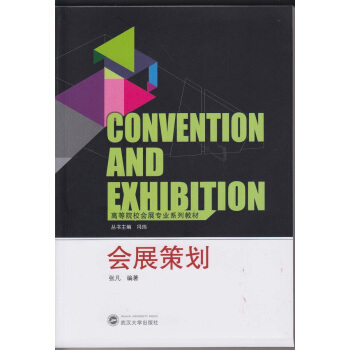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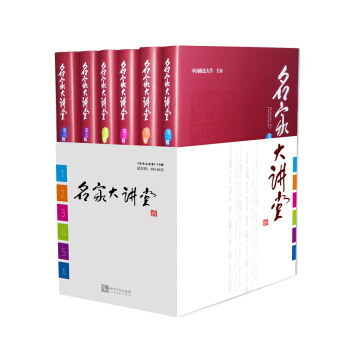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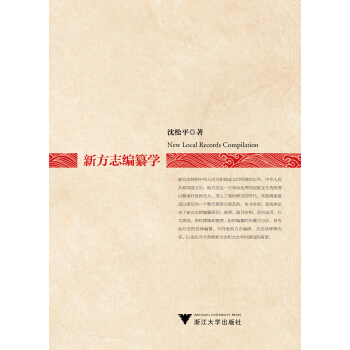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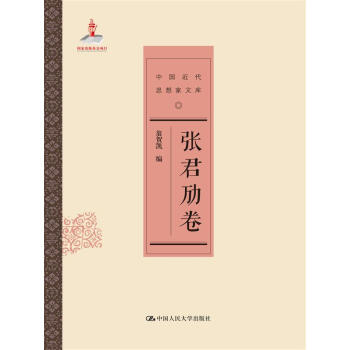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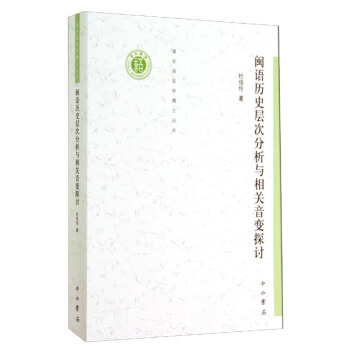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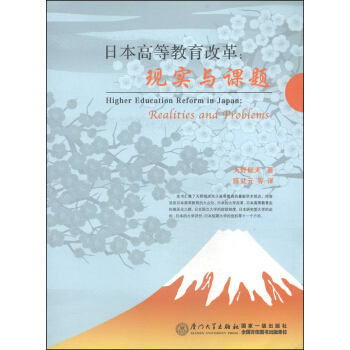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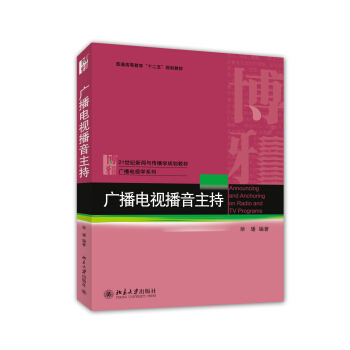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4)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99392/549769e9N6e76e05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