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台湾学者冯建三教授通过理论的梳理及对经典的迻译,以及对欧洲、北美与亚洲传媒进行个案研究,彰显其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对中国公共传媒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内容简介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态,其公共性与市场性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引起广泛争议,作为大众传媒形态,它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教育功能,而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又兼具逐利的本质。《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传媒公共性与市场》分为两部分,上篇为通论,主要讨论传媒的公共性与市场的复杂关系。下篇为个案,作者借鉴了大量西方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欧美、韩国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深度解剖,这部分对中国传媒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传媒公共性与市场》文献丰富、观点独到、视野开阔,作者冯建三教授为未来中国公共媒体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作者简介
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与硕士,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媒体改造学社与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成员。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国与西欧传媒研究、市场社会主义与传播媒体、传播科技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著有《广电资本运动的政治经济学》等六本学术专著,合作翻译作品十八本,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撰写有关传媒的报章杂志评论数百篇。目录
前言通论
第一章 传播:自由使用、平等分享、不论疆界
第二章 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史麦塞)
第三章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默多克)
第四章 传播、文化与劳动
第五章 反公共政策:科斯的传媒论述
第六章 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
案例
第七章 论欧洲联盟的《电视无疆界指令》
第八章 公共性的诡谲:公共电视的产权争议
第九章 公共广电、市场竞争与效率:关于BBC前途的论述
第十章 开或关,这是个问题:评价关电视机运动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批判传播学·文论系列:传媒公共性与市场》:第十章 开或关,这是个问题:评价关电视机运动
全世界第一个“关掉电视机”的定期活动,起源于1994年的美国,至今已经举办十二届,为期都是一周的“关掉电视,开启生活”(Turn�瞣ff TV, Turn�瞣n Life),均在每年四月实施。为了什么而关机?在美国,这个活动似乎就是目的。它认定电视这样的技术形式本身带来了莫大的问题。推动这个活动的社团认为,人们应该把看电视的时间(美国家庭电视机平均一日打开的长度是七小时四十分钟,其中,一个人平均一日看四小时),用来转为从事其他事情。1994年,这个组织列了51种活动让参与关机运动的人参考,到了2005年,他们不但发展到了101种,并且还逐月有趣的是,一年中列了11个月,独漏五月,原因为何,不详。建议该月可以特别从事的个人或团体活动(如拿出家庭相簿,回想一下家族史;听收音机;参观动物园;写信给朋友或亲戚;学习烹饪、植花伺草、园艺;开始写日记;想一则故事写下来等等)。推进这个运动的人似乎有个倾向,他们对于商业或非商业、制度与否,好像不怎么特别在意,他们要求者只是在于美国人应该减少接触电视这种有害身心、恶化了人际疏离且使人们退缩的传媒。我们从该活动所提自问自答的十个问题之一可见一斑:“电视都不好吗?收看公共电视频道不好吗?”他们提供的答案是:“所有电视都是被动、让人久坐不起的。大多数人会一出接着一出看下去,而不是只看一个节目就罢手的。关机运动就是不要参加者再去判断什么是好节目,什么是坏节目,而是要使人集中心力去发现、去参与、去动手。”
对于新技术、新传媒“本身”,特别是对于声光俱全的电视之厌恶,由来已久,就这个角度来看,以“关机”为目的、以之为一种深沉的抗议,并不新奇,也不特殊。比较有些意思而值得一提的是,这类不从“制度”层次,而只是从技术本身来传达人们对于电视的意见,在美国可能是比较发达的,相比之下,要求改变美国电视(及广播)体制的力量与社会运动(比如,要求要有平衡的广电产权结构,甚至要求以公共经营为主而不是私有利润挂帅),在历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失败后,一直要到2002年“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成军后,才告卷土重来。在部分美国学人眼中,举世最为可取(当然,是相对的意思,不是说其表现已然完善或没有大问题)的广电制度,从而其广电节目的表现比较符合民众的娱乐、信息与教育之需要的是英国Paulau, Burton(1981);2003年美英领衔入侵伊拉克前后,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转而通过网络或其他管道,从英国的卫报或BBC接触相关新闻与评论(Economist, 2003.5.3:60),其实也反映了美国传媒信息系统的问题。,却一直反而存在着声浪,要求更加完善或扩充其公营广电体制的组织。
然而,美国的有识之士难道不能察觉,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内容所展现的技术形式,诚然是有些问题因技术形式使然而存在,但也另有一些更大的范围,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技术形式,不如说是技术赖以运作的制度?应该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道理,以至于要求改变美国电视的营运动力(利润挂帅,并且归由私人支配)隐没了六七十年,到了三年前才再次重新出现?另一方面,摆脱电视这种“技术”的诉求不但不绝如缕,并且早在十多年前扩大为更大规模的关机运动?
作为一个移民及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美国相比于欧洲,具有不少特点,包括主流政党欠缺社会主义传统。这个性质似乎只能眼睁睁地坐视资本集团的统治更为紧密,表现在电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就显得无法拉高层级,造成一种传播工具应该私有的律令,改革者是以仅能在有限的节目方面作文章。除了这个背景因素,另一个造成美国改革社团的“政治无意识”(不认为能有重大的电视之结构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出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身上。这个举世知名的电信与广电传媒管制单位的表现,让美国想要改革电视的人,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
美国学界对于FCC不表信任,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如曾经担任FCC首席经济学家的史麦塞(Dallas W. Smythe)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控,FCC已经沦落为私人产业的“钦定工具”。到了1960年代,FCC主席丹尼(C. Denny)在离职后六个月就去担任他的规范对象,也就是全国电视网(NBC)的总裁,薪水是原职的三倍。鲍威尔(Michael Powell)在第一任期间,也就是1997年底至2002年,接受了媒体集团8万4921美元、共44次的旅行招待。他又在2003年6月放宽单一财团所能持有的媒体资源上限。不过,前文提及的美国“传媒改造学社”等团体群起反对,几经诉讼,迫使FCC不得不接受法院的裁决,并在2005年初宣布将研拟新规定后,另再召开公听会讨论。历任FCC主席当中最为知名、贤能的主席可能是米诺(Newton Minow),他在1961年对业者发表了“荒原讲演”(wasteland speech)。这是电视批评与愿景的里程碑,也是美国二十世纪百大讲演之一,他说,美国三大电视网在1960年的毛收入是12.7亿美元、税前利润是2.4亿,获利率达19.2%,但“你的产业获利良好,我有信心。但对你的产品,我不敢恭维”,美国的电视“是贫乏不毛的荒原大漠……”。又过了四十多年,至今美国电视并没有更好,而应该说是更为不堪了,这就使得许多美国人忍无可忍,他们在2004年夏天对“福斯新闻频道”提起了诉讼,要求司法单位取消该频道使用“公正与平衡”作为商标的权利,因为福斯的新闻实在是“误导视听、欺骗大众”。美国的娱乐节目则充斥着主持人“自豪地”表示,看的人够多,他就可以大谈特谈“我和我太太所有姊妹上过床”、“我男朋友在拉皮条”,然后台上台下互相叫嚣,至于诱使来宾在电视暴露隐私,事后造成当事人自杀,只好是牟利过程的失误。
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植根于历史积累而来的超稳定结构,使得私有产权体制原本动摇不易,这个背景,加上权大但不能依据公共利益而有效管制电视市场的政府机关FCC,可能是使得很多美国人“哀莫大于心死”的重要原因。但人心是不会永远死寂的、是会苏醒的,具有良知的美国人士在2002年后,也已经发动了传媒(其中最重要者仍是电视)结构的改造运动。他们的努力是不是终究会有些成绩,是不是能够与“关机”运动社团产生有机的联结,使得“关机”是目的,却同时也是“策略”、是改造电视(产权及营运动力之)结构的策略,除了继续观察之外,我们应该在此先行表明,假使关机只是目的,不但目的无法达成,也将另外纵容或恶化特定制度之下,电视的反民主后果,这特别是会使得民众当中的低收入、高龄与儿童等背景的观众,因为不能从电视节目中,稳定且持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以致等于是被排除在合宜的信息与娱乐环境之外,等同于遭到了歧视。
首先,虽然社会总体看电视的时间很高,也在持续增加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中国电视市场报告2004—2005》称,全国观众平均收视时间由2003年的179分钟,下降至2004年上半年的175分钟(1997—2001年均保持在185分钟上下)。但难以否认的是,即便没有关机活动,社会上早就存在为数不少的“关机”人口。不过,这类关机的人,动机有别,其中一种是在有选择的条件下,刻意选择不看;另一种是在没有选择下,被迫不能观看。造成这两种关机人的原因,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相同的是,他们尽管不看,但电视对于他们的影响,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同样存在。这是因为,这些人虽然不看,却还有更多的人在看,前者与后者这两种人必然还是有所往来,必然间接地通过传媒所设定的议题与社会氛围,隔空产生互动,或是直接面对面聊天、谈事情,谈很多私人的或公共事务的话题而在生活中互动。于是,就这个层次观察,不看电视的人等于是由看电视的人设定了大家所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话题与文化水平等等。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主动的选择,关机最多仅能在特定时刻使关机的人免于受到电视的干扰,但长期来看,这样的独善其身除了有所不能外,等于是让对于自己势将产生影响的传媒环境,拱手让人决定了。
这里并不是说,人们不能通过主流电视以外,找到更能符合自己需要的电视节目。事实上,主动选择关机的人,多少已经自力救济了。有位朋友是这样说的,由于这段话相当传神,就请允许我多引用一些:“我在大学里教学生不要浪费生命在一个沉沦的大众媒体所制造出来的信息垃圾当中,我也大约从一年多以前就停订有线电视频道。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不但没有抗议,而且很高兴一年省下的钱可以买很多Discovery与宫崎骏的精彩光盘!虽然家里唯一可以看的电视就是从公寓顶楼天线接收的三台半无线电视(半台是收讯不佳的公视),不过,好像也没有损失什么对于生命或社会有价值的讯息。”这是我的朋友吴泉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2004年4月26日发表在《新新闻周报》第894期,页58—59的文章片段,题目是《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媒体垃圾中》。读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不满意台湾主流商业电视环境的人,类如这位朋友与笔者(我自己从2002年就不订有线电视了。我们都是俗称的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我们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宽裕,工作形态比较允许我们以较多时间与子女互动,允许我们引导年幼子女看些要另外花费才能观看的节目。简而言之,我们因为有收入及时间的优势,不但自己,而且也能让家小在每一天若干时段(就说两三小时吧),无须接触饱受广告牵制的节目,也不用接触这些为迎合最大收视习惯公约数所制作的节目。但是,看完了这些节目,看完了这些我们另行付费购置的光盘等影视节目之后呢?我想,我们终究还是不能离群索居,我们置之不理的电视,以及影响电视产生这种表现的动力,还是兀自运转,这就使得我们多少有了无所遁逃之领悟了。
更为值得提醒的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进程中:“旧”广电科技的重要性很可能因为所得分配的日趋不均衡,以致其影视娱乐与信息的供输价值,势将更加突出。这是说,高或中所得民众因有余裕,使用数字、DVD、按片按频道付费等新科技的可能性,远大于中低所得,(影视)文化消费的双元结构,以后将更明显,通过电视造成的社会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境遇,未来会比现在严重。因此,假使关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做为改善电视环境的策略,那么,即便是救赎,得到救赎将只能是中上阶层。
……
应该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历史终结论的出现,后现代的全球化逐渐取得了主流论述的上风,世界不需要有本质上的改变了、也不可能改变了,人的宏愿不再可以依靠,人的信心徒然招惹讪笑。也许,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乐观而遭人理解为技术决定论的麦克卢汉之卷土重来,再领风骚,可以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观察。美国的关电视机运动表面上与麦克卢汉对电视地球村的拥抱,背道而驰,然而,从另一个侧面考察,若说双方都是轻视人之改变制度的能力,而专在技术之形式作文章,似乎并不为过。“关电视机”不能是一种目的,最多,关机可以是一种策略,目的在于让电视更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弄得我们陷入在“娱乐至死”的傻乐,五色令人目盲的茫然无知,或弄得我们失去了人际互动的能力。关机如果是目的,除了忽略了人所设计的电视制度,才决定了技术的命运,它也忘记了电视在当前制度下所具有的阶级—城乡—年龄等等的属性。关机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的任务,关机因此只能是一种策略,目标则是要求人们共造合适的电视制度。
……
前言/序言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对于徐志摩来说,“爱情”无法从“市场”购买。不但诗人不能,我们同样无法。这就凸显一个简单,但在“市场化不足、自由化不足”的话语中,反而隐晦不明的事实:我们所需要的、珍视的价值(情怀、财货、对象或产品),是不可能通过价格机制得到满足。当然,稍经提醒,几乎所有人都能同意,这是事实。未能解决的难题是,这样的“时候”,还有多少?爱情不能买,最好是两情相悦,也就是在分享中彼此趋向于完善。然而,还有哪些价值不能在市场上,经由价格的中介及买卖的行为完成呢?很多。亲情、友谊、人与人的沟通是明显的例子,依照不同的理解,(有些)公平正义也不(完全)能够通过市场,取得让人满意的“供需”水平;甚至,当事人只要知晓这些价值或行为,是从市场买来或透过金钱的交换而产生,顿时就会致使这些价值变形,不再是价值,等而下之,还可能成为痛苦的来源。爱情、亲情、友谊、人与人的沟通行为,以及公平正义等价值,若要运用市场机制的相关语汇描述,会出问题。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不同类型的商品,出于不同的原因,就其实务的运作来说,市场化的程度也有相当的差别。
“商品”可以粗分为三类:政府对其干预的力道,强劲微弱有别,效能高低不等。
干预最多的是“劳动力”商品,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跨国,任意前往他国受聘,他国人民,亦同,无法尽兴入本国工作;很多国家对于工作时数、最低工资或工作环境,也是高度规范。相比之下,“资本”商品比较自由,不但多数国家原则上欢迎外来投资、买卖股票,资本也自己另找出路,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资本自由逃避海外,不让本国课税的资金。据说一年就有11.5兆美元,世界各国为此短收的税金是2500亿美元。
“劳动力”与“资本”之外,我们可以将第三类商品,称作是“一般”商品,虽然其构成仍很复杂。其中,对于维持生计的农产品,各国都不敢掉以轻心,不愿意完全让市场决定农产品价值,因此常有大额补助。比如,相对富裕的“经济合作暨发展国家组织”(OECD)之34个会员国,都是大量贴补农产品,2011年的额度是2520亿美元,平均“只占”所有国家之农产总值的19%,但是,在人口较少或地狭人稠的挪威、瑞士、日本与韩国,这个比例是50%—60%。相对于口腹所需的农产品,人的“精神食粮”,也就是本书的主题,传媒,各国对其规范,亦远高于对制造业商品的管制。
“传媒”的意思浅显明白,主要就是指书报杂志、收音机、电视、电影,以及因特网(互联网)。手机与(平板)计算机是终端接收设备,是制造业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本书所说的传媒。对于这些社会效能不同的传媒,各国政府介入规范的程度也不相等。即便在号称汇流、全球自由化的现在,无线广电执照的所有权人在一般称之为相当自由化的美国,还是受到严格的管制,如外国人控股必须低于25%。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何以美国政府听任外国人购买其汽车厂、电影公司等,但不容许外国人购买无线广电公司,美国作此规范,不是着眼于“硬件”,不是禁止外国人拥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制造公司,而是收音机或电视机传载的“内容”,这是真正注意的规范对象。但假使广电“内容”要受这个规范,除了国籍考虑,再没有其他因素吗?甚至,国籍以外的因素,不能是同等或更重要的规范理由吗?再者,同样是传媒所负载的“内容”,何以美国人对无线广电的“内容”有更高的规范力度,报章杂志与电影或有线及卫星频道不也负载“内容”,何以美国及他国,对于后面这些传媒的产权与内容,规范少些?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相关提问,就是本书各章所要探索。也是本书名的由来。如果“传媒公共性”是指,值得社会大众知道、攸关公共利益的现象、事情与议题,能够全面充分与稳定持续地得到曝光的机会;那么,“市场”机制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是些什么?“谁”又有权,或虽然不应该有权,但事实上已经在决定“公共利益”的内涵?
这里的“谁”,不处理“个人”。我们作为个别的人,有各种身份,是消费者、是生产者、是公民,但我们不一定是“股东”;再者,即便我们是持有特定公司股票的人、是偶尔或经常进出股市的人,大多数有钱购买这些股票的“我们”,对于公司的决策也没有实质影响力,这样的“我们”,最关注的事情,通常就是明日、下周、来年的股市行情,会不会高一点。
这里的“谁”是“集体”,仍有多种可能身份。他也许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创立的公司行号,可能是公民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产生的政府及其文官体系,可能是政府依据公民授权而立法创设的公法行政法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也可能是这些身份的不同组合。
“市场”是什么呢?比较复杂。这里不谈市场的结构,究竟是一家厂商的独占,或是数家厂商的寡占,或是接近充分竞争的市场。这里是要借助英国学人冈恩(NicholasGarnham)的提醒。
冈恩1960年代在剑桥大学修习英格兰文学,曾在BBC工作十余年,一度对BBC疾声批评,亦对某些文化研究很有意见。大学期间,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学文献,其后,是英语世界重要的左翼文化政经学人。1970年代末,冈恩创办了标举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刊物与学系,双双是举世首创,但他提醒人们,自由派经济学对市场的分析,如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等概念,仍然值得参考。1980年代,法国米耶(BernardMiege)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以及德国哈贝马斯(JürgnHabermas)的公共领域观,陆续进入英语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并渐得重视、终成显学的过程,亦有冈恩与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引荐的贡献。
1979年保守党取得英国中央政府的权位后,冈恩在1983年为工党执政的伦敦市政府绸缪,发表了《文化诸概念:公共政策与文化工业》。他说,左派人士不能因为反对资本主义就一起反对市场,二者不是同义词,不是只有资本主义能够运用市场。冈恩说,流行传媒的市场运作,若无国家的宏观调节,往往无法产生合适的结果,因此,政府应该“对广告提出特别税捐……广告……将文化生产与发行纳入其结构,却不直接响应听众与观众的需求……课征……特别捐……藉此支持广告不支持的文化”。
冈恩理解,因此主张运用市场,但不迷信而是责成政府宏观介入,以求在合适范畴与水平,驾驭而不是为市场所役使,抽取广告捐只是调节手段之一,从来不是全部,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从文化与传媒公共政策的角度考虑,没有社会不需要在领会世界通则后,因地制宜,进而转化抽象的原则与概念,使成具体能够操作的手段,务实但并不放弃以进步的愿景图谋未来。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相当“颠覆性”的,它挑战了我过去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例如,作者对“透明度”这个被奉为圭臬的媒体美德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认为过度追求即时透明反而可能导致信息失焦和民粹情绪的泛滥。这种反直觉的论断,迫使我停下来,反复思索其背后的逻辑支撑。作者的语言风格时而如手术刀般精准犀利,时而又带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像一位在风暴中试图掌舵的船长。它不是那种读完后让你觉得“一切都明白了”的书,恰恰相反,它打开了更多的疑问,激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它让我意识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信息,而是更高质量的“筛选机制”和更具批判性的认知工具。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复杂、更有责任感的媒介世界的大门。
评分这本书的排版和装帧质量出乎意料地好,这在社科类学术读物中算是比较少见的了。纸张的手感很舒服,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特别疲劳。不过,抛开这些物理层面的感受,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是它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感。作者似乎完全没有沉溺于历史的故纸堆,而是紧紧咬住了当前数字化、去中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权力如何重新洗牌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了,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注意力”本身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而争夺这种资源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新的权力场域。我特别喜欢作者对“碎片化阅读”的反思,他论证了这种阅读习惯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侵蚀我们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像是上了一堂高强度的思维训练课,对当下媒体生态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那种对“公共利益”可能被牺牲的隐忧,久久不能散去。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非常有冲击力,那种深沉的蓝与醒目的白色字体组合,立刻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我本来是抱着随便翻翻的心态走进书店的,但光是浏览目录和前言,我就被作者那种对现有传播格局的深刻洞察所吸引。他似乎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媒体现象有着一种“抽离感”,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审视权力结构与信息流动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关于“公共领域”消逝的讨论,简直是一记重锤,让我这个长期关注媒体伦理的人感同身受。作者的论证逻辑严密,引用了大量社会学和哲学前沿的理论,但行文却并不晦涩难懂,反而充满了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批判精神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本书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看新闻”这件事都有了新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一个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的审视者。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著作,更像是一份对当代媒体环境的体检报告,虽然诊断结果不容乐观,但至少为我们指明了需要警惕的症结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内容深度绝对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主流媒体在商业压力下如何一步步偏离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作者在分析媒体的“市场化倾向”时,引用的数据和案例都非常扎实有力,绝非空泛的口号式批判。有一部分章节专门探讨了传统新闻业的困境与转型,那种对行业现状的复杂情感——既有对其衰落的痛惜,也有对其试图自我救赎的努力的客观描述——让人读起来既沉重又富有启发性。它没有给我一个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是呈现了一个多方博弈的复杂系统。我感觉作者对传播学的发展脉络有着极其清晰的把握,他能将经典理论与最新的网络传播现象完美对接,使得整本书既有学术的厚度,又有现实的锐度。对于任何想从事新闻、传播或公共关系工作的人来说,这本书都应该被列为必读书单的首位。
评分我得承认,我一开始对这本书的预期其实是比较低的,毕竟市面上关于媒体的“批判”书汗牛充牛车里,很多都是故作高深的堆砌辞藻。但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却非常独特,它没有一开始就抛出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从几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入手,比如某次重大事件中信息是如何被“塑形”的,某个社交媒体热点是如何被资本力量推上顶峰的。这种“由小及大”的切入点,让理论的引入变得水到渠成,不那么教条。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描述这些现象时所保持的那种冷静的笔调,他不是在发泄情绪,而是在进行一次精密的解剖。读到关于信息茧房形成机制的那一章时,我简直是拍案叫绝,那些原本以为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精巧的算法设计和商业逻辑。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教会我如何带着怀疑的目光去“阅读”这个世界,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喂给我的信息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4502/54dc732aN4ca66504.jpg)
![中国城市品牌认知调查报告(2015) [China’s City Brand Awareness Survey (201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1808/55417f89Nde955b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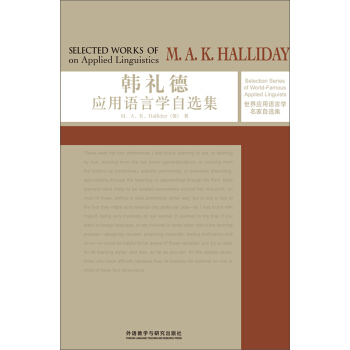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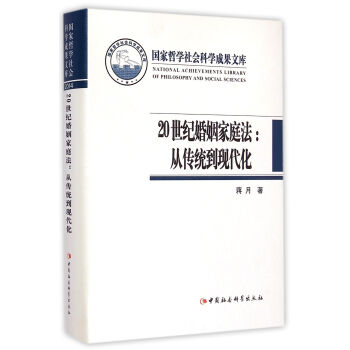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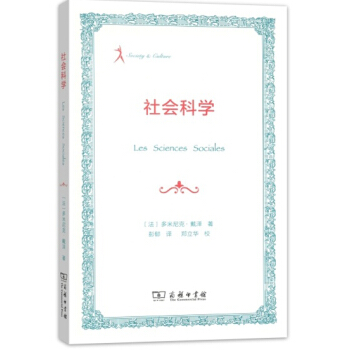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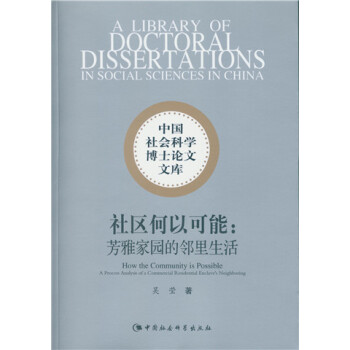
![舆情引导与危机处理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and Crisis Managemen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85147/5628b5f2N93e858aa.jpg)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On Self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12339/57569fe9Nf52e5298.jpg)


![凤凰出版研究译丛·文化商人:21世纪的出版业 [Merchants of Cultu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29809/576207e8N13cfb09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