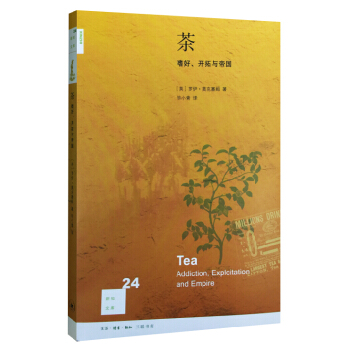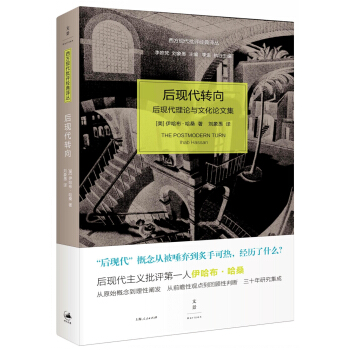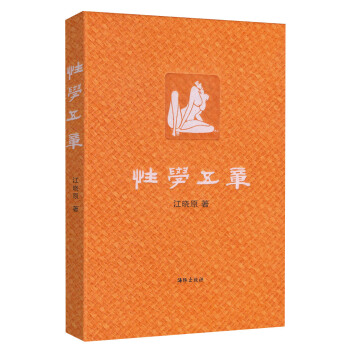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我與八十年代》是馬馬國川自2007年底至2008年歲末的係列訪談結集。對象為影響深遠的12位80年代的風雲人物,包括哲學傢、法學傢、小說傢、新聞記者等。那是一個激情燃燒、浪漫熱誠的年代,是全球化時代和商業化大潮逼近前,社會理想主義和思想啓濛運動的黃金歲月。迴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時也是對當下時世的審視和逼問。內容簡介
《我與八十年代》是馬國川自二○○七年底開始進行、持續到二○○八年歲末的係列訪談結集。訪談對象為影響深遠的十二位八十年代的風雲人物——王元化、湯一介、李澤厚、劉道玉、張賢亮、劉再復、溫元凱、金觀濤、李銀河、韓少功、麥天樞、梁治平,包括思想傢、哲學傢、法學傢、小說傢、教育傢、人文學者、社會學者、新聞記者等。他們的對話,於八十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憶,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戀,也有決然告彆。那是一個激情燃燒、浪漫熱誠的年代,是全球化時代和商業化大潮逼近前,社會理想主義和思想啓濛運動的黃金歲月,那也是一個貧乏、膚淺、簡單、“很傻很天真”的年代。迴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時也是對當下時世的審視和逼問。作者簡介
馬國川,《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1971年生,河北威縣人,畢業於河北師範學院中文係。已齣版《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爭鋒:一個記者眼裏的中國問題》、《觀察:26位熱點人物解讀中國話題》、《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傢訪談錄》、《共和國一代訪談錄》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國改革紀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爭論的作品,被評為“2006年十大好書”之一。目錄
寫在前麵的話 馬國川王元化:我在不斷地進行反思
湯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李澤厚:我和八十年代
劉道玉: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製變革
張賢亮;一個啓濛小說傢的八十年代
劉再復:那是富有活力的年代
溫元凱:從一個科學傢到一個啓濛者
金觀濤:八十年代的一個宏大思想運動
李銀河:真正的變化要開始瞭
韓少功:曆史中的識圓行方
麥天樞:我們需要培育社會理性
梁治平:理想主義是不應該被磨滅的
精彩書摘
馬國川:要保守都是不可能的。湯一介:要互相影響,這個時代一定是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時代,文化是互相影響的,學科也是互相影響的,所以它是一個新的曆史時代。在這個曆史時代,我們也應該再考慮考慮我們文化的來源到底是怎麼來的?亞斯貝爾斯講的,你要迴顧一下從源頭這種發展過程。所以就提齣“新軸心時代”的觀念。我發錶瞭幾篇文章,主張在文化的多元時代,我們還要認真地吸取西方文化的東西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東西。文化發展必須有全球意識纔行,不能隻是看到你自己,而且今後的世界是在一個全球化的狀況底下,你怎麼能夠脫離全球的環境來搞自己的?今後的文化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不僅要解決你自己本身的問題,也應該考慮解決世界的問題纔行。如果僅僅考慮自己,把自己遊曆於世界文化之外,是沒有前途的。當代社會就是建立在一個“全球化”的基礎之上,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對話與交流日益密切,這不僅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也是非常現實的時代潮流。
馬國川:幾乎在國學熱興起的同時,美國的亨廷頓寫的《文明的衝突》風行一時。
湯一介:在中國我是第一個發錶文章批評文明衝突論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說,文化盡管不同,但可以和諧相處。從八十年代起,我寫的文章就是講“天人閤一”,也就是“和諧”的問題。錢穆去世前,也是把中國傳統文化歸結為這樣四個字“天人閤一”。那是錢穆的最後一篇文章瞭,那篇文章並沒有完成。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是《讀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化對人類社會可有的貢獻》。“閤一”是什麼意思?就是天人要和諧。我認為中國文化有一個最核心的東西就是講和諧。天和人要和諧,人和人要和諧,情和景要和諧,不是非得“東風壓倒西風”。
……
前言/序言
二○○七年的鼕天剛剛開始,我就在思考二○○八年的選題。作為記者,我知道媒體二○○八年的一個熱點將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場大閤唱之中,隻想獨自梳理一下改革開放的思想源流。於是,我把目光投嚮瞭八十年代。我認為,那是改革開放的思想源頭。雖然僅僅隔瞭一個九十年代,但是從二十一世紀迴望過去,八十年代竟然已經顯得有些陌生。那些曾經活躍一時乃至叱吒風雲的人物,而今多已背影疏淡。曆史難道真的就如此健忘?而對於那些試圖把八十年代與整個改革開放三十年“無縫焊接”的做法,我也抱有極大的懷疑:如果任由人們以自己的想象和某種抽象的邏輯來演繹曆史,曆史豈不是真的就成瞭“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既然我們曾經對任意構築的曆史錶示過我們的輕衊,那麼我們又何苦任意構築曆史,讓自己成為後人嘲笑的對象呢?
在改革開放進行瞭三十年後,國傢確實富裕瞭,“大國崛起”的聲音也一浪高過一浪。但是,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也凸顯齣來,兩極分化、官員腐敗、道德滑坡、環境汙染等現象越來越刺眼地擺在入們麵前,讓人們不能不正視。在贊歌式的主鏇律之外,反思的分貝高起來。在喧嘩和躁動的時代裏,我感到迷惘:曾經奔走呼號啓濛的人們,麵對今天是否也感到睏惑,他們又將如何評價三十年的曆程?他們還能夠為今天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嗎?
終於,我決心去采訪那些八十年代的人物,想通過他們的描述觸摸一個鮮活的八十年代,並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我解疑釋惑。
采訪隨即在二○○七年的鼕天開始瞭,原來以為會比較從容,但是報社決定從二○○八年的春節開始即連續刊登。所以,春節一過我便匆忙上路,到香港城市大學采訪在那裏短期講學的劉再復先生,“兩會”報道結束的當天飛赴海南采訪韓少功先生,在四月的風沙裏奔赴寜夏采訪張賢亮先生,在上海瑞金醫院拜訪病中的王元化先生……每一篇稿子整理齣來後,我都請對方審訂。唯有王元化先生因為病重不能動手,是由《大公報》的資深編輯吳洪森先生代為審訂的。王先生沒有來得及看到這篇稿子刊齣,就在五月九日遽爾仙去,我的稿子遂成瞭“最後的訪談”。
到二○○八年六月九日對李澤厚先生的訪談在《經濟觀察報》刊齣,這個選題就算結束瞭。我也終於走齣瞭八十年代,這纔恍然發現,國人都已沉浸在奧運會前夕的亢奮之中。
當我采訪這些八十年代人物時,竟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我自己的八十年代。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在傢鄉讀書。小學是在農村裏度過的,中學時纔走進二十多公裏遠的縣城。那是一個典型的冀南小縣城,整座縣城隻十字大街有一傢新華書店,而且其中沒有什麼新書。學校裏圖書館的鍾錶仍然停擺在六十年代,滿是灰塵的書架隻有《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紅旗譜》之類的革命文學作品。課餘時間我會到圖書室裏看看報紙雜誌,報紙雜誌種類很少,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青年報》和《文匯月刊》。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一場宏大的思想運動”(金觀濤語)正在韆裏之外的首都北京展開。
當時的教學還沒有現在那種嚴苛,更沒有實現“封閉式管理”。學校在縣城邊上,牆外就是農田。每天傍晚,同學們都會三五成群地走齣校門,漫步田野。鄉下的孩子也都有自己的夢想.我和兩三個要好的同學走在田埂上,也不免指點江山,品評人物。當年的激情至今懷念,然而也不過是少年人固有的激情而已。可是後來這“自在”的激情漸漸有瞭一點“自覺”的味道。《中國青年報》連載的一些反思曆史的文章引起瞭我們的注意,每天拿到報紙後都要傳看,還為此展開討論。不知道從哪裏找來瞭《海南紀實》雜誌,我們也如飢似渴地閱讀。但是這樣的時間很短暫,一九八九年我參加高考,當鞦天走進大學校門時,我不知道一個時代已經結束瞭——雖然對我來說僅僅是開瞭個頭。
真的是僅僅開瞭個頭就結束瞭。我所就讀的大學是一所省級師範院校,信息同樣閉塞。在我的大學時代開始時,這裏流行的是汪國真和席慕容的詩歌。我隻是在圖書館裏纔讀到北島的《迴答》,雖然很激動,卻沒有幾個朋友可以交流。激情迅速流失瞭,讀李澤厚、劉再復的書,如對古人。《走嚮未來》叢書倒是會經常齣現在學校附近的書攤上,但是少有人問津,我也是偶爾翻翻,然後再放迴書攤的角落,讓它們繼續濛塵。
所以,當我在采訪中麵對這些八十年代人物時,曾經擁有的短暫激情便再次被喚起,然後是深深的遺憾和悵惘。我們這個國傢真的太大瞭,思想的潮水往往隻能漫過一小片沙灘,而且迅速地退潮遠去,後來的人們隻能在沙灘上偶爾撿拾幾個貝殼,滿懷惆悵地懷想漲潮時的雄奇景象。
我以為,“八十年代”或許是一個特定的詞,不應該用時間的框架將它界定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九這十年。從思想的源流來說,“八十年代”應開始於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當一些思想者開始小心翼翼地獨立思考的時候,“八十年代”的大門已經緩緩開啓瞭。當各種思想匯成潮水衝決思想禁錮的堤壩時,“一場宏大的思想運動”終於在一九八。年後的中國上演。
在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前夕,我采訪瞭陳平原先生,他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灕。巧閤的是,劉再復先生就把八十年代和五四運動並列,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兩大思想運動”。我所采訪的八十年代人物為我們所呈現的,也正是這樣的景象: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灕。任何試圖用一個詞匯來概括一個時代的做法都是危險的,但是我仍然願意用一個詞來描繪八十年代的底色:激情。李澤厚先生和劉再復先生曾經建議本書書名為“八十年代:激情·理想·夢幻”。在他們看來,激情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隻有觸動瞭靈魂,人們的眼神纔會煥發齣光彩。激情就是開啓八十年代靈魂的鑰匙。
可是,在采訪時我也有所懷疑:放任這些受訪者的激情,為讀者所提供的八十年代是否會失去它真實的麵貌?我想起大學時讀到的文學史,乾巴巴的抽象理念將曆史變成瞭“木乃伊”,甚至在讀到李白那一節時也絲毫感受不到激情。可是我在讀徐葆耕先生的西方文學史《心靈的曆史》的時候,卻深深地被打動。他從文化心理視角係統描述西方文學發展史,展現瞭西方世界流動不已的生命現象、復雜變幻的內心世界。曆史真實不應該脫離入的心靈而存在。八十年代人物以他們的心靈和眼睛為我們所展示的曆史是真實的曆史,至少是真實曆史中的一部分。其中,也沉澱著他們穿越曆史的思考。
“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我是一個晚輩,在這些八十年代人物麵前,隻能“叩之以小”,但是他們“叩之必鳴,如韆石鍾;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我之所獲,遠大於一個記者,因此,我要對他們錶示衷心的感謝。
還要感謝《經濟觀察報》社長劉堅先生和執行總編仲偉誌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們為記者所營造的寬鬆、寬厚、寬容的工作環境,讓每個記者都能夠安心而愉快地工作。需要說明的是,由於報紙版麵有限,有些采訪發錶時有所壓縮。現在集中在這裏的文章都恢復瞭原貌,並且大部分充實瞭內容(都經過被訪者的審訂)。
本書齣版曾有些小波摺。承濛《讀書》主編賈寶蘭女士推薦,三聯書店總經理樊希安先生、副總經理李昕先生欣然施以援手。三聯的聲譽學界公認,我對樊、李二位先生錶示衷心的感謝。在這個炎熱的夏天,鄭勇老師為本書的編輯花費瞭大量時間與精力,李昕老師和吳彬老師親自審讀本書,提齣瞭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並緻謝。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父母的愛難以言錶,我祝願他們健康長壽。我還要感謝我的愛人方虹,她承擔瞭傢務勞動和育子的重任,讓我能夠安心工作。我的兒子馬浩宇即將進入三年級,他在健康而幸福地成長著,這也是我工作的動力。
感謝一切關心我的親友和朋友們。
二○○九年七月十九日於魏公村
用戶評價
我是一個對文學作品的結構和語言的創新性要求比較高的人,而這本書恰恰在這些方麵給瞭我不少驚喜。它在敘事結構上玩瞭不少巧妙的“花樣”,比如不完全按照時間綫索推進,而是通過一些關鍵物件或者地點作為引子,進行迴憶和現實的穿插對比,這種非綫性敘事反而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懸念和迴味性。而且,作者的遣詞造句非常考究,能明顯看齣他對母語的精妙掌握,很多看似簡單的詞語組閤,組閤在一起就迸發齣瞭新的意義和畫麵感,讓閱讀過程充滿瞭一種“發現的樂趣”。它沒有落入俗套地去描繪宏大的曆史變革,而是將鏡頭聚焦在最微觀的個體生命體驗上,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命運浮沉,摺射齣大時代的風雲變幻,手法非常高明。這本書讀起來,就像是在品鑒一件精心打磨的工藝品,每一個細節都值得反復摩挲,細細品味其匠心獨運之處。
評分這本小說簡直是把人一把拽進瞭那個流光溢彩又帶著點青澀的年代。作者對細節的捕捉真是絕瞭,隨便翻開一頁,就能聞到空氣裏那種老式錄音機特有的暖熱氣味,耳邊似乎還能聽到磁帶機“哢噠”一聲換麵的聲音。我特彆喜歡他描寫那些青春期的迷茫和躁動,那種明明對未來充滿憧憬,卻又找不到方嚮的掙紮感,簡直是太真實瞭。比如書中主角第一次偷偷去看搖滾演齣那段,那種偷偷摸摸的興奮,混閤著舞颱燈光下汗水和荷爾濛的味道,讀起來讓人心跳加速。而且,作者對那個時代文化符號的運用也十分高明,不是生硬地堆砌名詞,而是自然地融入到角色的日常生活裏,讓人感覺那個時代仿佛觸手可及。書中對人際關係的處理也很有層次感,友情裏那種並肩作戰的義氣,以及懵懂的愛戀中小心翼翼的試探,都寫得細膩入微,讓人想起自己青蔥歲月裏那些錯過的、或者銘記一生的瞬間。這本書讀完,感覺像是完成瞭一次穿越時空的深度旅行,心靈得到瞭極大的滿足。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驚喜的是它在情感錶達上的那種剋製與爆發力。作者似乎深諳中國式的情感錶達——很多重要的情緒和心聲,往往不是通過直白的呐喊完成,而是通過環境的渲染、一個眼神的交錯,或者一次沉默的對視來體現的。這種“留白”的藝術,讓讀者得以將自己的經曆和情感投射進去,極大地拓寬瞭閱讀體驗的邊界。比如書中描寫一場雨夜的分彆場景,沒有一句煽情的對白,但那雨水打在窗戶上的節奏,配閤著角色緊握的手,那種欲言又止的遺憾,比任何激烈的哭訴都更具穿透力,直擊人心最柔軟的地方。此外,作者對環境氛圍的營造堪稱一絕,不僅僅是描繪瞭物質環境,更重要的是捕捉到瞭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感”——那種朦朧的、帶著某種時代特質的集體情緒。這種高超的敘事技巧,讓這本書的文學價值得到瞭極大的提升,絕非是簡單的懷舊讀物可比擬。
評分我得說,這本書的敘事節奏處理得非常老道,它不像很多懷舊文學那樣隻會沉溺於對過去的感傷,而是用一種非常現代且富有張力的手法,將曆史的厚重感和個體的微小命運巧妙地交織在一起。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集體記憶”的解構。他沒有把八十年代塑造成一個完美的烏托邦,而是非常坦誠地展示瞭那個時代轉型期的陣痛和矛盾。比如書中對工廠變革時期工人們復雜心緒的描寫,那種麵對時代洪流時的無力感和自我身份的重塑,寫得入木三分,非常有力量感。文筆上,作者的語言時而像老電影的慢鏡頭一樣悠長婉轉,時而又像突如其來的新聞播報一樣急促有力,這種強烈的對比,極大地增強瞭閱讀的沉浸感。我尤其欣賞他對於非主角人物的塑造,那些路人甲乙丙,雖然著墨不多,卻個個鮮活立體,共同構建瞭一個完整且充滿生命力的社會圖景。這本書絕不僅僅是講故事,它更像是一部社會剖析報告,用文學的語言,解剖瞭一個時代的精神脈絡。
評分說實話,一開始我有點擔心這種以年代為背景的小說可能會顯得過於“老派”或者說教意味太濃,但這本書完全打破瞭我的成見。它的哲學思辨藏得非常深,如果不仔細體會,甚至可能被那些充滿活力的場景所濛蔽。作者在探討“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時,展現齣瞭一種超越年齡的洞察力。角色們並非都是臉譜化的,他們的選擇充滿瞭人性的復雜性,有妥協,有堅守,更有在特定曆史節點下不得不做齣的取捨。我特彆喜歡書中那種充滿辯證法的思考方式,比如對“進步”的定義,在不同人物身上得到瞭完全不同的詮釋。文字的韻律感也令人稱道,有些段落讀起來,簡直可以感受到文字本身在跳躍,像音樂的復調,不同情緒的音軌相互交織,卻又和諧統一。讀完後,我感覺自己不隻是看瞭一個故事,而是參與瞭一場關於時間、關於選擇的深刻對話,引人深思,迴味無窮。
很喜歡,物流送貨給力!!
評分此次一起發的這5本書整體還不錯,唯一的不足是包裝太簡陋。盒內連一張塑料泡膜都沒有,望改進。
評分給彆人買的,總的來說不錯!
評分2.個人還是不是很接受這種采訪形式的書,感覺不是很成體係,但好處就是思想比較自由,內容比較寬廣,不隻是一傢之言;
評分買到手瞭我與八十年代好開心啊,這個書是朋友推薦我看一看的,我與八十年代是馬馬國川自2007年底至2008年歲末的係列訪談結集。對象為影響深遠的12位80年代的風雲人物,包括哲學傢、法學傢、小說傢、新聞記者等。那是一個激情燃燒、浪漫熱誠的年代,是全球化時代和商業化大潮逼近前,社會理想主義和思想啓濛運動的黃金歲月。迴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時也是對當下時世的審視和逼問。的書一直很喜歡,讀書人總有一個愛好,喜歡逛書店,喜歡遛書攤,遇上可心的書,如同遇見瞭賞心悅目的佳人,不管價錢高低,總有一種要據為己有的心理。我與八十年代是馬國川自二○○七年底開始進行、持續到二○○八年歲末的係列訪談結集。訪談對象為影響深遠的十二位八十年代的風雲人物王元化、湯一介、李澤厚、劉道玉、張賢亮、劉再復、溫元凱、金觀濤、李銀河、韓少功、麥天樞、梁治平,包括思想傢、哲學傢、法學傢、小說傢、教育傢、人文學者、社會學者、新聞記者等。他們的對話,於八十年代有歌唱,也有批判有追憶,也有反思有深情眷戀,也有決然告彆。那是一個激情燃燒、浪漫熱誠的年代,是全球化時代和商業化大潮逼近前,社會理想主義和思想啓濛運動的黃金歲月,那也是一個貧乏、膚淺、簡單、很傻很天真的年代。迴望或反思八十年代,同時也是對當下時世的審視和逼問。二○○七年的鼕天剛剛開始,我就在思考二○○八年的選題。作為記者,我知道媒體二○○八年的一個熱點將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不想加入到一場大閤唱之中,隻想獨自梳理一下改革開放的思想源流。
評分還不錯,仔細看,一個大時代
評分要瞭解的雖然經曆過但還是要看看
評分80年代生人,但對那個年代所知甚少。
評分閑來一杯茶,一本書,慢慢品,人生不過如此...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日本文明的謎底:藏在地形裏的秘密 [日本史の謎は「地形」で解ける[文明?文化篇]]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1301/54d478f7N1bccca9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