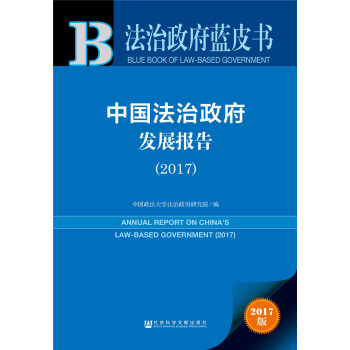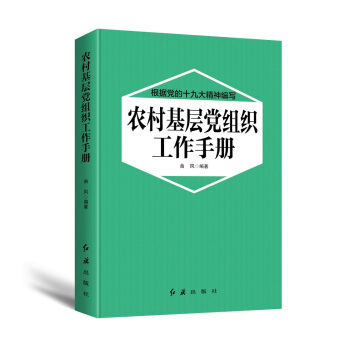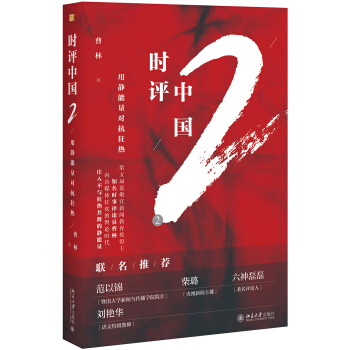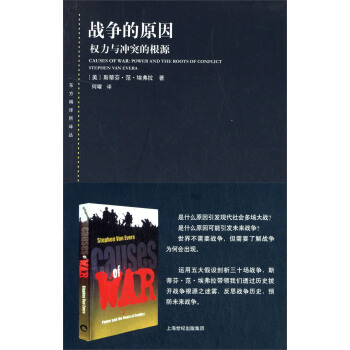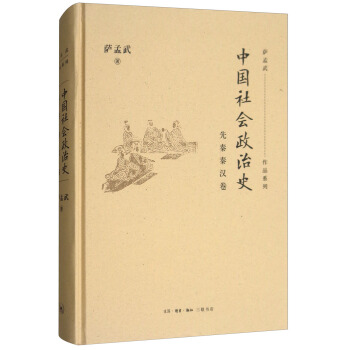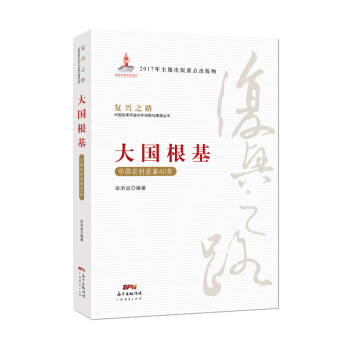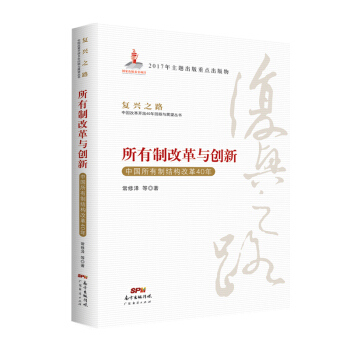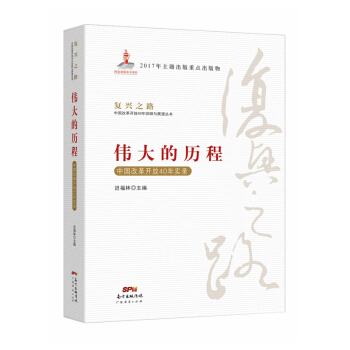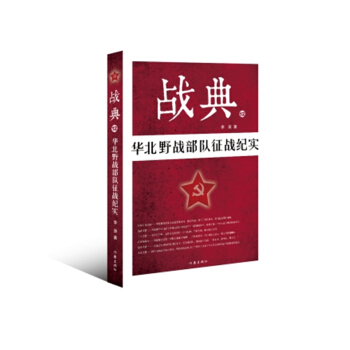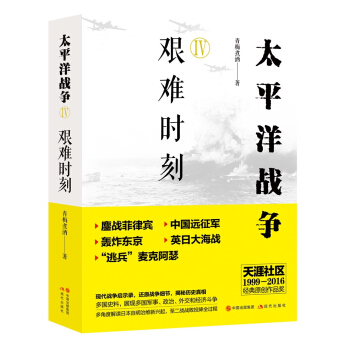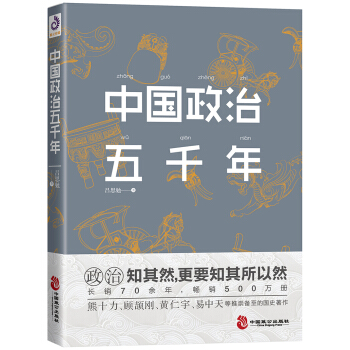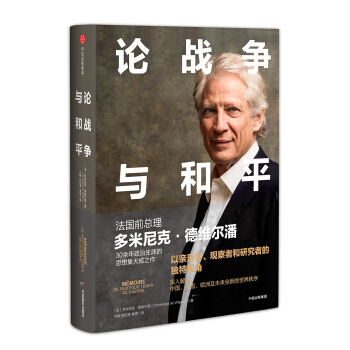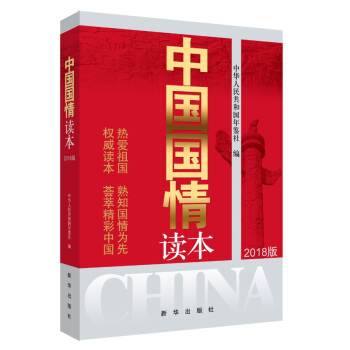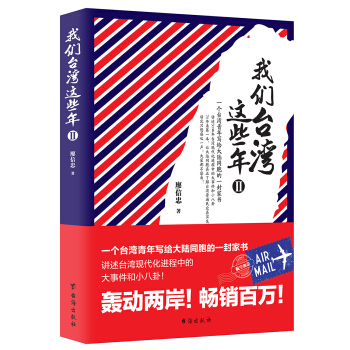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关于真正的台湾,你又了解多少?
这是我常常问大陆朋友的问题。
蒋氏家族,对台湾人来说有不寻常的意义:蒋介石被说成是“龟精”转世;蒋经国总是一袭夹克走天下。蒋孝文狂妄嚣张,喜欢乱来;蒋孝武被“江南案”影响了一生;蒋孝勇则性格收敛。台湾族群里,有让人同情的老荣民,也有比《宝岛一村》更真实的眷村生活;台湾教科书上不但有蒋介石的励志故事,更有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在金门和马祖当兵,还会冒出“无头部队”和“水鬼”的传说;在浩瀚的书籍和歌曲中,有许多已经改了名字,甚至被禁,远离人耳目。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真是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在这本书里,我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讲述三十多年来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和小八卦,与您分享台湾老百姓ZUI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
(作者廖信忠)
作者简介
关于廖信忠——
1977年,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1984年,李登辉当选“副总统”,廖信忠上小学;
1989年,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国中;
1993年,组建“新党”,廖信忠进入淡江高中读书;
1998年,马英九和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廖信忠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
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获胜,而陈水扁随后锒铛入狱,廖信忠也在上海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2009年以来,继续为两岸间的互相理解做工作。
目录
目 录第一章 『从关着门的台湾』到『打开门的台湾』
钢笔或汽水瓶都有可能是炸弹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很多人都成了马克思的亲戚
美国总统“卖花生的卡特”?
地方选举舞弊
扫地的校工成为“国民大会代表”
神明证明你拿了我的钱……
代夫出征说“老娘我”
“艋舺”那时还没有“太子帮”
民×党到民进党
“嘉年华”般的街头运动
采访大陆及开放大陆探亲
“山中传奇”和“植物人”代表
“要游行可以,只要不妨碍交通”
农民到街头“打游击”
20世纪80年代,大家开始有钱了
“国会”改选,李登辉读《圣经》寻求力量
跟大拜拜一样的“国是会议”
“二条一”:让人无可奈何的叛乱条例
在KTV不能通宵K歌?
摆平非主流派,李登辉好手段
地下电台与“全民出租车”
政治流行语:有那么严重吗?
第二章 蒋氏家族
蒋介石是“龟精”转世?
“我最尊敬的人”和“我的志愿”
生命的意义: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蒋公铜像”:戒严年代唯一的公共艺术
“勿忘在莒”变成“勿望再举”
蒋经国的“微服私访”:一袭夹克走天下
简朴之风——“梅花餐”
琼瑶剧里出现蒋经国的脸
核武器被美国人没收
部下兵变,连累蒋纬国不升官
喜欢乱来的蒋孝文
“江南案”影响蒋孝武的一生
蒋孝勇1996年回浙江奉化
蒋经国那两个温和的私生子
第三章 族?群
把自己的另一半称为“牵手”
“台湾钱,淹脚目”
“林投姐”和“周成过台湾”的传说
番薯、水牛、闽南人
二十五淑女墓
1949年“国军”入台:一个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眷村:没有血缘的家人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荣民:从部队到工程队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是“本地人”,也是“台湾人”
澎湖案:校长和部分学生被枪决
“相对剥夺感”与“彼此适应”
老荣民的凄凉晚年
“吴凤故事”的巨大影响力
“汤英伸案”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
有没有真正理解少数民族?
什么?他居然是客家人?
从康熙年间说起
说说天地会的故事:林爽文起义
为赢选举,争说自己是客家人
第四章 台湾过去的政治教育
汉语普及与“党化教育”
中小学考试都考“反攻大业”
上了中学,你就是“准军人”
课本上关于“蒋总统”的种种“事迹”
学校老师常用批判态度教“三民主义”
匪夷所思的地理课题
“太原五百完人”
《南海血书》的创作真相
第五章 金门与马祖
当兵的都不想抽到“金马奖”
在金、马当兵的“水鬼”传说
“蒋公”夜会“无头部队”
与“水鬼”换烟
金门的酒、福利和广播站
第六章 禁歌与禁书
从“保卫大台湾”到“包围打台湾”
“东洋味”与“苦酒满杯”
台湾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
被改歌词的民歌与“禁歌之王”
从读书会到私藏禁书
我们叫巴金为“巴克”
小孩帮大人买“党外杂志”
精彩书摘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在台湾,大家一提到山东,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泰山、青岛或蓝翔等标志,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脑中浮出的第一个东西竟然是大馒头,仿佛包子和馒头已经成为山东的符号。包子、馒头、烧饼、油条这些台湾人原本没在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外省人的移入才开始出现在台湾社会。现在台湾社会上有所谓“眷村口味”“眷村菜”,常常都把它当作怀旧料理来操作。眷村菜其实也不是多高明精致的菜,它是指那个年代眷村里的居民,这些老兵在思乡情绪之下,利用台湾本地的食材凑合着,想办法做出家乡口味的食物。
当年军人津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家庭,为了家计,许多眷村的妇女只好走出眷村,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花卷或各省口味的小吃,渐渐地,这些眷村口味也为一般台湾本省民众接受。因为这些眷村口味用的是台湾本地食材,常常没办法做得像家乡那么正宗,再加上大江南北的口味相互交流,左邻右舍互相学习,串门子串出一堆新菜来,就好像混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样,结果反而变成一种有新特色的口味,丰富了台湾本地菜的种类。
比如台湾南部高雄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是辣豆瓣酱。原来岗山也是“国军”空军官校所在地,空军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旁边眷村居住着1949年国民党从成都带走的最后一批空军官兵,他们试着用台湾食材做出四川口味的辣豆瓣酱,没想到久而久之也做出名堂,打出名号,成为岗山当地的特产。
台湾本省人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外省人很大的影响,比如台湾本省人过去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在早期台湾农业社会里,牛算是“工作伙伴”,一头牛在农家里从出生到终老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为了感念牛的辛劳与付出,在早期台湾是不吃牛肉的。这种风俗成为一种家训,直到现在仍有部分人在遵守。
所以,现在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红烧牛肉面”,其实也是这些外省人到台湾后凑合着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红烧汤头,再放美援品里牛肉罐头中的大块牛肉,在台湾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面的情况下,几十年后反而变成人尽皆知的台湾小吃。很多台湾人后来跑到四川去寻找最正宗的川味红烧牛肉面,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是在台湾发明出来的吃法。现在大陆很多“加州李先生”,就是台湾人过个洋水后回大陆开的,不过跟台湾口味落差真的蛮大的。
还有在大陆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浆”也是一样,与台北市一桥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许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选择定居之所。约在20世纪50年代,一群大陆北方人士搬来永和,为了谋生便卖起了豆浆,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开始辛勤工作,磨豆浆、煮豆浆。一开始,台湾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浆这种东西,就跟现在外地人到北京都觉得豆汁味道恶心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经营惨淡。
直到后来几年,台湾的棒球小将屡屡在大赛拿到佳绩,棒球队到外面参加比赛可是大事,这也掀起一股熬夜看转播的热潮。因为时差关系,每回比赛结束后几乎都已半夜或清晨,肚子也开始饿了,当时只有永和的豆浆店开得最早,也是唯一有早餐卖的店,大伙儿索性相约一起去吃早餐,豆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后来这种熬夜看棒球,清晨喝豆浆好像变成一种仪式,桥对面的台北市人也跑过来喝,慢慢地豆浆也传遍台湾,成为台湾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除了眷村里的小食口味,当年国民党大员也从各省带来一流厨师,这些厨师退休后自己跑去开店,所以川、湘、淮扬菜在台湾都有一定的市场。我到上海工作后,周围的朋友觉得我怎么吃得惯上海菜那么甜还有赤油酱汁,就是因为我家楼下就有一家上海老头开的上海菜餐馆,从小吃到大。很多大陆的菜系在台湾又进一步互相融合,发展出新做法,比如在欧美中餐馆必有的名菜左宗棠鸡(GeneralTso'sChicken),就是发明者彭长贵当初融合了湘菜及淮扬菜做法而做出的新菜式。他后来到美国开餐厅,这道菜大受欢迎而流传开来,倒是彭先生再过几年又回到故乡长沙开餐厅,当地人反而吃不惯,餐厅最后只好结束营业。
眷村区隔开了本省人跟外省人,很大程度阻断了两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多台湾本省的小朋友从小就被父母警告,没事不要走到眷村里面。眷村里的小孩也很团结对外,因为他们也总觉得台湾小孩都要欺负他们。
对于大陆的看法,外省人跟本省人也有很大歧义。对于本省人来说,根本就很少人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仅从政府的宣传中得到一个有关大陆的模糊概念,一点都不实际。对于外省人来说,大陆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时常怀念着,就算对于在台湾出生的下一代,也不断向他们描述家乡的美好,什么“唉……台湾的梨哪有老家的梨那么大……”“台湾的区区小溪哪有黄河长江那么壮阔”“台湾这个贫瘠小岛……什么都没大陆好……”,这些说法自然也在外省人的下一代中产生影响。
常常会看到,大陆这边对台湾人喊话总喜欢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试图引起台湾同胞共鸣,可这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那种乡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人以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湾本省人读了,并没什么感觉,对大陆还是感到疏离且陌生。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几十年来,眷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外面社会的封闭小社会系统,对外封闭,对内包容性却极强。在眷村里,各省奇人异士云集,相濡以沫,没事也只能回忆过去瞎扯。就像眷村菜汇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样,我的小学同学骂起街来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调都有:啥马的爸子、赤佬、落块麻麻、×他妈、×你娘(台湾话)……许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外省第二代,就是在那种听遍大江南北故事,尝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种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一种说法是,在眷村里也因此产生了一批在文艺领域创造性极强的作家、艺术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给他们大量创作的沃土,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内容:眷村小孩拉帮结党,与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乡与客居的现实内容。这些除了能让眷村外的民众慢慢了解眷村外,也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会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欢离合的记录。
可想而知,眷村因为组成人员与时代因素,对政治的立场也是相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当时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无时无刻不随着蒋介石他老人家的心愿而澎湃着,一心想“蒋总统”有一天一定会带他们回家。他们算得上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广播站大喇叭播放“蒋总统”语录,墙上也刷着如“反共抗俄”“蒋总统万岁”之类的标语。过去国民党的党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谓的“黄复兴党部”,每次一到选举,党部来一通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所以一直以来也戏称眷村是“铁票部队”。
几年前王伟忠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引起一阵旋风后,继续搬到大陆上演,也引起许多大陆朋友对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陆朋友看了后总觉得眷村生活很和乐美好,还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种意外反应倒是让居住过眷村的台湾外省人吓了一跳,呃,真的有那么好吗,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间的村民会像剧中相处得那么好。一来,照王伟忠自己生活在空军眷村的经验,本来就会好过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艺术虽然来自生活,为了健康向上的戏剧效果,许多负面的地方也不见了,所以也有人笑说像《宝岛一村》和电视剧《光阴的故事》里的眷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眷村,过于美好,却从来不曾存在过。
现在很多人就只记得眷村人情味浓,看到剧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人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展现的不是通常被颂扬的人性光辉,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为一个小社会,自然也是这样,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很多人性的阴暗面也就此产生。
在一些回忆眷村生活的文章、文学作品当中都会看到,因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间狭小,采光不良,房子大都挤在一起,暗暗的湿湿的,你写功课时,隔墙在“推炮”都听得一清二楚。为了搭违章建筑或争公用厨房使用时间,有人写黑函告邻居“通匪”。谁家有些小钱重新装修得好一点,三姑六婆就传说他们家女儿出去“卖”了。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为父母管不了,不学好加入帮派械斗(尽管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轻狂叛逆不羁)。有些外省军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会被排挤,生下的小孩常被骂杂种继续排挤。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真实的眷村,远不如剧里那样梦幻。
最大的误会是很多人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大多数人还是自己想办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整个外省群体。
在来台的外省人里,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还有一些有办法的商人,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说了,到哪里都会有办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亲就属这类人,到台湾后仍然过着上流社会海派生活。高级官僚或军官,也不用担心,继续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们想办法。对公教人员,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会准备宿舍,部队眷村也吸纳了部分来台人员。
用户评价
坦白讲,这本书的阅读门槛不算低,它要求读者对相关的历史脉络有一定的基础认知,否则初读时可能会感到信息量有点过载。但请相信我,一旦你跟上了作者的思路,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俯瞰这段历史。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对文化符号和集体心理的解读。作者巧妙地将政治经济的变迁,与流行文化、艺术思潮甚至是日常用语的演变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图谱。这种跨学科的融合,让原本可能枯燥的社会分析变得生动起来,充满了灵气和启发性。我个人认为,这本书非常适合那些已经读过一些基础历史著作,渴望寻求更深层次、更具批判性视角的读者。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套强大的提问工具。看完之后,我对于如何看待“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有了全新的思考维度。
评分这本书,哇,光是翻开扉页,那股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就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作者的笔触细腻得像是雕刻家手中的刻刀,对那些关键年代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心理的捕捉,简直是入木三分。我尤其欣赏他叙事时那种克制而又充满洞察力的角度,不急着下结论,而是像一个老练的观察者,把各个面向的观点和事实并置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梳理和感受。书中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那些鲜活的个体故事,常常让我停下来,陷入长久的沉思。感觉作者不仅仅是在记录历史的宏大叙事,更是在追问“人”在时代洪流中是如何定位自己、如何适应和抵抗的。对于一个对近现代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盛宴,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全新框架和深度。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过去几十年的台湾社会,有了一种更立体、更具层次感的理解,那种“原来是这样”的豁然开朗,是很多教科书无法给予的体验。
评分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犹豫,毕竟“新版”二字意味着它可能加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也担心它是否会冲淡了原有的那种纯粹感。然而,一旦沉浸进去,那种担忧立刻烟消云散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极好,张弛有度,绝不拖沓。它成功地搭建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但从未让读者迷失在繁复的资料堆砌中。作者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引入一些非常生活化的侧写——比如某个家庭的晚餐谈话,某个工厂的工人群像,这些微观的叙事片段,像闪烁的星光,为冰冷的历史线条增添了人性的温度和真实感。我特别喜欢它对不同政治光谱人士心态的描摹,那种复杂纠结,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被描绘得入木三分,让人在理解历史的同时,也对人性有了更深的共情。这绝不是一本简单的时间线梳理,它更像是一部关于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深度访谈录。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受是:非常“真诚”。作者的叙事态度非常坦荡,他似乎没有刻意去迎合任何既定的立场,而是忠实地记录和呈现他所观察到的复杂现实。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族群关系和身份认同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审慎和包容。它没有简单地把议题标签化,而是深入挖掘了不同群体之间历史性的误解、共同的挣扎,以及在变迁中逐渐形成的微妙平衡。在很多篇章中,作者用近乎散文诗般的笔触,描绘了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社会情绪,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不确定感和偶尔迸发的希望,都被捕捉得栩栩如生。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为我们保留了重要的历史记忆,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冷静的平台,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带着这份历史的重量,走向未来。这是一部需要细嚼慢咽,且回味无穷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充满挑战性的,但绝对是值得的。它的观点锋利,毫不避讳地触及了许多敏感且充满争议的议题。我发现自己常常需要放下书本,去查阅一些辅助资料,以求更全面地理解作者所引用的论据和背景。这种主动的求知过程,恰恰是好书带给读者的最大馈赠——它点燃了你对知识的饥渴。作者在分析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变化时,展现出的那种严谨的逻辑和对数据资料的精准运用,让人肃然起敬。它不像有些历史读物那样追求面面俱到,而是专注于挖掘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深层动力。读到后面,我甚至觉得,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台湾这些年”,不如说是在描绘一个小型社会如何在剧烈的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中,不断自我重塑和定义自身的过程。文字的力量,在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评分可以的,有内容,有提升,包装好,发货快~~~~~
评分京东打折真的太棒了 趁机把书单全部扫空 而且快递速度也特别快 棒棒
评分包装严实,物流迅速,书籍正版,内容丰富
评分早就想看了,赶上满减买的
评分很不错的一本书,作者以平民百姓角度去看台湾!
评分书的内容还可以,装帧印刷质量一般
评分X博士推荐的书,买了上下两侧册,装订很精美。挺赞!盖了自己的私章,哈哈,开卷有益。
评分好书,慢慢看…京东出品是精品
评分不错的书,了解台湾的细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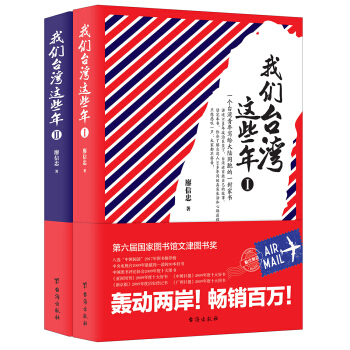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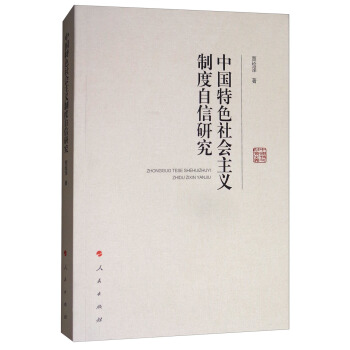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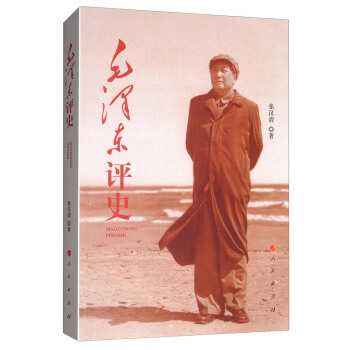
![危机后的世界 [ポスト?クライシスの世界——新多極時代を動かすパワー原理]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29389/5ad8427fN8ec52b6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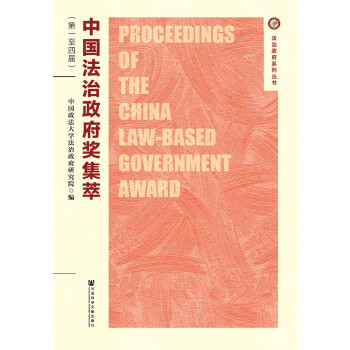
![非洲人在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及其对非洲-中国关系的影响 [Africans in China: A Sociocultural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29411/5acf4d89N58f85c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