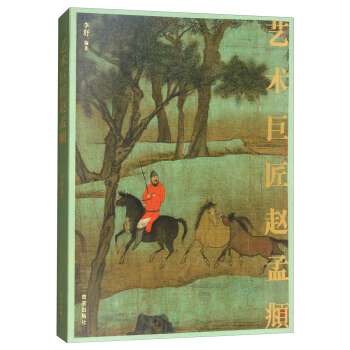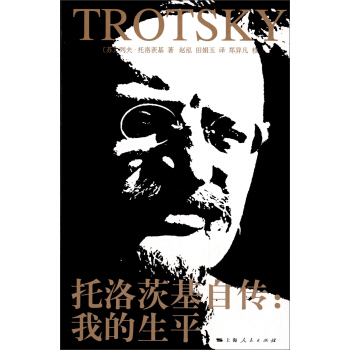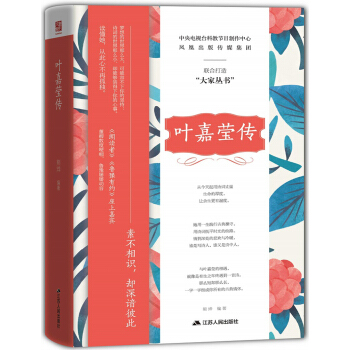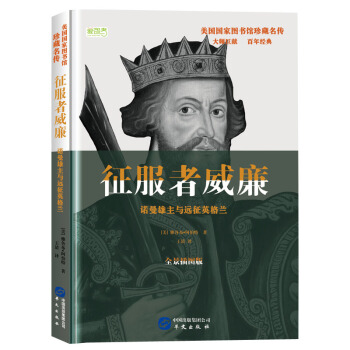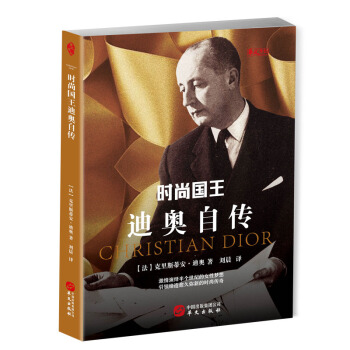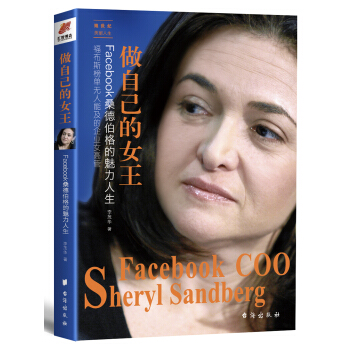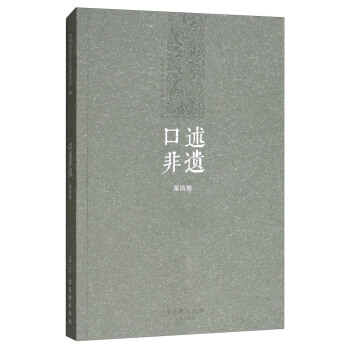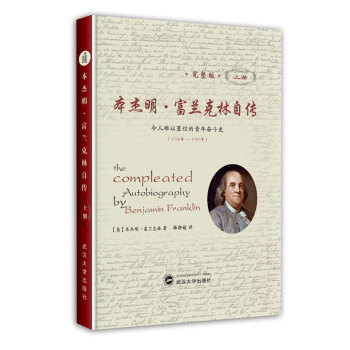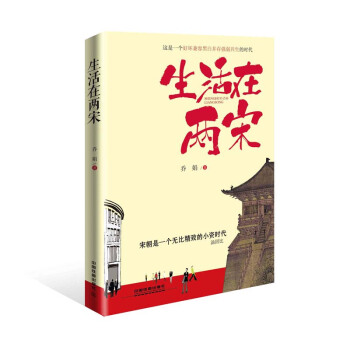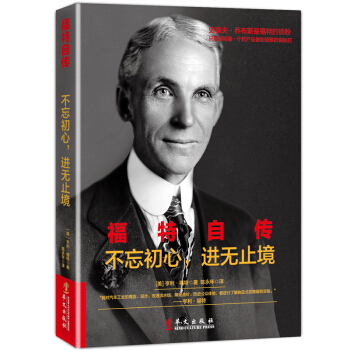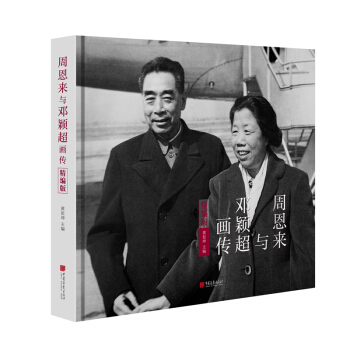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作者选取13位当代中国颇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王明明、盛小云、李鸣岩、薛伟、陈建中、陈幼坚、齐慧娟、六小龄童、董圆圆、郑渊洁、何水法、吴悦石、丁毅,围绕人生故事、心路历程和艺术见解展开对话。他们以画家、音乐家、设计师、戏曲名家、作家等不同身份,坦诚分享求艺之路上的辛酸甘苦,冷静解读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心得体悟。
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在通往成功道路上的艰难求索和寂寞耕耘,看到他们在盛名之下的冷静自省和对人生的豁达淡定。
作者简介
胡正跃,浙江余杭人,职业外交官。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河内大学、外交学院(进修)、美国乔治敦大学(进修)。1976年进入外交部。历任科员、副处长、驻越南使馆一秘、驻新加坡使馆公参、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目录
王明明:笔墨方寸,咫尺天地
盛小云:为评弹艺术而生
李鸣岩:要有肚子里长牙的劲儿
薛伟:从音符到音乐
陈建中:坚守内心的宁静
陈幼坚:工匠精神不能丢,也丢不起
齐慧娟:尽了力子烧炼,方得一粒丹砂
六小龄童:一生只做一件事
董圆圆:缘定京剧,是天赋也是努力
郑渊洁:成功源自赞美
何水法:只有胸中有丘壑,才能有激情
吴悦石:生死刚正谓之骨
丁毅:梁园虽好,心念故土
精彩书摘
郑渊洁:成功源自赞美
胡(胡正跃): 前两天在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看到令尊大人,看上去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感情充沛。您父母都是文化人吗?
郑(郑渊洁): 我生在石家庄,父母都是 1949 年前参加的解放军。父亲是山西人,读过三年私塾,在那个时代的解放军里很少见。因为他的爸爸是中医,所以有点钱。
我妈妈祖籍是浙江绍兴人,祖上是名医,被皇帝的人看中以后,举家从绍兴迁京,成了给妃子看妇科病的御医。这样,我父母两个人就在石家庄认识了。我妈妈在北京出生,后来就读女一中。她当时住在虎坊桥,小时候是骑着自行车去女一中上学,要穿过中南海,那时候中南海是一个街心公园。
但是我家再往上的成分不好,我爷爷是富农,姥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抄家斗死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应该是快 90 岁了。那时候我去看他,他跪在院子的炉灰渣上,旁边是红卫兵。我姥爷是名医,解放以后让他去光明医院当公家的医生,他不去,就要在自己家里行医,这是“文化大革命”斗他的一个原因。我姥爷跟施今墨一块儿办过“华北中医大讲堂”。施今墨比我姥爷有名多了,我姥爷跟他合作办学,培养了好多中医人才。
解放以后,解放军办了军事院校,把有文化的解放军调来当教员,我爸爸被选中了,到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当哲学教员。这时候他认识了我妈,后来结婚了。他们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大约只有 7 平方米的平房里面。我妈妈不是教员,是军校的财务。
我出生以后,因为地方小,我躺在床上都能看到我爸爸在干什么。他干的最多的事就是备课,因为他有压力,他只上过三年私塾,教人家一年,人家就该教他了,所以他要努力。最后他发现看书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大量地买书。当时我看得最多的场景就是他在一个小炕桌上写字、看书、备课。
我今天能当作家,就源于从小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对读书和写字有崇拜心理,因为我想让爸爸跟我玩,但他就是抱着我看书。我看他拿着笔在上面写眉批什么的,我也拿着笔乱画。我们家的《资本论》上现在还有我画的痕迹。其实教育孩子不用说话,身教效果最好。
我爸爸是整个高级步兵学校最能讲课和最能写的人,他讲马列主义讲得下边的人从头笑到尾,全是用故事的方法讲。我小时候听过他的课,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堂课他是这么开始的,他说:“大英博物馆一个桌子下面有两个脚印,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马克思长年累月去看书,看到高兴的时候就来回搓这个脚,把水泥地搓出印来……”最后他说:“马克思主义就在这诞生的,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
解放军后来成立一个部门,叫总政。总政就要到各个军事院校去挑能写的人,挑到石家庄高级步校,就找到校长滕海清,滕海清是开国上将。滕海清说:“我给你推荐小郑。”这一推荐我们全家就去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我上了西直门总政第一幼儿园。
胡: 你的小学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它对你后来的文学生涯有何影响?
郑: 到了该上学的时候,院里的孩子就都去了八一学校,军队的。我爸爸也想让我去,他带我报名去了。报名的时候人家就不要我,为什么呢?只收校官以上的孩子,我爸爸当时是大尉,他级别不够。当时我觉得他很失败,他很没面子。别的小孩都贬低过我,说:“你上不了八一校。”我说:“为什么?你们怎么能上?”他们说:“你爸不是少校。”后来我果然被拒之门外了。
那是 1962 年,我爸爸居然想让我上重点小学,也是很超前的。我记得八一学校门口有一条河,等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我爸爸一脚把石头踢到河里去了。我当时从他这个动作知道他很沮丧,当着儿子很没面子。他说:“那咱们就上管片儿的小学。”管片儿的小学叫马甸小学,当时马甸还全是坟地。马甸小学就是一个农村小学。去了以后第一天上学,老师说:“除了背书包,你们还要背一个东西。”我们说:“背什么?”说找一个篮子,干什么?捡马粪。那时候那里叫学院东路,就是现在的三环东路,跑的主要是马车,马会随地大小便。当时我们学校门口的贫下中农还需要种地,就让我们这些学生义务给他们捡马粪。就这么一个学校,条件很差。但是我三生有幸,碰到了好老师。
她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叫赵俐,当时 17 岁,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第一年教书,喜欢文学。她在小学二年级教作文。有一天她说:“今天我教你们写文章,我出一个题目,下课铃响的时候,你们组织一篇文章出来。”题目是《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她说:“你们想将来有出息吗?”我们说:“特想!”她说:“那小时候就得有远大理想。”我们说:“怎么叫有远大理想?”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反正就当这些有头有脸的,全都被她说了一遍,然后说:“开始写吧。”我们就开始写。
我妈妈是特有个性的人,从小她就告诉我一句话叫:“哪人多,你就别去哪。”我说:“为什么?”她说:“人多的地方不安全。”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跟别人一样。结果我就想,我妈从小这么告诉我,我没机会实践,我今天试试吧,老师都让我们说有远大理想,我就故意写一个谁也不会写的职业。
下课铃响了,我这作文就交上去了,题目就是《我长大了掏大粪》。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劳模叫时传祥,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跟他握手。我就说他的故事,我说我长大就要掏大粪。交上去以后我觉得很紧张,老师会不会觉得我跟她捣乱呢。
结果过了一个半月,有一天上课老师说:“郑渊洁,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她说:“你到前边来。”我到前边去了,我以为我犯事了。她说:“你在一个半月之前写的那篇《我长大了掏大粪》,老师认为与众不同,很有新意,给你推荐到学校的校刊上发表了。你现在免费领两本,其他同学每人花一毛八分钱买一本。”那一瞬间我就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全世界我郑渊洁写文章写得最好,谁也写不过我,这肯定是错觉,但这错觉一直保留到今天。要没这一下,我今天根本不可能以这个身份坐在这,一点可能都没有。从这件事情以后,她只要一留作文,我一写,就是范文。
董圆圆:缘定京剧,是天赋也是努力
由尚转梅,开排新戏
胡(胡正跃):之前您还是尚派,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梅派的?
董(董圆圆):从到北京开始,我的艺术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原本我是想继承尚派艺术的,而且一直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尚派戏,直到1987年的一天晚上,我特别有幸看到梅葆玖先生演出的《凤还巢》。当时我被师父的演唱、念白那纯正的梅派韵味和大气端庄的台风深深吸引,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梅派,我想我追求的,应该就是这样的艺术风格。机缘巧合,1987年中国戏曲学院校庆,院领导安排我演《霸王别姬》,为此特别请来了梅葆玖先生给我说这出戏,而且还请景荣庆先生提携我演霸王。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幸运了,做梦也想不到学演第一出梅派戏,就是跟梅葆玖先生学的。这出戏的唱、念、表演、剑舞都是先生一字一句、手把手教给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位于干面胡同的家中去学习的情景:我去的时候,虽事先约好了,但梅先生碰巧还没回来,家里只有我师娘在——那时候还没叫师娘,我叫阿姨。她说玖叔还没回来,叫我等他一会儿。一会儿,玖叔回来了——那时候我称他玖叔。玖叔叫我一起吃饭——炸酱面,我因为已经吃过了就到另外一间屋等着。他吃完饭开始一字一句给我说戏,到后来我们又换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北京京剧院老排练厅说身段和剑舞。
中间有件事特别令我遗憾,最后学舞剑的时候,我师父拿把剑,用大录音机放伴奏,跟着音乐的节奏教我。等我们俩练完已经晚上了,吃完晚饭我们想起来剑没拿,再回去排练厅找的时候门已经关了。第二天早上再去,这把剑就不见了,问谁都说没见着。后来我师父说,这把剑是当年梅大师用过的,丢了蛮可惜的,其实也是很珍贵的文物了。为了给我说这出戏,还丢了把剑,我特后悔。之后我又有幸接触另外一位老师——姜凤山先生,我叫他姜爷爷,就是给梅大师操琴的,还参与了《穆桂英挂帅》的编腔。他一辈子钻研梅派,对梅派的节奏、尺寸、韵味、劲头儿,研究掌握得太熟悉了。姜爷爷给我说唱,给我吊嗓子,台上给我伴奏。说来也巧,他跟我姥姥、我妈妈都合作过,算上我等于拉过我们家三代人。我是那种悟性较好又很刻苦认真的人,两位老师都喜欢我,说我很努力很勤奋,都说教我很省心。我从1987年开始学梅派到今天已经 30年了,向师父、姜爷爷学习了几乎所有梅派经典剧目:《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西施》《太真外传》《凤还巢》等。
胡:您是什么时候拜梅先生为师的?
董:我真正拜梅葆玖先生为师是 1995年。我学了这么多年,才敢说我想拜师,因为始终觉着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不够格,不敢说,不敢提。1995 年,北京京剧院重新恢复成立梅兰芳京剧团,5月4日成立,师父安排我 5月1日拜师,正式拜入梅门。他觉得“梅派”艺术这杆大旗他得扛起来,师父当时把我调入梅兰芳京剧团,建团那天我唱的还是《霸王别姬》。
董圆圆与师父梅葆玖先生合影(西施)
胡:“梅派”和“尚派”一样,可以说都是京剧由成熟走向鼎盛的标志。
董:是的。20世纪50年代,京剧绝对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个时候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还有很多大艺术家都还健在,出了一大批的经典剧目。那时候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党和国家来扶持、管理剧团。之前私人剧团是为了养家糊口,真正出精品还得靠国家扶持,把好角儿都集中在一起,可想而知这是多高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梅大师创演的《穆桂英挂帅》,观众席里坐的是毛主席、周总理,那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重视京剧,也真心喜欢、懂京剧。所以50年代是京剧艺术的巅峰时代。
胡:您拜入梅门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董:我拜入梅门后一直跟着师父好好继承,不但继承梅派艺术,更要继承梅兰芳大师永无止境的创新精神。我越学越演,就越爱梅派,越能感受到梅派艺术的博大精深。梅派艺术是这样,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不难,越学越觉得它深奥。我觉得任何东西,越简单大方的,也是越难的。由简到繁,由繁到简,艺术肯定都是这个过程。
京剧讲究传、帮、带,在我二三十岁艺术成长的关键时刻,我师父带我同台演出,两人分饰同一角色,比如《龙凤呈祥》《西施》等。同时,他还请很多好角儿提携我同台演出。第一位提携我的是景荣庆老师,后来是谭元寿老师——我叫他谭大爷,他跟我爸是师兄弟。粗略算来,先后提携过我的人有景荣庆、谭元寿、马长礼、张春华、尚长荣、叶少兰、张学津、计镇华等艺术大家。我师父一直希望有年轻人把梅派传下去,所以我在梅剧团这些年得到我师父和姜爷爷的栽培与扶持,学演了大量的梅派戏,而且几乎把所有梅派经典剧目都演了。
用户评价
这本书对我而言,是一次与智者对话的绝佳机会。我一直对那些在各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们充满好奇,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成功”的,又是如何理解“技艺”的。而这本书,恰好满足了我所有的疑问。对话的艺术大家们,他们用最朴实而又最深刻的语言,阐释了“功名”的真正含义。在我看来,那不是浮于表面的光环,而是内心价值的实现,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对时代精神的引领。而“功夫”,则被赋予了更加广阔的维度,它不仅仅局限于艺术技巧,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情,一种对专业的敬畏,一种对自我不断的打磨和超越。我惊叹于他们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他们的话语如同星辰大海,引导我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我喜欢书中那种开放式的探讨,没有绝对的答案,只有不断的追问和反思,这让我感觉自己也在参与到这场思想的盛宴中。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心中对于“成就”与“技艺”的迷茫,让我看到了通往更高精神境界的可能性。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我曾以为“功名”是人人追逐的末路,而“功夫”则是少数人才能企及的绝境,但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全然不同的解读。那些文化艺术大家们,他们将“功名”看作是自身价值的自然流露,是为社会奉献后应得的肯定,而非盲目追逐的虚荣。而“功夫”,则被描绘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对任何事物的认真投入,一种对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无论是在艺术创作,还是在人生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我特别欣赏书中那些关于“坚持”与“突破”的讨论,它们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我看到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在探索未知时的勇气,以及在突破自我时的豁达。每当读到他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会深有感触,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礼。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功名”与“功夫”,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蕴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和践行。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的渴望,也指引了我们前行的方向。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本打开的任意门,每一次翻阅都能带我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世界。初读时,我被那些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对话深深吸引,感觉像是坐在一间古老的茶馆里,听着几位智者抚须而谈,他们的声音穿越时空,抵达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书中人物的视角之广阔,让我得以窥见他们如何看待“功名”这个古老命题在当代文化艺术语境下的变迁,以及“功夫”——那种技艺的极致追求、精神的沉淀与锤炼——在现代人心中所承载的全新意义。我尤其着迷于他们如何将自身在各自领域的深耕细作,与对社会、时代、人性的洞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那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实则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考,引导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它不像一本枯燥的说教手册,更像是一场场引人入胜的思想漫游,每一次都伴随着豁然开朗的欣喜。我常常会在读完一段对话后,停下来,久久地回味,仿佛自己也参与了那场思想的盛宴,感受着那些文化大家们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与强大生命力。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能让你在阅读中不断地自我审视。我曾经以为“功名”就是金钱与地位的象征,而“功夫”就是精湛的技艺,但阅读了这本书后,我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些文化艺术大家们的对话,让我看到了“功名”的另一种解读:它是一种对社会贡献的认可,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生命影响力的延伸。而“功夫”,则被升华为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对专业的极致追求,一种对自我不断超越的内在驱动力。我被他们身上那种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所折服,他们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突破自我,敢于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内心的宁静与专注。书中关于“传承”与“创新”的讨论,尤其让我受益匪浅,它教会我如何在继承前人的智慧的基础上,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每次合上这本书,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充实和启发,仿佛自己也汲取了那些文化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变得更加坚定和从容。它是一次心灵的涤荡,让我重新认识了“功名”与“功夫”的真谛,也让我看到了生命更广阔的可能性。
评分这是一次充满惊喜的文化探索之旅。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本关于名利与技艺的书,但翻开后才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和深刻得多。书中的各位文化艺术大家,他们的声音如同一串串跳动的音符,奏响了时代的华彩乐章。我惊叹于他们对“功名”的豁达与超脱,那不是对物质的贪恋,而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是对社会贡献的认可。而“功夫”二字,则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它不再仅仅是技巧的熟练,更是对精神境界的不断攀升,是匠心独运的体现,是灵魂的磨砺。我喜欢书中那种率真自然的交流方式,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矫揉造作的辞藻,只有最纯粹的思想碰撞。他们谈论创作的艰辛,分享灵感的涌现,剖析艺术的本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艺术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时代变迁的深刻理解。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视野被极大地拓宽了,对艺术、对人生、对“功名”和“功夫”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像一位睿智的长者,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教会我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对理想的追求。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