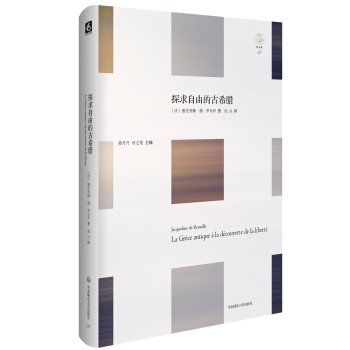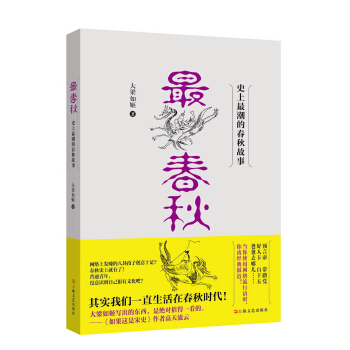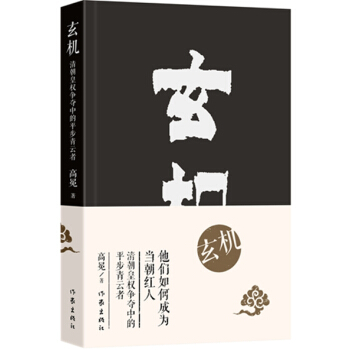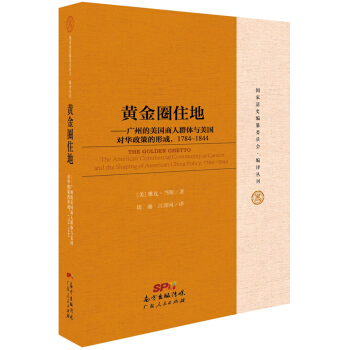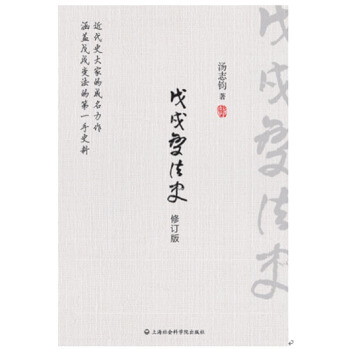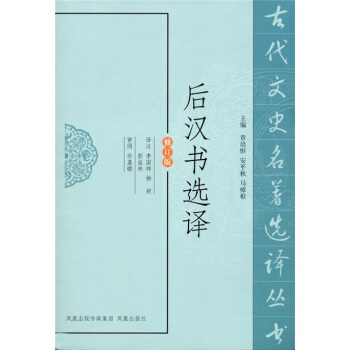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后汉书选译(修订版)》收录原文,加以简明的注释,力求准确地译为现代汉语,半于每一篇之前写有对该文的提示性说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收录种类相对齐全、译注质量较高的一本普及传统文化的今译书。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光武皇帝本纪
献帝伏皇后纪
刘玄传
冯异传
札诗传
梁冀传
郑玄传
班固传
王充传
仲长统传
张衡传
陈蕃传
张俭传
董卓传
张鲁传
王景传
阳球传
宦者列传序
蔡伦传
单超等传
许慎传
逸民列传序
严光传
曹世叔妻传
乐羊子妻传
编纂始末
丛书总目
精彩书摘
永兴二年,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总计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为大将军,妇人和女儿有食邑和“君”封号的七人,娶公主为妻的三人,其余担任卿、将、尹、校等职位的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权势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朝廷内外大施淫威,所有官员都不敢正面而视,没有谁敢违背他的命令,皇帝也只得对他恭敬,一切政务都不能亲自过问。桓帝对梁冀早就不满。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皇帝报告,发生灾害和日蚀等变异现象,罪过在于大将军。梁冀知道此事,就暗示洛阳令将陈授逮捕拷问,害死在狱中。桓帝由此发怒。当初,在掖庭供职的邓香的妻子宣,生了个女儿邓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父。孙寿将邓猛送进后宫,得到桓帝的宠幸,尊为贵人。因此梁冀想认邓猛做女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把邓猛改姓为梁。当时邓猛的姐夫邴尊任议郎之职,梁冀怕邴尊阻止宣让女儿改姓,于是在偃城结交了一个刺客,将邴尊刺死,又想把宣也杀掉。宣家住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为邻,梁冀派刺客登上袁家的房屋,打算从那里进入宣家。袁赦发觉了这件事,就击鼓集合众人,把事情告诉了宣。宣立即赶进宫向桓帝报告。桓帝大怒,于是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共同商定计谋,诛杀梁冀。这件事记载在《宦者传》里。
梁冀疑心单超等人,于是派中黄门张恽进宫值宿,以防单超等发动事变。具瑗就命令宫中小吏将张恽逮捕,罪名是擅入官禁,图谋不轨。桓帝因此来到前殿,把尚书们都召进来,公布了这件事,派尚书令尹勋拿着符节总领尚书丞和尚书郎以下官员,都手持武器守卫宫中各官署。集中所有的符节,送进宫中。派黄门令具瑗率领左右厩的骑士、虎贲勇士、羽林军和都候剑戟士等,合计有千余人,会同司隶校尉张彪,一起包围了梁冀的府第。派光禄勋袁盱持符节前去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降封他为比景都乡侯。
梁冀和妻子孙寿当天都自杀了。悉数逮捕了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族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梁氏官员,以及孙氏在朝廷内外的宗族和亲戚,把他们都关进诏狱,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梁不疑和梁蒙早已去世。其他牵连到的公卿、列校、剌史和郡守等被杀的共几十人,梁冀过去的属吏和宾客罢官和免职的三百多人,朝廷因此都空了,只有尚书令尹勋,光禄勋袁盱和廷尉邯郸义三人还在任上。
用户评价
阅读体验上,这本书成功地打破了我对传统史书的固有印象——即“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这种积极的阅读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流畅的叙事节奏。那些被选取的片段,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衔接,使得历史事件的推进过程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它没有将历史的演变简化为枯燥的年代罗列,而是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说书人,知道何时需要快进,何时需要慢条斯理地描绘冲突的高潮。特别是那些描绘特定人物性格和决策瞬间的文字,被翻译得极富画面感,让人能够轻易地代入情境,体会到历史人物在面对重大抉择时的纠结与挣扎。这种‘可读性’并非牺牲了深度,而是在深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化重构。可以说,它巧妙地架设起了一座桥梁,连接了严谨的史学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好奇心,让了解汉代风云不再是一件望而生畏的任务,而成为一种愉悦的智力探险。
评分这本书的导读和注释部分,可以说是我认为它价值所在的核心。我以前尝试阅读一些古代史籍的白话译本,常常会因为翻译腔过重或者对文化背景的解释过于肤浅而感到乏味,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的译文保持了足够的文雅和准确性,既没有生硬地用现代口语去“拉低”原文的格调,也没有晦涩难懂到需要频繁查阅工具书的程度,找到了一种非常优雅的平衡点。更值得称赞的是那些详尽的注释。每当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复杂的典章制度或者一个地域性的专有名词时,总能发现页脚有清晰而深入的解读。这些注释不是简单地解释词义,而是往往会引申出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分析,甚至会对比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这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理解维度。这说明编纂者不仅是文字的搬运工,更是深谙史学精髓的学者,他们深知一个不甚了解当时社会运作规律的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卡在哪里,并提前为我们铺好了所有必要的知识桥梁。
评分作为一部历史选本,这本书在选材上的考量体现了极高的水准和清晰的史学脉络梳理意图。它并没有一股脑地堆砌所有内容,而是非常精准地挑选了那些构筑了东汉历史关键转折点的核心篇章。例如,对于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这些历史性的痛点,它所选取的段落往往是论述最精辟、矛盾冲突最集中的部分,读起来酣畅淋漓,脉络清晰得仿佛眼前正在上演一场历史大戏。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社会风貌描摹时的细致。除了帝王将相的政治博弈,书中对于当时的士族阶层的生活状态、地方豪强的崛起、乃至一些底层民生的记载,都有所侧重。这种全景式的视角,使得东汉不再是一个扁平化的概念,而是拥有了立体感的社会结构。通过这些精选的文本片段,我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忧思、儒家思想的演变轨迹,以及权力更迭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远比单纯阅读大部头史书更具效率和洞察力。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很有质感,封面淡雅的米黄色调配上古朴的字体,初见就给人一种沉稳而厚重的感觉,这和它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非常契合。拿到手里掂量一下,分量十足,能感觉到印刷和纸张的质量都很扎实,显然不是那种拿来看一两遍就束之高阁的速食读物,而是能陪伴读者细细品味的工具书。我特别喜欢那种油墨散发出的淡淡的纸张气息,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过去,好像正在翻阅一本尘封已久的古籍。内页的排版也处理得相当精妙,行距和字号的比例掌握得恰到好处,即便是对于初次接触史书的读者来说,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压迫感。最让我满意的是,他们似乎在细节之处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页眉页脚的留白处理,既保证了信息的可读性,又没有显得过于拥挤,整体视觉体验非常舒适。这样的用心,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减少了许多视觉疲劳,可以更专注于文本本身的内容。这种对实体书品质的执着,如今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实在难能可贵,值得每一个热爱阅读的人珍藏。
评分从学术参考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修订版确实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努力。我注意到,相较于一些老旧的旧版选本,这次的版本在某些关键史实的引用和人名的翻译上进行了审慎的校订,这在专业的史学研究者看来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它仿佛是一扇门,让那些希望深入研究魏晋南北朝前奏的年轻学者,能够站在一个更为稳固和准确的起点上开始探索。此外,编者对于某些争议性事件的处理方式也显得尤为审慎和客观,他们倾向于呈现不同学派的观点,而非武断地下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佳的史学态度示范。这种严谨性体现在字里行间,让人在使用时倍感可靠。我甚至可以预见,在撰写任何与汉末历史相关的学术报告时,这本书的某些段落和注释将是极佳的旁证资料,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像是一个被精心维护的“历史参考工具箱”。
评分据说是根据以前的巴蜀出版社再版的……还可以吧,但我总觉得书籍怪怪的……
评分价格比较便宜,非常不错。
评分物流特别快,配送员相当负责,商品质量很好,堪称精品。
评分好
评分物流到货为什么不来电话?
评分华中师范大学学者选译,很信服
评分好书 不错我喜 支持京东
评分华中师范大学学者选译,很信服
评分前四史中的一部,推荐购买。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太平天国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704406/f33b63e4-6e99-403e-be80-5ea974441b9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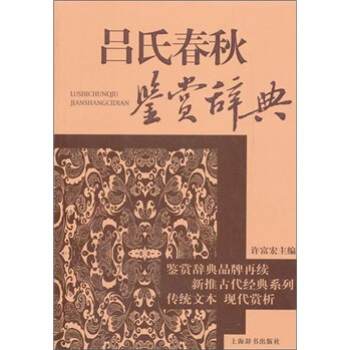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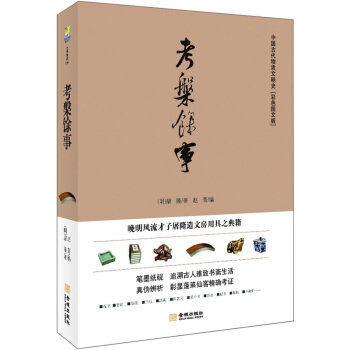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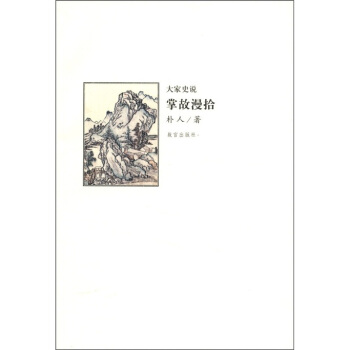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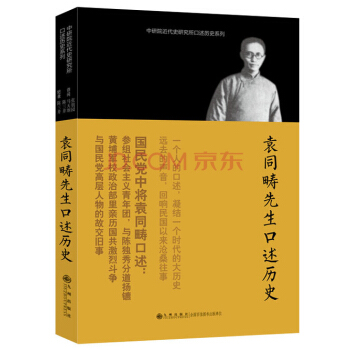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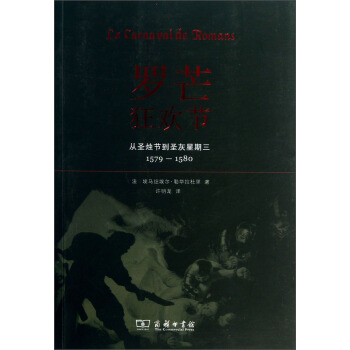
![欧洲风化史:风流世纪 [A Survey on Sexual Life in Europ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8652/rBEhVFKds5gIAAAAABQMQAITD7QAAGTdAILdTsAFAxY5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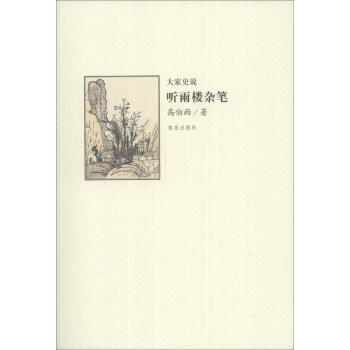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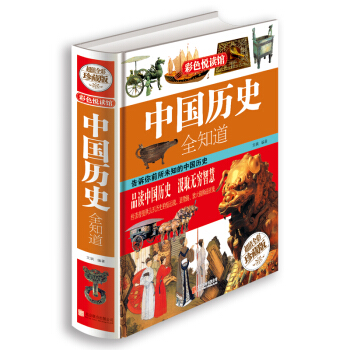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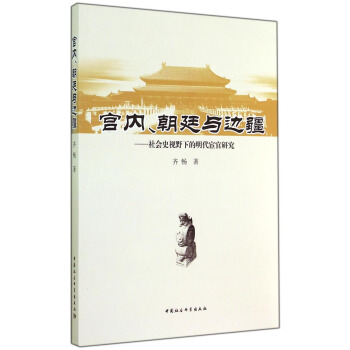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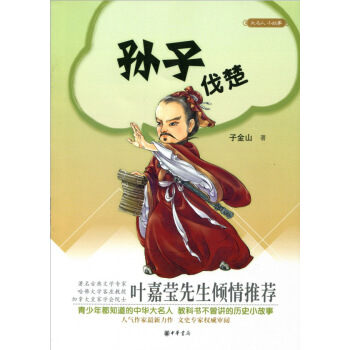
![第三帝国:非洲军团(修订本) [The Third Reich: Afrikakorp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9818/54d48a8cN01e9180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