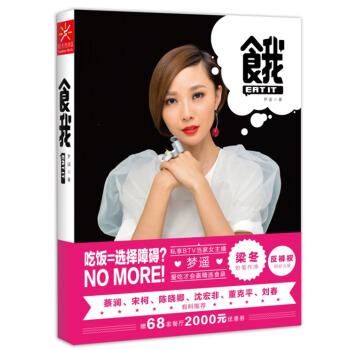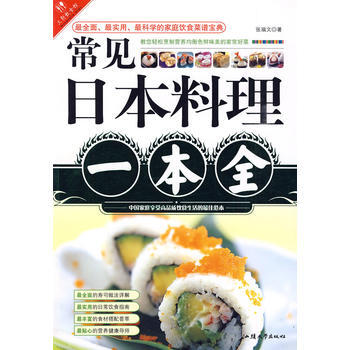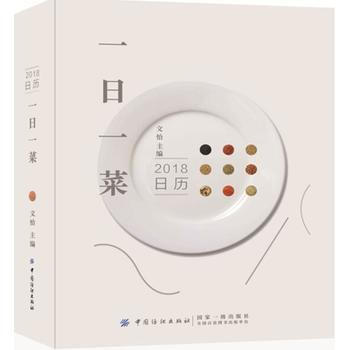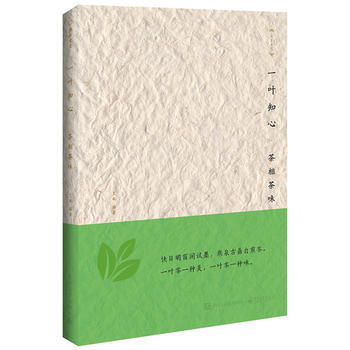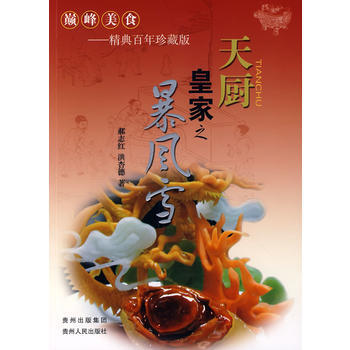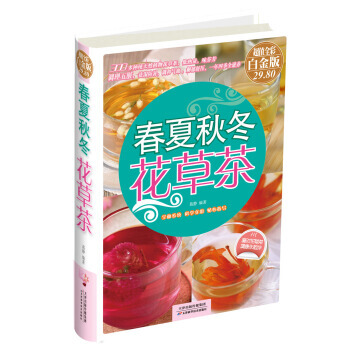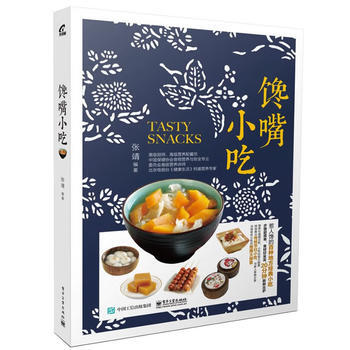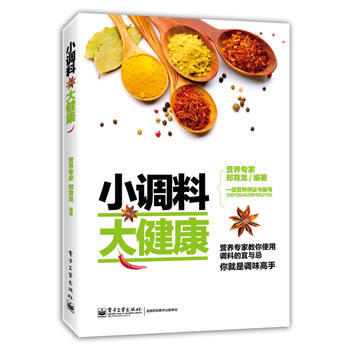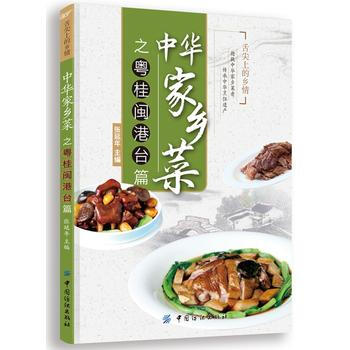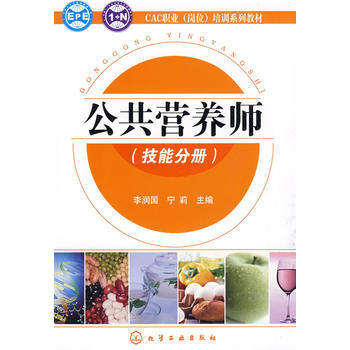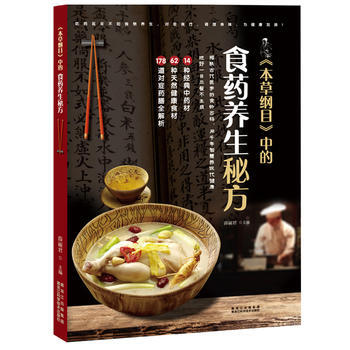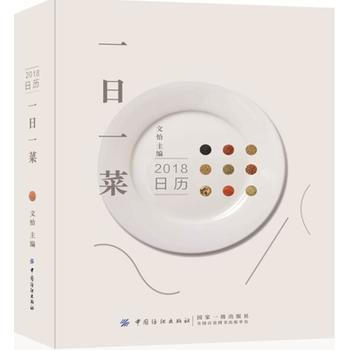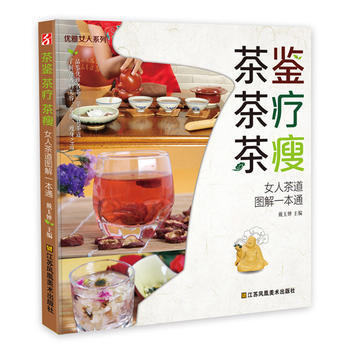具体描述
基本信息
书名:民间有味
定价:30.0元
作者:李汀
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9-01
ISBN:9787563944033
字数:129000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作者笔下的唯美乡村不欺不、不卑不亢、不弃不离,不怒不怨;作者笔下的美食有情有味,来自民间、食在民间;纯粹的野生美食,原始的土生食材,带给你舌尖上的快意人生……
※※友情推荐:
href='#' target='_blank'>饮啄杂谭、 href='#' target='_blank'>吮指谈吃、 href='#' target='_blank'>人间烟火、 href='#' target='_blank'>民间有味、 href='#' target='_blank'>川味好安逸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选择从一条味蕾的小径回乡,将川北民间饮食从文字中复活、唤醒,这一篇篇舌尖上的记忆,一道道大道至简的纯粹民间山野美食,浓浓的乡土感铺天盖地而来,过瘾、快意,有味道。
目录
作者介绍
李汀,男人一枚,四十好几。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做人从善,做事从简。孤陋寡闻,不通世情。文字敏感,想象简单。活着走着,走着累着。有时读闲书,无聊观山水。感谢文字,感恩生活。
文摘
辑土风
豆花珍珍饭
缺吃的年代,有玉米面吃的是殷实人家。把玉米磨成针尖一样的颗粒,黄的、白的堆在一起,闪亮闪亮的,不叫珍珠,我老家叫珍珍。这叫法现在一想起,感觉就像叫一个殷胖的女人,洁白、干净。
清晨,天蒙蒙亮,母亲要把一簸箕玉米磨成珍珍。玉米倒在磨台上,牵了磨坊外站着的枣红马,轻轻把拉磨的套子架在马背上,把磨杆咕噜咕噜推到马屁股后套好。母亲走到马前,把眼罩给它戴上。枣红马静静地站在磨坊的阳光下等待母亲做好这一切。母亲一拍马的肩膀,喊一声“走”,枣红马慢悠悠地摇晃着铃铛,稳稳地在磨道上来回转,玉米面筛糠一样磨下来。太阳在悠悠的铃铛声中慢慢升起。
母亲站在磨坊边上箩玉米面。深口的大簸箕上架着两个枝条的树杈,用镰刀把树枝打平,马尾箩儿放在上面,来回箩,树杈被磨得油亮。一箩儿玉米面来回箩四五遍,细面落在大簸箕里,粗颗粒留在细面箩儿里,匀出粗一点的颗粒重新倒回磨台,留在马尾箩里的就是颗粒均匀的珍珍了。细面用来蒸玉米面馍馍。珍珍用来煮豆花稀饭。悠悠马铃铛,悠悠箩面声,早晨的阳光照上木窗子。
先点豆花。铁锅上放一木架,将生丝或马尾箩儿放在架上,再把从手磨上磨好的豆浆倒进箩儿内,再让豆浆淌进锅里,同时灶内的柴火烧得正旺,并用水瓢往箩中投水,让豆浆一次次注入锅内,往返三四次。不断加温,豆浆慢慢沸腾,豆浆煮起来,将准备好的酸水,沿锅边倒下,将灶火退去。这一连贯性的动作,有民谣说:“屎胀、娃儿哭、豆浆瀑”,这是家乡妇女煮早饭的情境,自己的肠胃胀流了,内急;背上背的娃儿还在哭,心急。就是有这两急的事情,也要先解决急火的事情,止住沸腾的豆浆瀑出锅沿。此后,数次注入酸水,直到大砣的豆花浮起,豆浆水转清。再加柴火将水煮开,放些红苕或者洋芋煮,等红苕、洋芋半熟,然后抓一把刚磨的珍珍,摇晃摇晃让珍珍从手掌里徐徐漏下,用饭勺不停地搅动。这时候,柴火要旺,不能闪火。一边煮一边搅。放上盐,二十来分钟就可以吃豆花珍珍饭了。
再拌一盘火烧青椒拌蒜泥。地里的青辣子摘了洗净,用火钳钳着青辣子在滚烫的柴灰里翻滚,听见青辣子在柴灰里噼噼啪啪响。青辣子在柴灰里烫过后,辣味减了,清香溢出来。撸三五下,把烫蔫的青辣子放在木碓窝里,和着新蒜和盐捣碎,装进瓷盘子。一盘火烧青椒拌蒜泥放在木桌上,满屋子都是瓷实的清香。一筷子青椒拌蒜泥,一口豆花珍珍饭,那个香啊。
山里人每天早上都吃豆花珍珍饭。端一碗豆花珍珍饭,蹲在土院坝里,一条狗陪在身边。有时候,丢给它一块红苕或洋芋,狗歪着脑袋吞下去。然后,又静静地坐在主人身边,望着主人。稀点的豆花珍珍饭要沿着碗沿往下喝,“呼呼呼”,像是口技比赛。一碗豆花珍珍饭吃完,主人站起来舔舔舌头,又去厨房盛第二碗,狗也跟在主人身后舔舔舌头。
吃剩的豆花珍珍饭,一锅铲铲进厨房门外的狗盆里,狗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再把钢瓷盆子舔得“噌噌”响。遇到邻家的狗跑过来,两只狗兴奋地碰碰脑袋,亲热亲热。就像东家的主人端碗珍珍饭,西家的主人端碗珍珍饭,一边吃,一边谈论着庄稼地里的收成。再是,趁着院坝里的阳光好,狗也追撵追撵院坝里踱步的一群鸡,把鸡撵上房顶、撵上树枝、撵上草垛,撵得一院坝安静的阳光飘飘摇摇,撵得一院坝的尘土飞扬。
我已经离开村庄多年,老家木门上的锁已经锈迹斑斑,土院子里野草丛生。但我一想起村庄,心里立马翻腾起对农家饭菜的奇妙感觉,口水生津,我隐隐觉得,木结籽的内心,一直没有远离过乡村。而我终于明白,草木结籽的内心,豆花珍珍饭填饱的胃,我永远不了一个普普通通乡村人。
酸菜面鱼儿
酸菜缸挺着大肚子放在案板下,要吃了,掀开木盖子,舀一瓢出来。酸菜漩漩扯起,地上马上流出一条酸菜水滴成的路线,从酸菜缸到土灶台,就像一条水蛇躺在地上。
萝卜菜、山油菜扯回来,太阳坝里晒干露水。女人搭根板凳坐下来,把萝卜菜、山油菜上的泥巴抖干净,放进竹篾篓里切细。那青菜的山味,青菜的气息扑进鼻子。
女人端起切细的萝卜菜、山油菜,一阵风去了小河边,蹲下,翘起钩子,淘菜。阳光打过来,女人白嫩嫩的手臂上下翻动,青菜浮在竹篾篓里。翘起的钩子露出一抹白,时隐时现。河水里的木叶子鱼,在阳光里跳跃,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菜淘好了,女人把竹篾篓从水里拉出来,放在河边石头上,等竹篾篓里的水渗下。女人站在河边,看见水里印着自己的影子,笑了笑。一只五彩的水鸟飞过,“呀”叫了一声。女人抬头端起竹篾篓,走上那条小路,竹篾篓里的水还在“滴答滴答”滴。
淘好的菜放在街沿上,等铁锅里的水烧开,再把淘好的萝卜菜、山油菜在开水里煮上约十分钟,等青菜稍稍变了颜色,连水舀进案板下的缸缸里,加上一小把玉米面,再加上小瓢酸菜缸里原来的酸菜,搅匀,盖上木板,第二天,就可以吃酸菜了。一缸酸菜,一家四五口人,够吃上半个月了。
酸菜越酸越好。酸得人口水直流,那个酸呀,泥土的气息,陈醋的味道,木质的香醇,阳光的瓷实,都在那酸里。要是山油菜榨的酸菜,还有短短的苦,还有青草的脆,还有露水的净。如今,酸菜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某品牌老坛酸菜牛肉面撑起这个品牌方便面的半壁河山,靠的就是酸菜那股味儿。乡村的酸菜缸放在案板下,要吃了,舀一瓢倒进锅里,从酸菜缸里扯出来的酸水漩漩,一路滴进锅里。那个酸呀,大热天渴了,喝一瓢生酸菜水,渴倒是不渴了,可酸得打战战。
酸菜做好了,做一顿酸菜面鱼儿。舀一瓢酸菜,用菜油,加生姜丝、大蒜片、干红辣子爆炒。炒好后,用碗把酸菜盛起来。烧水和面。用柴火将铁锅里的水烧开。烧水的同时,把小麦面盛在面盆里,倒进冷水,用竹筷朝一个方向调,一圈一圈调,小麦面和水融成一体,干稀适度,过干,滴不成“面鱼子”;过稀,就成了面汤。干了,加点冷水再调;稀了,加点小麦面。
水烧开后,把面盆端在手上,欲往锅里倒的样子,但又不能叫面溢出盆来,然后用竹筷迅速往锅里刮调好的麦面。这时灶里的柴火不能“闪火”。一“闪火”,刮进锅里的面鱼子就结成面团团,就不是“面条条”了。等面鱼儿在锅里煮起来,再把爆炒好的酸菜倒进去,再煮上一阵,香喷喷的“面鱼儿”就可以起锅了。说起来,我小时候,家里穷,一年难得吃到一回“面鱼儿”。母亲做“面鱼儿”时,我个头就土灶头那么高,踮起两只脚,两眼看母亲往锅里刮面,就想,哪天长大,会做“面鱼儿”了,做一大锅,吃个够。
土灶,柴火,做出的酸菜面鱼儿,唏嘘吃着,那个香啊。再一想,这面鱼儿的叫法,就不由想起小河水里跳跃的木叶子鱼,把小麦面做成小河鱼的样子,做成小河鱼的味道,只有在这乡村了。再一想那柴火“噗噗”燃着,俗话说:“咬紧牙关,绝不能‘闪火’。”这样的紧要关头,犹如背一背东西爬坡上坎,腿上一“闪火”,那情景想得出来,山坡上滚石头一样越滚越快。
面鱼儿吃得大汗淋漓,那个畅快,像是打开身体的血管,身体变得异常干净、清新。
风中灰搅团
在我乡村的风里,拂面的人群里,已找不出几个我熟悉的身影。但我可以借助乡村的炊烟,找到贴近乡土胸膛的呼吸。
一位老人站在院坝里,端着一碗灰搅团,“呼噜呼噜”吃着,我对乡村的记忆,一下子被摇醒了。老人起身,那草木一样的身子,草木一样的表情,使我的脸上,有一双手滑过的感觉。熟悉的温度,重新回到我的脑海。
我说:“灰搅团开胃,好浇上一小瓢熟油辣子,辣乎乎的,酸溜溜的。”
老人又咂吧一下嘴巴说:“用腊肉颗颗炒青菜,做成腊肉汁浇在碗里,好吃。”
我说:“用郫县豆瓣炒料,烧成汤汁,过瘾。”
老人说:“吃搅团,关键是汤汁呢,少不了麻油。”
我说:“别说了,我口水都下来了。”
老人一拍大腿,说:“你看,光顾着说话,你来一碗搅团?”
我迫不及待地说:“来一碗。”
挨着老人坐下来,一碗灰搅团端过来,金灿灿的搅团卧在土碗里,就像一小座冰山卧在湖水里。山油菜酸菜,用豆瓣炒了,用姜、蒜、葱调配的汤汁,浇在金灿灿的搅团上。用筷子夹一小坨,用汤汁蘸了,吃上两三坨,满满的辣,满满的酸,满满的香,弥漫进胃里。
灰搅团的灰,是土灶膛里的冷柴灰,用细箩筛过,细细的,软软的,温暖。把手插进去,像是触到婴儿的皮肤,不忍心动弹一下手指,怕弄醒了这熟睡的婴儿。
苞谷颗粒是去皮的,磨成大米大小的颗粒。然后用一碗筛好的柴灰,拌一碗去皮的苞谷颗粒,搅匀泡在冷水里。柴灰要放合适,多了,渗进苞谷颗里的碱就重,吃起来夹口;少了,无味,吃起来粉嗒嗒的。柴灰是强碱弱酸盐,还含有少量的硼、铝、锰等微量元素。泡十个小时左右,如果泡的时间太长,发臭;太短了,未入碱性,无味。苞谷颗在微强碱弱酸盐的作用下,渐渐呈现出淡淡的浅绿,用清水反复淘洗去柴灰。苞谷颗粒清水洗涤,弥漫着清水的味道、柴灰的气息。
把泡好的苞谷颗粒磨成浆,在小石磨上磨。淘净的苞谷粒掺清水,苞谷粒本来的颜色被柴灰包裹,被那种淡淡的绿色包裹。一手舀半瓢带水苞谷粒,灌在小石磨的磨眼里,一手握着石磨的木柄开始磨,带水苞谷粒磨成浆,慢慢流进石磨下放着的木盆里。石磨转动,柴灰的味道、石磨的味道、苞谷的味道像一股股白色或金黄色的乳汁流出来,浸染了乡村沉静、醇厚的早晨。
“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飘飘不觉寒。”“千军万马城里过,个个出来脱衣裳。”这两个谜语的谜底都是石磨。这苞谷颗粒就是在石磨上脱了衣裳,磨成了浆。
苞谷浆磨好了,倒少许在铁锅中,灶内燃以柴火,待锅内苞谷浆温度逐渐升高,这时右手要用擀面杖慢慢搅动,左手拿瓢慢慢将盆中的苞谷浆添加到锅内,锅内温度不断升高,右手搅动的力量和速度也要加快、加大。一直到苞谷浆添加完,这时需双手紧握擀面杖用力回旋搅动。“要得搅团好,就得三百六十搅”,搅到三百六十搅左右,将擀面杖平行于锅面举起,擀面杖上浓缩的苞谷浆能挂起像窗帘状的帘子,搅团就搅好了。灶里柴火开始时要烧得大,中间要大,然后是由大转小。见母亲搅搅团,随着擀面杖一圈圈地搅动,她脸上的肌肉在跳动,长发在飞舞,那分明是一种旋律、一种舞蹈、一种意志、一种韧劲……搅出的是甜蜜,是希望……有时候,父亲从城里回到乡下,赶上母亲搅搅团,父亲接过母亲手里搅动的擀面杖,“我来吧。”父亲就像接过一种甜蜜、一种希望,柴火印亮灶房。
灰搅团冷热都好吃。趁热吃,用菜油加豆瓣炒酸菜,加入姜、蒜、葱、盐、水调配汤汁,浇在热灰搅团上,就可以吃了。冷灰搅团切成细条,红油辣子凉拌,有嚼头,烩上吃,滑口鲜嫩。舌尖上的辣、舌尖上的酸、舌尖上的灰,让整个身体舒坦起来、流畅起来。
在城里想吃灰搅团,就买了擀面杖,买了磨好的苞谷面,做了搅团吃,总吃不出乡村那种味道。就想,城里哪里去找那种土灶、那种柴火、那种柴灰、那种石磨。
灰搅团在民间。
黄金炒炒饭
炒炒饭也叫“金裹银”。
金裹银,黄金和银子裹在一起,那是怎样一种金黄?那又是怎样一种银色?黄,诱人。银,诱人。山里早晨的太阳染在瓦房上的颜色,金黄。山沟里溪水跳跃的颜色,银亮。树笼笼里突然冒出的一两句山歌,金黄。“一把扇子里面黄,上面画着姐和郎,郎在这边望情姐,姐在那边望小郎。”野花笼笼里跳出的山歌,银亮。
山里水田少,几分水田,打不了多少稻米。要吃一顿米饭,得等到过年。在那个缺衣少食、不得温饱的年月里,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足矣让人垂涎欲滴。读初中的时候,寄宿在亲戚家里,亲戚是挣工资的,晚上吃白米饭,还配一两个小菜。吃剩下的一小坨白米饭,盛在小瓷碗里。我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在食堂定量吃的一碗糊面条,不一会儿,肚子就空了。总也睡不着,就想亲戚放在案板上,剩在小瓷碗里的白米饭。越想越饿,越饿越睡不着。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起来看案板上那碗白米饭。拳头大一坨白米饭卧在青花瓷碗里,小小白米挤黏在一起,亲密、甜蜜。我嗅到白米的味道,口水直流。顾不了亲戚要是发现一小坨白米饭不见了,会生气责备。端起小瓷碗,倒一点白开水进去,再放一两滴酱油。酱油在碗里散开,白大米在厚厚的红褐色里铺开。我几口扒拉进了肚,甚至连白开水也一口气喝了。现在一想起那一小坨白米饭,米饭的香甜,酱油的气息,一下子把味蕾激活了。记得那夜我还做了一个美梦,梦见好多的白米饭,把肚皮撑得圆滚滚的。
姐在灶房里箜炒炒饭。把一大把大米放在清水里淘净,把大米放在铁锅里煮,大米六分熟,就连铁锅里的米汤、米一起舀进筲箕里,米汤从筲箕里漏下来,漏进事先准备好的瓷盆里。把米汤滤尽,然后再把筲箕的米,和上黄苞谷珍珍重新倒进铁锅里箜。这时候,灶里的柴火要小,用微小的火苗舔铁锅底。火候要掌握好,柴火大了,铁锅里的苞谷珍珍和大米会焦。慢火蒸,慢火箜。姐姐把这些做好后,就倚在厨房门上,轻轻哼上一首山歌:“哥也勤来妹也勤,二人同心土变金,你在行船我发水,你要下雨我布云。”
铁锅里箜的炒炒饭,有香气飘出来,姐姐揭开锅盖,用铁铲翻一遍,盖上锅盖继续箜。把酸菜炒了,撒在炒炒饭上箜,就成了酸菜炒炒饭。把青菜切细,炒三分熟,撒在炒炒饭上箜,就成了青菜炒炒饭。箜上二十分钟,揭开锅盖,米饭的香气、珍珍的香气、青菜的香气糅合在一起,飘出好远都还闻得到。放上盐,翻动几次,就可以吃炒炒饭了。要是有人从厨房后墙经过,闻到香气,会不自觉走过来:箜炒炒饭啊。遇见大方人家,铲上一小碗炒炒饭,让路人吃了。路人走到哪里,都会记起那碗炒炒饭:“那天,李家吃了一碗炒炒饭,香。”咂吧几下嘴巴,那个香还在嘴里回味无穷。
姐姐成家后,姐夫总是夸姐姐箜的炒炒饭。“一碗炒炒饭,哄到一起的。”对呀,男人都是好吃的,要哄住男人的心,首先要哄住他的胃。一碗炒炒饭、一首山歌,姐夫不醉才怪。
炒炒饭稍微箜久点,铲了炒炒饭,锅里就有一层锅巴。黄苞谷珍珍,金黄;白大米,银亮;青菜苔,青绿。黄里有银,银里裹金,金里泛绿。铁锅里一层锅巴,也是黄里点上那么几点银,银里透出一些绿来。把锅巴放在米汤里泡了,慢慢嚼起来,有一点柔润,有一丝脆香。
那时候放学回家,放下书包,首先就是冲进厨房找吃的。揭开锅盖,一碗炒炒饭沏在锅里,会端起碗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箜苞谷珍珍和小许大米的金裹银,一年里吃不上几回。多数时候,为了把苞谷珍珍吃出白米饭的味道来,就用全是苞谷珍珍和酸菜箜成炒炒饭,苞谷珍珍的糙,会满口窜。即便那样,能吃上一碗苞谷珍珍炒炒饭,也是香的。
几十年过去了,炒炒饭满口窜的香和糙还在梦里萦绕。可不知怎的,现在的饮食变得越来越精细,却再也吃不出炒炒饭那满口窜的香和糙了。
火烧馍
一到冬天,每家每户老屋的堂屋里生起疙瘩柴火。
堂屋是老屋的正房,乡村许多重大的决策都在堂屋议定,祭祖、婚丧喜庆的礼仪,以致拜年、重要客人会面,都在堂屋。堂屋正墙上有神龛,在正墙上掏一个神龛一样的窟窿,再把做好的木雕神龛锵进去,木雕上有太阳火焰蒸腾图饰,有吉祥纹饰。神龛正中铺上红纸,红纸上竖写着“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字,还有“某氏(本门)宗祖”、“东厨司命”等小字分列。有的还在神龛前摆放先人雕像、画像或木牌位,有的也摆上香炉烛台,逢重大节日先给先人们上一炷香。
堂屋背风的一角掏上一个大坑,大坑里镶上烂底的大铁锅。乡村总是能变废为宝,一个烂底的铁锅舍不得丢,就镶成堂屋烤火的用具。铁锅内堆起疙瘩柴,一天一天燃烧,慢慢地就堆起半铁锅柴灰。疙瘩柴燃烧的时候,柴灰的温度就升起来。柴灰烫,老家叫烫灰。在烫灰里放上洋芋,一家人围着疙瘩火烤火取暖、唠话,洋芋也在柴灰里烤火。舒服极了。看过寓言故事:温水里的青蛙。要是把青蛙直接扔到开水里它会蹦出来,但是把水慢慢加温,直到煮沸,青蛙也不会跳出来。在温水慢慢加热的过程中,青蛙舒服死了。我就想,要是青蛙在柴灰里过冬,也会在慢慢升温的烫灰里变成一具化石。
烫灰里的火烧馍馍,别有一番味道。火烧馍馍可防霉变,夏天也能存放七八天,不发霉、不变味。乡村外出做活路,或者赶场,要带的盘缠干粮,就是火烧馍。火烧馍馍,是在麦面或者麦面里掺上苞谷面,加适量的菜油和水,使劲在面板上搓揉。搓揉成团,在面板上团成瓷碗大小的圆形规模,再擀成饼。然后放在温热的铁锅里,用微火炕,炕成黄黄的一块饼,再放进堂屋滚烫的烫灰里烧。柴灰的温度不要过高,达到馍不焦灼,又能使馍里外熟透。烧火烧馍馍要有耐心,保持烫灰的温度不高不低。乡村许多事情急不得,一急,就乱了阵脚。看着风在村里横冲直撞,母亲却一点也不急,坐在老屋屋檐下,静静地飞针走线,用善良、柔情观看着这世界的疾风骤雨。母亲说:“急啥,该来的,总要来。”急也急不来。母亲把手里的一块布摊在一件大衣上,她要把大衣上的一个洞补上,母亲细心地裁剪着那一块布,就像裁剪着身边的一块土地。那块布染着阳光和泥土的气息,不急不躁。
火烧馍馍要粘上泥土和阳光的气息,只有不急,只有让那金灿灿的阳光慢慢渗透进火烧馍里,只有让那滚烫的柴灰慢慢渗透进火烧馍里。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和麦面、苞谷面混合在一起。把火烧馍馍从烫灰里夹出来,用手在火烧馍的平面上拍击,发出“噗、噗”的鸣响,这火烧馍就熟透了。火烧馍熟透了,乡村熟透了。
乡村的许多粮食,都夹杂着泥土的气息、阳光的气质。我走出乡村的那个早晨,带着瓷碗大的火烧馍馍。乡村小路上的蒲公英、蒿蒜子,还有那岩边的闷头花,一路开着,一路香着。草叶上的气息,火烧馍的气息,让我走出乡村的那个早晨充满了温暖。
这个充满泥土和粮食气息的早晨,总能围绕着我的行走,在我的前方忽明忽灭闪现,照亮着我生活的许多细节。
甜浆饭
初夏,乡村的阳光和空气都是甜的。谁发现的?
是这些灵性的鸟儿。乡村立在苞谷地里的稻草人一动不动,这些鸟儿早知道那是个假人儿,不闹不叫的,穿着的衣服七长八短,它们笑上一阵子,还站上稻草人的头发呆、瞭望。见没有人来,就站在苞谷穗上啄食嫩苞谷。啄一下,望一下四周。再啄,再望。嘴里不时发出“甜、甜、甜”的叫声。一发现不远处的人走过来,它们扑棱棱飞走,叫嚷着“甜、甜、甜”。鸟儿铺天盖地地在阳光里弹起又落下,看见它们的高兴劲,真想伸手抓一把,放在手掌心里仔细认一认: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鸟儿?跑进苞谷地的农人,捡起地里的小石块,向鸟儿飞翔的方向打去,驱赶它们少吃苞谷。石块“嘭”一声闷响落在苞谷地里。鸟儿在树梢上还没有停稳,又弹起往远处飞。
苞谷地里烦人的是这些诡秘的老鼠们。苞谷灌浆的时候,乡村老鼠的鼻子灵透,一丝的甜味它们都嗅得到。老鼠缩头缩脑钻出洞,望望金黄的阳光,望望碧绿的庄稼,一溜烟爬上苞谷秆,咬开苞谷壳,就开始不停地啃嫩苞谷。老鼠用牙齿“吭吭吭”撕咬苞谷的声音,在乡村初夏的阳光里显得格外清脆。有脚步声传过来,老鼠赶快从苞谷秆上溜下来,躬起背一溜烟逃进了洞里。
这甜是土地温润的气息,乡村生灵们一生与草木相伴、与这些气息相融,许多自然的物语,也只有它们能够感知得到。确实,春天来的时候,是蚯蚓先咬开泥土的大门。夏天来的时候,是青蛙叫嚷着星星坠落。这嫩苞谷的一丝丝甜味,当然也只有这些纯粹的小家伙们首先感知了。其实,乡村的幸福也就在这些家伙们的捣乱中存在。
乡村风里的气息,裹着这甜,裹着这泥土腥味。地上的尘土被风吹起来,空气里丝丝缕缕的甜味被风搅动起来。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味?就是在这风里,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唐山大地震前几个晚上,一户人家被老鼠折腾得几个晚上都没睡。它们在追赶老鼠的途中,躲过了地震中房屋的压塌。地震中土墙房屋倒了,山石飞走,乡村一片狼藉。乡亲们逃出家园,站在高处,人声嘈杂,惊恐声、哭喊声混成一团。牛羊猪被房屋堆压着,一些逃出来的牛羊猪也颤颤巍巍地站在山坡上,惊恐地望着乡村。乡亲和他的那几只老鼠都站在一个山坡上,乡亲已经是吓得寸步难行,但几只老鼠站在不远处,用爪子洗刷着小脸,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是在与主人玩一场游戏一样。这场游戏显然是老鼠成了赢家。难道这老鼠是灵鼠,它懂得在地震来临之前如何撤退?老鼠在地震来临的前几个晚上,就开始向乡亲通风报信。然而,乡亲们听不懂老鼠的语言,也不知道和老鼠周旋的过程,是逃生的过程。地震改变了一切,主人的粮食已经被尘土深深淹没,老鼠跳到废墟上,拼命用爪子刨尘土,主人顺着老鼠刨的地方,用铁棍撬,一点一点又抢出了粮食。粮食堆在平地上,主人搭起简易的灶台,开始生火做饭。炊烟升起,乡村又活过来了。主人这时候,望着那一眼鼠洞,感慨地说:“这些老鼠,还晓得报答。”一抹阳光照在乡村半坡上,风吹来,吹得苞谷林“哗哗哗”响。主人望着快成熟的苞谷,心里甜滋滋的。
主人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了一句:“人是铁来饭是钢,整个甜浆饭来吃。”主人走进苞谷林,掰了几个苞谷,撕了苞谷壳,主人蹲在刚刚搭起的灶台边,把苞谷米一颗一颗掐下来。苞谷米还有些嫩,一掐,浆就蹦了出来,弄得手指甲上到处都是,一会儿,指甲被染成了黄苞谷米浆的颜色,嫩黄嫩黄的。主人掐完四五个苞谷的米,太阳都升高了,照在主人的额头上,闪闪发光。主人站起来,又习惯性用双手拍了拍身子,对着阳光咧嘴笑了笑。主人把掐下来的苞谷米,用水磨磨成浆。主人烧开了铁锅里的水,又找到尘土里的酸菜缸,舀了一瓢酸菜到锅里。主人把磨好的苞谷浆在一个小勺子里兑水一小勺一小勺搅化,然后倒进锅里煮。煮上二十多分钟,甜浆饭煮好。一家四五口各舀一碗,蹲在歪歪倒倒的房屋院坝里,就着碗边边“嘘嘘嘘”喝起来,那声音甜啊。这时候,乡村的其他声音都得为这甜蜜的“嘘嘘”声让路。
要是有空,把嫩苞谷磨成稍微干点的浆,捏成团,摊开擀成厚皮,裹上炒半成熟的南瓜丝,或者裹上炒了的豆芽,捏成三角形,外面用桑叶或者桐子叶包裹,免得粘笼床。放在蒸笼蒸半小时后,就可以吃水面角了。外面用桑叶包的,可以不剥桑叶直接吃。桑叶的清香和嫩苞谷的香甜裹在一起,有粗糙的苞谷味道,也有桑叶的细腻气息。要是包的桐子叶,把桐子叶剥了,桐子叶的味道还裹在嫩苞谷面上,一口咬下去,迅速触动味蕾,打开身体。
酸菜杂面
我们乡下人顿顿吃酸菜。几个乡里人在城里下饭馆,坐定之后,不是点菜,而是直接各要一碗酸菜面,再各来一碗毛干饭。搞得饭馆老板直瞪眼。用酸菜面下白米饭,有谁见过?谁见过都觉得没有关系,乡里人已经就着一碗酸菜面下白米饭,热腾腾吃起来了。
一碗酸菜面,是乡村缺吃少穿年代珍贵的接待了。
山里盛产苞谷、黄豆,小麦是要用来换稻米的,一般舍不得吃。于是,乡里人为了吃上面,就在麦子里掺上苞谷,再掺上黄豆,用这三种粮食混合在一起磨,磨成一种杂面。母亲常常是白天要在地里干活,晚上才开始磨杂面。月明星稀之下,母亲在磨坊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磨过一遍了,母亲就开始箩面,把箩在上面的粗面又重新倒回石磨上,又开始一圈又一圈地磨。看见母亲吃力地在磨坊里推着一扇石磨一圈一圈地走,我和弟弟跑过去,推着磨杆帮母亲跑上一圈,母亲跑不赢我们,就在磨道里小跑着说:“不要跑那么快,一会儿就没力气了。”一会儿,母亲喘着粗气,我们兄弟俩也喘着粗气,蹲在磨坊里,笑得肚子疼。记得那个时候,月光透过竹林,走在磨坊的台阶上,月光里印着我和弟弟的小影子,母亲的影子很高大。有浅浅的风声从磨坊山梁轻荡下来,翻卷起夜的衣衫,竹林开始婆娑起舞,田地里的虫声密集。磨碎的黄豆、苞谷,还有那小麦,像是被撕开封纸的酒坛子,生黄豆的气息、甜苞谷的味道、稠小麦浆的流动,你抓我,我抓你地拥挤着、伸展着、飘扬着,黄豆的身体、苞谷的穴位、小麦的味道,在月光里被打开、放大。我身体忽然抖动了一下,月光里我地把身体张开,像是一只越过旷野的夜莺。
好大一片黄豆地,五颜六色的黄豆花盛开,还有好多的鸟儿,在黄豆地上空歌唱。我躺在那五颜六色的黄豆花里,像是躺在一条丝绸里,更像是躺在一片偌大的五彩羽毛上,我的身体是那么轻盈,飘呀飘,我暗自欢喜。突然,一只鸟儿俯下身子,拥抱着我。哦,她好像是一位仙女。一头长发,像羽毛那样柔柔的、软软的。突然我身体抖动了一下,我的身体穿过重重群山,“轰”一声落地……我的梦醒了。我的身体在月光下的黄豆气息里,完成了次打开。
我和弟弟趴在磨盘上睡着了。母亲喊我们醒来的时候,杂面已经磨完。母亲说:“做梦了吧,看你笑的。”我揉了揉眼睛,月光里生黄豆的气息一阵阵浓烈。母亲说:“快去睡吧,明天又有杂面吃了哦。”
母亲擀杂面的时候,我就帮着看着灶膛里的火。母亲撮上一木瓢杂面,用水和了,揉成一块小小的面团。这面要和得软硬适中,母亲用手来回搓揉,把面团揉得瓷光瓷光的,那面团的颜色像是月光照在瓷器上,柔和,瓷白。搓揉好的面团,母亲并不急着擀。母亲说:“叫那面再醒醒吧。”醒面?母亲是要那面团里的气息都醒过来吗,生黄豆的气息、甜苞谷的味道、稠小麦浆的流动,都要在母亲的搓揉中醒来吗?母亲望着天边的一抹彩霞,一会儿变幻成山峰,一会儿变幻成万马奔腾,母亲转身走向案板,我仿佛看见那搓揉的面团在案板上晃动了一下,醒了。母亲用二尺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开,把擀开的面卷在擀面杖上,母亲躬着腰,身体一前一后,一起一伏,双手随擀面杖前推后拉,左右压均匀,不断重复。那面团在母亲的擀面杖下一次次变薄。擀上一会儿,母亲要停下把卷在擀面杖上的面展开,再在面上撒一些干苞谷面,用手铺均匀,以防止粘连,然后继续卷在擀面杖上擀。卷起,展开,擀上那么四五遍,展开用手指捻捏一下整张面的厚薄,合适了,就把整张面展开,再撒上一层苞谷面。把整张面皮叠成手掌那么宽,就开始切面,菜刀在母亲手中伴随着“”声起起落落,均匀的面条一口气就切好了。宽细一致、薄厚一致,母亲用手轻轻拿起一把面条,抖了抖,苞谷面纷纷落下来,母亲微微汗湿的脸上,绽开了像一朵花,一朵淡紫的黄豆花。
等母亲把杂面煮好,整个厨房就只听到吃面的哧溜声,没人说话,母亲笑了一声说:“像你们这么吃,有谁家养得起。”我们三兄弟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养自己。”这时母亲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乡里人,想去女方家当上门女婿。一天,这男的去女方家里串门,女方母亲擀面招待这即将成为的上门女婿,面擀好,煮好,给男的盛了一小面钵端上来,男的二话不说,埋着头一口气吃完了。看得老丈人目瞪口呆,心里想:“这么能吃,谁养得起呀。”后,这门亲事就这么完了。母亲总结了一句:“这就叫,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得见。”
后来,我知道这“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得见”出自《红楼梦》。母亲断然是没有看过《红楼梦》的,但母亲这心谁也蒙不了。我总惦记那个能吃的男的,要是今天,结局肯定就大不一样,能吃就能干呀。可惜,那是个缺吃的年代,都要勒紧裤腰带。
荞面软面子
荞麦是乡村的一块紫云。紫红的荞秆,黑红的籽粒,青青的荞叶,白色的花。籽已结了,花却还在开。荞麦在收割时,有果实,还有花。远看,那一大片荞地,像镶嵌在秋天天边的一团紫云,更像爱情的颜色。近看,那黑压压一坡厚实的黑红荞籽,像一颗颗会说话的星星,让人想到爱情的那个乡村夜晚。
荞子是乡村紫黑的女子。在我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一千年前,有一位民间医生上山采药,忽然看到有两位仙女在山间一会儿结伴游戏,一会儿尽情歌舞。民间医生看傻了眼,仙女笑呵呵地走过来和民间医生搭讪。霎时,云绕波涌,如鱼滚动,民间医生竟不知不觉地跟着仙女走进了山间的一个洞中。哪知洞内温暖如春,四季常青。仙女对民间医生百般照顾,一日三餐,必吃两顿荞面。民间医生只待到第三天,便思念亲人想要出山回家。哪知,民间医生走出山洞,已物是人非,子孙已历五世。这时民间医生方才知晓,他在山洞里过的时日,人世间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他却还长生不老。民间医生这才恍然大悟:山洞每日两餐吃的荞面,原来是长生不老的食物。从那以后,乡亲们开始祖祖辈辈种荞麦,吃荞面,变着花样吃。那以后,荞子更像是紫黑敦厚的女子,时时站在山头,静静守候着乡村。
想到一个词,山河入梦,岁月静好。只要那山间还在就好,只要那山间的荞麦花还在就好。
秋天的荞麦刚刚收割打理磨成面粉,那长着棱角的黑脸的荞粒里面,打开全卧的是白胖子。山间农家的土灶上,黑红的乡村女子正忙着蒸荞面馍。先将荞面粉用水和成稀稠状,然后将其倒进垫着纱布的竹笼,猛火蒸半小时,将蒸笼揭开,竹笼里蒸成的大块状荞面馍冒着热气。在清香苦甜的热气里,那黑红的乡村女子的笑容是那么瓷实亮光。一下子,就把人带到了乡村医生描述的那个仙境了。云蒸雾绕,芬芳怡人。其实,进入一种境界更多是靠一种气息的形成来维护的。热气散开,回到现实中,用菜刀将竹笼里大块的荞馍切开,切成一块一块的,那放在蒸笼里的一块块紫玉,和站在一旁的黑红女子,竟是那么的神似。黑里透着红,红里闪着亮光。荞面馍是一块紫玉,乡村女子是一块紫玉。二爷是乡村养蜂人,几槽蜂子架在山坡上,蜂子每天飞出飞进采花酿蜜。起蜜的时候,二爷笑开了花,用喝净的沱牌酒瓶子,满满接一瓶子,然后用荞面馍蘸着乡村蜂蜜吃,花的气息,露水的甜,还有乡村青草的苦,都在这荞面馍里。二爷笑着说:“晓得不,这就是地主家的生活。”
母亲把荞面做成软面子。母亲说:荞面不是有些硬吗,那就用酸菜把它软一下。于是,母亲把荞面和水稀成泥,再放点酸菜进去,用筷子搅均匀。柴锅里的火生旺,把菜油煎熟后,退了柴火,用菜油把锅涂透,然后把和好的荞面倒进锅里,用锅铲把荞面摊开,薄薄摊开在锅里,用余火慢慢焙,等焙烤到荞面边边金黄的时候,再翻过焙另一面。反复焙烤几次,就可以起锅了。母亲说:焙酸菜荞面软面子,急不得。不用急火,不用急脾气。一急,就焙焦了。一急,就坏了好好的荞面。急不得,母亲说,说话急不得,再有理也急不得。一急,话说不伸展还得罪人。急不得,母亲说,做事急不得,毛手毛脚做不好事。不是火烧房子牛滚岩的事,急啥?急了,就是焙荞面软面子这小事,都做不了。急不得,母亲说,活人急不得,人活一辈子得一天一天过,一山一山过。急了,把人都急老了。
所以,母亲在焙荞面软面子的时候,静静地把荞面摊开在锅里,就站在土灶边,看天边的那一抹彩云,欣赏飞鸟在空中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母亲还把我喊到她身边:“天边那彩云,像什么?像不像一匹飞翔的骏马。”我无心欣赏天边的彩云,丢了一句:“管它像啥。”跑开了。母亲不急,等把荞面软面子焙好的时候,递一块给我,然后再指了指天边。我一边吃荞面软面子,一边对母亲说:“不像是骏马,像一头狮子。”母亲慢慢说:“像骏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母亲就是在这种“急不得”中来教育我们的,现在想来,荞面软面子的那一点点的揉劲,就是母亲慢慢焙出来的。
一次,高中同学元去我家里,母亲正好焙了荞面软面子,同学元接连吃了两搭子,元说:“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味道了。这荞面正宗,这酸菜正宗。”后来,元这样记录在我家吃荞面软面子的情境:“家乡的味道一下子浓烈起来,一边吃着荞面软面子,一边想象一个母亲站在土灶前默默焙软面子的样子,心里那种温暖直往外蹦。多想回家,种田一畦,梦在瓜下,粗粝终老,所愿止此。”
炕饼
还有许多馍和饼:炕肉客蚂,炕洋芋馍,炕红苕馍,炕茄子馍,炕南瓜花馍,油炸茴香鱼,油炸椒叶,软面馍馍蘸蜂蜜,水面角,火烧馍等。这些馍和饼炕的也好,炸的也好,蒸的也好,都活泛着乡村水的清凉,散发着乡村风的气息,渗透着乡村草的味道。
从山里忙活一天回到家的女人们,喝上一罐老鹰茶,又开始在厨房忙起来。木碗柜里取出一块煮好的腊肉。腊肉油浸浸的,夕阳从厨房木格子窗户透进来,打在油浸浸的腊肉上,打在女人汗渍渍的脸上。腊肉切成片,在案板上泛着油光。小麦面在木桶里,揭开木桶,舀上一木瓢,盛在面盆里,倒进冷水,用筷子朝一个方向调,一圈一圈地调,小麦面和水融成一体,干稀适度,再把切好的腊肉放进调好的面里。
这时候的夕阳已经退出厨房,有点暗的厨房里,女人哼起了山歌:“想郎想得四念三,白日当作月夜天。清风吹得花枝响,像是情郎在眼前。”女人幽幽唱完,绯红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意。
这时候的炊烟已经升起,在灰灰白的天空下游走,绕过竹林,绕过房前的庄稼地,绕过草地上那一群花花绿绿的鸡,绕啊绕,力气尽了,星星在天空眨着眼睛。一只狗在土路上疯跑,它要追逐什么,是天空那一抹夕阳,还是无影无踪的炊烟?也许,就是一趟追逐,什么也不去追。狗在乡村,更懂得与乡村一种气息的同时存在。
这时候的女人,已经停止哼唱。菜油倒进滚烫的铁锅里,不要倒太多。女人开始在心里默念丈夫吃肉客蚂的样子,开始想着丈夫幸福的笑容。菜油在铁锅里冒起了热烟,女人急忙退了柴灶里的柴火,女人又悄悄说了一句:丈夫呢,在外面吃得饱不?女人有热泪从眼眶流出来,有甜蜜,也有辛酸。
女人用筷子夹起面盆里裹好的腊肉片,丢进滚烫的油锅里。油锅里马上吱吱冒着油泡泡,炕上一两分钟,又翻到背面炕。四五分钟,两面泛黄的肉客蚂就炕好了。让腊肉片裹上面泥,睡在热油锅里,那些腊肉的香味就开始一点点唤醒过来,那些小麦的气息开始一丝丝抽出来。女人咕噜了一句:这个香哦。炕好的肉客蚂趁热吃,满嘴的腊肉油咂出来,香;面泥炕得焦黄,脆。香脆,香脆。
炕肉客蚂是老家农村的名小吃。沿海一带的老板到川北来,一盘肉客蚂端上桌,老板问:这是什么东西,挺好吃的。一桌陪客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其中一个偷笑着说:这个东西啊,好吃。沿海老板一边吃,一边重复:这个好吃。
把洋芋、红苕、茄子切成片裹上面泥,花椒叶、南瓜花裹进小麦面泥里,在油锅里炕出来,又别有一番风味。那种泥土瓷实的味道,清晨露水的清新,鲜花绿叶的野味,一起进了肠胃。种子入土,鲜花盛开,绿叶舒展。青花一样的瓷盘里放上这些炕饼,让人有一种在自然沐浴的感觉。有时候自然的东西离我们远了,但一想起就会被无边的渴望覆盖。哪天,坐在鸽子笼的房子里想起这些东西了,就咽着口水怀着美妙的想象,做上一回,感觉里像是回到乡村的土院坝里,吃着炕饼,望着天边的星星。
夏天,嫩青苞谷在田野里鼓着腮帮子,扳几个青苞谷回来,撕了青壳壳,把青苞谷米粒一颗一颗掐下来。一颗一颗的青苞谷米粒在筲箕里堆着,一点一点的苞谷浆溢出来,淡淡的黄,浅浅的甜。一颗颗苞谷米放在小水磨上磨成稠密的浆浆,再把稠密的苞谷浆摊在嫩桑叶上,再在苞谷浆上摊一点炒南瓜,然后按桑叶的主纹络对折,用苞谷浆的黏性黏住,放在蒸格上蒸熟,就成了可口的水面角。苞谷的粗糙,苞谷的甜糯;南瓜的水汽,南瓜的清香;桑叶的清爽,桑叶的绿色,一起都在水面角里。桑叶一起吃了,夏天的阳光、雨露都在桑叶上。
川北农村女人都有一手绝活,她们把山里粗鄙的粮食做得精细又可口。一碗小麦面粉,她们只单单在面粉里和上水,山里清凉的山泉水,什么都不加,就能做出可口的擀面,还能做出可口的火烧馍。冷水和面,再揉面,揉成面疙瘩,一点一点把面和水揉在一起。水知道答案,女人的心思揉进了面里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它不像很多美食散文那样追求华丽的辞藻堆砌,反而采取了一种近乎纪录片的冷静观察和细腻刻画。我最喜欢它对“仪式感”的挖掘,那种渗透在民间饮食文化中的无形规矩。比如,在讲述某个特定节气里的特定食物时,作者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而是先铺陈了当地人围绕这顿饭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熏制、晾晒,到第二天清晨集体劳作后的共同分享,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富有深意。这种“过程大于结果”的叙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它让我反思,我们现代人吃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快餐化、越来越少地去体味食物从自然中走来,经过人力加工最终抵达舌尖的整个链条。书里的一些插图或者作者随手画的草图,也透露出一种朴素的美感,它们不是为了美化食物,而是为了更准确地记录工具的形状、火候的烟雾缭绕,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让人倍感亲切。这是一本能让你放慢脚步,重新审视自己日常饮食习惯的佳作。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惊喜的是它那种近乎“文学性”的语言张力,完全跳脱了传统美食书籍的窠臼。作者在描摹食物的口感时,运用的比喻常常出人意料,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冲击力。比如,形容某种用陈年老酒浸泡的肉类时,用的词汇是“时间的琥珀”,而非常见的“醇厚入味”。这种对语言的精雕细琢,使得即便是描述一种再普通不过的家常小菜,也能读出史诗般的厚重感。而且,书中很多段落是以第一人称的对话或场景再现来展开的,仿佛读者就是那位坐在火炉边,听长辈娓娓道来故事的倾听者。这种代入感极强,我甚至能感受到冬日炉火带来的暖意,以及老人们讲述时语速的停顿和眼神的闪烁。这种叙事技巧的运用,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沉浸感和情感共鸣度,让人在了解烹饪技法的同时,也被深深地卷入了那些充满烟火气的动人故事之中,体会到食物背后人与人之间复杂而温暖的联结。
评分翻开这本书,你很难用单一的“地方志”或者“美食指南”来定义它,它的野心显然更大,更像是人类学的一个侧面切片。作者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对“边缘知识”的尊重与抢救意识。那些流传在特定地域、仅靠口耳相传的古老技艺,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几乎随时可能消亡,但作者却像一个耐心的守夜人,将这些“行话”、“手诀”悉心记录下来。我特别对其中关于“山野采集”的部分印象深刻,如何辨识有毒和无毒的野菌,如何判断土壤的酸碱度对草药风味的影响,这些信息专业性极强,但作者的表达却清晰易懂,没有任何故作高深的架子。这种知识的传承,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来得珍贵。它让我意识到,我们脚下的大地,隐藏着比书本上记载的更丰富、更深厚的智慧宝库,而这本书,就是一把开启这宝库的钥匙。每次读到那些关于时间与土地的篇章,内心都会涌起一股敬畏感,感叹于先人们的生存智慧。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带给我的,远超乎我对“美味”的想象,它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返乡之旅”。它没有刻意去美化贫穷或艰辛,而是真实地展现了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和耐心,从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中榨取出最大的满足感和仪式感。书中对于“物尽其用”原则的展现尤为到位,哪怕是一点点边角料、一小撮残渣,在特定的处理下都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风味。这种对资源的珍惜和循环利用的思想,在今天这个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每章末尾留下的思考题,它们不是让你去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菜,而是引导你去回忆自己的童年记忆,去探寻自己家乡那些被遗忘的味道。这种由外向内、由食物回归自我的过程,是一种非常宝贵的阅读体验,它让这本书成为了我书架上那种会时不时被重新翻开,并总能带来新感悟的“常青树”。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光是听着就让人心里痒痒的,感觉像是一场深入寻常百姓家的美食探险。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那种“活着的味道”的捕捉能力,那种不是教科书式的烹饪记录,而是带着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描绘。比如,书中对某个乡村小店里,店家坚持用古法石磨磨制豆腐的场景描写,那种粗粝的石子摩擦声,混着豆浆特有的清香,仿佛能透过文字直接钻进读者的鼻腔。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食材本身,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食物背后承载的家族记忆和社会变迁。我记得有一章讲到某种失传已久的发酵工艺,为了还原它,作者跑遍了几个偏远的村落,甚至在寒冬腊月里,和当地的老人们一起蹲守在土窖旁,记录下那份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时间味道”。这种近乎田野调查的精神,让整本书不仅仅是食谱的集合,更像是一部生动的、有温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册。读完后,我立刻动手尝试了其中一个看似简单却极有讲究的腌菜方子,那种从泥土到餐桌的转换过程,让人对食物多了一份敬畏和珍惜。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有味”,藏在那些最不经意间的日常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