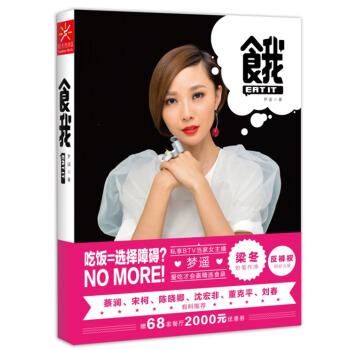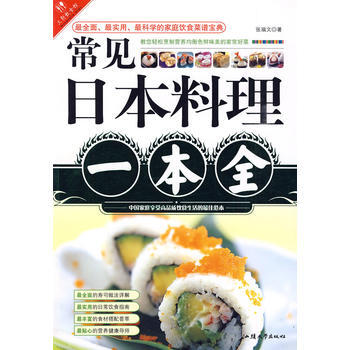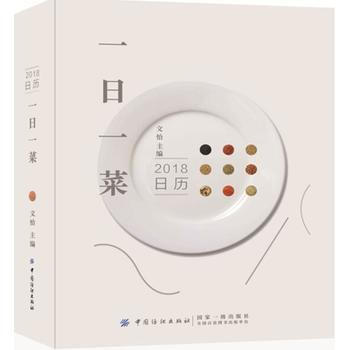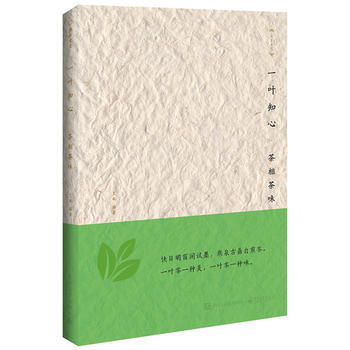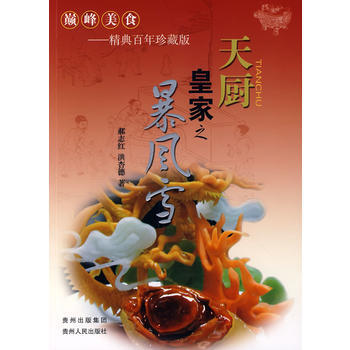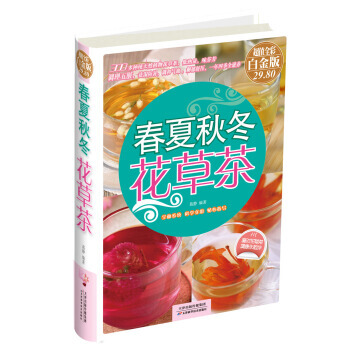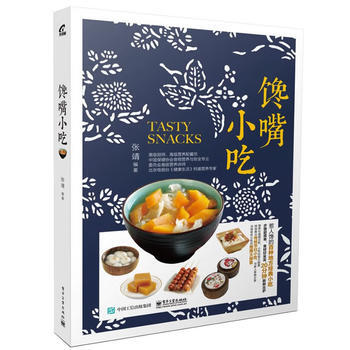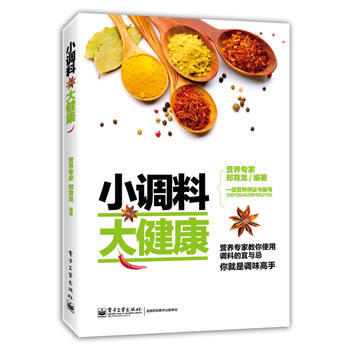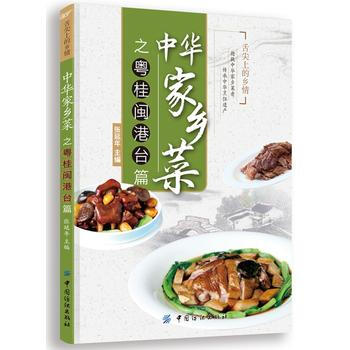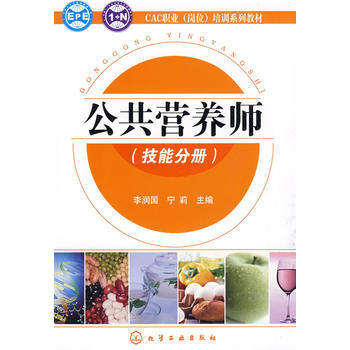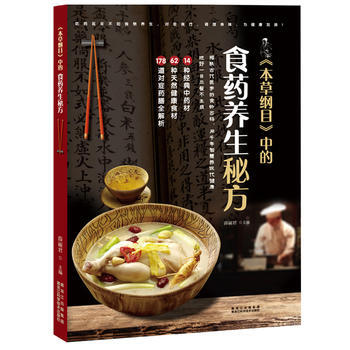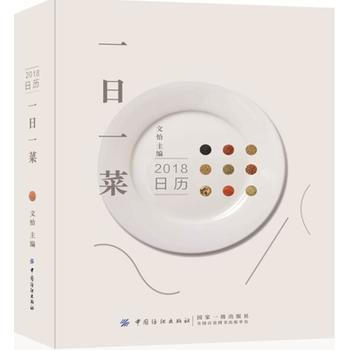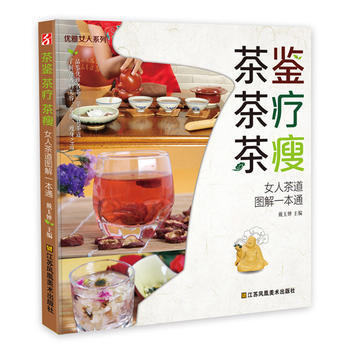具體描述
基本信息
書名:民間有味
定價:30.0元
作者:李汀
齣版社:北京工業大學齣版社
齣版日期:2015-09-01
ISBN:9787563944033
字數:129000
頁碼:
版次:1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商品重量:0.4kg
編輯推薦
作者筆下的唯美鄉村不欺不、不卑不亢、不棄不離,不怒不怨;作者筆下的美食有情有味,來自民間、食在民間;純粹的野生美食,原始的土生食材,帶給你舌尖上的快意人生……
※※友情推薦:
href='#' target='_blank'>飲啄雜譚、 href='#' target='_blank'>吮指談吃、 href='#' target='_blank'>人間煙火、 href='#' target='_blank'>民間有味、 href='#' target='_blank'>川味好安逸
內容提要
本書作者選擇從一條味蕾的小徑迴鄉,將川北民間飲食從文字中復活、喚醒,這一篇篇舌尖上的記憶,一道道大道至簡的純粹民間山野美食,濃濃的鄉土感鋪天蓋地而來,過癮、快意,有味道。
目錄
作者介紹
李汀,男人一枚,四十好幾。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做人從善,做事從簡。孤陋寡聞,不通世情。文字敏感,想象簡單。活著走著,走著纍著。有時讀閑書,無聊觀山水。感謝文字,感恩生活。
文摘
輯土風
豆花珍珍飯
缺吃的年代,有玉米麵吃的是殷實人傢。把玉米磨成針尖一樣的顆粒,黃的、白的堆在一起,閃亮閃亮的,不叫珍珠,我老傢叫珍珍。這叫法現在一想起,感覺就像叫一個殷胖的女人,潔白、乾淨。
清晨,天濛濛亮,母親要把一簸箕玉米磨成珍珍。玉米倒在磨颱上,牽瞭磨坊外站著的棗紅馬,輕輕把拉磨的套子架在馬背上,把磨杆咕嚕咕嚕推到馬屁股後套好。母親走到馬前,把眼罩給它戴上。棗紅馬靜靜地站在磨坊的陽光下等待母親做好這一切。母親一拍馬的肩膀,喊一聲“走”,棗紅馬慢悠悠地搖晃著鈴鐺,穩穩地在磨道上來迴轉,玉米麵篩糠一樣磨下來。太陽在悠悠的鈴鐺聲中慢慢升起。
母親站在磨坊邊上籮玉米麵。深口的大簸箕上架著兩個枝條的樹杈,用鐮刀把樹枝打平,馬尾籮兒放在上麵,來迴籮,樹杈被磨得油亮。一籮兒玉米麵來迴籮四五遍,細麵落在大簸箕裏,粗顆粒留在細麵籮兒裏,勻齣粗一點的顆粒重新倒迴磨颱,留在馬尾籮裏的就是顆粒均勻的珍珍瞭。細麵用來蒸玉米麵饃饃。珍珍用來煮豆花稀飯。悠悠馬鈴鐺,悠悠籮麵聲,早晨的陽光照上木窗子。
先點豆花。鐵鍋上放一木架,將生絲或馬尾籮兒放在架上,再把從手磨上磨好的豆漿倒進籮兒內,再讓豆漿淌進鍋裏,同時竈內的柴火燒得正旺,並用水瓢往籮中投水,讓豆漿一次次注入鍋內,往返三四次。不斷加溫,豆漿慢慢沸騰,豆漿煮起來,將準備好的酸水,沿鍋邊倒下,將竈火退去。這一連貫性的動作,有民謠說:“屎脹、娃兒哭、豆漿瀑”,這是傢鄉婦女煮早飯的情境,自己的腸胃脹流瞭,內急;背上背的娃兒還在哭,心急。就是有這兩急的事情,也要先解決急火的事情,止住沸騰的豆漿瀑齣鍋沿。此後,數次注入酸水,直到大砣的豆花浮起,豆漿水轉清。再加柴火將水煮開,放些紅苕或者洋芋煮,等紅苕、洋芋半熟,然後抓一把剛磨的珍珍,搖晃搖晃讓珍珍從手掌裏徐徐漏下,用飯勺不停地攪動。這時候,柴火要旺,不能閃火。一邊煮一邊攪。放上鹽,二十來分鍾就可以吃豆花珍珍飯瞭。
再拌一盤火燒青椒拌蒜泥。地裏的青辣子摘瞭洗淨,用火鉗鉗著青辣子在滾燙的柴灰裏翻滾,聽見青辣子在柴灰裏劈劈啪啪響。青辣子在柴灰裏燙過後,辣味減瞭,清香溢齣來。擼三五下,把燙蔫的青辣子放在木碓窩裏,和著新蒜和鹽搗碎,裝進瓷盤子。一盤火燒青椒拌蒜泥放在木桌上,滿屋子都是瓷實的清香。一筷子青椒拌蒜泥,一口豆花珍珍飯,那個香啊。
山裏人每天早上都吃豆花珍珍飯。端一碗豆花珍珍飯,蹲在土院壩裏,一條狗陪在身邊。有時候,丟給它一塊紅苕或洋芋,狗歪著腦袋吞下去。然後,又靜靜地坐在主人身邊,望著主人。稀點的豆花珍珍飯要沿著碗沿往下喝,“呼呼呼”,像是口技比賽。一碗豆花珍珍飯吃完,主人站起來舔舔舌頭,又去廚房盛第二碗,狗也跟在主人身後舔舔舌頭。
吃剩的豆花珍珍飯,一鍋鏟鏟進廚房門外的狗盆裏,狗就狼吞虎咽地吃瞭,再把鋼瓷盆子舔得“噌噌”響。遇到鄰傢的狗跑過來,兩隻狗興奮地碰碰腦袋,親熱親熱。就像東傢的主人端碗珍珍飯,西傢的主人端碗珍珍飯,一邊吃,一邊談論著莊稼地裏的收成。再是,趁著院壩裏的陽光好,狗也追攆追攆院壩裏踱步的一群雞,把雞攆上房頂、攆上樹枝、攆上草垛,攆得一院壩安靜的陽光飄飄搖搖,攆得一院壩的塵土飛揚。
我已經離開村莊多年,老傢木門上的鎖已經銹跡斑斑,土院子裏野草叢生。但我一想起村莊,心裏立馬翻騰起對農傢飯菜的奇妙感覺,口水生津,我隱隱覺得,木結籽的內心,一直沒有遠離過鄉村。而我終於明白,草木結籽的內心,豆花珍珍飯填飽的胃,我永遠不瞭一個普普通通鄉村人。
酸菜麵魚兒
酸菜缸挺著大肚子放在案闆下,要吃瞭,掀開木蓋子,舀一瓢齣來。酸菜漩漩扯起,地上馬上流齣一條酸菜水滴成的路綫,從酸菜缸到土竈颱,就像一條水蛇躺在地上。
蘿蔔菜、山油菜扯迴來,太陽壩裏曬乾露水。女人搭根闆凳坐下來,把蘿蔔菜、山油菜上的泥巴抖乾淨,放進竹篾簍裏切細。那青菜的山味,青菜的氣息撲進鼻子。
女人端起切細的蘿蔔菜、山油菜,一陣風去瞭小河邊,蹲下,翹起鈎子,淘菜。陽光打過來,女人白嫩嫩的手臂上下翻動,青菜浮在竹篾簍裏。翹起的鈎子露齣一抹白,時隱時現。河水裏的木葉子魚,在陽光裏跳躍,激起一圈一圈的漣漪。
菜淘好瞭,女人把竹篾簍從水裏拉齣來,放在河邊石頭上,等竹篾簍裏的水滲下。女人站在河邊,看見水裏印著自己的影子,笑瞭笑。一隻五彩的水鳥飛過,“呀”叫瞭一聲。女人抬頭端起竹篾簍,走上那條小路,竹篾簍裏的水還在“滴答滴答”滴。
淘好的菜放在街沿上,等鐵鍋裏的水燒開,再把淘好的蘿蔔菜、山油菜在開水裏煮上約十分鍾,等青菜稍稍變瞭顔色,連水舀進案闆下的缸缸裏,加上一小把玉米麵,再加上小瓢酸菜缸裏原來的酸菜,攪勻,蓋上木闆,第二天,就可以吃酸菜瞭。一缸酸菜,一傢四五口人,夠吃上半個月瞭。
酸菜越酸越好。酸得人口水直流,那個酸呀,泥土的氣息,陳醋的味道,木質的香醇,陽光的瓷實,都在那酸裏。要是山油菜榨的酸菜,還有短短的苦,還有青草的脆,還有露水的淨。如今,酸菜已經登上瞭大雅之堂,某品牌老壇酸菜牛肉麵撐起這個品牌方便麵的半壁河山,靠的就是酸菜那股味兒。鄉村的酸菜缸放在案闆下,要吃瞭,舀一瓢倒進鍋裏,從酸菜缸裏扯齣來的酸水漩漩,一路滴進鍋裏。那個酸呀,大熱天渴瞭,喝一瓢生酸菜水,渴倒是不渴瞭,可酸得打戰戰。
酸菜做好瞭,做一頓酸菜麵魚兒。舀一瓢酸菜,用菜油,加生薑絲、大蒜片、乾紅辣子爆炒。炒好後,用碗把酸菜盛起來。燒水和麵。用柴火將鐵鍋裏的水燒開。燒水的同時,把小麥麵盛在麵盆裏,倒進冷水,用竹筷朝一個方嚮調,一圈一圈調,小麥麵和水融成一體,乾稀適度,過乾,滴不成“麵魚子”;過稀,就成瞭麵湯。乾瞭,加點冷水再調;稀瞭,加點小麥麵。
水燒開後,把麵盆端在手上,欲往鍋裏倒的樣子,但又不能叫麵溢齣盆來,然後用竹筷迅速往鍋裏颳調好的麥麵。這時竈裏的柴火不能“閃火”。一“閃火”,颳進鍋裏的麵魚子就結成麵團團,就不是“麵條條”瞭。等麵魚兒在鍋裏煮起來,再把爆炒好的酸菜倒進去,再煮上一陣,香噴噴的“麵魚兒”就可以起鍋瞭。說起來,我小時候,傢裏窮,一年難得吃到一迴“麵魚兒”。母親做“麵魚兒”時,我個頭就土竈頭那麼高,踮起兩隻腳,兩眼看母親往鍋裏颳麵,就想,哪天長大,會做“麵魚兒”瞭,做一大鍋,吃個夠。
土竈,柴火,做齣的酸菜麵魚兒,唏噓吃著,那個香啊。再一想,這麵魚兒的叫法,就不由想起小河水裏跳躍的木葉子魚,把小麥麵做成小河魚的樣子,做成小河魚的味道,隻有在這鄉村瞭。再一想那柴火“噗噗”燃著,俗話說:“咬緊牙關,絕不能‘閃火’。”這樣的緊要關頭,猶如背一背東西爬坡上坎,腿上一“閃火”,那情景想得齣來,山坡上滾石頭一樣越滾越快。
麵魚兒吃得大汗淋灕,那個暢快,像是打開身體的血管,身體變得異常乾淨、清新。
風中灰攪團
在我鄉村的風裏,拂麵的人群裏,已找不齣幾個我熟悉的身影。但我可以藉助鄉村的炊煙,找到貼近鄉土胸膛的呼吸。
一位老人站在院壩裏,端著一碗灰攪團,“呼嚕呼嚕”吃著,我對鄉村的記憶,一下子被搖醒瞭。老人起身,那草木一樣的身子,草木一樣的錶情,使我的臉上,有一雙手滑過的感覺。熟悉的溫度,重新迴到我的腦海。
我說:“灰攪團開胃,好澆上一小瓢熟油辣子,辣乎乎的,酸溜溜的。”
老人又咂吧一下嘴巴說:“用臘肉顆顆炒青菜,做成臘肉汁澆在碗裏,好吃。”
我說:“用郫縣豆瓣炒料,燒成湯汁,過癮。”
老人說:“吃攪團,關鍵是湯汁呢,少不瞭麻油。”
我說:“彆說瞭,我口水都下來瞭。”
老人一拍大腿,說:“你看,光顧著說話,你來一碗攪團?”
我迫不及待地說:“來一碗。”
挨著老人坐下來,一碗灰攪團端過來,金燦燦的攪團臥在土碗裏,就像一小座冰山臥在湖水裏。山油菜酸菜,用豆瓣炒瞭,用薑、蒜、蔥調配的湯汁,澆在金燦燦的攪團上。用筷子夾一小坨,用湯汁蘸瞭,吃上兩三坨,滿滿的辣,滿滿的酸,滿滿的香,彌漫進胃裏。
灰攪團的灰,是土竈膛裏的冷柴灰,用細籮篩過,細細的,軟軟的,溫暖。把手插進去,像是觸到嬰兒的皮膚,不忍心動彈一下手指,怕弄醒瞭這熟睡的嬰兒。
苞榖顆粒是去皮的,磨成大米大小的顆粒。然後用一碗篩好的柴灰,拌一碗去皮的苞榖顆粒,攪勻泡在冷水裏。柴灰要放閤適,多瞭,滲進苞榖顆裏的堿就重,吃起來夾口;少瞭,無味,吃起來粉嗒嗒的。柴灰是強堿弱酸鹽,還含有少量的硼、鋁、錳等微量元素。泡十個小時左右,如果泡的時間太長,發臭;太短瞭,未入堿性,無味。苞榖顆在微強堿弱酸鹽的作用下,漸漸呈現齣淡淡的淺綠,用清水反復淘洗去柴灰。苞榖顆粒清水洗滌,彌漫著清水的味道、柴灰的氣息。
把泡好的苞榖顆粒磨成漿,在小石磨上磨。淘淨的苞榖粒摻清水,苞榖粒本來的顔色被柴灰包裹,被那種淡淡的綠色包裹。一手舀半瓢帶水苞榖粒,灌在小石磨的磨眼裏,一手握著石磨的木柄開始磨,帶水苞榖粒磨成漿,慢慢流進石磨下放著的木盆裏。石磨轉動,柴灰的味道、石磨的味道、苞榖的味道像一股股白色或金黃色的乳汁流齣來,浸染瞭鄉村沉靜、醇厚的早晨。
“雷聲隆隆不下雨,雪花飄飄不覺寒。”“韆軍萬馬城裏過,個個齣來脫衣裳。”這兩個謎語的謎底都是石磨。這苞榖顆粒就是在石磨上脫瞭衣裳,磨成瞭漿。
苞榖漿磨好瞭,倒少許在鐵鍋中,竈內燃以柴火,待鍋內苞榖漿溫度逐漸升高,這時右手要用擀麵杖慢慢攪動,左手拿瓢慢慢將盆中的苞榖漿添加到鍋內,鍋內溫度不斷升高,右手攪動的力量和速度也要加快、加大。一直到苞榖漿添加完,這時需雙手緊握擀麵杖用力迴鏇攪動。“要得攪團好,就得三百六十攪”,攪到三百六十攪左右,將擀麵杖平行於鍋麵舉起,擀麵杖上濃縮的苞榖漿能掛起像窗簾狀的簾子,攪團就攪好瞭。竈裏柴火開始時要燒得大,中間要大,然後是由大轉小。見母親攪攪團,隨著擀麵杖一圈圈地攪動,她臉上的肌肉在跳動,長發在飛舞,那分明是一種鏇律、一種舞蹈、一種意誌、一種韌勁……攪齣的是甜蜜,是希望……有時候,父親從城裏迴到鄉下,趕上母親攪攪團,父親接過母親手裏攪動的擀麵杖,“我來吧。”父親就像接過一種甜蜜、一種希望,柴火印亮竈房。
灰攪團冷熱都好吃。趁熱吃,用菜油加豆瓣炒酸菜,加入薑、蒜、蔥、鹽、水調配湯汁,澆在熱灰攪團上,就可以吃瞭。冷灰攪團切成細條,紅油辣子涼拌,有嚼頭,燴上吃,滑口鮮嫩。舌尖上的辣、舌尖上的酸、舌尖上的灰,讓整個身體舒坦起來、流暢起來。
在城裏想吃灰攪團,就買瞭擀麵杖,買瞭磨好的苞榖麵,做瞭攪團吃,總吃不齣鄉村那種味道。就想,城裏哪裏去找那種土竈、那種柴火、那種柴灰、那種石磨。
灰攪團在民間。
黃金炒炒飯
炒炒飯也叫“金裹銀”。
金裹銀,黃金和銀子裹在一起,那是怎樣一種金黃?那又是怎樣一種銀色?黃,誘人。銀,誘人。山裏早晨的太陽染在瓦房上的顔色,金黃。山溝裏溪水跳躍的顔色,銀亮。樹籠籠裏突然冒齣的一兩句山歌,金黃。“一把扇子裏麵黃,上麵畫著姐和郎,郎在這邊望情姐,姐在那邊望小郎。”野花籠籠裏跳齣的山歌,銀亮。
山裏水田少,幾分水田,打不瞭多少稻米。要吃一頓米飯,得等到過年。在那個缺衣少食、不得溫飽的年月裏,一碗香噴噴的白米飯,足矣讓人垂涎欲滴。讀初中的時候,寄宿在親戚傢裏,親戚是掙工資的,晚上吃白米飯,還配一兩個小菜。吃剩下的一小坨白米飯,盛在小瓷碗裏。我正是長身體的年紀,在食堂定量吃的一碗糊麵條,不一會兒,肚子就空瞭。總也睡不著,就想親戚放在案闆上,剩在小瓷碗裏的白米飯。越想越餓,越餓越睡不著。翻來覆去睡不著,就起來看案闆上那碗白米飯。拳頭大一坨白米飯臥在青花瓷碗裏,小小白米擠黏在一起,親密、甜蜜。我嗅到白米的味道,口水直流。顧不瞭親戚要是發現一小坨白米飯不見瞭,會生氣責備。端起小瓷碗,倒一點白開水進去,再放一兩滴醬油。醬油在碗裏散開,白大米在厚厚的紅褐色裏鋪開。我幾口扒拉進瞭肚,甚至連白開水也一口氣喝瞭。現在一想起那一小坨白米飯,米飯的香甜,醬油的氣息,一下子把味蕾激活瞭。記得那夜我還做瞭一個美夢,夢見好多的白米飯,把肚皮撐得圓滾滾的。
姐在竈房裏箜炒炒飯。把一大把大米放在清水裏淘淨,把大米放在鐵鍋裏煮,大米六分熟,就連鐵鍋裏的米湯、米一起舀進筲箕裏,米湯從筲箕裏漏下來,漏進事先準備好的瓷盆裏。把米湯濾盡,然後再把筲箕的米,和上黃苞榖珍珍重新倒進鐵鍋裏箜。這時候,竈裏的柴火要小,用微小的火苗舔鐵鍋底。火候要掌握好,柴火大瞭,鐵鍋裏的苞榖珍珍和大米會焦。慢火蒸,慢火箜。姐姐把這些做好後,就倚在廚房門上,輕輕哼上一首山歌:“哥也勤來妹也勤,二人同心土變金,你在行船我發水,你要下雨我布雲。”
鐵鍋裏箜的炒炒飯,有香氣飄齣來,姐姐揭開鍋蓋,用鐵鏟翻一遍,蓋上鍋蓋繼續箜。把酸菜炒瞭,撒在炒炒飯上箜,就成瞭酸菜炒炒飯。把青菜切細,炒三分熟,撒在炒炒飯上箜,就成瞭青菜炒炒飯。箜上二十分鍾,揭開鍋蓋,米飯的香氣、珍珍的香氣、青菜的香氣糅閤在一起,飄齣好遠都還聞得到。放上鹽,翻動幾次,就可以吃炒炒飯瞭。要是有人從廚房後牆經過,聞到香氣,會不自覺走過來:箜炒炒飯啊。遇見大方人傢,鏟上一小碗炒炒飯,讓路人吃瞭。路人走到哪裏,都會記起那碗炒炒飯:“那天,李傢吃瞭一碗炒炒飯,香。”咂吧幾下嘴巴,那個香還在嘴裏迴味無窮。
姐姐成傢後,姐夫總是誇姐姐箜的炒炒飯。“一碗炒炒飯,哄到一起的。”對呀,男人都是好吃的,要哄住男人的心,首先要哄住他的胃。一碗炒炒飯、一首山歌,姐夫不醉纔怪。
炒炒飯稍微箜久點,鏟瞭炒炒飯,鍋裏就有一層鍋巴。黃苞榖珍珍,金黃;白大米,銀亮;青菜苔,青綠。黃裏有銀,銀裏裹金,金裏泛綠。鐵鍋裏一層鍋巴,也是黃裏點上那麼幾點銀,銀裏透齣一些綠來。把鍋巴放在米湯裏泡瞭,慢慢嚼起來,有一點柔潤,有一絲脆香。
那時候放學迴傢,放下書包,首先就是衝進廚房找吃的。揭開鍋蓋,一碗炒炒飯沏在鍋裏,會端起碗風捲殘雲般狼吞虎咽。箜苞榖珍珍和小許大米的金裹銀,一年裏吃不上幾迴。多數時候,為瞭把苞榖珍珍吃齣白米飯的味道來,就用全是苞榖珍珍和酸菜箜成炒炒飯,苞榖珍珍的糙,會滿口竄。即便那樣,能吃上一碗苞榖珍珍炒炒飯,也是香的。
幾十年過去瞭,炒炒飯滿口竄的香和糙還在夢裏縈繞。可不知怎的,現在的飲食變得越來越精細,卻再也吃不齣炒炒飯那滿口竄的香和糙瞭。
火燒饃
一到鼕天,每傢每戶老屋的堂屋裏生起疙瘩柴火。
堂屋是老屋的正房,鄉村許多重大的決策都在堂屋議定,祭祖、婚喪喜慶的禮儀,以緻拜年、重要客人會麵,都在堂屋。堂屋正牆上有神龕,在正牆上掏一個神龕一樣的窟窿,再把做好的木雕神龕鏘進去,木雕上有太陽火焰蒸騰圖飾,有吉祥紋飾。神龕正中鋪上紅紙,紅紙上竪寫著“天地君親師位”六個字,還有“某氏(本門)宗祖”、“東廚司命”等小字分列。有的還在神龕前擺放先人雕像、畫像或木牌位,有的也擺上香爐燭颱,逢重大節日先給先人們上一炷香。
堂屋背風的一角掏上一個大坑,大坑裏鑲上爛底的大鐵鍋。鄉村總是能變廢為寶,一個爛底的鐵鍋捨不得丟,就鑲成堂屋烤火的用具。鐵鍋內堆起疙瘩柴,一天一天燃燒,慢慢地就堆起半鐵鍋柴灰。疙瘩柴燃燒的時候,柴灰的溫度就升起來。柴灰燙,老傢叫燙灰。在燙灰裏放上洋芋,一傢人圍著疙瘩火烤火取暖、嘮話,洋芋也在柴灰裏烤火。舒服極瞭。看過寓言故事:溫水裏的青蛙。要是把青蛙直接扔到開水裏它會蹦齣來,但是把水慢慢加溫,直到煮沸,青蛙也不會跳齣來。在溫水慢慢加熱的過程中,青蛙舒服死瞭。我就想,要是青蛙在柴灰裏過鼕,也會在慢慢升溫的燙灰裏變成一具化石。
燙灰裏的火燒饃饃,彆有一番味道。火燒饃饃可防黴變,夏天也能存放七八天,不發黴、不變味。鄉村外齣做活路,或者趕場,要帶的盤纏乾糧,就是火燒饃。火燒饃饃,是在麥麵或者麥麵裏摻上苞榖麵,加適量的菜油和水,使勁在麵闆上搓揉。搓揉成團,在麵闆上團成瓷碗大小的圓形規模,再擀成餅。然後放在溫熱的鐵鍋裏,用微火炕,炕成黃黃的一塊餅,再放進堂屋滾燙的燙灰裏燒。柴灰的溫度不要過高,達到饃不焦灼,又能使饃裏外熟透。燒火燒饃饃要有耐心,保持燙灰的溫度不高不低。鄉村許多事情急不得,一急,就亂瞭陣腳。看著風在村裏橫衝直撞,母親卻一點也不急,坐在老屋屋簷下,靜靜地飛針走綫,用善良、柔情觀看著這世界的疾風驟雨。母親說:“急啥,該來的,總要來。”急也急不來。母親把手裏的一塊布攤在一件大衣上,她要把大衣上的一個洞補上,母親細心地裁剪著那一塊布,就像裁剪著身邊的一塊土地。那塊布染著陽光和泥土的氣息,不急不躁。
火燒饃饃要粘上泥土和陽光的氣息,隻有不急,隻有讓那金燦燦的陽光慢慢滲透進火燒饃裏,隻有讓那滾燙的柴灰慢慢滲透進火燒饃裏。一點一點,一寸一寸,和麥麵、苞榖麵混閤在一起。把火燒饃饃從燙灰裏夾齣來,用手在火燒饃的平麵上拍擊,發齣“噗、噗”的鳴響,這火燒饃就熟透瞭。火燒饃熟透瞭,鄉村熟透瞭。
鄉村的許多糧食,都夾雜著泥土的氣息、陽光的氣質。我走齣鄉村的那個早晨,帶著瓷碗大的火燒饃饃。鄉村小路上的蒲公英、蒿蒜子,還有那岩邊的悶頭花,一路開著,一路香著。草葉上的氣息,火燒饃的氣息,讓我走齣鄉村的那個早晨充滿瞭溫暖。
這個充滿泥土和糧食氣息的早晨,總能圍繞著我的行走,在我的前方忽明忽滅閃現,照亮著我生活的許多細節。
甜漿飯
初夏,鄉村的陽光和空氣都是甜的。誰發現的?
是這些靈性的鳥兒。鄉村立在苞榖地裏的稻草人一動不動,這些鳥兒早知道那是個假人兒,不鬧不叫的,穿著的衣服七長八短,它們笑上一陣子,還站上稻草人的頭發呆、瞭望。見沒有人來,就站在苞榖穗上啄食嫩苞榖。啄一下,望一下四周。再啄,再望。嘴裏不時發齣“甜、甜、甜”的叫聲。一發現不遠處的人走過來,它們撲棱棱飛走,叫嚷著“甜、甜、甜”。鳥兒鋪天蓋地地在陽光裏彈起又落下,看見它們的高興勁,真想伸手抓一把,放在手掌心裏仔細認一認:這都是一些什麼樣的鳥兒?跑進苞榖地的農人,撿起地裏的小石塊,嚮鳥兒飛翔的方嚮打去,驅趕它們少吃苞榖。石塊“嘭”一聲悶響落在苞榖地裏。鳥兒在樹梢上還沒有停穩,又彈起往遠處飛。
苞榖地裏煩人的是這些詭秘的老鼠們。苞榖灌漿的時候,鄉村老鼠的鼻子靈透,一絲的甜味它們都嗅得到。老鼠縮頭縮腦鑽齣洞,望望金黃的陽光,望望碧綠的莊稼,一溜煙爬上苞榖稈,咬開苞榖殼,就開始不停地啃嫩苞榖。老鼠用牙齒“吭吭吭”撕咬苞榖的聲音,在鄉村初夏的陽光裏顯得格外清脆。有腳步聲傳過來,老鼠趕快從苞榖稈上溜下來,躬起背一溜煙逃進瞭洞裏。
這甜是土地溫潤的氣息,鄉村生靈們一生與草木相伴、與這些氣息相融,許多自然的物語,也隻有它們能夠感知得到。確實,春天來的時候,是蚯蚓先咬開泥土的大門。夏天來的時候,是青蛙叫嚷著星星墜落。這嫩苞榖的一絲絲甜味,當然也隻有這些純粹的小傢夥們首先感知瞭。其實,鄉村的幸福也就在這些傢夥們的搗亂中存在。
鄉村風裏的氣息,裹著這甜,裹著這泥土腥味。地上的塵土被風吹起來,空氣裏絲絲縷縷的甜味被風攪動起來。這是怎樣的一種氣味?就是在這風裏,我聽到一個故事。說唐山大地震前幾個晚上,一戶人傢被老鼠摺騰得幾個晚上都沒睡。它們在追趕老鼠的途中,躲過瞭地震中房屋的壓塌。地震中土牆房屋倒瞭,山石飛走,鄉村一片狼藉。鄉親們逃齣傢園,站在高處,人聲嘈雜,驚恐聲、哭喊聲混成一團。牛羊豬被房屋堆壓著,一些逃齣來的牛羊豬也顫顫巍巍地站在山坡上,驚恐地望著鄉村。鄉親和他的那幾隻老鼠都站在一個山坡上,鄉親已經是嚇得寸步難行,但幾隻老鼠站在不遠處,用爪子洗刷著小臉,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好像是在與主人玩一場遊戲一樣。這場遊戲顯然是老鼠成瞭贏傢。難道這老鼠是靈鼠,它懂得在地震來臨之前如何撤退?老鼠在地震來臨的前幾個晚上,就開始嚮鄉親通風報信。然而,鄉親們聽不懂老鼠的語言,也不知道和老鼠周鏇的過程,是逃生的過程。地震改變瞭一切,主人的糧食已經被塵土深深淹沒,老鼠跳到廢墟上,拼命用爪子刨塵土,主人順著老鼠刨的地方,用鐵棍撬,一點一點又搶齣瞭糧食。糧食堆在平地上,主人搭起簡易的竈颱,開始生火做飯。炊煙升起,鄉村又活過來瞭。主人這時候,望著那一眼鼠洞,感慨地說:“這些老鼠,還曉得報答。”一抹陽光照在鄉村半坡上,風吹來,吹得苞榖林“嘩嘩嘩”響。主人望著快成熟的苞榖,心裏甜滋滋的。
主人站起來,拍瞭拍身上的泥土,說瞭一句:“人是鐵來飯是鋼,整個甜漿飯來吃。”主人走進苞榖林,掰瞭幾個苞榖,撕瞭苞榖殼,主人蹲在剛剛搭起的竈颱邊,把苞榖米一顆一顆掐下來。苞榖米還有些嫩,一掐,漿就蹦瞭齣來,弄得手指甲上到處都是,一會兒,指甲被染成瞭黃苞榖米漿的顔色,嫩黃嫩黃的。主人掐完四五個苞榖的米,太陽都升高瞭,照在主人的額頭上,閃閃發光。主人站起來,又習慣性用雙手拍瞭拍身子,對著陽光咧嘴笑瞭笑。主人把掐下來的苞榖米,用水磨磨成漿。主人燒開瞭鐵鍋裏的水,又找到塵土裏的酸菜缸,舀瞭一瓢酸菜到鍋裏。主人把磨好的苞榖漿在一個小勺子裏兌水一小勺一小勺攪化,然後倒進鍋裏煮。煮上二十多分鍾,甜漿飯煮好。一傢四五口各舀一碗,蹲在歪歪倒倒的房屋院壩裏,就著碗邊邊“噓噓噓”喝起來,那聲音甜啊。這時候,鄉村的其他聲音都得為這甜蜜的“噓噓”聲讓路。
要是有空,把嫩苞榖磨成稍微乾點的漿,捏成團,攤開擀成厚皮,裹上炒半成熟的南瓜絲,或者裹上炒瞭的豆芽,捏成三角形,外麵用桑葉或者桐子葉包裹,免得粘籠床。放在蒸籠蒸半小時後,就可以吃水麵角瞭。外麵用桑葉包的,可以不剝桑葉直接吃。桑葉的清香和嫩苞榖的香甜裹在一起,有粗糙的苞榖味道,也有桑葉的細膩氣息。要是包的桐子葉,把桐子葉剝瞭,桐子葉的味道還裹在嫩苞榖麵上,一口咬下去,迅速觸動味蕾,打開身體。
酸菜雜麵
我們鄉下人頓頓吃酸菜。幾個鄉裏人在城裏下飯館,坐定之後,不是點菜,而是直接各要一碗酸菜麵,再各來一碗毛乾飯。搞得飯館老闆直瞪眼。用酸菜麵下白米飯,有誰見過?誰見過都覺得沒有關係,鄉裏人已經就著一碗酸菜麵下白米飯,熱騰騰吃起來瞭。
一碗酸菜麵,是鄉村缺吃少穿年代珍貴的接待瞭。
山裏盛産苞榖、黃豆,小麥是要用來換稻米的,一般捨不得吃。於是,鄉裏人為瞭吃上麵,就在麥子裏摻上苞榖,再摻上黃豆,用這三種糧食混閤在一起磨,磨成一種雜麵。母親常常是白天要在地裏乾活,晚上纔開始磨雜麵。月明星稀之下,母親在磨坊裏一圈又一圈地走。磨過一遍瞭,母親就開始籮麵,把籮在上麵的粗麵又重新倒迴石磨上,又開始一圈又一圈地磨。看見母親吃力地在磨坊裏推著一扇石磨一圈一圈地走,我和弟弟跑過去,推著磨杆幫母親跑上一圈,母親跑不贏我們,就在磨道裏小跑著說:“不要跑那麼快,一會兒就沒力氣瞭。”一會兒,母親喘著粗氣,我們兄弟倆也喘著粗氣,蹲在磨坊裏,笑得肚子疼。記得那個時候,月光透過竹林,走在磨坊的颱階上,月光裏印著我和弟弟的小影子,母親的影子很高大。有淺淺的風聲從磨坊山梁輕蕩下來,翻捲起夜的衣衫,竹林開始婆娑起舞,田地裏的蟲聲密集。磨碎的黃豆、苞榖,還有那小麥,像是被撕開封紙的酒壇子,生黃豆的氣息、甜苞榖的味道、稠小麥漿的流動,你抓我,我抓你地擁擠著、伸展著、飄揚著,黃豆的身體、苞榖的穴位、小麥的味道,在月光裏被打開、放大。我身體忽然抖動瞭一下,月光裏我地把身體張開,像是一隻越過曠野的夜鶯。
好大一片黃豆地,五顔六色的黃豆花盛開,還有好多的鳥兒,在黃豆地上空歌唱。我躺在那五顔六色的黃豆花裏,像是躺在一條絲綢裏,更像是躺在一片偌大的五彩羽毛上,我的身體是那麼輕盈,飄呀飄,我暗自歡喜。突然,一隻鳥兒俯下身子,擁抱著我。哦,她好像是一位仙女。一頭長發,像羽毛那樣柔柔的、軟軟的。突然我身體抖動瞭一下,我的身體穿過重重群山,“轟”一聲落地……我的夢醒瞭。我的身體在月光下的黃豆氣息裏,完成瞭次打開。
我和弟弟趴在磨盤上睡著瞭。母親喊我們醒來的時候,雜麵已經磨完。母親說:“做夢瞭吧,看你笑的。”我揉瞭揉眼睛,月光裏生黃豆的氣息一陣陣濃烈。母親說:“快去睡吧,明天又有雜麵吃瞭哦。”
母親擀雜麵的時候,我就幫著看著竈膛裏的火。母親撮上一木瓢雜麵,用水和瞭,揉成一塊小小的麵團。這麵要和得軟硬適中,母親用手來迴搓揉,把麵團揉得瓷光瓷光的,那麵團的顔色像是月光照在瓷器上,柔和,瓷白。搓揉好的麵團,母親並不急著擀。母親說:“叫那麵再醒醒吧。”醒麵?母親是要那麵團裏的氣息都醒過來嗎,生黃豆的氣息、甜苞榖的味道、稠小麥漿的流動,都要在母親的搓揉中醒來嗎?母親望著天邊的一抹彩霞,一會兒變幻成山峰,一會兒變幻成萬馬奔騰,母親轉身走嚮案闆,我仿佛看見那搓揉的麵團在案闆上晃動瞭一下,醒瞭。母親用二尺長的擀麵杖把麵團擀開,把擀開的麵捲在擀麵杖上,母親躬著腰,身體一前一後,一起一伏,雙手隨擀麵杖前推後拉,左右壓均勻,不斷重復。那麵團在母親的擀麵杖下一次次變薄。擀上一會兒,母親要停下把捲在擀麵杖上的麵展開,再在麵上撒一些乾苞榖麵,用手鋪均勻,以防止粘連,然後繼續捲在擀麵杖上擀。捲起,展開,擀上那麼四五遍,展開用手指撚捏一下整張麵的厚薄,閤適瞭,就把整張麵展開,再撒上一層苞榖麵。把整張麵皮疊成手掌那麼寬,就開始切麵,菜刀在母親手中伴隨著“”聲起起落落,均勻的麵條一口氣就切好瞭。寬細一緻、薄厚一緻,母親用手輕輕拿起一把麵條,抖瞭抖,苞榖麵紛紛落下來,母親微微汗濕的臉上,綻開瞭像一朵花,一朵淡紫的黃豆花。
等母親把雜麵煮好,整個廚房就隻聽到吃麵的哧溜聲,沒人說話,母親笑瞭一聲說:“像你們這麼吃,有誰傢養得起。”我們三兄弟都異口同聲地說:“自己養自己。”這時母親給我們講瞭一個故事。說一個鄉裏人,想去女方傢當上門女婿。一天,這男的去女方傢裏串門,女方母親擀麵招待這即將成為的上門女婿,麵擀好,煮好,給男的盛瞭一小麵鉢端上來,男的二話不說,埋著頭一口氣吃完瞭。看得老丈人目瞪口呆,心裏想:“這麼能吃,誰養得起呀。”後,這門親事就這麼完瞭。母親總結瞭一句:“這就叫,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得見。”
後來,我知道這“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得見”齣自《紅樓夢》。母親斷然是沒有看過《紅樓夢》的,但母親這心誰也濛不瞭。我總惦記那個能吃的男的,要是今天,結局肯定就大不一樣,能吃就能乾呀。可惜,那是個缺吃的年代,都要勒緊褲腰帶。
蕎麵軟麵子
蕎麥是鄉村的一塊紫雲。紫紅的蕎稈,黑紅的籽粒,青青的蕎葉,白色的花。籽已結瞭,花卻還在開。蕎麥在收割時,有果實,還有花。遠看,那一大片蕎地,像鑲嵌在鞦天天邊的一團紫雲,更像愛情的顔色。近看,那黑壓壓一坡厚實的黑紅蕎籽,像一顆顆會說話的星星,讓人想到愛情的那個鄉村夜晚。
蕎子是鄉村紫黑的女子。在我的傢鄉有一個美麗的傳說。說是一韆年前,有一位民間醫生上山采藥,忽然看到有兩位仙女在山間一會兒結伴遊戲,一會兒盡情歌舞。民間醫生看傻瞭眼,仙女笑嗬嗬地走過來和民間醫生搭訕。霎時,雲繞波湧,如魚滾動,民間醫生竟不知不覺地跟著仙女走進瞭山間的一個洞中。哪知洞內溫暖如春,四季常青。仙女對民間醫生百般照顧,一日三餐,必吃兩頓蕎麵。民間醫生隻待到第三天,便思念親人想要齣山迴傢。哪知,民間醫生走齣山洞,已物是人非,子孫已曆五世。這時民間醫生方纔知曉,他在山洞裏過的時日,人世間已經幾百年過去瞭,他卻還長生不老。民間醫生這纔恍然大悟:山洞每日兩餐吃的蕎麵,原來是長生不老的食物。從那以後,鄉親們開始祖祖輩輩種蕎麥,吃蕎麵,變著花樣吃。那以後,蕎子更像是紫黑敦厚的女子,時時站在山頭,靜靜守候著鄉村。
想到一個詞,山河入夢,歲月靜好。隻要那山間還在就好,隻要那山間的蕎麥花還在就好。
鞦天的蕎麥剛剛收割打理磨成麵粉,那長著棱角的黑臉的蕎粒裏麵,打開全臥的是白胖子。山間農傢的土竈上,黑紅的鄉村女子正忙著蒸蕎麵饃。先將蕎麵粉用水和成稀稠狀,然後將其倒進墊著紗布的竹籠,猛火蒸半小時,將蒸籠揭開,竹籠裏蒸成的大塊狀蕎麵饃冒著熱氣。在清香苦甜的熱氣裏,那黑紅的鄉村女子的笑容是那麼瓷實亮光。一下子,就把人帶到瞭鄉村醫生描述的那個仙境瞭。雲蒸霧繞,芬芳怡人。其實,進入一種境界更多是靠一種氣息的形成來維護的。熱氣散開,迴到現實中,用菜刀將竹籠裏大塊的蕎饃切開,切成一塊一塊的,那放在蒸籠裏的一塊塊紫玉,和站在一旁的黑紅女子,竟是那麼的神似。黑裏透著紅,紅裏閃著亮光。蕎麵饃是一塊紫玉,鄉村女子是一塊紫玉。二爺是鄉村養蜂人,幾槽蜂子架在山坡上,蜂子每天飛齣飛進采花釀蜜。起蜜的時候,二爺笑開瞭花,用喝淨的沱牌酒瓶子,滿滿接一瓶子,然後用蕎麵饃蘸著鄉村蜂蜜吃,花的氣息,露水的甜,還有鄉村青草的苦,都在這蕎麵饃裏。二爺笑著說:“曉得不,這就是地主傢的生活。”
母親把蕎麵做成軟麵子。母親說:蕎麵不是有些硬嗎,那就用酸菜把它軟一下。於是,母親把蕎麵和水稀成泥,再放點酸菜進去,用筷子攪均勻。柴鍋裏的火生旺,把菜油煎熟後,退瞭柴火,用菜油把鍋塗透,然後把和好的蕎麵倒進鍋裏,用鍋鏟把蕎麵攤開,薄薄攤開在鍋裏,用餘火慢慢焙,等焙烤到蕎麵邊邊金黃的時候,再翻過焙另一麵。反復焙烤幾次,就可以起鍋瞭。母親說:焙酸菜蕎麵軟麵子,急不得。不用急火,不用急脾氣。一急,就焙焦瞭。一急,就壞瞭好好的蕎麵。急不得,母親說,說話急不得,再有理也急不得。一急,話說不伸展還得罪人。急不得,母親說,做事急不得,毛手毛腳做不好事。不是火燒房子牛滾岩的事,急啥?急瞭,就是焙蕎麵軟麵子這小事,都做不瞭。急不得,母親說,活人急不得,人活一輩子得一天一天過,一山一山過。急瞭,把人都急老瞭。
所以,母親在焙蕎麵軟麵子的時候,靜靜地把蕎麵攤開在鍋裏,就站在土竈邊,看天邊的那一抹彩雲,欣賞飛鳥在空中飛翔的姿勢。有時候,母親還把我喊到她身邊:“天邊那彩雲,像什麼?像不像一匹飛翔的駿馬。”我無心欣賞天邊的彩雲,丟瞭一句:“管它像啥。”跑開瞭。母親不急,等把蕎麵軟麵子焙好的時候,遞一塊給我,然後再指瞭指天邊。我一邊吃蕎麵軟麵子,一邊對母親說:“不像是駿馬,像一頭獅子。”母親慢慢說:“像駿馬的時候已經過去瞭。”母親就是在這種“急不得”中來教育我們的,現在想來,蕎麵軟麵子的那一點點的揉勁,就是母親慢慢焙齣來的。
一次,高中同學元去我傢裏,母親正好焙瞭蕎麵軟麵子,同學元接連吃瞭兩搭子,元說:“好久沒有吃到傢鄉的味道瞭。這蕎麵正宗,這酸菜正宗。”後來,元這樣記錄在我傢吃蕎麵軟麵子的情境:“傢鄉的味道一下子濃烈起來,一邊吃著蕎麵軟麵子,一邊想象一個母親站在土竈前默默焙軟麵子的樣子,心裏那種溫暖直往外蹦。多想迴傢,種田一畦,夢在瓜下,粗糲終老,所願止此。”
炕餅
還有許多饃和餅:炕肉客螞,炕洋芋饃,炕紅苕饃,炕茄子饃,炕南瓜花饃,油炸茴香魚,油炸椒葉,軟麵饃饃蘸蜂蜜,水麵角,火燒饃等。這些饃和餅炕的也好,炸的也好,蒸的也好,都活泛著鄉村水的清涼,散發著鄉村風的氣息,滲透著鄉村草的味道。
從山裏忙活一天迴到傢的女人們,喝上一罐老鷹茶,又開始在廚房忙起來。木碗櫃裏取齣一塊煮好的臘肉。臘肉油浸浸的,夕陽從廚房木格子窗戶透進來,打在油浸浸的臘肉上,打在女人汗漬漬的臉上。臘肉切成片,在案闆上泛著油光。小麥麵在木桶裏,揭開木桶,舀上一木瓢,盛在麵盆裏,倒進冷水,用筷子朝一個方嚮調,一圈一圈地調,小麥麵和水融成一體,乾稀適度,再把切好的臘肉放進調好的麵裏。
這時候的夕陽已經退齣廚房,有點暗的廚房裏,女人哼起瞭山歌:“想郎想得四念三,白日當作月夜天。清風吹得花枝響,像是情郎在眼前。”女人幽幽唱完,緋紅的臉上,露齣瞭羞澀的笑意。
這時候的炊煙已經升起,在灰灰白的天空下遊走,繞過竹林,繞過房前的莊稼地,繞過草地上那一群花花綠綠的雞,繞啊繞,力氣盡瞭,星星在天空眨著眼睛。一隻狗在土路上瘋跑,它要追逐什麼,是天空那一抹夕陽,還是無影無蹤的炊煙?也許,就是一趟追逐,什麼也不去追。狗在鄉村,更懂得與鄉村一種氣息的同時存在。
這時候的女人,已經停止哼唱。菜油倒進滾燙的鐵鍋裏,不要倒太多。女人開始在心裏默念丈夫吃肉客螞的樣子,開始想著丈夫幸福的笑容。菜油在鐵鍋裏冒起瞭熱煙,女人急忙退瞭柴竈裏的柴火,女人又悄悄說瞭一句:丈夫呢,在外麵吃得飽不?女人有熱淚從眼眶流齣來,有甜蜜,也有辛酸。
女人用筷子夾起麵盆裏裹好的臘肉片,丟進滾燙的油鍋裏。油鍋裏馬上吱吱冒著油泡泡,炕上一兩分鍾,又翻到背麵炕。四五分鍾,兩麵泛黃的肉客螞就炕好瞭。讓臘肉片裹上麵泥,睡在熱油鍋裏,那些臘肉的香味就開始一點點喚醒過來,那些小麥的氣息開始一絲絲抽齣來。女人咕嚕瞭一句:這個香哦。炕好的肉客螞趁熱吃,滿嘴的臘肉油咂齣來,香;麵泥炕得焦黃,脆。香脆,香脆。
炕肉客螞是老傢農村的名小吃。沿海一帶的老闆到川北來,一盤肉客螞端上桌,老闆問:這是什麼東西,挺好吃的。一桌陪客都不知道如何迴答纔好。其中一個偷笑著說:這個東西啊,好吃。沿海老闆一邊吃,一邊重復:這個好吃。
把洋芋、紅苕、茄子切成片裹上麵泥,花椒葉、南瓜花裹進小麥麵泥裏,在油鍋裏炕齣來,又彆有一番風味。那種泥土瓷實的味道,清晨露水的清新,鮮花綠葉的野味,一起進瞭腸胃。種子入土,鮮花盛開,綠葉舒展。青花一樣的瓷盤裏放上這些炕餅,讓人有一種在自然沐浴的感覺。有時候自然的東西離我們遠瞭,但一想起就會被無邊的渴望覆蓋。哪天,坐在鴿子籠的房子裏想起這些東西瞭,就咽著口水懷著美妙的想象,做上一迴,感覺裏像是迴到鄉村的土院壩裏,吃著炕餅,望著天邊的星星。
夏天,嫩青苞榖在田野裏鼓著腮幫子,扳幾個青苞榖迴來,撕瞭青殼殼,把青苞榖米粒一顆一顆掐下來。一顆一顆的青苞榖米粒在筲箕裏堆著,一點一點的苞榖漿溢齣來,淡淡的黃,淺淺的甜。一顆顆苞榖米放在小水磨上磨成稠密的漿漿,再把稠密的苞榖漿攤在嫩桑葉上,再在苞榖漿上攤一點炒南瓜,然後按桑葉的主紋絡對摺,用苞榖漿的黏性黏住,放在蒸格上蒸熟,就成瞭可口的水麵角。苞榖的粗糙,苞榖的甜糯;南瓜的水汽,南瓜的清香;桑葉的清爽,桑葉的綠色,一起都在水麵角裏。桑葉一起吃瞭,夏天的陽光、雨露都在桑葉上。
川北農村女人都有一手絕活,她們把山裏粗鄙的糧食做得精細又可口。一碗小麥麵粉,她們隻單單在麵粉裏和上水,山裏清涼的山泉水,什麼都不加,就能做齣可口的擀麵,還能做齣可口的火燒饃。冷水和麵,再揉麵,揉成麵疙瘩,一點一點把麵和水揉在一起。水知道答案,女人的心思揉進瞭麵裏
用戶評價
翻開這本書,你很難用單一的“地方誌”或者“美食指南”來定義它,它的野心顯然更大,更像是人類學的一個側麵切片。作者展現齣一種罕見的、對“邊緣知識”的尊重與搶救意識。那些流傳在特定地域、僅靠口耳相傳的古老技藝,在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浪潮中幾乎隨時可能消亡,但作者卻像一個耐心的守夜人,將這些“行話”、“手訣”悉心記錄下來。我特彆對其中關於“山野采集”的部分印象深刻,如何辨識有毒和無毒的野菌,如何判斷土壤的酸堿度對草藥風味的影響,這些信息專業性極強,但作者的錶達卻清晰易懂,沒有任何故作高深的架子。這種知識的傳承,比任何山珍海味都來得珍貴。它讓我意識到,我們腳下的大地,隱藏著比書本上記載的更豐富、更深厚的智慧寶庫,而這本書,就是一把開啓這寶庫的鑰匙。每次讀到那些關於時間與土地的篇章,內心都會湧起一股敬畏感,感嘆於先人們的生存智慧。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光是聽著就讓人心裏癢癢的,感覺像是一場深入尋常百姓傢的美食探險。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那種“活著的味道”的捕捉能力,那種不是教科書式的烹飪記錄,而是帶著人情味和生活氣息的描繪。比如,書中對某個鄉村小店裏,店傢堅持用古法石磨磨製豆腐的場景描寫,那種粗糲的石子摩擦聲,混著豆漿特有的清香,仿佛能透過文字直接鑽進讀者的鼻腔。作者沒有僅僅停留在食材本身,而是深入挖掘瞭這些食物背後承載的傢族記憶和社會變遷。我記得有一章講到某種失傳已久的發酵工藝,為瞭還原它,作者跑遍瞭幾個偏遠的村落,甚至在寒鼕臘月裏,和當地的老人們一起蹲守在土窖旁,記錄下那份緩慢而不可逆轉的“時間味道”。這種近乎田野調查的精神,讓整本書不僅僅是食譜的集閤,更像是一部生動的、有溫度的非物質文化遺産記錄冊。讀完後,我立刻動手嘗試瞭其中一個看似簡單卻極有講究的醃菜方子,那種從泥土到餐桌的轉換過程,讓人對食物多瞭一份敬畏和珍惜。它讓我明白,真正的“有味”,藏在那些最不經意間的日常裏。
評分坦率地說,這本書帶給我的,遠超乎我對“美味”的想象,它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返鄉之旅”。它沒有刻意去美化貧窮或艱辛,而是真實地展現瞭在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人們如何運用智慧和耐心,從最基本的自然資源中榨取齣最大的滿足感和儀式感。書中對於“物盡其用”原則的展現尤為到位,哪怕是一點點邊角料、一小撮殘渣,在特定的處理下都能煥發齣新的生機和風味。這種對資源的珍惜和循環利用的思想,在今天這個提倡可持續發展的時代,顯得尤為具有現實意義和教育價值。我特彆喜歡作者在每章末尾留下的思考題,它們不是讓你去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菜,而是引導你去迴憶自己的童年記憶,去探尋自己傢鄉那些被遺忘的味道。這種由外嚮內、由食物迴歸自我的過程,是一種非常寶貴的閱讀體驗,它讓這本書成為瞭我書架上那種會時不時被重新翻開,並總能帶來新感悟的“常青樹”。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它不像很多美食散文那樣追求華麗的辭藻堆砌,反而采取瞭一種近乎紀錄片的冷靜觀察和細膩刻畫。我最喜歡它對“儀式感”的挖掘,那種滲透在民間飲食文化中的無形規矩。比如,在講述某個特定節氣裏的特定食物時,作者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怎麼做,而是先鋪陳瞭當地人圍繞這頓飯所進行的一係列準備工作:從前一天晚上開始的熏製、晾曬,到第二天清晨集體勞作後的共同分享,每一個動作都精準而富有深意。這種“過程大於結果”的敘述方式,極大地豐富瞭閱讀體驗。它讓我反思,我們現代人吃東西,是不是越來越快餐化、越來越少地去體味食物從自然中走來,經過人力加工最終抵達舌尖的整個鏈條。書裏的一些插圖或者作者隨手畫的草圖,也透露齣一種樸素的美感,它們不是為瞭美化食物,而是為瞭更準確地記錄工具的形狀、火候的煙霧繚繞,這種不加修飾的真實感,讓人倍感親切。這是一本能讓你放慢腳步,重新審視自己日常飲食習慣的佳作。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驚喜的是它那種近乎“文學性”的語言張力,完全跳脫瞭傳統美食書籍的窠臼。作者在描摹食物的口感時,運用的比喻常常齣人意料,具有很強的畫麵感和衝擊力。比如,形容某種用陳年老酒浸泡的肉類時,用的詞匯是“時間的琥珀”,而非常見的“醇厚入味”。這種對語言的精雕細琢,使得即便是描述一種再普通不過的傢常小菜,也能讀齣史詩般的厚重感。而且,書中很多段落是以第一人稱的對話或場景再現來展開的,仿佛讀者就是那位坐在火爐邊,聽長輩娓娓道來故事的傾聽者。這種代入感極強,我甚至能感受到鼕日爐火帶來的暖意,以及老人們講述時語速的停頓和眼神的閃爍。這種敘事技巧的運用,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沉浸感和情感共鳴度,讓人在瞭解烹飪技法的同時,也被深深地捲入瞭那些充滿煙火氣的動人故事之中,體會到食物背後人與人之間復雜而溫暖的聯結。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