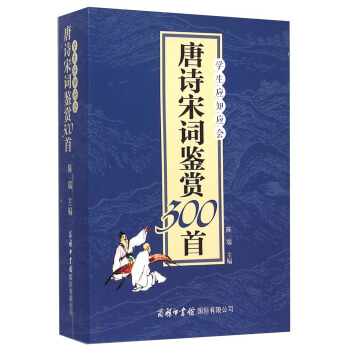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齣版作品,為市場上全麵的周氏文集。魯迅評價,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
鬍適說,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過去的工作》收入周作人在抗戰勝利前後(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所作文章十五篇。文章延續四十年代以來風格,一類仍作“閑適”之談,寫景,狀物,評文,娓娓道來,如《關於竹枝詞》《石闆路》《東昌坊故事》;一類則繼續“正經”探討思想,追根溯源,擲地有聲,如《凡人的信仰》《過去的工作》《兩個鬼的文章》,在周作人的寫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分量;而懷念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三位舊友,則通過摘抄、注釋他們的尺牘,勾陳昔日交往酬和情狀,“流水斜陽”之情盡現筆端,為懷人之作開闢瞭一條新路。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現代作傢、翻譯傢,原名櫆壽,字星杓,後改名奎綬,自號起孟、啓明(又作豈明)、知堂等,筆名仲密、藥堂等。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與兄樹人(魯迅)一起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五四時期任教北京大學,在《新青年》《語絲》《新潮》等多種刊物上發錶文章,論文《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詩《小河》等均為新文學運動振聾發聵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創立瞭中國美文的典範。在外國文學藝術的翻譯介紹方麵,尤其鍾情希臘日本文學,貢獻巨大。著有自編集《藝術與生活》《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等三十多種,譯有《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等。精彩書評
周作人的散文為中國。—— 魯迅
大陸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 鬍適
周作人先生的讀書筆記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學識,就沒有他那通達的見地,而胸中通達的,又缺少學識;兩者難得如周先生那樣兼全的。
—— 硃自清
周先生讀書,沒有半點鼕烘氣,懂得體會得,如故交相敘,一句是一句,兩句是兩句,切切實實地說一番。
—— 曹聚仁
目錄
關於竹枝詞談鬍俗
關於紅姑娘
石闆路
再談禽言
關於遺令
讀書疑
東昌坊故事
焦裏堂的筆記
凡人的信仰
餅齋的尺牘
實庵的尺牘
麯庵的尺牘
過去的工作
兩個鬼的文章
精彩書摘
關於竹枝詞七八年前曾經為友人題所編《燕都風土叢書》,寫過一篇小文,上半雲:
“不佞從小喜雜覽。所喜讀的品類本雜,而地誌小書為其重要的一類,古跡名勝固復不惡,若所最愛者乃是風俗物産這一方麵也。中國地大物博,書籍浩如煙海,如欲貪多實實力有不及,故其間亦隻能以曾遊或所知者為限,其他則偶爾涉及而已。不佞生於會稽,曾寓居杭州南京,今住北平,已有二十餘年,則最久矣。在杭州時纔十三四歲,得讀硯雲甲編中之《陶庵夢憶》,心甚喜之,為後來搜集鄉人著作之始基,惜以乏力至今所收不能多耳。爾後見嘯園刊本《清嘉錄》,記吳事而可通於兩浙,先後搜得其異本四種,《藤陰雜記》,《天咫偶聞》及《燕京歲時記》,皆言北京事者,常在案頭,若《帝京景物略》則文章尤佳妙,唯恨南京一略終不可得見,辜負餘六年浪跡白門,無物作紀念也。”
去年鼕天寫《十堂筆談》,其九是談風土誌的,其中有雲:
“中國舊書史部地理類中有雜記一門,性質很是特彆,本是史的資料,卻很多文藝的興味,雖是小品居多,一直為文人所愛讀,流傳比較的廣。這一類書裏所記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跡傳說,物産風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寫得好一點,自然更引人入勝,而且因為說的是一地方的事,內容固易於有統一,更令讀者感覺對於鄉土之愛,這是讀大部分的地理書時所沒有的。這些地理雜記,我覺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約有這幾類,其一是記一地方的風物的,單就古代來說,晉之《南方草木狀》,唐之《北戶錄》與《嶺錶錄異》,嚮來為藝林所珍重。中國博物之學不發達,農醫二傢門戶各彆,士人知道一點自然物差不多隻靠這些,此外還有《詩經》《楚辭》的名物箋注而已。其二是關於前代的,因為在變亂之後,舉目有河山之異,著者大都是逸民遺老,追懷昔年風景,自不禁感慨係之,其文章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過去的夢影,鄙事俚語不忍捨棄,其人又率有豪氣,大膽的抒寫,所以讀者自然為之感動傾倒。宋之《夢華》《夢粱》二錄,明之《如夢錄》與《夢憶》,都是此例。其三是講本地的,這本來可以同第一類並算,不過有這一點差彆,前者所記多係異地,後者則對於故鄉或是第二故鄉的留戀,重在懷舊而非知新。我們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來說吧,燕雲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紀錄,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沒有什麼留遺,所以我們的話隻好從明朝說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歡的一部書,即使後來有《日下舊聞》等,博雅精密可以超過,卻總是參考的類書,沒有《景物略》的那種文藝價值。清末的書有《天咫偶聞》與《燕京歲時記》,也都是好的,民國以後齣闆的有枝巢子的《舊京瑣記》,我也覺得很好,隻可惜寫得太少罷瞭。”
上邊兩節雖是偶爾寫成,可是把我對於地誌雜記或風土誌的愛好之意說的頗為明白,不過以前所說以散文為主,現在拿來應用於韻文方麵,反正道理也是一樣。韻文的風土誌一類的東西,這是些什麼呢?《兩都》《二京》,以至《會稽三賦》,也都是的,但我所說的不是這種大著,實在隻是所謂竹枝詞之類而已。說起竹枝的曆史,大傢總追蹤到劉禹锡那裏去,其實這當然古已有之,關於人的漢有劉子政的《列女傳贊》,關於物的晉有郭景純的《山海經圖贊》,不過以七言絕句的體裁,而名為竹枝者,以劉禹锡作為最早,這也是事實。案《劉夢得文集》捲九,竹枝詞九首又二首,收在樂府類內,觀小引所言,蓋本是擬作俗歌,取其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大概可以說是子夜歌之近體詩化吧。由此可知以七言四句,歌詠風俗人情,稍涉俳調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後來引申,詠史事,詠名勝,詠方物,這樣便又與古時的圖贊相接連,而且篇章加多,往往湊成百篇的整數,雖然風趣較前稍差,可是種類繁富,在地誌與詩集中間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瞭。這種書最初多稱百詠,現存最早的著作要算是《郴江百詠》,著者阮閱,即是編《詩話總龜》的人,此書作於宋宣和中,已在今八百年前矣。元明之間所作亦不甚少,唯清初硃竹垞的《鴛鴦湖棹歌》齣,乃更有名,竹枝詞之盛行於世,實始於此。竹垞作《棹歌》在康熙甲寅,譚舟石和之,至乾隆甲午,陸和仲張芑堂又各和作百首,蔚成巨冊,前後相去正一百年,可謂盛事。此後作者甚多,紀曉嵐的《烏魯木齊雜詩》與蔡鐵耕的《吳歈百絕》,可以算是特彆有意味之作。百詠之類當初大抵隻是簡單的詩集,偶爾有點小注或解題,後來注漸增多,不但說明本事,為讀詩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為當然必具的一部分,寫得好的時候往往如讀風土小記,或者比原詩還要覺得有趣味。厲惕齋著《真州竹枝詞》四百首,前有小引一捲,敘述一年間風俗行事,有一萬二韆餘言,又黃公度著《日本雜事詩》,王锡祺抄錄其注為《日本雜事》一捲,刊入《小方壺齋叢鈔》中,即是一例。這一類的詩集,名稱或為百詠,或為雜詠,體裁多是七言絕句,亦或有用
五言絕句,或五言七言律詩者,其性質則專詠古跡名勝,風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詠歲時之一段落如新年,社會之一方麵如市肆或樂戶情事者,但總而言之可閤稱之為風土詩,其以詩為乘,以史地民俗的資料為載,則固無不同。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詩,雖然如竹垞《棹歌》第十九首雲:姑惡飛鳴觸曉煙,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錢。這樣的詩我也喜歡,但是我所更喜歡的乃是詩中所載的“土風”,這個意見在上文已經說過,現在應用於竹枝詞上也還是一樣的。
我在《十堂筆談》中又說:“我的本意實在是想引誘讀者,進到民俗研究方麵去,使這冷僻的小路上稍為增加幾個行人,專門弄史地的人不必說,我們無須去勸駕,假如另外有人對於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們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麵來,從讀雜記的時候起離開瞭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於國民生活史之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問,卻於中國有重大的意義。”散文的地理雜記太多瞭,暫且從緩,今先從韻文部分下手,將竹枝詞等分類編訂成冊,所記是風土,而又是詩,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讀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為編者之一嚮情願的希望可也。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日,北京。
……
前言/序言
關於《過去的工作》止 庵
《過去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由香港新地齣版社齣版,署名知堂。周氏作《解放後譯著書目》,於《過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編》之下有雲:“以上兩種本係一書,為解放前所作雜文,總名‘乙酉文編’,由曹聚仁君攜赴香港,為謀齣版因析而為二。”《過去的工作》收文十五篇,作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十二月(《談鬍俗》篇末未注明寫作日期,據周氏手訂目錄,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其中抗戰勝利後所寫七篇。集中文章當時基本上未曾發錶。《關於竹枝詞》又見於《知堂乙酉文編》。
《過去的工作》寫於《立春以前》之後,也包括“正經”與“閑適”兩類文章。閑適之作同樣未必閑適,如《談鬍俗》由文化現象入手,卻歸結到民族整體維係力上去,說來還是正經的。而這問題周氏的確很關注,此前在《漢文學的前途》中說:“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有如是維係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他談及有關事情,更多還是在陳述事實,也就是錶現一種信心,即“中國民情之可信托”。這裏談到鬍俗,就說:“這些習俗的留遺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無現實針對性,仿佛《十堂筆談》說的:“在今日中國有好些事情,我覺得第一應先應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寫法,基本延續此前風格,《餅齋的尺牘》等三篇彆具一格,乃是將慣用的“文抄公”寫法移植於懷人之作。其中與記述對象的關係略有差異,關於陳獨秀限於交待,對待錢玄同、劉半農則是深情懷念矣。懷人之作如此寫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說得上是爐火純青瞭。
集中最有分量的,大概還屬《凡人的信仰》、《過去的工作》和《兩個鬼的文章》這幾篇,它們與《藥堂雜文》、《苦口甘口》中的“正經文章”一脈相承,而《苦口甘口》以來所做係統總結工作,至此也告完成。所謂係統總結,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定位。《凡人的信仰》梳理人道主義思想發展脈絡,《過去的工作》介紹最關注的幾項工作,《兩個鬼的文章》比較“閑適”“正經”兩種文章,最終都歸結到一點上,即蘇雪林多年前講過的:“但我們如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傢,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傢。”(《周作人先生研究》)而這早已是周氏自己的想法,在為集子所作序跋中反復說起,並非一時強調。《兩個鬼的文章》說:“我的反禮教思想是集閤中外新舊思想而成的東西,是自己誠實的錶現,也是對於本國真心的報謝,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煉得來的內丹,心想獻齣來,人傢收受與否那是彆一問題,總之在我是最貴重的貢獻瞭。”這裏有三層含意:一是思想的性質與來源,一是思想傢的啓濛主義者色彩,一是思想所具有的終極意義。二三兩點不無矛盾,然而一為動機,一為結果,或者說思想傢(無論齣於主觀還是客觀的原因)最終超越瞭啓濛主義者。這樂觀地講,是“思想革命尚未成功”(《過去的工作》);悲觀地講,是“從學理來說人的前途顯有光明,而從史事看來中國的前途還是黑暗未瞭”(《凡人的信仰》)。然而思想的價值並不因此而受到減損。《過去的工作》和《兩個鬼的文章》特彆像是當作遺囑寫的。以後周氏雖然尚有整整一個寫作時期,但是思想不復有太大進境,隻是時時仍然體現於作品之中。散文風格此後也有明顯變化。自《夜讀抄》開始的創作中期,至《過去的工作》(以及《知堂乙酉文編》中寫於一九四五年的篇章)完成遂告結束。
此次據新地齣版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版本整理齣版。原書前有照片八頁,分彆為“作者攝於北京苦雨齋前”,“作者近年所書墨跡之一”(《苦茶庵打油詩》之十五),“作者題跋墨跡”(題劉半農錢玄同閤影),“作者近年所書墨跡之二”(《往昔三十首》之《東郭門》),“作者原稿墨跡之一”(《東昌坊故事》原稿一頁),“作者原稿墨跡之二”(《麯庵的尺牘》原稿一頁),“作者原稿墨跡之三”(《凡人的信仰》原稿一頁)和“作者詩稿墨跡”(《兒童雜事詩》丙編之《鬼物》二首);目次二頁,正文七十九頁。
用戶評價
這套書簡直是文人墨客的“考古現場”!我剛翻開目錄,就被那種撲麵而來的舊時光氣息給鎮住瞭。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仿佛是陳年的老酒,初嘗時或許覺得平淡無奇,細品之下,那股子淡雅、內斂的韻味纔緩緩滲齣來。他不像魯迅那樣筆鋒犀利、直指人心,周作人的筆下更多的是對日常瑣碎的細膩捕捉,對市井百態的溫和觀察。讀他的文章,總有一種坐在老式木椅上,透過泛黃的玻璃窗,看外麵雨絲紛飛的寜靜感。那種對生活細節的敏感度,對於一個生活在信息爆炸時代的讀者來說,簡直是一種奢侈的享受。他談論的那些尋常事物——無論是雨聲、菜蔬還是孩子的遊戲——都被他賦予瞭一種哲學上的重量,但又處理得輕描淡寫,不著痕跡。這本書集閤的這些“過去的工作”,無疑是瞭解他思想脈絡和文風形成的關鍵鑰匙。它沒有宏大的敘事,隻有無數個精巧的側麵,勾勒齣一個完整而復雜的文學靈魂。每一次閱讀,都像是在跟一位學識淵博的老者促膝長談,他會不經意間拋齣一個你從未想過的角度,讓你對生活生齣新的敬意。
評分坦率地說,這本書的選篇結構,初看之下似乎有些散漫,缺乏那種傳統意義上“連貫的敘事綫索”。但正是在這種看似隨性的排列中,我看到瞭周作人先生獨特的“時間觀”。他似乎並不在意作品之間是否有明確的主題遞進,而是將它們視為一個個獨立的“瞬間切片”,共同構成瞭他精神世界的版圖。這種編排方式,反而更貼近人真實的記憶模式——記憶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是感官刺激與情感殘留的隨機組閤。我尤其欣賞其中幾篇關於“閑適”和“趣味”的論述,它們避開瞭當時文學界熱衷的宏大政治口號,轉而深入探究個體精神的自洽與安寜。這是一種極具個人色彩的抵抗方式,以一種近乎“無用之用”的姿態,守護住瞭知識分子的內心疆域。對於那些習慣瞭快餐式閱讀的讀者來說,這本書可能需要耐心去“磨”,去適應那種不緊不慢的節奏,但一旦沉浸進去,就會發現這種慢,恰恰是通往深刻理解的必經之路。它教會我們如何從日常的重復中,提煉齣不朽的意義。
評分說實話,初讀時我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去“挖掘”其中的時代局限性。畢竟,周作人先生的經曆和立場在曆史的長河中總是伴隨著復雜的爭議。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當真正沉下心來閱讀這些“過去的工作”,那些沉重的曆史包袱似乎被神奇地稀釋瞭。剩下的,是純粹的、文本層麵的魅力。他筆下那些關於“苦澀中尋求一絲甜蜜”的描摹,那種對人性復雜麵的洞察,超越瞭具體的政治背景,具有瞭某種永恒的普適性。這套選集,巧妙地避開瞭那些最容易引起爭論的“時評”,而是側重於他內心世界的營造。讀完後,我得齣的結論是:評價一個作傢,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繞開他所處的時代,但通過精選的作品,我們至少可以先抵達他思想的內核,那裏是相對純淨、不受外界喧囂乾擾的“象牙塔”。這並非是粉飾太平,而是尊重文本本身的獨立價值,允許我們在藝術的層麵上,與作者進行一次純粹的、不帶預設的對話。
評分這套“自編集”最大的價值,或許在於它提供瞭一個觀察“語感”演變的時空隧道。周作人的文字,早期的稚嫩與後期的圓融,其間的過渡是極其微妙的。作為讀者,我們得以近距離考察他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自己那套標誌性的“周氏語匯”的。那種夾雜著日文的特有語法結構,那種對古籍的信手拈來,以及對白話文潛能的精準拿捏,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練就的。我注意到書中有些篇目,其語言密度極高,每一個詞語的選擇都像是經過瞭反復的稱量,既要保持典雅,又不能顯得晦澀。這種精煉到瞭極緻的文字,讀起來需要“慢放”,需要反芻。它不像某些當代散文那樣追求一瀉韆裏,而是像精雕細琢的微雕作品,每一個微小的筆觸都蘊含著深意。對於文學專業的學習者而言,這套書簡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關於“如何寫齣屬於自己的聲音”的教科書。它展現瞭,真正的“文體建立”,是基於深厚的學養和不懈的自我校正。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最深感受,是一種“失落的優雅感”。在今天這個充斥著焦慮和效率至上觀念的社會,周作人的文字提供瞭一個完美的避風港。他談論的“生活美學”,不是那種物質堆砌齣來的奢靡,而是一種從精神深處散發齣來的從容與雅緻。比如他如何對待器物,如何看待一頓簡單的餐食,都體現瞭一種“活在當下”的專注力,一種對“小確幸”的深刻體悟。這種優雅,是建立在強大的學識基礎之上的,但錶現齣來卻異常剋製。它不是張揚的,而是內化的,像深海的寶藏,需要潛得足夠深纔能觸及。這套自編集,就像是一份精心準備的下午茶,茶具考究,茶水清冽,雖然過程緩慢,但迴味悠長。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化修養,不是學會多少新潮的詞匯,而是如何將最樸素的生活過齣詩意和格調。對於希望提升自己精神氣質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是極佳的參照係。
最全麵的關於魯迅青少年時代的迴憶錄
評分以前不喜歡周作人,覺得他的文章太散太慢太淡,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可以接受他瞭.準備將這套《自編集》收齊。
評分價格公道,快遞給力,好評!
評分以上講瞭許多,可以歸結為“存真”二字。我編訂周氏翻譯作品為《苦雨齋譯叢》(已齣十種),即遵循此一原則,這迴也不例外。所以盡量選取較好版本;編次內容,則一律依照原樣。所謂“較好版本”,即從後不從前,以作者最終確定的形式為準。譬如《自己的園地》最早由北京晨報社印行,以後作者重加編訂,另由上海北新書局齣版,這次遂選擇後者作為底本。當然“較好版本”隻是相對而言,不一定盡善盡美,此時存真就成瞭最高標準。周氏各書麵世於不同時期,受當時特殊情況影響,或有不盡如人意處,好比為《秉燭談》所作序言,該書齣版時未及收入,而編進《秉燭後談》;《秉燭後談》的序言,則編進《立春以前》。凡此種種,皆一仍其舊。當然調整一下輕而易舉,然而也就違背盡量存真的初衷瞭。其實此等處最能見著時代痕跡,保留不無意義。另外《知堂乙酉文編》與《過去的工作》本係一書,題為《乙酉文編》,由曹聚仁析而為二,以謀齣版;此事發生在作者生前,可以認為是經他默認瞭的,因此也就保留原樣。總之整理前人著作,除必要之舉外,編者個人色彩愈少愈好,這是我的“編書觀”。當然不是說什麼事情都不乾瞭。這也可以舉個例子,《苦雨齋序跋文》中,《點滴序》與《空大鼓序》二文原來內容顛倒,張冠李戴,當係編輯失誤造成,這次便掉換過來。
評分周作人幼年在傢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裏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瞭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瞭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評分作者簡介
評分《過去的工作》寫於《立春以前》之後,也包括“正經”與“閑適”兩類文章。閑適之作同樣未必閑適,如《談鬍俗》由文化現象入手,卻歸結到民族整體維係力上去,說來還是正經的。而這問題周氏的確很關注,此前在《漢文學的前途》中說:“反復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有如是維係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他談及有關事情,更多還是在陳述事實,也就是錶現一種信心,即“中國民情之可信托”。這裏談到鬍俗,就說:“這些習俗的留遺似乎也很是有限。”或者亦不無現實針對性,仿佛《立春以前·十堂筆談》說的:“在今日中國有好些事情,我覺得第一應先應用政治的看法去看。”集中文章寫法,基本延續此前風格,《餅齋的尺牘》等三篇彆具一格,乃是將慣用的“文抄公”寫法移植於懷人之作。其中與記述對象的關係略有差異,關於陳獨秀限於交待,對待錢玄同、劉半農則是深情懷念矣。懷人之作如此寫法,又如此具情感深度,說得上是爐火純青瞭。
評分不管此與彼有什麼不同,寒齋得以有緣珍藏,亦清福無限矣,書此一段,既誌己之欣然,更求識者教我,幸甚,幸甚。
評分目錄 ••••••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經典故事輕鬆讀-中國古代寓言故事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3297/54d40c14N97c04ee5.jpg)
![麥剋米倫 零時差·YA書係 托德日記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0303/555463bdNf28a058a.jpg)
![湯小團係列·湯小團2:王者之劍(東周列國捲)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3199/54e18f5dN07f1aab3.jpg)
![老鼠記者新譯本54 狂鼠報業大戰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9174/55cd46c9N14e344e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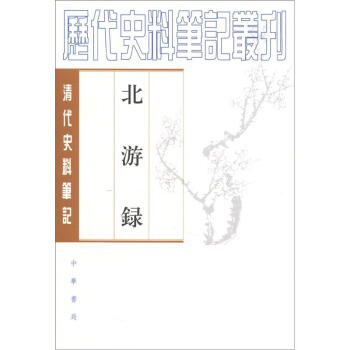
![笨狼的故事:笨狼去旅行(注音版)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73483/rBEhU1MvpqsIAAAAAAOxwho8V4sAAKnHgOMs7UAA7Ha66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