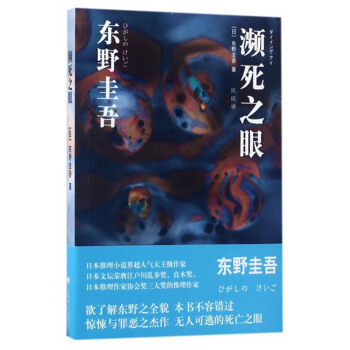![爱 [Lov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82792/rBEGD0-p8I4IAAAAAAAkwWZtC5MAAA5jgCwS2EAACTZ949.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出生于英国伊斯特本(Eastbourne),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书写风格混杂魔幻写实、歌特式以及女性主义。卡特著有八部小说:《魔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奖)、《数种知觉》(获萨默塞特·毛姆奖)、《英雄与恶徒》、《爱》、《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以及《明智的孩子》。《爱》为其中一册。
内容简介
就算在吸血鬼风靡,大爱哥特的今天,《爱》也不可能成为一本畅销书。有一天,你足够幸运,足够不幸,在书店最不起眼的角落发现它。阅读它,就是没办法畅快呼吸,像在观赏一个骨瘦嶙峋的女人跳艳舞,用艳俗的施虐受虐的形式拆解并颠覆爱。明明是不起眼的卑鄙人间,背景幕布却是睡莲间垂死的奥菲利娅。21世纪已过去了10年,这个性与暴力的怪诞年代,在《爱》面前,不过是一张白腊腊的廉价纸,淡得没分量。作者简介
安吉拉·卡特出生于英国伊斯特本(Eastboume),是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书写风格混杂魔幻写实、歌德式以及女性主义。卡特著有八部小说:《魇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奖)、《数种知觉》(获毛姆奖)、《英雄与恶徒》、《爱》、《霍夫曼博士的地狱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马戏团之夜》,以及《明智的孩子》。三本短篇小说集《染血之室》、《烟火:九个世俗故事》,以及《圣人与陌生人》。卡特的作品也深受媒体喜爱:短篇小说《与狼为伴》和《魔幻玩具铺》曾拍成电影,《马戏团之夜》和《明智的孩子》改编成舞台剧于伦敦上演,2006年更被喻为是安吉拉·卡特之年,在英伦掀起一阵卡特热潮。目录
一座充满背叛,疏远,离失的迷宫。“一段极度风格化的故事,有关发生于波希米亚外省的一场致命三角恋……小说和它的后记构成了一项迷人的研究,一个过去审美的客体,拆解成现实主义与承诺。”
——洛娜·塞奇(Lorna Sage),《卫报》
“卡特带着一种冷酷的超然,研究自己的主人公,仿佛他们是一页玻璃片上的标本……她敏锐地捕捉到“摇摆伦敦”风潮衰败之后,他们这爱的一代临死前的痛苦挣扎。”
——肖恩·弗伦奇(Sean French),《新社会》
“安吉拉·卡特的语言在指尖。”
——《新政治家》
“不论主题是什么,安吉拉·卡特像梦一样般写作——有时是噩梦。”
——《周日电讯》
精彩书摘
一天,安娜贝尔在天空中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月亮。这景象让她魂飞魄散。恐惧耗尽了她,直到那一晚以灾难结束时才放手。面临含混,她毫无自卫的本能。那时她正穿过公园往家走。她用通感解释身边的世界。在此体系中,这公园尤为重要,她爱在灰黄的冬日之光下,沿杂草丛生的小路走,略带紧张的快感。这时节,树秃了,日落时,冷火环绕树枝。某位十八世纪的园艺师将公园种植在一座宅邸周围。宅邸早已被拆毁,一度和谐的人造荒野,如今被时间随机地打乱,绿色缠结洒满小山的高肩。离穿越城市港区的繁忙公路仅一箭之遥。前宅邸仅有的残骸是几件建筑上的辅料,如今已归城市博物馆所有。有一座马房造在那微型帕台农神庙①的边缘,仿佛只为慧驷②而建;那些柱状的门廊,在满月的光线下尤其有效,任谁也踏不进。它不过是一件纯粹的设计品,小山南侧绿色构图中的一个焦点。安娜贝尔很少走那儿,宁静使她厌烦,公园这部分地中海似的样貌提不起她的兴趣。她更喜欢哥特式的北侧,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塔楼,大格的尖顶拱窗潜伏在树丛中。怕文物破坏者掠夺,这两座异想天开的可爱建筑都被安全地锁好。它们的存在仍扮演最初的角色——公园变成一座预谋好的剧场,在典雅和谐又晦涩古怪的环境中,罗曼蒂克的想象可上演任意一出表演。公园稀有的寂静放大了它的奇异古怪。足球轻落于长草问,零星的鸟儿在啼唱。在这散漫骚动的城市中,无论怎样捂住噪音,都给这鬼祟无风的安静,添了一分不自然。
公园单单保留了一个人口,叫人过目不忘。一对大而重的锻铁门,装饰着小天使,兽面,风格化了的爬虫,和镀金剥落的矛头。两扇门从不打开或关闭,总微微半开,随着年龄的增长从门枢上缓慢下沉;它们已失去作用,公园周围的所有栏杆早已不知去向,从任何一处进入都简单无偿。处在这样的高地之上,公园仿佛悬在空气中,下面是一块辽阔而多雾的城市模型,那些穿越它的人总感觉过多地暴露于天气。有时,一切看上去不过是一块为风准备的操场,另一些时候,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沟,为天空能倒下的所有雨水。
安娜贝尔穿越公园是在多风且气候骇人的季节,一个冬日傍晚。她恰好抬头看了天空。
右侧,太阳照耀着一排月牙形房屋,正是她住的那块区域,同时,在她左侧,在城市的摩天大楼和教堂尖顶之上,渐渐升起的月亮,静挂在一牙儿纯夜的裂口中。尽管一个在降落另一个在升起,太阳和月亮发出同样的光辉,天空同一时刻容纳了两种极端。安娜贝尔向上惊骇地凝望,目睹这对常态的可怕反叛。她找不出一则神话替自己解围,突然感觉是整个宇宙无助的中心点,仿佛太阳,月亮,星星和空中所有的天体都绕着她——这无意志力的轴心,旋转。
就这样,穿过长草冲出小路,找寻遮掩以躲避天空。她身不由己,蹒跚地呈之字形前进,移动飘忽不定,分明任由狂风怒号随意摆布;她光怪陆离,被逐渐逼近的尘土模糊,不过是那地方、那时节的散发物而已。
小山顶上,她狂躁地挥动双手,用投降的姿态,将自己向小路的一侧倾倒,掩埋在一丛金雀花下,躺着呻吟喘息了一会儿。风将她的发缕缠上金雀花尖,该和预想的那样,纹丝不动才好,直到那可怕含混的时刻,完全溶解在夜晚中。她逗留着,一个疯女孩,沉醉在恐惧中,倚着一丛荆棘林颤抖,痛不欲生,每当挨紧她年轻丈夫白皙的肉体,这痛苦也会袭来。睡在她身边,却不知她的梦魇,尽管他是个美丽的男孩,人见人爱。
……
前言/序言
《冰风暴》的原著作者里克·穆迪,曾经是卡特的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实验写作的大本营布朗大学,你还能遇见实验写作的大师,安吉拉·卡特,罗伯特·库佛,写《第二层皮》的约翰·霍克斯。20岁时遭遇卡特,对于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简直是脱离平庸的最好途径。课堂上有人刁难她:“你的作品什么样?”“我的作品像冰刀一样切过男人阴茎根部。”
她1940年生于英国的港口城市伊斯特本,毕业于布里斯托尔大学,写小说,写诗,也写散文。《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一句话将她的作品总结:“充满了毛骨悚然、巧妙的超现实之感,大量利用象征主义,及来源于传统童话故事和民间神话的主题。”60年代卡特在英国崭露头角,67年凭借《魔幻玩具铺》获约翰·勒维林·里斯纪念奖,夸张虚饰的文风,让她从此和魔幻现实主义分不开。此后的小说有一种“更独特的新哥特式风格,通常用一种强烈,并非侵入式的女权主义情感支持”。71年的中篇《爱》,“相对墨守成规”。77年《新夏娃的激情》,拿女权主义问题大做文章。79年,她对传统材料重新改编,把玩情色,重写了童话《血窟》。91年,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明智的孩子》,讨论两个戏剧家庭的编年史。92年,51岁的卡特死于肺癌。
69年,卡特移居日本,在随后的两年里写了《爱》。首次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描述人间,所以显得“相对墨守成规”。卡特在后记中提到:“风格上华丽的拘泥,与我一开始从哪儿得来《爱》的想法有一点关系,那是本杰明·贡斯当十九世纪早期的情感小说《阿道尔夫》。写一个现代通俗《阿道尔夫》的想法让我着了迷,尽管在我从英国乡间生活中多次提取精华,用以软化整个故事之后,大概没人能找到两者的相似之处。”阿道尔夫爱上埃莉诺,像渥伦斯基爱上卡列尼娜,撩拨她爱的火焰,再整个地熄灭。小说大段地告白,为何爱为何又不爱,鱼死网破要得到,再嫌弃,踏在脚下用力碾,带着非人世间的清醒,“要想唤醒那垂死的感情,仅仅凭着一种出于责任感的决心,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这一句话似乎就促成了卡特软化后的《爱》。给予浪子现实的责任心,又有什么用?
《阿道尔夫》不过是贡斯当闲谈时想说的一个故事:“当时把它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两三位和我一起待在乡下的朋友信服,在情境不变的情况下,把一部小说的主角压缩到两人,同样可以写出一些味道来。”六万字的《爱》同样集中于三个主人公,性格迥异的弟兄俩,外加一个疯了的女孩。只是再不走情感小说畅销罗曼史的套路。它更像三个非人的故事,像爱伦·坡,或者霍夫曼,华丽丽地乱伦渎神。直觉在卡特小说中彻底失灵,没人跟得上她变幻的愤怒节奏。没有人快乐,因为她批判,明显分得清对错。她过分用力地描写一个人知道错误,却又挑衅地将错误一针管一针管注入血脉。
就算在吸血鬼风靡,大爱哥特的今天,《爱》也不可能成为一本畅销书。有一天,你足够幸运,足够不幸,在书店最不起眼的角落发现它。阅读它,就是没办法畅快呼吸,像在观赏一个骨瘦嶙峋的女人跳艳舞,用艳俗的施虐受虐的形式拆解并颠覆爱。明明是不起眼的卑鄙人间,背景幕布却是睡莲间垂死的奥菲利娅。21世纪已过去了10年,这个性与暴力的怪诞年代,在《爱》面前,不过是一张白腊腊的廉价纸,淡得没分量。
用户评价
这本厚重的小说,初翻开时便被它那股扑面而来的历史的尘烟所笼罩。作者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肌理,人物的生存状态,描摹得极其细致入微,仿佛我不是在阅读文字,而是亲身走进了那些狭窄的、弥漫着煤烟味的街道巷陌。每一个角色,无论主仆,都有着其深刻的时代烙印,他们的挣扎、妥协与微小的反抗,都让人感同身受。特别是对那些底层人物命运的刻画,那种深入骨髓的无奈和在绝境中依然闪烁的人性光辉,着实令人动容。叙事节奏的处理非常老辣,时而如缓流的江水,娓娓道来,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剖析得淋漓尽致;时而又陡然加速,如同疾风骤雨,将重大的历史转折和命运的突变毫无预警地砸到读者面前,让人喘不过气。这本书的结构宏大,线索繁复,却又井然有序,展现了作者驾驭复杂叙事的能力。它不像是一本单纯的故事书,更像是一部用文学笔法写就的社会编年史,读完之后,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敬畏感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复。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对“权力运作”机制的冷峻解剖。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没有波澜壮阔的爱情故事,而是将焦点集中在一个封闭、高压的组织内部,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层级间的微妙张力、信息如何被过滤和扭曲,以及个人如何在体制的巨大惯性面前逐渐被异化。作者对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则有着惊人的洞察力,那些看似荒谬的规定、潜规则的博弈、以及人与人之间基于利益的结盟与背叛,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看得不寒而栗。叙述视角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冷静观察者视角,笔触克制而疏离,几乎不带感情色彩地陈述事实,反而让这些事实的残酷性更加凸显。通篇读下来,你会深刻体会到,在某些结构下,个体意志是何其的微不足道。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去戏剧化”处理,它让你思考的不是角色命运的悲欢,而是结构本身的必然性与压迫性。
评分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场对“记忆碎片”的精妙拼贴艺术。作者的语言风格极其跳跃且富有现代感,句子结构常常是破碎的、充满内省式的独白和突兀的意象跳跃。它不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逻辑,而是通过一系列意象、梦境片段和看似毫不相关的场景切换,构建起一个迷离而又极其私密的内心世界。阅读体验是充满挑战性的,你必须主动去填补那些留白的意义,去跟随作者那种近乎意识流的思维脉络。这种写作手法极大地解放了叙事的束缚,使得情感的表达不再需要冗长的解释,而是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象征意义直接抵达读者的潜意识。我尤其欣赏其中几处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它们并非简单的背景烘托,而是直接充当了人物复杂心境的隐喻,那些晦暗的色调和潮湿的空气,都渗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疏离感。这本书更像是一面棱镜,将日常琐碎折射出令人不安的哲学反思。
评分读完这部作品,我脑海中浮现的不是情节的高潮迭起,而是那些弥漫在空气中难以言喻的“氛围感”。作者似乎更关注情绪的共振而非事件的驱动。全书弥漫着一种精致的、近乎病态的美感,语言运用华丽而考究,大量的比喻和通感手法将各种感官体验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迷幻而又忧郁的基调。角色的对话往往是含蓄的,隐藏着巨大的张力,很多关键信息需要通过角色的肢体语言、眼神的细微变化,乃至他们沉默的间隙来捕捉。这种阅读体验就像是在鉴赏一件极其精美的、但表面布满裂痕的瓷器,你必须小心翼翼地去触摸,去感受那些隐藏在光洁表面下的脆弱和历史的沉淀。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或明确的结局,而是将主角那份永恒的追寻和若即若离的希望,如同一个未解的音符,悬挂在读者的心头,久久不散。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更像是一场艰苦的智力攀登,但一旦成功登顶,那视野的开阔感是无与伦比的。作者构建了一个极其复杂且自洽的“伪历史”世界,其中涉及了架空的地理、独特的语言体系,以及一套令人费解的历法和宗教信仰。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几乎都在搭建这个世界的基石,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梳理各种名词和概念之间的关联。但正是这份严谨的“世界构建”(Worldbuilding),赋予了故事非凡的真实感和厚度。它不像许多奇幻小说那样只是披着外衣,而是真正深入到社会结构和文化内核的深处去进行了再创造。那些充满古老韵味的对话,那些关于信仰冲突的辩论,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本功底和惊人的想象力。这本书不适合碎片化阅读,它要求你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去学习、去理解,它回馈给你的,是对“人类构建意义体系”这一行为的深刻洞察。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3.一天,安娜贝尔在天空中同时看见了太阳和月亮。
评分收到了就好,好书收到了
评分活动时买的,很赞
评分快快乐乐来来来啦啦啦快快乐乐啦
评分18.深海里的鱼发光识别彼此;男人和女人对与自己相似的人群,难道不能同样发出某种缄默的冷光?
评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吧少年!
评分爱~好书,值得一读!!!!
评分不过就是太薄了,贵了点。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首席女法医(02):肉体证据(2014版) [BODY OF EVIDEN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92361/53ab8371N6d8cd96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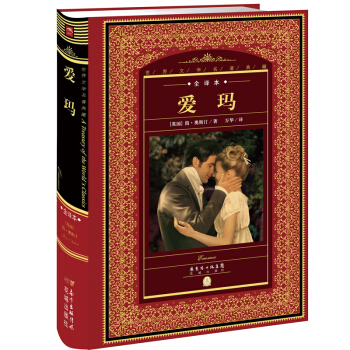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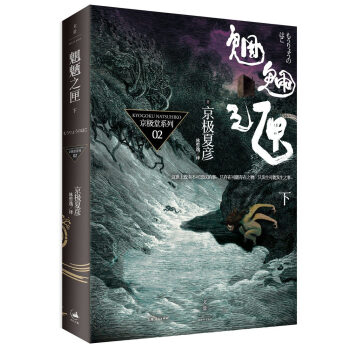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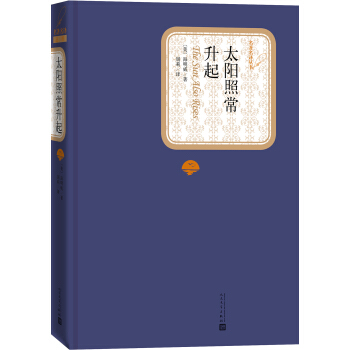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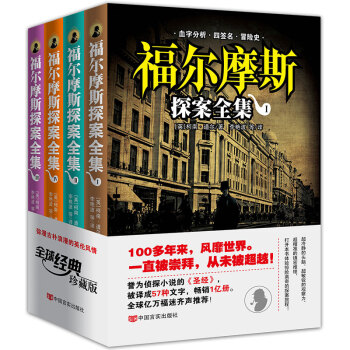
![图夫航行记 [Tuf?Voyag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19549/592fdeecN8f085bdb.jpg)
![泥河·萤川 [蛍川泥の河]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63014/9a2731a1-ac6d-4d8f-a484-2a80f1b6d71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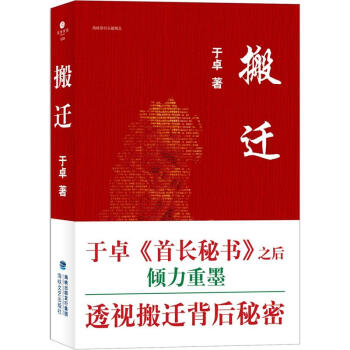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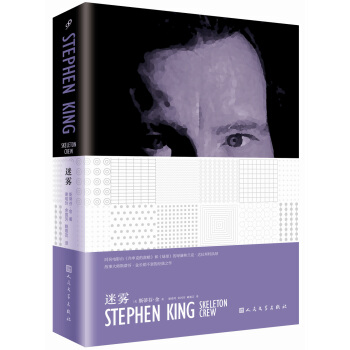


![数不清的井 [数えずの井戸]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17524/571daa85N84f3a99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