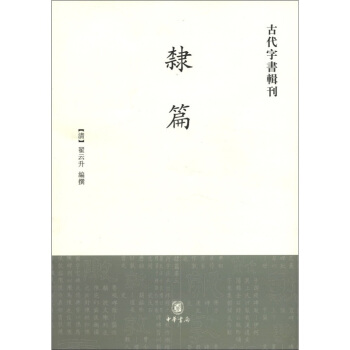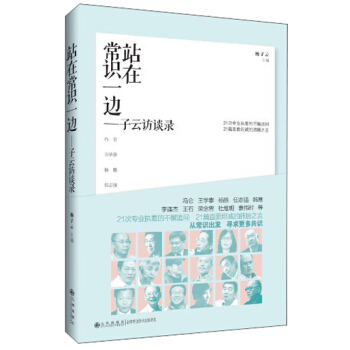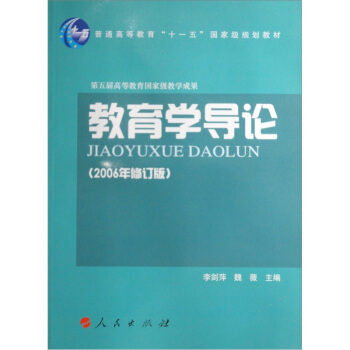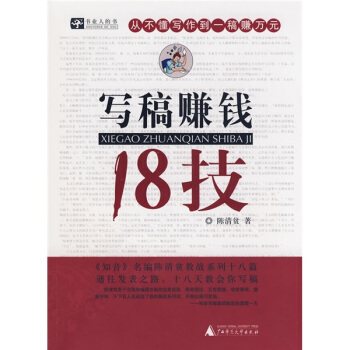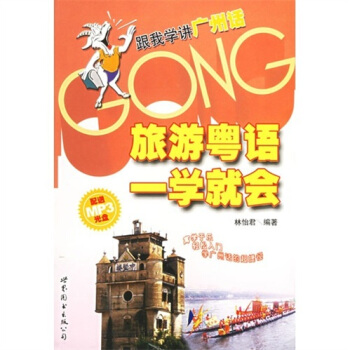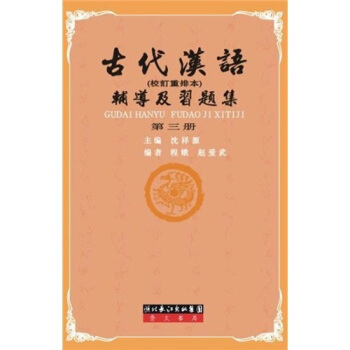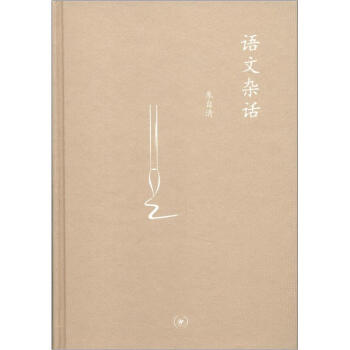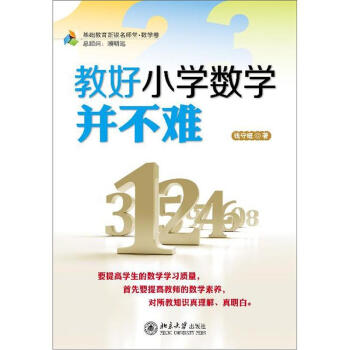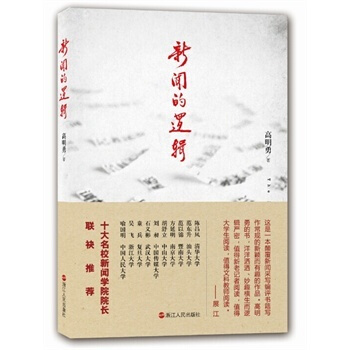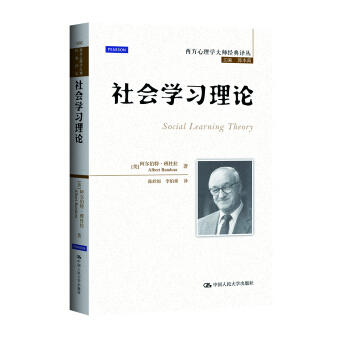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文化人类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目录
序第一篇 人类学总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人类学的定义及其对象
第三章 人类学的名称
第四章 人类学的分科
第五章 人类学的地位及其与别种科学的关系
第六章 人类学的目的
第二篇 文化人类学略史
第一章 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巴斯蒂安及拉策尔
第二章 社会演进论派
第三章 传播论派
第四章 批评派或历史派
第五章 文化压力说(以上各说的总评)
第三篇 原始物质文化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发明
第三章 原始物质文化之地理的分布
第四章 取火法
第五章 饮食
第六章 衣服
第七章 原始的住所
第八章 狩猎
第九章 畜牧
第十章 种植
第十一章 石器
第十二章 金属物
第十三章 陶器
第十四章 武器
第十五章 交通方法
第四篇 原始社会组织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结婚的形式
第三章 结婚的手续
第四章 结婚的范围
第五章 母系母权父系父权
第六章 家族氏族半部族部落
第七章 结社
第八章 阶级
第九章 妇女的地位
……
第五篇 原始宗教
第六篇 原始文艺
第七篇 原始语言文字
精彩书摘
第二种的来源是文化的“遗存物”(survivals)。有些风俗或制度现在已经没有何种作用,但它们的存在可以证明它们在以前也是有作用的,这便是所谓遗存物。主张乱婚说的人举出几种风俗说它们是以前乱婚时代的遗留物,由此可以证明乱婚制的存在。但反对派以为这些风俗却另有别种意义,不能即说是乱婚制的遗留物。这些风俗之中,其(1)是“兄弟妇婚”(levirate),依这俗,兄弟死后应娶其寡妻。据乱婚说的学者说,这便是乱婚的遗俗。反对者则以为这种风俗可以不必解释为遗存物,因为他是有现存的作用的。据魏斯特马克、泰勒(E.B.Tylor)、罗维(R.HLowie)等人说这风俗实是由于以结婚为家族与家族间的契约而死者的家庭应当负担其寡妻的生活。还有一种“妻姊妹婚”(sororate)也是因为是家族与家族的契约,故一个死了再续一个。(2)乱婚的又一种证据是“生殖器崇拜”(phallicworship)。反对派则说这种风俗其实并不行于最原始的民族中,而是行于文化较高的人民如希腊、罗马、印度等。在印度其发生且更迟。崇拜这种生殖的能力即生命的象征,并没有什么难解的意义。这种风俗实和农业有关,因为希望农产物的丰收常有行使魔术的仪式的,而这种风俗也确曾见于许多民族的春节。(3)还有古时巴比伦、希腊、迦太基、意大利等处所行的“神圣卖淫”(sacred
prostitution),反对派也解释为宗教上的淫乱仪式,不过是特别发展的崇拜生殖的风俗。(4)还有所谓“秽恶的结婚仪式”,如“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等。据巴霍芬(Bachofen)和拉伯克(Lubbock)都说这是“个人结婚的赎罪”(expiation For individual marriage)。他们说妇女由公有而转入个人之手时便是犯了团体的权利,故须先向大众赎罪,赎罪的手续便是使新妇先侍寝于酋长、僧侣等领袖以及新郎的朋友,这便谓之初夜权。还有欧洲中古时“封君的权利”(Droit du Seigneur)也是相同的。反对派如魏斯特马克则说这种风俗或者是由于“处女血恐怖”,故希望由宗教人物或显要人物之交合而祛除不吉,即使是一种权利,也不过是个人的威权的结果,未必便是古代乱婚制的证据。(5)“群婚制”(见下文)在乱婚说派以为是乱婚变成,但反对派又以为此制反是一夫一妻制的变体,即起于一对夫妇而扩大其性的关系,不像是缩小范围的乱婚制。(6)还有亲族等级制度(classificatory system of relationship)也是乱婚证据。最著名的是夏威夷的风俗,凡属同辈行的亲族便当作一个等级,除年龄及性别外只用一个名称。例如“父亲”一个名称除用于本父以外,凡父的兄弟以及母亲的兄弟都呼以此名。又如“母亲”除用于母亲以外又用于母的姊妹以及父的姊妹。“兄弟”“姊妹”用于兄弟姊妹以及父之兄弟姊妹的子女及母的兄弟姊妹的子女。这种风俗据摩尔根说可以证明以前在同辈行中都有性的关系。一个人的伯叔父、舅父也称为“父亲”是因为他们可以和他们的母亲及姊妹有性的关系,而一个人的所有甥侄也便是他的子女,因为他和他的姊妹、从姊妹、表姊妹都可以有性的关系,他们都是他以及其他“兄弟”的妻。反对派以为这样以亲族名词为源于性的关系的说法,很有难处;因为照此说“父亲”的意义为“生殖者”或“或然的生殖者”,但母亲便不能依此说法了,因为她们只生自己的子女,至于其他的子女却显然不是她所产生的。由此可见,以此为乱婚的证据实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制度不过是根于血缘的亲族关系,并不是根于性的关系。
……
用户评价
说实话,一开始我拿到手的时候,有点担心这书会不会过于学术化到脱离现实。毕竟,现代学术著作往往陷于理论的泥淖,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但是,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成功地在宏大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的“人”的经验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比如,书中对某种传统技艺传承过程的描述,简直就像一幅高清的纪录片在眼前播放。那种对手艺人手指的动作、眼神的专注、以及在特定仪式下工具的使用,都有着极其细腻的捕捉。我甚至能想象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材料的气味和汗水的气息。这种基于扎实田野工作的描写,让抽象的文化概念变得鲜活可触。我意识到,文化不是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而是活生生的、在日常琐碎中不断被再生产和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人类学家真正做的工作,不是去“发现”异域文化,而是去“看见”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意义网络。它教导我们如何以一种更谦卑、更细致的目光,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域”。
评分我对人类学一直抱持着一种好奇又敬畏的态度,总觉得那是通往理解“他者”的钥匙。这本书,确实是提供了一把精巧的钥匙。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跨文化比较时的那种克制与审慎。他没有急于下结论,更没有采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审判者”视角,而是真正沉浸到被研究对象的语境之中,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自洽性。记得有一章专门讲了某个群体关于“时间”的感知,这简直颠覆了我固有的线性时间观。在我们习惯于“分秒必争”的现代社会,去理解那种循环往复、与自然节律紧密结合的时间观念,是一种极大的智力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作者的笔触冷静而富有洞察力,他像一个高明的翻译家,将一种完全陌生的思维模式,精准地转译给了我们这些“局外人”。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合上书本,消化一下刚才读到的观念。它不像小说那样让你一口气读完,它更像是一场需要反复咀嚼的盛宴,每翻过一页,都有新的味道在舌尖和心头弥散开来。
评分这本书的编排结构也值得称赞。它显然经过了精心布局,不是简单地将田野笔记堆砌在一起。每一章节之间的逻辑推进,都像是精心设计的乐章,层层递进,由表及里。初读时,你会发现它似乎在描绘各种各样奇特的习俗,带有一种探索新大陆的兴奋感;但读到中段,你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习俗之间隐藏着惊人的关联性和系统性。作者非常擅长设置“对照点”,他总能巧妙地将一个看似孤立的现象,置入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或历史背景中去审视,从而揭示出普遍的人类境况。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禁忌”的讨论,它不仅仅是关于“不能做什么”,更是关于“必须维护什么”的社会秩序。这种深度挖掘,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一种“解谜”的乐趣。它要求读者不能满足于表面的信息,而必须深入思考每一个文化表象背后所负载的生存智慧和集体记忆。读完这一部分,我感觉自己的思维被拉伸和重塑了一遍,对“秩序”的理解不再是单向度的法律条文,而是多维度力量博弈的结果。
评分坦白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作者的叙事风格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他似乎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引入一个意想不到的细节,瞬间打破你对某个文化的刻板印象。例如,在描述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时,他没有聚焦于权力斗争,而是花了大量篇幅去描写最底层的劳动者如何通过微妙的非言语交流来表达不满或进行联合,这才是真正体现出文化生命力的所在。这种关注“边缘声音”和“微观实践”的处理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阅读体验。这本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它培养了一种“多重透视”的能力——即在理解一个文化时,不能只用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尺去衡量,而是要切换到他们自己的“文化眼镜”去看世界。这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文化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它让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种合理且自洽的生存之道,而我们的“常识”,仅仅是其中一种偶然的显现。
评分这本大部头,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历史厚度。我特地挑了个安静的周末,泡了壶浓茶,打算一头扎进去。拿到书的那一刻,我就被它那古朴又严谨的装帧设计吸引住了。封皮的材质摸上去很有质感,配色也极其考究,透露出一种对知识的敬畏感。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毕竟“丛书”的名头摆在那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堆砌着专业术语、令人望而生畏的文本。然而,翻开第一页,作者的行文方式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将那些看似冷冰冰的理论框架,用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读着读着,我仿佛走进了那些遥远的村落,亲眼见证了那些仪式、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那种代入感,不是简单的“了解”,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共情”。尤其是在讨论某个特定族群的亲属关系结构时,作者没有止步于枯燥的图表,而是通过详尽的田野记录,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联结,让人不禁反思我们现代社会中,那些被简化和异化的“连接”。这本书记载的那些细微之处,是构成人类文明肌理的基石,读完后,我对“文化”这两个字的理解,都被重塑了。
评分诸种原因之中,加缪更倾向于最后一种,而在这最后一种中,他的兴趣又专注于西绪福斯的重返人间之后。加缪告诉人们,使西绪福斯留恋人间的,是水,是阳光,是海湾的曲线,是明亮的大海和大地。他之受到神的惩罚,是因为他不肯放弃人间的生活,而人间的生活虽然有黑暗的地狱作为终点,但其旅程究竟还是可以充满欢乐的。
评分印刷和装帧都很不错。
评分非常棒的书
评分这套书的内容很好,装帧也不错,推荐大家购买哒。嘿嘿嘿。
评分经典版本,无需赘言。评价纯为积分而来,嘿嘿。
评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这专业名称的开始,是在1901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大学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当时,它仅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以美国特有的”历史-相对文化学“为代表,《菊与刀》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评分这套书的内容很好,装帧也不错,推荐大家购买哒。嘿嘿嘿。
评分很不错的一本书啊。发人深思。
评分物流很快,价钱偏贵,但质量好~好书,想看很久了,趁活动入手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