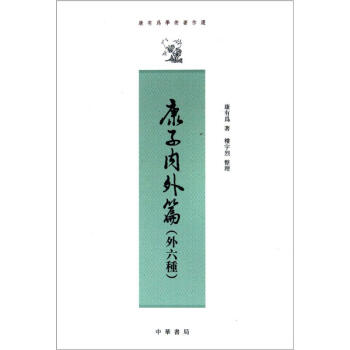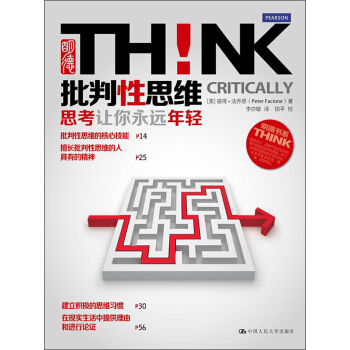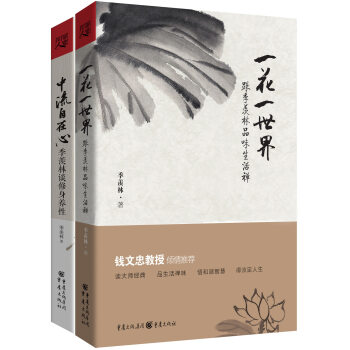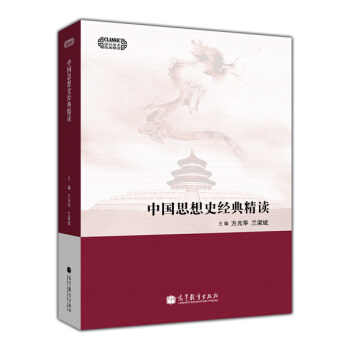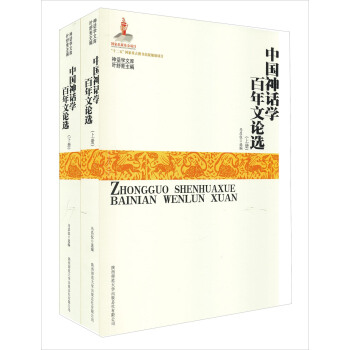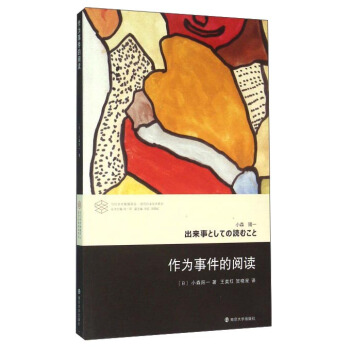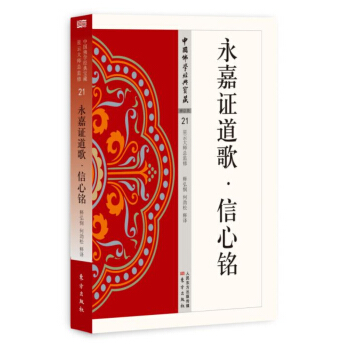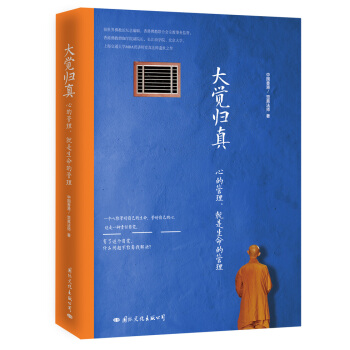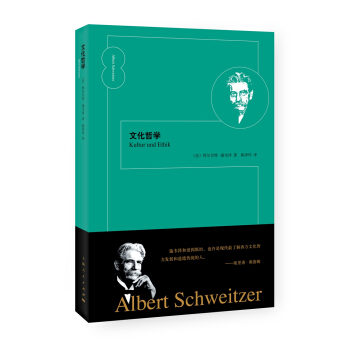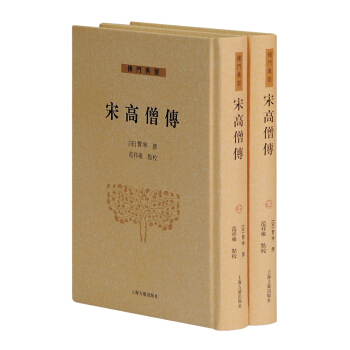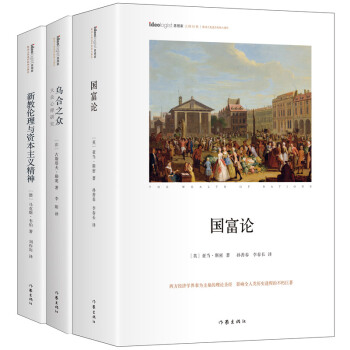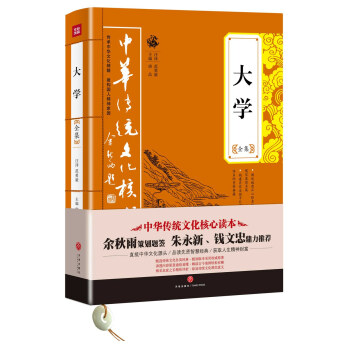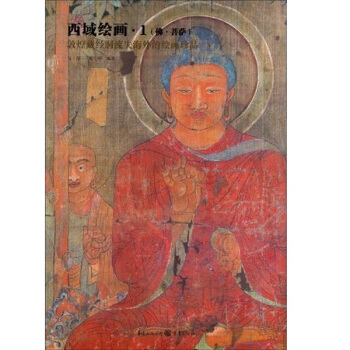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佛与菩萨两部分。佛画中《树下说法图》是敦煌藏经洞中创作年代最早、保存状态最完好的一件作品。其中不论主尊、胁侍菩萨,还是女供养人的勾勒和敷色都十分细腻,特别是六位比丘弟子的表情刻画得极为生动,是敦煌遗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关于《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同样的题材出现在干佛洞Ch.VⅢ洞窟甬道南壁的壁画上,尺幅和场面更为宏大。读者不妨将两者做一对比,定然会对因不同材质而限定的绘制技法有所理解。《释迦瑞相图》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虽为断片,但细密劲健的勾线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当年“曹衣出水”的风采。书中《阿弥陀·八大菩萨图》、《干手干眼观世音菩萨图》均属于曼荼罗类型的作品,即依照一定的佛典仪轨而绘制,供修行者借相悟体、修持密法之用。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宝树华盖之下,释迦牟尼佛身着朱红色的和软袈裟,跏趺坐于宝莲台,正在向四围的众菩萨、比丘说法。莲座呈多层装饰之须弥座,和上方的华盖相应。四尊菩萨端坐莲台,姿态相各异,手中分别持莲花、净瓶、宝珠等,神情皆安详雍容。六弟子侍立佛后,闻听妙法而心生欢喜,颜色和悦疏朗。画面上方,天女乘祥云俯身散花,飘带共云气随风舒卷。下方各有男女供养人,右侧男供养人已缺损。女供养人为一少女形象,椎式发髻,窄袖衫裙,双手持莲,长跪于方形垫上,态度温婉闲静。下方正中留有题写发愿文的位置,作石碑形,空白未题记。该作品的创作年代约为8世纪初,是敦煌藏经洞中绢画年代较早的一件。从以下几方面可以进行时代的印证。首先,相同的说法题材,其构图与敦煌唐初洞窟的表现最为类似;而且,这一图式正是从隋代石窟壁画中表现佛与二胁侍菩萨的简单图像中演化而来。其次,主尊嘴角的线描式样,与永泰公主墓室壁画非常相近。因为到了8世纪后半叶,一般上下唇之间的勾线,两端要稍粗一些;再到10世纪,线条则拉得更长,末端弯曲得很尖。再次,画中女供养人的发型、着装,甚至是表情,完全与唐初壁画、陶俑中的侍女形象相一致。最后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该作品的创造年代,即华盖、莲座上灵芝状的祥云,也正是唐初敦煌壁画常见的图样。
值得一提的是,该作在表现人物肌肤的立体感上尤为独到。除了线描本身的刻画,自北朝以来从西域所传的晕染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晕染法通常沿轮廓线向内染,边沿部分颜色较深,高光部分颜色浅。在鼻梁、眉棱、脸颊等部位往往先施白色,再以肉色相晕染。从而造就了肌肤的微妙变化。观作品正中的释迦牟尼佛,眼神透出无限悲悯,这跟细腻的晕染技法是分不开的。
敦煌遗画中,许多作品皆以对称工致的布局示现。该幅作品即是一例,如胁侍菩萨、六比丘弟子的安排无不是围绕主尊分左右而设,异常的严整对称。有些读者难免产生这样的误会:缺乏变化的布局将限制画工的自由发挥。这里何以称作误会,大致缘于读者忽略了两点重要的信息:其一,佛画的构图往往需要严格遵循相关佛典中所记载的仪轨,不可能像后来文人画家那般随意发挥。其二,高明的画工善于凭借细微处的精妙变化,来化解严整布局所带来的局限。前者此处就不详述了,就后者而言,不妨做几处提示。如画面下方左右二胁侍菩萨,侧面的角度、表情、身姿、手姿都有明显的差异;上方有二比丘均被菩提树遮挡,但眼神各异。再如画中的女供养人,上方是菩萨乘坐的莲花宝座,从莲茎斜出一花蕾,恰好衬出她乌黑的头发、娇嫩的脸庞。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最后,我想谈谈“佛·菩萨”在世俗生活中的投射。西域的佛教艺术,其魅力不仅仅在于描绘神性,更在于它如何将这些神祇拉入人间。例如,那些供养人的形象,他们的服饰、发型、社会身份,都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古时期西域社会风貌的珍贵窗口。我希望这本书能有一部分篇幅,专门讨论这些“陪衬”人物的艺术价值。他们是宗教热忱的体现,也是当时时尚和审美的缩影。此外,如果书中能够对不同地域的寺院建筑与绘画的结合进行分析,探讨洞窟的布局如何引导信徒的朝拜路线和视觉焦点,那会让读者对整体的“宗教空间”有更立体的理解。总而言之,对于这样一本题材宏大的画册,我期待它能既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又不失对艺术之美的细腻捕捉,带领读者穿透历史的尘埃,直抵那片神秘而辉煌的艺术疆域。
评分我非常好奇这本书对于“西域”这一概念的界定。它是否仅仅局限于新疆的克孜尔、高昌等地?还是将广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如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艺术、中亚的粟特遗址、甚至帕米尔高原的零散发现都囊括进来?一个优秀的艺术史著作,应当展现出清晰的地域性脉络和跨文化交流的证据。如果这本书的编排能像是一条流动的丝绸之路,从西向东,或者反之,展示不同艺术中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模仿,那将是一次极佳的视觉旅行。例如,早期受犍陀罗风格影响的佛像,其衣纹处理和立体感与后期的敦煌风格有何本质区别?这种对比,不仅是美学的差异,更是宗教传播路径和地方化适应的结果。我期待这本书能用扎实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背景,为这些精美的图像提供坚实的支撑,而不是让它们沦为孤立的、仅仅是“好看”的装饰品。如果能有详细的考古发掘信息和年代测定,那就更好了。
评分提到“佛·菩萨”,这无疑是佛教艺术的核心主题。但仅仅描绘这些神圣形象,未免有些单薄。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本书能深入挖掘这些图像背后的“叙事性”和“仪式感”。比如,一幅描绘“说法图”的壁画,它不仅仅是佛陀的肖像,更是对教义传播场景的记录。书中的文字如果能结合当时的佛教宗派流传情况,解释为什么某一特定菩萨(比如观音、弥勒)在某个时期特别受重视,其形象特征又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信仰需求,那阅读的价值就会大大提升。另外,西域绘画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是矿物颜料的细腻晕染,还是泥塑与彩绘的结合?书中是否能探讨颜料的来源和保存难度,例如,一些矿物色料的稀有性是否也反过来影响了画作的地位?如果能附带一些侧重于艺术技法分析的章节,比如线条的运用——是流畅的“吴带当风”,还是坚实的勾勒——这将极大地拓宽普通读者对绘画艺术本身的认知深度。我对于那些专注于描绘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细节特写非常感兴趣,那体现了古代匠人对“完美神性”的极致追求。
评分这本《西域绘画1(佛·菩萨)》的书名确实吸引人,但我手头没有这本书的实体或电子版,所以无法就其具体内容进行评论。不过,光凭书名,我倒是能联想到一些关于西域佛教艺术的方方面面,或许能从读者的期待角度谈谈。首先,西域,这个地理概念本身就充满了神秘色彩和历史厚重感。它连接着中原与犍陀罗、印度乃至更远的波斯、希腊文化。因此,对于一本聚焦于此地绘画的画册,我最期待看到的是其对不同文化元素交融的细致描摹。比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它从早期受犍陀罗风格影响的瘦长、浓眉深目,到盛唐时期雍容华贵的本土化转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部视觉史诗。我希望这本书能清晰地梳理出这种风格演变的时间脉络,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图片,而是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洞窟的佛像、菩萨像的造型、色彩运用,来阐释艺术如何响应宗教思想和世俗审美的变迁。例如,菩萨的面容如何从异域的冷峻变得日益慈悲圆润,衣饰的纹理如何从写实的褶皱变为程式化的飘带,这些细节的解读,才是真正让读者“读懂”画作的关键。如果书中能配有精良的拓印或高清晰度的照片,让那些失落的、斑驳的色彩依然能展现出昔日的辉煌,那将是极大的享受。
评分抛开学术性不谈,纯粹从视觉体验的角度来看,西域绘画的色彩往往是震撼人心的。它们经历了千年的风沙侵蚀,却依然能透出那种极度饱和的异域风情。一本画册的印刷质量至关重要。如果色彩还原度不高,那些标志性的朱红、石青、孔雀绿便会黯然失色,失去了原作的感染力。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印刷能够最大程度地捕捉到壁画上那种厚涂的质感和光影变化,让人仿佛能触摸到那粗粝的墙面。此外,排版设计也是衡量一本艺术图书水准的重要标准。图文的排布是否合理?是否留白得当?是倾向于大跨页、沉浸式的全景展示,还是侧重于对局部细节的特写放大?对于研究佛像面部表情、手印(Mudra)的变化,局部特写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这本书能做到图文并茂,且图片质量上乘,那么它就超越了一般的艺术普及读物,而成为一本值得收藏的参考资料。
评分很喜欢很好。。。。。。。。。。。
评分内容精典,印刷品质不错,看到我们的历史文物,感叹古人的智慧及大师的技艺
评分主要是印刷质量好,定价太高,3折多就不错。
评分此书印刷清晰,包装精美,书内有整体图还有局部细致图。适合喜欢佛教、信仰佛教、广大美术爱好者、创作者等收藏、观看、临摹。
评分很不错,印刷清楚,值得收藏和学习
评分之前在书市买过六本,这次补齐啦,就是“1” 的书角有些损坏
评分中国文化瑰宝,可以流传千古。
评分③我们的教师为了控制课堂,总担心秩序失控而严格纪律,导致紧张有余而轻松不足。轻松的氛围,使学生没有思想顾忌,没有思想负担,提问可以自由发言,讨论可以畅所欲言,回答不用担心受怕,辩论不用针锋相对。同学们的任何猜想、幻想、设想都受到尊重、都尽可能让他们自己做解释,在聆听中交流想法、
评分隋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伪经,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撰的佛经,《报父母恩重经》是根据《孝经》杜撰的。唐代洞窟里有此经变,中部为佛陀与圣众,四周描写十月怀胎、分娩成长、长大成人、忤逆、不孝等情节。这不是宣传佛教,而是宣扬儒家孝道思想。在许多净土变的深层境界中,多蕴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政治境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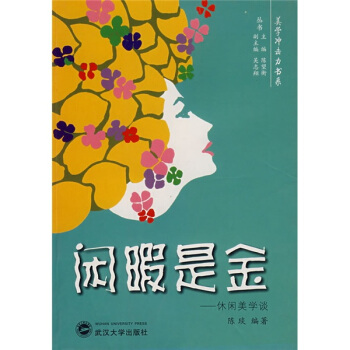
![柏拉图著作集2(英文本)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nalyses and Introductions by Benjamin Jowet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378239/30e71aae-07b7-4ae9-89cd-0c729ed47ae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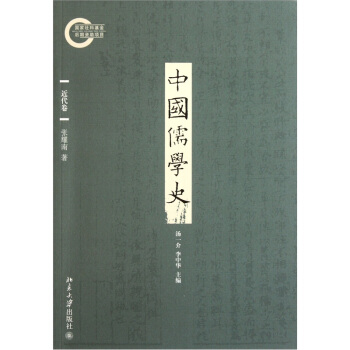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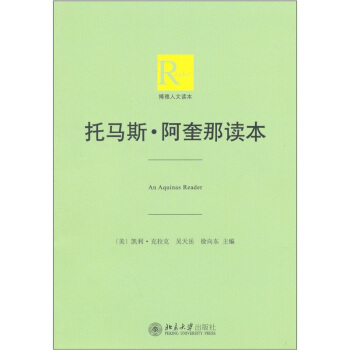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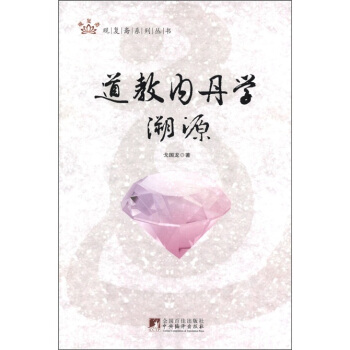
![中国史话·思想学术系列:道教史话 [A Brief History of Taoism in Chin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17052/rBEIDE_sBRsIAAAAAAAlwDAH9T0AADD_wDOlhQAACXY3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