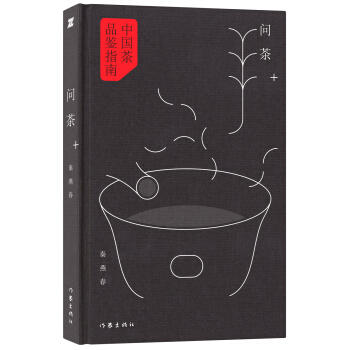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北大文学博士、学者秦燕春女士 匠心之作,时隔七年,修订完整版全新呈现;
★《问茶》整体设计由中国美图书设计师王志弘亲自操刀;
★四色彩印,近百幅中国名家绘画、书法、篆刻插图;
★美食家欧阳应霁隆重推荐,具人文色彩之中国茶品鉴指南;
★新版增加数万字,茶品与地理、历史、人文并重;
★首次将茶性与人性天地自然完美结合。
内容简介
自古以来,茶为素业,平常老百姓“吃茶去”,谈及的往往是其味蕾层面,却止步于此,不能道尽其妙。《问茶》一书,则将茶品和地理、人文、历史相结合,使我们在谈茶论茶时,超脱于五色五味,将茶性和人性、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作者以产区为路径,以品饮为指引,兼及地域文化与民风民俗的魅力与神韵,为读者一一讲述苏州碧螺春、西湖龙井、六安瓜片、安吉白茶、擂茶、乌龙茶、黑茶等各式茶的来历、特性、口感以及与茶相关的人文掌故、历史风烟……如此方式展现“茶性关乎天地人”的现代作者,秦燕春尚属首例。在她笔下,茶是有出身、有经历、有归宿的生命。
作者简介
秦燕春,女,初读医学,转攻文学,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中国文化》杂志责任编辑。发表有《晚清以来弹词研究的误区与盲点》、《鸳蝴文人的民间情结》、《以"史"救弊:大师的自励与启蒙》、《章太炎的晚明想像》、《青楼传奇:秦淮记忆的晚清命运》等论文10余篇,还有《献给唐文治的"尊敬与同情"》、《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茶到中年》等专业书评与文学评论约20篇。合作出版的学术专著有:《历史的重要》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章太炎卷);《近代散文史》(第七章《清末民初白话散文》)。翻译学术著作:B.A.Elman《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海外汉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精彩书评
秦燕春笔下的茶不仅文字充满美感,更重要的是,她把茶性和人性乃至天地自然结合在一起。在她的文章中,读者能清晰地看到“茶性关乎天地人”。
——《新商报》
秦老师开篇一句「茶行人世间,天地清沉沉」,就把我勾引进这接天引地的茶世界。一本《问茶》,是我这半月来研读得欢喜的好书。
……
把新近买来的《问茶》一书一直带在身边翻掀,几乎一口气看完一遍后一辑一辑倒看一遍做笔记,恐怕这回真的是激发起我的「茶心」,再不能像从前的有茶喝茶,喝完也就完事忘情。
——欧阳应霁
各种茶品与当地的人文“故事”、民风人情、地质人性囊括其中,风骚、雅趣并存,茶史、人性统一,视接万里,心极广袤,无所不包,无地不风流,无处不关情。
——刘文华
目录
导言 茶行人间世,天地清沉沉
一辑 江南茶色,罗裳一溪碧透
—江苏、浙江
二辑 黄梅调里好婵娟,中原天外天
—安徽,从信阳到湖北,瘦硬的江西
三辑 潇湘地,湖南人,霸蛮茶
四辑 “乌龙茶是男人茶”
—岭南闽外宗
五辑 不醉不大
—云、贵、川、桂
六辑 神秘“野生茶”
—北回归线上的照亮
七辑 “镜花水月”
—茶的伴侣,与水之爱
余韵 茶道日本与禅之精神
尾声 万物皆妩媚,问道小有春
后记 云忆台北茶
精彩书摘
一辑 江南茶色,罗裳一溪碧透——江苏、浙江
谈江浙茶,不仅无论如何都“不该”绕过碧螺春与龙井,且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碧螺春与龙井。
一
太湖东山岛,相传是倾国倾城的美女西施,和爱她爱到丢了江山社稷的吴王夫差炎夏避暑之地。生此岛上的碧螺春,涵养湖光山色,长于百果之间,桃李争芬,梅杏夺艳,果树茶树枝桠相联、根脉相通,果香茶香不分彼此、一体两面。碧螺春还有着凄艳传说赋予的另一个名字:吓煞人香。且后世文人更要敷衍说,那摘下新茶置于襟怀,捂出这“吓煞人香”的,一定须是清秀如茶的苏州的清白女儿,精气不关火焙足:“娥眉十五来摘时,一抹酥胸蒸绿云。”(梁同书)
此茶如闺女?
然而民间传说版的“女儿茶”来历,可是比这文人轻薄煽情来得伤感悲情,见得血泪淋浪:名唤“碧螺”的水边的姑娘为了救治她深爱的男子的生命,找到堪为灵药的佳茗,为早日成药施救,她逐一用嘴吻衔含每片新芽,用体温促其生长,又用身体捂焙摘下的新叶。灵茶果有奇效。但男子还阳之日即姑娘离魂之时,盖其元气精魄已附体于茶,一命抵一命去了。
这故事的精义,和吴地炼剑传说中名剑如干将莫邪之类若想出炉必用“人祭”,大抵相类。那临头跳入熔炉以人性而尽助天工的,往往就是剑师一个美丽纯净的闺女。
凡好物出世,常有此惨伤的惊动乃至代价,抑或这也是天妒英才的一种体现罢?因此古谚才有不得“暴殄天物”的教训。因那紧关天意的物件原是有性有命的,唐突不得,否则欺天。
碧螺春曾经是美好的童年记忆,一直觉得这茶的好处,就在贴皮贴肉水润气润的合适,一如贴皮贴肉湿头湿脚才踏实的江南的日子。每每一罐明前新茶在手,启封时候香沁入骨,竟生出欢愉之极至于泪下的心:如何人间还能有这样一尘不染的清中之香?!无言语看蜷曲的翠毫在透明玻杯中浮沉,黛螺渐次打开,成为纤细的条索、成为苗条的叶芽,茸毛披覆,银绿隐翠,常常,人就跟着一起沉到了水里。
似乎不再需要方向。
这类娇嫩的绿茶,因为未经发酵、小小发酵,其香其味清淡天然,茶性的保持特别完整、分明,这种辨识与区分的体味,是让茶人真正其乐无穷的事。用比较冷寂的水,来慢慢发出茶的香气韵味,所得体验往往最为丰富,宛如玉笛清远,低回宛转,一步三回头处一套昆曲,一套烟波画船里的雨丝风片,一套惊梦寻梦,一套拾画叫画,一套幽媾神欢……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是好处相逢无一言?(《牡丹亭?山桃红》)
碧螺春的娇弱最是如此,因为芽叶鲜嫩美艳,水温太高,茶就会被烫死。
品味绿茶的细节有点像品味葡萄酒,例如多半先喝清淡的年轻的白酒,再喝浓甜的年长的红酒。绿茶的茶性较之其他,亦是如此,需要浅入深出。这样,茶的天然纯粹方才不至被遮蔽,茶的本来面目方才不至被忽略。设若品饮江浙茶之前,先品尝了重浊的中原茶、“杀口”的江西茶、清烈的云贵茶(更别说乌龙或者普洱这些非绿茶),那可真要改天再蓄这一杯江南碧色的翠琉璃,才是最好。
春水青裳,水天一色的恍惚。
面对江南的茶,人的味蕾也需要耐着心思“将养”?
近些年已经越来越不敢喝碧螺春了。假茶太多。这种乾隆年间就经“御笔亲赐”命名的茶,应该已太为声名所累。“茶虽易茁,气韵反薄”(许次纾《茶疏》),为追求高产利润的人工追肥,已经完全可以把娇媚的深山林仙变成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肥胖姑娘,一如靠“三素”(激素、抗生素、维生素)养成故而能让人吃出诸多毛病的阳澄湖大闸蟹。何况碧螺春还有来自贵州等地的著名替身,处处可见的张冠李戴、李代桃僵。以至在最无能为力的时刻,我开始怀疑自己关于碧螺春的童年记忆:是茶香美化了年少,还是华年美化了茶香?那关于茶的理想与理想的茶,原是可望不可及的仙乡?
那年春天一段奇遇则又多少帮我挽回了对碧螺春的信心:第四届中国昆曲、苏州评弹艺术节举办期间恰在江南游荡,得逢苏州朋友神秘兮兮带来两罐茶,说买不到得好。返回京城,凑集了几个还算可靠的舌尖与相宜的茶具和不错的水源,便开启了这茶。那晚一个痴茶的朋友入口之后险些马上落泪,转而竟责备说,以后不要再带这样的茶“害人”,因为,“以后喝不到了,会难过”,因为,“这样的茶不可能年年都有”。
那一罐碧螺春气脉奔涌,气运入血不止于奔放与洪大,还有一丝血不归经的跌宕与迷乱。
然到底止于所当止。
这就依然是纯贞的碧螺春。
二
同样盛名之下难为完卵的江浙茶,就是西湖的龙井了。在京城已有好几年没喝到真正的狮峰龙井。偶尔在神通广大的师友家喝到一两回好的,经常会让我诧异而可笑地惊问:这真的是龙井?龙井还能这么好?!
那份鲜绿鲜香,旗枪招展,依然能够美如梦幻。
这当然不是西子湖自己的错。在一个任何物事都追求“大众普及”、“品牌意识”的工业、商业地球上,名茶同样难以避免被“盗版”的命运。如今浙江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只要是采用扁形炒青技术制成的所谓富有“糙米色”“炒豆香”的茶叶,都被冠名以“龙井”了。然而形似离开神似,不知几多远。入口的东西,造不得一丝儿假。真材实料永远比“技术进步”更重要,否则,那技术就是“伪装”了。好听一点说,也是“化妆”。
平心而论,真正的好龙井,一如杭州城,那是处处准备好了的茶,要豪放有豪放,要收敛有收敛,见多识广又能从容得体。不过,略略还是有着几分江南的书生意气,是箫心敛着剑气,绸缎里面包裹了一把好快刀,是“风云才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饶是“料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了,旖旎里面依然不忘“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一份高华大方。
张泓在《滇南新语》中、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一例称道龙井的“中和”、清远之气,这话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喝到过好龙井。
最精绝而俏皮的是,在同为清人(康熙年间)的陆次云(《湖壖杂记》)笔下,似乎这龙井的真实性已经受到挑战了:
龙井真者,甘香如兰,幽而不冽,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
龙井中的可疑角色呢,则始终有点怪怪的“混浊”,或者客气一点说,是“刚火”不尽。你会始终觉得这茶有些清中之“荤”,所以并不通脱。仿佛还想“用世”的书生,因此犹有“红尘气”?!仕宦滚打中的男人因此多出了浑浊气象的不清明。
真的,也许竟是尘世的烦嚣遮蔽了这茶之天性自然。
犹记得有一年,在龙井村的茶农家里,细雨迷梦,酽酽喝足好茶,同游几个人,骑着脚踏车,从山上顺着九溪十八涧,一路飞翔般,放到钱塘江边去吃野鱼……记得当时年纪小,居然有兴致骑了自行车爬狮峰,而且有胆量信任自己的友谊、体力与自行车闸。更记得当天晚上用雪碧瓶子背了新安米酒到处找大螃蟹吃。那绵甜适口可后劲极大的米酒,当场放倒了好几个女孩子。大家迷迷糊糊开始合唱或对唱越剧《梁祝》里面最著名的一段“十八相送”:
(女):书房门前一枝梅,树上鸟儿对打对,喜鹊满树喳喳叫,向你梁兄报喜来;
(女):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梁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梁兄你愿不愿配鸳鸯?
(男):离了井,又一堂,前面到了观音堂。
时而戏词儿也被趁乱随意窜换掉,例如一个唱“前面走过观音堂,男人怎能配鸳鸯”,一个就接上“观音大士媒来做啊,两个男子照拜堂”!
笑着打闹成一片后,不记得是谁,突然唱起早已“弃戏就影”的当年越剧小百花当家花旦何赛飞(就是张艺谋电影版《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个为了和心爱男人“寻快活”“哪怕下刀子也要去”,最后丢了小命的三姨太)那段最拿手的撕心裂肺的“楼台相会”:
梁兄啊!
我与梁兄难成对,爹爹允了马家媒。
我与梁兄难成婚,爹爹受了马家聘。
我与梁兄难白头,爹爹饮过马家酒。
爹爹之命不能违,马家势大亲难退。
女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特别懂事的萧萧,听到这里不禁失声,连说换茅威涛吧换茅威涛,《何文秀·桑园访妻》,要么干脆就是徐玉兰的《北地王》。萧萧那声南部方音特有的将“走啊”发成“举啊”的叹息声一出口,一伙疯疯癫癫的女孩子就突然安静下来。
萧萧就是祝英台似的一个人,“女扮男装”来得那个好。流行弹词小说的江南闺阁记忆,仿佛根底都有个《再生缘》里“自身能养自身来”的孟丽君在,“既然要做聪明者,须做聪明绝顶人。如此闺娃天下少,我竟是,春风独占上林枝”!昆曲与越剧中,最动人处,还真的是“小生”这个角色,尤其当这角色是由骨相清俊、典雅洒脱的女孩子反串的时候。
这一点惊心动魄,始终让我觉得,江南绿茶,即使算不得洁白纯正女儿茶,也是苏昆中冷板水磨那个《牡丹亭》,杜丽娘眼前心中的柳梦梅,是明清中国尤其戏剧舞台上独有身段的一个特殊的男人品种抑或男性想象—这个“小生”的美啊,他似乎经常是“她”,是那些反串男子的女孩一个调皮的梦。“杏子阴假凤泣虚凰”,当不得真,然而美如妖精。
二十几岁的后青春期的女孩子,还能有那样的豪放与打开,我至今都满是感恩的心。
于是就觉得,我此后再没有喝到过那样的好龙井了。
这便说明,在很多时候,关于茶的记忆,品质而外,亦关乎心情,更关乎心情。犹如碧螺春做了童年的底色,龙井茶成了青年的回味。
因此,有时候,长久滞留北地的我,还是会怀念一些远在天涯的江南茶社,例如秦淮河畔的伴月茶馆,例如子胥野渡的茅草小庐,例如苏州几年前还少有人烟的耦园—似乎如今被称许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早年一度曾经独自默默在此读书写作的。
听说近来的耦园,居然也摆设了花灯展览,地方零杂、陡然热闹起来了。
那年那日在耦园,一色儿极朴素的茶具茶壶,一色儿极简陋的方桌条凳,甚至没留意点泡的什么茶。和一个宜兴籍的朋友,几乎一言不发就喝了整下午的茶。
三
早些年,那苏州的茶楼,大多纸帘垂地,幽光寂寂,配合着江南雨声的乍有乍无、时大时小,开窗往往便是一墙绿得实实在在的爬山虎,楼下拐角处,自在生出几杆青竹,“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不似京城紫竹院里那一小片面黄肌瘦的竹竿,样子活脱脱是捉襟见肘的表演。时常有情致悠闲的壮年茶客聚拢来,似乎一个下午都在围棋戏耍,只要一杯淡茶。
生命的节奏怎么可以如此迂徐安适?
听。隔壁三弦叮咚,清脆欲滴,如流水走过三生石畔,旧日精魂折腰相见,薛筱卿大段琵琶烘托之下,是以“哑糯”著名的沈(俭安)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苏州评弹《珍珠塔》中,一段“七十二他”。
苏州茶馆的韵味,很多时候不止于口吻,其实更是声音的。
例如以“老、旧”著名的“和平里书场”。
穿过几道逼仄、狭窄、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子,绕过吴语滴沥的老妪好奇而温顺的眼光,呈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位于马大箓巷的这家老书场了。不少老年人汇聚于此,喝茶、聊天、乃至牌戏—假如没有先生说书。
书场对面是上书“安静致远”的高大牌楼,建筑物破旧、周遭环境杂乱,而那破败下又有一份骨意中的清洁与雍容,似乎是从地气与水意得来,婉转天成。如果有弹词演出呢,则书场中一个个轻言轻动、无烟无话的白发老人,一杯清茶淡水在手,就能在书场消磨上一个下午。苏州书场的“老耳朵”(内行、资深听客)之文静、内敛、不动声色,确实修养到家,无论自己的真实感受、褒贬若何,却基本无哗声、无嘘声,亦无叫好声、议论声,其笑语低徊、轻颦细捻,都是温吞吞的,甚至似是而非一般。
和苏州相比,杭州听客的风格,也有如苏州茶和杭州茶的区别,亦大有改变。例如在“湖畔居”那样甚为高档的书场,也不断会有人抽香烟、吃零食,听书一段后,杭州人更喜欢鼓掌致意。整个书场气氛显得热闹,活泼,随意,亲切,但的确也有点嘈杂,空气也自污淖不少。
杭州的老人是很爱和人聊天的,常有人拍摄了从前来此演出过的历档书先生的照片,开书之前彼此传阅。
不过,杭州这份身先士卒、身不由己的敞开与豁亮,高谈阔论后面,底子还是宽和忠厚,想来跟它几次成为帝国都城的经历有关。凡为帝都者,城市必然有被迫打开的一面,日久天长,习惯也就成了自然。不像苏州,历朝历代都是个休养生息的“后花园”,“薄命怜卿甘作妾”似的,满满的哀怨美,那温婉宁静中何尝没有侧身揖让的淡淡委屈。只这委屈打磨至纯熟精美,便也是一份修养。
杭州方言至今都有中州口音,算客家话,和吴侬软语一掐一把水汪汪的苏州话不可同日而语。
对一个地域一种文化提供最后的保护、捍卫与屏障的,其实是语言—她的母语。
也是因此,如今那个数百万常住人口当中不到半数还是本地人的苏州也是越来越面目模糊了,渐行渐远的何止一杯薄茶清淡。
那年初夏在苏州,日日面对小新加坡一样的工业园区,已经完全沦为假冒伪劣的七里山塘,一片光怪陆离的老城市区……我发现我已经不再认识我记忆里的苏州,焦躁与疏离攥紧我的心脏。直到有一天,我一个人冒着小雨跑到木渎,寂寥的小镇那日游人稀少,只有满街芝麻枣泥烧饼的焦香唤醒她的清晨,西施临水梳洗的“香溪”流过村落中心,与之伴行的,居然是“胥江”—纪念的乃是一直对来自越国的西施姑娘耿耿于怀的吴国的忠实老臣伍子胥。这份民间并行不悖的幽默与从容,格外亲切可爱,想起刚刚结束的本届评弹艺术节上,苏州市吴中区贡献的参赛曲目就是《吴宫遗恨》,那个有点宝里宝气却很憨厚慈仁的夫差挤兑在美人与良将之间为难,真如心肝与肱股般无法割舍,不禁也不仅,让人独自莞尔。
不远处,就是灵岩山上姑苏台了,“轻绡催趁,馆娃宫里,要换舞时衣”,一片苍绿泠泠处,曾经“十载西湖,傍柳系马”的南宋词人吴文英寻根问古来了么?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①采香径前响屐廊,花容足以沉鱼的美人的千古足音已经袅袅如天际归云。传说国灭身死的夫差以自刎的方式追随曾经“对不起”的伍子胥于地下,却没有跟掌中的明珠西施“秋后算账”。因此,他到底是有史以来难得一个有“爱的能力”的男人?可惜辜负了一国生灵关于政治清明的期待,因此,他到底是那个时代一个不够资格的君王。
在木渎镇上,我看到了那座据说建造于明代崇祯二年(1629)已经五百岁大的怡泉亭,亭中罩住一方古井。一切的构造材料,便是简单流畅几块巨大花岗岩石条的垒叠,古拙、质朴,却大气、从容,时光柔和了一切粗粝坚硬的东西,只余剩下一些平淡凝重的肌理。
江南在这个瞬间,回到我的眼眸,然而,这个瞬间还能保留多久?
前言/序言
导言 茶行人间世 天地清沉沉
既然也是一本写茶的书,就不能数典忘祖,纲举目张处要从全世界第一本“写茶的书”—一本用中文写成、以“茶”为“经”的书开始。 回眸就是千年以前,名唤陆羽的孤单人一路为茶走南闯北,水里来火里去。 历史记载中的陆羽(733—804)自称桑苎翁,字鸿渐,又号东冈子,是唐代复州之竟陵(即现在的湖北省天门县)人氏。公元756年,未及而立的陆羽开始了他探访南北茶区、亲炙深山老林、直入幽谷古寺的“茶道之旅”,烟霞羡独行,野饭石泉清。公元760年,经过数载探询、体验、品味、专研之后,为避“安史之乱”离乡远行的陆羽隐居到了位于苏南、浙北之交的湖州苕溪,停下一路清香甘润的脚步,安稳心神,收蓄精华,写成一部属他的《茶经》。其正式出版完成,则在公元780年。 人在地上,茶在路上,清清澈澈,沉沉郁郁。 这本世界第一的茶之专著,陆羽准备并书写了整整二十五年。 痴情于茶的陆羽却似乎是个自卑的人,他在自传当中,居然如此写到:“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 一代茶圣原来如此其貌不扬、笨嘴拙舌? 似乎他还是个苦命人儿,幼年失怙,长于丛林,姓与名皆像一个天与人的传说,乃是《易经》中《蹇》之《渐》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养活其命的老僧便如此命名了他。不过,他的这份自卑抑或自谦,也可能是只为他太过清洁?那是大茶人本色。 于是明人冯时可在著述《茶录》时,毫不客气点出陆羽的另层深心、或真心:“鸿渐伎俩块垒,是《茶经》盖以逃名也,示人以处其小,无志于大也,意亦与韩康市药事相同。”范晔《后汉书》有《韩康传一则》,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世家巨族,却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冯时可拟陆羽以韩康,意指隐士逃名,生当乱世,华族的文士代代有类似的选择。借物语之酒杯,浇薄命运之困厄,《茶经》一书竟而成为韬光养晦、自我保全的用具。安处卑微,意在高明,正如《茶经》而外他还有《会稽东小山》诗传世所示:
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
千古繁华交付于一声猿啼,哀伤下涕,独自飘落茶盏,犹如灿烂绽放之后迅疾凋零于幽暗的一朵枯淡的莺花。 爱茶与吃茶,似乎很久以来在文人眼里都是需要条件的,茶为嘉木,能欣赏茶的清淡之美的味蕾与人品,都不可太过浓烈奔肆。早在魏晋风流的时代,茶事就被时人视为“素业”了。明代专品真味、大放异彩的“文人茶”,更将此意蕴推向高潮中的高潮。 例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之第十七子朱权著有《茶谱》,认为“(茶饮)本是林下一家生活,傲物玩世之事,岂白丁可共语哉?予法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 另一明代文人屠隆在《考槃余事·山斋笺》中,则具体规定了这“茶寮”的具体设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同时人许次纾在《茶疏》中更列具了适合品茗的非常时刻,诸如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夜深共语、风日晴和、轻阴微雨、荷亭避暑、小院焚香等等,无疑都是些斯文雅客清赏的余事、遣怀的勾当。 这茶之于百姓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似乎已经有了距离。 耐人寻味的是,在较早的唐宋年间,茶味当中的人间烟火气象,倒更为丰足一些,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旧唐书·李珏传》)。例如顾况(唐)《茶赋》中专意强调茶的实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价值,所谓“滋饭疏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梅尧臣(宋)《南有嘉茗赋》中,赋予茶更为广阔的天地人生,“南有山原兮,不凿不营。乃产嘉茗兮,嚣此众氓”,这茶是雅俗共赏、养生厚生的,“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而不宁”。 说茶发乎神农氏而闻于鲁周公是对的,药食一家,药毒一家,其文化意味的兴与盛,则毕竟在唐宋,从药用、食用,到饮用、品用。在茶作为“文化”的童年时代,在陆羽那第一本《茶经》里,其具体内容共分作了十节: “一之源”,阐述茶之起源、茶树的生物特性、自然条件与茶的品质关系,饮茶对人类身心影响的功效;“二之具”,阐述茶叶采摘及制作过程中的十五种工具及其使用方法;“三之造”,介绍茶叶采摘的要求,各类成品茶不同品质的形制特点、对制茶工艺的要求;“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所用的二十五种器物,明确煮茶、饮茶的正确方法及原则;“五之煮”,阐述炙茶、煮茶的要领,阐述茶叶品质的标准;“六之饮”,论述茶叶的煮饮方法,指出加工茶叶的九项关键技术;“七之事”,记述茶之历史衍变、嗜好饮茶的名人的轶事故事,并介绍茶之药用功效;“八之出”,记载陆羽的时代即唐代茶叶产区的分布及所产之茶的质量评述;“九之略”,阐明在深山野寺等特殊环境下加工、烹煮茶叶可省略的一些过程及其器具;“十之图”,将所有茶事内容写成图卷,陈列于室,以志备忘。 在陆羽的时代,那个大唐盛世,国人喝茶,较之如今实在另有不同方法,其别致之处,某种程度上,如今只有“田夫野老”所在例如大西南地区、湖南的“擂茶”或白族的“三道茶”之类,才大有古风存其余韵:茶饼不仅要烤干、碾碎,烹煮时更要加盐、加香。而后,流行于斯文宋代的“龙凤茶团”,甚至要掺入多种名贵郁烈稀有之香料,这是让今日茶人咋舌不已的“贵族待遇”。 这样一种味道浓重而风格丰腴的“茶汤”,有点像江南乡下流行的“阿婆茶”:女性农闲聚会之时自喝的茶,也是香喷喷甜丝丝五味俱全。我在苏南浙北交界的小莲庄—隶属于陆羽当年隐居栖息之地湖州,喝到过一种藤豆茶,也庶几近之:把炒熟的青豆、陈皮、椒盐、桂花,加茶叶一起冲泡。 如果深研,则这“阿婆茶”也是有来历的。在经常被作为中国宋元话本小说出挑之作的《快嘴李翠莲记》中,描述多嘴多舌的翠莲姑娘如何当家待客,她先是“走到厨下,洗刷锅儿,煎滚了茶,复到房中,打点各样果子,泡了一盘茶”,然后“托至堂前”就说了如下一番话:
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抄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柤。
这里描述的,该是元明时代一直颇为风尚的一种“民间俗茶”吃法。《金瓶梅》中更有关于此类茶事的大量具体描写。 茶史之上,从烹煮到清饮的划时代的大变革,发生在文绉绉的明朝,且似乎就是江浙导其先鞭。 文人喜欢作酸的明朝偏偏有个杀人如麻的第一天子朱元璋,但这放牛小子无赖儿郎不小心好像还成就了一回风雅领袖,诏令“罢造龙团,唯采茶芽以进”,其关乎政治民生的理由倒是很有平民风味,是为团茶要“碾而揉之,压以银板”,此举过分劳民伤财。正是这项“改团饼为散茶”的制度变革,使得茶叶的生产与饮用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改蒸焙为炒青,改煮烹为沸水冲泡”。只是笔者又有些多疑,如此优雅天然的改变,难不成因为朱元璋自己就是个来自茶乡的土生土长的“草根”安徽人?众所周知,宋代流行的有点跟“茶”较劲的“点茶”、“斗茶”之游戏精神,与同靠茶吃饭的平头百姓的民间日常,其实隔膜得很。有此一举,却使得作为“文化”体现的中国饮茶方式的历史演变,成为“原始粥茶法—饼茶煮茶法—研膏团茶点茶法—散茶泡茶法”这样一道风景线了。 当然,散茶“撮泡”作为饮法,其实南宋时期在江南例如绍兴早就出现,陆游《安国寺试茶》一诗中已经有了“不团不饼而曰炒青”的越茶,名唤“日铸”。这一点缘故,扬之水先生在其《奢华之色》中考证茶匙细事时正说得好:“饮茶法的雅和俗始终是并行的,并且各有发展,也各有自己的精致。”而马端临(元,1254—1323)《文献通考》中给出的考证,暗示相当伤感:“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也。”这得益于地域的茶制度变迁,却是国破家亡的历史伤感。 元人朱升尝有诗写《茗理》:
一抑重教又一扬,能从草质发花香。神奇共诧天工妙,易简无令物性伤。
虽是理学气味丰足的体道之意,但于制茶之抑扬顿挫乃使草木得花果滋味处见识茶心,也是别有趣解。尤其称道“简易”而护惜物性,心学眉目之外(南宋心学鼻祖陆象山与理性巨子朱熹问难,道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更可见及彼时“清饮”之风习于士人日常生活应该并不陌生。 清代虽为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当家,饮茶之风却更是盛况空前,特别乾隆皇帝,他几下江南,至于和杭州名茶龙井、苏州名茶碧螺春,均结下一段又一段不解之缘。但改革积习总是艰难的,何况在这个泱泱中华,东西南北走过,天时地利不同,人的舌尖与胃口便常常相差甚远。喜欢且难免“抬杠”似乎是此种文化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这个苗头可是在先秦诸子的时代就开始了罢。谓予不信的读者可自去查点古籍,参阅老、孔、庄、韩诸子“掐架”的雄姿英风好了。 关于茶,例如作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茶考》一书,居然还在抨击茶的清饮之法,“北人”很是不屑“南人”的此种改革: 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北客多哂之,予亦不满。一则味不尽出,一则泡一次而不尽用,亦费而可惜,殊失古人蟹眼、鹧鸪斑之意。
在今日茶人看来,此种“古意尽失”,实在正是茶有史以来的“救赎”:还茶一个自性清明,一个自由自在,一个自然而然。 享受且迷恋着茶的本色清纯的今日茶人,是很难领会古人涵泳于那种五彩缤纷的茶汤中的独特妙处的。对于今日爱茶吃茶的凡俗素人,我们最渴望达成的,或者就是让我们的眼眸、鼻翼、口吻与情致,一起联袂“上路”,循着茶香,走问天涯,地头海角处,青青华盖那满枝头的春深,便是不老无忧、远离造化污染、沉沉稳稳一株茶了。 既然迷醉了“茶圣”陆羽并让他因此选择“落叶归根”的首先就是江南茶,这“茶道之旅”第一站,就从江南出发吧。
用户评价
刚拿到这本书,就被它的名字吸引了。一个“问”字,就充满了探索和好奇,而“茶”又是如此日常又富有深意。我一直以为自己对茶的认识仅限于“解渴”或者“提神”,但读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肤浅。作者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与茶相关联的文化、习俗、甚至是一些不为人知的传说都串联了起来。读到关于某个边远地区独特的采茶方式时,我仿佛看到了采茶姑娘们在晨雾中劳作的身影;读到某个朝代的文人墨客以茶会友的场景,我又仿佛听到了他们吟诗作对的谈笑声。最让我触动的是,作者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并没有刻意地去拔高或者神化,而是用一种非常平实、真诚的笔调,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底蕴和人文关怀。它不像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位老友在分享他所见所闻所感,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温度。读完之后,我对待一杯茶的态度都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匆忙地一饮而尽,而是会去感受它的香气,体会它的滋味,甚至会去想象它背后的故事。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有一种很静谧的氛围,浅色的水墨晕染,一株淡雅的兰花,仿佛能闻到淡淡的茶香。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原本以为会是一本关于茶叶种类、冲泡技巧的实用指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它远不止于此。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温润的情感。读着读着,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色古香的茶室,听着雨打芭蕉,品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那些关于茶的故事,不是简单的历史陈述,而是融入了人的情感、经历和哲思。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茶道”的探讨,它不仅仅是泡茶、喝茶的仪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自然、与内心对话的方式。作者用了很多生动的比喻,将抽象的茶道精神具象化,让我这个对茶道一知半解的读者也能有所感悟。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慢”的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能有这样一个空间,让人停下来,静静地品味生活中的点滴,是一件多么奢侈而美好的事情。它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但却有一种淡淡的余味,萦绕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评分我一直认为,真正的书籍,是能够带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而这本书,无疑就是这样的存在。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惊心动魄的 plot,但它却拥有着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茶的了解仅限于日常饮用,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的笔触是如此的细腻,仿佛将我带到了古老的茶园,感受着晨露的清凉,也带我穿越了几个世纪,目睹了茶文化的演变。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不同茶类背后故事的描绘,那些故事充满了人情味,让我看到了茶与人的紧密联系,看到了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它不仅仅是在介绍茶,更是在讲述生活,讲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讲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本书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压力,也没有给我设定任何的目标,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用它独特的方式,给我带来一种平和、宁静的力量。合上书本,我感觉自己的内心也像被涤荡过一般,变得更加澄澈。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位知心的老友,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能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让我真正放松下来,并且从中获得一些启发的生活读物,而这本书恰好填补了我的这份渴望。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复杂的论证,而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关于茶的点点滴滴呈现在读者面前。读到那些关于茶的传统习俗和民间故事时,我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岁月,感受到了古人对于茶的热爱和崇敬。书中关于“慢生活”的理念,尤其让我产生共鸣,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去品味一杯茶,去感受生活的美好,这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它让我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烦恼,或许只需要一杯茶的时间,就能得到释怀。这本书不是那种读完就丢的书,它更像是可以在书架上常年陪伴的良师益友,每一次翻阅,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感悟和力量。
评分我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着较高追求的人,但同时又不喜欢过于繁复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这本书就完美地契合了我的这种偏好。它不是那种教你如何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书,也不是那种灌输你“成功学”的鸡汤。相反,它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关于“何以为人”的深入思考。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本真”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正是茶文化最核心的魅力所在。一杯好茶,它的美在于其自然,在于其纯粹,在于它能让你回归到最真实的自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书中对“禅意”与“茶”之间联系的阐述,那不是刻意为之的宗教仪式,而是融入生活中的一种平和与淡然。读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诗和远方”,其实就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生活里,只是我们被太多的浮躁和喧嚣所蒙蔽了双眼。它教会我如何在一杯茶的氤氲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如何在一片茶叶的舒展里,体会生命的律动。
评分闲来无事,买了几本书,每天翻翻
评分喜欢喝茶,喜欢看这一方面的书。
评分喜欢喝茶,喜欢看这一方面的书。
评分物流很快,服务态度很好,支持京东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老爸看了节目,指名要买,等了好久才送来。包装不错,内容只好听老爸反馈了
评分好书,值得一看
评分书籍印刷质量好,内容文采高,对于茶文化的介绍很吸引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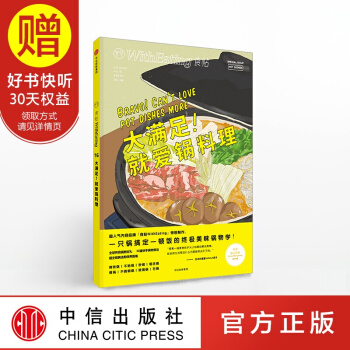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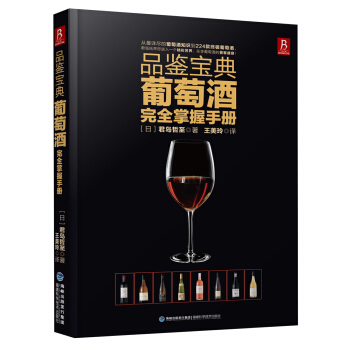
![一学就会的拉花咖啡(超值版) [Tasty Foo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1292/55c2bd58N3651cd0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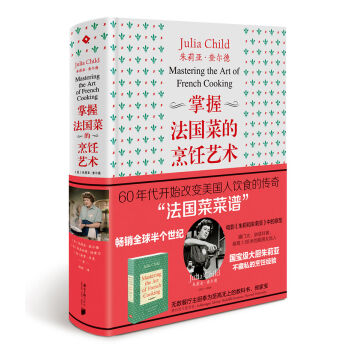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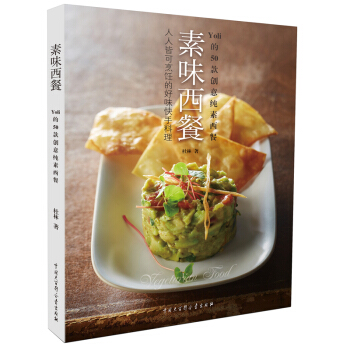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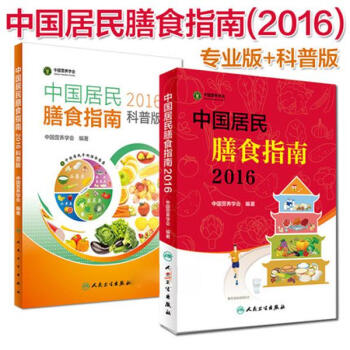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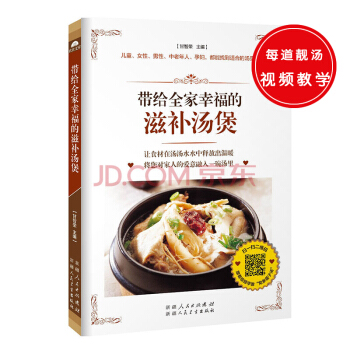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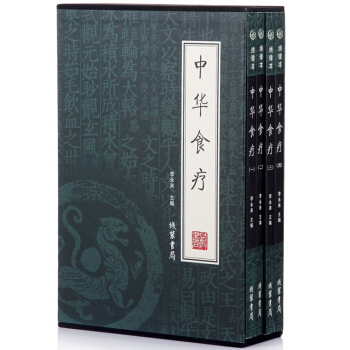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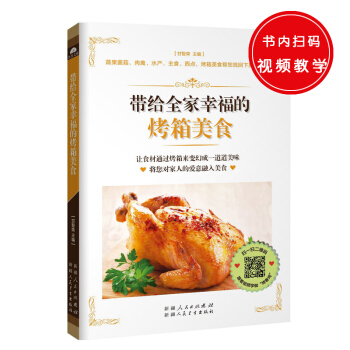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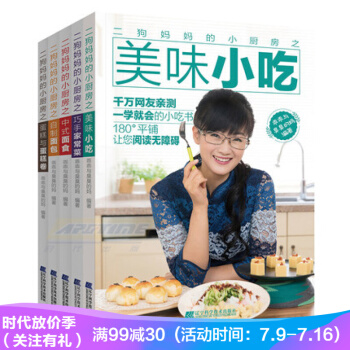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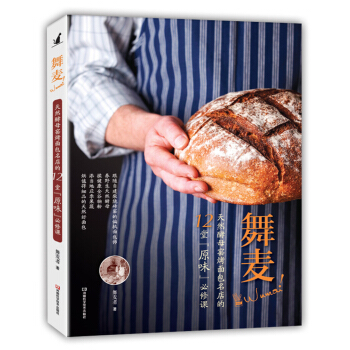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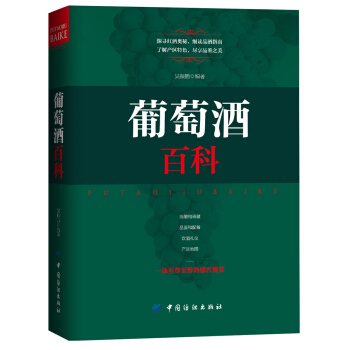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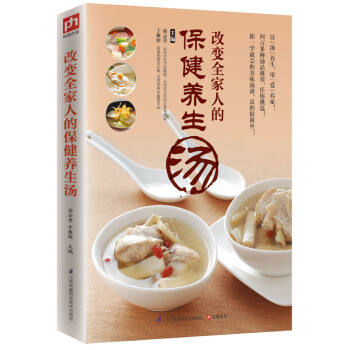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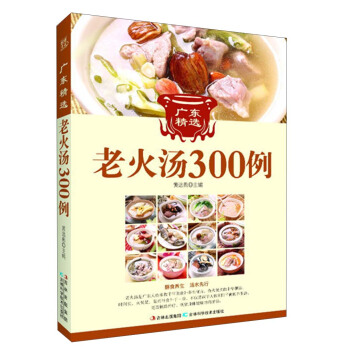
![咖啡原来是这样的啊 [This is Coffe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51294/54389e72N2a58dee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