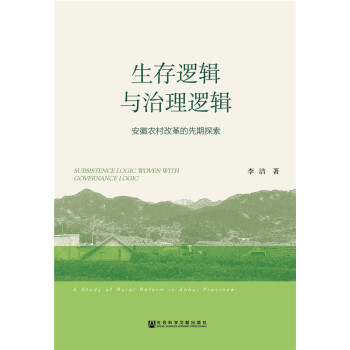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对“农村改革何以可能”这一关乎中国市场转型源流的重大议题,已有研究往往以“小岗典型”为原型,将其简单地描述为农民自发推动、国家顺应民众意愿的过程。然而通过对安徽省农村改革早期实践过程的历史材料和地方档案材料的收集、分析和互证,本书试图再现农村改革初期的实践逻辑和复杂面相。作者简介
李洁,女,1981年出生,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先后就读于安徽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7~2008年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2009年获得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曾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多次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重大研究课题。目录
第一章 引言:小岗故事的画外篇第二章 农村改革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 对国家-社会关系框架的反思
二 农村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人类学”:划分与联合
三 研究方法
四 生产责任制相关术语的界定
第三章 乡土社会的集体化改造及其后果
一 乡土社会成为国家改造的重要目标
二 农民的应对与抗争
三 陷入治理僵局的国家
四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转变的契机:灾害下的政策变通与村庄自救
一 灾害、危机与国家应对
二 分层的村庄记忆:对不同叙述文本的并置
三 分层叙述背后的权力关系
四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从“试点”到示范:国家改革派对农民意愿的凝聚
一 试点的拣选:村庄行动进入权力视野
二 试点的确立:对群众意愿的调动
三 试点的阻力:来自国家科层制内部的紧张与化解
四 试点验收、示范与推广
五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改革的推进:作为事件与作为符号的小岗
一 作为事件的小岗:包干到户的顺势而生
二 作为符号的小岗:国家合法性转变的重要意象基础
三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两种逻辑的相互投射与构成
一 安徽省农村改革的进程
二 生存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构
三 农民自身对转变赋予的意义
参考文献
附 录
后 记
精彩书摘
《生存逻辑与治理逻辑》:但是在市场转型的进程中,特别是作为市场转型的第一步,打开制度性缺口的农村家庭责任制的试点,却具有与上述试点不同的性质。它不但没有获得当时中央文件的支持,而且直接与当时的文件规定相抵触。也就是说,这种试点并不具有国家政策允许的合法性基础,那么它一定要另外寻找一种支持性的力量。这或许是为什么民众的意愿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如此之大的重要性。民众集体意愿可以说是除国家中央政策文件之外,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的另一个有效来源。然而在实际情形中,恰恰不能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并不是一个没有分化的整体,而是存在由生产方式、劳动分工、家庭结构、世代经历等不同原因造成的农民之间的分化,以及以此决定的农民对包产到户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三十年集体化话语的宣传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上演也让农民对触碰“包产到户”这一政治禁区有所忌惮。因此吊诡的是,为了打破集体化时期形成的制度和话语桎梏,改革派领导者反而需要运用土改以来逐步形成的类似“工作队下乡”“政策宣讲”“群众发言”等社会动员技术,才能让普通民众的声音得以表述并向上传达;但是这次“试点”的目标已经与之前历次尝试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
前言/序言
序 希望的田野还是乡愁之地郭于华
李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研究专著《生存逻辑与治理逻辑》就要出版了。在当今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其社会关注程度不成比例的情境下,这样一部著作或许不会成为吸引目光的畅销书,但一定是重要和值得人们思考的学术成果。
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型时期,而当代社会转型是从农村开始的,或者可以说农村改革是整个中国改革的发祥之地。李洁博士的研究以转型社会学的视角,运用口述历史方法,通过与农村改革亲历者们的互动,以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获得第一手宝贵材料,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安徽农村改革发端期的故事。
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农村改革的结构性因素、动力机制、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和张力等始终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国家与农民谁是农村改革的真正推动者?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究竟是底层农民的“伟大创举”,还是各级领导者抑或顶层的设计?市场经济到底姓“资”还是也可以姓“社”?一个社会主义的农业大国之转型,无疑是一个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和偶然性的艰难历程,如果没有结构-过程互构的视角,没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探索,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是难以回答上述问题的。
李洁博士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村改革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安徽省农村改革实践的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市场转型的源流问题:农村改革何以发生?如何发生?研究再现了集体化末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与农村改革初期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过程,力图恢复“历史”本身的多重面貌,致力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历史,并从中洞悉文明运作的逻辑。从她的论述中读者可以获知,中国农村改革并非简单的国家巨手推动抑或农民自下而上地发起,事实上,在各种权力关系与历史话语框架互相嵌套与掣肘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推进整个改革进程。在某些情境下,国家与农民甚至需要借助对方的话语和逻辑,以实现政策层面的灵活变通与国家统一治理的协同与自洽。
本书的出版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运作逻辑和中国农村改革深层结构的理解,其意义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理解现实并寻求农村发展的路径。
当年改革初期的乡村变迁与今日农村的社会结构状态及农民的出路有着内在的关联。改革开放是旧体制走到尽头、不得不进行变革的行动;时至今日变革的脚步仍在行进之中。换句话说,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的出路何在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农村社会的转型步履维艰,仍是横亘于人们心头的思虑。不知起自何时,怀有乡愁,记住乡愁,成为已经城市化的人们的一种情怀,然而,思念寄于何乡何土却已然成了问题与困惑。在中国语境下,所谓乡愁,既有人们对故土田园生活方式的怀念,更有对农民困境和乡村凋敝的担忧。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一边惊异于城市面积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一边又感叹着乡村精英的流失和乡村社会的凋敝,悲哀着乡愁无所寄托,并时常将其归因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越来越突显,且似乎的确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点并用结构性视角去看待分析这些问题,就无法回避这样的思考:今日乡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杀率上升、儿童认知能力偏低、家庭生活不正常等仅仅是由于人口流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吗?
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通常是一个“农民终结”的趋势。“农民的终结”曾经是法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命题,而今天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命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农民的终结》的作者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终结”的。他所说的终结并非指农村消失了,农业不存在了或居住在乡村的人不存在了。其书再版时(1984年)法国正在经历作者所言的“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表现为:(1)农业人口的外流仍在继续,同时乡村人口的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人员经常占大多数。(3)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4)通信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5)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70年代完成的)。“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里溜走,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当前在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永恒的“农民精神”在我们眼前死去了,同时灭亡的还有家族制和家长制。这是工业社会征服传统文明的最后一块地盘。于是“乡下人”成为化石般的存在物(孟德拉斯,1991)。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是农村趋于凋敝,而农民并未“终结”。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严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表述。
其一是城市化制约。长久以来制度安排形成的结构性屏障限制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农民作为国民人口的大多数、粮食商品率稳定在35%以下,是持续已久的现实。直到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1.27%。而农民进入大城市的制度瓶颈依然存在,并且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在就业、生计、保障和后代可持续发展方面也依然存在困境。已故的“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先生曾经批评:“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需要绿化美化,在农村看到一棵大树很漂亮就要搬到城里去;连大树都城市化了,却不让农民城市化。”
其二是农民工困境。与城市化问题相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农民工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这支流动大军的主体。我们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所谓“新生代”并不仅仅是年龄或代际概念,还是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世界工厂”时代的劳工群体。与其父辈相比,他们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关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不愿认命,有着更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们所面临的似乎无解的现实却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难以化解的矛盾表现为新生代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这种特色体制造成并维持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留守儿童、老人、女性的悲剧和每年“春运”的独特景观。
上述困境让人无法不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谁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如何实现?显而易见,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只要劳力不要农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人们常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为农民、农村和农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大最难的问题;人们也常说,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这并非同义反复的强调,而是说所谓“三农”问题仅仅从农村和农业范围着手是无从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须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中去思考和解决。
从农民的概念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农民从来不是作为farmer存在的,他们不是农业经营者或农业企业家,而是作为peasant 的小农,他们从事的只是家户经济。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根本上不是从业的、职业的区别,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中国语境下,无论将农民放在社会分层的什么位置上——工人阶级最亲密的同盟军也好,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也罢,中国农民都不是劳动分工意义上的类别,而是社会身份和地位上的类别。
从中国农民的结构位置看,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剥夺的位置,在特定时期甚至被剥夺殆尽。长久以来,他们总是社会变革的代价的最大承受者,却总是社会进步的最小获益者。农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对象——劳动力、农产品、税费、资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远被利用、被开采、被索取,没有投入,没有休养生息,只会越来越贫瘠。不难看出,农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缘起于市场化改革后的劳动力流动,农民作为弱势人群的种子早已埋下:传统的消失,宗族的解体,信仰的缺失,地方社会之不存,这些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注定。
经历了长久的城市与农村的分隔状态,所谓城乡二元已经不止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成为一种思维结构。剥离了农民的权利所进行的城市化,是缺少主体及其自主选择权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权利被忽略或被轻视,农民被作为丧失了主体性,自己过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决策的弱者群体。解决农民问题,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给农民还权赋能(empower),即还他们本应具有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一些底层群体的悲剧,农民和农业的困境,以及乡村社会的颓败之势是否可以避免呢?
从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进程开始,梳理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李洁博士的努力对于我们如何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面思考解决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当有所启发。
2017年10月18日
参考文献
孟德拉斯,1991,《农民的终结》(1964/1984),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文笔堪称一绝,语言充满了张力和诗意,但又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它有一种冷峻的现实主义色彩,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作者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无论是对宏大场面的描绘,还是对细微情感的捕捉,都精准到位。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回味那些精彩的句子,它们如同打磨过的宝石,闪烁着独特的光芒。这本书在探讨生存困境时,展现出一种近乎残酷的诚实,但恰恰是这种诚实,让读者得以直面现实的复杂性。它不是一本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的书,但它的深刻性绝对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细细品味。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它打破了我对传统叙事结构的固有认知。作者似乎在构建一个平行宇宙,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故事的走向充满了意外,每一次看似合乎逻辑的发展,都可能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颠覆。这种不可预测性,让阅读过程充满了刺激感。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将抽象的社会学概念,融入到具体的故事情节中,让复杂的理论变得可感、可触摸。它迫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环境,思考那些看不见的约束力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模式的。这是一部非常需要读者积极参与、主动思考的作品,因为它绝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摆在你的面前。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相当独特,它仿佛带领我走进了一个宏大而又细腻的叙事迷宫。作者的笔触极其老练,擅长在看似日常的场景中埋下深刻的隐喻。我尤其欣赏它对复杂人际关系的处理,那些微妙的权力动态和潜藏的欲望,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解开一个关于人性本质的谜题。书中对环境的描写也极具感染力,那种压抑却又充满生机的氛围,让人仿佛能亲身感受到角色的挣扎与抗争。整体来看,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结构严谨的作品,它强迫你去思考,去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像是在构建一个可以供人反复揣摩的哲学空间。那种沉浸式的阅读感受,久久不能散去。
评分这是一部极具野心和深度的作品,它在主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高度。作者似乎对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有着深刻的洞察,并通过这部小说,构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立体而复杂,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每个人都在各自的逻辑下挣扎求生。我特别欣赏它对冲突的描写,那些冲突不是简单的正邪对抗,而是不同生存策略之间的碰撞与角力。这种对复杂性的接纳和展现,使得这本书的耐读性极高。每一次重读,或许都会有新的领悟,因为它所触及的议题,是永恒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它是一次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探索。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它的叙事节奏掌握得炉火纯青。它并非那种一上来就抛出所有线索的直白叙述,而是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棋手,步步为营,将悬念层层递进。故事的张力在不知不觉中累积,直到关键时刻爆发,让人拍案叫绝。作者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也十分到位,那些挣扎在道德边缘的角色,他们的动机和选择都显得无比真实可信。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这本书在探讨现代社会某种深层焦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将问题抛给了读者,引发了关于个体在宏大结构下如何自处的深思。这种引人深思的特质,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一般的消遣读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小说创作基本技巧:从计划到出版 [Novel: plan it. Write it. Sell i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49399/5a1e8790N9d6619e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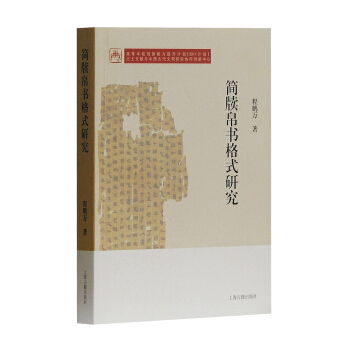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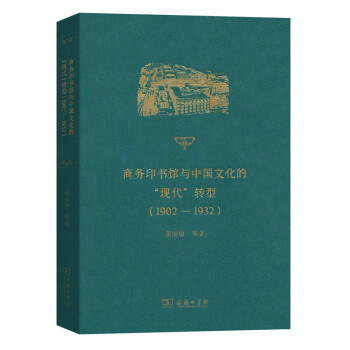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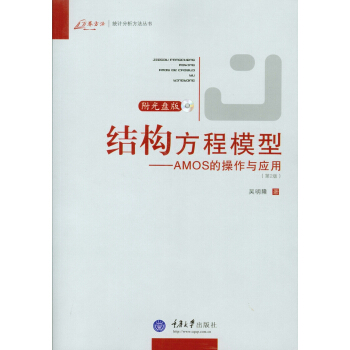



![基因传(悦享版) [The Gene:An Intimate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0679/5a31138cN833bbe5e.jpg)
![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7)/新闻业观察报告蓝皮书系列,人民日报传媒书系 [An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Journalism (2017)]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0951/5a38cf4fN2e4b30b5.jpg)

![属性数据分析 [An Introduction to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1293/5a5c6b71Nbcba14e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