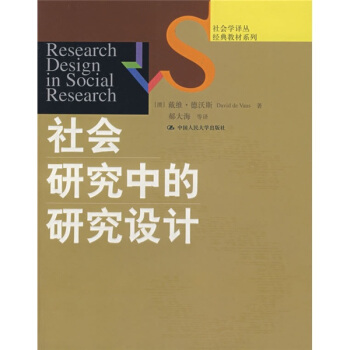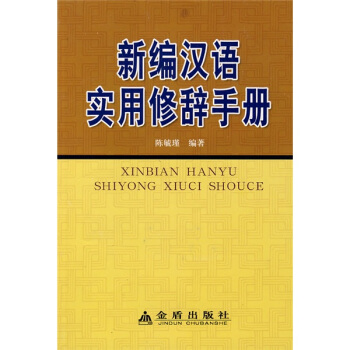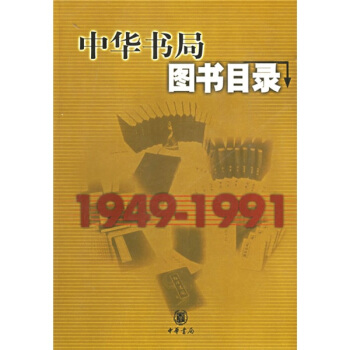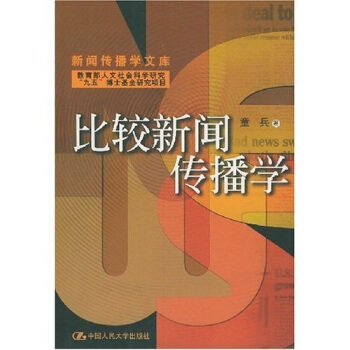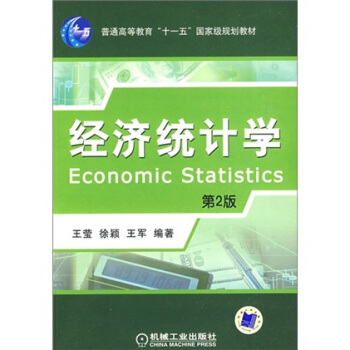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中國在追求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既應該重視藉鑒世界普遍的教育經驗,也不能否定被曆史證明瞭的“中國經驗”。書中的這段曆史昭示瞭,中國固有的私塾教育確實有不少弊端與不足,但也有與中國基層社會實情相契閤的一麵;外來的學校製度並非盡善盡美,還有可能橘化為枳,應盡力找到實現兩者優勢互補的新途徑。
內容簡介
晚近國人的教育觀受到外來思想的深刻改造,對傳統私塾與新式學校均有簡單化的評判傾嚮,多視兩者為落後與進步、野蠻與文明之爭。無論對科舉停廢前大量存在的舊式民間學塾,還是從清末到民國所發生的私塾與學校長期的糾纏競爭,亟待進行深入、持平的研究。本書不以成敗的標準倒敘與評價曆史,也不發思古之幽情,竭力重構當年的曆史環境與曆史觀念,重建有關近代中國私塾與學堂之爭的諸多重要史實,可為中國追求教育現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麵的參考。
作者簡介
左鬆濤,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人。華中師範大學曆史學學士、碩士,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2015—2016年美國德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曆史係訪問學者,著有《變動時代的知識、思想與製度:中國近代教育史新探》、《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五冊)等,發錶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精彩書摘
科舉停止,學堂競立,人心搖動。1905年,山西舉人同時亦是塾師的劉大鵬觀察到風氣已有替換,認為“下詔停止科考,士心渙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彆圖他業,以使子弟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由於前途不再,以教授舉業為主的學塾多有倒閉,塾師齣路堪虞。10月22日,劉大鵬在太榖縣城聚會,“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可謂觀感一緻。從11月日記開始,劉大鵬不斷記錄同行停業的消息,11月3日記“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記“頃聞同人失館者多”,次年3月19日記“去日在東陽鎮遇諸舊友藉舌耕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緻失館無他業可為”。
類似情形,在其日記中不斷齣現。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資印證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學子硃峙三也注意到:“縣市教書先生今春學生甚少,蓋各生傢庭均觀望城內新開之三堂小學也,紛紛問訊。”
該處小學堂所招學生,基本在十四歲以上,甚至三十多歲者亦有多人前來報考。《圖畫日報》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道清末上海新年齣現的新現象,稱:“新年已過學堂開,學子莘莘魚貫來。寶貴光陰休混擲,各將子弟快栽培。新學昌明舊俗除,不須香燭把誠舒。皮包一個攜將去,上課鍾鳴即讀書。講堂優禮謁先生,脫帽鞠將右手擎。不比昔時須下拜,磕頭習慣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訓濛,趙錢孫李教兒童。一心隻望新生至,開館收來贄見豐。”
【插圖一】
《開學堂》,《圖畫日報》第196號第7頁
一旦失去瞭“朝為田捨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稍有風吹草動,塾生也就可能棄學塾於不顧,或轉學到一般來說設學地點更為安全的學堂中去。艾蕪曾迴憶,“我的祖父和父親他們,對於讀書這一道,早已厭倦瞭,並不希望我在讀書方麵,有何成就。事實上,科舉既沒有瞭,讀好瞭書除瞭教學生而外,確也使他們看不齣讀書會有多大的齣息。他們不勉強我讀書,不鼓勵我發憤,我也就趁能偷懶的時候偷懶,馬馬虎虎地讀讀算瞭。心裏一點也沒有起過大誌嚮。”
影響所及,部分的傢塾、族塾及若乾同業公會所辦的學塾或改辦學堂,或直接停辦。例如,溫州“自學堂之設,嚮有之數十金、數百金之傢塾,皆不復存立”。族塾設立本意,以培養宗族人纔、振興宗族為宗旨,正如學者多賀鞦五郎指齣的“實際上宗族教育的目的並不是為瞭國傢、民族,它隻是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異族統治也好,族塾並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
但是,清末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宗族、同業公會等辦理的學塾也逐漸被納入國民教育體係,性質發生改變。宗祠等公所機構最為方便辦理學堂,是公私兩利,朝廷官員及報刊輿論都有一緻看法。
盡管不少民間學塾因為各種原因停閉,但學塾之於學堂,總體上看,優勢還是非常明顯。新知識人聲稱學堂的種種優越之處難以落實,而私塾諸多所謂難以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眾看來,卻並非問題。
新知識人認為,學堂是陶鑄國民的大工場。然而無論是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難以實現,隻是空談。一方麵,民眾未必認知自己肩負有“國民義務”,也不認為入學堂讀書是“義務”之舉。有人感嘆將“國民義務”這類觀念通過演說等手段灌輸給民眾之難,“你說的話若是程度稍微高一點,他們就不明白瞭。就讓是他明白,你說甚麼是愛國,甚麼保種的些話,他聽著也沒有甚麼旨味。久而久之,他們看著同講耶穌教一樣的,誰也不去聽瞭。”
即使同一陣營中的知識人,也不認同學堂是造就“國民”之地說法。1906年,王國維因丁憂迴籍浙江海寜,地方紳士上門請其擔任勸學所總董,謀劃學堂普及。王國維卻斷然拒絕,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員稱職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學校,如此之教員,欲以造就國民資格,蓋亦難矣。吾傢有兒童及學齡矣,寜委諸私塾,而不願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勸人?”
民眾對於興辦伊始的新式學堂,往往視其為固有的義學,是救濟貧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間就將初等小學等同於義學,認為是下流階層子弟的專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鄉知縣對鄉民演講的白話文可作印證:
本縣仰遵聖旨,要在桐鄉各村,並多設鄉學。已經會同學老師並紳士,籌集經費,挑選本地品性極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莊,教導你們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裏支送,不要你們再齣分文。從前逢年逢節應送先生禮物,現在也不一概要你們送格哉。……此番請的先生通是熱心熱腸,極肯用心教導的,決不像從前的義塾,有名無實瞭。……快把子弟送到學堂去讀書罷,快把子弟送到學堂去讀書罷!
知縣苦口婆心勸學,聲稱學堂的許多妙處,但在民眾看來學堂實際都與原有的義學運作非常類似。學堂教習“會同學老師並紳士”挑選而來,義學塾師也多是如此派定,學童傢長均無權主動參與選擇。學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節禮物,也是義學具有的慈善性。該知縣極力說明學堂“決不像從前的義塾,有名無實瞭”,恰好證明普通鄉民的確將“學堂”與義學對應。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內地各地情形如齣一轍。據餘傢菊迴憶,清季湖北黃陂“其時小學一切皆公費,且月給零用錢數百(文)。鄉人視為平民學校,多不肯入。”
1908年,直隸視學員調查武清縣的學務狀況,稱該縣大良鎮人民“知有義塾,而不知學堂之名稱”,下九百戶村人民“不知有學堂,並不樂聞學堂二字”。
次年,直隸的視學員注意到學堂與私塾學生精神麵貌截然不同,反應齣社會不同階層的分彆:“各私塾學生,氣象多秀靜者;官小學生,氣象多粗野者。風氣不開,於此可見矣。上中社會,皆以疾視學堂,寜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數日加多。中下社會,非不崇私塾,強令子弟入學堂,而學堂之人數日加少。”
新知識人認為,學堂所教授各種“科學”是營謀生活的最佳場所。實際辦理過程中,“科學”威力卻極為有限,以緻構成學堂形象負麵化的要因之一。劉大鵬式舊讀書人心目中,大多認為學堂“以科學為隨從洋人,有違聖教”,固然偏激,但他們對學堂教授的某些知識不滿,卻不能說毫無道理。劉大鵬1905年日記寫到“學堂者外洋各國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為,最重測算、技巧、格物一門工藝也。講求工藝之精巧,非吾人所謂格物,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學術之壞,不知伊於鬍底耳。”
他敏感體察齣新式學堂與中土學塾,教育理路存在差異。新式學堂注重實用,將知識分門彆類教授,不以一師為範圍,學生轉益多師,師道尊嚴大失。舊有學塾強調道德教育,單純的知識授受,僅是教育的一部分,學塾以一師為中心,所習以老師德行文章為模範,是所謂“師教”。兩種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長所短,並非一方絕對高明。不過,學堂初興,所謂“科學”大多流於錶淺,甚至買櫝還珠,在移植、傳播過程中變形,不僅可能失去原有精義,甚至格義附會,乃至謬種流傳。清末先讀傢塾,後入學堂的郭沫若後來迴憶,學堂課程極其零亂,“凡是新式課目與數學、格緻之類,教師都不能勝任。對於我自己在傢塾裏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他在小學堂、中學堂讀書時,感興趣的仍是固有的經學之類。由於學堂學風糟糕,他“開設接觸瞭人性的惡濁麵”、“自暴自棄,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郭沫若後來所讀四川嘉定中學堂,教學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開設的中學,更是一塌糊塗,笑話百齣。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甚至連講國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而講為“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幾個拼音就教瞭我們半年。在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養老。
即或學堂教授的“科學”較之民間學塾所學要精深高明,但多數學生畢業之後,其學問在社會生活中很難發生作用,成為無法實踐的屠龍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原南洋公學)齋務長陸瑞清撰寫《學生服勞說》一文,論說學堂學生不適應本土社會。新知識人對興學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時希望卻逐漸轉變為失望。文章首先指齣學堂雖未遍設,但數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數十矣,府各數百矣,其學童之列籍者更數韆數萬矣,民智稍稍開,科學稍稍具矣”。但是“試問國也族也傢也,其可免於亡焉、滅焉、喪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數也。”答案是“學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學堂風氣所緻,學生所學“科學間有精深,而豪華之意氣深印於腦紋,一見舊社會之狀態,皆以野蠻目之”。在畢業之後,難以得到社會認可,“某邑高等小學學生數十人,畢業後介紹入商。不三月,而盡行見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學堂學生為徒弟。某女學校之某某齣嫁後,不知烹飪、縫紉之職,而見惡於翁姑,貽笑於戚族。某鎮之人誓不娶女學生為媳。”陸瑞清建議,學堂課程應作改變,學生要從事勞作,“女子中學則於正課手工之外,加應用之縫紉、烹飪焉”。隻有這樣,學生畢業後“其能力足以應用,其見解足以識時,其處置得宜己,閤適者生存之公例,決不見絕於人群。”
這篇文章首先在《申報》刊齣,又在四川《廣益叢報》登載,兩年之後,還作為商務印書館所辦《教育雜誌》的“社說”齣現,其指齣的問題深中肯綮,又難以輕易解決。可見,清末的學堂多與普通人群相隔閡,見絕於實際社會生活。
無獨有偶,幾乎同時有名為董雲龍的北洋師範學堂學生上書當局,指陳普通鄉民仍送子弟入讀私塾,寜願廢學也不入學堂的緣故。他注意到,直隸寜河縣小學堂忽視學生的習字教育,所學的“算術”,僅停留在紙上作業的筆算,而不講習生活需要的珠算。學生畢業之後“寫不能寫,算不能算”,“其無力入中學者,欲就他種職業,每不免有所遺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經曆為例說明,最初教書時,以“讀書、習字、作文三必要”,但當地鄉下人情卻以“能寫能算”為尊貴,因此前來就讀的學生寥寥無幾。揣摩之後,“於三必要中特重習字,又創設珠算教授法”,來學者逐漸增多,年勝一年。
新知識人宣傳,塾生在私塾讀書多年,國文不通,學堂的成效較為明顯。然而,經過短暫實踐,情況恰好相反。1907年,《中國日報》有文章指齣廣東學堂中琳琅滿目的各科教學,實際隻有形式而無內容,“若夫所謂學堂者,則大率虛聲純盜,襲外貌而不計實功。新學既未貫通,舊學轉緻拋荒。其學科則貪多務得,以耀外觀,其章程中如物理、圖畫、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門,有如賽會。究其實,則教物理者多不通算術,教圖畫者隻閤兒戲,有學科而無教員,亦何必以多為貴也。”而私塾科目雖少,但至少語言文字教學基本過關,“夫尋常濛塾,如諺所謂子曰館者,其鬍鬧者固居其大多數,然亦不無認真訓迪,令兒童粗解國文。雖學科未備,新學欠缺,然通解國文,乃中國人之本務。”兩者對照,差彆明顯,“邇來小童入校數年,而國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濛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結論是小學堂學科應歸於簡易。
《中國日報》為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機關報,素持革命立場,撰文者當非守舊之人,其說法較具客觀性。這一觀察,多有旁證可資參證。1909年,京師舉行高等小學畢業考試,不僅“經學、國文無一佳捲”,而且“各堂學生於經學、國文殊少閤格”,最後追究原因,在於“均係教授未能認真之故”。
學生經學、國文程度急劇下降,鏇即引起督學局、學部注意。1909年,《教育雜誌》刊齣評論,報道揚州辦理學堂之人,卻不讓其子弟到學堂讀書的怪異現象,“某君言,正初返裏,偶遇學堂職員數人,談及學堂辦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學堂。群阻之曰,學堂絕無成效,萬不可進去。餘等非期君,餘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學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學堂之益者,聞言頗駭異。詰其故,答曰,學堂不主背誦,不施夏楚。君試思,讀書而不背誦,果能記憶乎?不施夏楚,學生果有畏懼乎?吾恐入學堂數年,將字亦不識矣。君疑我言乎?君試往吾校一觀即知其故矣。餘與君至好,故進此言,願留意焉。”
鄭超麟的後來迴憶,印證此事不假。他生於清末福建龍岩書香之傢,其幼年學習經曆是:“本縣已經有瞭官立小學堂(入民國後改名縣立小學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親是會計,是校産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沒有允許我們兄弟進學堂讀書。學堂已經畢業瞭甲、乙、丙、丁四班,我們和若乾同地位的人傢還在私塾讀書。”
1910年3月20日,《申報》“清談”欄目發錶時評稱:“人傢兒童,每有入學堂一二年,轉返而延師課讀者。此其何故歟?豈不以學堂教法未善,兒童之就學者,有紛心而無進步,其父兄乃翻然變計歟?凡有教育之責者奈之何弗思。”
作傢艾蕪迴憶自己經過在其祖父所開辦的私塾一年的學習,讀完瞭“四書”和《詩經》,“在鄉下人看來,一年能讀這麼多的書,那是比新式學堂劃算多瞭。在新式學堂至多隻能讀六本,兩本國文,兩冊修身,兩冊算術。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術在他們眼中,還不能算是書呢。”
學堂教學不主背誦,重視講解,對於理化科目的教學比較適閤,但對於漢語識字階段的教學而言,若不注意成誦,教學效率明顯不高。利用兒童機械記憶力強的特點,不斷重復、大量識字,是私塾在識字教學上比學堂高明的地方。
不僅在知識層麵,學堂脫離瞭本土社會,就是日常生活也體現齣有所區隔。作傢穆木天迴憶自己童年的經曆,對清末吉林學堂的惡感猶在,稱:“巡警隊與洋學生,這是當時的二橫。我永遠不忘的,就是那些學生好打人,就是軍警都怕他們呀。學校門口,掛著兩根紅漆的軍棍和四個虎頭牌子。所謂虎(頭)牌子者,是一個長方形的木闆,上邊是畫著一個橫橫勢勢的虎頭,下邊是四個紅圈圈,每圈裏是一個大大的黑字。那四個虎頭牌子上的字語是‘學堂重地,禁止喧嘩,倘敢故違,定行究辦。’每天,學生大概是不讀書,除一二一二地下體操而外,就是聚在門口,一邊吵鬧著,窺視著行人,如果有人走過來——當然,對士紳們,學生是不敢問津的——學生就開玩笑,說屁話兒,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靜而受之的話,那他們可真是要‘究辦’瞭。幾個學生按著,乒乓地就是二十軍棍啊!”比較起學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雖是寂寞,可是沒感受著苦楚”。
……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相當老道,它並沒有一味地沉溺於宏觀政治經濟環境的渲染,而是巧妙地將筆觸聚焦於教育載體——那些具體的、充滿煙火氣的場所。無論是那些在偏僻山村中搖搖欲墜的私塾,還是在省城拔地而起、氣派堂皇的新式學堂,每一個空間都被賦予瞭鮮明的文化代碼。作者似乎在用一種近乎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細緻,去描摹這些空間內的日常儀式:私塾先生的闆書與戒尺,新式學堂裏的鍾聲與軍訓口令。這種對“物質文化”的關注,極大地增強瞭閱讀的代入感。通過對這些物理空間的對比,讀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教育的革命不僅僅是課程的更換,更是對時間感、對知識權威、對師生關係的徹底顛覆。那種老派學問的“慢”與新式教育追求的“快”之間的較量,在字裏行間跳躍著,引人入勝。
評分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人物群像時的剋製與深刻。這部作品展現的教育之爭,絕不是“進步”與“落後”的簡單標簽戰,而是不同社會角色基於自身利益、文化信仰和生存策略所做齣的理性選擇。那些堅守私塾的老師,他們不僅僅是落伍的守舊派,他們更可能是傳統道德秩序的最後捍衛者;而那些投身新學堂的士紳子弟,他們的“進步”背後,往往夾雜著對功名路徑的重新規劃和對外部世界知識的渴望。作者沒有預設任何價值判斷,而是將這些人物置於一個巨大的曆史熔爐中,任由他們的動機與後果自行展開。讀罷掩捲,腦海中浮現的不是一個清晰的結論,而是一係列復雜的人物側影,他們都在各自的坐標係裏,試圖找到一條能讓自己和傢族安身立命的齣路,那種曆史的無奈感,撲麵而來。
評分這部關於近代中國教育變遷的著作,以其深厚的史料挖掘和獨到的分析視角,為我們打開瞭一扇通往那個風雲變幻時代的窗口。作者似乎並未滿足於簡單的事件羅列,而是深入探究瞭傳統與現代在教育理念、教學內容乃至社會功能上的激烈碰撞。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對於地方性知識體係如何在宏大敘事中被重塑或消解的描繪。那種滲透在鄉村社群、傢族傳承中的非正式教育脈絡,在麵對自上而下推行的標準化、國傢化的學堂體係時,展現齣的那種既抵抗又妥協的復雜張力,被刻畫得淋灕盡緻。尤其是在探討特定地域的精英階層如何權衡利弊,決定是堅守舊規還是擁抱新製時,那種人性的掙紮和時代洪流的必然性交織在一起,讀來令人深思。它不像某些教科書那樣把曆史事件描繪得涇渭分明,而是充滿瞭灰度的敘事,讓人感覺曆史的肌理是如此的粗糲而真實。
評分這部著作最打動我的一點,是它對“中斷”與“連續”的辯證思考。近代中國的教育變革,常常被描述為一次徹底的斷裂,將舊時代一筆勾銷。然而,作者的敘述卻揭示瞭遠比想象中更為微妙的“縫閤”過程。新舊體係並非完全水火不容,它們之間存在著大量“混閤體”——一些新式學堂依然保留瞭舊式私塾的某些管理習俗,而一些頑固的私塾也在悄悄引入新課本的某些片段。這種在夾縫中生存、在適應中轉化的生命力,恰恰是曆史的常態。它提醒我們,社會變革不是簡單的開關切換,而是一個漫長而充滿矛盾的“混閤發酵”過程。這種對曆史復雜性的尊重,使得這部作品的價值遠遠超越瞭單純的曆史記錄,成為瞭一部關於文化適應與身份重塑的深刻寓言。
評分從文本結構上來看,這部作品的史學功力令人信服。它顯然是建立在對海量檔案、地方誌甚至傢族信劄的細緻爬梳之上的,但令人稱道的是,作者成功地將這種學術的厚重感轉化為一種流暢易讀的敘事。他善於運用類比和隱喻,將原本枯燥的製度變遷講述得富有張力。例如,他對於“教材”這一媒介的討論,就顯得尤為精妙。私塾裏世代相傳的《三字經》與學堂中開始推行的地理、算術課本,它們所承載的“世界觀”之間的鴻溝,被作者描繪得如同橫亙在兩個世紀之間的深淵。這種對知識載體的深入剖析,超越瞭單純的教育史範疇,觸及到瞭文化霸權轉移的核心議題,讓我對知識如何塑造國民性有瞭更深一層的理解。
在萬聖書園看到這本書的,後來網上買瞭,個人研究這個
評分書不錯,喜歡文史的朋友可以看看!!
評分經典之作,值得一讀再讀!
評分包裝嚴實,書籍完好,滿意的一次購物。
評分經典之作,值得一讀再讀!
評分教育的變遷,曆史的滄桑。
評分書很好,看瞭之後會感覺又學到瞭很多東西
評分書可以,就是為什麼裏麵有夾頁,而且兩邊的都有些損壞,是二手的吧??
評分給力,太給力瞭,好東西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