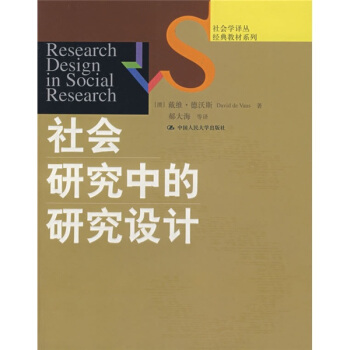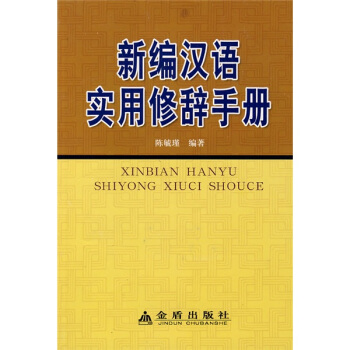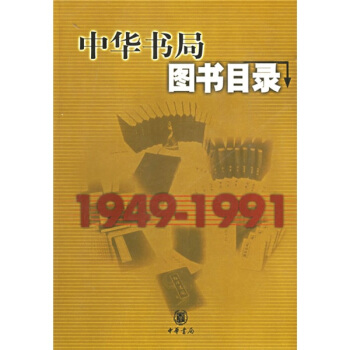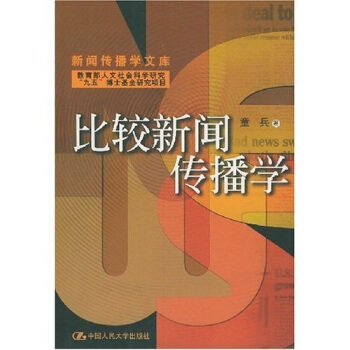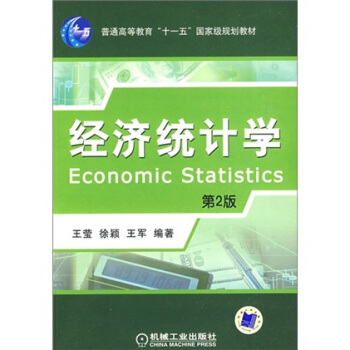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在追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应该重视借鉴世界普遍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否定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国经验”。书中的这段历史昭示了,中国固有的私塾教育确实有不少弊端与不足,但也有与中国基层社会实情相契合的一面;外来的学校制度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可能橘化为枳,应尽力找到实现两者优势互补的新途径。
内容简介
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本书不以成败的标准倒叙与评价历史,也不发思古之幽情,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作者简介
左松涛,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15—2016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访问学者,著有《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五册)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精彩书摘
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插图一】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
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之举。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说法。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
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
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
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所教授各种“科学”是营谋生活的最佳场所。实际办理过程中,“科学”威力却极为有限,以致构成学堂形象负面化的要因之一。刘大鹏式旧读书人心目中,大多认为学堂“以科学为随从洋人,有违圣教”,固然偏激,但他们对学堂教授的某些知识不满,却不能说毫无道理。刘大鹏1905年日记写到“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人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他敏感体察出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不过,学堂初兴,所谓“科学”大多流于表浅,甚至买椟还珠,在移植、传播过程中变形,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精义,甚至格义附会,乃至谬种流传。清末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后来回忆,学堂课程极其零乱,“凡是新式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他在小学堂、中学堂读书时,感兴趣的仍是固有的经学之类。由于学堂学风糟糕,他“开设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郭沫若后来所读四川嘉定中学堂,教学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
即或学堂教授的“科学”较之民间学塾所学要精深高明,但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其学问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发生作用,成为无法实践的屠龙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斋务长陆瑞清撰写《学生服劳说》一文,论说学堂学生不适应本土社会。新知识人对兴学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时希望却逐渐转变为失望。文章首先指出学堂虽未遍设,但数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数十矣,府各数百矣,其学童之列籍者更数千数万矣,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矣”。但是“试问国也族也家也,其可免于亡焉、灭焉、丧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数也。”答案是“学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学堂风气所致,学生所学“科学间有精深,而豪华之意气深印于脑纹,一见旧社会之状态,皆以野蛮目之”。在毕业之后,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陆瑞清建议,学堂课程应作改变,学生要从事劳作,“女子中学则于正课手工之外,加应用之缝纫、烹饪焉”。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其能力足以应用,其见解足以识时,其处置得宜己,合适者生存之公例,决不见绝于人群。”
这篇文章首先在《申报》刊出,又在四川《广益丛报》登载,两年之后,还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杂志》的“社说”出现,其指出的问题深中肯綮,又难以轻易解决。可见,清末的学堂多与普通人群相隔阂,见绝于实际社会生活。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有名为董云龙的北洋师范学堂学生上书当局,指陈普通乡民仍送子弟入读私塾,宁愿废学也不入学堂的缘故。他注意到,直隶宁河县小学堂忽视学生的习字教育,所学的“算术”,仅停留在纸上作业的笔算,而不讲习生活需要的珠算。学生毕业之后“写不能写,算不能算”,“其无力入中学者,欲就他种职业,每不免有所遗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经历为例说明,最初教书时,以“读书、习字、作文三必要”,但当地乡下人情却以“能写能算”为尊贵,因此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揣摩之后,“于三必要中特重习字,又创设珠算教授法”,来学者逐渐增多,年胜一年。
新知识人宣传,塾生在私塾读书多年,国文不通,学堂的成效较为明显。然而,经过短暂实践,情况恰好相反。1907年,《中国日报》有文章指出广东学堂中琳琅满目的各科教学,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若夫所谓学堂者,则大率虚声纯盗,袭外貌而不计实功。新学既未贯通,旧学转致抛荒。其学科则贪多务得,以耀外观,其章程中如物理、图画、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门,有如赛会。究其实,则教物理者多不通算术,教图画者只合儿戏,有学科而无教员,亦何必以多为贵也。”而私塾科目虽少,但至少语言文字教学基本过关,“夫寻常蒙塾,如谚所谓子曰馆者,其胡闹者固居其大多数,然亦不无认真训迪,令儿童粗解国文。虽学科未备,新学欠缺,然通解国文,乃中国人之本务。”两者对照,差别明显,“迩来小童入校数年,而国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蒙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结论是小学堂学科应归于简易。
《中国日报》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素持革命立场,撰文者当非守旧之人,其说法较具客观性。这一观察,多有旁证可资参证。1909年,京师举行高等小学毕业考试,不仅“经学、国文无一佳卷”,而且“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最后追究原因,在于“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
学生经学、国文程度急剧下降,旋即引起督学局、学部注意。1909年,《教育杂志》刊出评论,报道扬州办理学堂之人,却不让其子弟到学堂读书的怪异现象,“某君言,正初返里,偶遇学堂职员数人,谈及学堂办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学堂。群阻之曰,学堂绝无成效,万不可进去。余等非期君,余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学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学堂之益者,闻言颇骇异。诘其故,答曰,学堂不主背诵,不施夏楚。君试思,读书而不背诵,果能记忆乎?不施夏楚,学生果有畏惧乎?吾恐入学堂数年,将字亦不识矣。君疑我言乎?君试往吾校一观即知其故矣。余与君至好,故进此言,愿留意焉。”
郑超麟的后来回忆,印证此事不假。他生于清末福建龙岩书香之家,其幼年学习经历是:“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丁四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的人家还在私塾读书。”
1910年3月20日,《申报》“清谈”栏目发表时评称:“人家儿童,每有入学堂一二年,转返而延师课读者。此其何故欤?岂不以学堂教法未善,儿童之就学者,有纷心而无进步,其父兄乃翻然变计欤?凡有教育之责者奈之何弗思。”
作家艾芜回忆自己经过在其祖父所开办的私塾一年的学习,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在乡下人看来,一年能读这么多的书,那是比新式学堂划算多了。在新式学堂至多只能读六本,两本国文,两册修身,两册算术。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术在他们眼中,还不能算是书呢。”
学堂教学不主背诵,重视讲解,对于理化科目的教学比较适合,但对于汉语识字阶段的教学而言,若不注意成诵,教学效率明显不高。利用儿童机械记忆力强的特点,不断重复、大量识字,是私塾在识字教学上比学堂高明的地方。
不仅在知识层面,学堂脱离了本土社会,就是日常生活也体现出有所区隔。作家穆木天回忆自己童年的经历,对清末吉林学堂的恶感犹在,称:“巡警队与洋学生,这是当时的二横。我永远不忘的,就是那些学生好打人,就是军警都怕他们呀。学校门口,挂着两根红漆的军棍和四个虎头牌子。所谓虎(头)牌子者,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边是画着一个横横势势的虎头,下边是四个红圈圈,每圈里是一个大大的黑字。那四个虎头牌子上的字语是‘学堂重地,禁止喧哗,倘敢故违,定行究办。’每天,学生大概是不读书,除一二一二地下体操而外,就是聚在门口,一边吵闹着,窥视着行人,如果有人走过来——当然,对士绅们,学生是不敢问津的——学生就开玩笑,说屁话儿,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静而受之的话,那他们可真是要‘究办’了。几个学生按着,乒乓地就是二十军棍啊!”比较起学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虽是寂寞,可是没感受着苦楚”。
……
用户评价
这部著作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对“中断”与“连续”的辩证思考。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常常被描述为一次彻底的断裂,将旧时代一笔勾销。然而,作者的叙述却揭示了远比想象中更为微妙的“缝合”过程。新旧体系并非完全水火不容,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混合体”——一些新式学堂依然保留了旧式私塾的某些管理习俗,而一些顽固的私塾也在悄悄引入新课本的某些片段。这种在夹缝中生存、在适应中转化的生命力,恰恰是历史的常态。它提醒我们,社会变革不是简单的开关切换,而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矛盾的“混合发酵”过程。这种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使得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记录,成为了一部关于文化适应与身份重塑的深刻寓言。
评分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人物群像时的克制与深刻。这部作品展现的教育之争,绝不是“进步”与“落后”的简单标签战,而是不同社会角色基于自身利益、文化信仰和生存策略所做出的理性选择。那些坚守私塾的老师,他们不仅仅是落伍的守旧派,他们更可能是传统道德秩序的最后捍卫者;而那些投身新学堂的士绅子弟,他们的“进步”背后,往往夹杂着对功名路径的重新规划和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渴望。作者没有预设任何价值判断,而是将这些人物置于一个巨大的历史熔炉中,任由他们的动机与后果自行展开。读罢掩卷,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一个清晰的结论,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人物侧影,他们都在各自的坐标系里,试图找到一条能让自己和家族安身立命的出路,那种历史的无奈感,扑面而来。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相当老道,它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渲染,而是巧妙地将笔触聚焦于教育载体——那些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场所。无论是那些在偏僻山村中摇摇欲坠的私塾,还是在省城拔地而起、气派堂皇的新式学堂,每一个空间都被赋予了鲜明的文化代码。作者似乎在用一种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细致,去描摹这些空间内的日常仪式:私塾先生的板书与戒尺,新式学堂里的钟声与军训口令。这种对“物质文化”的关注,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代入感。通过对这些物理空间的对比,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教育的革命不仅仅是课程的更换,更是对时间感、对知识权威、对师生关系的彻底颠覆。那种老派学问的“慢”与新式教育追求的“快”之间的较量,在字里行间跳跃着,引人入胜。
评分这部关于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著作,以其深厚的史料挖掘和独到的分析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窗口。作者似乎并未满足于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深入探究了传统与现代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乃至社会功能上的激烈碰撞。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于地方性知识体系如何在宏大叙事中被重塑或消解的描绘。那种渗透在乡村社群、家族传承中的非正式教育脉络,在面对自上而下推行的标准化、国家化的学堂体系时,展现出的那种既抵抗又妥协的复杂张力,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在探讨特定地域的精英阶层如何权衡利弊,决定是坚守旧规还是拥抱新制时,那种人性的挣扎和时代洪流的必然性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深思。它不像某些教科书那样把历史事件描绘得泾渭分明,而是充满了灰度的叙事,让人感觉历史的肌理是如此的粗粝而真实。
评分从文本结构上来看,这部作品的史学功力令人信服。它显然是建立在对海量档案、地方志甚至家族信札的细致爬梳之上的,但令人称道的是,作者成功地将这种学术的厚重感转化为一种流畅易读的叙事。他善于运用类比和隐喻,将原本枯燥的制度变迁讲述得富有张力。例如,他对于“教材”这一媒介的讨论,就显得尤为精妙。私塾里世代相传的《三字经》与学堂中开始推行的地理、算术课本,它们所承载的“世界观”之间的鸿沟,被作者描绘得如同横亘在两个世纪之间的深渊。这种对知识载体的深入剖析,超越了单纯的教育史范畴,触及到了文化霸权转移的核心议题,让我对知识如何塑造国民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评分京东的品质值得信赖,加上活动给力!
评分有点用处
评分给力,太给力了,好东西
评分书真的很棒,感觉可以提高我的学术水平
评分很棒的书,羡慕已久,今天终于拿到手,很喜欢,会和家人一起阅读,度过美好时光。
评分书可以,就是为什么里面有夹页,而且两边的都有些损坏,是二手的吧??
评分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
评分经典之作,值得一读再读!
评分教育的变迁,历史的沧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