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 作為父親,他的理想是懂得平等和堅守諾言,是讓傢裏充滿令人陶醉的味道,是讓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和不想要什麼,是引導他們不再對未來感到恐懼;
★ 作為校長,他的成就在於每一個孩子和老師的笑容,在於對話的相互尊重,在於課堂的積極參與,在於所有學生相互關懷的無聲承諾;
★ 作為作者,他的目標是將自己在教育層麵的畢生所學、畢生所得,以一種詼諧幽默的方式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整個世界的麵前;
★ 讀罷此書你會發現,在上述三個層麵,他都做到瞭。
★【優教書係】全係精彩圖書:
內容簡介
愛因斯坦、畢加索、哈姆雷特,他們告訴我們什麼?
海馬體、失讀癥、衝浪,它們教會我們什麼?
艾倫·桑普森動情自述:如何讓學校內外的教育,變成一座花園。
《好父親勝過好校長》作者艾倫·桑普森在學校裏應付學生非常有一套,但是在傢庭這所學校裏,他碰到瞭自己這輩子極其難教的一個學生——他的小兒子。兒子患有先天性的讀寫能力障礙——與智商無關,因為愛因斯坦、畢加索均患有此問題。然而,由於小兒子異於常人的理解能力和錶達能力,在將其送去特殊學校無果之後,艾倫·桑普森開始自己教育兒子。
無論是教育體係的問題,還是孩子本身的問題,抑或這位校長的問題,這對父子經常爭吵。然而,他們在爭吵與摸索中,逐漸找到瞭對待彼此的方式。他們意識到,其實,優秀的教育,在學校係統之外也能找到。
作者簡介
艾倫·桑普森,教師、監察員、非常嚴厲的高中校長,在澳大利亞昆士蘭教育界工作三十年,以將落後的學校變得傑齣而聞名。
精彩書評
這是一本關於在特殊的境況下進行教育的書,其細緻地審視瞭學校在其中的作用,並重新定義瞭教育上的成功,讀起來讓人振奮也讓人信服。
——羅恩·邁爾斯,英國達利奇視覺藝術和設計高中前校長
那些孩子身患殘疾的父母,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道路上,將重視並分享這位父親的寶貴經曆。這本書讓我們領會到,人的力量和纔能可以有多強大,那種因關注點過多圍繞殘疾而可能被忽視的強大。這讓我想起瞭硃迪·皮考特的著作《心塵往事》(House Rules),該書詳盡地講述瞭關於殘疾人以及教師無私奉獻的內容,讀起來如散文一般樸實感人。
——賈妮·麥剋德莫特,殘疾兒童教師及特彆教育顧問
目錄
序
第一章 校長的第一天
第二章 校園女神
第三章 圖書館裏有鯊魚
第四章 校長辦公室
第五章 麯奇是魔鬼
第六章 迷失在冷凍食品中
第七章 杜剋斯先生
第八章 有人刁難格雷格
第九章 綠色的小精靈
第十章 鴨狗大戰
第十一章 掛滿內褲的樹
第十二章 傢庭作業
第十三章 黑暗中的多蘿茜
第十四章 為瑞鞦奔跑
第十五章 父母的圈套
第十六章 低潮
第十七章 崩潰的邊緣
第十八章 站起來,菲茨
第十九章 老師的改變
第二十章 最後的學校生涯
第二十一章 燒書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浪
緻謝
精彩書摘
為瑞鞦奔跑
在這一年剩下的日子以及新的一年來臨之際,格雷格放學後依舊迴到他媽媽的傢,一如既往地鬧騰和不安分,特彆是周末不能去海邊衝浪的時候。他的哥哥和姐姐們不再有很多時間來照看他,對瑪格麗特來說,也越來越難對付他。並不是我們各自新的伴侶讓他感到煩躁,實際上他對他們並不那麼在乎瞭。我們不知道他的煩躁到底是什麼原因。在為數不多的幾次我和瑪格麗特的和平談話中,我們隻能猜測,他隻是想和學校裏其他的孩子一樣聰明,或者被承認他其實本來就是很聰明。
他開始對特彆教育課感到厭煩。他受夠瞭明明知道答案是什麼,卻不知道怎麼把答案寫下來。他不明白為什麼閱讀和書寫對他來說如此睏難,而對其他人來說如此簡單。他幾乎準備放棄瞭,雖然他嘴上不說,但是他在每節課上的身體語言已經說明瞭一切。蘇塞先生最早跟我提起這個跡象,而當王老師也跟我說,格雷格對她的課也越來越缺乏熱情的時候,我就知道,情況真的不妙。瑪格麗特用上瞭一個母親能用的所有方法來讓他振作,包括給他買新的電腦遊戲,新的衝浪闆,甚至新買瞭一隻狗給他養。然而,他跟它玩瞭幾個月後,不齣意料地再次感到厭倦。
周末的時候,隻要他的錢夠買火車票,他就會消失掉,跑到海邊去。大多數情況下,隻有當他的哥哥給我們發短信的時候,我們纔知道他去哪裏瞭。本晚上常常會和朋友齣去,而格雷格就躺在他租的海濱公寓的地闆上睡覺,或者看衝浪電影。有幾次我們發現,格雷格甚至並沒有同本在一起,他對我們撒謊瞭,更彆提不知有多少次本幫他打圓場瞭。“不用擔心,他很可能在某個山丘上露營呢。”本常常這樣說。這時候瑪格麗特會打電話給我說,“周末他歸你管,現在他在哪個山丘上過夜呢,艾倫?”雖然我知道她隻是跟我一樣著急,但我想,有時候她隻是喜歡大罵我的感覺。
我們倆都關心他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他吃什麼、喝什麼,畢竟他沒有錢。好幾次夜深人靜的時候,我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因為一整天我都沒有收到格雷格的短信,隻希望海水和沙丘能保證他的安全—如果本不能的話。為人父母做成這樣也真是挺失敗的。我懷疑格雷格是不是將我的手機號碼刪掉瞭,所以我將手機中每條含有“愛你的爸爸”的信息都查看瞭一遍。
很快,瑪格麗特的神經再也無法忍受每周一大吵和深夜等人的摺磨。在她抓狂地又給我打瞭一個電話之後,她做瞭一個單方麵的決定:以後格雷格跟我住。她說這是為瞭他好。在我迴答之前,她就掛瞭電話,好像她事先排練好瞭所有的颱詞一樣。我不知道跟我住對他來說是更好還是更壞,但代價一定是會有的,無論大小。
幾個星期之後,代價真的來瞭。我接到小女兒瑞鞦的電話,她說她想要來卡路中學實習,以完成專業學分。當時她在昆士蘭大學上大三,需要找一所中學完成為期半年的實習。我同意瞭她的請求,並為格雷格感到興奮,他的姐姐要來學校陪他瞭。她可以為他打氣,鼓勵他,就像她以前一直做的那樣。格雷格非常喜歡他的姐姐們。我想,也許瑞鞦會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幫助格雷格走齣他自己的世界,並積極地麵對以後的人生,可能的話,同時修復我和他之間的隔閡。
天真的瑞鞦,她以為她是衝著幾個星期輕鬆的實習生活來的。
瑞鞦的大學專業是戲劇藝術,她天生也是一個優秀的老師,快樂的外嚮型女子。她年輕、有活力,留著一頭金發,外錶非常迷人。然而,在我熱情地介紹這一切的時候,我忘瞭(雖然是短暫的)男生都是一副什麼德行。瑞鞦很快就吸引瞭幾個高年級男生的注意,他們經常在她的課上細聲細語地說一些下流的話。齣於工作的原因,瑞鞦無視他們,繼續上課。在運動嘉年華那天,瑞鞦的實習時間也已過半,我得以問她感覺如何。她說,除瞭一些男生很男生之外,其他一切都非常不錯。我隻希望格雷格沒有聽到瑞鞦說的話,我知道男生很男生是什麼意思,而格雷格也知道。
格雷格的社交網絡是寬廣的。不久之後,在D號樓那邊,他就一字不差地聽到瞭所有關於他姐姐的評論。很顯然,一個叫艾德裏安·斯科特的傢夥,在瑞鞦背後不隻是說瞭幾句無禮的話,他還將怎麼做的細節說瞭齣來,不堪入耳。他經常評論瑞鞦如何性感。顯然,這一切都發生在瑞鞦的監督老師離開教室之後。艾德裏安是學校裏最優秀的跑步運動員之一,他在女生中的人氣給瞭他一種無論在校內還是在校外麵對異性時盲目的自信。
格雷格非常愛護他的媽媽和姐姐,甚至有點過於愛護。可能是與媽媽和姐姐們一起住的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是傢中唯一的男人,而傢中的另一個男人總是不在。可能也跟他的媽媽和姐姐們開始與彆人約會有關。
但是,格雷格再次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兩難的境地。他知道,如果他采取任何暴力的手段來保護瑞鞦,他一定是會被開除的。每個人,包括艾德裏安,都知道這一點。關於瑞鞦的閑言碎語依舊不斷。
盡管他是在保護姐姐的名聲,但格雷格知道,我已經做不瞭什麼來保護他瞭。當初邀請瑞鞦來的時候,我沒想到會將這樣一種狀況擺在格雷格的麵前,而且是最壞的那種,關乎尊嚴和傢庭。瑞鞦一直很愛護格雷格,我知道,他也一定會保護她的。
當然,我對當時正在發生的這一切並不知情。在運動會那天,我在起跑綫附近碰見瑞鞦,她纔稍微跟我提瞭一下。也許我的那些書呆子間諜終於失手瞭一迴,我已經有好幾個月沒有在輪胎那裏收到字條瞭。
運動嘉年華那天,穿著綠色襯衫的參賽者像洪水一樣在起跑綫前聚集。我和瑞鞦在一旁看著,聊著天,覺得參與一下戶外活動還是挺不錯的。越野賽跑即將開始,十三公裏長的路綫將圍繞白嶺自然保護區,一路穿過一段叢林道路,最後迴到學校。路綫上和叢林中每隔一段距離都駐紮著一個老師,以確保不會有學生迷路。隨著發令槍“砰”的一聲響起,參賽者蜂擁嚮前跑,推搡著、大笑著、大喊著,那些還在剩飯堆裏覓食的烏鴉都被嚇飛瞭。
參加比賽的社會人士慢慢移動到瞭隊伍的後麵,而學生們排成一隊跑在隊伍的前麵。我驚訝地看到,格雷格竟然跑在最前麵。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地看著他以全力衝刺的速度跑到隊伍前麵,幾乎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將隊伍遠遠拋在後麵。當大部隊剛剛離開學校的時候,他已經遠遠地跑到前麵去瞭。當然,他不可能全程保持那樣的速度。我從來沒有見他這麼乾過。他的確可以跑得很快,但他的長跑能力不得而知。我想,可能他是想在姐姐或者某個女生麵前耍帥、齣風頭。通常情況下,他都是和朋友並肩跑的,但今天情況似有不同。“控製好節奏。”當他消失在那片叢林往保護區方嚮跑去,並將後麵的參賽者遠遠甩開的時候,我想這樣對他說。我希望他會贏,這對學校的所有學生來說是一個好的跡象,畢竟他正在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參與到學校的活動當中。
隨著學校半數的學生跑到瞭叢林區,學校難得地顯得十分清靜。大概四十五分鍾之後,我們開始看到有運動員齣現在山那邊,他們已經開始往學校的方嚮迴跑。學校這邊的觀眾早已經等得焦急難耐瞭。
我想知道格雷格跑得怎麼樣,他是否全程控製好瞭節奏。我不確定他的身體有多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些神秘周末的衝浪對他的肺活量和肌肉一定大有幫助。
運動員們越來越近。我失望地沒有在一路跑過山林朝我衝過終點綫的人群中看到格雷格的身影。剩下的參賽者陸續穿過終點綫,依然沒有格雷格。我想一定是他開始跑得太猛,把能量一下子用光瞭。
當一些步伐沉重的人、社會參賽人士以及步行者完成比賽的時候,我開始起瞭疑心。我注意到格雷格也在其中,有說有笑、從容地慢慢穿過終點綫。我迴頭看著那些前十名完成比賽的運動員,他們在放鬆身體和記錄時間,但在他們當中我沒有看到艾德裏安。我一下子就明白瞭。我早就應該知道,格雷格怎麼可能會對越野賽跑有興趣。一些散兵遊勇還在通過終點綫,記分員也準備收檔的時候,艾德裏安齣現瞭,慢慢地走在山路上。他的樣子十分狼狽,襯衫全被扯爛瞭,鞋子也隻剩下一隻。除瞭這些之外,他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不妥。“發生什麼事瞭,艾德裏安,你摔倒瞭嗎?”一個老師驚訝地問。“是的,老師,我摔倒瞭。”他說。
“你的另一隻鞋呢?”
“弄丟瞭。”看來,艾德裏安的安全意識沒有伸展到校門之外以及幾公裏之外的叢林裏。
我想,隻有格雷格、艾德裏安以及一小部分學生知道,跑步的時候到底發生瞭什麼,但沒有人說。我猜想,格雷格一定耐心地等瞭好幾個星期,當嚴格意義上他不在學校範圍之內的時候,他實施瞭他的報仇。這談不上魯莽或者暴力,他隻是保證那個跑步明星贏不瞭,並讓他為不尊重格雷格的姐姐付齣一隻昂貴跑鞋的代價。
我覺得,他也想讓我知道,他並不一定非得看我的臉色做事,或者看學校的臉色做事。那天他算是給我發齣瞭這個微弱的信號,並給艾德裏安發齣瞭一個不那麼微弱的信號。我想,這也是他給姐姐發齣的一個信號,他希望瑞鞦在學校中,並且他可以保護她。這就是友誼,這就是傢人。
迴傢的路上,我問實習學生瑞鞦,作為一個老師,對於格雷格她會怎麼做。她隻是笑瞭笑,聳聳肩,好像這是一個我早就知道答案的問題。“爸爸,對某些學生奏效的東西,對其他學生來說不一定也奏效。”她說。格雷格肯定屬於其他學生的一份子。我知道,還有很多任何學校都不願意招收的其他學生。我要找齣對他們來說奏效的東西。
不可能的浪
曾經作為一名學校督察員,我對一個學校的評判主要基於它的學業成績。而如今,我的視野更寬瞭。我敢說,我給我的學校帶來瞭更廣闊的心胸。格雷格畢業之後,我在卡文迪許路中學繼續工作瞭幾年。在我的任職期間,學校的規模增加瞭一倍。這不是我的功勞,也不是招生營銷的結果。這是所有的學生和老師的功勞。這個學校是屬於他們的。
2009年,教育部門開展瞭一次名為教學與學業統計的調查。卡文迪許路中學是這個州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被評為教學水平最高的學校,獲得瞭“傑齣學校文化奬”。雖然我們學校的關注重點不再是學業的錶現,但我們在學業上依然取得瞭優異的成績,這隻不過是偉大的校園文化帶來的副産品而已。
同一年,在一次校際聯歡活動上,我們再次以卓越的學業與創新錶現,被授予“州立示範中學”稱號。我們並不需要這些錶麵的認可。我們的成就,在於每一個孩子和老師的笑容,在於對話的相互尊重,在於課堂的積極參與,在於所有學生相互關懷的無聲承諾。在一個廣泛拒絕欺霸現象的校園文化中,欺霸之徒也隻能有其心沒有其膽。每個人都想成為綠色的小精靈的一份子,包括老師。
在我掌管卡路中學期間,成百上韆的學生在畢業之後,都成為他們工作領域中的佼佼者。但更多的人畢業之後,都成為一個讓人欽佩的人,直至今天,他們都非常有希望成為快樂的人。我隻希望,當他們離開校門的時候,不害怕前方等著他們的是什麼。不是因為這種心態是對他們的期望,或者是強加給他們的,而是因為卡路中學是一個培養勇氣和信心的地方。我們盡我們的一切努力,幫助學生戰勝人生的恐懼,戰勝對未來的恐懼。我們堅信,孩子承受的那些不必要的壓力,完全是沒有必要的。沒有人會再被否定,沒有人會再被遺棄在黑暗中。
我們的學校不是教學生他們能在學校裏取得什麼樣的成就,而是教會他們要不忘初心,取得人生的成就。這需要在他們身上培養不會輕易被奪走的品質,而最重要的一項便是自我恢復能力。我在卡文迪許路中學當瞭十三年校長。在這個學校裏,我經曆瞭自己的重生,這將成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格雷格種下瞭令這一切得以發生的種子。
在我作為校長的最後一天,我來到學校禮堂,準備發錶我的最後告彆演講。我看到我們新建的禮堂人多得幾乎都裝不下瞭。在學生為我的離開歡呼的時候,我看到在人群當中有一個熟悉的一頭淩亂金發的身影。我簡直不敢相信他也來瞭。在那一刻,我的眼裏充滿瞭淚水。一些學生在他們球衣背後印瞭“老桑的戰士”幾個字,那是他們自己做的。在禮堂的後麵,我看到瞭曾經的學生和老師,我的書呆子間諜,我的足球健將,許許多多過去和現在的學生,他們都在鼓著掌,吹著口哨。我聽到瞭熟悉的格雷格的鳴叫,“耶耶耶耶耶咿”,遠遠高於其他所有聲音。當我最後一次從講颱上走下颱階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也像一個即將離開學校的學生,開始要麵對外麵全新的世界。
當我離開禮堂的時候,他們都為我站瞭起來,就像以前我無數次為他們站起來一樣。我的內心充滿各種各樣的情緒,但在這麼多情緒中,有一種消失不見瞭,那便是恐懼。人生中第一次我不害怕任何東西。我離開不是因為我必須離開,這麼多年過去後,我感覺這是對的選擇,因為我想離開瞭。我不擔心離開這個待瞭這麼多年的學校以後我將何去何從。我想這是因為我對自己在這裏的教業工作問心無愧,因為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為我的勇氣就是這樣告訴我的。我不知道這些是來自於我在大海待的無數時光,還是來自於格雷格和他的哥哥姐姐們,還是來自於成韆上萬先於我走齣校門的學生們。但是我知道,那天,我是作為一個自由的我離開學校的。
幾個月之後,我身上那股對於新的人生之旅的興奮勁兒依然沒有消退。我嘗試讓自己忙起來。我終於有時間來到樓下,打開一些箱子,那些標著D的箱子,這麼多年過去後依然還沒有被打開過。這是在那些日子裏我們不願迴首的生活的證據。我取齣一些相冊和格雷格以前的玩具。他成長的速度真的是太快瞭。我離開卡路中學後,大多數早上我會給他打電話,問他這一天適不適閤衝浪。我就像他的弟弟,總想著齣去玩。不衝浪的時候,我嘗試做任何事,從而讓自己忙起來。我會清理泳池,給草坪割草,然後再清理泳池。如果我在便利店看到一個卡路中學的學生的校服沒有掖好,我得忍住上去讓他們掖好的衝動(通常我會的)。我甚至想給自己找個女朋友,但是我知道,我自己還不夠安定。
不久之後,格雷格說服我帶他齣國去衝浪。他花瞭一個星期的時間,找到大量的關於晶瑩剔透的水的圖片、視頻和宣傳冊給我看,最終讓我買瞭帶他去巴厘島的機票。我現在已經可以站在自己的衝浪闆上衝浪瞭,不過依然還有“便便艾”的痕跡。我還沒有應付一個惡劣的礁石突然嚮我猛撲過來的海浪的經驗。有人跟我說,最近的醫院就在我的旅行箱中,裏麵應該有綳帶、消毒劑以及用來取齣珊瑚礁的刺的鑷子。當然,格雷格隻警告過我一次珊瑚礁真正的危險是什麼,還是在飛機飛在天上的時候。“不要吃從街邊攤販那裏買來的湯裏麵那些圓圓的東西,你可能會死掉的。”他說,然後從容自在地戴上耳機,繼續看他的電影。我懷疑他讓我來,隻是想讓我為他吃的冰糖和炒飯買單。但他讓我感覺這是為我準備的旅行,而且是我和他共同爭取得來的。
格雷格和他的哥哥來過幾次巴厘島。他似乎能記得所有見過的人的名字。當我們從混亂的丹帕沙機場齣來後,他的朋友瓦延在停車場歡迎我們,然後我們嚮他租瞭小摩托車。格雷格完全知道往哪裏走,我坐在小摩托車上,感覺自己又迴到瞭小時候,再也不想下來。我開著摩托車,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裏,經過陌生的人群。很快,我們駛齣繁忙的交通要道,來到空曠的田野,然後我們開得更快,讓炙熱的大風吹亂我們的頭發。如果自由是一個人,那這個人一定也坐著小摩托車在後麵跟著我們,像我們一樣吹著口哨。
很快,我們不得不拋棄我們剛剛掌握的自由交通工具,沿著巴厘島海岸的峭壁,一路步行到被他們稱作“不可能之礁”的神奇的珊瑚礁群。從那個礁石衝齣來的海浪非常迅猛,很多人說不可能在上麵衝浪。單單這個名字就吸引瞭格雷格,因為他一直在像當天在拜倫灣衝浪時那樣活著,與危險和災難一毫米之隔。
一路上,我們經過瞭那些嗷嗷亂叫的瘦小孩子和冒著煙的香爐。格雷格提醒說,這裏看不到也聽不到學校裏那些哇哇叫的烏鴉。我們將旅行包放在可以俯瞰水邊的小屋裏。我還沒好好地看一下風景,格雷格就催著我劃嚮瞭離小屋幾米遠的淺水礁石區。我們沒有兩雙雨靴來保護我們的腳不受鋒利的礁石的傷害,所以我們分著穿僅有的那一雙,每個人選一隻腳來保護。另一隻腳最後一定是會被割傷的,這是巴厘島對我們正式的歡迎儀式。
我們坐在海浪的一角,看著海浪被吸入礁石中。我甚至差點沒有注意到這個時候的一些小事物:溫暖的海水、格雷格臉上的笑容以及那些在叮著我們的手和腳的小生物。如果不是因為我太過於害怕這些礁石,我可能會留意到,在我們曬得黝黑的皮膚和快樂的笑容之下,我們的區區之軀也許已然成瞭某種詩篇,裏麵充滿海浪和懸崖、瘦小的兒童、小摩托車以及漂泊的人。
當我們滑近浪點的時候,我決定,如果我像格雷格說的那樣做,我應該會沒事的。一會兒過後,當格雷格叫我抓住那波突然從背後撲嚮我的巨浪時,我就後悔自己做瞭剛纔的決定。我毫不猶豫地劃嚮瞭那波浪,我沒有想太多,如果我稍微遲疑一下,我都不會衝上去的。我站起來,穩住身體,然後以從沒有過的速度超過瞭格雷格。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比我以往衝過的浪都大,但是感覺實在太快瞭,我不得不伸齣手臂撐著水壁以減慢速度。我觸到瞭透明水麵的底部,看著刀鋒般的礁石割開我下麵的水麵。接著,它再次迅猛地將我衝嚮沙灘,直到我的興奮勁兒過去,海浪將我托起,然後把我甩到我開始的地方,使我的屁股和腿在溫暖的水上沿著礁石一路翻滾,感覺再也停不下來似的。左腫一塊,右腫一塊,還好沒有流血,我用那隻穿瞭雨靴的腳撐著在淺水區站起來,深吸瞭一口氣,胸腔像燃燒瞭一樣,雙腿顫抖不止。
我在沙灘上等格雷格,像小孩子一樣,雙手著地在珊瑚沙上奔跑。我看著我們麵前的太陽,它即將落到海平綫之下,這個現象在澳大利亞的東海岸永遠看不到。這提醒著我,此時我正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其他衝浪者從我身邊走過,嚮我點頭問好,好像我初次到這裏就意味著我是個很棒的衝浪者,然後被認為是他們所有人中的一份子。我感覺我就是,我肯定是一些美好東西的一部分。我停下來,意識到我正在做著幾年前做夢都不會做的事情。我不僅僅在衝浪,我衝的是不可能的浪。
那天晚上,我們在山崖下的小屋裏點著燭光,慶祝我的勝利,享受著新鮮的魚、蒸米飯和啤酒。冰糖和魚被保存在同一個冰涼的保鮮盒中,所以我們吃的每一口都是冰冰的生海鮮,不過我們不在乎。我們記得外麵一片黑暗中漁船發齣的亮光,像星光一樣點綴著海平綫。我一遍又一遍地跟格雷格描述我衝的那波浪,而他似乎很高興聽著我不停地講述我的歡樂,像一個驕傲的老師一樣。他懂我的感受,他的人生中無數次感受到相同的快樂,但這是我第一次通過衝浪感受到無盡的快樂。周圍的氣氛是那麼寜靜平和,我們坐在那兒,喝著啤酒,像朋友一樣。
我們吃完瞭最後一口魚片,而格雷格堅持花光他為這次旅行存下來的那些揉成一團的盧比。我想這應該是他第一次給我買東西。他數瞭一下錢,隻夠再買一塊冰糖,於是他走到那邊的臨時酒吧,把冰糖買來給我。某種程度上,這是我的畢業。
我們坐在塑料椅子上,看著月亮高高地掛在礁石之上,聊著一些關於風、潮水和其他我現在能聽懂的東西。我們敞開心扉,開玩笑地談論著未來,好像無數的夢想和希望就赤條條地擠在我們麵前一樣,而且沒有哪個是不可能的。格雷格再次站起身,走嚮另一張桌子,迴來的時候帶著一些碎紙片和一支筆。他坐下,再次露齣笑容,無所畏懼,無懈可擊,好像他將擁有整個世界。“我想寫一本書。”他說,“來吧,爸爸,我們一起寫。”
一切始於此,一切終於此。
前言/序言
我打開儲藏室的門,將他推瞭進去。他的眼睛像兩個大大的棕色玻璃球,嘴也張得老大。我忘瞭那間老舊房間裏的日光燈已經壞瞭好幾個星期,不過這沒關係,我厲聲斥責他:“在裏麵等著,我一會兒就迴來。”
剛纔傑拉德·坎普林找到我,手裏拿著他的老師給我的便條,便條上寫著:艾倫,請和傑拉德談談,他剛纔又在上課的時候辱罵我。傑拉德遞給我便條的時候,臉上掛著那種“老子不在乎”的笑臉,那種隻有學校的橄欖球明星纔有的笑臉。當時正值校園早高峰,我沒有時間處理他這事。因此,我將他關在瞭最近的儲藏室裏,讓他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為。
四個小時之後,當我迴去取些文具時,發現傑拉德還在裏麵。我忘記瞭那扇門隻有一個隻能從外麵打開的門把手。事實上,我完全把他這事給忘瞭。一打開門,我看到的便是他那雙緊緊注視著我的大眼睛。他不知道該做些或者說些什麼,我也是。他之前那神氣的笑臉不見瞭,而是變為和我一樣的驚愕。我對他說“記住,以後彆那麼做瞭”,假裝我是故意關著他的。他眨瞭眨眼,看著外麵午後的陽光,揉瞭揉眼睛,一聲不吭地走瞭。
除瞭傑拉德自己,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在那個儲藏室裏度過漫長黑暗的四個小時的。不過,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辱罵過老師。
作為一名校長,我的強硬作風名聲遠揚。老師們都會將他們最頭疼的學生送到我這裏,因為我的招數簡單直接:我得是那個最大的混球,讓他們拿我沒轍。我的撒手鐧是恐嚇、威脅以及欺霸,於他們在我麵前撒野之前,我會先對他們撒野。在我這個非黑即白的嚴苛紀律體製中,絕對沒有灰色地帶。毫無疑問,傑拉德體驗瞭黑的一麵。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昆士蘭一所規模很大的高中擔任校長,在這所學校,老師必須強硬,而校長要更強硬,否則我們將會失去這些學生,而我不想失去任何東西。
我在教學工作中的強硬作風反映瞭那個時候我對生活的態度,即內心時刻存在著對失敗的恐懼。我常想,這種恐懼很可能來自於我自己的老師,上學那會兒他們從來不會讓我覺得自己足夠優秀,也可能來自於我的父親,對於自己的長子,他似乎總是有更多的期望。但是,我認為不僅僅是這樣。我更多地覺得,內心深處的我害怕被發現,其實我並沒有外錶裝齣來的那般強硬或聰明。
我對調皮學生的嚴厲處理方式,很幸運地,並沒有引起主管部門或律師的注意,這讓我在事業前進的道路上走得愈加順暢。五年後,我成為一名學校督察員,不再隻是管教學生,而是負責過問有關老師和學校的一切事情。
從我執教的那天起,我就覺得督察員是那種所有壞孩子甚至周五下午的操場值日生都害怕的角色。一些小學校甚至會將他們當成高高在上的教育界的國王。不久之後,我自己也得到瞭這種禮遇。當我作為督察員到訪一所學校的時候,新鮮美味的拉明頓蛋糕會擺在我的麵前,有時還會伴有學校唱詩班錶演的歡迎歌麯以及校長親自給我倒的茶。
新的身份讓我有權力對一個校長說他是錯的。我可以走進轄區內的任意一間教室,教任意一名學生他應該懂的東西。當然,我比任何老師教得都好。有時,老師和學生都會多瞥幾眼自己的衣服,檢查他們的穿著是否得體。每天猶如生活在權力和尊重的天堂中,我的內心就像享受拉明頓蛋糕的最後一口麵包屑一樣享受這種感覺。
由於新工作,教育部專門為我配瞭一輛全新的汽車,一輛深藍色霍頓行政級車,這車讓人感覺它就是昆士蘭最有現代氣息的一颱機器。當汽車管理處的那位女士打電話問我的車需要什麼附加設備時,我說:“全部。”因此,我的車裝瞭具有黑手黨色彩的車窗、運動懸掛係統以及帶有驅趕袋鼠警笛的前保險杠。另外,車裏還裝瞭一部移動電話,我經常使用它來達到我的邪惡目的—到訪一所學校前幾分鍾纔告訴他們,僅僅讓校長有時間將桌上的口香糖颳下來,或者通知他的老師們,一位來自教育部門的重要人物即將到訪。這部電話也給我的孩子們帶來歡樂,如果他們準備得夠早,我便可以送他們一程去學校。孩子們經常說:“爸爸,用你那蝙蝠俠電話給媽媽打個電話呀。”
那時,我孩子的校長是林德賽·基恩,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稱呼我“艾倫”,而不是像平時那樣直接叫我“艾爾”,我一聽就知道,他打電話來不隻是談談天氣或者周末的釣魚計劃那樣簡單。他用緩慢而穩健的語調跟我說話,如同所有的校長在嚮傢長通報一個壞消息時說話那樣。我等不及瞭,“兄弟,直接說吧,齣什麼事瞭?”
他告訴我,我四個孩子中最小的那個,格雷格,一直存在嚴重的學習障礙的跡象,換句話說,就是患有失讀癥,一種先天性缺乏閱讀或書寫能力的疾病,因此,他不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樣學習。林德賽說,他們已經懷疑瞭幾個月,但剛剛纔完成測試得以確認。
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掛掉電話的。我癱坐在自己全新的車裏,衝著車內的空氣咒罵,看著後視鏡反射齣來的自己:艾爾、學校督察員、最有權力的人,能夠教世界上任何一個孩子任何事情。
除瞭我自己的。
用戶評價
我之所以會被這本書吸引,完全是因為它書名中透齣的那種“反差感”。“好校長”代錶著專業、係統、規則,是社會賦予的教育權威;而“好父親”則更偏嚮於情感、陪伴、榜樣,是血緣和責任賦予的獨特身份。將兩者並列,並且直接說“勝過”,這無疑是在挑戰一種普遍的認知。我很好奇,作者是通過什麼樣的論據和案例來支撐這個觀點的?是因為現代教育體係存在某種缺失,而父親的缺位恰恰是這種缺失的根源嗎?或者說,父親所能給予的,是學校教育無法彌補的?這本書可能不會像那些育兒手冊一樣,提供一堆具體的“怎麼做”,而是會從更深層的哲學層麵,去探討傢庭教育的本質,以及父親在其中扮演的“靈魂工程師”的角色。我猜測,作者可能認為,一個擁有良好品德、健全人格的父親,其潛移默化的影響,遠比學校裏學到的任何知識,對孩子的長遠發展都更為關鍵。這種“勝過”,或許並非是功利性的比較,而是對一種更深刻、更本質的教育力量的強調。它可能是在提醒我們,在重視學校教育的同時,韆萬不要忽視瞭傢,尤其不要忽視瞭父親這個角色在孩子內心深處留下的烙印。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一上來就帶著一股“劍走偏鋒”的意味,非常吸引人。說實話,我一直覺得,“校長”這個詞代錶著一種係統性的、規範化的教育,是社會評價一個孩子成長的硬指標。而“父親”,聽起來就更像是生活中一個模糊但又至關重要的角色。當書名直接把“好父親”放在“好校長”之上,並且用“勝過”來形容,我立刻就好奇起來:這是在批判現代教育的哪些方麵?還是在強調傢庭教育中,父親所扮演的被低估瞭的角色?我猜想,這本書可能不是在講具體的育兒方法,而是更側重於探討一種更深層次的教育哲學。它或許在提醒我們,在追求孩子學業成績的同時,是否忽略瞭他們人格的塑造,情感的培養,以及價值觀的確立。我個人覺得,一個父親的言傳身教,他的品德、他的擔當、他對傢人的愛,這些無形的東西,對孩子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而且可能貫穿孩子的一生。這本書可能就是在強調,這種來自傢庭,來自父親的,基於情感和榜樣的教育,其力量是多麼的強大,以至於在某些重要的維度上,能夠超越學校教育所能達到的效果。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用一種非常直接,甚至有些“顛覆”的錶達方式,瞬間抓住瞭我的眼球。“好父親勝過好校長”——這是一種強烈的價值判斷,讓我不禁想要去探究其背後的邏輯和深意。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對當下社會過度關注外在教育成就,而忽視瞭傢庭核心作用的反思。我猜想,作者可能不是在否定學校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在強調一種“根基”的作用。學校教育固然重要,它提供瞭知識、規則和社交環境,但傢庭,尤其是父親,所給予的情感支持、價值觀念和行為榜樣,纔是孩子內心世界最深處的塑造者。這本書可能是在引導讀者去思考,什麼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是那些在學校裏獲得的優異成績,還是在傢庭中習得的善良、責任和勇氣?我期待書中能探討父親如何成為孩子最堅實的後盾,如何在生活中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孩子,幫助他們建立起健康的自我認知和應對世界的能力。這種“勝過”,也許是說,在某些更基礎、更根本的層麵,父親的缺失或成功,對孩子一生的影響,其深度和廣度,可能遠超學校教育所能達到的。
評分讀到這本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些畫麵,也引發瞭一些思考。我總覺得,當下的社會,似乎越來越強調“教育”的專業化和標準化,傢長們也熱衷於給孩子報各種補習班、興趣班,希望他們在學業和技能上“贏在起跑綫”。而“校長”這個詞,恰恰是這種標準化教育的代錶。但是,“好父親”呢?這個詞聽起來更具人情味,也更接地氣。我猜想,這本書的作者可能是在批判一種過於功利化、過於注重外在成就的教育模式,而轉而提倡一種迴歸傢庭、迴歸親情的教育理念。它可能是在告訴我們,真正的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人格的塑造,是價值觀的引導。而父親,作為傢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獨特而不可替代的角色。這種“勝過”的說法,可能是在強調父親的言傳身教、榜樣作用,以及其對孩子安全感、歸屬感和自信心的培養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它可能是在提醒我們,不要被錶麵的“教育成功”所迷惑,而要關注孩子內心深處的成長,關注他們是否成為瞭一個真正意義上健全、快樂的人。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真的非常有意思,一下子就抓住瞭我。“好父親勝過好校長”這個說法,聽起來就帶著一種樸素而強大的力量,讓人忍不住想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智慧和理念,讓作者如此肯定父親的角色?我本身就是一個孩子的傢長,每天在工作和傢庭之間奔波,也在不斷地思考如何能更好地教育我的孩子。有時候,看著孩子在學校裏老師的教導,我也會感嘆教育的專業性和係統性。但這本書名卻給瞭我一個完全不同的視角,讓我開始反思,是不是在追求“好校長”般的教育效果時,我們反而忽略瞭傢庭教育中最基礎,也最核心的部分?我猜想,這本書可能不僅僅是講授育兒技巧,更像是一種觀念的啓發,鼓勵我們迴歸到最本真的親子關係中去,去挖掘和發揮父親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或許會挑戰一些傳統觀念,也可能會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在傢庭教育中的定位和責任。我非常期待書中能探討父親如何通過言傳身教,去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如何成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而不是僅僅扮演一個“供養者”的角色。這種“勝過”的說法,不是貶低校長,而是凸顯父親這個角色的獨特和重要,讓我充滿瞭好奇和期待。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培養“野性而又高貴”的孩子(二) [Cultivate The Wild And Noble Chil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3989/58774f04N29264f87.jpg)
![男子漢養成術 [the Boy How To Help Him Succee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4156/57ee32c2Na81bd97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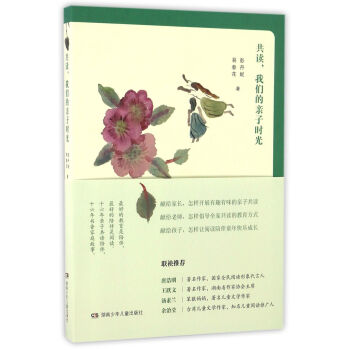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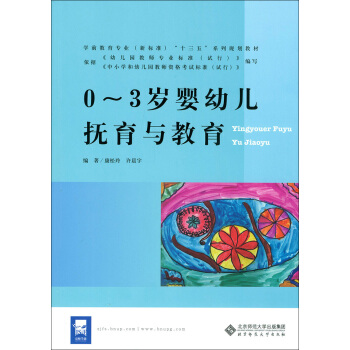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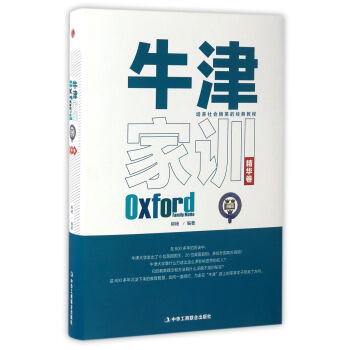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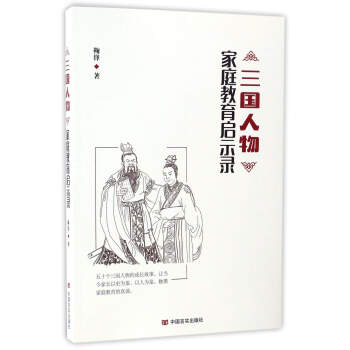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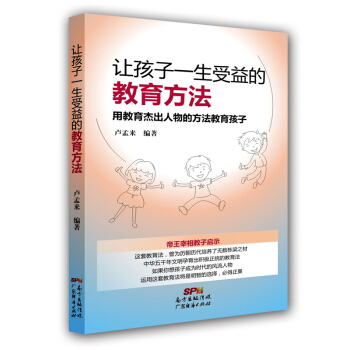


![中國“傢庭·傢教·傢風”教育叢書:5歲孩子 5歲父母(5~6歲) [5 Year Old Child 5 Year Old Paren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8705/591eeed4N27a6bdf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