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作为父亲,他的理想是懂得平等和坚守诺言,是让家里充满令人陶醉的味道,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是引导他们不再对未来感到恐惧;
★ 作为校长,他的成就在于每一个孩子和老师的笑容,在于对话的相互尊重,在于课堂的积极参与,在于所有学生相互关怀的无声承诺;
★ 作为作者,他的目标是将自己在教育层面的毕生所学、毕生所得,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整个世界的面前;
★ 读罢此书你会发现,在上述三个层面,他都做到了。
★【优教书系】全系精彩图书:
内容简介
爱因斯坦、毕加索、哈姆雷特,他们告诉我们什么?
海马体、失读症、冲浪,它们教会我们什么?
艾伦·桑普森动情自述:如何让学校内外的教育,变成一座花园。
《好父亲胜过好校长》作者艾伦·桑普森在学校里应付学生非常有一套,但是在家庭这所学校里,他碰到了自己这辈子极其难教的一个学生——他的小儿子。儿子患有先天性的读写能力障碍——与智商无关,因为爱因斯坦、毕加索均患有此问题。然而,由于小儿子异于常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将其送去特殊学校无果之后,艾伦·桑普森开始自己教育儿子。
无论是教育体系的问题,还是孩子本身的问题,抑或这位校长的问题,这对父子经常争吵。然而,他们在争吵与摸索中,逐渐找到了对待彼此的方式。他们意识到,其实,优秀的教育,在学校系统之外也能找到。
作者简介
艾伦·桑普森,教师、监察员、非常严厉的高中校长,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教育界工作三十年,以将落后的学校变得杰出而闻名。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关于在特殊的境况下进行教育的书,其细致地审视了学校在其中的作用,并重新定义了教育上的成功,读起来让人振奋也让人信服。
——罗恩·迈尔斯,英国达利奇视觉艺术和设计高中前校长
那些孩子身患残疾的父母,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道路上,将重视并分享这位父亲的宝贵经历。这本书让我们领会到,人的力量和才能可以有多强大,那种因关注点过多围绕残疾而可能被忽视的强大。这让我想起了朱迪·皮考特的著作《心尘往事》(House Rules),该书详尽地讲述了关于残疾人以及教师无私奉献的内容,读起来如散文一般朴实感人。
——贾妮·麦克德莫特,残疾儿童教师及特别教育顾问
目录
序
第一章 校长的第一天
第二章 校园女神
第三章 图书馆里有鲨鱼
第四章 校长办公室
第五章 曲奇是魔鬼
第六章 迷失在冷冻食品中
第七章 杜克斯先生
第八章 有人刁难格雷格
第九章 绿色的小精灵
第十章 鸭狗大战
第十一章 挂满内裤的树
第十二章 家庭作业
第十三章 黑暗中的多萝茜
第十四章 为瑞秋奔跑
第十五章 父母的圈套
第十六章 低潮
第十七章 崩溃的边缘
第十八章 站起来,菲茨
第十九章 老师的改变
第二十章 最后的学校生涯
第二十一章 烧书
第二十二章 不可能的浪
致谢
精彩书摘
为瑞秋奔跑
在这一年剩下的日子以及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格雷格放学后依旧回到他妈妈的家,一如既往地闹腾和不安分,特别是周末不能去海边冲浪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姐姐们不再有很多时间来照看他,对玛格丽特来说,也越来越难对付他。并不是我们各自新的伴侣让他感到烦躁,实际上他对他们并不那么在乎了。我们不知道他的烦躁到底是什么原因。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我和玛格丽特的和平谈话中,我们只能猜测,他只是想和学校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聪明,或者被承认他其实本来就是很聪明。
他开始对特别教育课感到厌烦。他受够了明明知道答案是什么,却不知道怎么把答案写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阅读和书写对他来说如此困难,而对其他人来说如此简单。他几乎准备放弃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是他在每节课上的身体语言已经说明了一切。苏塞先生最早跟我提起这个迹象,而当王老师也跟我说,格雷格对她的课也越来越缺乏热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情况真的不妙。玛格丽特用上了一个母亲能用的所有方法来让他振作,包括给他买新的电脑游戏,新的冲浪板,甚至新买了一只狗给他养。然而,他跟它玩了几个月后,不出意料地再次感到厌倦。
周末的时候,只要他的钱够买火车票,他就会消失掉,跑到海边去。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他的哥哥给我们发短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去哪里了。本晚上常常会和朋友出去,而格雷格就躺在他租的海滨公寓的地板上睡觉,或者看冲浪电影。有几次我们发现,格雷格甚至并没有同本在一起,他对我们撒谎了,更别提不知有多少次本帮他打圆场了。“不用担心,他很可能在某个山丘上露营呢。”本常常这样说。这时候玛格丽特会打电话给我说,“周末他归你管,现在他在哪个山丘上过夜呢,艾伦?”虽然我知道她只是跟我一样着急,但我想,有时候她只是喜欢大骂我的感觉。
我们俩都关心他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吃什么、喝什么,毕竟他没有钱。好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因为一整天我都没有收到格雷格的短信,只希望海水和沙丘能保证他的安全—如果本不能的话。为人父母做成这样也真是挺失败的。我怀疑格雷格是不是将我的手机号码删掉了,所以我将手机中每条含有“爱你的爸爸”的信息都查看了一遍。
很快,玛格丽特的神经再也无法忍受每周一大吵和深夜等人的折磨。在她抓狂地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她做了一个单方面的决定:以后格雷格跟我住。她说这是为了他好。在我回答之前,她就挂了电话,好像她事先排练好了所有的台词一样。我不知道跟我住对他来说是更好还是更坏,但代价一定是会有的,无论大小。
几个星期之后,代价真的来了。我接到小女儿瑞秋的电话,她说她想要来卡路中学实习,以完成专业学分。当时她在昆士兰大学上大三,需要找一所中学完成为期半年的实习。我同意了她的请求,并为格雷格感到兴奋,他的姐姐要来学校陪他了。她可以为他打气,鼓励他,就像她以前一直做的那样。格雷格非常喜欢他的姐姐们。我想,也许瑞秋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帮助格雷格走出他自己的世界,并积极地面对以后的人生,可能的话,同时修复我和他之间的隔阂。
天真的瑞秋,她以为她是冲着几个星期轻松的实习生活来的。
瑞秋的大学专业是戏剧艺术,她天生也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快乐的外向型女子。她年轻、有活力,留着一头金发,外表非常迷人。然而,在我热情地介绍这一切的时候,我忘了(虽然是短暂的)男生都是一副什么德行。瑞秋很快就吸引了几个高年级男生的注意,他们经常在她的课上细声细语地说一些下流的话。出于工作的原因,瑞秋无视他们,继续上课。在运动嘉年华那天,瑞秋的实习时间也已过半,我得以问她感觉如何。她说,除了一些男生很男生之外,其他一切都非常不错。我只希望格雷格没有听到瑞秋说的话,我知道男生很男生是什么意思,而格雷格也知道。
格雷格的社交网络是宽广的。不久之后,在D号楼那边,他就一字不差地听到了所有关于他姐姐的评论。很显然,一个叫艾德里安·斯科特的家伙,在瑞秋背后不只是说了几句无礼的话,他还将怎么做的细节说了出来,不堪入耳。他经常评论瑞秋如何性感。显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瑞秋的监督老师离开教室之后。艾德里安是学校里最优秀的跑步运动员之一,他在女生中的人气给了他一种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面对异性时盲目的自信。
格雷格非常爱护他的妈妈和姐姐,甚至有点过于爱护。可能是与妈妈和姐姐们一起住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家中唯一的男人,而家中的另一个男人总是不在。可能也跟他的妈妈和姐姐们开始与别人约会有关。
但是,格雷格再次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知道,如果他采取任何暴力的手段来保护瑞秋,他一定是会被开除的。每个人,包括艾德里安,都知道这一点。关于瑞秋的闲言碎语依旧不断。
尽管他是在保护姐姐的名声,但格雷格知道,我已经做不了什么来保护他了。当初邀请瑞秋来的时候,我没想到会将这样一种状况摆在格雷格的面前,而且是最坏的那种,关乎尊严和家庭。瑞秋一直很爱护格雷格,我知道,他也一定会保护她的。
当然,我对当时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不知情。在运动会那天,我在起跑线附近碰见瑞秋,她才稍微跟我提了一下。也许我的那些书呆子间谍终于失手了一回,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在轮胎那里收到字条了。
运动嘉年华那天,穿着绿色衬衫的参赛者像洪水一样在起跑线前聚集。我和瑞秋在一旁看着,聊着天,觉得参与一下户外活动还是挺不错的。越野赛跑即将开始,十三公里长的路线将围绕白岭自然保护区,一路穿过一段丛林道路,最后回到学校。路线上和丛林中每隔一段距离都驻扎着一个老师,以确保不会有学生迷路。随着发令枪“砰”的一声响起,参赛者蜂拥向前跑,推搡着、大笑着、大喊着,那些还在剩饭堆里觅食的乌鸦都被吓飞了。
参加比赛的社会人士慢慢移动到了队伍的后面,而学生们排成一队跑在队伍的前面。我惊讶地看到,格雷格竟然跑在最前面。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地看着他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队伍前面,几乎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将队伍远远抛在后面。当大部队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已经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当然,他不可能全程保持那样的速度。我从来没有见他这么干过。他的确可以跑得很快,但他的长跑能力不得而知。我想,可能他是想在姐姐或者某个女生面前耍帅、出风头。通常情况下,他都是和朋友并肩跑的,但今天情况似有不同。“控制好节奏。”当他消失在那片丛林往保护区方向跑去,并将后面的参赛者远远甩开的时候,我想这样对他说。我希望他会赢,这对学校的所有学生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毕竟他正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到学校的活动当中。
随着学校半数的学生跑到了丛林区,学校难得地显得十分清静。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开始看到有运动员出现在山那边,他们已经开始往学校的方向回跑。学校这边的观众早已经等得焦急难耐了。
我想知道格雷格跑得怎么样,他是否全程控制好了节奏。我不确定他的身体有多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些神秘周末的冲浪对他的肺活量和肌肉一定大有帮助。
运动员们越来越近。我失望地没有在一路跑过山林朝我冲过终点线的人群中看到格雷格的身影。剩下的参赛者陆续穿过终点线,依然没有格雷格。我想一定是他开始跑得太猛,把能量一下子用光了。
当一些步伐沉重的人、社会参赛人士以及步行者完成比赛的时候,我开始起了疑心。我注意到格雷格也在其中,有说有笑、从容地慢慢穿过终点线。我回头看着那些前十名完成比赛的运动员,他们在放松身体和记录时间,但在他们当中我没有看到艾德里安。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早就应该知道,格雷格怎么可能会对越野赛跑有兴趣。一些散兵游勇还在通过终点线,记分员也准备收档的时候,艾德里安出现了,慢慢地走在山路上。他的样子十分狼狈,衬衫全被扯烂了,鞋子也只剩下一只。除了这些之外,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发生什么事了,艾德里安,你摔倒了吗?”一个老师惊讶地问。“是的,老师,我摔倒了。”他说。
“你的另一只鞋呢?”
“弄丢了。”看来,艾德里安的安全意识没有伸展到校门之外以及几公里之外的丛林里。
我想,只有格雷格、艾德里安以及一小部分学生知道,跑步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没有人说。我猜想,格雷格一定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星期,当严格意义上他不在学校范围之内的时候,他实施了他的报仇。这谈不上鲁莽或者暴力,他只是保证那个跑步明星赢不了,并让他为不尊重格雷格的姐姐付出一只昂贵跑鞋的代价。
我觉得,他也想让我知道,他并不一定非得看我的脸色做事,或者看学校的脸色做事。那天他算是给我发出了这个微弱的信号,并给艾德里安发出了一个不那么微弱的信号。我想,这也是他给姐姐发出的一个信号,他希望瑞秋在学校中,并且他可以保护她。这就是友谊,这就是家人。
回家的路上,我问实习学生瑞秋,作为一个老师,对于格雷格她会怎么做。她只是笑了笑,耸耸肩,好像这是一个我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爸爸,对某些学生奏效的东西,对其他学生来说不一定也奏效。”她说。格雷格肯定属于其他学生的一份子。我知道,还有很多任何学校都不愿意招收的其他学生。我要找出对他们来说奏效的东西。
不可能的浪
曾经作为一名学校督察员,我对一个学校的评判主要基于它的学业成绩。而如今,我的视野更宽了。我敢说,我给我的学校带来了更广阔的心胸。格雷格毕业之后,我在卡文迪许路中学继续工作了几年。在我的任职期间,学校的规模增加了一倍。这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招生营销的结果。这是所有的学生和老师的功劳。这个学校是属于他们的。
2009年,教育部门开展了一次名为教学与学业统计的调查。卡文迪许路中学是这个州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被评为教学水平最高的学校,获得了“杰出学校文化奖”。虽然我们学校的关注重点不再是学业的表现,但我们在学业上依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只不过是伟大的校园文化带来的副产品而已。
同一年,在一次校际联欢活动上,我们再次以卓越的学业与创新表现,被授予“州立示范中学”称号。我们并不需要这些表面的认可。我们的成就,在于每一个孩子和老师的笑容,在于对话的相互尊重,在于课堂的积极参与,在于所有学生相互关怀的无声承诺。在一个广泛拒绝欺霸现象的校园文化中,欺霸之徒也只能有其心没有其胆。每个人都想成为绿色的小精灵的一份子,包括老师。
在我掌管卡路中学期间,成百上千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都成为他们工作领域中的佼佼者。但更多的人毕业之后,都成为一个让人钦佩的人,直至今天,他们都非常有希望成为快乐的人。我只希望,当他们离开校门的时候,不害怕前方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不是因为这种心态是对他们的期望,或者是强加给他们的,而是因为卡路中学是一个培养勇气和信心的地方。我们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帮助学生战胜人生的恐惧,战胜对未来的恐惧。我们坚信,孩子承受的那些不必要的压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没有人会再被否定,没有人会再被遗弃在黑暗中。
我们的学校不是教学生他们能在学校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而是教会他们要不忘初心,取得人生的成就。这需要在他们身上培养不会轻易被夺走的品质,而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自我恢复能力。我在卡文迪许路中学当了十三年校长。在这个学校里,我经历了自己的重生,这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格雷格种下了令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种子。
在我作为校长的最后一天,我来到学校礼堂,准备发表我的最后告别演讲。我看到我们新建的礼堂人多得几乎都装不下了。在学生为我的离开欢呼的时候,我看到在人群当中有一个熟悉的一头凌乱金发的身影。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也来了。在那一刻,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些学生在他们球衣背后印了“老桑的战士”几个字,那是他们自己做的。在礼堂的后面,我看到了曾经的学生和老师,我的书呆子间谍,我的足球健将,许许多多过去和现在的学生,他们都在鼓着掌,吹着口哨。我听到了熟悉的格雷格的鸣叫,“耶耶耶耶耶咿”,远远高于其他所有声音。当我最后一次从讲台上走下台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个即将离开学校的学生,开始要面对外面全新的世界。
当我离开礼堂的时候,他们都为我站了起来,就像以前我无数次为他们站起来一样。我的内心充满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在这么多情绪中,有一种消失不见了,那便是恐惧。人生中第一次我不害怕任何东西。我离开不是因为我必须离开,这么多年过去后,我感觉这是对的选择,因为我想离开了。我不担心离开这个待了这么多年的学校以后我将何去何从。我想这是因为我对自己在这里的教业工作问心无愧,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的勇气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不知道这些是来自于我在大海待的无数时光,还是来自于格雷格和他的哥哥姐姐们,还是来自于成千上万先于我走出校门的学生们。但是我知道,那天,我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我离开学校的。
几个月之后,我身上那股对于新的人生之旅的兴奋劲儿依然没有消退。我尝试让自己忙起来。我终于有时间来到楼下,打开一些箱子,那些标着D的箱子,这么多年过去后依然还没有被打开过。这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愿回首的生活的证据。我取出一些相册和格雷格以前的玩具。他成长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我离开卡路中学后,大多数早上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这一天适不适合冲浪。我就像他的弟弟,总想着出去玩。不冲浪的时候,我尝试做任何事,从而让自己忙起来。我会清理泳池,给草坪割草,然后再清理泳池。如果我在便利店看到一个卡路中学的学生的校服没有掖好,我得忍住上去让他们掖好的冲动(通常我会的)。我甚至想给自己找个女朋友,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还不够安定。
不久之后,格雷格说服我带他出国去冲浪。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找到大量的关于晶莹剔透的水的图片、视频和宣传册给我看,最终让我买了带他去巴厘岛的机票。我现在已经可以站在自己的冲浪板上冲浪了,不过依然还有“便便艾”的痕迹。我还没有应付一个恶劣的礁石突然向我猛扑过来的海浪的经验。有人跟我说,最近的医院就在我的旅行箱中,里面应该有绷带、消毒剂以及用来取出珊瑚礁的刺的镊子。当然,格雷格只警告过我一次珊瑚礁真正的危险是什么,还是在飞机飞在天上的时候。“不要吃从街边摊贩那里买来的汤里面那些圆圆的东西,你可能会死掉的。”他说,然后从容自在地戴上耳机,继续看他的电影。我怀疑他让我来,只是想让我为他吃的冰糖和炒饭买单。但他让我感觉这是为我准备的旅行,而且是我和他共同争取得来的。
格雷格和他的哥哥来过几次巴厘岛。他似乎能记得所有见过的人的名字。当我们从混乱的丹帕沙机场出来后,他的朋友瓦延在停车场欢迎我们,然后我们向他租了小摩托车。格雷格完全知道往哪里走,我坐在小摩托车上,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再也不想下来。我开着摩托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经过陌生的人群。很快,我们驶出繁忙的交通要道,来到空旷的田野,然后我们开得更快,让炙热的大风吹乱我们的头发。如果自由是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也坐着小摩托车在后面跟着我们,像我们一样吹着口哨。
很快,我们不得不抛弃我们刚刚掌握的自由交通工具,沿着巴厘岛海岸的峭壁,一路步行到被他们称作“不可能之礁”的神奇的珊瑚礁群。从那个礁石冲出来的海浪非常迅猛,很多人说不可能在上面冲浪。单单这个名字就吸引了格雷格,因为他一直在像当天在拜伦湾冲浪时那样活着,与危险和灾难一毫米之隔。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那些嗷嗷乱叫的瘦小孩子和冒着烟的香炉。格雷格提醒说,这里看不到也听不到学校里那些哇哇叫的乌鸦。我们将旅行包放在可以俯瞰水边的小屋里。我还没好好地看一下风景,格雷格就催着我划向了离小屋几米远的浅水礁石区。我们没有两双雨靴来保护我们的脚不受锋利的礁石的伤害,所以我们分着穿仅有的那一双,每个人选一只脚来保护。另一只脚最后一定是会被割伤的,这是巴厘岛对我们正式的欢迎仪式。
我们坐在海浪的一角,看着海浪被吸入礁石中。我甚至差点没有注意到这个时候的一些小事物:温暖的海水、格雷格脸上的笑容以及那些在叮着我们的手和脚的小生物。如果不是因为我太过于害怕这些礁石,我可能会留意到,在我们晒得黝黑的皮肤和快乐的笑容之下,我们的区区之躯也许已然成了某种诗篇,里面充满海浪和悬崖、瘦小的儿童、小摩托车以及漂泊的人。
当我们滑近浪点的时候,我决定,如果我像格雷格说的那样做,我应该会没事的。一会儿过后,当格雷格叫我抓住那波突然从背后扑向我的巨浪时,我就后悔自己做了刚才的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划向了那波浪,我没有想太多,如果我稍微迟疑一下,我都不会冲上去的。我站起来,稳住身体,然后以从没有过的速度超过了格雷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比我以往冲过的浪都大,但是感觉实在太快了,我不得不伸出手臂撑着水壁以减慢速度。我触到了透明水面的底部,看着刀锋般的礁石割开我下面的水面。接着,它再次迅猛地将我冲向沙滩,直到我的兴奋劲儿过去,海浪将我托起,然后把我甩到我开始的地方,使我的屁股和腿在温暖的水上沿着礁石一路翻滚,感觉再也停不下来似的。左肿一块,右肿一块,还好没有流血,我用那只穿了雨靴的脚撑着在浅水区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胸腔像燃烧了一样,双腿颤抖不止。
我在沙滩上等格雷格,像小孩子一样,双手着地在珊瑚沙上奔跑。我看着我们面前的太阳,它即将落到海平线之下,这个现象在澳大利亚的东海岸永远看不到。这提醒着我,此时我正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冲浪者从我身边走过,向我点头问好,好像我初次到这里就意味着我是个很棒的冲浪者,然后被认为是他们所有人中的一份子。我感觉我就是,我肯定是一些美好东西的一部分。我停下来,意识到我正在做着几年前做梦都不会做的事情。我不仅仅在冲浪,我冲的是不可能的浪。
那天晚上,我们在山崖下的小屋里点着烛光,庆祝我的胜利,享受着新鲜的鱼、蒸米饭和啤酒。冰糖和鱼被保存在同一个冰凉的保鲜盒中,所以我们吃的每一口都是冰冰的生海鲜,不过我们不在乎。我们记得外面一片黑暗中渔船发出的亮光,像星光一样点缀着海平线。我一遍又一遍地跟格雷格描述我冲的那波浪,而他似乎很高兴听着我不停地讲述我的欢乐,像一个骄傲的老师一样。他懂我的感受,他的人生中无数次感受到相同的快乐,但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冲浪感受到无尽的快乐。周围的气氛是那么宁静平和,我们坐在那儿,喝着啤酒,像朋友一样。
我们吃完了最后一口鱼片,而格雷格坚持花光他为这次旅行存下来的那些揉成一团的卢比。我想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给我买东西。他数了一下钱,只够再买一块冰糖,于是他走到那边的临时酒吧,把冰糖买来给我。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毕业。
我们坐在塑料椅子上,看着月亮高高地挂在礁石之上,聊着一些关于风、潮水和其他我现在能听懂的东西。我们敞开心扉,开玩笑地谈论着未来,好像无数的梦想和希望就赤条条地挤在我们面前一样,而且没有哪个是不可能的。格雷格再次站起身,走向另一张桌子,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些碎纸片和一支笔。他坐下,再次露出笑容,无所畏惧,无懈可击,好像他将拥有整个世界。“我想写一本书。”他说,“来吧,爸爸,我们一起写。”
一切始于此,一切终于此。
前言/序言
我打开储藏室的门,将他推了进去。他的眼睛像两个大大的棕色玻璃球,嘴也张得老大。我忘了那间老旧房间里的日光灯已经坏了好几个星期,不过这没关系,我厉声斥责他:“在里面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刚才杰拉德·坎普林找到我,手里拿着他的老师给我的便条,便条上写着:艾伦,请和杰拉德谈谈,他刚才又在上课的时候辱骂我。杰拉德递给我便条的时候,脸上挂着那种“老子不在乎”的笑脸,那种只有学校的橄榄球明星才有的笑脸。当时正值校园早高峰,我没有时间处理他这事。因此,我将他关在了最近的储藏室里,让他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四个小时之后,当我回去取些文具时,发现杰拉德还在里面。我忘记了那扇门只有一个只能从外面打开的门把手。事实上,我完全把他这事给忘了。一打开门,我看到的便是他那双紧紧注视着我的大眼睛。他不知道该做些或者说些什么,我也是。他之前那神气的笑脸不见了,而是变为和我一样的惊愕。我对他说“记住,以后别那么做了”,假装我是故意关着他的。他眨了眨眼,看着外面午后的阳光,揉了揉眼睛,一声不吭地走了。
除了杰拉德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在那个储藏室里度过漫长黑暗的四个小时的。不过,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辱骂过老师。
作为一名校长,我的强硬作风名声远扬。老师们都会将他们最头疼的学生送到我这里,因为我的招数简单直接:我得是那个最大的混球,让他们拿我没辙。我的撒手锏是恐吓、威胁以及欺霸,于他们在我面前撒野之前,我会先对他们撒野。在我这个非黑即白的严苛纪律体制中,绝对没有灰色地带。毫无疑问,杰拉德体验了黑的一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昆士兰一所规模很大的高中担任校长,在这所学校,老师必须强硬,而校长要更强硬,否则我们将会失去这些学生,而我不想失去任何东西。
我在教学工作中的强硬作风反映了那个时候我对生活的态度,即内心时刻存在着对失败的恐惧。我常想,这种恐惧很可能来自于我自己的老师,上学那会儿他们从来不会让我觉得自己足够优秀,也可能来自于我的父亲,对于自己的长子,他似乎总是有更多的期望。但是,我认为不仅仅是这样。我更多地觉得,内心深处的我害怕被发现,其实我并没有外表装出来的那般强硬或聪明。
我对调皮学生的严厉处理方式,很幸运地,并没有引起主管部门或律师的注意,这让我在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愈加顺畅。五年后,我成为一名学校督察员,不再只是管教学生,而是负责过问有关老师和学校的一切事情。
从我执教的那天起,我就觉得督察员是那种所有坏孩子甚至周五下午的操场值日生都害怕的角色。一些小学校甚至会将他们当成高高在上的教育界的国王。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得到了这种礼遇。当我作为督察员到访一所学校的时候,新鲜美味的拉明顿蛋糕会摆在我的面前,有时还会伴有学校唱诗班表演的欢迎歌曲以及校长亲自给我倒的茶。
新的身份让我有权力对一个校长说他是错的。我可以走进辖区内的任意一间教室,教任意一名学生他应该懂的东西。当然,我比任何老师教得都好。有时,老师和学生都会多瞥几眼自己的衣服,检查他们的穿着是否得体。每天犹如生活在权力和尊重的天堂中,我的内心就像享受拉明顿蛋糕的最后一口面包屑一样享受这种感觉。
由于新工作,教育部专门为我配了一辆全新的汽车,一辆深蓝色霍顿行政级车,这车让人感觉它就是昆士兰最有现代气息的一台机器。当汽车管理处的那位女士打电话问我的车需要什么附加设备时,我说:“全部。”因此,我的车装了具有黑手党色彩的车窗、运动悬挂系统以及带有驱赶袋鼠警笛的前保险杠。另外,车里还装了一部移动电话,我经常使用它来达到我的邪恶目的—到访一所学校前几分钟才告诉他们,仅仅让校长有时间将桌上的口香糖刮下来,或者通知他的老师们,一位来自教育部门的重要人物即将到访。这部电话也给我的孩子们带来欢乐,如果他们准备得够早,我便可以送他们一程去学校。孩子们经常说:“爸爸,用你那蝙蝠侠电话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那时,我孩子的校长是林德赛·基恩,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称呼我“艾伦”,而不是像平时那样直接叫我“艾尔”,我一听就知道,他打电话来不只是谈谈天气或者周末的钓鱼计划那样简单。他用缓慢而稳健的语调跟我说话,如同所有的校长在向家长通报一个坏消息时说话那样。我等不及了,“兄弟,直接说吧,出什么事了?”
他告诉我,我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格雷格,一直存在严重的学习障碍的迹象,换句话说,就是患有失读症,一种先天性缺乏阅读或书写能力的疾病,因此,他不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学习。林德赛说,他们已经怀疑了几个月,但刚刚才完成测试得以确认。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挂掉电话的。我瘫坐在自己全新的车里,冲着车内的空气咒骂,看着后视镜反射出来的自己:艾尔、学校督察员、最有权力的人,能够教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事情。
除了我自己的。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真的非常有意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好父亲胜过好校长”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带着一种朴素而强大的力量,让人忍不住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和理念,让作者如此肯定父亲的角色?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每天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奔波,也在不断地思考如何能更好地教育我的孩子。有时候,看着孩子在学校里老师的教导,我也会感叹教育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但这本书名却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在追求“好校长”般的教育效果时,我们反而忽略了家庭教育中最基础,也最核心的部分?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不仅仅是讲授育儿技巧,更像是一种观念的启发,鼓励我们回归到最本真的亲子关系中去,去挖掘和发挥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或许会挑战一些传统观念,也可能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定位和责任。我非常期待书中能探讨父亲如何通过言传身教,去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如何成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而不是仅仅扮演一个“供养者”的角色。这种“胜过”的说法,不是贬低校长,而是凸显父亲这个角色的独特和重要,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用一种非常直接,甚至有些“颠覆”的表达方式,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好父亲胜过好校长”——这是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让我不禁想要去探究其背后的逻辑和深意。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对当下社会过度关注外在教育成就,而忽视了家庭核心作用的反思。我猜想,作者可能不是在否定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而是在强调一种“根基”的作用。学校教育固然重要,它提供了知识、规则和社交环境,但家庭,尤其是父亲,所给予的情感支持、价值观念和行为榜样,才是孩子内心世界最深处的塑造者。这本书可能是在引导读者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是那些在学校里获得的优异成绩,还是在家庭中习得的善良、责任和勇气?我期待书中能探讨父亲如何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如何在生活中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孩子,帮助他们建立起健康的自我认知和应对世界的能力。这种“胜过”,也许是说,在某些更基础、更根本的层面,父亲的缺失或成功,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其深度和广度,可能远超学校教育所能达到的。
评分我之所以会被这本书吸引,完全是因为它书名中透出的那种“反差感”。“好校长”代表着专业、系统、规则,是社会赋予的教育权威;而“好父亲”则更偏向于情感、陪伴、榜样,是血缘和责任赋予的独特身份。将两者并列,并且直接说“胜过”,这无疑是在挑战一种普遍的认知。我很好奇,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论据和案例来支撑这个观点的?是因为现代教育体系存在某种缺失,而父亲的缺位恰恰是这种缺失的根源吗?或者说,父亲所能给予的,是学校教育无法弥补的?这本书可能不会像那些育儿手册一样,提供一堆具体的“怎么做”,而是会从更深层的哲学层面,去探讨家庭教育的本质,以及父亲在其中扮演的“灵魂工程师”的角色。我猜测,作者可能认为,一个拥有良好品德、健全人格的父亲,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远比学校里学到的任何知识,对孩子的长远发展都更为关键。这种“胜过”,或许并非是功利性的比较,而是对一种更深刻、更本质的教育力量的强调。它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在重视学校教育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了家,尤其不要忽视了父亲这个角色在孩子内心深处留下的烙印。
评分读到这本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些画面,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我总觉得,当下的社会,似乎越来越强调“教育”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家长们也热衷于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希望他们在学业和技能上“赢在起跑线”。而“校长”这个词,恰恰是这种标准化教育的代表。但是,“好父亲”呢?这个词听起来更具人情味,也更接地气。我猜想,这本书的作者可能是在批判一种过于功利化、过于注重外在成就的教育模式,而转而提倡一种回归家庭、回归亲情的教育理念。它可能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塑造,是价值观的引导。而父亲,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角色。这种“胜过”的说法,可能是在强调父亲的言传身教、榜样作用,以及其对孩子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心的培养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可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教育成功”所迷惑,而要关注孩子内心深处的成长,关注他们是否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健全、快乐的人。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一上来就带着一股“剑走偏锋”的意味,非常吸引人。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校长”这个词代表着一种系统性的、规范化的教育,是社会评价一个孩子成长的硬指标。而“父亲”,听起来就更像是生活中一个模糊但又至关重要的角色。当书名直接把“好父亲”放在“好校长”之上,并且用“胜过”来形容,我立刻就好奇起来:这是在批判现代教育的哪些方面?还是在强调家庭教育中,父亲所扮演的被低估了的角色?我猜想,这本书可能不是在讲具体的育儿方法,而是更侧重于探讨一种更深层次的教育哲学。它或许在提醒我们,在追求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是否忽略了他们人格的塑造,情感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确立。我个人觉得,一个父亲的言传身教,他的品德、他的担当、他对家人的爱,这些无形的东西,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可能贯穿孩子的一生。这本书可能就是在强调,这种来自家庭,来自父亲的,基于情感和榜样的教育,其力量是多么的强大,以至于在某些重要的维度上,能够超越学校教育所能达到的效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培养“野性而又高贵”的孩子(二) [Cultivate The Wild And Noble Chi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3989/58774f04N29264f87.jpg)
![男子汉养成术 [the Boy How To Help Him Succee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34156/57ee32c2Na81bd97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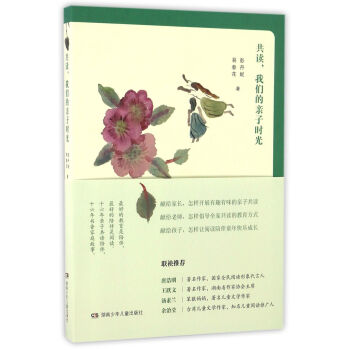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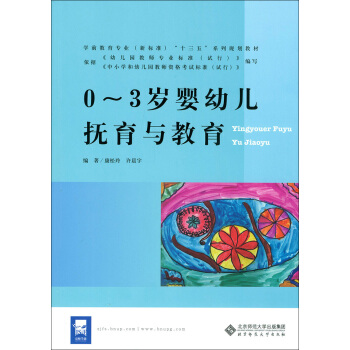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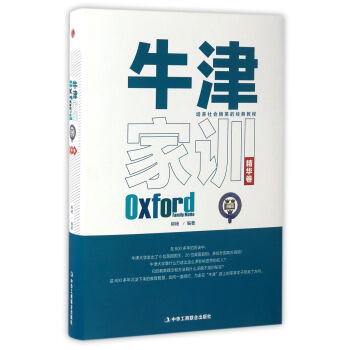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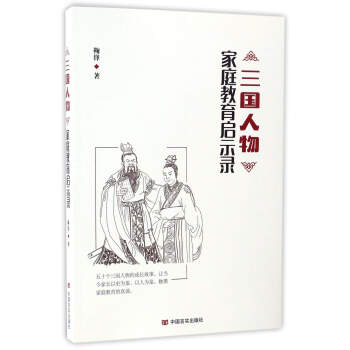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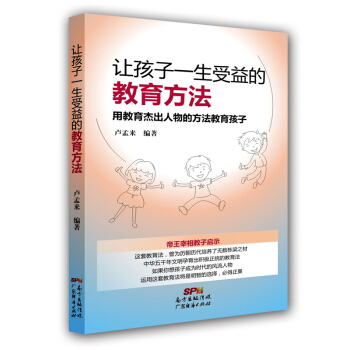


![中国“家庭·家教·家风”教育丛书:5岁孩子 5岁父母(5~6岁) [5 Year Old Child 5 Year Old Par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8705/591eeed4N27a6bdf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