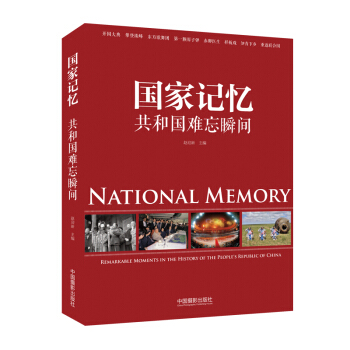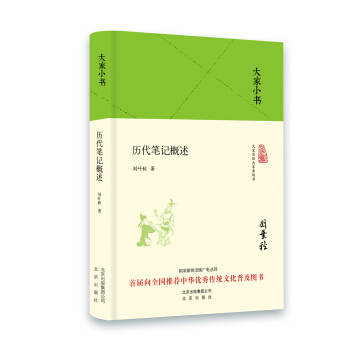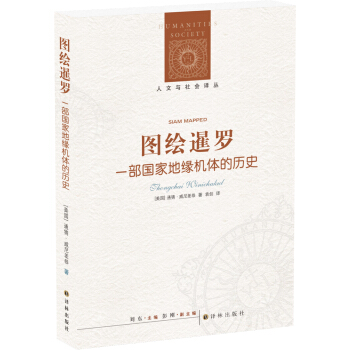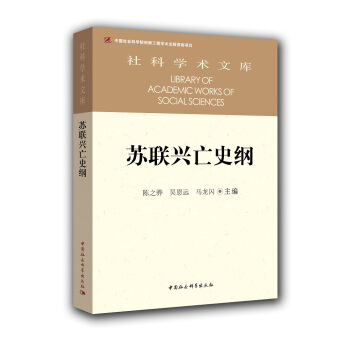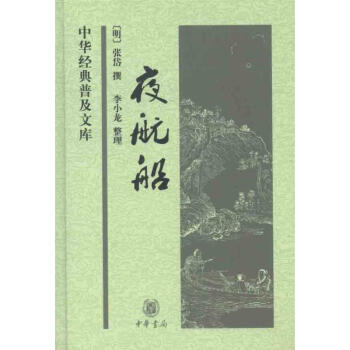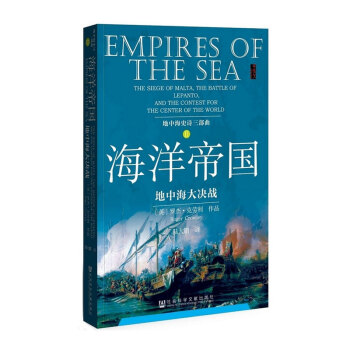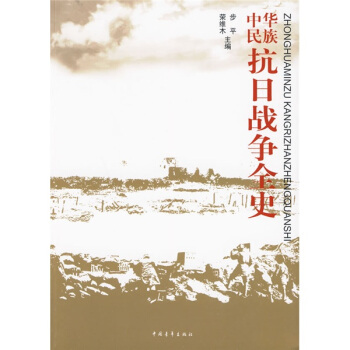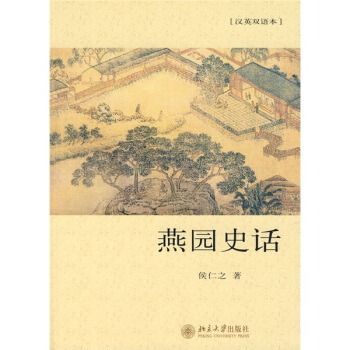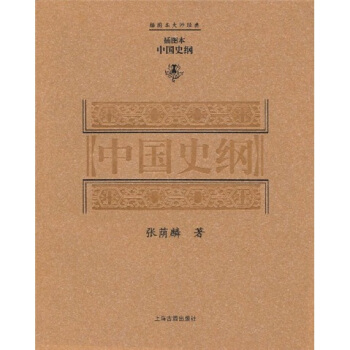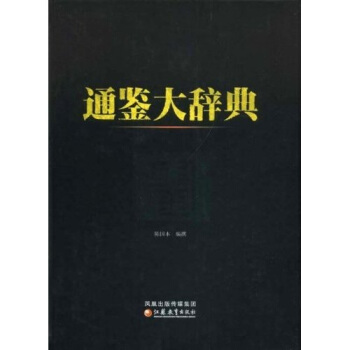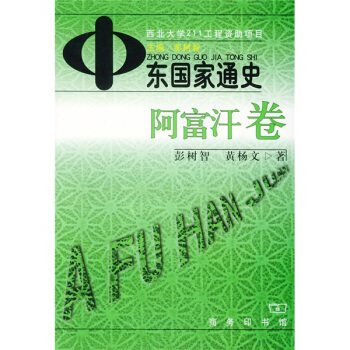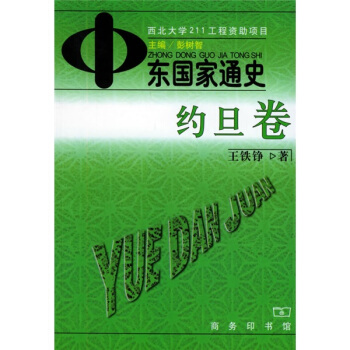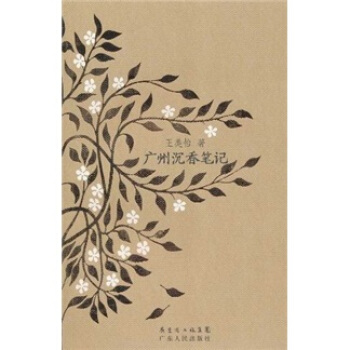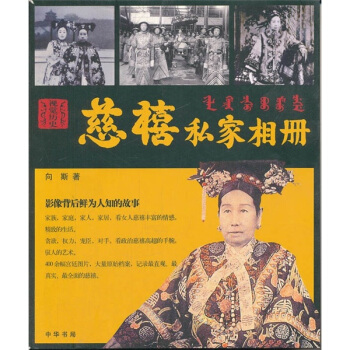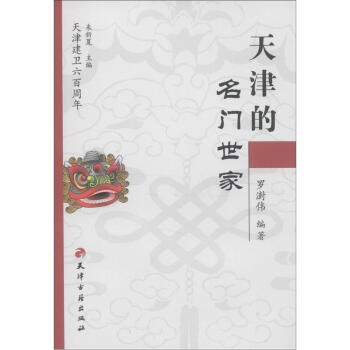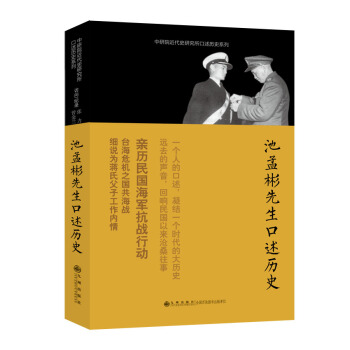![惊悦:C.S.刘易斯自传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7630/57d11e60Naa885d94.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如果你相信,或者哪怕只是怀疑,生长在现代社会的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也是可以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的;如果你好奇于刘易斯是如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理解信仰,并最终接受信仰,为信仰而辩护——你可以读《惊悦》。
如果你是英国文学的爱好者,或者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应该很容易就会喜欢上《惊悦》,并且同意这是一本供茶余饭后“闲读”的好书。
如果你相信童年经历对人的性格形成和精神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并且想了解一些个体真实的经历,那么刘易斯在《惊悦》中所记录的正是他对于自己早年人生的细致入微的回忆以及内省式的思考批评。
阅读《惊悦》较大的收获或许在于,刘易斯在这本书里努力记录描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一种徘徊于灵魂深处的渴望。
内容简介
《惊悦:C.S.刘易斯自传》是C.S.刘易斯的自传,这一年他55岁。自传从他出生的1898年写起,止于1930年前后。《惊悦》一书记录了刘易斯对于自己早年人生的细致入微的回忆以及内省式的思考批评,在记叙传主的成长历程中,呈现独特的生命体验。刘易斯在书中广征博引,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经典如数家珍;刘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则会读者的阅读倍添欢乐,惊喜连连。作者简介
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又称C.S.刘易斯,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他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尤其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尤深,堪称英国文学研究的巨擘。他一直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较著名的高等学府,被当代誉为“伟大的牛津人”,也是二十世纪较具领导地位的作家兼思想家。他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真正较喜爱的作者。C.S刘易斯一生的著作包括了诗集、小说、童话、文学批评,以及阐明基督教精义的作品,不下五十多本。较有名的代表作当首推七部描写“纳尼亚王国”的系列童话。这些作品在他于1963年逝世后,仍持续再版发行,盛况至今不衰。
目录
译者前言第一章 人之初
第二章 集中营
第三章 蒙特布莱肯与坎贝尔
第四章 拓展心智
第五章 文艺复兴
第六章 血青族
第七章 光与影
第八章 解脱
第九章 伟大的诺克
第十章 命运的垂青
第十一章 戛然而止
第十二章 枪炮和战友
第十三章 新视角
第十四章 将!
第十五章 开端
精彩书摘
第九章 伟大的诺克
你常常会遇到天性如此乖张之人,以至于审慎的诗人不愿冒险将他们搬上舞台。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9月的一天,穿过利物浦抵达伦敦之后,我又一路到了滑铁卢,再南下到大布克汉姆镇。我听说萨里郡是个“郊区”,而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却让我大吃一惊。我看到陡峭的小山,溪水潺潺的山谷,还有长着大树的牧地,按我威尔文和爱尔兰的标准就算是森林了;到处是蕨丛;一个长满红色、黄褐色和黄色植物的世界。甚至那些星星点点的郊区别墅(比现在少多了)也让我愉快。这些木头红瓦的房屋绿荫环绕,与贝尔法斯特郊区拉毛粉饰的丑陋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我以为会看到沙砾车道、铁门、没完没了的月桂和南美杉,结果我看到的是蜿蜒的盘山小路,通向柳条门,两边是果树和白桦。这些房屋在一个品味比我严肃的人眼里也许会显得可笑;然而我却忍不住觉得设计房屋和花园的人已然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即表达幸福。这些房屋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对家庭生活的渴望,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圆满的家庭生活;看着这些房屋你会想起茶盘。
我的老师在布克汉姆迎接我——“科克”,或者“诺克”,或者“伟大的诺克”,我的父亲、我的哥哥、还有我自己都是这么称呼他的。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听他的故事,因此我对于自己即将面对什么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即将忍受一场不温不火的情感淋浴,对此我已做好准备。这是我为自己无比幸福的逃学要付的代价;沉重的代价。我父亲讲过一个故事,尤其给我不详的预感。他很喜欢讲述在卢根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他遇到了某个麻烦或者困难,“老诺克”,是亲爱的“老诺克”把他拉到一边,双臂“轻轻地自然地”环住他,然后他亲爱的老八字胡就贴在了我父亲年轻的脸颊上,然后悄悄地说了些安慰的话……而此刻布克汉姆终于就在我的眼前,这位感伤主义老大亲自来迎接我了。
他身高超过6英尺,穿着很邋遢(我觉得像个园丁),瘦得活像一根钉齿耙,棱角分明,只要是看得见的部分;他蓄了八字须和连鬓胡,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就像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当时我非常关心的就是他的连鬓胡,您想必能理解。我的脸颊已经有些痒痒地不自在。他会立即贴上来吗?肯定会有眼泪;也许还有更糟的。我从来都受不了来自同性的拥抱和亲吻,这是我一生的弱点之一。(很不男子汉的一个弱点,顺便说一句。埃涅阿斯、贝奥武夫、罗兰、兰斯洛特、约翰逊、还有纳尔逊都没有这毛病。)
然而,老人明显耐着性子不表态。我们握了握手,尽管他这一握硬如铁钳,时间倒是不长。几分钟后,我们已经走出车站了。
“你现在,”科克说道,“是走在大布克汉姆和小布克汉姆之间的主干道上。”
我偷偷瞥了他一眼。这一地理学绪言是个大玩笑吗?还是说他在努力掩饰自己的情感呢?然而,他的脸上却只是一副坚定不移的严肃表情。我开始“没话找话”,就是我在那些晚会上学会的可悲套路,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跟我父亲只能这样说话。我说萨里郡的“景致”令我惊讶;比我期待的“天然得多”。
“停!”科克突然大喝一声,吓了我一大跳。“你说的天然是什么意思,你不期待天然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回答我不知道,我还在“没话找话”。一个接一个的回答被驳倒,我终于意识到他是真地想知道。他不是在没话找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为了斥责我;他就是想知道。我受了刺激,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回答。几个回合足以让我意识到我关于“天然”并没有任何清楚明了的概念,而且要是说我还知道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天然”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你难道意识不到,”伟大的诺克总结道,“你说的话毫无意义吗?”我做好了生一会儿闷气的准备,想当然地以为这个话题总算要结束了。但是我一辈子数这一次错得最厉害。科克分析完我的用词之后,又开始继续讨论我的整个立论。我对于萨里郡的植被和地质情况的期待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他把“基础”念成了“基主”)?是地图、照片、还是书本?我一样也说不出来。科克又做了一次总结——不带一丁点儿的感情,同样在我看来也没有带上一丁点儿的礼貌:“那么,你难道意识不到,你对于这个话题完全没有发表任何观点的权利吗?”
当时我们俩刚认识了三分半钟;但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谈话的这种基调由始至终地保留了下来,贯穿我在布克汉姆度过的所有那些年。眼前这个人与我父亲念念不忘的“亲爱的老诺克”相去不啻十万八千里。我了解我父亲铁打般只说真话的本意,也知道事实一旦进入他的大脑会经历怎样奇怪的变形,所以我确定他没有故意要骗我们。但是,如果说科克一生中曾经在某个时刻把一个男孩拉到一边,然后“轻轻地自然地”用他的连鬓胡去摩挲男孩的脸颊,那我宁愿相信他有时候会改变一下态度,然后轻轻地自然地拿一个大顶,把他那颗令人尊敬的、光秃秃的脑袋立在地上。
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接近纯粹的逻辑实体,那么这个人就是科克。晚出生几年,他会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人类使用发声器官的唯一目的是交流和发现真理,除此之外任何目的在他看来都是荒谬绝伦的。最不经意的一句话也会被他看作是辩论的邀请。我很快了解了他三种开场白的不同含义。大喝一声“停!”是为了阻止一大段已经让他忍无可忍的废话;不是因为他不够耐心(他从来没这么想过),而是因为这是浪费时间,会模糊判断力。更为急促而轻声的“抱歉!”是为了引入纠正或者辨析,这起到补充作用,预示着经过如此纠偏,你可以被允许说完你的话而不至于显得荒谬。最鼓舞人的是“我听着呢”。这意味着你说的话有意义,只是有待驳斥;你的话已经升格到颇有尊严的错误。驳斥(如果我们能走到这一步的话)的顺序一成不变。这是我在书里读到的吗?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有任何数据证明吗?我有任何基于个人经验的证据吗?如此这般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你难道意识不到,你没有任何权利,等等等等。”
有些男孩不会喜欢这种待遇;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牛肉加啤酒。我本来想当然地以为我在布克汉姆的闲暇时光会在很多“成人对话”中度过。而你早就知道了,这很不对我的胃口。在我的经历中,这意味着对话都是关于政治、钱、死亡、以及食物消化。我本以为喜欢这样的对话就跟吃芥末酱或者看报纸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水到渠成(目前为止,这三样期待统统落空了)。我唯一喜欢的两类谈话一是几乎纯与想像力相关的,二是纯理性的;前者如我跟我哥哥关于伯克思恩以及跟阿瑟关于瓦尔哈拉 的对话,或者如我和我的谷希舅舅关于天文学的对话。我不可能在任何科学领域有所作为因为所有科学的道路上都有数学这只拦路虎。数学中只要是仅仅凭逻辑思维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几何),我也做的很愉快;但是一旦有计算部分出现,我就无可救药了。我能掌握原理,但是我的答案永远是错的。然而,尽管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我有着科学的冲动,一如我有想像的冲动,而且我热爱推理的过程。科克激起并满足了我的一部分冲动。这些是真正有内容的对话。这个人考虑的不是你,而是你说了什么。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当然也气急败坏过;但是,总体上来说,我热爱这样的待遇。被无数次击倒之后,我开始学会一些防守和攻击的招数,我的智力慢慢也练出了肌肉。最终,我成了一个不能被小瞧的拳击对手,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这个长期以来致力于暴露我的含糊其辞的人最终提醒我要注意过度精确的危险,那真是了不起的一天。
如果科克无情的辩证法只是一个教学工具,我可能会感到厌恶。但是除此之外任何的谈话方式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无论年龄性别无人能幸免于他的逻辑反驳。有人会不愿意获得清晰的思路、不愿意被纠正错误,这对科克来说永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位颇有身份的邻居在某个星期天的拜访过程中以不容置疑地口吻总结道:“好吧,好吧,科克帕特里克先生,这个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你是个自由派,而我是保守派;我们自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时科克回答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想像自由派和保守派从一张桌子的两头对着一个长方形的‘事实’玩躲猫猫游戏吗?”如果一个不经意的来访者试图回避一个话题而这样说:“当然了,我知道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科克会举起双手惊叹道:“老天啊!我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任何观点可言。”他最喜欢的箴言是“花九个便士你就能获得启蒙,而你偏偏宁愿无知。”最普通的比喻也会被一再追问,直到那令人难堪的真相无处藏身。“德国人那些恶魔般的罪行——”“可是恶魔难道不是想像出来的吗?”——“好吧,那么,那些野蛮的罪行——”“可是没有哪个野蛮人干过这样的事!”——“好吧,我该叫它们什么好呢?”“我们就该简简单单称它们是人的罪行,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最让他鄙夷的莫过于其他校长们的对话,他自己是卢根中学校长的时候有时不得不在会议上忍受那些对话。“他们会走过来问我,‘对一个做了这样这样的事情的男孩,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老天啊!就好像我对任何人或者任何男孩有过某种态度似的!”有时候,但是很罕见,他会被迫使用嘲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嗓音会比往常更严肃,只有他鼻孔的扩张会让那些熟悉他的人窥破实情。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表了以下这段评论:“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 是全宇宙最重要的生命体之一。”
可以想像科克帕特里克夫人的日子不容易;且看以下这个场景:她的丈夫因为某个奇怪的失误发现自己身处客厅,他太太组织的一场桥牌会刚刚开场。大约半个小时后,人们观察到他的太太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起身离开了房间;几个小时之后,“伟大的诺克”却被发现依然坐在一张板凳上,在七位上了年纪的太太们中间(“倦容满面地” )恳求她们明确定义自己的用词。
我已经说过他几乎只讲逻辑;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他曾经是个长老会信徒,但我遇见他时已经是无神论者。他星期天在花园里劳动,就跟他工作日大多数时候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他年轻时身为长老会信徒的一个有趣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每到星期天劳动的时候他总会穿一件不同的、更体面的外套。一位阿尔斯特苏格兰人也许会不再信仰上帝,但是他不会在主日穿着工作日的衣服。
既已说明他是个无神论者,我就得赶紧补充一句他是个老派、严肃且不带偏见的十九世纪类型的“理性主义者”。因为自那以后无神论就开始落魄了,逐渐与政治同流合污,学会了趟浑水。如今给我寄反上帝杂志的匿名赠送者毫无疑问是想刺痛我体内的基督徒;而他真正刺痛的是我体内那位“前无神论者”。我从前的同志以及科克从前的同志(这更为重要)竟然已经堕落到如此程度,这让我深以为耻。真所谓今非昔比;哪怕麦克卡比的文章也是个男人写出来的。我认识科克的时候,他的无神论的燃料属于人类学的、悲观主义的类型。他精通《金枝》和叔本华。
读者应该记得我自己的无神论和悲观主义早在我去布克汉姆之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了。我在那里只是获得了新的弹药,用以保卫一个已然选定的立场。即便这些也是我间接从他的思想风格中获得的,或者来自于独立阅读他的书籍。他从未在我面前攻击过宗教。有一类事实没有人能基于对我人生的表面了解推断得出,这是其中之一,但这就是一个事实。
我星期六到加斯顿斯(诺克家房子的名字),他宣布我们星期一开始读荷马。我解释说除了阿提卡方言 我从没读过一个字的其它任何方言,我满以为告诉他这一点他就会从某些有关史诗语言的入门课着手,再过渡到荷马。他的回答只是他在对话中经常会发的一个鼻音,我只能写作“哼。”这让我很是忐忑不安;星期一早晨醒来时我对自己说:“这就要荷马了!天哪!”这个名字让我肃然起敬。九点整我们在楼上的书房里坐下,开始上课,很快这个屋子对我来说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屋里有一张沙发(他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并排坐在上面),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一个人时坐椅子),一个书橱,一个煤气炉,还有一张镶起来的格莱斯顿先生 的照片。我们打开各自的《伊利亚特》第一卷。诺克没有做一个字的介绍便以“新”发音把前二十句左右的诗文大声念了一遍,这种发音我以前从没听到过。和斯缪吉一样,他也是位吟诵者;他的声音不如斯缪吉甜醇,然而他饱满的颚音和翻卷的R以及多变的原音感觉很适合青铜器时代的史诗,正如斯缪吉如蜜似糖的嗓音适合贺拉斯的诗。科克虽然在英格兰住了那么多年,却还是满口纯正的乌尔斯特音。随后他翻译了大约一百句,只有很少、非常少的解释。我还从没见过哪个经典作家被如此狼吞虎咽。译完之后他递给我一本克鲁西斯的《词典》 ,告诉我把他刚才翻译的部分再读一遍,能读多少就读多少,随后他便离开了房间。这看起来是个奇怪的教学方式,但是很管用。起先,在他开拓出来的这条路上我只能走一小段,但是每天我都能走得更远些。很快我就能全程跟上了。接着我能比他指出的最北面再多走一两行。再后来看看能多走多少成了一种游戏。在当时的阶段科克似乎更看重速度而不是准确性。最大的收获是我很快就能不经过翻译(哪怕是在心里)便读懂很多文本;我开始用希腊文思考了。这是学习任何语言都需要跨越的决定性界线。有人只有在词典中寻找某个希腊词汇的时候这个词对他来说才是活的,然后他会找一个英语词来代替这个希腊词,这样的人根本不是在读希腊语;他们只是在解决一个谜题。“Naus的意思是船”,这样的公式是错的。“Naus”和“船”意指同一样事物,但它们并不互为定义。在Naus的背后,在navis和naca 的背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副画面,一个暗憧憧的长长的物体,有帆有桨,爬过风尖浪顶,我们不需要好事的英语单词横插一手。
这段时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作息规律,从此以后在我心里成为一种原型,以至于我现在说“正常的”一天(并且悲叹正常的日子如此稀少)指的仍然是在布克汉姆时的作息表。如果我能随心所欲,我就会永远过我在那里过的日子。我会选择永远在八点整吃早饭,九点坐到书桌前,在那里读书写作直到一点。如果十一点的时候有人能给我拿来一杯浓茶或者咖啡,那就再好不过。出门一步,来一品脱啤酒,效果就差多了;因为男人不喜欢一个人喝酒,而你要是在酒吧跟朋友碰面,休息时间就可能要超过十分钟。一点整的时候午饭得在桌上摆好;最晚两点我就会在路上了。不跟朋友一起,除了偶尔的休息时间。散步与谈话是两样极大的乐趣,但是把二者合在一起却是个错误。我们自己发出的噪音把外面世界里的声音和安静一齐抹去了;而谈话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向抽烟,那就只能跟自然拜拜了,单就我们的某个感官而言。唯一可以一起散步的朋友得和你有着完全一致的关于乡野的品味,包括那里的每个色调(正如我假期时在阿瑟身上找到的),一个眼神,一次驻足,至多是用肘轻轻一推,就足以让我们心领神会彼此的喜悦。散步归来应该刚刚好是上茶的时候,不能晚于四点一刻。茶点应该独自享用,我在布克汉姆的时候只要科克帕特里克夫人不在家就是这样独个儿喝茶;诺克本人鄙视茶歇。吃东西和读书是相得益彰的两件乐事。当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边吃东西边读。在饭桌边读诗不啻为一种亵渎。你需要的是那种八卦类的、杂乱无章、随处都能翻看的书。我在布克汉姆学会这样去读的书有鲍斯威尔 ,希罗多德的英译本,以及兰的《英国文学史》。同样适合边吃边读的还有《项狄传》,《伊利亚随笔》以及《忧郁的解剖》。五点就又该工作了,然后一直干到七点。接着,晚饭以及饭后就是聊天时间了,或者没人聊的话就可以来点轻松读物;之后,除非你是要跟你的老伙计们混一晚上(在布克汉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否则晚于十一点上床就没道理了。可是该把写信安排在什么时间呢?您忘了我是在描绘我跟科克一起时的幸福生活,或者是我但愿自己能过上的理想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你几乎不会收到信,永远不需要担心邮差来敲门。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我每周只收发两封信;一封来自我父亲,这是职责,一封来自阿瑟,这是每个星期的亮点,因为我们会把所有令我们陶醉的乐趣一股脑儿倾倒在纸上,告诉彼此。我哥哥这时正在军队服役,他的信内容和间隔都更长些,我的回复也是如此。
这便是我的理想生活,而当时这种“稳定的、平静的、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几乎)一度实现了。那以后我基本上没能过这样的生活,这毫无疑问对我是件好事,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彻底自私的生活。自私,但不是自我中心: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心灵会被引向一千种事物,其中没有一件跟我自己有关。这一区别并非无足轻重。我认识的人里最幸福也最让人愉快的一个恰恰极其自私。另一方面,我也认识一些能真正自我牺牲的人,可他们的人生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是一种折磨,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自怨自艾和自怜自惜。任何一种情形最终都会摧毁人的灵魂。但是末日来临之前,还是给我一个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哪怕是占我的便宜)然后大谈特谈其它各种事情的家伙,也别给我一个一面为我服务一面总在说他自己的人,他的付出就是持续不断的对别人的指责,持续不断地要求获得怜悯、感激和赞誉。
当然,科克并没有让我除了荷马谁都不读。“最无聊二人组”(狄摩西尼 和西塞罗 )是不可能不读的。还有(哦,多么美妙!)卢克来修、卡图卢斯、塔西佗、希罗多德。以及我至今都没法真正喜欢的维吉尔。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作。(说也奇怪我竟然可以活到五十好几还没读过一个字的恺撒 。)有欧里彼得斯、索福克里斯、埃斯库罗斯。傍晚跟着科克帕特里克夫人学法语,教学方法就跟她先生教荷马差不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读完了很多很好的小说,很快我就开始自己买法语书了。我曾希望能学英语散文,但是科克从来没给我读过一篇英语散文,不知道是因为他觉得没法忍受我写的散文,还是因为他很快猜到我掌握的散文艺术(对于英语散文他几乎肯定是嗤之以鼻的)已经足够了。第一个星期前后他给过我一些英语阅读的指导,不过一旦发现就算没人管,我也不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就给了我绝对的自由。在我后来的学习阶段我们又开始了德语和意大利语。他的教学法依然如故。在匆匆接触了语法做了一些练习之后,我就一头扎进了《浮士德》和《地狱》。意大利语我们是成功拿下了。而德语我毫不怀疑如果我跟科克能再多待一些时间也一样可以拿下。但是我离开得太早了,我的德语也就一辈子停留在了学生水平。每次我想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就总会被这样那样更紧急的任务打断。
……
前言/序言
译者前言
1.
出版于1955年的《惊悦》是英国作家C.S.刘易斯的自传,这一年他57岁。自传从他出生的1898年写起,止于他皈依有神论的1930年前后,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我的前半生”。在最后一章“开端”里,刘易斯告诉读者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有神论过渡到基督教信仰的,他给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也是婉转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继续去写1930年之后的二十多年生命经历。因为,刘易斯觉得,在拥有信仰之后,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关注“自己的观点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是终于“走出自己”了。
对于有信仰者来说,刘易斯的所谓“走出自己”应该不难理解。上帝是万物之源,仰望上帝便是生而为人的本分;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不再为我自己而活,“我”也因此变得微不足道。刘易斯对于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二十多年的人生感受,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微不足道”了。
细读《惊悦》的前十四章,最让人震撼的是作者强大的记忆力。一位55岁的男子,竟然可以清晰地记得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某个时刻,周围的情景,内心的思绪,某种强烈的感触,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只发生在昨日。刘易斯大脑中的回忆触角几乎可以探伸至岁月深处的每个角落——一只盖着苔藓和嫩枝小花的饼干桶带给仍是幼儿的他关于美的第一次体验;童年恶梦的昆虫主题是因为育儿室里的一册绘本,上面有一只带着活动触角的鹿角甲虫;而第一句直击7岁少年灵魂的诗歌至今还在他耳畔回响: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喊,
美丽的巴尔德尔
死了,死了——
就是一个有着这样惊人的记忆力的刘易斯,对于离他自己最近的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生命经历却说: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已经不重要了。而我们知道的是,在那二十几年里,刘易斯写出了他最广为人知的经典奇幻小说《纳尼亚传奇》;二战期间他的名字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因为他应邀在BBC电台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系列讲座,成功鼓舞了英国民众抵抗纳粹德国的士气,战后这些演讲稿被结集出版,名为《返璞归真》;而今天你走进任何一家基督教书店,都会发现《返璞归真》仍然是那里畅销书榜单上的第一名。几乎刘易斯所有最重要的仍然拥有广泛读者的书,都是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写成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竟然让我想起托尔斯泰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许在刘易斯看来,他的后半生不必写进自传,恰恰因为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与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并无本质不同,他们的人生都已进入同样的完全臣服于上帝的“忘我”境界,而在他自己看来,这显然正是他作为人应该过的唯一一种正当而幸福的生活。至于他在现世的成败得失,与他的精神生活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管他取得多少世俗眼光中的“成就”,在他内心深处永远是“微不足道”这四个字。与此相反,他的前半生既背离上帝,也便充满了各种独特的“不幸”,各种跌宕起伏,各种“堕落”、痛苦、挣扎、绝望,以及最终的希望和救赎。回忆这些经历并用文字如实记录下来,对刘易斯来说,也是在整理追溯自己走向信仰的精神之旅,而这份真诚的追忆,当然更是他基督教信仰的见证,又一份独一无二的见证。
2.
记得翻译《惊悦》期间,一位诗人朋友曾经随口问起我眼下在译什么书,我告诉他是C. S.刘易斯的自传。“可是,有谁会看这本书呢?”他脱口而出。虽然在这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旦问题被提出来,我倒觉得提问者的困惑既真实也容易理解。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刘易斯的书,也不知道他是谁,自然不会想到读他的自传。而我和我的编辑朋友之所以一拍即合,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立即动手翻译刘易斯的自传,也是因为我们俩早已是刘易斯的“粉丝”,他重要的护教类作品几乎都读过一遍。所以,似乎确实可以这么说,《惊悦》这本书首先是为熟悉并喜爱刘易斯的读者们准备的,而这样一个读者群在中国显然也是存在的。刘易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著名作品在两岸三地都早已有了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即便是我自己小小的朋友圈里也总能找到愿意坐下来聊聊刘易斯的朋友。
另一方面,如果是一位从没有接触过刘易斯的读者,当他翻开《惊悦》,会不会也有如书题所言的体验呢——惊讶于意想不到的喜悦?我想这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凡这位读者会对我说到的以下几点中的任何一点生发出兴趣。
如果你相信,或者哪怕只是怀疑,生长在现代社会的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也是可以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学者,英国中世纪文学研究者,儿童文学作家,剑桥大学终身教授,是如何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全英格兰“最不情愿的一个皈依者”;如果你好奇于这样一个皈依者如何自始至终保持着最清醒的理性主义,他又是如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来认识、理解信仰,并最终接受信仰,为信仰而辩护——你可以读《惊悦》。
如果你是英国文学的爱好者,或者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应该很容易就会喜欢上《惊悦》,并且同意这是一本供茶余饭后“闲读”的好书。我已经记不清刘易斯在他的传记里提到了多少西方作家和作品,其中大多数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经典,你不一定认同他对书的个人品味,但很可能他的某句话,某个暗示、揶揄,就会让同样熟悉经典的你唇角泛起会心的一笑。而你若碰巧也常读英国散文,那么刘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肯定会让你的阅读倍添欢乐,惊喜连连。
如果你相信童年经历对人的性格形成和精神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并且想了解一些个体真实的经历,那么刘易斯在《惊悦》中所记录的正是他对于自己早年人生的细致入微的回忆以及内省式的思考批评。刘易斯幼年丧母,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可以说直到他父亲去世,父子之间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这种始于童年的与父辈的精神隔阂,其实也正是我自己以及很多同龄人共有的经历,读来难免唏嘘感慨。但更重要的乃是刘易斯的反省精神,他在描述父亲的种种不可理喻的同时,总不会忘记强调自己因年轻无知而表现出的任性、自私、不体谅甚至残忍。而刘易斯与他唯一的哥哥始终兄弟情深,面对父亲很早达成攻守同盟,不乏令人捧腹又耐人寻味的童年趣闻。至于每个人此生会交到的第一个朋友,遇到的第一位让你或恐惧或敬畏的老师,第一位终生难忘的启蒙导师,第一次这样那样的致命诱惑,刘易斯都会向你娓娓道来,诚实地与你分享他 大脑中每一寸或美丽或高贵或痛苦或羞辱的记忆之地。
最后,对我个人来说,翻译《惊悦》最大的收获在于,刘易斯在这本书里努力记录描述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一种徘徊于灵魂深处的渴望;刘易斯用了一个最初来自德语的词汇“Sehnsucht”来命名这种渴望,大致可以解释为对不明之物的强烈渴望。至于“喜悦”这个中心词,只是用来描述当这份渴望获得满足时那种稍纵即逝的、极大的、幸福到锥心彻骨的感觉。这正是我一直感觉到却苦于无法把握、难以名状的存在体验,如果你也有着同样的让你充满困惑的渴望,那么《惊悦》也许正是你该读的下一本书。刘易斯认为自己的前半生始终没有弄明白这种渴望的对象,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味追求“喜悦”,错把这种感觉本身当作了渴望的目标。在他接受信仰之后,目标当然立即明确了,就是上帝,刘易斯对天堂的解释便是与上帝同在,既深刻又简单。而值得回味探究,值得与人分享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个充满彷徨和困惑的过程,给后来的朝圣者们一点提醒,一些慰藉。
3.
2015年是我做文学翻译的第十个年头,但我译书并不勤快,最近完成的《惊悦》只是第7部作品。《惊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整本书的翻译过程相比我之前的经历,无疑是最顺畅的一次,有点儿一气呵成的感觉。原因应该有很多,自传的结构相对简洁,刘易斯的用词平实,风格流畅,字数也不多,但这都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从翻译一开始便接连亲历“惊悦”,翻译中一些主要的困难随之不攻自破。
前文提到,刘易斯在自传中提到了无数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事实上,他兴之所至,还常常会引用某部作品中的原话,却又不说明出处。作为一个西方经典阅读量不及作者万一的译者,这些每隔两三页就会出现的人名书名,以及突然冒出来的引文,着实挺让我头疼。他提到或者引用的作者作品虽然大都是文学界认可的大家,但有些也相当冷僻,并非普通读者所喜闻乐见,有些甚至维基百科上都难觅踪迹。所幸我的烦恼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因为翻译到第二章时,我就无意间遇到了一个题为“LEWISIANA.NL”的网页,细看之下,是一位北欧人为《惊悦》全书出现的引用和典故所做的完整注解,按章节索引。内容极其细致全面,很多注解不仅包括作者和原著基本信息,甚至详细到引文出现在原著第几章第几页,也常常提供上下文给读者做参考。我当时的感觉,说如获至宝、喜出望外,都不算夸张。
过了没多久,又一个惊喜不期而至。《惊悦》全文共十五章,每一章开头都会有一句独立引文,呼应暗示本章内容的精神,所以充分理解这些引文对于做好整个章节的翻译显得至关重要。LEWISANA.NL对这些引文虽然也都做了出处说明,但也仅限于此。有一次,我又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找到了一篇刘易斯研究专家约翰?布莱莫专门讨论《惊悦》各个章节标题以及题头引文的长篇论文 ,可以想像那一刻我心头的雀跃。所以读者们在中译本中读到的关于题头引文的注解大部分内容是基于布莱莫先生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我把握每个章节的要旨也有很大帮助,几乎是立竿见影地提高了我的翻译效率。
最后一个惊喜出现在翻译的尾声阶段,2015年夏天我去了离伦敦不远的苏塞克斯郡开会,旅途全部的空余时间都用来完成《惊悦》最后三章的翻译。我按计划在离开英国前去了一趟牛津大学,寻访刘易斯故居。一路滂沱大雨,坐了火车又换汽车,中午时分终于到达牛津镇,下车时雨刚好停了。在步行去故居的路上,我经过了牛津的圣三一教堂,记起那里是刘易斯生前常去的教堂。于是当然要进去看看。眼前的入口似乎通向一个弄堂,走进去,果然是个窄窄长长蜿蜒向前的石弄,两边石墙上爬满了青藤,虽是阴雨天气,路面却也干爽。石弄里暗影憧憧,格外清凉幽静,我一路走着,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还有偶尔几声雀鸣,感觉就像走在梦境里。百余米之后,走到尽头,推开矮矮的院门,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就是教堂前的空地和公墓了。一片青草地上立着高高低低形状各异的墓碑,还有好几棵葱郁的大树。我径直朝教堂走去,大门关着,推不开。
于是我又退到公墓边,一眼看到一块小小的牌子上写着“刘易斯墓地”。我怎么没想到他有可能就是葬在这里呢?我放轻脚步向前走,心里琢磨着,这么多墓碑,恐怕得好一会儿才能找到刘易斯。正想着,走到一棵树下,一低头,一块长方形水平放置的墓碑上正写着“怀念我的弟弟克莱夫·斯坦普尔斯·刘易斯(1898-1963)”,再往下是刘易斯哥哥沃伦的生卒年月,这应该先是沃伦为刘易斯立的墓碑,后来沃伦自己也与弟弟合葬于此。我在墓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心里起伏感动,难以描摹。随后我在墓碑边一截湿漉漉的老树根上坐了下来,看到旁边一丛不能辨识的紫花,正开得热闹,毕竟是8月。我享受了一会儿少有的内心与周遭完全合拍的宁静感,直到天又开始下雨,我看着落在自己赤裸的臂膊和同样赤裸光滑的墓碑上的雨滴,八月的雨让身体感到清凉的惊喜。这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愉悦传到大脑,我身在梦里的感觉却不减反增,这时想起了刘易斯谈什么是我们最清晰的意识——“就是意识到自己碎片的、昙花一现的本质,觉醒到我们并非做了一个梦,我们就是一个梦而已。”
两天后,我完成了《惊悦》全书的翻译。
用户评价
从情感共鸣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种超越时空的连接感。探讨“早期生活”必然涉及到青春期的敏感、对归属感的渴望,以及面对宏大世界时的渺小感。刘易斯无疑是一位极具共情力的作家,我期待他能以一种坦诚到近乎残忍的笔触,描绘出那些成年人常常选择遗忘或美化的自我怀疑与焦虑。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思想巨人,也曾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这种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如果他能成功地捕捉到那种“初识”的震撼——无论是对自然之美、文学之妙,还是对某种更高实在的朦胧感知——那么这本书就能成为一本关于“如何保持敏锐”的指南。它不只讲述“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讲述“那感受起来是什么样的”,这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所在。
评分作为一名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我更看重的是这本书如何展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原材料”是如何被塑造的。我们了解刘易斯的成熟观点,但真正引人入胜的是那些观点尚未成形之前的混沌状态。这本书应该会揭示他早期阅读了哪些书籍、遇到了哪些影响深远的人物,以及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是如何与主流思潮进行抗争或融合的。我期待看到他对特定文学作品、哲学论点所做出的早期反应,这些反应或许稚嫩,但却代表了其思想原型的萌芽。如果作者能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他如何辨识、过滤和吸收外界信息,从而构建起自己的内在宇宙,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极高了。它提供了一个观察“思想铸造厂”内部运作的独特视角,让我们理解卓越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无数次内部对话和外部碰撞的结果。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它仿佛不是一部简单的个人回忆录,而是一段深入灵魂的旅程。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和思想碰撞,才能塑造出那样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它承诺揭示这位巨匠内心世界的形成过程,那种从迷茫到顿悟,从怀疑到坚定的转变,一定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内心戏。它不仅仅是记录过去,更像是一场对“惊悦”这一核心体验的哲学探讨。我期待看到的是,作者如何细腻地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灵感火花,以及那些塑造他世界观的关键时刻。想象一下,跟随他的脚步,重温那些青春的困惑、学术的探索,以及最终找到信仰归宿的激动,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这本书的价值可能远超于对刘易斯生平的了解,它更像是一份关于如何诚实面对自我、追寻生命意义的行动指南。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我想一定非常独特。考虑到刘易斯的文学功底和清晰的逻辑思维,我预估它不会是一部线性叙事的流水账。更可能的是,它会围绕着“早期生活”这一主题,以一种非编年体的方式,将那些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体验碎片化地呈现出来,然后通过对“惊悦”这一主题的反复回溯与深化,最终将这些碎片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精神肖像。我猜想,作者在讲述那些看似平常的童年场景或求学经历时,会不经意间植入日后理解的智慧,让当时的困惑与后来的洞察形成一种迷人的对比。这种“已然知晓”的视角,会给予读者一种独特的阅读乐趣——看一个伟大的头脑如何艰难地走过它必经的弯路。这种复杂的叙事编排,正是区分一本普通传记和一部经典作品的关键所在。
评分阅读体验上,我非常期待它能有一种沉浸式的代入感,仿佛作者就坐在我对面,娓娓道来那些早年的心绪。从书名就可以推断,作者必然会深入剖析“惊悦”——那个无法用逻辑完全解释的、超越性的喜悦瞬间——是如何渗透和重塑他早期生活的基调。我尤其好奇他是如何处理那些看似矛盾的经历的:一个早期的无神论者,又是如何一步步被那些不期而遇的“光亮”所吸引和俘获的?这种从理性堡垒中走向信仰的历程,想必充满了微妙的心理拉锯战。如果作者能够将那种探寻过程中的挣扎、困惑和最终的豁然开朗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么这本书就不再是枯燥的自述,而是一部关于心智成长的史诗。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阅读的节奏感,时而深沉内省,时而又因某个发现而欢快雀跃,如同一次精彩的探险,最终揭开了一个深藏的秘密。
评分这书不错囤起来慢慢看书很新研读
评分送货快,服务态度好。
评分挺好的质量不错
评分价格实惠,送货快,谢谢京东。
评分这书不错囤起来慢慢看书很新研读
评分质量不错,价格便宜,优惠价购入
评分好书,还没来得及看
评分挺好的质量不错
评分当故事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