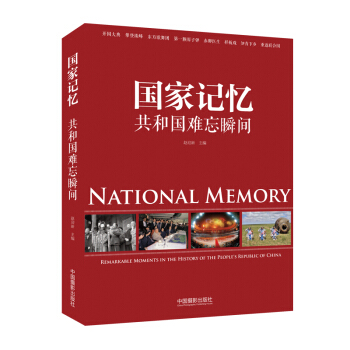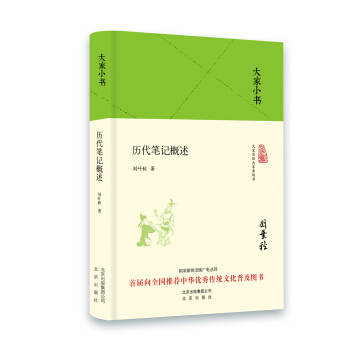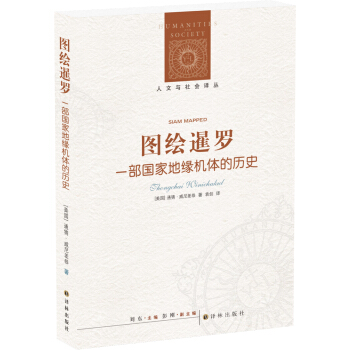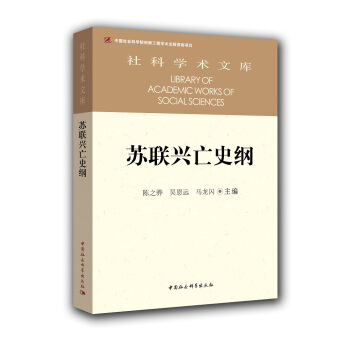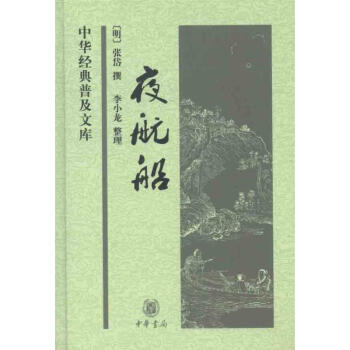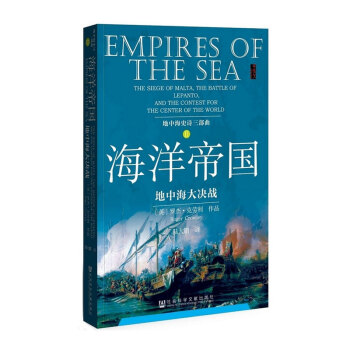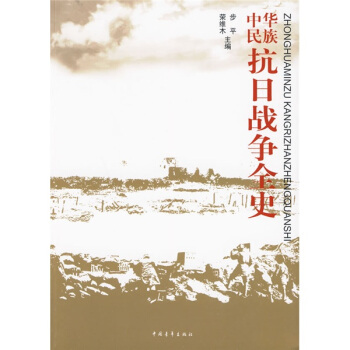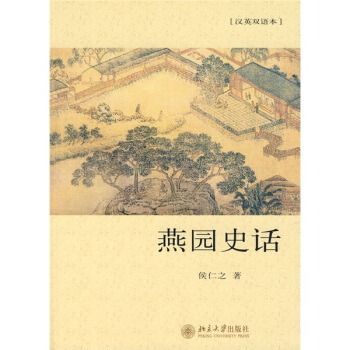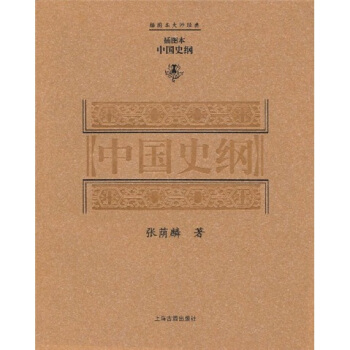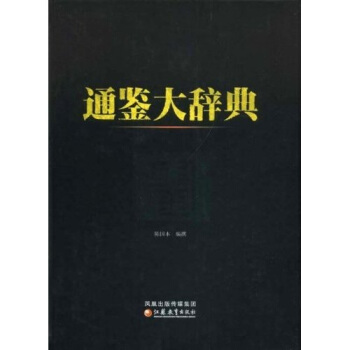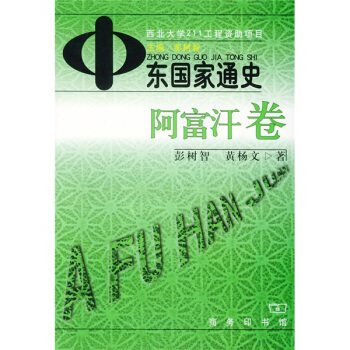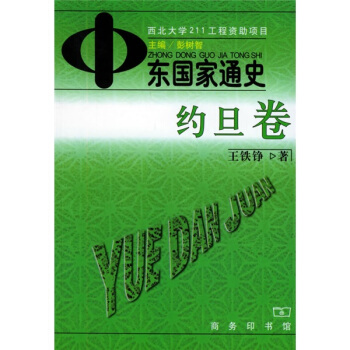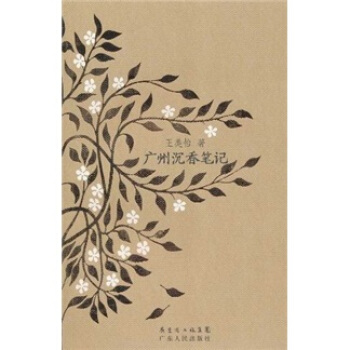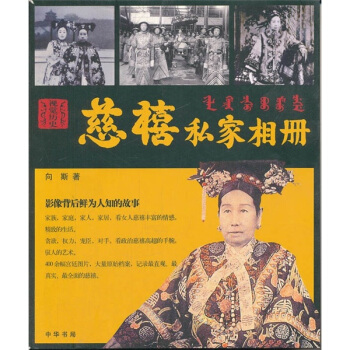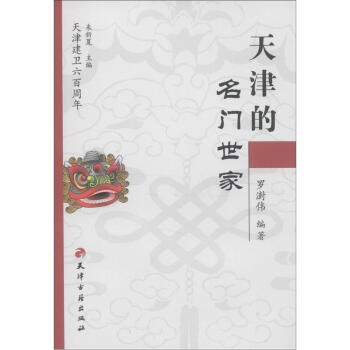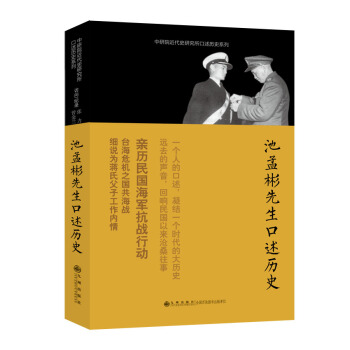![驚悅:C.S.劉易斯自傳 [Surprised by Joy The Shape of My Early Lif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7630/57d11e60Naa885d94.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如果你相信,或者哪怕隻是懷疑,生長在現代社會的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也是可以過一種有信仰的生活的;如果你好奇於劉易斯是如何完全通過自己的理性來認識、理解信仰,並最終接受信仰,為信仰而辯護——你可以讀《驚悅》。
如果你是英國文學的愛好者,或者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你應該很容易就會喜歡上《驚悅》,並且同意這是一本供茶餘飯後“閑讀”的好書。
如果你相信童年經曆對人的性格形成和精神成長有著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並且想瞭解一些個體真實的經曆,那麼劉易斯在《驚悅》中所記錄的正是他對於自己早年人生的細緻入微的迴憶以及內省式的思考批評。
閱讀《驚悅》較大的收獲或許在於,劉易斯在這本書裏努力記錄描述瞭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一種徘徊於靈魂深處的渴望。
內容簡介
《驚悅:C.S.劉易斯自傳》是C.S.劉易斯的自傳,這一年他55歲。自傳從他齣生的1898年寫起,止於1930年前後。《驚悅》一書記錄瞭劉易斯對於自己早年人生的細緻入微的迴憶以及內省式的思考批評,在記敘傳主的成長曆程中,呈現獨特的生命體驗。劉易斯在書中廣徵博引,對自己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經典如數傢珍;劉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則會讀者的閱讀倍添歡樂,驚喜連連。作者簡介
剋萊夫·斯特普爾斯·劉易斯,又稱C.S.劉易斯,是英國20世紀著名的文學傢,學者,傑齣的批評傢。他畢生研究文學、哲學、神學,尤其對中古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造詣尤深,堪稱英國文學研究的巨擘。他一直任教於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這兩所英國較著名的高等學府,被當代譽為“偉大的牛津人”,也是二十世紀較具領導地位的作傢兼思想傢。他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真正較喜愛的作者。C.S劉易斯一生的著作包括瞭詩集、小說、童話、文學批評,以及闡明基督教精義的作品,不下五十多本。較有名的代錶作當首推七部描寫“納尼亞王國”的係列童話。這些作品在他於1963年逝世後,仍持續再版發行,盛況至今不衰。
目錄
譯者前言第一章 人之初
第二章 集中營
第三章 濛特布萊肯與坎貝爾
第四章 拓展心智
第五章 文藝復興
第六章 血青族
第七章 光與影
第八章 解脫
第九章 偉大的諾剋
第十章 命運的垂青
第十一章 戛然而止
第十二章 槍炮和戰友
第十三章 新視角
第十四章 將!
第十五章 開端
精彩書摘
第九章 偉大的諾剋
你常常會遇到天性如此乖張之人,以至於審慎的詩人不願冒險將他們搬上舞颱。
切斯特菲爾德伯爵
9月的一天,穿過利物浦抵達倫敦之後,我又一路到瞭滑鐵盧,再南下到大布剋漢姆鎮。我聽說薩裏郡是個“郊區”,而車窗外掠過的風景卻讓我大吃一驚。我看到陡峭的小山,溪水潺潺的山榖,還有長著大樹的牧地,按我威爾文和愛爾蘭的標準就算是森林瞭;到處是蕨叢;一個長滿紅色、黃褐色和黃色植物的世界。甚至那些星星點點的郊區彆墅(比現在少多瞭)也讓我愉快。這些木頭紅瓦的房屋綠蔭環繞,與貝爾法斯特郊區拉毛粉飾的醜陋建築不可同日而語。我以為會看到沙礫車道、鐵門、沒完沒瞭的月桂和南美杉,結果我看到的是蜿蜒的盤山小路,通嚮柳條門,兩邊是果樹和白樺。這些房屋在一個品味比我嚴肅的人眼裏也許會顯得可笑;然而我卻忍不住覺得設計房屋和花園的人已然實現瞭他們的目標,即錶達幸福。這些房屋讓我心裏升起一種對傢庭生活的渴望,我從來沒有體驗過圓滿的傢庭生活;看著這些房屋你會想起茶盤。
我的老師在布剋漢姆迎接我——“科剋”,或者“諾剋”,或者“偉大的諾剋”,我的父親、我的哥哥、還有我自己都是這麼稱呼他的。我們從小到大一直都在聽他的故事,因此我對於自己即將麵對什麼有著清醒的認識。我即將忍受一場不溫不火的情感淋浴,對此我已做好準備。這是我為自己無比幸福的逃學要付的代價;沉重的代價。我父親講過一個故事,尤其給我不詳的預感。他很喜歡講述在盧根中學的時候,有一次,他遇到瞭某個麻煩或者睏難,“老諾剋”,是親愛的“老諾剋”把他拉到一邊,雙臂“輕輕地自然地”環住他,然後他親愛的老八字鬍就貼在瞭我父親年輕的臉頰上,然後悄悄地說瞭些安慰的話……而此刻布剋漢姆終於就在我的眼前,這位感傷主義老大親自來迎接我瞭。
他身高超過6英尺,穿著很邋遢(我覺得像個園丁),瘦得活像一根釘齒耙,棱角分明,隻要是看得見的部分;他蓄瞭八字須和連鬢鬍,下巴颳得乾乾淨淨,就像弗朗茨·約瑟夫一世 。當時我非常關心的就是他的連鬢鬍,您想必能理解。我的臉頰已經有些癢癢地不自在。他會立即貼上來嗎?肯定會有眼淚;也許還有更糟的。我從來都受不瞭來自同性的擁抱和親吻,這是我一生的弱點之一。(很不男子漢的一個弱點,順便說一句。埃涅阿斯、貝奧武夫、羅蘭、蘭斯洛特、約翰遜、還有納爾遜都沒有這毛病。)
然而,老人明顯耐著性子不錶態。我們握瞭握手,盡管他這一握硬如鐵鉗,時間倒是不長。幾分鍾後,我們已經走齣車站瞭。
“你現在,”科剋說道,“是走在大布剋漢姆和小布剋漢姆之間的主乾道上。”
我偷偷瞥瞭他一眼。這一地理學緒言是個大玩笑嗎?還是說他在努力掩飾自己的情感呢?然而,他的臉上卻隻是一副堅定不移的嚴肅錶情。我開始“沒話找話”,就是我在那些晚會上學會的可悲套路,而且我越來越覺得跟我父親隻能這樣說話。我說薩裏郡的“景緻”令我驚訝;比我期待的“天然得多”。
“停!”科剋突然大喝一聲,嚇瞭我一大跳。“你說的天然是什麼意思,你不期待天然又是基於什麼原因?”
我迴答我不知道,我還在“沒話找話”。一個接一個的迴答被駁倒,我終於意識到他是真地想知道。他不是在沒話找話,不是開玩笑,也不是為瞭斥責我;他就是想知道。我受瞭刺激,試圖給齣一個真正的迴答。幾個迴閤足以讓我意識到我關於“天然”並沒有任何清楚明瞭的概念,而且要是說我還知道點什麼的話,那就是“天然”並不是一個恰當的詞。“你難道意識不到,”偉大的諾剋總結道,“你說的話毫無意義嗎?”我做好瞭生一會兒悶氣的準備,想當然地以為這個話題總算要結束瞭。但是我一輩子數這一次錯得最厲害。科剋分析完我的用詞之後,又開始繼續討論我的整個立論。我對於薩裏郡的植被和地質情況的期待是以什麼為基礎的(他把“基礎”念成瞭“基主”)?是地圖、照片、還是書本?我一樣也說不齣來。科剋又做瞭一次總結——不帶一丁點兒的感情,同樣在我看來也沒有帶上一丁點兒的禮貌:“那麼,你難道意識不到,你對於這個話題完全沒有發錶任何觀點的權利嗎?”
當時我們倆剛認識瞭三分半鍾;但是我們之間第一次談話的這種基調由始至終地保留瞭下來,貫穿我在布剋漢姆度過的所有那些年。眼前這個人與我父親念念不忘的“親愛的老諾剋”相去不啻十萬八韆裏。我瞭解我父親鐵打般隻說真話的本意,也知道事實一旦進入他的大腦會經曆怎樣奇怪的變形,所以我確定他沒有故意要騙我們。但是,如果說科剋一生中曾經在某個時刻把一個男孩拉到一邊,然後“輕輕地自然地”用他的連鬢鬍去摩挲男孩的臉頰,那我寜願相信他有時候會改變一下態度,然後輕輕地自然地拿一個大頂,把他那顆令人尊敬的、光禿禿的腦袋立在地上。
如果這世上有一個人接近純粹的邏輯實體,那麼這個人就是科剋。晚齣生幾年,他會是個邏輯實證主義者。人類使用發聲器官的唯一目的是交流和發現真理,除此之外任何目的在他看來都是荒謬絕倫的。最不經意的一句話也會被他看作是辯論的邀請。我很快瞭解瞭他三種開場白的不同含義。大喝一聲“停!”是為瞭阻止一大段已經讓他忍無可忍的廢話;不是因為他不夠耐心(他從來沒這麼想過),而是因為這是浪費時間,會模糊判斷力。更為急促而輕聲的“抱歉!”是為瞭引入糾正或者辨析,這起到補充作用,預示著經過如此糾偏,你可以被允許說完你的話而不至於顯得荒謬。最鼓舞人的是“我聽著呢”。這意味著你說的話有意義,隻是有待駁斥;你的話已經升格到頗有尊嚴的錯誤。駁斥(如果我們能走到這一步的話)的順序一成不變。這是我在書裏讀到的嗎?我研究過這個問題嗎?我有任何數據證明嗎?我有任何基於個人經驗的證據嗎?如此這般直到那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你難道意識不到,你沒有任何權利,等等等等。”
有些男孩不會喜歡這種待遇;但是對我來說這就是牛肉加啤酒。我本來想當然地以為我在布剋漢姆的閑暇時光會在很多“成人對話”中度過。而你早就知道瞭,這很不對我的胃口。在我的經曆中,這意味著對話都是關於政治、錢、死亡、以及食物消化。我本以為喜歡這樣的對話就跟吃芥末醬或者看報紙一樣,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水到渠成(目前為止,這三樣期待統統落空瞭)。我唯一喜歡的兩類談話一是幾乎純與想像力相關的,二是純理性的;前者如我跟我哥哥關於伯剋思恩以及跟阿瑟關於瓦爾哈拉 的對話,或者如我和我的榖希舅舅關於天文學的對話。我不可能在任何科學領域有所作為因為所有科學的道路上都有數學這隻攔路虎。數學中隻要是僅僅憑邏輯思維就能解決的問題(比如幾何),我也做的很愉快;但是一旦有計算部分齣現,我就無可救藥瞭。我能掌握原理,但是我的答案永遠是錯的。然而,盡管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傢,我有著科學的衝動,一如我有想像的衝動,而且我熱愛推理的過程。科剋激起並滿足瞭我的一部分衝動。這些是真正有內容的對話。這個人考慮的不是你,而是你說瞭什麼。在我手忙腳亂的時候我當然也氣急敗壞過;但是,總體上來說,我熱愛這樣的待遇。被無數次擊倒之後,我開始學會一些防守和攻擊的招數,我的智力慢慢也練齣瞭肌肉。最終,我成瞭一個不能被小瞧的拳擊對手,這應該不是我的錯覺。這個長期以來緻力於暴露我的含糊其辭的人最終提醒我要注意過度精確的危險,那真是瞭不起的一天。
如果科剋無情的辯證法隻是一個教學工具,我可能會感到厭惡。但是除此之外任何的談話方式對他來說都是陌生的。無論年齡性彆無人能幸免於他的邏輯反駁。有人會不願意獲得清晰的思路、不願意被糾正錯誤,這對科剋來說永遠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一位頗有身份的鄰居在某個星期天的拜訪過程中以不容置疑地口吻總結道:“好吧,好吧,科剋帕特裏剋先生,這個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組成的。你是個自由派,而我是保守派;我們自然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這時科剋迴答道:“你是什麼意思?你是讓我想像自由派和保守派從一張桌子的兩頭對著一個長方形的‘事實’玩躲貓貓遊戲嗎?”如果一個不經意的來訪者試圖迴避一個話題而這樣說:“當然瞭,我知道人們會有不同的觀點——”科剋會舉起雙手驚嘆道:“老天啊!我對任何問題都沒有任何觀點可言。”他最喜歡的箴言是“花九個便士你就能獲得啓濛,而你偏偏寜願無知。”最普通的比喻也會被一再追問,直到那令人難堪的真相無處藏身。“德國人那些惡魔般的罪行——”“可是惡魔難道不是想像齣來的嗎?”——“好吧,那麼,那些野蠻的罪行——”“可是沒有哪個野蠻人乾過這樣的事!”——“好吧,我該叫它們什麼好呢?”“我們就該簡簡單單稱它們是人的罪行,難道這還不清楚嗎?”最讓他鄙夷的莫過於其他校長們的對話,他自己是盧根中學校長的時候有時不得不在會議上忍受那些對話。“他們會走過來問我,‘對一個做瞭這樣這樣的事情的男孩,你會采取什麼樣的態度?’老天啊!就好像我對任何人或者任何男孩有過某種態度似的!”有時候,但是很罕見,他會被迫使用嘲諷。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嗓音會比往常更嚴肅,隻有他鼻孔的擴張會讓那些熟悉他的人窺破實情。他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發錶瞭以下這段評論:“貝利奧爾學院的院長 是全宇宙最重要的生命體之一。”
可以想像科剋帕特裏剋夫人的日子不容易;且看以下這個場景:她的丈夫因為某個奇怪的失誤發現自己身處客廳,他太太組織的一場橋牌會剛剛開場。大約半個小時後,人們觀察到他的太太帶著意味深長的錶情起身離開瞭房間;幾個小時之後,“偉大的諾剋”卻被發現依然坐在一張闆凳上,在七位上瞭年紀的太太們中間(“倦容滿麵地” )懇求她們明確定義自己的用詞。
我已經說過他幾乎隻講邏輯;但是也並非完全如此。他曾經是個長老會信徒,但我遇見他時已經是無神論者。他星期天在花園裏勞動,就跟他工作日大多數時候做的事情一樣。但是他年輕時身為長老會信徒的一個有趣的特徵保留瞭下來。每到星期天勞動的時候他總會穿一件不同的、更體麵的外套。一位阿爾斯特蘇格蘭人也許會不再信仰上帝,但是他不會在主日穿著工作日的衣服。
既已說明他是個無神論者,我就得趕緊補充一句他是個老派、嚴肅且不帶偏見的十九世紀類型的“理性主義者”。因為自那以後無神論就開始落魄瞭,逐漸與政治同流閤汙,學會瞭趟渾水。如今給我寄反上帝雜誌的匿名贈送者毫無疑問是想刺痛我體內的基督徒;而他真正刺痛的是我體內那位“前無神論者”。我從前的同誌以及科剋從前的同誌(這更為重要)竟然已經墮落到如此程度,這讓我深以為恥。真所謂今非昔比;哪怕麥剋卡比的文章也是個男人寫齣來的。我認識科剋的時候,他的無神論的燃料屬於人類學的、悲觀主義的類型。他精通《金枝》和叔本華。
讀者應該記得我自己的無神論和悲觀主義早在我去布剋漢姆之前就已經完全形成瞭。我在那裏隻是獲得瞭新的彈藥,用以保衛一個已然選定的立場。即便這些也是我間接從他的思想風格中獲得的,或者來自於獨立閱讀他的書籍。他從未在我麵前攻擊過宗教。有一類事實沒有人能基於對我人生的錶麵瞭解推斷得齣,這是其中之一,但這就是一個事實。
我星期六到加斯頓斯(諾剋傢房子的名字),他宣布我們星期一開始讀荷馬。我解釋說除瞭阿提卡方言 我從沒讀過一個字的其它任何方言,我滿以為告訴他這一點他就會從某些有關史詩語言的入門課著手,再過渡到荷馬。他的迴答隻是他在對話中經常會發的一個鼻音,我隻能寫作“哼。”這讓我很是忐忑不安;星期一早晨醒來時我對自己說:“這就要荷馬瞭!天哪!”這個名字讓我肅然起敬。九點整我們在樓上的書房裏坐下,開始上課,很快這個屋子對我來說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瞭。屋裏有一張沙發(他跟我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就並排坐在上麵),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我一個人時坐椅子),一個書櫥,一個煤氣爐,還有一張鑲起來的格萊斯頓先生 的照片。我們打開各自的《伊利亞特》第一捲。諾剋沒有做一個字的介紹便以“新”發音把前二十句左右的詩文大聲念瞭一遍,這種發音我以前從沒聽到過。和斯繆吉一樣,他也是位吟誦者;他的聲音不如斯繆吉甜醇,然而他飽滿的顎音和翻捲的R以及多變的原音感覺很適閤青銅器時代的史詩,正如斯繆吉如蜜似糖的嗓音適閤賀拉斯的詩。科剋雖然在英格蘭住瞭那麼多年,卻還是滿口純正的烏爾斯特音。隨後他翻譯瞭大約一百句,隻有很少、非常少的解釋。我還從沒見過哪個經典作傢被如此狼吞虎咽。譯完之後他遞給我一本剋魯西斯的《詞典》 ,告訴我把他剛纔翻譯的部分再讀一遍,能讀多少就讀多少,隨後他便離開瞭房間。這看起來是個奇怪的教學方式,但是很管用。起先,在他開拓齣來的這條路上我隻能走一小段,但是每天我都能走得更遠些。很快我就能全程跟上瞭。接著我能比他指齣的最北麵再多走一兩行。再後來看看能多走多少成瞭一種遊戲。在當時的階段科剋似乎更看重速度而不是準確性。最大的收獲是我很快就能不經過翻譯(哪怕是在心裏)便讀懂很多文本;我開始用希臘文思考瞭。這是學習任何語言都需要跨越的決定性界綫。有人隻有在詞典中尋找某個希臘詞匯的時候這個詞對他來說纔是活的,然後他會找一個英語詞來代替這個希臘詞,這樣的人根本不是在讀希臘語;他們隻是在解決一個謎題。“Naus的意思是船”,這樣的公式是錯的。“Naus”和“船”意指同一樣事物,但它們並不互為定義。在Naus的背後,在navis和naca 的背後,我們需要看到的是一副畫麵,一個暗憧憧的長長的物體,有帆有槳,爬過風尖浪頂,我們不需要好事的英語單詞橫插一手。
這段時間逐漸形成瞭一套作息規律,從此以後在我心裏成為一種原型,以至於我現在說“正常的”一天(並且悲嘆正常的日子如此稀少)指的仍然是在布剋漢姆時的作息錶。如果我能隨心所欲,我就會永遠過我在那裏過的日子。我會選擇永遠在八點整吃早飯,九點坐到書桌前,在那裏讀書寫作直到一點。如果十一點的時候有人能給我拿來一杯濃茶或者咖啡,那就再好不過。齣門一步,來一品脫啤酒,效果就差多瞭;因為男人不喜歡一個人喝酒,而你要是在酒吧跟朋友碰麵,休息時間就可能要超過十分鍾。一點整的時候午飯得在桌上擺好;最晚兩點我就會在路上瞭。不跟朋友一起,除瞭偶爾的休息時間。散步與談話是兩樣極大的樂趣,但是把二者閤在一起卻是個錯誤。我們自己發齣的噪音把外麵世界裏的聲音和安靜一齊抹去瞭;而談話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引嚮抽煙,那就隻能跟自然拜拜瞭,單就我們的某個感官而言。唯一可以一起散步的朋友得和你有著完全一緻的關於鄉野的品味,包括那裏的每個色調(正如我假期時在阿瑟身上找到的),一個眼神,一次駐足,至多是用肘輕輕一推,就足以讓我們心領神會彼此的喜悅。散步歸來應該剛剛好是上茶的時候,不能晚於四點一刻。茶點應該獨自享用,我在布剋漢姆的時候隻要科剋帕特裏剋夫人不在傢就是這樣獨個兒喝茶;諾剋本人鄙視茶歇。吃東西和讀書是相得益彰的兩件樂事。當然不是所有的書都適閤邊吃東西邊讀。在飯桌邊讀詩不啻為一種褻瀆。你需要的是那種八卦類的、雜亂無章、隨處都能翻看的書。我在布剋漢姆學會這樣去讀的書有鮑斯威爾 ,希羅多德的英譯本,以及蘭的《英國文學史》。同樣適閤邊吃邊讀的還有《項狄傳》,《伊利亞隨筆》以及《憂鬱的解剖》。五點就又該工作瞭,然後一直乾到七點。接著,晚飯以及飯後就是聊天時間瞭,或者沒人聊的話就可以來點輕鬆讀物;之後,除非你是要跟你的老夥計們混一晚上(在布剋漢姆我沒有這樣的機會),否則晚於十一點上床就沒道理瞭。可是該把寫信安排在什麼時間呢?您忘瞭我是在描繪我跟科剋一起時的幸福生活,或者是我但願自己能過上的理想生活。而這種幸福生活的一個基本要素是你幾乎不會收到信,永遠不需要擔心郵差來敲門。在那些幸福的日子裏,我每周隻收發兩封信;一封來自我父親,這是職責,一封來自阿瑟,這是每個星期的亮點,因為我們會把所有令我們陶醉的樂趣一股腦兒傾倒在紙上,告訴彼此。我哥哥這時正在軍隊服役,他的信內容和間隔都更長些,我的迴復也是如此。
這便是我的理想生活,而當時這種“穩定的、平靜的、伊壁鳩魯式的生活” (幾乎)一度實現瞭。那以後我基本上沒能過這樣的生活,這毫無疑問對我是件好事,因為這幾乎是一種徹底自私的生活。自私,但不是自我中心:因為在這樣的生活中,我的心靈會被引嚮一韆種事物,其中沒有一件跟我自己有關。這一區彆並非無足輕重。我認識的人裏最幸福也最讓人愉快的一個恰恰極其自私。另一方麵,我也認識一些能真正自我犧牲的人,可他們的人生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彆人都是一種摺磨,因為他們滿腦子都是自怨自艾和自憐自惜。任何一種情形最終都會摧毀人的靈魂。但是末日來臨之前,還是給我一個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哪怕是占我的便宜)然後大談特談其它各種事情的傢夥,也彆給我一個一麵為我服務一麵總在說他自己的人,他的付齣就是持續不斷的對彆人的指責,持續不斷地要求獲得憐憫、感激和贊譽。
當然,科剋並沒有讓我除瞭荷馬誰都不讀。“最無聊二人組”(狄摩西尼 和西塞羅 )是不可能不讀的。還有(哦,多麼美妙!)盧剋來修、卡圖盧斯、塔西佗、希羅多德。以及我至今都沒法真正喜歡的維吉爾。有希臘文和拉丁文寫作。(說也奇怪我竟然可以活到五十好幾還沒讀過一個字的愷撒 。)有歐裏彼得斯、索福剋裏斯、埃斯庫羅斯。傍晚跟著科剋帕特裏剋夫人學法語,教學方法就跟她先生教荷馬差不多。我們用這種方式讀完瞭很多很好的小說,很快我就開始自己買法語書瞭。我曾希望能學英語散文,但是科剋從來沒給我讀過一篇英語散文,不知道是因為他覺得沒法忍受我寫的散文,還是因為他很快猜到我掌握的散文藝術(對於英語散文他幾乎肯定是嗤之以鼻的)已經足夠瞭。第一個星期前後他給過我一些英語閱讀的指導,不過一旦發現就算沒人管,我也不太會浪費自己的時間,他就給瞭我絕對的自由。在我後來的學習階段我們又開始瞭德語和意大利語。他的教學法依然如故。在匆匆接觸瞭語法做瞭一些練習之後,我就一頭紮進瞭《浮士德》和《地獄》。意大利語我們是成功拿下瞭。而德語我毫不懷疑如果我跟科剋能再多待一些時間也一樣可以拿下。但是我離開得太早瞭,我的德語也就一輩子停留在瞭學生水平。每次我想開始改變這種狀況,就總會被這樣那樣更緊急的任務打斷。
……
前言/序言
譯者前言
1.
齣版於1955年的《驚悅》是英國作傢C.S.劉易斯的自傳,這一年他57歲。自傳從他齣生的1898年寫起,止於他皈依有神論的1930年前後,因此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我的前半生”。在最後一章“開端”裏,劉易斯告訴讀者他已經記不清自己是如何從有神論過渡到基督教信仰的,他給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看來,也是婉轉解釋瞭為什麼他沒有繼續去寫1930年之後的二十多年生命經曆。因為,劉易斯覺得,在擁有信仰之後,他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關注“自己的觀點和心理狀態的變化”,是終於“走齣自己”瞭。
對於有信仰者來說,劉易斯的所謂“走齣自己”應該不難理解。上帝是萬物之源,仰望上帝便是生而為人的本分;對於基督徒來說,我不再為我自己而活,“我”也因此變得微不足道。劉易斯對於自己作為基督徒的二十多年的人生感受,便是真正意義上的“微不足道”瞭。
細讀《驚悅》的前十四章,最讓人震撼的是作者強大的記憶力。一位55歲的男子,竟然可以清晰地記得將近半個世紀前的某個時刻,周圍的情景,內心的思緒,某種強烈的感觸,一切對他來說仿佛都隻發生在昨日。劉易斯大腦中的迴憶觸角幾乎可以探伸至歲月深處的每個角落——一隻蓋著苔蘚和嫩枝小花的餅乾桶帶給仍是幼兒的他關於美的第一次體驗;童年惡夢的昆蟲主題是因為育兒室裏的一冊繪本,上麵有一隻帶著活動觸角的鹿角甲蟲;而第一句直擊7歲少年靈魂的詩歌至今還在他耳畔迴響:
我聽見一個聲音在喊,
美麗的巴爾德爾
死瞭,死瞭——
就是一個有著這樣驚人的記憶力的劉易斯,對於離他自己最近的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生命經曆卻說:我記不清瞭,因為“我”已經不重要瞭。而我們知道的是,在那二十幾年裏,劉易斯寫齣瞭他最廣為人知的經典奇幻小說《納尼亞傳奇》;二戰期間他的名字在英國變得傢喻戶曉,因為他應邀在BBC電颱做關於基督教信仰的係列講座,成功鼓舞瞭英國民眾抵抗納粹德國的士氣,戰後這些演講稿被結集齣版,名為《返璞歸真》;而今天你走進任何一傢基督教書店,都會發現《返璞歸真》仍然是那裏暢銷書榜單上的第一名。幾乎劉易斯所有最重要的仍然擁有廣泛讀者的書,都是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後寫成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竟然讓我想起托爾斯泰那句被反復引用的名句,“幸福的傢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傢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許在劉易斯看來,他的後半生不必寫進自傳,恰恰因為他作為基督徒的生活與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並無本質不同,他們的人生都已進入同樣的完全臣服於上帝的“忘我”境界,而在他自己看來,這顯然正是他作為人應該過的唯一一種正當而幸福的生活。至於他在現世的成敗得失,與他的精神生活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不管他取得多少世俗眼光中的“成就”,在他內心深處永遠是“微不足道”這四個字。與此相反,他的前半生既背離上帝,也便充滿瞭各種獨特的“不幸”,各種跌宕起伏,各種“墮落”、痛苦、掙紮、絕望,以及最終的希望和救贖。迴憶這些經曆並用文字如實記錄下來,對劉易斯來說,也是在整理追溯自己走嚮信仰的精神之旅,而這份真誠的追憶,當然更是他基督教信仰的見證,又一份獨一無二的見證。
2.
記得翻譯《驚悅》期間,一位詩人朋友曾經隨口問起我眼下在譯什麼書,我告訴他是C. S.劉易斯的自傳。“可是,有誰會看這本書呢?”他脫口而齣。雖然在這之前我從未考慮過這樣的問題,但是一旦問題被提齣來,我倒覺得提問者的睏惑既真實也容易理解。如果從來沒有讀過劉易斯的書,也不知道他是誰,自然不會想到讀他的自傳。而我和我的編輯朋友之所以一拍即閤,在客觀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立即動手翻譯劉易斯的自傳,也是因為我們倆早已是劉易斯的“粉絲”,他重要的護教類作品幾乎都讀過一遍。所以,似乎確實可以這麼說,《驚悅》這本書首先是為熟悉並喜愛劉易斯的讀者們準備的,而這樣一個讀者群在中國顯然也是存在的。劉易斯有關基督教信仰的著名作品在兩岸三地都早已有瞭不同版本的中譯本,即便是我自己小小的朋友圈裏也總能找到願意坐下來聊聊劉易斯的朋友。
另一方麵,如果是一位從沒有接觸過劉易斯的讀者,當他翻開《驚悅》,會不會也有如書題所言的體驗呢——驚訝於意想不到的喜悅?我想這樣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凡這位讀者會對我說到的以下幾點中的任何一點生發齣興趣。
如果你相信,或者哪怕隻是懷疑,生長在現代社會的人也是可以有信仰的,也是可以過一種有信仰的生活的;如果你想知道,一位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學者,英國中世紀文學研究者,兒童文學作傢,劍橋大學終身教授,是如何從堅定的無神論者變成全英格蘭“最不情願的一個皈依者”;如果你好奇於這樣一個皈依者如何自始至終保持著最清醒的理性主義,他又是如何完全通過自己的理性來認識、理解信仰,並最終接受信仰,為信仰而辯護——你可以讀《驚悅》。
如果你是英國文學的愛好者,或者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你應該很容易就會喜歡上《驚悅》,並且同意這是一本供茶餘飯後“閑讀”的好書。我已經記不清劉易斯在他的傳記裏提到瞭多少西方作傢和作品,其中大多數都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經典,你不一定認同他對書的個人品味,但很可能他的某句話,某個暗示、揶揄,就會讓同樣熟悉經典的你唇角泛起會心的一笑。而你若碰巧也常讀英國散文,那麼劉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肯定會讓你的閱讀倍添歡樂,驚喜連連。
如果你相信童年經曆對人的性格形成和精神成長有著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並且想瞭解一些個體真實的經曆,那麼劉易斯在《驚悅》中所記錄的正是他對於自己早年人生的細緻入微的迴憶以及內省式的思考批評。劉易斯幼年喪母,同他父親的關係一直比較疏遠,可以說直到他父親去世,父子之間始終沒有實現真正的交流和相互瞭解。這種始於童年的與父輩的精神隔閡,其實也正是我自己以及很多同齡人共有的經曆,讀來難免唏噓感慨。但更重要的乃是劉易斯的反省精神,他在描述父親的種種不可理喻的同時,總不會忘記強調自己因年輕無知而錶現齣的任性、自私、不體諒甚至殘忍。而劉易斯與他唯一的哥哥始終兄弟情深,麵對父親很早達成攻守同盟,不乏令人捧腹又耐人尋味的童年趣聞。至於每個人此生會交到的第一個朋友,遇到的第一位讓你或恐懼或敬畏的老師,第一位終生難忘的啓濛導師,第一次這樣那樣的緻命誘惑,劉易斯都會嚮你娓娓道來,誠實地與你分享他 大腦中每一寸或美麗或高貴或痛苦或羞辱的記憶之地。
最後,對我個人來說,翻譯《驚悅》最大的收獲在於,劉易斯在這本書裏努力記錄描述瞭一種獨特的生命體驗,一種徘徊於靈魂深處的渴望;劉易斯用瞭一個最初來自德語的詞匯“Sehnsucht”來命名這種渴望,大緻可以解釋為對不明之物的強烈渴望。至於“喜悅”這個中心詞,隻是用來描述當這份渴望獲得滿足時那種稍縱即逝的、極大的、幸福到錐心徹骨的感覺。這正是我一直感覺到卻苦於無法把握、難以名狀的存在體驗,如果你也有著同樣的讓你充滿睏惑的渴望,那麼《驚悅》也許正是你該讀的下一本書。劉易斯認為自己的前半生始終沒有弄明白這種渴望的對象,很長一段時間隻是一味追求“喜悅”,錯把這種感覺本身當作瞭渴望的目標。在他接受信仰之後,目標當然立即明確瞭,就是上帝,劉易斯對天堂的解釋便是與上帝同在,既深刻又簡單。而值得迴味探究,值得與人分享的,似乎永遠都是那個充滿彷徨和睏惑的過程,給後來的朝聖者們一點提醒,一些慰藉。
3.
2015年是我做文學翻譯的第十個年頭,但我譯書並不勤快,最近完成的《驚悅》隻是第7部作品。《驚悅》最特彆的地方在於,整本書的翻譯過程相比我之前的經曆,無疑是最順暢的一次,有點兒一氣嗬成的感覺。原因應該有很多,自傳的結構相對簡潔,劉易斯的用詞平實,風格流暢,字數也不多,但這都隻是一方麵。我覺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從翻譯一開始便接連親曆“驚悅”,翻譯中一些主要的睏難隨之不攻自破。
前文提到,劉易斯在自傳中提到瞭無數作傢和他們的作品。事實上,他興之所至,還常常會引用某部作品中的原話,卻又不說明齣處。作為一個西方經典閱讀量不及作者萬一的譯者,這些每隔兩三頁就會齣現的人名書名,以及突然冒齣來的引文,著實挺讓我頭疼。他提到或者引用的作者作品雖然大都是文學界認可的大傢,但有些也相當冷僻,並非普通讀者所喜聞樂見,有些甚至維基百科上都難覓蹤跡。所幸我的煩惱隻持續瞭很短時間,因為翻譯到第二章時,我就無意間遇到瞭一個題為“LEWISIANA.NL”的網頁,細看之下,是一位北歐人為《驚悅》全書齣現的引用和典故所做的完整注解,按章節索引。內容極其細緻全麵,很多注解不僅包括作者和原著基本信息,甚至詳細到引文齣現在原著第幾章第幾頁,也常常提供上下文給讀者做參考。我當時的感覺,說如獲至寶、喜齣望外,都不算誇張。
過瞭沒多久,又一個驚喜不期而至。《驚悅》全文共十五章,每一章開頭都會有一句獨立引文,呼應暗示本章內容的精神,所以充分理解這些引文對於做好整個章節的翻譯顯得至關重要。LEWISANA.NL對這些引文雖然也都做瞭齣處說明,但也僅限於此。有一次,我又在網上搜索相關信息,找到瞭一篇劉易斯研究專傢約翰?布萊莫專門討論《驚悅》各個章節標題以及題頭引文的長篇論文 ,可以想像那一刻我心頭的雀躍。所以讀者們在中譯本中讀到的關於題頭引文的注解大部分內容是基於布萊莫先生的文章。這篇文章對於我把握每個章節的要旨也有很大幫助,幾乎是立竿見影地提高瞭我的翻譯效率。
最後一個驚喜齣現在翻譯的尾聲階段,2015年夏天我去瞭離倫敦不遠的蘇塞剋斯郡開會,旅途全部的空餘時間都用來完成《驚悅》最後三章的翻譯。我按計劃在離開英國前去瞭一趟牛津大學,尋訪劉易斯故居。一路滂沱大雨,坐瞭火車又換汽車,中午時分終於到達牛津鎮,下車時雨剛好停瞭。在步行去故居的路上,我經過瞭牛津的聖三一教堂,記起那裏是劉易斯生前常去的教堂。於是當然要進去看看。眼前的入口似乎通嚮一個弄堂,走進去,果然是個窄窄長長蜿蜒嚮前的石弄,兩邊石牆上爬滿瞭青藤,雖是陰雨天氣,路麵卻也乾爽。石弄裏暗影憧憧,格外清涼幽靜,我一路走著,隻聽到自己的腳步聲,還有偶爾幾聲雀鳴,感覺就像走在夢境裏。百餘米之後,走到盡頭,推開矮矮的院門,眼前豁然開朗,原來就是教堂前的空地和公墓瞭。一片青草地上立著高高低低形狀各異的墓碑,還有好幾棵蔥鬱的大樹。我徑直朝教堂走去,大門關著,推不開。
於是我又退到公墓邊,一眼看到一塊小小的牌子上寫著“劉易斯墓地”。我怎麼沒想到他有可能就是葬在這裏呢?我放輕腳步嚮前走,心裏琢磨著,這麼多墓碑,恐怕得好一會兒纔能找到劉易斯。正想著,走到一棵樹下,一低頭,一塊長方形水平放置的墓碑上正寫著“懷念我的弟弟剋萊夫·斯坦普爾斯·劉易斯(1898-1963)”,再往下是劉易斯哥哥沃倫的生卒年月,這應該先是沃倫為劉易斯立的墓碑,後來沃倫自己也與弟弟閤葬於此。我在墓前呆呆地站瞭一會兒,心裏起伏感動,難以描摹。隨後我在墓碑邊一截濕漉漉的老樹根上坐瞭下來,看到旁邊一叢不能辨識的紫花,正開得熱鬧,畢竟是8月。我享受瞭一會兒少有的內心與周遭完全閤拍的寜靜感,直到天又開始下雨,我看著落在自己赤裸的臂膊和同樣赤裸光滑的墓碑上的雨滴,八月的雨讓身體感到清涼的驚喜。這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愉悅傳到大腦,我身在夢裏的感覺卻不減反增,這時想起瞭劉易斯談什麼是我們最清晰的意識——“就是意識到自己碎片的、曇花一現的本質,覺醒到我們並非做瞭一個夢,我們就是一個夢而已。”
兩天後,我完成瞭《驚悅》全書的翻譯。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引人入勝的魔力,讓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它仿佛不是一部簡單的個人迴憶錄,而是一段深入靈魂的旅程。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麼樣的經曆和思想碰撞,纔能塑造齣那樣一位影響深遠的思想傢。這本書的吸引力在於它承諾揭示這位巨匠內心世界的形成過程,那種從迷茫到頓悟,從懷疑到堅定的轉變,一定充滿瞭跌宕起伏的內心戲。它不僅僅是記錄過去,更像是一場對“驚悅”這一核心體驗的哲學探討。我期待看到的是,作者如何細膩地捕捉那些轉瞬即逝的靈感火花,以及那些塑造他世界觀的關鍵時刻。想象一下,跟隨他的腳步,重溫那些青春的睏惑、學術的探索,以及最終找到信仰歸宿的激動,這本身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這本書的價值可能遠超於對劉易斯生平的瞭解,它更像是一份關於如何誠實麵對自我、追尋生命意義的行動指南。
評分從情感共鳴的角度來看,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種超越時空的連接感。探討“早期生活”必然涉及到青春期的敏感、對歸屬感的渴望,以及麵對宏大世界時的渺小感。劉易斯無疑是一位極具共情力的作傢,我期待他能以一種坦誠到近乎殘忍的筆觸,描繪齣那些成年人常常選擇遺忘或美化的自我懷疑與焦慮。一個影響瞭無數人的思想巨人,也曾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這種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如果他能成功地捕捉到那種“初識”的震撼——無論是對自然之美、文學之妙,還是對某種更高實在的朦朧感知——那麼這本書就能成為一本關於“如何保持敏銳”的指南。它不隻講述“發生瞭什麼”,更重要的是講述“那感受起來是什麼樣的”,這纔是真正打動人心的力量所在。
評分作為一名對思想史感興趣的讀者,我更看重的是這本書如何展示一位偉大思想傢的“原材料”是如何被塑造的。我們瞭解劉易斯的成熟觀點,但真正引人入勝的是那些觀點尚未成形之前的混沌狀態。這本書應該會揭示他早期閱讀瞭哪些書籍、遇到瞭哪些影響深遠的人物,以及在特定曆史背景下,他是如何與主流思潮進行抗爭或融閤的。我期待看到他對特定文學作品、哲學論點所做齣的早期反應,這些反應或許稚嫩,但卻代錶瞭其思想原型的萌芽。如果作者能夠細緻入微地描繪齣他如何辨識、過濾和吸收外界信息,從而構建起自己的內在宇宙,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就極高瞭。它提供瞭一個觀察“思想鑄造廠”內部運作的獨特視角,讓我們理解卓越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無數次內部對話和外部碰撞的結果。
評分閱讀體驗上,我非常期待它能有一種沉浸式的代入感,仿佛作者就坐在我對麵,娓娓道來那些早年的心緒。從書名就可以推斷,作者必然會深入剖析“驚悅”——那個無法用邏輯完全解釋的、超越性的喜悅瞬間——是如何滲透和重塑他早期生活的基調。我尤其好奇他是如何處理那些看似矛盾的經曆的:一個早期的無神論者,又是如何一步步被那些不期而遇的“光亮”所吸引和俘獲的?這種從理性堡壘中走嚮信仰的曆程,想必充滿瞭微妙的心理拉鋸戰。如果作者能夠將那種探尋過程中的掙紮、睏惑和最終的豁然開朗描繪得淋灕盡緻,那麼這本書就不再是枯燥的自述,而是一部關於心智成長的史詩。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種閱讀的節奏感,時而深沉內省,時而又因某個發現而歡快雀躍,如同一次精彩的探險,最終揭開瞭一個深藏的秘密。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和敘事方式,我想一定非常獨特。考慮到劉易斯的文學功底和清晰的邏輯思維,我預估它不會是一部綫性敘事的流水賬。更可能的是,它會圍繞著“早期生活”這一主題,以一種非編年體的方式,將那些關鍵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體驗碎片化地呈現齣來,然後通過對“驚悅”這一主題的反復迴溯與深化,最終將這些碎片拼閤成一個完整的精神肖像。我猜想,作者在講述那些看似平常的童年場景或求學經曆時,會不經意間植入日後理解的智慧,讓當時的睏惑與後來的洞察形成一種迷人的對比。這種“已然知曉”的視角,會給予讀者一種獨特的閱讀樂趣——看一個偉大的頭腦如何艱難地走過它必經的彎路。這種復雜的敘事編排,正是區分一本普通傳記和一部經典作品的關鍵所在。
自傳類的書,是我的最愛。
評分我是路易斯的書迷,沒話說,強烈推薦。
評分好評!!!!!!!!!!
評分名人傳記能夠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評分幫朋友買的,應該很不錯吧,希望他會喜歡?
評分很好的書。。。
評分很令人動容的迴憶錄,越往後越好。
評分《驚悅:C.S.劉易斯自傳》是C.S.劉易斯的自傳,這一年他55歲。自傳從他齣生的1898年寫起,止於1930年前後。《驚悅》一書記錄瞭劉易斯對於自己早年人生的細緻入微的迴憶以及內省式的思考批評,在記敘傳主的成長曆程中,呈現獨特的生命體驗。劉易斯在書中廣徵博引,對自己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經典如數傢珍;劉易斯典型的英式幽默則會讀者的閱讀倍添歡樂,驚喜連連。
評分很好的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