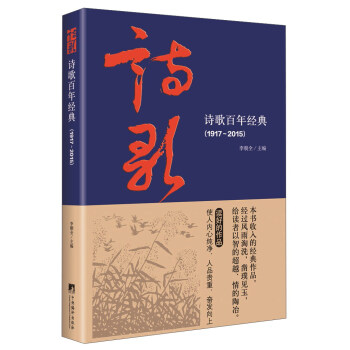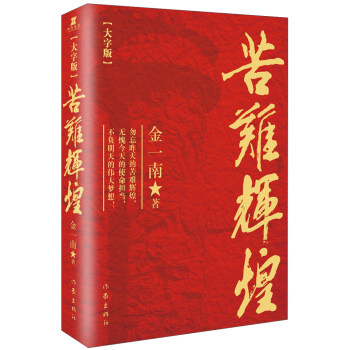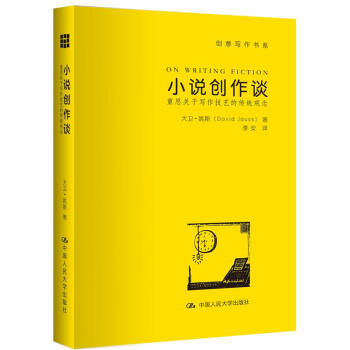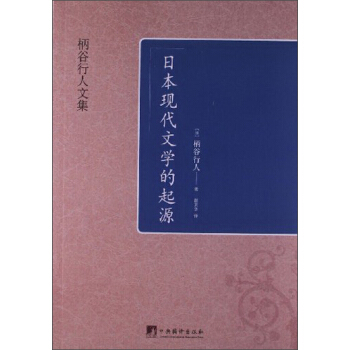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材料与注释》:让材料与注释对话,呈现历史的多面性。将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叙述并置的做法,展现出历史的多面与复杂,也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内容简介
《材料与注释》收录了洪子诚教授的学术论文:主体为对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呈现,材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出历史现场的复杂局面,使得不熟悉当年材料的学生及研究者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另外的文章为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及教学的探讨。作者简介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等。目录
目?录自序......2
材料与注释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3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21
1962年大连会议......64
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105
张光年谈周扬......128
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152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
“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213
当代文学史答问
关于作家协会的答问......233
当代文学史教学及其他......245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257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282
精彩书摘
道德与权力的关系(节选自《“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作为一种道德尺度,和“两面派”相对立的真实、真诚等自然不是无足轻重;无论是从个体品格修养,还是从社会关系的维系层面上看,都是如此。但在回顾“当代”文艺史时,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的道德捍卫者和指控者,他们使用的也可能是不那么“诚实”,甚至可以说也是类乎“两面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历史问题在她去延安之后已有结论,却在没有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坐实她的叛变自首,然后滥情地施以“不忠诚”的指斥。在对丁玲的批判中,还采用了以作家的思想言行来解释她所写的人物,又以对人物的阐释反过来构造作家形象的循环论证:先说丁玲是个人主义者、变节分子和反党分子,然后说她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陆萍(《在医院中》)也同样极端个人主义、变节和反党,接着又将这些人物与其创造者画上等号,来进一步落实丁玲的罪名,得出“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名字”的结论。
又譬如,周扬等明明没有看过鲁迅答徐懋庸信原稿,却说已经到鲁迅博物馆看过,信誓旦旦地说这封信是冯雪峰笔迹,鲁迅只改了四个字,用来证明冯雪峰操刀代笔,蒙蔽鲁迅。明明对冯雪峰的批判,是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行为——召开过多次会议,商讨批判内容、步骤、方法,布置有重磅炸弹效果的发言,组织30年代左翼文学界人士当场表态呼应——可是在和冯雪峰谈话时,却说“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批判胡风时,没有批判你,党外党内都有人有意见”;本来准备做总结了,“但中央认为还没有斗争透”:总之,斗争冯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们所愿。再譬如,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会议之前邵荃麟与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多次商议,获得一致意见,周扬还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完全肯定邵荃麟他们的看法。但是,在1964年中宣部和作协展开的批判中,一切“罪过”全都归咎于邵荃麟,邵就成为政治风暴将至的“替罪羊” 。当然,在后来周扬等成为“两面派”的时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断章取义、任意编排、引申发挥的“不诚实”的方法。而“文革”过后,当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同样获得“两面派” “披上革命外衣”的评语 。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错动甚至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上“不老实” “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些人。“两面派”的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头上,不久就落到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
这样描述发生在当代文艺界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要把水搅浑,将历史视作一笔糊涂账,以为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被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的思想品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而在于让我们能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的关系的实质。这也就如有学者在分析历史某个时期权力与道德关系时指出的: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 。
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讨论了“真诚”的起源所涉及的社会环境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只有在个人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之后才会出现。因而,“一旦研究真诚问题,我们就要涉及公共意见甚至政治考虑”。在“真诚”的评价标准上,他认为至少涉及这样的问题:进行评价的人是否真诚;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这些,都与社会环境,社会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从上面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当代”,当道德评价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的时候,办法之一是尽量掩盖道德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将它孤立抽象化,将它与社会体制状况分离,看作对纯粹的个人品格的追问,并以此建构那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的评价趋向。而这种道德至上的绝对主义,其实正是产生于个体“自由”空间狭小的,“一体化”的社会里。这种“一体化”的意识形态统制,包含权力与道德关系的重要内容。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前,徐中玉在《文艺报》的文章中说到“当代”有这样一种人,他们:
当教条主义还很吃香的时候,他的文章里不仅充满了教条,也积极支持过各色各样的别人的教条主义;当粗暴批评还被当作“原则性强”来看的时候,他不但写过许多粗暴之至的文章,并且也曾实际鼓励了这种敌我不分的风气。……接着情况变了,教条主义终于被揭露为马列主义的大敌,敌我不分的粗暴批评终于被斥为严重的错误,人们大概就会这样想,这种人现在总应该检查一下,坦白那么几句了吧,然而不然,他却又在大写其痛骂教条主义和粗暴批评的文章了。真所谓摇身一变,仿佛他过去什么文章,什么话,什么事都不曾写过说过做过一样。
没有原则的转向、见机行事,自然遭人嫌弃。但是,这种现象如果普遍产生,就不能仅从个体品质上解释。费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中就委婉指出,知识分子对于“百家争鸣”的号召所表现的矛盾、犹豫、摇摆,重要原因是对权力可能深藏的谋略、圈套的担心。这里,费孝通关注了与道德相关的心理现象,和行为的社会根源。换句话说,不少“不真诚”的,或“两面派”的道德现象,不论是强者基于地位权力的觊觎争夺,还是弱者迫于压力,为保护自己而选择心口不一,除了从社会个体的行为品格上观察之外,还存在着应该深入考察的“一个社会所宣称的准绳与其形态相对应程度”,和“一个社会培育或败坏其公民的真诚的程度”的空间。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经验看,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有时个人连“置身事外”的“边缘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选择,在这样的时候不去讨论“环境”问题而专事追究他的“真诚”,确是有点模糊事情的焦点。1955年,中国作协在内部秘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时候,据黄秋耘的叙述,不得不参加会议的陈翔鹤就有这样的感叹:
(陈翔鹤)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遭怨憎’。”
人在自己生命处理上的无奈,在陈翔鹤60年代初写的短篇《陶渊明写“挽歌”》 《广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说,在一个“言论的强迫统一”的社会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在他们自己的四壁里的本来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是本来的,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语言” 。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
从这里可以提出的问题有,为什么“道德”拥有“超凡权力”的规范性力量?为什么它具有“终极评价”的地位?谁有资格、权力做出道德评价?审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问题时,是否便证明他的“道德纯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这个问题,涉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国作家法斯特宣布脱离共产党,中国文艺界对他展开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里就触及了令自由知识分子苦恼的这个问题 。“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过,从“当代”文艺史看,当年标榜的正义、崇高目的(捍卫“正确文艺路线”、还原“历史真相”等等),许多都未能经得起检验。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目的的崇高性,这样的忧虑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过无情手段促进的人性理想,有变成其相反物的危险;自由,变成以自由为名而行压迫;平等,变成以维护平等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头体制; 公道,变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协,人类爱则变成怨恨所有反对以残暴手段达成人类爱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蛰存在《才与德》的文章中说,“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20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这看起来是“士”对“君主”谏言的现代版本,目的当在争取“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不过,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对“当代”“道德主义”趋向的警惕;这种“道德主义”是在承担推进“一体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功能,是在促使这样的现象产生:一边是绝对的纯洁正义,另一边则完全是欺骗和邪恶——端看谁掌握着权力而进行这种二元的道德分配。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刚收到这本书,名字叫做《材料与注释》,封面设计很简洁,让人有一种沉静的感觉,很适合我最近想要深入研究的领域。我一直对那些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微观细节充满好奇,总是想知道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究竟是由哪些基础构件组成的,它们又是如何被组合和处理的。这本书的名字恰好点出了这种探究的本质——不仅是材料本身,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些材料产生的理解和解读。我预感它会是一本能够填补我知识空白的书,让我从一个更扎实的角度去审视我所接触到的各种信息和事物。拿到手后,我迫不及待地翻阅了目录,看到了一些我从未接触过的概念,这让我既感到一丝挑战,又充满了学习的动力。我期待书中能有清晰的逻辑脉络,能够循序渐进地引导我理解复杂的理论,同时,我也希望它能提供一些实际的应用案例,让我能够将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看到理论的价值所在。这本书的厚度也适中,既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又足够承载丰富的内涵。总的来说,我对这本书的初印象是非常积极的,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我学习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评分这本书的到来,就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我一直对“注释”这个词语有着特别的偏爱,总觉得它蕴含着一种对事物的深度理解和精确表达。而当它与“材料”结合时,我仿佛看到了将抽象概念具象化,将无形知识实体化的过程。《材料与注释》这个书名,无疑触动了我内心深处对探究本质的渴望。我想要了解的是,那些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它们拥有怎样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又是如何通过“注释”——也就是一系列的解释、说明、甚至是对其加工和改造——来为我们所理解和利用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我深入到材料的微观层面,去理解它们的分子结构、物理性质、化学反应,然后,再通过“注释”的视角,去解读这些性质如何影响着它们的用途,以及人类是如何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运用,创造出无数的奇迹。这种由基础到应用,由物质到精神的探索过程,是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我对这本书的期望,不仅在于它能提供给我知识,更在于它能教会我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分析,如何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解体系。
评分看到《材料与注释》这个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位学者,手捧一本厚重的典籍,专注地研究着书中的每一个字句,并在旁边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仿佛要将书中所有的精髓都挖掘出来,化为己有。这种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精神,正是我在学习过程中所欠缺的。我常常会浮于表面,对事物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那种精雕细琢的耐心。这本书的名字,就仿佛在提醒我,学习不仅仅是囫囵吞枣,更需要细致的审视和深刻的解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教会我如何去“注释”——如何去审视,如何去辨析,如何去理解背后的逻辑和原理。它不仅仅是关于“材料”的知识,更是关于如何对待知识,如何消化知识的方法论。我期待它能提供给我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以更严谨、更深刻的态度去面对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挑战。这本书的出现,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启迪,一次学习态度的重塑。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材料与注释》。它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材料”是基础,是骨架,而“注释”则是血肉,是灵魂,是对骨架的丰富和升华。我总是对那些能够将事物本质抽离出来,并对其进行细致阐释的著作心生敬意。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不仅仅是提供一些关于“材料”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能教会我如何去“注释”这些材料,如何去理解它们存在的意义,如何去运用它们,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一种透视事物本质的能力,让我能够看到事物的深层结构和运行机制。它不应该仅仅是一本知识的堆砌,而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启迪,一种洞察真相的引导。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让我看到,那些看似普通寻常的“材料”,在经过“注释”之后,能够焕发出怎样的生命力,能够承载起怎样的意义。对我而言,这本书更像是一种解锁,一种对事物更深层理解的钥匙。
评分《材料与注释》这个名字,让我联想到了一种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学习路径。我一直认为,真正的理解,是从最基础的“材料”开始的。只有了解了事物的构成要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整体的运作方式。而“注释”则代表着对这些材料更深层次的解读和阐释,是知识的延伸和拓展。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让我能够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一步步地构建起我对某个领域的深刻认知。它不应该是一本充斥着晦涩术语、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书,而应该是一本能够循序渐进,将复杂的概念解释得清晰易懂的书。我希望它能够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耐心地引导我,让我能够理解那些看似遥远、难以触及的知识。同时,我也希望它能在提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注释”,带领我探索更广阔的领域,发现更多隐藏的联系和规律。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更是一个学习的地图,指引我探索未知的领域。
评分好书共欣赏,经典名著,值得一读
评分经典著作,值得珍藏
评分好书共欣赏,经典名著,值得一读
评分好看
评分京东买东西很好,是正版,没问题!
评分好多过去的新鲜材料
评分这是洪子诚老师的一本新书,很久就想看一看啦,终于买到了,文章有些是在杂志上连载过的,书更容易看出它的整体的思路。好书新书很快,可以开始阅读了。
评分好
评分物流很快,质量也很好,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阳光宝贝 睡前5分钟 儿童智慧故事第一辑(套装共8册) [2-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92123/58044611Nac915ef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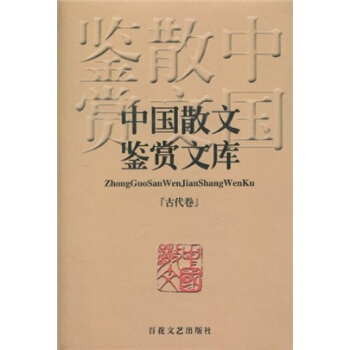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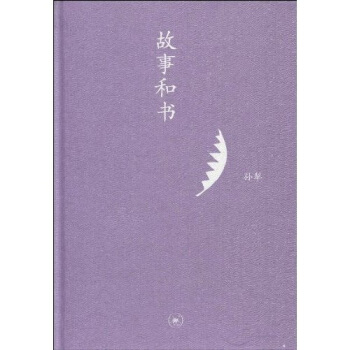

![特种兵学校3:树屋上的敌人 [10-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60792/5609ee08N93413e0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