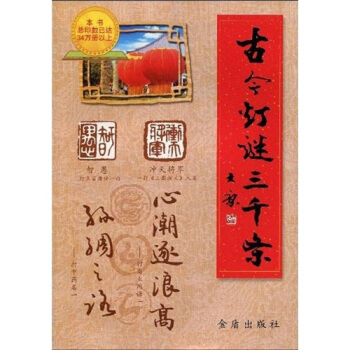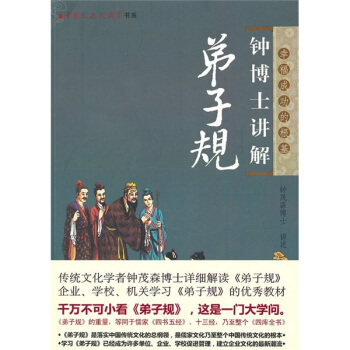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切入中国音乐、古典乐器、生命情性不可多得的一本经典之作。谈音乐难,因为音乐抽象。《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却独辟蹊径,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五种重要乐器与国人特殊生命情性关联起来,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乐器zui关键zui性情的特质。
内容简介
《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作者以其对中国器乐和古今中西文化的熟稔,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五种重要乐器与国人特殊生命情性关联起来,从琴与高士、琵琶与侠客、笛与书生、筝与儿女、胡琴与常民生命性的相形相契入手,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概述了中国乐器zui关键zui性情的特质。乐器与生命属性的此种连接,因此也就不只反映了中国器乐独特的历史发展,更根柢地映照了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作者简介
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台北书院山长。在禅与艺术外,1988年后又以海峡开放恰可印证生命所学之真实与虚妄,频仍来往两岸,从事文化观察与评论。代表作品有:《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禅?两刃相交》《千峰映月》《画禅》《归零》《落花寻僧去》《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观照——一个知识分子的禅问》《茶与乐的对话》《生命之歌——从胎教到生命完成》等。目录
目 录幽雅阅读 ....................................................................吴志攀 / 1
以器映道,深体人文 .................................................林谷芳 / 1
楔子 ........................................................................................ / 1
一 余响入霜钟 琴/高士 ................................................... / 1
琴是文人音乐的代表,寄寓的是山林之志,正如高士。高士
融入自然,体得春秋,超于物外。在此,生命虽纵浪大化,丘壑
却静观而得。
二 执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 侠客/ 琵琶......................../ 46
琴属文人,琵琶则在江湖;琴是高士,琵琶则为侠客。明朗
直捷是琵琶的本色,正如侠客在现前当为中承担,这生命的大气
使琵琶出入雅俗而无碍。
三 长吟入夜清 笛/ 书生.................................................../ 94
一根竹管,看似日常,却映现无比风光。笛如书生,风流俊逸,
悠扬潇洒。相对于琴的山林志、琵琶的江湖行,笛则须有书剑香。
四 玉柱冷冷对寒雪 筝/儿女............................................. /126
筝擅写儿女之情,或幽微、或淡雅、或质朴,却都温润体贴,
娓娓道来。琴与筝,形虽似,映现的却是两般风光。
五 百姓的讴歌 胡琴/ 常民................................................. /154
“地本庸微”的胡琴,原与戏曲高度相连,拉的就是百姓心声。
形制众多,因地而变,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音乐写照。
结语:乐器的当代生命............................................................ /180
历史乐器原有其一定之生命性,执此器者亦必就此生命性观
其长短,于器乃得有成,于人就能相应。到此,人器合一,道器合一,
才真是道艺一体的体现。而中国音乐虽大,由此契入,正如禅门
依学人情性举公案锻炼般,一超直入,亦必可期!
“幽雅阅读丛书”策划人语..................................................../199
精彩书摘
林谷芳:以器映道 深体人文中国人喜谈“道器”,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乃多有着力于“道器之辨”者,就怕以器害道,使人文流于表象,生命落于枝节。但其实,谈道器,在“严其别”外,更可举“道器合一”。
说不能只执于别,是因以器害道,固让人孜孜于末节,但以道轻器,尤让人流于空疏。以艺术而言,只在器上转,你就追逐技术,花指繁弦,虚矫呈现;但若就在道上谈,你仍然只执于概念,离乎作品,空言大义。以此,真正的艺术家乃须道器得兼,对具体的外现能掌握,对内在的精神能呼应。且何止得兼,能被称为大家者,更就道器合一,“以道显器,以器映道”。
个人如此,历史中成其典型的文化亦然。有形上的拈提总有形下的映现,有形下的呼应就有形上的标举,以此,你想契入,固可“以道入”,亦可“以器合”。
而虽说“以道入”“以器合”因人而异,但谈音乐,先以器入,则有其必须。必须,是因音乐抽象整体,直以道入,空疏之病尤大。
以器合,可以就作品论,但音乐艺术的门坎高,没受专业训练,就难在此判准。以器合,也可以直接就乐器说,它内在讯息的丰富会让你惊讶。
乐器不像许多人所想的,只纯然是个表现音乐的载具而已,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化美学的外现,也因此,它有自己的个性。而在中国,这个性尤为突出,因为它直指一定的生命情性,“见器犹见人”,你可以由此拉出的,何止于音乐,更是生命。
这生命,在古琴,是高士;在琵琶,是侠客;在竹笛,是书生;在筝,是儿女;在胡琴,是常民百姓。可以说,涵盖了中国人生命情性的全面。
而何止于生命,更及于文化,这其中所能契入的,还涉及社会阶层、文化特质,乃至历史气象的变迁,透过这具象的存在,许多抽象的精神竟可以如此被我们深刻而贴近地感受着。
所以这书,既在谈乐器,也不只在谈乐器,虽聚焦于音乐,映现的却是更广的人文。对一般人而言,它不构成门坎,但真掌握了它,你其实也就掌握了一把开启生命观照、契入中国文化的钥匙。
林谷芳:《宛然如真》楔子
一、 谈中国文化,为何独缺音乐一环?
谈音乐难,因为音乐抽象。就因这抽象,谈来乃多主观之想象。
谈中国音乐更难,因为抽象之外,它又居于弱势。
弱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相对于西方音乐,它真弱势得可以,所以一般不谈它;要谈,就只用西方的观点直接加诸其他。
不仅面对西方弱势,弱势也来自它在自体文化的地位。
中国是个大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广袤,影响深远,诸事乃多有可观者。可有意思也令人遗憾的是:诸方皆擅,却“似乎”于音乐例外。
音乐例外,的确,我曾在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下列的句子问过大家:
提起中国文化,你可能想起:
哲学里的老庄孔孟、大乘佛学;
文学里的诗经楚辞、李杜苏辛;
绘画里的范宽、李成、八大、石涛;
史学里的史记、资治通鉴;
书法里的王羲之、黄山谷……
但音乐呢?
提起中国音乐,论人,你很难直接想起可与上述哲人、画家、诗人、书家并列者;论作品,又哪里有可与《溪山行旅图》《鹊华秋色图》《快雪时晴帖》《寒食帖》及其他经典诗作、文章相论者。也所以,近代论中国文化之诸君子,于哲思、于书画、于诗词固多有发扬,固多能由之发而为美学者,却独于音乐少有提及;有,也只在神话传说或个人的片面经验中带过。
神话传说,是指中国的礼乐。
礼乐在官方或儒家的说法中,被认为“尽善尽美”,许多人常举“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说明它有多好。
但实情是,用句现代话讲,礼乐本是种“政治仪式音乐”,而仪式音乐之感人并不在音乐本身,在它仪式的神圣性。政治仪式音乐就像祭孔音乐般,重点在它理念的象征。礼乐,是以音乐强化社会秩序,是在型制象征上直接体现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音乐。听它,跟听一般音乐不同。
历代最完备的封建制度在周代,周代礼乐因此成为各朝师法的对象。所谓“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封建制度的完备,礼与乐功不可没,它将社会秩序直接连接于天地法则,所以天子有天子之礼、天子之乐,诸侯有诸侯之礼、诸侯之乐,一丝一毫、逾矩不得。孔子感叹“礼崩乐坏”,正在感叹社会失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作礼乐、记春秋,正是要匡复这社会秩序。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其实是见到先王之乐仍存,匡复有望的激动,与音乐本身的艺术感人并无直接相关。
礼乐虽是历史的实存,但礼乐却被神化,诸多哲人、史家乃至文人,提起中国音乐,就在这神话中作想象的满足。
而个人的片面经验呢?这是指论者将自己少数的中国音乐经验放大为全体,举例而言,当代新儒家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于美学、诗词、书画多有论及,谈音乐则仅寥寥两三页,所述就在古琴与京昆,不仅量上极为不足,也谈不上什么论点。
寥寥几笔中,琴常被谈及,是因琴棋书画,琴列四艺之首,它已成为文化象征。画家多不谙音律,但携琴图、松下弹琴图、弹琴观瀑图却是水墨常见之题材。此外,琴是乐器中唯一留有大量论述——琴论者,其哲思与文采,正可让文人不须借助实质的音乐经验而另有所得,引用自众。
谈昆,主要因它为文人日常雅好,文学性强。但正因如此,文人谈它,多的乃是词情,于声情着墨就少;而即使有声情,昆在中国音乐中毕竟也只为戏曲之一种,更遑论戏曲之外另有器乐、歌乐、曲艺乃至宗教音乐。至于京剧虽不同于昆曲,能通于雅俗,但依然只独占一味。
正因如此,我那《谛观有情》的一问,许多人的确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会不会正因中国音乐确如上述,它只在神话传说里放异彩,只在某些独特片面的领域里有可观?
答案当然不是!
二、 关键在态度:视角一变,眼界就开。
不是,可以来自论理。
规模小的文化,在发展上可只独占一味,但大文明不然。
部落文化可精于雕刻,而拙于绘画;可在诗歌大放异彩,而于建筑则无可观。
大文明不然,它积聚众多人口,须满足不同阶层需要,历史悠久,都市发展,都使它有更多积累,加以文化交流,触动既多,面相就广。
因此,它在各领域之建树,相差不会太多。何况文学、美术、音乐都是基底艺术,是只要有人就有的一种文化,你如何去解释中国有如此灿然大观的文学与美术,而独缺深刻之音乐?
不是,更可以来自经验。
经验是实际去了解、去接触,接触后你就晓得它的样态是如何丰富,难怪查一下音乐辞典,它会说,中国的民歌何止万首,戏曲就有约四百种,曲艺就有两百多类,器乐的多样更不在话下。
但为何音乐这么多,接触的人还那么少,是因为急速的现代化使传统变得稀薄?实情不然!关键在清末民初西潮刚入时,多数人固还在听传统音乐,但有论述能力的知识分子眼中却已无中国音乐了!
所以说,缺乏中国音乐的经验是果,原因是在你先排斥去接受这种经验,根柢的,还是个态度问题。
态度决定视野。君不见,世界的文化如此多彩多姿,人类学估计全世界约有三千种文化,但在殖民时代,西方人眼中除开西欧,其他的都叫野蛮,要待得人类学出现,才逐渐打开视野。
知识分子对中国音乐的态度,来自西潮东渐而致的文化位差。这文化位差使我们对传统丧失信心,总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它。
五四对传统就是个典型。
然而,尽管如此,文学、美术却都挺住了,虽然有段低迷,但不久,中国人提起它,似乎仍有几份骄傲――尽管不时的,也“自然”流露出这些虽好,却都属于过去的荣光,我们还得跟西方多多学习的表情。
相较之下,音乐不然,西潮摧枯拉朽地将它彻底击倒了。
会如此,导因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录音机发明之前,音乐是不能被“独立”保存的。
文学、美术的作品离开人还可“独立”存在,你一时看不清它的价值,物换星移或观念一改,看它,又是另一番景象。
音乐不然,它活体保存在人身上,你忽视了它,没人传唱,哪天即便观念改了,却也无法再找回来。
历史中的音乐因此流失得特别快,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乐”,改朝换代,前朝的音乐常就不见了。
就因此,虽都同样在西化思潮中被否定,可要摆荡回来,音乐就较文学、美术难上许多。
但难,并不代表不可能,关键仍旧在态度。
态度一转,你就发觉传统音乐虽大量流失,真要接触,也没想象的困难,中国文化毕竟绵延广袤,中国音乐的类型毕竟繁多,尽管有消失,许多东西却只是由显而隐。
态度一转,你就会发觉,“乐为心声”,它像语言般,有它的顽固性在,也所以尽管自清末“学堂乐歌”开始,我们学校的音乐教育已全盘西化,但多数人唱歌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唱,多数人视谱,也仍旧喜看数字谱,只因数字谱的谱性与传统的工尺谱相同。
这种顽固性缘自对自身艺术特质的偏好,这特质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它自成系统,有其内在的美学自圆性。这美学自圆性,最贴合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心灵特征,离开它,想达致乐为心声就不可能,其情形正如中国人之用中文表达,中国水墨无论从笔墨章法都与西方不同般。
的确,从艺术特质切入,你就发觉中国音乐自成天地,独擅一格,与西方相较,既各有所长,谈民族心声,则远为贴切。
谈中国音乐的艺术特质,可以自许多面相进入,从美学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以至有机而完整的乐曲,在在都因它自成圆满,有心人乃可以从单一的线索回溯整体。
举例而言,就因有阴阳相济的宇宙观,才产生虚实相生的美学,由此中国音乐乃特别重视实音(主音)与虚音(行韵)的运用,由之而产生如古琴或昆曲般一唱三叹的音乐风格。
再有,就因中国美学深受老庄自然哲学的影响,于是中国音乐才有许多从标题就直示放情山水的乐曲,曲中也不乏大量“自然声响”的直接引入,就如丝竹名曲《春江花月夜》的摇橹声流水声、琴曲《流水》中大段以滚拂指法带出的流水段落般,中国音乐何只不排斥自然声响的引入,乐器如果不能以模拟或象征的手法处理自然,就不可能成为主要乐器。
这样的首尾相贯、系统有机,使我们谈中国音乐不能分割来谈,例如以为中国乐器不科学,因此尽可以直接用西方乐器来表达中国文化深刻的生命观照。
这首尾相贯、系统有机,也使纯然地在音乐中区分形上形下缺乏意义:谈形上看似核心,却可能空疏,谈形下看似有限,却一样可以举一赅万。
三、 乐器是把钥匙
举一赅万,是通透,看事物就在通透,能通透,从具体入,反更能寻迹而得,而具体的关键之一,就在乐器。
乐器是器乐之本,是器乐的载体,而器乐则是歌乐之外音乐的总称。以音乐与生命的贴近而言,自以歌乐为最,因为声是人所发、歌是人所唱,人乃最能共鸣;且歌乐通常有词,语言文字既是人类抒发情感、沟通彼此最自然有力的工具,歌乐之动人与重要乃不在话下。
相对于此,器乐抽象,美学距离感较远,引起贴身的感动较难,但器乐也有歌乐没有的优势。
优势首先在它的幅度,尽管人声在不同艺术形式因不同发展而多彩多姿,但毕竟受限于声带,未若器乐吹、打、拉、弹,只要能发声的,都可入乐。
优势更在它的极限。人声有音域、音色乃至速度、和声、复调的一定限制,器乐则远远冲破了这个局限。
优势也在它较远的美学距离感。陶潜对声乐与器乐的感染力曾有传世的名言: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他说的是:弹弦乐器的感染力不如吹管,吹管则不如人声。
陶渊明的时代并无拉弦乐器,丝就是发出点状音的弹弦乐,点状音与人声距离最远,所以与人较难直接感通;吹管虽是连续音,可惜多受音孔所限,不好发出人声般穿越音阶的弹性音、滑音―─而这类音正是人类不用意义语言表达情绪时的声调,所以也远了一些。
然而,这美学的排列倒过来也说得通:
肉不如竹,竹不如丝。
在人的情感经验里,所谓“不关己,关己则乱”,意指情感过度地贴近,人就丧失了对事物观照的能力,也就无以从当下的情境中扩充超越。用中国艺术的说法,这艺术就少了意境,而这意境,正就是弹弦的特色,琴、琵琶一两个单音,往往就能点出一种意境来,但“歌,唱得很有意境”却是很少见到的形容。
意境,是生命的扩充与超越,于是在器乐里,我们反更能感受一个民族更深的内在。
优势也在器乐有它更深、更直接的真实。歌乐感人,中国的歌乐讲究声情与词情兼备,声情是音乐的感染,词情是歌词的牵引,而后者还往往成为主要的部分。
器乐不然,它直接要求音乐,音乐抽象,不好藉事论理,但因此也就不流于文字的概念与装饰,也所以透过器乐可以更照见一个人、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文化的真实。
器乐重要,音乐世界里谁都不敢轻忽它,而乐器是器乐的载体,重要自不在话下,但中国乐器实际受到的待遇却大有不同。
一般人乃至音乐家眼中,有些乐器的确重要,例如钢琴、小提琴,号称乐器之王、之后,原因无它,因它性能卓越,表现力既深且广。但更多的民族乐器则不然,原因也无它,因它性能有限,表现力受限。
这样来论列乐器,似乎自然,但如果再进一步问,要有怎样的性能与表现力时,问题就来了。
你要用水墨画出油画凝固堆栈的量感,水墨当然就是拙劣的媒材,但换个角度,你要用油画写出水墨晕染渗透的流动,油画也只能相形见绌。
所以说谈性能、谈表现力,还先得谈想表现的是什么。
要洪亮伟大,西方声乐头腔体腔的共鸣就专长,要水磨婉转、一唱三叹,中国戏曲的行腔转韵就扣人心弦。
声乐如此,广垠的器乐更如此,谈和声、音响,钢琴自是不做他人想,但要讲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则不能做出弹性音、滑音这行韵手法的乐器又怎能成为称职的乐器。
所以关键还在观念。
这观念的误区,在以西方的标准看待自己,而更根柢的,是无视于乐器乃历史演化的结果,它并非只是工艺科技上的“客观”成果。
举例而言,中国的古琴音量很小,正缘于琴是用来进德修身,用来给自己与三两知音听的,音量原不须大;且小,更逼使听者须沉下心来听,这是个高明的心理学设计,否则以周代中国已可以铸造每钟可发出两个音的编钟,对由木板合成的琴要说无法扩充其音量,其谁能信?
所以说,历史乐器之成为现在的样貌,其实是美学理念与音乐表现长期激荡的结果,此结果使乐器充满了独特性,从这独特性还原,也就可直接窥到这文化的心灵特征。
正因乐器具有独特的性能与外表,又可直溯那心灵与美学的特征,所以从乐器进入音乐乃至文化系统确是一种方便与殊胜,也所以,尽管我在自己所著的《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中,以最多的篇幅在生命境界美学理念与表现手法上做了系统的连接,但有意思的是,许多非中乐界者尤其西方音乐家最直接的触动,却来自我谈中国乐器的那章。
谈乐器可以有许多谈法,从材质、结构、演奏法到美学,而我在这章尽管各部分都点到了,但许多人最感兴趣、印象也最深刻的则是它的“宛然实在”。在这章里我说明了中国传统的五个重要乐器,与特殊生命情性的关联:琴/高士、琵琶/侠客、笛/书生、筝/儿女、胡琴/常民,西方人在此,尤其讶异于中国乐器彼此间竟有这么明显的生命对应,相较之下,西方乐器固也有它的个性,但与某种生命属性的连接并不明显。
这是个有意思的对照,“乐为心声”,乐器与生命属性的连接,因此也就不只反映了中国器乐独特的历史发展,更根柢地映照了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
由此切入,你就拥有了一把译码中国音乐的钥匙。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名字,在我看来,就像是在邀请我去参加一场盛大的文化筵席,而桌上的主角,正是那些承载了千年中华文明的乐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以一种极为细腻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去描绘这些乐器的“生命”。何谓“生命”?我想,那不仅仅是它们能发出悦耳的声音,更在于它们如何与人、与历史、与自然发生联系,并从中汲取养分,生长、演变、传承。这本书是否会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带我游览那些琳琅满目的中国乐器世界?它是否会为我细致地讲解每一种乐器的起源、发展,以及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所呈现出的独特风貌?我尤为期待的是,作者是否会深入探讨乐器背后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例如,古琴的“涤除玄览”,是否就蕴含着道家的清静无为?而编钟的宏大庄重,又是否象征着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这本书,或许不仅仅是关于乐器的知识普及,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精神内核的探索。我希望能从中读出,那些乐器是如何在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是如何成为人们表达情感、寄托情思、甚至沟通天地的重要媒介。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将冰冷的物质,赋予了如此鲜活的灵魂,使其“宛然如真”。
评分当我看到《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书名时,我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知欲。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好奇的读者,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乐器,比如古琴、琵琶、二胡、笛子等等,它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发声工具,更是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哲学思想和历史记忆的载体。书名中的“生命性”,更是让我感觉这本书会带给我一种全新的、更具深度和温度的阅读体验。我设想,作者一定是一位对中国乐器有着深厚情感和渊博知识的学者,他/她能够超越对乐器结构和演奏技巧的简单介绍,而是深入挖掘乐器本身所蕴含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或许体现在乐器的材质选择和制作工艺上,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或许体现在乐器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宫廷到民间,从庙堂到江湖的流变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又或许体现在那些与乐器相关的诗词歌赋、文人雅事中,乐器与人的情感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让我重新认识中国乐器,不仅仅是了解它们的种类和声音,更重要的是去感受它们背后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以及这些古老的乐器是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它们独特的光彩,并且继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评分《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书名,自带一种古朴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气息,让我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我一直觉得,中国乐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发声器,它们是历史的沉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生命性”这个词,更是点燃了我对这本书的强烈期待。我很好奇,作者会如何赋予这些乐器以“生命”?是会深入剖析它们的制作工艺,揭示其中蕴含的匠心独运和对自然的敬畏?是会讲述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流转,如何从皇家殿堂走向民间,又如何穿越战争与变革,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声音?还是会描绘那些与乐器相伴的文人墨客、市井百姓,他们如何将自己的情感、思绪、理想寄托在悠扬的旋律之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破我对中国乐器的刻板印象,展现它们的多元化、创新性以及在当代社会依然拥有的巨大潜力。我想,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乐器的书,更是一次关于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我期待,通过这本书,我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感受到那些乐器所蕴含的东方哲学和审美意境。我想,读完之后,我定然会对中国乐器产生一种全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情。
评分翻开《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本书,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世界。书名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哲思,让我忍不住去探寻,究竟是什么样的“真”能被如此生动地描绘,又是什么样的“生命性”在这些古老的乐器中跳动。我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各种中国乐器的外观和发声原理,而是能带领我深入了解它们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故事。我希望,作者能够以一种充满感情的笔触,去描绘每一件乐器,它们可能是在深宫大院中奏响过庄严的乐章,也可能是在市井巷陌中吟唱过悠扬的歌谣。我尤其想知道,这些乐器是如何与中国人的情感、思想、甚至哲学观念紧密相连的。比如,古琴那“泛音、按音、散音”的丰富表现力,是否就蕴含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而编钟那宏大而又和谐的音响,又是否象征着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我打破对中国乐器的一些固有印象,让我认识到它们的多元化、创新性,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依然能够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我期待,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以及这些古老的乐器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并继续滋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
评分看到《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标题,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许多画面:在古朴的庭院中,一位老者抚弄着古琴,琴音如流水潺潺;在热闹的市井,艺人怀抱琵琶,弹奏着婉转的乐章;在庄严的宫殿,编钟齐鸣,奏响着洪亮的礼乐。而“生命性”这个词,更是给我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本书绝非一本枯燥的技术手册,而更像是一次深情的对话,一次跨越时空的灵魂交流。我好奇,作者是如何捕捉并展现中国乐器那独特的“生命力”的?是通过对乐器材质、结构、音色的细致描摹,让我们感受到其内在的韵律和张力?是通过追溯乐器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展现其适应时代变迁、传承创新、生生不息的韧性?抑或是,是通过解读乐器与文学、艺术、哲学、甚至民间信仰的紧密联系,揭示其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和精神寄托?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让我意识到,中国乐器并不仅仅是某种特定时期、特定场合的“老古董”,而是拥有独立生命,能够与当代人产生共鸣的活态文化遗产。我希望能通过阅读,不仅了解各种乐器的名称和声音,更能体会到它们背后所蕴含的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审美情趣以及对生命的理解。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重新发现,那些曾经被遗忘或忽视的音乐之美,并从中汲取力量和灵感。
评分当我第一次看到《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书名时,一种久违的文化冲动便在我心中激荡开来。我一直认为,中国乐器,是中华民族情感的流露,是历史的回响,是哲学思想的具象化。而“生命性”这个词,更是直接点燃了我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我期待,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乐器的种类、构造和演奏方法,而是更深入地去挖掘乐器本身所蕴含的那种“活生生”的特质。我设想,作者可能会从乐器的起源和发展入手,讲述它们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又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形成独特的风格。我同样期待,书中会深入探讨乐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比如乐器在古代文人雅士生活中的地位,它们如何成为表达情感、寄托情怀的媒介,以及它们如何与绘画、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相互辉映。这本书,是否会让我感受到,那些古老的乐器,即便历经沧桑,依然能够发出动人的声音,依然能够触动现代人的心灵?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不仅仅是它的旋律,更是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这本书,或许能成为一把钥匙,帮助我打开通往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大门。
评分《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书名,自带一种古典的优雅和深邃的意境,立刻吸引了我。我一直对中国传统乐器充满着好奇和敬畏,它们不仅仅是发出声音的工具,更是凝聚了数千年智慧、情感和哲学的艺术品。而“生命性”这个词,更是让我觉得,这本书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解读这些古老的器物。我猜想,书中会讲述许多关于乐器的故事,它们可能关于乐器的诞生,关于匠人的心血,关于文人墨客的钟爱,也关于它们在历史洪流中的跌宕起伏。我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极其细腻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去描绘这些乐器,不仅仅是它们的形体、材质和音色,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如何与人类的情感、思想、精神相连接,又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繁衍生息。这本书,是否会让我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乐器,比如古筝的典雅、琵琶的灵动、二胡的忧伤?我希望,它能带我领略中国乐器那独特的东方韵味,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深沉而又细腻的情感力量。读完这本书,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这些古老的乐器,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依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并继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评分《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个书名,仿佛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古老东方智慧的大门。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中国乐器的书,更是一种对生命、对文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我迫切地想要知道,作者是如何将“生命性”这一概念,注入到那些冰冷的乐器之中,让它们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我猜想,书中会讲述许多关于乐器的故事,不仅仅是它们的历史渊源和制作工艺,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命运变迁,以及它们如何与人们的情感、思想、精神紧密相连。我期待,作者能够以一种诗意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去描绘那些或古朴、或典雅、或激昂的乐器,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能听到悠扬的琴声,感受到激越的鼓点,触摸到岁月的痕迹。这本书,是否会带领我穿越时空,去感受古人如何通过音乐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如何通过乐器来寄托他们的家国情怀?我希望它能够展现出中国乐器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它们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传递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读完这本书,我希望自己能够对中国乐器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不仅仅是它们的“形”,更是它们的“神”,不仅仅是它们的“声”,更是它们的“魂”。
评分读过不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书籍,但《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这样独特的切入点,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我一直对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古老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中国乐器,在我看来,它们不仅仅是乐器的本身,更是凝聚了无数匠人智慧、文人情怀以及时代印记的艺术品。这本书的标题——“生命性”,更是给我一种强烈的暗示,作者并非仅仅将它们视为冰冷的器物,而是赋予了它们鲜活的灵魂和情感。我很好奇,作者将如何展现这种“生命性”?是通过对乐器材质、制作工艺的深入剖析,来揭示其内在的生命力?还是通过追溯乐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合的演变和应用,来展现其功能的拓展和精神内涵的丰富?亦或是,通过解读那些与乐器相关的诗词歌赋、传说故事,来挖掘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打破我们对中国乐器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它们只适用于古典场合,或者只适合某些特定年龄段的人群。相反,我期待它能展现出中国乐器的多样性、创新性,以及它们在当代社会依然能够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这本书,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这些古老的乐器,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依然保持着它们独特的魅力,并且继续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评分初次翻开《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被这书名便吸引住了。那“宛然如真”四个字,仿佛带着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魔力,让人忍不住去探寻,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才能被描绘得如此生动?中国乐器,在我们许多人的印象中,或许是博物馆里的陈列,或许是传统戏曲的点缀,又或是古装剧里的背景音。但这本书,似乎要颠覆这种刻板的认知。它不是一本枯燥的乐器图鉴,也不是一本艰深的音乐理论著作。从书名传递出的那股“生命性”来看,作者定然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解构、去品味这些承载着华夏民族魂魄的器物。我期待它能带领我走进那些尘封的时光,去感受古人如何将情感、智慧、哲学,甚至是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巧妙地注入到每一根弦、每一个孔、每一块木头之中。它是否会讲述那些乐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否会揭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独特角色?是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一件乐器,绝不仅仅是发声的工具,更是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载体,以及人类情感的直接表达。我甚至能想象,在阅读的过程中,那些古老的旋律仿佛会从纸页间流淌出来,在我的脑海中回响,勾勒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我体会到中国传统音乐那深沉而又细腻的魅力。这本书,或许能成为一把钥匙,为我打开通往中华文化深处的一扇门,让我与那些“宛然如真”的乐器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评分在京东购物较多,无法一一详评,有这段文字说明我对产品质量是满意的。如果质量差我会给差评,至于性价比,因为我不敢保证你买的价格和我买时的价格相同,所以不作评论。
评分很好,就是定价有点高…………………………………………………………………………
评分不错,有需要,再来买书
评分啦咯啦咯啦咯拒绝啦咯啦咯啦
评分书包装完好,送货很快,推荐阅读好书
评分一直在京东买东西,东西很好,需要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评分啦咯啦咯啦咯拒绝啦咯啦咯啦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老师让买了但没有看额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