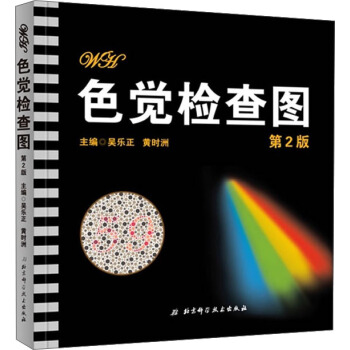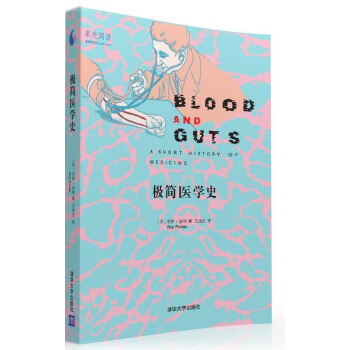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两小时纵观西方医学史如此全面又如此精悍
只有罗伊·波特做得到
内容简介
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在为生存与健康而战,这就是原始普遍的斗争。本书源自罗伊·波特上课的讲稿,以八个主题概述西方医学史,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波特机智风趣,视野广阔,从远古到现代,他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战,告诉读者,面对坚不可摧又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医学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国际知名的英国学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和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的名誉院士。2001年自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医学史研究所退休,退休后不满九个月就因心脏病发去世,学界同声惋惜。倾其一生投入研究、写作与教学,在英国社会史、科学史、医学史等领域都有精彩专著,撰写与编辑的书超过百部,尤以医学史领域的作品著名,其具野心的作品当属出版于1997年的《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王道还,中国台北市出生,生物人类学者,译作包括《第三种黑猩猩》、《盲眼钟表匠》等。
精彩书评
医学史学家不应只考虑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关照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并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论这一点,没人比得上罗伊· 波特。——理查德· 霍顿(Richard Horton),《柳叶刀》主编
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奥利弗· 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作家
这本书是一位杰出学者对一个重要话题所做的介绍,读来畅快,信息丰富。
——杰拉德· 格罗布(Gerald N. Grob, Ph.D.),罗格斯大学名誉教授
目录
导读(李尚仁)致谢
序
第一章 疾病
第二章 医师
第三章 身体
第四章 实验室
第五章 治疗
第六章 外科医学
第七章 医院
第八章 医学与现代社会
进阶书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人体是疾病与医生的战场。这场战争有开场,有中场,却没有收场;换言之,医学史并不是个简单的故事,并不只是一连串胜利铺成的进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旧约?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故事,都暗示我们:疾疫、疫疠与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同,大多是人类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会,疾病一向是社会产物,过去是,未来也是,与疾病对抗的医学更是。文明不仅滋生精神官能症,也滋生疾病。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大约六百万年以前,第一个猿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非洲出现。他们额头低、颚骨大、脑子与黑猩猩一样大。四百万年之后,以直立体态行走、脑量开始增长的直立人祖先演化出来了。他们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术。一百八十万年前,这群杂食性的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大约十五万年前,他们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们的直接祖先。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艰苦又危险的环境里,寿命很短。然而,他们却不受大疫侵扰,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生活在受大疫蹂躏的社会里。他们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有些类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里,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想来他们从来不曾遭遇过传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类的疾病),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感染对象,或者潜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因此不会污染水源,或遗留大量的污秽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虫。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家畜。在人类历史上,家畜的角色可说一言难尽:家畜是创造文明的基础,但是它们也是传染病的温床,有时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
人类生养众多,以地球为殖民地,自己也成了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肠道寄生虫,例如吸虫、绦虫、蛔虫,与寄生昆虫,如跳蚤、虱子;还有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它们的繁殖速率极高,能在宿主体内制造严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因而捉摸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仅他们自身有了保障,还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些微生物敌人与人类陷入了演化竞争,难以自拔。这种竞争的特征是,没有最终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不稳定的共存。
人类发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后,先在亚洲与南欧的温暖地区生活,然后再向北方迁移。直到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冰河时代(更新世)结束了,人类都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猎物枯竭后,加上再也没有大片无人地带了,人类迫于人口压力,只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没有其他办法。
民以食为天,人类以试错法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将野草培育成谷类——小麦、大麦、稻米、玉米等,同时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驯化,还有鸡、鸭、鹅等家禽。也不过几千年,石器时代的猎人已转变成牧人与农人,有能力支配农牧业不够先进的邻近社群了。人类通过了第一个生存考验。
人类掌握了畜牧与农耕的技术之后,社群中的人口数就能够不断扩增。开荒、收割,以及后续的食物处理,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农牧生产足以供应他们。这些发展最后导致更有组织、更永久性的小区(村庄、城镇、都市),它们有君长、法律、社会阶层,然后还有法庭与官员。在其他行业与职位中,治疗疾病的专家出现了。
虽然农业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可是也释出了新的危险:传染病。一向只在野生动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经过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转变成能够感染人的病原;原来的动物疾病,跳越了物种界限,成为人类疾病。这种演化适应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过六十种,而人与其他家畜、家禽的共患疾病,只比这个数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时代,牛已在人类病原库中添加了结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猪与雁鸭传递了流感病毒,马带来了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热病)病原从牛与家犬转进到人身上的结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疯牛病危机,家畜的疯牛病(BSE)与人类的克雅病(CJD)同源。经营农场的人贪婪又马虎,会促成更多动物病原跳跃到人身上,制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面,人也相当脆弱。农场和家屋里的家畜、小动物(如老鼠、蟑螂),会散布沙门杆菌和其他细菌;它们的粪便会污染家庭用水,传播小儿麻痹症、霍乱、伤寒、肝炎、百日咳、白喉;谷仓则会受细菌、有毒真菌、鼠类排遗与昆虫污染。简言之,人定居后,也招揽了疾病上门定居。
同时,蠕虫成了人体内的永久居民。蛔虫是寄生性线虫,专门寄生人体的蛔虫也许是猪蛔虫演化出来的,会导致下痢与营养不良。其他的蠕虫也在人的肠道定居,例如钩虫。寄生在淋巴系统中的丝虫导致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症的丝虫则寄生在皮下组织。农业只要依赖灌溉,不管它在哪儿生根,都在当地造成严重的地方病,例如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华南。水田里藏有许多寄生虫,能进入赤脚农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虫。
就这样,永久性的人类小区为蟑螂、鼠类、寄生虫等生物创造了最佳的生存与繁衍机会。此外,农业使人类过度依赖富含淀粉的单一作物,它们往往缺乏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例如玉米。发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各种疾病,例如缺乏维生素B3(烟酸)就会生糙皮病,缺乏维生素C引起坏血病,缺乏蛋白质与热量会使身体羸弱不堪。在非洲,严重的营养不良是新生儿与儿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质缺乏症(Kwashiorkor)。从居无定所的生活形态转型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人类的健康情况就恶化了,传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连身高都受影响,人类变矮了。
定居生活还招来了疟疾。直到现在,居住在气候温暖地区的人仍受疟疾威胁,随着大气不断暖化,它可能会散布到更广大的区域里。 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区,化森林为农场的行动,产生了温暖的水洞与犁沟,它们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环境。疟疾的症状,古希腊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们才知道病因,因为那时热带医学已经证明疟疾的症状是由疟原虫造成的,而疟原虫是疟蚊传播的。疟蚊叮咬人的皮肤吸血,疟原虫因而进入人体血管,随血流进入肝脏,疟疾发病前一两个星期(所谓“潜伏期”),它们就在那里繁殖。等到疟原虫回到血流中,首先攻击的就是红细胞,红细胞大量破坏,造成剧冷剧热交替反复的症状。
疟疾紧盯着农业社群不放,从非洲扩散到近东、中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与华南沿海地带,也难逃它的诅咒。到了16世纪,欧洲人将疟疾带到了新世界。
拥挤的定居社群制造了大量废物与污物,培育了横行的传染病,可是人类的雄心与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继续扩张下去,才不管生活在其中对身体健康多么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时就有大疫流行,它们只会暂时消歇,从不消灭。在农业出现之前,全球人口大约有500万左右;到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时),已膨胀到1亿,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张仲景、华佗时代,人口翻了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达60.8亿,估计21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会增加一倍。
现在,人口压力已造成广泛的匮乏与粮食不足,再度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但是,营养不良也好、寄生虫也好、大疫也好,人类从来不是只能坐待疾病侵袭,束手无策。大疫的幸存者,身体里会有一些抗体;最后,由于天择,人的免疫系统变得越来越精密,使人能够与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婴儿通过胎盘与母乳,可以获得一些母亲的免疫力;还有基因盾,可以保护身体不受病原的侵袭,例如身上有一个“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人,对间日疟有抵抗力,这个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较多,学者认为是当地疟疾流行的结果(哪里知道,这个天赋反而使他们成为美洲农场的理想劳工)。针对致命病原,人类的适应能力因此有机会挫其锋锐。
……
前言/序言
序本书探讨人、疾病、健康照护之间的历史互动,将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与信仰脉络中观察。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讨论西方医学——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医学传统。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医学的古今之变,而不是它的一脉相传,至于题材,则尽可能应有尽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种治疗疾病的人(第二章);对身体的研究(第三章);发源于实验室的现代生物医学与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第四章);治疗疾病的手段,特别是科学医学(第五章);外科医学(第六章);医院——关键的医疗机构(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则评估现代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
我对有血有肉的个人,着墨不多,例如个人的生病经验,以及生病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但是患者的反应,例如患者对生病的反应、对因生病而失能的反应、面对死亡威胁的反应,是我在写作时念兹在兹的潜台词。对疾病担惊受怕(无论是潜在的威胁还是实质的威胁),急、慢性病导致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经验。人类为应付病痛与死亡,理性与感性、个人与群体都动员了,宗教与哲学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个社会都有许多清规戒律与法门,平时预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们又是对抗、处置与认知的工具。“为什么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这种疑问苦缠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冲着患者而发作的,是报应,或者有道德意义。因此,有的疾病“坏”,如麻风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结核与天才有关,而痛风则是绅士的符记。疾病也可以解读成上帝的惩罚——这个过时观念在艾滋病问世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再度浮现。医学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关于身体的信念(不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病体)居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因而是“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书焦点是医学史,无法深究这些疾病的个人诠释与“体”验,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书末“进阶书目”的有关文献。不过,对疾病与医师的焦虑是普遍现象。任何叙述受苦与解除苦难的故事,都该将这些恐惧编织进去,而不该将它们当作不重要的素材,因为自我是身/心连续体,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书诉说的是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是患者与濒死者的苦难。
用户评价
当我拿到《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下可以系统地了解一下医学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了。这本书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它就像一个耐心细致的老师,将医学这门古老又现代的学科,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医学概况的介绍,让我对古代医学的局限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比如,那些关于草药的知识,虽然在现代看来可能不够精确,但却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最初尝试。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重大医学发明背后的故事的讲述,比如X射线的发现,它在医学影像学上的突破,让医生能够“透视”人体,诊断疾病,这在当时无疑是颠覆性的。这本书也让我看到了医学发展中那些“弯路”,比如一些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疗法,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恰恰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和不断进步的本质。它让我明白,医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正的过程,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更接近真理的探索。这本书也让我对那些默默奉献的医护人员充满了敬意,他们的辛勤付出,构成了医学不断前进的基石。
评分我一直对那些能够“纵览全局”的书籍情有独钟,而《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恰恰满足了我这一点。它就像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医学全景的窗户。这本书的结构设计非常精巧,从人类最早的医疗实践,到中世纪的宗教医学,再到近代科学的崛起,最终抵达现代医学的辉煌成就,时间线索清晰明了,内容层层递进。我惊喜地发现,原来医学的发展并非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甚至倒退。书中对那些曾经盛行一时却后来被推翻的理论,比如炼金术在医学中的应用,也做了客观的描述,这让我深刻理解了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医学实践的探讨,比如早期的手术,那些在没有麻醉和消毒的条件下进行的“治疗”,读起来让人心惊胆战,同时也更加体会到现代医学的来之不易。这本书也让我看到了医学发展中的伦理困境,比如早期的人体实验,以及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医疗保障问题。作者的分析非常中肯,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它让我明白,医学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和知识的进步,更是社会进步和伦理完善的体现。这本书也让我对未来的医学发展充满了好奇,在基因技术、再生医学等领域,医学将如何继续改写人类的命运?
评分说实话,我之前对“医学史”这个概念有点敬而远之,总觉得会是堆砌枯燥的年代、人名和事件。《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就像一个友善的向导,牵着我的手,在医学的奇妙世界里漫步。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吸引人,它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更像是一系列精彩的“医学故事”。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将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充满趣味。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一些重大医学事件的描写,比如黑死病的肆虐,霍乱的流行,这些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灾难,更是促使医学不断反思和进步的催化剂。读到那些关于瘟疫的章节,我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恐慌和无助,也能看到医生们在绝望中的挣扎和探索。书中对不同文明在医学发展中的贡献也做了很好的梳理,让我了解到,医学的进步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专利。从古埃及的草药疗法,到古希腊的理性思维,再到伊斯兰世界的药物学和手术技术,以及中国古代的针灸和本草,每一个文明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医学不仅仅是关于疾病和治疗,更是关于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如何与疾病抗争,以及如何追求健康和长寿的智慧。它让我从一个宏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医学的意义和价值。
评分我一直对那些能够“串联”知识的书籍非常着迷,而《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正是这样一本能够将医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串联成一条清晰脉络的杰作。它以一种非常宏大的视角,带领我回顾了医学从萌芽到繁荣的漫长历程。书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医学发展的比较,也让我耳目一新。我能看到,即使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下,人类对于疾病和健康的追求,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尤其欣赏书中对那些“边缘”医学分支的探讨,比如心理学在医学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这让我明白,医学不仅仅是关于生理上的疾病,更是一个与人类身心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复杂系统。这本书也让我对“进步”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医学的进步,并非是简单的技术迭代,而是伴随着伦理、社会和人文观念的同步发展。它让我看到了,在每一次医学革命的背后,都蕴含着人类对自身更深刻的认识和对生命的更高尊重。它也让我对未来的医学发展,充满了期待,特别是那些能够兼顾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的新型医学模式。
评分我一直对人类的探索精神感到着迷,而医学史无疑是这种精神最直接的体现之一。《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来审视这种精神。它不仅仅是罗列医学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地剖析了医学发展背后的驱动力——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对疾病的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渴望。书中对那些颠覆性的医学理论和技术的出现,都做了详尽的阐述,比如疫苗的诞生,它如何从一种半信半疑的尝试,最终改变了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历史。我特别欣赏书中对那些“非主流”医学思想的介绍,比如民间疗法、巫医等,虽然它们在科学上可能存在局限,但它们同样反映了人类在不同时期,为解决健康问题所做的努力和智慧。这本书让我明白,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的路径。它也让我对那些在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仅仅是他们的科学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我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以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这本书让我对医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我相信,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还在,医学就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
评分我一直认为,理解事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它的起源开始。《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正是我寻找的那个“起源”。它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医学世界的大门。书中对人类最早的医学实践的描述,让我感受到了生存的艰辛和智慧的闪光。从巫术、祭祀到经验性的治疗,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我尤其喜欢书中对那些关键人物的刻画,他们不仅仅是医学史上的符号,更是鲜活的个体,有着自己的梦想、困惑和坚持。比如,我读到了关于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故事,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 serendipity(意外发现),让人感叹科学的奇妙。这本书也让我对现代医学的成就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些曾经困扰人类的瘟疫、疾病,如今已经有了有效的防治手段,这背后是无数代医学工作者不懈努力的成果。它也让我看到了医学发展中的一些哲学思考,比如关于生与死,关于健康与疾病的本质。这本书不是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一种思想的启迪,让我重新审视了生命和医学的意义。它也让我对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更多的思考,特别是那些能够真正改善人类福祉的创新。
评分我一直在寻找一本能够系统性地梳理医学发展脉络的书,而且不希望过于学术化,能够轻松地阅读并有所收获。《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完美地契合了我的需求。它以一种非常“轻”的方式,带我穿越了医学的长河。从那些早期的经验主义治疗,到科学方法的引入,再到现代医学的精细化分工,整个过程的梳理非常清晰,逻辑性很强。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中融入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因素,这让我明白,医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紧密相连。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对解剖学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又如何影响了医疗器械和治疗手段的革新。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的介绍也很到位,不仅仅是列出他们的贡献,更展现了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我仿佛看到了帕斯德尔和科赫在显微镜前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找出致病的微生物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医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完美,只有持之以恒的求索。它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些曾经被认为是“灵丹妙药”的疗法,后来被证明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拥抱不确定性,勇于自我否定,以求真理。这本书也让我对未来的医学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在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影响下,医学将走向何方?这让我充满了期待。
评分拿到《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我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一直觉得医学史是一个庞杂而难以企及的领域,没想到这本书却用一种极其友好的方式,将这个庞大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它的语言风格非常活泼,甚至带有一点幽默感,这让我完全没有产生阅读疲劳。书中对一些医学概念的解释,也做得非常到位,用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例子,将复杂的原理化繁为简,让我这个医学小白也能轻松理解。我尤其喜欢书中对那些“意外的发现”的描写,比如青霉素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它让我明白,科学的进步并非总是按部就班,有时候灵感和运气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本书也让我对那些在医学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们在那个男权社会中,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为医学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它让我明白,医学的进步,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分性别,不分种族。这本书也让我对“治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消除疾病,更是让生命焕发活力,让个体重拾尊严。
评分第一次拿到《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这本书,我以为会是一本严肃到让人打瞌睡的史料汇编,没想到它却是如此地引人入胜,甚至可以说是“接地气”。这本书的叙事风格非常独特,它没有使用大量晦涩的专业术语,而是用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语言,讲述医学发展过程中那些鲜活的故事和人物。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小人物”的关注,比如那些默默无闻的护士,那些在战争中救死扶伤的军医,他们的奉献同样是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书也让我看到了医学发展中那些“意想不到”的关联,比如一些伟大的发现,并非完全是出于预设的研究目标,而是源于偶然的观察和灵感的碰撞。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某些疾病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的描述,就如同在阅读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充满了悬念和推理。它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疾病会突然出现,又为什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其形态。这本书也让我对“健康”的定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仅仅是身体没有疾病,更包含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福祉,这与现代医学的整体观不谋而合。它也让我思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和获取医学信息,避免被误导。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是医学领域的一场启蒙,我之前对医学的认识,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迷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拿到《极简医学史/果壳阅读》后,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从那些古老的传说,比如巫术和神灵的治疗方式开始,一直到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整个过程就像是在看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作者的笔触非常有画面感,我仿佛能看到那些最早的医生们,在简陋的环境下,用最原始的工具,一点点地探索人体,一点点地积累经验。那些关于解剖学的早期探索,虽然充满了禁忌和风险,但正是这些勇敢的尝试,为我们揭开了人体内部的奥秘。我特别喜欢书中对那些重要转折点的描述,比如微生物的发现,抗生素的发明,疫苗的诞生,这些不仅仅是科学上的突破,更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我能想象到,在那个时代,当人们第一次看到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小怪物”是如何致病的,以及如何用药物去对抗它们,那种震撼和惊喜是多么巨大。书中对于不同时期医学思想的演变也描绘得非常生动,从希腊的体液学说到中国的阴阳五行,再到后来的细胞学说和基因理论,每一种理论的兴起和衰落,都反映了当时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和进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也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本书让我对医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敬畏之心,原来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医疗手段,背后是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它不是枯燥的史实罗列,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讲述,让我看到了医学发展中人性的光辉,也感受到了科学探索的魅力。
评分有空看
评分有趣之书@
评分快速了解医学的发展史。
评分1
评分还好还好还好还好,挺不错的,值得看一看,学一学。
评分^_^写得挺好的。
评分包装坏了,书没问题,希望以后不要用纸袋包装,书还没看,
评分适合任何人看,很有趣味
评分本书源自罗伊·波特上课的讲稿,以八个主题概述西方医学史,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波特机智风趣,视野广阔,从远古到现代,他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战,告诉读者,面对坚不可摧又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医学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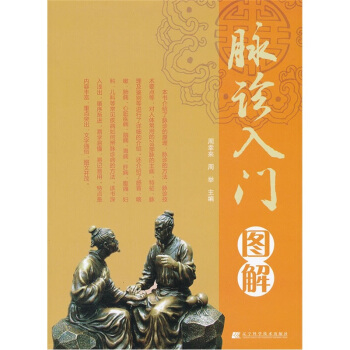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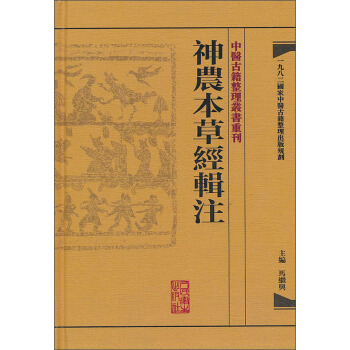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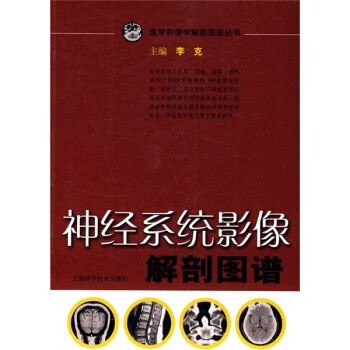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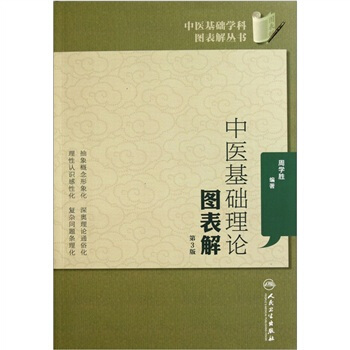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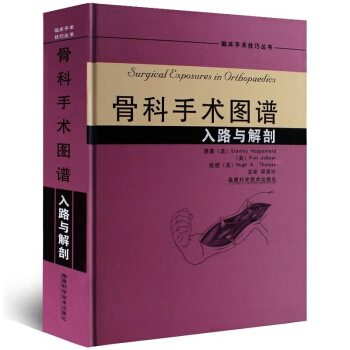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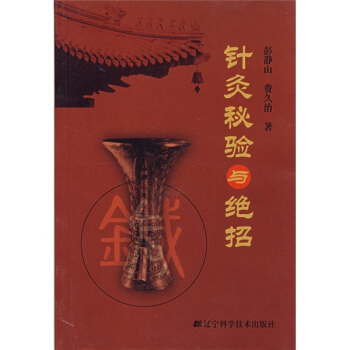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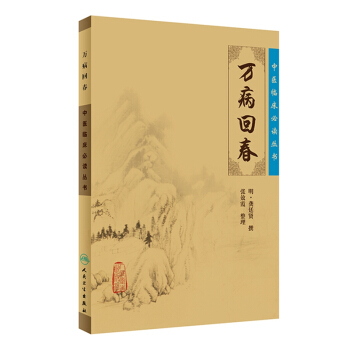



![Pain实用临床疼痛学 [Pratical Pain Managemen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96364/cc93737a-3e8a-4615-8994-41b4f432a90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