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三十余万字、六十余幅珍贵照片
首度集中披露
内容简介
周扬死后,荒煤、张光年等“我辈”皆无文章,为何?伟人说:“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何解?
1964年,电影界“老头子”夏衍遭遇怎样的噩运?
雎水关十年,沙汀为何一直念念不忘?
窗外喧哗,晚年巴金内心又有怎样的孤独?
“书生作吏”
八位新中国文坛亲历者们的内心独白
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
……
一切,尽在此书!
作者简介
严平,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创作小说、散文等,发表研究文章、人物专访、散文、小说等十余种。著有《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等。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历史人物研究,在《收获》杂志主持专栏写作“遗失的青春记忆”、“潮起潮落”。
目录
周扬“我辈”无文章
最后的启航
夏衍
夏衍的1964
刻入年轮的影像
沙汀
生命的承受
何其芳
历史的碎片
陈荒煤
告别梦想
许觉民
人去楼空
冯牧
在激流涌动中
巴金
孤独与喧哗
后记
精彩书摘
最后的启航一再聚首
周扬和他的战友们再度聚首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1977年10月,头上还戴着三顶反动帽子在重庆图书馆抄写卡片的荒煤,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来临,他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文艺界组织起来:
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
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虽然历史上两次被周扬批判,“文革”入狱更与周扬分不开,在狱中,荒煤也从未想到有生之年还要和周扬并肩战斗。但当解冻的春风吹来时,他还是立刻就意识到文艺界需要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仍非周扬莫属。
写这封信的时候,周扬从监狱出来赋闲在家已有两年。从四川到京看病的沙汀,怀着关切和期待的心情屡次前往周扬住处看望;张光年则利用自己复出的地位为周扬早日在文艺界露面创造条件;而文艺界更多的人士纷纷以写信、探望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周扬的关注和期望。尽管有“两个凡是”的影响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影,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似乎仍然故我。
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夏衍、冯乃超、曹靖华等一百多位老文艺工作者应邀出席。周扬首次露面,时任《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的刘锡诚称,这是此次会议中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清楚地记得,周扬到达会场时,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这位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未曾露面的老领导的出现,当面容苍老了许多的周扬步入会场时,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扬的心情显得异常激动,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刘锡诚说:
大概因为这是周扬在多年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在作家朋友们面前讲话的关系,显得很拘谨,用词很谨慎。他在讲话开始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这个座谈会,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很虔诚地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从他的脸上汹涌地流下来,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这次会上所做的检讨和自责,以及他的讲话的全部内容,得到了到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和谅解。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事后看,周扬当时的讲话虽然开放幅度并不很大,但他的出现不仅让在场的人感到了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也给各地文艺界的人士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只停泊了十几年的大船虽然百孔千疮却没有被彻底摧毁,它将缓缓地收拾起碎片,调整好风帆,在大风来临的时候启航。
远在重庆的荒煤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新的动向。在夏衍的鼎力相助下,他开始向中央申诉。很快,由邓小平批转中组部。1978年2月25日,平反结论终于下达。一个月后,荒煤在女儿的陪同下踏上了回京的列车。
那是一个早春的时节,在轰隆隆驶向北方的车厢里他怎么都无法入睡。1975年,作为周扬一案的重要成员,他被宣布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罪状仍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定叛徒纯属捏造。后来他才知道,专案组一直为他的叛徒问题大伤脑筋,但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三年前,他就是戴着这三顶帽子,被两个从重庆来的人押着上了火车。临上车前专案组交给他一只箱子,那正是1966年夏天他接到通知匆忙赴京时拎着的一只小箱子。在列车洗漱间的镜子里他看见了自己,这是入狱七年来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模样,镜子里的人脸色浮肿而灰暗,目光呆痴,头发几乎全都掉光了,隆起的肚子却像是得了血吸虫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一年他六十二岁。
现在他回来了,三顶帽子虽然甩掉了“叛徒”一顶,还有两顶却仍旧戴在头上,这使他在激动不已的同时也感到了很深的压抑。不过他牢记夏衍的嘱咐,只要不是叛徒其他一切回京再说。重要的是速速回京!从报纸上发表的消息看,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已经纷纷露面,他是归来较晚的人。想到还有许多老友再也无法回来了,他们永远地消失在漫漫的黑夜中,眼泪就禁不住悄然涌上他的眼眶。
火车在七点多钟停靠站台。走出站口,灯光并不明亮的广场上,张光年、冯牧、李季、刘剑青等人急急地迎上前来,几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问候声、笑声响成一团,让荒煤在春寒料峭的夜晚感觉到一阵阵扑面而来的暖意。
从张光年的日记看,那天,这已是他们第二次前往车站迎候了。按照列车抵达的时间,一行人六点二十曾准时赶到车站,火车晚点一小时,于是他们回到离车站较近的光年家匆匆用过晚饭再次前往,终于接到了荒煤。很多年后,荒煤都能清楚地想起那个清冷的夜晚,人群熙攘的北京站广场上,那几张久违了的面孔。多年不见,他们虽然都已明显见老,但久经风霜的脸上,却充满着惊喜和掩饰不住的热情。
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的张光年先于他人而复出,此时已是《人民文学》主编,并担负着筹备恢复作协、《文艺报》的工作。这位诗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较少提及:“‘文革’初期那几年,我们这些由老干部、老教师、老文化人(科学家、文学家、文艺家等等),组成的‘黑帮’们,日日夜夜过的是什么日子?身受者不堪回忆。年轻人略有所闻。我此刻不愿提起。但愿给少不更事的‘红卫兵’留点脸面,给‘革命群众’留点脸面,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吧。”(张光年《向阳日记》引言,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他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个被江青操纵的中央专案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他在十五岁时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他最痛心的是,他的妹妹——一个与周扬从未见过面远在乌鲁木齐的中学教师,却因周扬“黑线”牵连而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他的衰老怕事的老父亲因两次抄家受惊,脑血栓发作而去世……他自己在经历了残酷的斗争后又经历了七年干校时光,风餐露宿、面朝黄土背朝天,学会了在黑夜里喘息,也在黑夜里思考……
1978年那晚的北京站广场,出现在荒煤面前的冯牧面色消瘦,声音却一如既往的干脆洪亮。青年时代起冯牧就饱受肺病折磨,父亲曾担心他活不到三十岁,他却带病逃离沦陷的北平,不仅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战争考验,还闯过了病魔把守的一道道险关。“文革”时,他和侯金镜等人因暗地诅咒林彪江青被关押,凶狠的造反派竟挥拳专门击打他失去了功能的左肺……他挺过来了。从干校回城看病的日子里,他曾经用篆刻排遣漫长的时光,倾心之作便是一方寄托了许多寓意的“久病延年”,“病”字既代表肉体上的创痛,也暗指那场席卷祖国大地的政治风暴带给人们心灵上无以复加的深切痛苦。当得知周扬从监狱中放出来的消息时,他和郭小川等人立刻赶去看望。为了不被人发现,用的是假名。那天,周扬看见他们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说起在狱中,为了使鲁艺的同志不受牵连,为了防止络绎不绝的“外调者”发起突然袭击,他曾经一个个地努力回忆鲁艺的每一个人,竟然想起了二百多个人的名字……听到这里,冯牧和同去的人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
前言/序言
后记事实上,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从未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写下这样一些人物,如果早知如此,或许我会做更好的准备。
记得八十年代初,在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对我说:写一本日记吧,就把你每天所经历的如实记录下来……那时候,我正做着秘书工作,在繁杂的事务中应对无穷尽的问题,忙忙碌碌,带着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人特有的没心没肺,和我与生俱来的任性、随心所欲。很多年后,当我重温这段话,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给我的最好的建议。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她深知在那个风云多变万象更新的年代里,只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就是一部最好的纪实作品,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这样做。我也写日记,断断续续的,而且所记多半是个人的看法和情绪,发生在那些文坛“大人物”身上的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东西就在我的疏懒中被漏掉了。
然而,记忆是抹不掉的,尽管随着岁月的远去,我们早已远离了昔日文坛那些重要的人物;尽管斗转星移世事变迁许多人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但历史终归是历史,而这些人物,有时候他们会在寂静的夜晚,悄悄地走出来,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你是有着这样的不能不说的经历!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寻。
我遵守的第一位原则是真实,将叙述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基础上。同时,我又发现,讲述他们,单凭经历是远远不够的。以我那时候的年龄和阅历,个人的接触毕竟太有限,而他们是太复杂和太了不得的一群,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个人的记忆和角度或许都显狭小,我必须在写作的过程中为记忆和第一手材料补充历史背景,寻找佐证,也探寻那些未解的谜团……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工作:循着记忆的线索,补充大量材料,力图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当史料对他们的动机和行为保持沉默的时候,在诸多空白的地方我试图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推论……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新认识的过程,因而,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一个曾经亲历历史的人对昨天的探寻和研究。
如果说回忆是苦涩的,思考却充满着挑战的快意。每当我在回忆中重新走近他们,我就愈加清醒地看到,这些昔日文坛的“掌门人”——他们既是投身革命的一代,又是“五四”和民国文化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极其复杂,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断地卷入政治和艺术的矛盾漩涡,每一步充满艰辛的跋涉都代表着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曲折历程;他们个人的痛苦,也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蜕变和升华。他们是多元的,在分析他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追寻“唯一性“,而必须用开放和多元的目光审视历史,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引导我们走向误区。我便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张抗抗在读了《历史的碎片》之后曾写信来说:“你能够把何其芳那么一个‘复杂’又‘单纯’的人物,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与内心的矛盾,处理得特别合情合理,真的不容易。既写出了‘诗人毁坏’的历史因缘,也写出了‘好人好官’未泯的良知……那是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也可见作者的善意与温情。要害处轻轻点到,读者已心领神会;既为诗人的‘认真’惋惜,更为革命的严酷怵然……你把这一类人物的‘历史深度’表现出来了,犹如那个时代活生生立在眼前。”她阅读了我的每一篇文章,并在自己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中多次发来邮件与我讨论:“我一直在反思我们这代人那种‘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上一辈人的革命留给我们的负资产……所以对你描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特别在意、特别看重。你已经越过了那道门槛,‘恰到好处’其实就是对人和世界的认识。……”我赞同她的观点,却绝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真正的客观和“恰到好处”,因为认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老实说,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很难说都看懂了,真正地走入了他们的内心。
历史已经远去,但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却不会消失殆尽。走近他们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昔日的一切透过历史的尘埃显露出他们朴实坚韧的本色,我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他们永远在那里,在我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建筑起一面牢固的墙,让我抵御人生的艰难,让我在最孤独的时候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此书收入的文章都曾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整理时除了《我辈无文章》一文加入新发现的荒煤回复张光年的信之外,其余文章除个别文字均未做改动。感谢《收获》主编李小林,是她鼓励和督促我写下这些我们所共同熟悉的人物。我们常在电话里一起讨论,共同回忆,有时兴奋,有时感叹,有时迷茫,有时沉默……更重要的是她像一个“工头”似的钉在我身旁,在我疲惫的时候鼓励我坚持;在我沮丧的时候、想要偷懒和忽略什么的时候提醒我告诫我;她对文字的严格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对我的“作”、“做”不分之类的毛病不厌其烦的纠正、对发稿的时间也决不通融……有时候,我在电话中看到她的来电显示就会感到紧张,甚至想逃避……但当我走过这个过程,我深知她的付出,并发自内心的感动。
感谢《收获》钟红明、李筱在我发表专栏文章时付出的辛勤劳动,更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应红、郭娟和刘伟对出版这本书给予的大力支持。刘伟是我《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一书的责任编辑,再次合作,我感到非常愉快和欣慰。
走近历史是沉重的,但也同样令人愉快,希望此书能为每一位真诚地面对昨天和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收获,希望人们能够在他们的故事中思考并汲取力量……
2015年1月21日于北京
用户评价
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新中国文坛的变迁,也映照出时代变迁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她总能捕捉到那些最细微的情绪变化,最深刻的内心挣扎。我读到一些描写作家在困境中坚持创作的段落时,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也能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不屈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作者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她还在引领我们思考。她会提出一些问题,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去形成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阅读体验,它鼓励读者主动参与,而不是被动接受。我感觉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启发,一种对人生、对社会、对文学更深层次的理解。它让我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游戏,更是时代的记录,是人性的写照。
评分读完这本书,脑海里涌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沉静”。作者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它不像某些文章那样咄咄逼人,而是像一股涓涓细流,缓缓地渗透进你的内心。你不会感觉到被强迫去接受某种观点,而是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着去思考。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一些经典作品的解读,她没有简单地罗列人物关系或者情节梗概,而是深入剖析了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一些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她能从一个不起眼的词语,一段不起眼的对话中,挖掘出令人震撼的深意。读她的文字,就像是在和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对话,他睿智而平和,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着最深刻的道理。那种感觉,是一种涤荡心灵的宁静,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去感受文字的力量。我感觉自己仿佛也置身于那个年代,和作者一起,重新审视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学作品,发现了它们全新的生命力。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踏上了一段充满探索的旅程。作者以一种非常独到的视角,审视着新中国文坛的潮起潮落。她不回避那些复杂和矛盾,而是用一种坦诚的态度去面对。我尤其喜欢她对于某些“遗珠”的挖掘,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但却闪耀着光芒的作品和作家,在她笔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她的文字充满了人文关怀,她不仅仅是在分析文学作品,更是在关注那些创作出作品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困境,他们的梦想。这本书让我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我不再仅仅把它看作是文字的组合,而是看作是时代的回声,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是思想碰撞的火花。它让我看到了文学的韧性,以及它在塑造一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沙龙。作者的叙述非常流畅,她总能巧妙地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读她的书,我感觉自己就像坐在一个温暖的书房里,听着一位博学多才的朋友,娓娓道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她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梳理,对于一些文学思潮的演变,都写得非常清晰透彻,即使是对文学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能轻松理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评价某些作家的时候,既有肯定,也有保留,她的批评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基于深刻的理解和客观的分析,这种平衡感做得非常到位。她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本身,更是那个时代下的文人心路历程,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与创作的。这种立体化的呈现方式,让我对新中国文坛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很有味道,是那种淡淡的米白色,上面用一种略带沧桑感的书法体写着书名。拿在手里,纸张的质感也很好,不是那种光滑的铜版纸,而是略带磨砂的触感,让人感觉很踏实。我翻开第一页,里面的排版也很舒服,字号大小适中,行距也留得恰到好处,读起来一点都不会费眼睛。我还注意到,书的开头部分,作者引用了几句古代的诗词,虽然我不是文学专业出身,但那种意境和感觉一下子就抓住了我,让我觉得作者是个很有深度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本书里,作者会带我们走进怎样一个充满思索的文学世界。我特别喜欢封面上的那抹潮水的意象,隐隐约约间,似乎能听到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这会不会是作者在暗示,新中国文坛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潮起潮落,起伏不定,如同大海的呼吸一般?这种感觉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期待,仿佛已经置身于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和文学气息的空间。
评分京东买书服务不错实惠,下次继续!
评分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三十余万字、六十余幅珍贵照片,首度集中披露
评分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历史人物研究,在《收获》杂志主持专栏写作“遗失的青春记忆”、“潮起潮落”
评分据说很流行,买来看看,包装很好!
评分不错……
评分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三十余万字、六十余幅珍贵照片,首度集中披露
评分使用部门说质量非常好
评分不错
评分好书。不知道现在文化部的衙门里,有如此文笔,思想的秘书,还能有几个:)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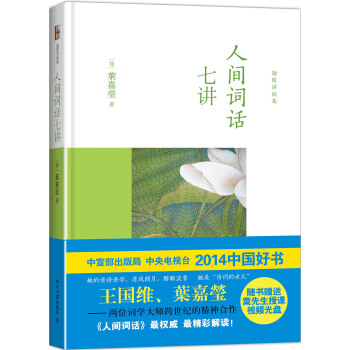

![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 [Tolstoy or Dostoevsky An Essay in the Old Critic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50012/286b4267-77c6-4a6c-be6e-15f02f191eb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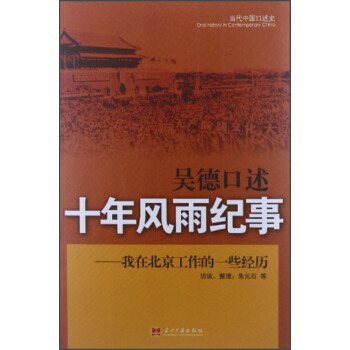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小熊温尼(第2版 青少年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93957/rBEhV1Iy6ysIAAAAAAkni-vJehwAADKsgK520YACSej278.jpg)

![商晓娜作品 王小天和他的伙伴们(套装共6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04876/54a39266N07a170a6.jpg)
![泰戈尔英文诗全集(中英双语读本 套装1-4册) [Collected Poem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51060/56c2ef94Ne2f8714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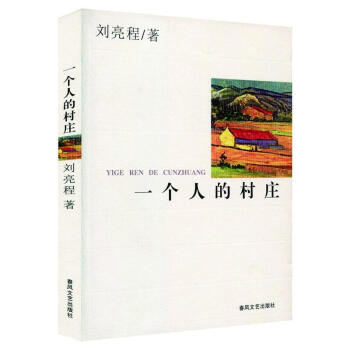

![故事奇想树:八卦森林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655763/53c6428eN2556564f.jpg)

![笨狼的故事:半小时爸爸(注音版)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41742/rBEQYFMvpi0IAAAAAAPIsw-Jqr4AADMTgNEit0AA8jL59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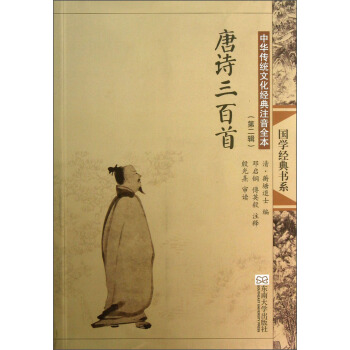


![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豺王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61899/rBEbRlN0dkwIAAAAAAQW4VY6mGAAABPjANwaGoABBb562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