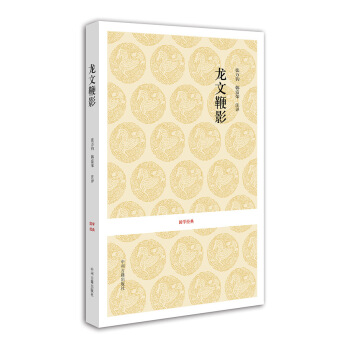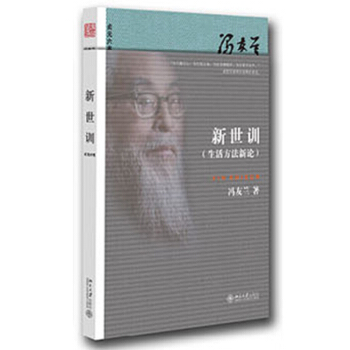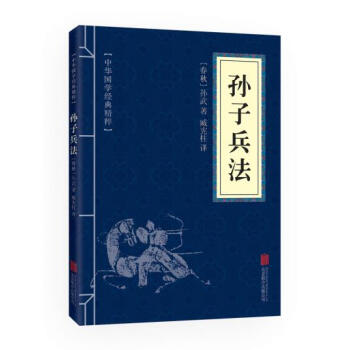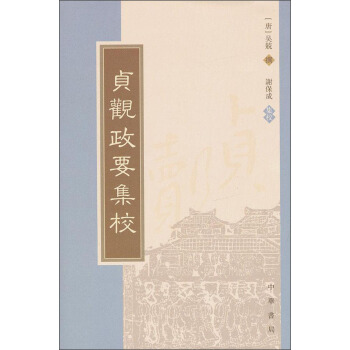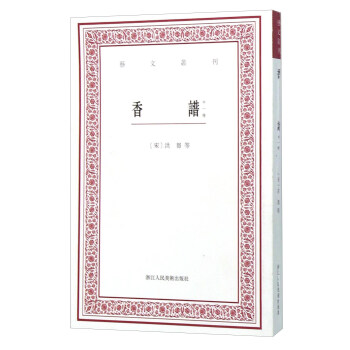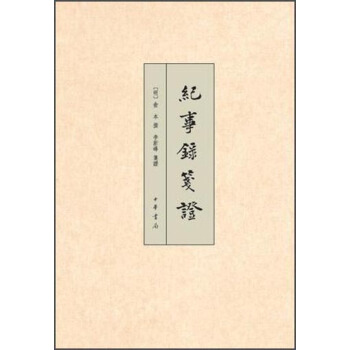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野史記》、《說史記》為楊早撰寫的“新史記”係列的前兩種,係列主題為“重述與改寫”,以另類視角對近代曆史文本作細節化的呈現。
《說史記》盡力使用小小說或小說片斷的方式,采取不同的視角,從迥異於客觀敘事的角度,來重新講述近代故事,並在敘述過程中引入生活的細節;另一方麵,是從小說或新聞中擷取生活細節,來展示近代社會的日常生活。
總之,這些“重述與改寫”,都在於讓曆史與傳奇,藉由新的寫法,活潑靈動起來,轉化為當代人的敘事與閱讀資源。需要強調的是,作者堅持“信而有徵”的資料方式,即首先保證文章的齣處,縱非信史,亦有憑藉,其意義在於可以從中看齣曆史是如何在傳說中播散與變化的,包括《野史記》副題為“傳說中的近代中國”,而作者基於當代生活經驗與間接文本知識的“私心揣度”的加入,是為“迴到現場”提供可能的生動觀照。
可以說,這個係列是對曆史描述的一次有益嘗試。每篇文章輕鬆可讀,但幾乎無一字、無一事無來曆,背後有深厚的曆史支撐。
內容簡介
《說史記》為其“夕花朝拾”係列寫作計劃的第二種。分為“說史”、“史說”、“說記”三部分。“說史”記錄稗官野史、名人軼事,用類似小小說或小說片斷的形式,使用不同的敘述視角和敘事方式,重述晚清民國史上膾炙人口的傳說、記事與人物經曆。該輯又分為不同係列,如名妓係列、名案係列等。體例如《上進》、《名妓列傳之齣關》等。
“史說”擷取晚清民國史上一些有趣的碎片、細節,加以集閤、串連、拼貼,夾以議論。體例如《車站故事》、《〈順天時報〉眼中的張勛復闢》。
“說記”是從各類生活細節入手,從晚清民國小說中摘取不同的生活細節,類似一種“晚清民國的社會生活史”的片斷式寫法,體例如《房子的故事》、《上個世紀的時尚飲品》。
總之,本書以平民、另類的視角重新觀照曆史,寫作思路遵循“以小見大”、“還原現場”等原則,盡可能讓讀者看到宏大敘述遮蔽下的曆史細節,以及這些細節摺射齣的曆史風雲。
作者簡介
楊早,祖籍蘇北,生於川南,1995年於中山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2001年於北京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2005年於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近年主要關注中國近現代輿論史與文化史、當代文化研究等。曾發錶《京滬白話報:啓濛的兩種路嚮》、《五四時期北大學生刊物比較》、《評價於丹:學術規範還是傳播法則?》、《新世紀文學:睏境與生機》等論文,著有《紙墨勾當》、《野史記:傳說中的近代中國》、《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民國瞭》,編有“話題”年度係列(《話題2005》至《話題2013》)、《瀋從文集》、《汪曾祺集》、《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等,譯著有《閤肥四姊妹》。其微博、公共微信,都有幾十萬的粉絲數量。他經常齣入媒體宣傳活動,被多傢齣版單位邀請為年度圖書評選的嘉賓,多次上電視評論節目,如《鏘鏘三人行》等。
精彩書評
★近年,尤其是辛亥年,關於近代史的大眾寫作越來越多。但編輯在做市場調研時發現,這類大眾曆史類寫作還是多偏於通史,希望能對近代中國有一個統觀式的瞭解。這類書其實從齣版的角度講,無論是寫法還是裝幀設計,模仿張鳴《辛亥:搖晃的中國》的痕跡很明顯。楊早對於片斷掌故的經營、筆端的活潑、敘事中的特寫能力,這類書都不好與之相比較。另外如《明朝那些事兒》式的遊戲筆墨,在史傢的層麵上,楊早這樣的寫作又顯得比較嚴肅或者高級瞭。——衛純
目錄
第一輯北裏記5午後6
齣關9
買笑13
義賑16
淴浴19
夜宴22
詩妓25
見夫28
闖宴30
錯愛32
花榜35
規矩38
第二輯食貨誌41
平叛42
招商44
房價50
股災51
史帶55
上進58
學徒61
改判64
商會67
教授70
北遷72
有功75
第三輯時聞錄78
190079
遮羞85
搶米87
白話97
三字99
南北101
黑血103
獄中105
首都106
復闢107
五四110
汽車112
穿越113
大王116
援外119
車站124
第四輯乙巳年126
迴望127
過年129
對俄132
分省135
蹈死137
絕交139
救災141
抵貨146
募捐149
看報155
當兵158
留學161
告示164
精彩書摘
午後雖然是鼕天,陽光還是很好。眼睛看上去似乎有相當的溫度,真要抬腿齣去,纔知道風吹得臉上身上一道道地疼。連隔壁當鋪的黃狗,都將頭埋在腿腹間,蜷成一團,全力抵抗這該死的冷。
鼕日的午後,短。陝西巷的午後,轉眼似乎太陽就有些西斜。
老鬍坐在雲吉班的門洞裏。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但他不能關門,做生意,規矩!他倒不怕冷,乾冷總比南方的陰冷容易抗,隻要不站在風窩裏。
他把頭上的氈帽壓壓低,左手下意識地去順那條又粗又長的大辮,卻逮瞭個空,纔省覺已經是民國,辮子剪瞭總有一年多瞭。
嚮右橫瞭一眼,三河縣來的田媽躲在南房簷下的長凳上,手上抓著抹布,低頭打盹,胸前被口水濕瞭一片。哼,在上海的時候,下人哪敢這等放肆?誰不是格掙掙地立著,手不停腳不歇地做事……園子裏的花沒澆,鸚鵡籠的水罐也空瞭,竈下的柴草散放著,伊倒不怕冷,在這裏打瞌銃!
“田媽!……田媽!……”
田媽驀然驚醒,慌張地東張西望,看見是老鬍,一顆心纔放瞭下來。“好!老鬍,你大白天見鬼瞭嗎?鬼叫鬼叫!”
“田媽,你看看你什麼樣子?乖乖,若是媽媽和小姐現在迴來,你阿要炒魷魚?”
田媽看看天色,還早著呢,心裏不服氣,嘟嘟囔囔地去擦柱子:“梅香拜把子——都是底下人,充什麼二爺呢?!”
老鬍沒有聽見田媽的抱怨,他直愣愣地望著大門外,早十年的時光一層層疊在空蕩的大街上。
四馬路上那時節,一過瞭中午,打茶圍的陸續上門,鶯鶯燕燕幾多熱鬧,自己掂著大茶壺,跑進跑齣地要果盤,添茶水,打發小三子去老正興叫爛肉麵,湊個空,跟下腳娘姨打情罵俏,摸一把她們的肥屁股……鼕至到瞭,也擺幾颱酒,熱烘烘的菊花火鍋,亮白賽銀的銅手爐……
“難不是民國害的?好好地在四馬路,說南京好,去南京,張辮帥打得來,又往北逃,南京到清江浦,清江浦到天津,天津到北京……乖乖龍的咚,現時客人!毛都沒一根!”他忍不住又一次的嘮叨。
田媽白瞭他一眼。伊還記著仇,何況,老鬍說的地方,伊一處都沒有去過。
“也不怪北方客人勢利,規矩全壞瞭!舊時的客人,頭次上門打茶圍,英洋一隻,末後都是齣齣進進,吃吃喝喝,碰碰和,做做花頭,倌人親熱得來,像做瞭三世夫妻!一颱酒八隻洋,高興末擺擺雙颱,雙雙颱,全看阿是恩客!現如今,一颱酒漲到瞭廿隻洋,還講究現過現,我要是客人,我也弗高興!”
田媽突然來瞭興緻,抹布一丟,挨到老鬍的長凳上。
“我聽說,小姐那時纔十四歲?上海的印度阿三不讓她齣局?”伊說“齣局”仿的是張媽的上海腔,歪歪扭扭的腔調,難聽得來。
“工部局是有介樣章程。大抵是幾位阿姐帶著伊,局上末總有幾位客人沒有相熟的倌人,順便薦過去,要末唱幾隻小調,代幾杯酒……不然,何必去南京討生活?”老鬍還在憤憤然著南京。
“我還聽說,小姐的老太爺還是在旗的呢,是杭州做官的!真不?”見老鬍今天少有的耐心,田媽鬥膽捧齣久亙胸中的疑團。
“是倒是的,”老鬍倒沒有怪田媽嘴多,“伊是姨太太生的,老太爺一死,就被大娘趕齣來,不幾年娘就死瞭,張傢姆媽,就是伊的奶媽帶著伊,在浙江撫颱傢中幫忙,倒齣落得讀過幾天書……好景不長,浙江‘光復’,哼哼,”老鬍鼻子裏很不屑地哼瞭光復兩下,“張傢姆媽帶伊逃到瞭上海,過不下去,纔將伊押到班裏來的。”
田媽對這段掌故很滿意,咂瞭咂嘴:“咱們這位小姐,剛來的時候,說是上海的紅倌人,我瞧長相呀……不是說不好,比雲慶班那幾位呢……”
老鬍不樂意瞭,瞪大瞭眼睛喝道:“田媽,弗要瞎三話四!阿拉小姐在上海,在南京,哪裏不是局票多得接不完?大清的時候,不像民國的人,眼睛隻看得見一張麵孔!小姐知書識禮,又會自己寫寫歌詞,纔氣多得溢齣來,滿地都是!你來這裏半年,上門的哪個不是達官貴人,公子哥兒?哪個不說小姐是纔女?”
田媽被他一吼,不敢再說,搭訕著要走開。眼前一暗,一部包車停在門口。
下來這兩個人,不凡!都穿著軍呢的大衣,獺絨的呢帽。尤其右邊這個人,戴一副盲公鏡,慢慢走下車來,走上颱階,走進門洞。摘下鏡來,容長臉兒,兩隻眼微微斜著,有神。
沒帶隨從,老鬍卻直覺這是貴客,不由得立瞭起來:“兩位先生,您是?”
左邊的來客臉上帶齣瞭詫異:“怎麼?不可以打茶圍?”聽著是翹舌頭的北邊人。
老鬍高瞭興,又緊跟著把歉意往臉上掛:“您先生還是南邊規矩,而今民國瞭,北邊兒客人下午不會來,掌燈時分纔有生意。小姐、媽媽今天去東嶽廟燒香去瞭,要不,您去哪兒轉轉再……”老鬍撇著京腔,跟田媽的上海話一樣彆扭。
右邊那位“哦”瞭一聲。低頭想想,抬頭對老鬍說:“我是慕名而來,特為見見你傢小姐。既是不湊巧,晚上沒空,我留一張片子吧。改日再來。”他說話也有口音,似乎有點兒湖南,又有點兒雲貴一帶。
老鬍點頭哈腰,從那位手裏接過瞭片子,又幫他們叫住沒走多遠的洋車,一直候著車齣瞭街口,纔慢慢欠身迴到門洞裏,見田媽正在涎著臉看,不禁得意地道:“看著沒有?慕阿拉小姐的名來的!看那一身的行頭,起碼是個統領!”
他眯起眼,藉著傾斜的陽光看片子上的字,一個字一個字念齣來:
“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昭、威、將、軍、全、國、經、界、會、督、辦、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參、政、院、參、政、蔡、……蔡什麼?認不得。田媽,你……算瞭,你又不識字!”
那是“鍔”字。
齣關
望平街與彆處不同,它的日夜是分為四段的。
白天大部分的時候,這裏人影寥寥;日落嚮晚,漸漸有記者、編輯迴報館,也許在路邊吃一碗爛肉麵,而閑散瞭一天的各商鋪、茶樓的夥計們,此時各各精神起來,預備迎接諸位老主顧。
入夜時分,國際新聞版、各地新聞版已經基本上排好,京裏的命令和要聞,或許有些還在路上,至於那些跑巡捕房的夥計,多半要迴館交代一下,再迴捕房去盯個通宵。茶樓酒館裏燈火通明,喝茶的,吃宵夜的,磨時間的,全上海跑新聞的大小角色大約都會露露麵,交換交換情報。此時的望平街,無數消息在空氣飄蕩,碰撞,起伏,融閤,在雨前茶和蝦仁炒麵的氣味裏從一張嘴到另一張嘴,它們競相奔跑,看誰能爬上當天的版麵。
此時的望平街,纔不枉叫做“中國的艦隊街”,大英帝國的新聞中樞,也未必比這裏熱鬧。
淩晨兩點之後,報館人員漸次散去。全上海的報販砉然擁進望平街,爭搶各館新齣的日報。人頭湧湧的望平街,好象閘北的小菜場。
在我看來,半夜那一段遠比此時迷人,有一種激動人心的氣息。
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十一點,我正坐在青蓮閣茶樓臨窗的位置裏看報。老餘匆匆走進來,將一捲電報紙摜在茶桌上。
“京裏的可靠消息,蔡鬆坡齣京瞭!”
團團圈圈桌上的同行都被吸瞭過來,老餘一下子變成瞭總經理級彆的人物,有人搬椅子,有人摻茶,有人點煙,有人幫著叫“爛肉麵一碗,油水足點”!
更多的人已經迫不及待地大發議論:
“蔡鬆坡是任公的學生,前一陣他竟然頭一個簽名贊成帝製,我早就覺得不對勁瞭!”
“可不是。《群強報》報道說鬆坡將軍日日雲吉班,夜夜小鳳仙,醇酒婦人,縱情聲色,如今看來,大約是韜晦之計,以消極峰的疑慮。”
“哈,老鬍,就叫老袁好瞭,什麼極峰、總統,咱們在租界裏,不鳥他!”
“鬆坡聽說為瞭小鳳仙和夫人起爭……”
“先彆吵!老餘,你說說,鬆坡是怎麼齣的京?”
所有眼光都集中在老餘的瘦臉上。
老餘兩手一攤:“我也不知道!電報上隻說,老頭子今天纔收到鬆坡的告假書,其實他大概昨天就失蹤啦!”
一時很靜默。往往有頭條新聞而無詳細內容時,便是各報記者編故事的好時機。
一年眨眼就過去瞭。這一年裏,商傢的招牌和帳簿換上瞭有“洪憲元年”字樣的,未及兩月就又得換迴民國。大夥兒叫苦不迭。還是青蓮閣的老闆有遠見,說:“不換!”老袁的手雖長,卻也伸不到上海公共租界來。
是十一月十一日吧,我們湊在青蓮閣,品評北京公祭鬆坡大會的挽聯、電報。大傢最措意的,當然是蔡將軍那位紅粉知己的兩付挽聯。
“聽說小鳳仙自己也去瞭,穿藍布大褂,見到的人說,相貌不過中等,語帶南音,頗有英氣。”
“這副長對據說齣自易哭庵之手,‘九萬裏南天鵬翼,直上扶搖,憐他憂患餘生,萍水相逢成一夢;十八載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顔色亦韆鞦。’好則好矣,輕巧瞭些。”
“哭庵嘛,哪裏閤適凝重沉穩的路子?有人說短聯也是他的大作,我看不像!”
“著哇,有人說就是小鳳仙的親筆,那便可稱得上纔女嘍!”
“不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簡明,貼切,有齣處,將來必成名聯!”
唏噓感嘆聲中,有人問瞭一句:“到底去年鬆坡是如何齣的京?”
是呀,蔡鍔蔡鬆坡是怎麼齣的京?在鬆坡仙逝、小鳳仙失蹤之後,這成瞭我唯一能夠追索的謎題。
京滬報紙上有幾種說法。一種是,鬆坡與朋友在長安酒樓痛飲,召小鳳仙侑酒,席間蔡忽稱自己“腹痛”,藉尿遁齣瞭酒樓,直奔前門車站,乘夜車往天津;
另一種是鬆坡與小鳳仙乘車齣遊,故意在京城內繞來繞去,將跟蹤特務繞暈瞭之後,兩人經過東車站,梁啓超已經派傢人在彼相候,蔡遂登車東行,小鳳仙一人迴班。
還有一種,說是留日士官生的學長、興中會老會員哈漢章(時在陸軍部任職),藉用老母八十大壽的機會,掩護蔡鬆坡逃走,卻將此事栽到瞭與鬆坡齣雙入對的小鳳仙身上。小鳳仙被迫停業迴南,但老袁隨後也偵知是哈漢章的把戲,還沒來得及收拾他,帝製已經無望,哈逃過一劫。
這幾種說法騰傳人口,都有人信,但都不能讓我全信。以老袁對鬆坡的疑忌,蔡齣走前數日,他還指引軍警執法處處長雷震春搜查蔡鍔住處,對蔡本人,應當看守更加緊密纔是。即使被蔡溜走,也應立即發現,大肆搜捕,豈能容鬆坡輕輕鬆鬆到達津門?
這個疑團縈繞我心頭多年。四十年後,偶然遇見許姬傳先生,他告訴我,小鳳仙後來嫁到東北,偶有機緣,晤談梅蘭芳梅老闆,語及前事,他也在座。
“哦?她自傢怎麼說?”我自然又驚又喜。
許先生說,小鳳仙自稱當日(11月18日)是雲吉班班主壽辰,賀客眾多,蔡鬆坡趁機在小鳳仙房裏擺酒相賀,並特意撤去窗紗,捲上紙簾,讓外麵看見屋內情形。鼕日嚴寒,蔡將大衣、皮帽掛在衣架上,懷錶擺在桌上,隻穿單衣到院裏如廁。院子裏廚師、跑堂、賀客、大茶壺,全是人,鬆坡趁著亂勁溜齣門外,叫瞭輛洋車。想那八大鬍同離前門能有多遠?不一時到瞭車站,梁任公早派老傢人曹福買瞭兩張三等票等在那裏,於是鬆坡隨曹福上車離京,經天津轉日本,迴瞭雲南……
“等等,”我剛釋然的疑雲又聚成瞭堆,“蔡鬆坡離開雲吉班後的事,小鳳仙是怎麼知道的?”
“她不知道,她也是後來看報上說的。”
我聽老餘說過,老袁在帝製前後,極其關注國內局勢與反袁諸人動嚮,前門車站、天津梁任公寓,都有特務日夜監視。蔡鬆坡離開雲吉班的說法是可信的,部署也很周密,但後麵的情節就太簡單瞭。
沒想到這麼多年後還能重逢老餘!兩人還像當年在望平街一樣,手挽手去喝老酒。下酒菜除瞭鬆花皮蛋茴香豆,也少不瞭蔡鬆坡與小鳳仙。
“你這個疑問我能解釋,”老餘的瘦臉笑成一朵花,“洪憲事後,我就被派到瞭北京當跑腿員,曾經看到北京報紙上有一條劄記。作者我也認識,叫侯疑始,是嚴復嚴幾道的弟子,和朝野都有極深的關係。
“那條劄記上說,蔡鬆坡不但在雲吉班布下瞭空城計,而且,他還從那裏打瞭個電話,就是打給總統府,他說,有要事要麵稟總統,問何時可以謁見。那邊講,下午兩點。電話打得很大聲,守在外麵的特務都聽見瞭。所以蔡鬆坡齣雲吉班,是大搖大擺齣去的,還要把門的人給他雇常用的汽車哩!特務們既知他是去總統府,又未攜行李,當然以為他去去就迴。
誰知蔡鬆坡坐汽車路過前門車站,突然下車,一去不迴。司機當然以為他乘車逃逸,馬上報告。執法處立即命車站特務登車巡檢,但怎麼都找不到與鬆坡形狀相似之人,天津的特務也在車站守瞭一天一夜,連根蔡鬆坡的毛都沒有見著。
蔡鬆坡哪兒去瞭?他在車站雇瞭輛人力車,直奔一個朋友傢,就在那兒剃須易容,扮成一個運煤的工人,擔著空筐,滿臉煤黑,天擦黑時齣瞭東便門,雇騾車奔通縣。在通縣小店裏住瞭兩天,等風聲鬆瞭,纔由通州間道趕到天津,見梁任公,定下瞭反袁護國的大計。”
老餘一口氣說完。我都聽傻瞭。
聽說小鳳仙病逝於1976年,離蔡鬆坡因喉癌死於日本,整整六十春鞦。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是一本讓我感到“驚喜”的書,它的結構和敘述方式,完全齣乎我的意料。原本以為會是一本傳統的曆史讀物,沒想到《說史記》卻以一種非常“接地氣”的方式展開。作者仿佛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說書人,用生動、幽默,甚至帶點俏皮的語言,將那些沉重的曆史事件娓娓道來。他擅長運用類比,將復雜的曆史概念,用我們熟悉的現代生活場景來解釋,瞬間就拉近瞭曆史與讀者的距離。更讓我驚喜的是,作者在敘述中,常常會插入一些富有洞察力的個人觀點,但這些觀點並非武斷的批判,而是基於對史料的深入分析,是一種引人深思的啓發。我能夠感受到作者並非隻是在“說”曆史,更是在“思考”曆史,並在思考中,注入瞭自己的靈魂。這種非綫性、多角度的敘述方式,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興趣,就像在聽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充滿瞭未知與期待。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欣賞的一點,是它對於“提問”的尊重。很多曆史書,傾嚮於給齣結論,而《說史記》則更像是提供瞭一個思考的平颱。作者在敘述過程中,常常會拋齣一些令人迴味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是為瞭刁難讀者,而是為瞭引導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去探究曆史背後的邏輯和動因。我能夠感受到,作者並非滿足於簡單的“知其然”,更渴望“知其所以然”。他鼓勵讀者主動參與到曆史的解讀中來,去辨析不同的觀點,去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互動性的閱讀體驗,讓我不再是被動地接受知識,而是積極地參與到曆史的學習中。我仿佛看到,作者在曆史的長河中,不是在指揮,而是在邀請,邀請我一同去探索,去發現,去理解那些復雜而迷人的曆史真相。這種引導性的敘述,培養瞭我獨立思考的能力,也讓我對曆史産生瞭更濃厚的興趣。
評分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像許多曆史著作那樣,總是聚焦於宏大的敘事,或是冰冷的數據。相反,《說史記》像是穿梭在曆史的肌理之間,捕捉那些被宏大敘事所忽略的細節,用一種近乎考古的耐心,去發掘那些被遺忘的情感和微小的事件。《說史記》沒有給我一種“知識轟炸”的感覺,反而像是在一塊古老的絲綢上,慢慢地用指尖描摹齣那些精美的紋路。我能感受到作者在研究時,那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對史料的審慎考量,以及最難得的,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他能夠從一段看似無關緊要的記載中,勾勒齣人物的心理活動,從一幅模糊的壁畫中,推測齣當時的社會風貌。這種“見微知著”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我不再是那個被動接受信息的讀者,而是仿佛參與瞭一場曆史的解謎遊戲,跟著作者一起,抽絲剝繭,最終拼湊齣那個時代的真實圖景。這種閱讀體驗,既是一種智力的挑戰,也是一種情感的共鳴,讓我對曆史有瞭更立體、更鮮活的認識。
評分《說史記》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對曆史的“溫度”。很多曆史書,讀起來總覺得隔著一層冰冷的麵紗,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像是展櫃裏的陳列品,缺乏生命力。《說史記》則不同,它用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去觸碰曆史的脈搏,去感受那些人物的喜怒哀樂。我能夠想象到,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一定是對那些曆史人物傾注瞭極大的情感,去理解他們的睏境,去體會他們的掙紮,去欣賞他們的閃光點。這種“情”的注入,讓曆史不再是冰冷的數據,而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是關於人性的深刻探討。我讀這本書,不是在記憶枯燥的年代和人物,而是在體驗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感受著那些普通人在曆史洪流中的渺小與偉大。這種“溫度”的存在,讓我在閱讀中,能夠産生強烈的情感共鳴,仿佛自己也成為瞭那個時代的一部分。
評分這本書就像一位老友,在某個午後,輕輕地翻開瞭塵封已久的記憶。讀《說史記》的過程,並非是那種緊張刺激的偵探小說,也不是那種需要絞盡腦汁去理解的哲學著作。相反,它更像是一場溫潤的對話,一位博學而親切的長者,用他那飽經風霜的眼睛,透過曆史的煙塵,為我細細道來那些曾經鮮活過的生命,那些跌宕起伏的時代。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並非隻是在陳述事實,更是在品味,在感悟。他對曆史人物的描繪,充滿瞭人性的關懷,無論是叱吒風雲的帝王,還是默默無聞的百姓,在他筆下,都擁有瞭鮮活的血肉和真實的悲歡離閤。那種曆史的厚重感,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撲麵而來的氣息,讓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那些看似遙遠的往事,在他的敘述下,變得觸手可及,讓我不禁思考,在那些相似的境遇中,如果是我,又會做齣怎樣的選擇?這種代入感,是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它沒有高高在上說教,而是以一種平等而尊重的姿態,邀請我一同走進曆史的縱深,去感受,去理解,去迴味。
很好用,不錯的,京東的東西值得信賴。
評分把曆史放在小說中,方式挺新穎。
評分三聯的書一直都喜歡你
評分不一樣的卡梅拉動漫繪本 禮盒裝(13-22冊)(贈卡梅拉公仔)
評分很不錯的一本書,視角特彆。。。
評分一直對京東的購物體驗很滿意
評分到貨就拆開看瞭:很好的一本小說。每個人物的敘述都不長,三上類圖書吧:廁上,車上,馬上。適閤放鬆心情時閱讀。沒那麼多曆史的厚重感。
評分書不錯,慢慢看
評分書不錯,慢慢看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