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爱伦·坡奖年度最佳小说
影响整整一代欧美作家的活传奇——詹姆斯·李·伯克代表作
内容简介
——“戴夫,你的脸怎么是湿的?”
——“我刚才洗脸了,小家伙。”
戴夫·罗比乔克斯是一名前缉毒警,妻子被害后,他和养女相依为命。
——“我就知道你会来。有些人永远不会变。”
布鲁斯歌手迪克西发现石油公司在印第安人保留区杀人征地。随之而来的离奇爆炸案让迪克西险些丧命,他向老友戴夫求助。
——“罗比乔克斯先生,他们找到了有你指纹的折刀。”
戴夫接手此案,小女儿却遭到死亡威胁,自己也成了一桩谋杀案的最大嫌疑人。
——“我敢打赌,现在蒙大拿的雪还没化,我想咱们俩最好去看看,小家伙。”
他带着女儿来到北方的印第安人保留区,结识了同在调查此案的印第安女孩达莲娜。
——“达莲娜……见鬼,老兄。她死了。”
——“那个人要杀死你之前和之后的照片,所以我给你拍了照。”
达莲娜死了,戴夫也落入职业杀手的圈套。一向秉持的正义感似乎将他拉入了绝望的深渊……
作者简介
詹姆斯·李·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李·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一九六○年,伯克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面天堂》。《纽约时报》书评版为伯克的处女作发表了头条评论,评论家将其与纪德、福克纳、海明威、萨特以及哈代等人相比较。一举成名后,伯克的新作屡遭拒绝,《失而复得的布基》出版前被出版社拒绝了一百一十一次。此书后来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提名。在等待出版的九年中,伯克饱受酗酒带来的精神和健康问题的折磨。为了养家糊口,他做过石油公司工程师、记者、社工、大学英语教授。最后,詹姆斯·李·伯克转而创作侦探小说,推出了“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该系列作品占据了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榜首,售出多部电影改编版权。
詹姆斯·李·伯克曾两次获得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这一成就在该奖项的历史上极为罕见。伯克的作品如同一部美国南部编年史,记录了被种族主义和贫富差距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南方社会。他关注现代工业对传统和自然的影响,崇尚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擅长心理描写,这些特点为他在评论界赢得了“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的美名。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侦探小说家之一,詹姆斯·李·伯克影响了一代作家,其中包括约翰·康奈利、彼得·梅尔等。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有相似的看法,即:其中的神圣之处并非来自作家本人,因而他们都怀有谦卑之心。他将自己的才华视为天赐的礼物,而写作仅仅是“为答谢这份礼物而做的回报”。
二○○九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授予詹姆斯·李·伯克大师头衔。伯克目前住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和路易斯安那的新伊比利亚,他和来自中国的妻子结婚五十七年,育有四个子女。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怀旧黑色小说领域的重量级冠军。
——《纽约时报》
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专注于回归传统价值的主题——父爱,友情,英雄主义,他的故事总能触及人性深处的悲伤、失落、恐惧、愤怒、仇恨。
——《出版人周刊》
充满诗意的冷硬风格迎面袭来,令人猝不及防。
——《华尔街日报》
精彩书摘
我驾车穿过圣马丁维尔,回到新伊伯利亚。太阳已经爬上了河边的树顶,朦胧的晨光中,湿漉漉的树林里依然弥漫着团团薄雾。现在刚到三月,和往常一样,经过了二月漫长阴暗的雨季,春的气息已经涌入南路易斯安那。新伊伯利亚的东大街上,所有的院子里都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娇艳的芙蓉,格架和凉亭上爬满了牵牛花和一簇簇紫藤萝。我驾着车轰隆隆地驶过吊桥,开上了小镇南边沿河的土路,我在那儿的钓鱼码头经营一个鱼饵店,那里还有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用柏树和橡树造的一幢老房子,现在我和一个六岁的萨尔瓦多小难民一起住在这幢房子里,她的名字叫阿拉菲尔。
房子的木头没有刷漆,颜色暗沉,坚硬如铁。屋顶的横梁凿出凹槽,挂上了钩子。前院里的山核桃树高大茂盛,树叶上的雨水滴下来,敲打着走廊的铁棚顶叮咚作响。院子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暗绿色枝叶覆盖。替我照顾阿拉菲尔的老妇人正在侧院里,忙着扯下兔子笼上的挡雨布。她叫克拉瑞斯,是个混血儿,古铜色的皮肤,蓝绿色的眼睛,南路易斯安那很多法国血统的黑人都有这样的特征。她经常吸鼻烟和手卷烟,皮肤上布满皱纹,四肢像树枝一样干瘦。虽然在家里总把我使唤得团团转,但是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勤快。从我儿时起,她就对我们家忠心耿耿。
现在,阳光洒满了我的码头,另一个为我工作的黑人——巴提斯特——正在帮两个白人往船上搬冰柜。他光着上身,冰柜压得他肩膀和宽阔的后背上的肌肉高高隆起。他能徒手拍灭烧烤火堆的余烬。我还见过他拽住一条六英尺长鳄鱼的尾巴,把它猛地拖出水面,甩到岸上。
我绕过院子里的水坑,来到走廊里。
“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只浣熊?”克拉瑞斯问我。
我的浣熊只有三条腿,大家叫它“三脚架”。它平时拴着链子,链子一端绑在一条金属晾衣绳上,这样它就可以在侧院里跳上跳下。现在,克拉瑞斯拎着链子把它提到空中,它拼命扭动挣扎,像被吊在绞刑架上一样。
“克拉瑞斯,住手。”
“我真想砍了它,你看它都干了些啥。”她说,“你过来瞅瞅我的洗衣篮,来瞅瞅你的衣服,昨天还是蓝色的,现在变成棕色的了!你自己过来闻闻这味儿。”
“我马上就把它带到码头去。”
“告诉巴提斯特,别再把它带回来了。”她把勒得半死的三脚架丢在地上,“它要是再敢到我房间来,你就等着吃浣熊肉配红薯吧。”
我把三脚架的链子从晾衣绳上解开,牵着它走到码头上的鱼饵店和小餐馆。我一度对白人至上的思想在南方的影响力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我家,发号施令和实际操纵的明明都是有色人种。
巴提斯特和我一起把前一晚暴雨留下的积水从船舱里舀出去,给自动售货机装满香烟和糖果,用网把鱼饵舱里死掉的小鱼捞出来,接着给冰柜排水,再把新鲜的冰块放在苏打水和啤酒上面,然后生火为中午回来的渔民准备午饭。最后,我张开大太阳伞,插在桌子中间的孔里,所谓的桌子是一些巨大的木制电缆线轴,所以中间有个圆孔。做完这些,我就转身回家了。
雨过天晴,景色非常漂亮。天空湛蓝,田野里的草被雨滋润得碧绿如新,走廊里凉风习习,后院里浓荫密布。我的红木花箱上滴着水珠,里面是茂盛的牵牛花和火焰草。阿拉菲尔穿着睡裤趴在厨房桌子上,在往我前天给她买的米老鼠画册上涂色。她的黑发剪成平平的齐刘海儿,棕色的大眼睛明亮动人,圆圆的脸蛋仿若烤派的盘子,皮肤晒成漂亮的小麦色。如果硬要给她的长相找出缺点的话,那就是她的门牙缝有点儿宽,这让她在笑的时候嘴更大了。很难相信,一年前在墨西哥湾,当我把她从失事飞机里拉出来的时候,她还像鸟一样轻,嘴巴喘息着,看起来就像我妻子裙兜里垂死挣扎的鱼。
我用手轻轻梳理她柔软的黑发。
“过得怎么样,小家伙?”我说。
“你去哪儿了,戴夫?”
“我被暴风雨耽搁了,只能待在巴吞鲁日。”
“哦。”
她继续涂颜色。然后停下来,冲我咧开嘴笑了,满脸开心。
“三脚架在克拉瑞斯的篮子里拉了。”她说。
“我听说了。听着,不要说‘拉’,要说‘它排泄了’。”
“不能说拉?”
“是的,要说它排泄了。”
她跟着我重复这个词,我们俩的头一起一点一点的。
她在新伊伯利亚的教会学校读一年级。不过,她从克拉瑞斯和巴提斯特夫妇那儿学来的英语,比跟我和修女学到的标准英语还多。你每天都能从他们三个嘴里听到这几句话:“什么钟点啦?”“你干啥在我的窗户底下烧叶子,啊?”“我上次开你的卡车,有人往轮子下面扔钉子,胎给爆了。”
我拥抱了阿拉菲尔,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回卧室洗澡。窗外吹来的风夹杂着潮湿泥土和树木的气味,以及花丛中紫茉莉的淡淡幽香。这春天的早晨本应让我精力充沛,我却感到无精打采,筋疲力尽,不仅是因为前一夜的噩梦和失眠。这种感觉不知何时就会猛然向我袭来,让我觉得心脏里的血都凝固了。突然间,我脑中就会浮现那些画面,耳中尽是可怕的声音,让我无力抵抗。
这种现象随时会发生。现在,就在卧室里,这种感觉又出现了。我已经换了好几面墙板,把弹孔一个个修补好——先用细木屑填满,再用砂纸磨光。原本碎裂的床头板上血迹斑斑,像画笔甩上去的褐色斑点。现在,这些床板都被撂在房子一角老仓库的角落里。但是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看到黑夜中子弹迸射,火花四溅,听见可怕的枪声如同雷电般炸响,听见她蜷缩在被单下,试图保护自己时发出的尖叫。我从暴雨中疯狂地朝屋子冲去,绝望的吼叫声淹没在滚滚雷鸣中。
每当这种黑暗的梦魇在白天袭来,总是让我无法挣脱。于是,我穿上运动裤和球鞋去后院练举重。我用一根九十磅的杠铃练习提举、曲臂举、坐举,十个一组,一共做六组。然后沿着河边的土路跑上四英里。阳光像烟雾一般穿过茂密的橡树和柏树叶,在我头顶旋转。鱼儿在树叶间捕捉昆虫,在两片树荫相交的地方,我有时能看到大嘴黑鲈在水下翻滚。
我跑到吊桥再折返回去,转身时向看桥的人挥挥手,回家时精神振奋。我的气色很好,血液在胸膛里奔流,腹部平坦而结实。但是,我不知道,对于死亡和痛苦的记忆,还能抵挡多久。
我是个赌马的赌徒,总是试图凭直觉掌控未来,但除了死死地盯着赔率表,我无能为力。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很少看到一部作品能将“宿命感”描绘得如此厚重而又富有诗意。它似乎在低语着,有些结局是写在羊皮卷上的,无论如何挣扎,也无法逃脱既定的轨迹。然而,这种宿命论并非让人感到绝望,反而是从中提炼出一种壮烈的悲剧美。作者没有采用常见的戏剧化爆发来推动高潮,而是让一切都以一种缓慢、不可逆转的姿态发生,就像冰川融化,虽然过程缓慢,但结果的不可抗拒性令人心碎。书籍中多次出现的意象——比如一座被雾气常年笼罩的灯塔,或者一艘永远无法靠岸的船——都强化了这种“徒劳的抗争”的主题。它以一种近乎古典悲剧的庄严感,探讨了个人意志在庞大历史洪流面前的渺小与伟大。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简直像夏日午后忽然降下的暴雨,措手不及却又酣畅淋漓。作者在构建人物群像时,展现出惊人的洞察力,每一个配角都有着自己的纹理和重量,绝非推动情节的工具人。特别是那位总是坐在街角咖啡馆,只点黑咖啡的老妇人,她的每一次凝视都似乎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兴衰。我特别欣赏作者对环境描写的细致入微,那些老旧的石板路、弥漫着潮湿气息的地下室,乃至光线如何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切割出几何图形,都成了烘托人物内心挣扎的有力道具。情节推进中,那些微妙的、未言明的张力,比直接的冲突更令人窒息。它不是那种开门见山的故事,更像是一幅精美的、需要你驻足细品的油画,每一笔色彩的堆叠都服务于整体的情绪基调。读到中段时,我感觉自己完全被吸入了那个特定的时空,呼吸都跟着书中的人物慢了下来,那种沉浸感是近年来少有的体验。
评分故事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它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法,像打碎的镜子一样,将时间线和人物视角不断地跳跃、重组。起初我有些混乱,需要不断在脑海中梳理“这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角色和上一个场景有什么关联?”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这种碎片化的信息开始拼凑出一幅宏大的、令人震撼的画面。这种“拼图”式的阅读体验,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感和探索欲。它要求你主动去连接那些看似无关的点,去挖掘字里行间隐藏的因果链条。尤其是在最后三分之一处,当所有线索如同水银泻地般汇聚时,那种豁然开朗的震撼感是无与伦比的。这种高难度的结构,恰恰证明了作者对叙事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掌控力,完全不是新手能够驾驭的水平。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具挑战性,它不是为了迎合大众阅读习惯而存在的。作者似乎痴迷于使用一些非常古典、甚至略显晦涩的词汇和复杂的长句结构,初读时会让人感到吃力,需要反复回味才能捕捉到那层深意。但一旦适应了这种独特的韵律,你会发现其中蕴藏着一种近乎音乐般的美感。它不是那种直白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精妙的意象转换和隐喻,将复杂的情绪层层剥开。比如,对“遗忘”的描绘,他没有直接说“人们忘记了”,而是写道“记忆的碎片像被海水冲刷的贝壳,光滑而空洞地躺在时间的沙滩上”。这种文学性的锤炼,使得整本书的格调瞬间拔高,它更像是一部文学实验品,而非传统的商业小说。对于追求文字功底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盛宴,但恐怕会劝退那些只求轻松阅读的读者。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它对“道德模糊地带”的探讨。这里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局限和痛苦中做出了挣扎的选择。作者极其克制地展示了冲突的根源,从不进行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让你站在每一个角色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做出那些“错误”决定的必然性。特别是关于“背叛”主题的处理,它不是简单的黑白对立,而是探讨了忠诚与自我救赎之间的永恒拉扯。我至今还在思考,如果我处于那种极端的情境下,是否能做出比书中人物更光彩的选择。这种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普通的故事讲述,上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它让你在合上书本后,依然久久不能释怀,关于“选择的代价”这个问题。
评分22. 侦探采用福尔摩斯式调查进行线索搜集和解谜。即先搜索后假设(含法庭派的“已搜索再假设”),证据足够再去怀疑:先搜集大量物证人证,再从已有证据出发确定调查方向,继而确定嫌疑人,一旦确定,立即逮捕定罪(因为证据前面都基本找齐了)。——24
评分每当这种黑暗的梦魇在白天袭来,总是让我无法挣脱。于是,我穿上运动裤和球鞋去后院练举重。我用一根九十磅的杠铃练习提举、曲臂举、坐举,十个一组,一共做六组。然后沿着河边的土路跑上四英里。阳光像烟雾一般穿过茂密的橡树和柏树叶,在我头顶旋转。鱼儿在树叶间捕捉昆虫,在两片树荫相交的地方,我有时能看到大嘴黑鲈在水下翻滚。
评分艰难的复仇之路,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这是犯罪小说中的福克纳。
评分——“达莲娜……见鬼,老兄。她死了。”
评分达尔文的发现颠覆了人类以往的自满与自信,其震撼力非其他科学革命所能比拟。稍可相提并论的,是哥白尼及伽利略。这两人将人类从宇宙中心的地位,贬到一个环绕太阳的小小周边物体上。但天体的重新排列只粉碎了我们的不动产美梦,达尔文进化论革命的对象,却是人的意义及本质(限于科学可以讨论的范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和其他的生物关系如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进化论取代了过往令人心安的自然神学解释:一位慈爱的神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让人主宰整个地球与所有生物,而整个地球的历史,除了头五天之外,都很荣幸地有人类参与。进化论却指出生命之树巨大茂密,所有枝丫皆一脉相承,彼此相连,而人类只代表其中一小枝;而且“智人”(H·m· sapiens)这一小枝,出现的时间就地质学而言,仿佛昨日;我们繁盛的时段对浩瀚宇宙来说,不过一瞬。(智人只存在10万年左右,整个人类谱系和我们现生血缘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分支的时间,距今也不过600万到800万年而已。相对的,地球上最古老的细菌化石却有36亿年的历史。) 如果我们能信奉某种和旧信仰--如人类之必要性及先天优越地位--不相抵触的进化理论,上述事实所造成的冲击或许还不至于这么大。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进化论暗示进化的方向可以预测,且循序渐进,所以即使人类起源得晚,仍可视为进化的必然结果及登峰造极之作。但根据我们对进化运作的了解--即关于进化机制最为人所接受的“理论”,而非上一节所提及的简单“事实”--却发现就连这种观念上的自满都是假象。有真凭实据亦最受肯定的达尔文自然选择说,便完全不支持这类相信人类在宇宙中之必要性及重要性的传统冀望。
评分——“达莲娜……见鬼,老兄。她死了。”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一次买了很多,这本是侦探悬疑的,还没有看,期待
评分詹姆斯 李 伯克一九三六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九六○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伯克的表兄,安德烈 杜布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为了同表兄一较高下,詹姆斯 李 伯克在十九岁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一次买了很多,这本是侦探悬疑的,还没有看,期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城堡 [Kafka Das Schlos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7511/56e928cfN366e772a.jpg)


![副本 [The Ahered Carb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41565/5948e14fN04c49af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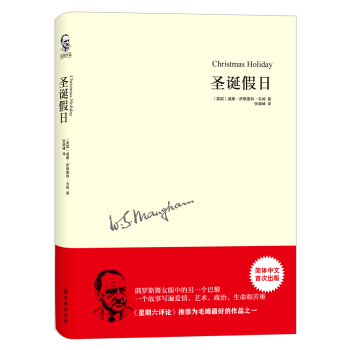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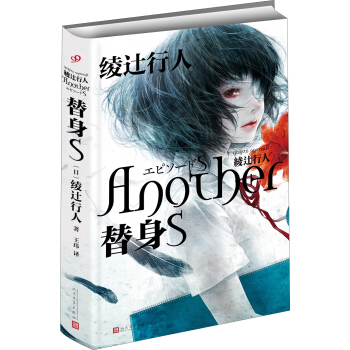
![骷髅方丈 [髑髏検校]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80194/560b41daN0b232bb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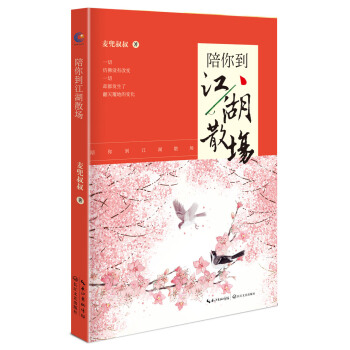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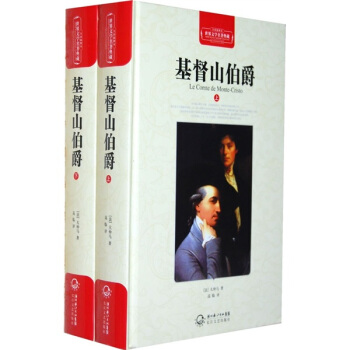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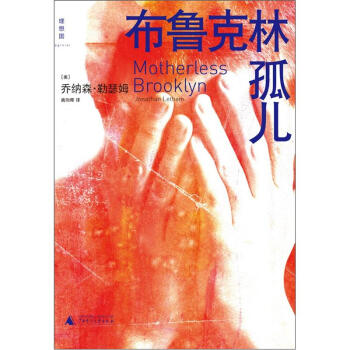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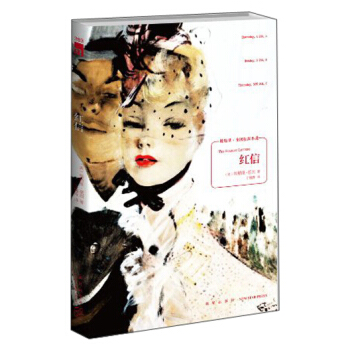
![召唤死者 [Call For The Dea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9821/53ce2092Nc44f1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