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米格尔街 [Miguel Street]](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64958/rBEhU1JwWKgIAAAAABJ9tmaEKP4AAEwRgNAyKQAEn3O631.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
米格尔街和米格尔街上人,都像盐一样平凡,像盐一样珍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成名作,获毛姆文学奖
《米格尔街》糅合了契诃夫式的幽默和特立尼达岛居民即兴编唱的小调,确立了奈保尔作为幽默家和街头生活作家的地位。
——诺贝尔奖授奖辞
内容简介
《米格尔街》是中国读者熟悉的诺奖得主奈保尔的作品。由十七个平行展开的短篇小说精心编织而成,各篇小说相对独立,但小说与小说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穿插,形成在纵横两个维度彼此交互的结构。
米格尔街生活着一群有脾气、有盼头的小人物:“哲学家”波普,要做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艺术家”摩根,扬言美国国王会来买他的花炮;“诗人”布莱克?华兹华斯,在写一首全世界伟大的诗;“疯子”曼曼,频频参加议员竞选;“机械天才”巴库,百折不挠地改造一辆辆进口汽车……
他们兴高采烈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作者简介
V.S.奈保尔(V.S.Naipaul),英国知名作家。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
5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米格尔街》、《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自由国度》、《河湾》、“印度三部曲”、《非洲的假面剧》等。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V.S.奈保尔将深具洞察力的叙述和不受世俗侵蚀的探索融为一体,迫使我们去发现被压抑历史的真实存在。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那些被遗忘的人。
——奈保尔
他童年的街头生活为他定下了基调。
——诺奖评委会
目录
鲍嘉没有名字的东西
乔治和他的粉红房子
职业选择
曼曼
B.华兹华斯
懦夫
花炮师
精彩书摘
鲍嘉每天早上,哈特起床后,总要坐到屋后阳台的栏杆上,扯大嗓门朝对面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鲍嘉总会在床上翻个身,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咕哝道:“有什么事吗,哈特?”
大伙儿为什么叫他鲍嘉可是个谜;不过,我猜一定是哈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电影《卡萨布兰卡》上映的那年。就是那年,鲍嘉的名字红遍了整个西班牙港,小伙子们纷纷开始仿效鲍嘉那种冷硬的姿态。
人们在叫他鲍嘉以前叫他佩兴斯,因为他从早到晚总在玩那种游戏。但其实,他并不喜欢打牌。
你不论什么时候走进鲍嘉的小屋,都会发现他坐在床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七行纸牌。
“伙计,有什么事吗?”若有人来,他总是这么轻声招呼一句,然后就不说话了,一沉默就是十或十五分钟。你会觉得真要和鲍嘉说点什么几乎不可能,他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傲气十足。他眼睛很小,总是睡意蒙咙,脸很胖,头发黝黑发亮,手臂圆润丰满。可他并不滑稽。他做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即使洗牌时舔一下大拇指的动作也十分优雅。
他是我见过的最百无聊赖的人。
他假装要开缝纫店谋生,甚至还付钱让我为他写个招牌:
本店专事裁缝
定做各种西服
价格低廉公道
他买了台缝纫机和一些蓝、白、棕色的粉笔。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能和什么人竞争;而且印象中,他连一件西服也没做过。他有点像隔壁的那个木匠波普,波普就从未做过一件像样的家具,可整天总是计划呀,刨呀凿呀,做着我想被他称作榫头的东西。每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在做什么呀?”他总是回答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鲍嘉倒好,连这点作为也没有。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鲍嘉是怎么挣钱的。那时,我总以为人长大了自然就会有钱。波普有个干各种活计的老婆,而且她最终成了许多男人的朋友。我简直想不出鲍嘉会有母亲或者父亲,他也从不往他的小屋带女人。他住的那间小屋叫仆人房,但里面从没有什么伺候那栋主屋住户的人住过。不过是建筑上的设计罢了。
像鲍嘉这样的人居然也会交朋友,在我看来可真是奇迹。但他确实有许多朋友;有一阵他还算得上是我们街最受欢迎的人呢。过去我常见他蹲在人行道上,身边围着的都是这条街上的大人物。连哈特、爱德华和埃多斯这样的人说话时,他也总是眼皮朝下,手指在地上画圈圈。他笑时从来不出声,也从不讲什么故事,但每逢聚会,大家总要说:“我们得请鲍嘉来。那家伙鬼着呢。”我猜,鲍嘉一定给了他们很多安慰和快乐。
不然哈特怎么会像我刚才说的,每天早上都要扯着嗓门喊:“有什么事吗,鲍嘉?”
不然他怎么有耐心天天去等鲍嘉那句模糊不清的回应:“有什么事吗,哈特?”
但有天早上,哈特喊过之后,没人回应。过去那种似乎不可改变的东西消失了。
鲍嘉不见了。他走了,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我们。
整整两天,街上的伙计们都闷闷不乐的。大家聚在鲍嘉的小屋里。哈特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副纸牌,又若有所思地将它们两三张两三张地抛落下来。
哈特说:“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去了委内瑞拉?”
但没人知道。鲍嘉很少对他们吐露什么。
第二天早上,哈特起床后,点了一支烟,走到屋后的阳台上,刚要张口喊,突然想起鲍嘉离开了。那天早晨他给牛挤奶的时间比平时要早,牛很不高兴。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鲍嘉还是没有回来。哈特和朋友们索性将鲍嘉的房间当成了俱乐部。他们在那儿打牌、喝朗姆酒、抽烟,有时还把偶遇的女人带过去。没过多久,哈特就因聚众斗殴、赌博遭到警方的关顾,他得花一大笔钱贿赂才能把自己从麻烦中解救出来。
就好像鲍嘉从没来过米格尔街一样。毕竟,他在这条街上只住了四年左右。他刚来时只带了只手提箱,想找个住处,哈特正蹲在家门口,一面抽烟,一面读着晚报上有关板球积分的报道,鲍嘉就问了问他。即使是那会儿他的话也不多。据哈特讲,他当时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哪儿有房子?”哈特把他领到隔壁的院子里,就是这问带家具的仆人房间,每月租金八元。他立刻在那儿安置下来,然后取出一沓纸牌,独自玩起“佩兴斯”来。
哈特对此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他一直神神秘秘的。他成了“佩兴斯”。
等到哈特和其他人已经或快要把鲍嘉忘了的时候,他却回来了。他是在某天早晨七点左右回到家的,进门后发现埃多斯和一个女人在他床上。那女人尖叫着跳了起来。埃多斯也跳起来,但并不害怕,只是很尴尬。
鲍嘉说:“走开!我累了,想睡觉。”
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五点钟,醒来时发现屋里挤满了老朋友。埃多斯的嗓门又大又聒噪,好掩盖他的难堪。哈特带来了一瓶朗姆酒。
哈特说:“有什么事吗,鲍嘉?”
“有什么事吗,哈特?”哈特见鲍嘉接过了话茬,好不高兴。
哈特打开朗姆酒,又吆喝博伊去买瓶苏打水。鲍嘉问:“哈特,你的牛都还好吗?”
“都好着呢。”
“博伊呢?”
“也好。我刚才还叫过他,你没听见?”
“那埃罗尔呢?”
“他也很好。不过鲍嘉,出了什么事?你好吗?”
鲍嘉点点头,然后喝了一大口马德拉斯产的朗姆酒,接着又一口,又一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把那瓶朗姆酒喝光了。
“不要紧,”鲍嘉说,“我再去买一瓶。”
大伙儿从未见鲍嘉喝过这么多酒,也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他们都很惊讶,可是没人敢问鲍嘉去了哪儿。
鲍嘉说:“你们这帮小子就一直没离开过我这屋吗?”
“没你在,不一样。”哈特回答道。
不过大伙儿都很紧张。鲍嘉平时总是抿着嘴说话,可这次他微微咧着嘴,口音里还带点美国腔。
“当然,当然。”鲍嘉这话说得纯正极了。他就像个演员。
哈特拿不准鲍嘉是不是醉了。
你们知道,光看相貌,哈特很像演员雷克斯-哈里森,而他平时也总是极力加强这种相像。他也把头发朝后梳,两眼眯缝着,说起话来简直就是哈里森。
“见鬼,鲍嘉,”哈特说,他变得颇像雷克斯·哈里森,“你还是快点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鲍嘉露出牙齿笑了笑,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会说的。”他说完站起身来,将两只大拇指插进腰带,“别急,我会把一切都说出来的。”
他点了一支烟,朝后仰去,烟熏着了他的眼睛,他眨了眨眼,然后慢条斯理地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一条船上谋了份差事,去了英属圭亚那。从那儿他下船去了内陆地区,在鲁普努尼当上了牛仔,向巴西走私物品(他没说是什么),他还将一些年轻的巴西女子带到乔治敦。他在那儿开了一家最棒的妓院,干得正红火,拿了他贿赂的警察却背信弃义,将他抓了起来。
“那地方可高级了,”他说,“没有乞丐,都是些法官、医生和市政要员。”
“然后呢?”埃多斯问,“进了监狱?”
“你怎么这么蠢!”哈特说,“要那样,这老兄怎么还会和我们在这里待着?为什么你们这帮人都这么蠢?你干吗不让他讲下去?”
可是鲍嘉生气了,拒绝再说一个字。
从那时起,这帮兄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鲍嘉成了电影中的鲍嘉。哈特成了哈里森。早晨的对话变成了这样:
“鲍嘉!”
“住嘴,哈特!”
鲍嘉现在成了这条街上最让人害怕的人。据说连“大脚”比佛都很怕他。此时的鲍嘉竭尽酗酒、打牌、赌博之能事,经常朝独自走在街上的女孩骂脏话。他买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他常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那堵高高的水泥护墙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抵着墙,嘴里永远叼着根香烟。他几乎成了一处固定的风景。
后来,他又不见了。他本来正和一帮朋友在他屋里打牌,突然起身说:“我去上趟厕所。”
他们就四个月再没见到他。
等他回来时,人长胖了点,不过脾气也变坏不少。这次口音可完全美国化了。为了完成那模仿,他开始同孩子们亲近起来。他在街上招呼他们,给他们钱买口香糖和巧克力。他喜欢轻拍他们的脑袋,给他们忠告。
他第三次离开又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问里为这条街所有的孩子(或用他的话说,“小家伙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聚会。他买了好几箱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差不多一蒲式耳。的糕点。
后来,那个住在米格尔街四十五号的警官查尔斯来了,把鲍嘉抓了起来。
“别胡来,鲍嘉。”查尔斯警官说。
但是鲍嘉没明白他的暗示。
“怎么回事,伙计?我可什么也没做呀。”
查尔斯警官便告诉了他。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对鲍嘉的指控是重婚罪,不过报上并没有披露细节,所有内幕都得靠哈特去挖掘了。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哈特在人行道上说,“那老兄离开了他在图那普纳的第一个老婆,然后来到了西班牙港。他们生不出孩子。他在这儿一直觉得很伤心,很压抑。然后他又走了,在卡罗尼找了个姑娘,让她有了个孩子。卡罗尼人从不在这种事上凑合,所以鲍嘉只好和那姑娘结了婚。”
“可他为什么又离开了她?”埃多斯问。
“为了做条汉子,和咱哥们在一起。”
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自家后院芒果树下那个马口铁的小工棚。就是这么个小工棚他也没有盖完。他懒得给屋顶上的马口铁皮钉钉子,只在上面压了几块大石头。一刮大风,屋顶就像散了架似的发出乒乒乓乓的可怕声响,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不过波普从不闲着。他总是在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看他干活。我喜欢那些木头——乔木、香树和蟾蜍树的香味,我喜欢那些木屑的颜色,也喜欢那些锯末像粉一样落在波普鬈曲的头发上。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总是说:“哈,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就喜欢波普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我想做点东西。”“你想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到底要什么。
“你看,”波普说,“你也在想一样没有名字的东西啦。”
最后我决定做一个鸡蛋架。
“你做这东西给谁?”波普问。
“我妈。”
他笑了笑。“你觉得她会用这东西?”
你别说,我母亲还挺满意那个鸡蛋架,用了差不多一星期。后来她好像把它给忘了,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往碗里或碟子里放鸡蛋了。
我把这事讲给波普听,他笑道:“孩子,要做东西,就要做没有名字的。”
我给鲍嘉的裁缝店写了招牌以后,波普也要我给他写一个。
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一截红笔头,琢磨着该怎么写。起先,他想称自己是建筑师,但我劝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他的拼写老没个准儿。写好后的招牌如下:
建造师及承包人
木匠
家具师
招牌由我执笔,所以我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招牌前。不过,不熟悉他的人前来咨询时,他总不免有点紧张。
“那个木匠伙计?”波普总这么说,“他搬走了。”我觉得波普要比鲍嘉随和得多。鲍嘉很少同我说话,波普却特别健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发觉他真的很爱跟我说话。
但在这条街上,波普却不是招人喜欢的人。倒不是大家觉得他疯疯癫癫或很傻。哈特常说:“你们听着,波普太傲气了。”
这么说波普不公道。波普有个习惯,每天早上总要拿着一杯朗姆酒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他从不喝杯里的酒,只是见有熟人,他就用中指蘸蘸酒,再舔舔手指,然后朝那个人挥挥手。
“我们也买得起朗姆酒呀,”哈特总说,“但我们就不像波普这样炫耀。”
我自己倒从来没这么觉得。一天我向波普问起这事。
波普说:“孩子,早晨太阳刚出来,天还有点凉,要是知遭你一起床就能出去走走,一边晒太阳,一边喝点朗姆酒,你会觉得很舒服。”
波普从不挣钱,都是他妻子出去工作。好在他们没有孩子,这样倒也过得去。波普说:“女人爱干活就让她们干吧,反正男人生来不是干活的。”
哈特说:“波普娘娘腔,不是条好汉。”
波普的妻子在我学校附近的一个大户人家做厨娘。那时她下午常等我,然后带我去她的大厨房,还给我好多好吃的。我唯一不喜欢的就是我吃东西时她坐在一旁盯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为她吃似的。她让我叫她阿姨。
经她介绍,我认识了那个大户人家的园丁。他是个棕色皮肤的英俊男人,很爱花。我喜欢他照看的花园。花园里的花圃总是黑幽幽、湿漉漉的,草坪上的草长得又绿又水灵,又总需要修剪。有时我会帮他给花圃浇水。他常把割下的草放在小袋里,让我拿回家给我母亲。草对于老母鸡可是好东西。
有一天,我没见着波普的妻子。她没在等我。
第二天早上,我也没见波普在人行道上用手指蘸杯里的朗姆酒。
那天晚上,我还是没看见波普的妻子。
我发现波普伤心地待在他的工棚里。他坐在一块木板上,手指问搓着木屑。
……
前言/序言
在线试读
《米格尔街》精彩连载用户评价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次阅读体验,我会选择“痛快”。这种痛快并非来自情节的高潮迭起,而是源于作者叙事上的彻底解放和对题材的精准把握。他没有被任何既定的文学范式所束缚,而是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充满生命力的姿态,书写他所观察到的世界。我仿佛透过作者的眼睛,重新审视了“家园”、“归属感”和“理想”这些宏大概念在普通人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地域气息和强烈的命运感,那种宿命论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但同时,那些微弱的、不屈服的生命火花又让人看到了希望的微光。这本书的优秀之处在于,它将严肃的社会批判隐藏在了最生活化的场景和人物互动之中,让你在不自觉间完成了对复杂现实的深刻理解。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嚼慢咽,才能品出其中真味的杰作。
评分说实话,一开始翻开这本书,我对它的预期是比较低的,毕竟这类聚焦于特定社区或群体的叙事,很容易陷入刻板印象的窠臼。然而,这本书很快就打破了我的这种偏见。作者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他仿佛是一个游走在人群边缘的观察者,既保持着必要的疏离感,又对这些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时间”的处理,那种悠长而缓慢的节奏感,完美地契合了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状态——一种被命运缓慢推搡着前行的无力感。你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尘土味和汗水的咸味,感受到阳光的灼热是如何一点点消磨掉人们的锐气。它展现的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微观的人类情感的潮起潮落,那些微小的背叛、不经意的善举、日复一日的坚持,汇聚成了强大的情感洪流。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那么地克制而精准,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每一个词语都像是经过千锤百炼后留下的精华,带着掷地有声的力量,读起来酣畅淋漓,又令人回味无穷。
评分这本小说读完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种对生活最本真、最原始的描摹,如同冷水浇头,让人不得不正视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地忽视掉的角落。作者的笔触犀利却不失温情,他总能精准地捕捉到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渴望,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在他的刻画下也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我尤其欣赏他对于环境氛围的营造,那种潮湿、闷热,带着某种独特香料气味的异域街景,仿佛能穿透纸页,直抵读者的感官。那些人物的对话,自然流畅得像是生活本身,没有丝毫的雕琢痕迹,充满了地方色彩和底层民众特有的生存智慧与无奈的幽默。它不是那种提供标准答案或心灵鸡汤的作品,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立场与判断。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真实的旅行,虽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但灵魂的某些部分似乎还留在了那个充满烟火气和未解之谜的地方。这本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真实和不加掩饰,它不试图美化生活,而是忠实地记录生活,这种力量是极其震撼的。
评分坦白讲,这本书的节奏是有些慢的,它不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反而更像是一首结构复杂的交响乐,需要你耐下心来品味每一个声部的起伏变化。但正是这种“慢”,赋予了人物深刻的厚度和立体感。作者对于角色内心世界的挖掘,达到了近乎残酷的坦诚,他毫不留情地撕开那些维持体面的表皮,直抵人性中最赤裸的欲望和恐惧。我尤其欣赏他对沉默的运用,有时候,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具毁灭性或治愈性。透过这些平淡的记述,我看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个体在巨大社会惯性面前的挣扎与妥协。这本书的文字简洁有力,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每一次重读,似乎都能从中挖掘出新的层次和更隐晦的社会观察。它迫使你走出自己舒适的“象牙塔”,去直面那些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生命状态。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极其沉浸式的,它不是那种让你能轻松跳脱出来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作品,而是一种把你直接“扔进”那个世界,让你和角色一同呼吸、一同体验困境的书。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自洽的微观宇宙,里面的规则、价值判断,乃至是非标准,都与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有着微妙的差异。我常常在想,作者是如何做到如此细腻地捕捉到这些细枝末节的?那些关于邻里关系、关于贫穷带来的尊严挑战、关于青春期的懵懂与莽撞,都被描绘得入木三分。它没有刻意去煽情,但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苍凉与韧性,却能自然而然地触动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读罢全书,我感受到的不是某种结论性的答案,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人性的基本需求——被看见、被尊重——从未改变,这才是跨越文化和地域的普世主题。
评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评分物美价廉,值得购买,不错
评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
评分好。。。。。。。。。。。
评分奈保尔26岁就写出的经典著作,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兴高采烈地活着。
评分不重复哦哦哦坎坎坷坷坎坎坷坷
评分帮朋友买的书,618活动,满减券,结合白条券,600元买了一大堆文学书,性价比超高。
评分风格比较简单,故事也可以,还算不错
评分奈保尔是当今难得一见的短中长小说都可以掌控,而且还可以写出杰作的伟大作家,十分荣幸可以一本一本的读到他的书,感谢新经典!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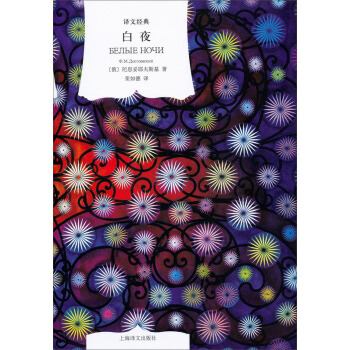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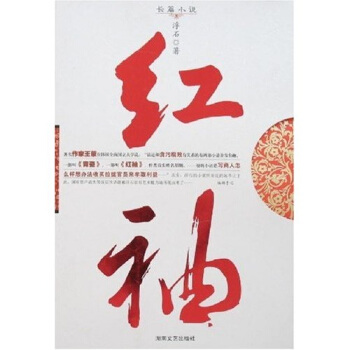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34167/55b09461N59f5ef8b.jpg)







![追忆似水年华(第1卷):在斯万家这边 [A?la?recherche?du?temps?perdu]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30510/101aaab9-dc49-4a79-9775-8327ab9ad0b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