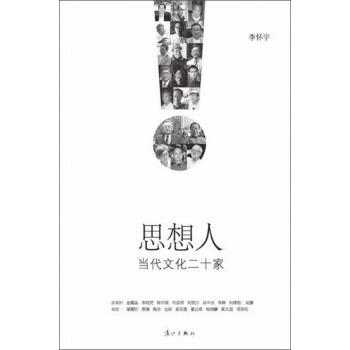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如果以我出生的1976年为界,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生活的巨变更是我童年时所不敢想象。而我们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国”的国运与民生,是我念兹在兹的问题。因此,《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将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对辛亥百年的思考作为开头两篇,略有破题之意。而诸位先生的生活与思想,可视为同一时代的多元答卷。内容简介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是文化记者李怀宇对多位著名学者的采访记录。访谈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历史人生,今集成此书,或可视作一位后学向前贤问道解惑的对话,从中探求一些知人论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见。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于广东澄海。传媒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知识人》、《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目录
自序余英时
开启共和之梦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
李欧梵
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
陈平原
时代转折成就人才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
刘荒田
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
吴中杰
反思历史人物的命运
李辉
重现惊心动魄的历史
刘绪贻
大学是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地方
吴灏
绘画与文学就像两姐妹
吴宏一
文学有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蔡澜
我的正业是玩
陶杰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也斯
尝试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夏伯嘉
追索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董启章
整个世界都是小说
杨锦麟
不断寻找新的事业气场
梁文道
我只在乎是否尽到责任
周保松
探求自由和平等
……
精彩书摘
余英时:开启共和之梦001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清廷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后来黎元洪被逼参加革命,也是这样的道理。
李怀宇: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李怀宇: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发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李怀宇: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开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捐钱,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的心理,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当然清政府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上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清廷没有什么办法。
李怀宇: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如果谈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而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清廷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洲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清廷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李怀宇: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李怀宇: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英国的君主立宪,是鼓励清廷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怀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李怀宇: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因为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政府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还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个秩序,也不用怕。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李怀宇: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
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是感觉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
李怀宇: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
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李怀宇:为什么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农家的子弟一夜之间也可以成为进士出身了。民国没有了,都是靠党的关系,中国的朋党制度成为政治上的党派,就是一群人组成一个团体,打一个现代的号召,好像是有一个原则,其实是次要的,只是夺权的借口。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改变。
在辛亥革命以后,大家又不满意新的现实,又想用更积极的办法去改造中国。这是我们的毛病,老想照一种理想,用一个主义去改造中国,事实上,社会是不允许这样搞的。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念头:要重新改造中国社会。要让民间老百姓自己发展,少干预,只要民间的发展不会影响整个秩序,就要宽容,给予自由。另外一个关键,日本的侵略是我们一切灾难的开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了一步,打开了某一些门户。但是我们走出来就有问题,因为还有外面的影响。中国要做共和之梦,但是有一些很恶的势力,或者是国外,或者是国内,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会于不顾。
李怀宇: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俄的路子,改组以后他说法算数。孙中山想利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新。孙中山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弱点。原来康有为见都不要见他,梁启超一度跟他关系搞得还好,所以孙梁合作的问题引起立宪派内部的紧张,说梁启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孙行者”。梁启超想借华侨的力量去捐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关系给他,可见孙中山还很坦率,并不是说:我的关系,我不介绍给你。因为大家就只有这么一个财源。孙中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出来的人,但是没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样。当然,人家也叫他“孙大炮”。但是,他是一个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把中国的某些观念推到现代化的路上去了。现代化不是一下子能够就完成,得慢慢来。
李怀宇: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的文化思想界一度出现天才成群而来的现象?
余英时:在军阀时代,军阀对文化、文学、思想问题都不重视,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活动很积极,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接着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了,所以有很多人才冒出来。孙中山在广州开始准备北伐,采取苏俄一党专政的制度,但是孙中山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实行宪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他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很宽松的,所以专家学者还有空间发展自己的观念。比如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也很赞扬;孙中山和胡适早期关系还很好,常常写文章要请胡适批评。国民党办的杂志上,胡适写过好多文章。廖仲恺、胡汉民跟胡适都有交往,因为孙中山对胡适很尊敬。193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对学术思想界的控制还是有限,因为民间还有别的势力,如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理论,差不多有一半的县都实现了乡村建设,这是因为山东政权在另外一个旧军阀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并没有把所有私人财产都没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机构还可以容纳人才。另外,西方的教会大学也可以保护中国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国出了很多学术思想界的人才,也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和日本对这段时期的学术成绩非常重视,所以这段时期的学术也影响了世界汉学。
李怀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余英时: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现代型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工商企业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钱做本乡的建设工作。比如说,无锡的荣家后来创办了江南大学,也造了无锡的大桥。所以我们看民国以后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为例,阎锡山的建设被很多人看成为模范。另外,像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地方的绅士和商人共同开创的。从民间社会的观点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可观的。我认为这是社会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个计划逼着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计划地全面改造社会叫做“社会工程”,他们对于“社会工程”是否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识来建立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个计划不能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地方。中国这么大,定一个全面计划在每个地方实行是会制造出很大的混乱的。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自动的进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这个进程打断了。西方的史学家像费正清就曾经对这段进程非常欣赏,惋惜它的中断。从这方面看,民间在动,在一步步往前走,不过是没有一个计划的。有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计划往往会用不好的。
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方式非常吸引人,它没有采用枯燥的学术论述,而是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将二十位“思想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仿佛能够看到他们活跃在各自的领域,与时代对话,与观念碰撞。书中关于艺术家如何打破常规,挑战既有审美标准的描写,让我看到了创造的巨大能量;关于哲学家如何追问存在的意义,揭示人性的复杂,让我对自身的生命有了更深的思考;关于社会活动家如何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他们的勇气和坚持,更是让我感动不已。我尤其喜欢书中有时穿插的个人访谈和回忆片段,这些鲜活的细节让“思想人”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故事的个体。这让我觉得,思想的火花,往往就蕴藏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经历中。这本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它让我感受到,每一个伟大的思想背后,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程。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我了,一种复古又现代的碰撞感,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智识世界的任意门。我一直觉得,了解当代文化,就得抓住那些在思想的沃土上耕耘的“人”,他们不仅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更是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塑造者。这本书的名字《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恰恰点出了这一点,它没有泛泛而谈,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个体身上,这让我觉得非常有亲切感和期待感。我很好奇,书中收录的这二十位“思想人”究竟是谁?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在当代文化中留下印记的?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还是科学家?他们的观点是否尖锐,他们的洞察是否独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领我走进他们的思想世界,去感受他们的智慧光芒,去理解他们是如何剖析和解读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的。我尤其关注的是,这本书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让我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思想是如何汇聚成一股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并最终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社会进程。这不仅仅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次思想的旅行,一场与智者的对话。
评分坦白说,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当代文化”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知。它似乎是一个模糊而庞大的集合体,包含着无数的元素,让我感到有些无从下手。然而,《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这本书,就像是为我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它通过聚焦二十位在各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思想人”,将抽象的当代文化具象化,并以一种非常有条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了解到,原来当代文化的发展,并非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了各种观念的碰撞、张力和演变。书中的每一位“思想人”,都像是时代的某个侧面,他们的思考和实践,共同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文化景观。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关于不同文化流派的知识,也更理解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去辨别和吸收有价值的思想。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理解当代文化,需要我们有批判性思维,也需要我们拥抱多元。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思维被极大地拓宽了,像是从一个狭窄的井底,瞬间看到了广阔的天空。书中对这二十位“思想人”的解读,并非简单的生平介绍或观点罗列,而是深入到了他们思想的根源,探讨了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孕育、发展并最终形成其独特性的。作者在分析这些思想家时,展现了深厚的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精准地抓住他们思想的核心要义,并用清晰易懂的语言阐释出来。我尤其欣赏的是,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些思想家思想中的争议之处,而是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呈现,这使得读者的思考空间更加 open。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化,不能只看表面的流行趋势,更要深入挖掘那些潜藏在深处的思想脉络。这二十位“思想人”,就像是二十个不同的棱镜,折射出当代文化斑斓的色彩,让我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份思想的地图,指引我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解读方式感到非常惊喜。它不仅仅是在介绍“思想人”本身,更是在剖析这些思想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相结合。比如,书中有一章深入探讨了一位作家作品中对当下社会焦虑的精准捕捉,以及另一位学者对新兴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些分析让我看到了“思想人”是如何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和“瞭望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梳理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联系时,展现了一种宏观的视野,能够看到他们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争鸣。这让我觉得,当代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而非孤立的个体贡献。这本书不仅让我认识了二十位杰出的“思想人”,更让我对当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了一个制高点,能够俯瞰整个当代文化的生态系统。
评分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岭南自从清季以来,就是思想文化的前沿,不用说康有为梁任公,就是后来的孙大炮也是广东人。所以,这本书开始就以余英时和金耀基谈辛亥革命开始,以梁文道周保松畅谈香港文化的前景为终,这样的布局,虽然是以访谈录为形式的书里,还是有章法可寻的。余英时先生谈的是晚清的改革,认为满清政府由于利益关系,所以不肯改革,所以革命才最终取得了主流。这是在谈论晚清,还是在讨论世事?想来,余英时先生是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古典今典的写作方法,连访谈录中也会流露一二。
评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们的思想。
评分书很好,包装好,内容也不错。
评分那么,如今的现状是否是我们曾经的期望?书名《思想人》,代表受访者自然都是这个问题的思索者。从他们的回答来看,虽然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对当代文化状况,确是消极看法为主。文化刚刚从政治的胁迫中挣扎而出,却陷入了后工业商品时代的异化大潮中。表观建筑形式的“水泥化”;大学教育的功利化;文学研究的“工匠化”;文学作品本身的日渐凋零,这些都令人难掩失望之情。文化对现实的关怀,对人性的反思,对独立人格的塑造,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似乎都还做得不够。也难怪近来“民国风度”成为人们追忆的热点,对往昔的缅怀,其实体现的正是对现实的不满。“大师不再”、“文学已死”之类的叹息,我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不过,固然现状难令人满意,但悲观之中也不是没有希望。身处中华文明最大转型期,弯路和挫折有时在所难免。但只要不忘初衷,那么即使是黑暗中的摸索,前方未必没有光明。毕竟“自由”这一文明之魂,并没有完全丢失。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些,正如书中一位受访者所说,大师之类,是后世的眼光,而当世之人的标准和判断,有时反而会“当局者迷”。
评分对于余先生的政治关怀,我读书的时候是知道一些的,这样的开篇预示着这本书的一些基本的基调。金耀基先生谈论的中
评分深入,点点掌握,关键还在于把握自己的读书速度。至于“熟读”,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自己看过的书在看,在看,看的滚瓜烂熟,,能活学活用。而“精思”则是“循序渐进”,“熟读”的必然结果,也必然是读书的要决。有了细致、精练的思索才能更高一层的理解书所要讲的道理
评分认识李怀宇和他的访谈,是从《知识人》开始。时隔一年,他的这本《思想人》出炉,依旧是一本访谈集。因为读前作觉得颇合口味,对这本书自然也就有了兴趣。
评分好书,好书,很好书。
评分好书,好书,很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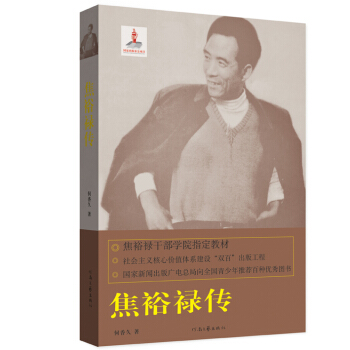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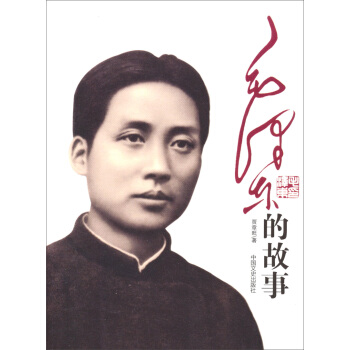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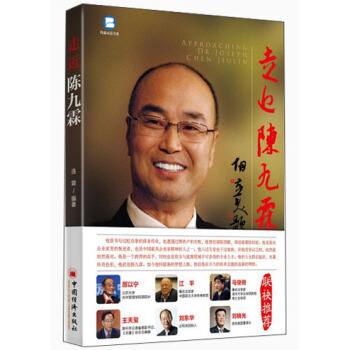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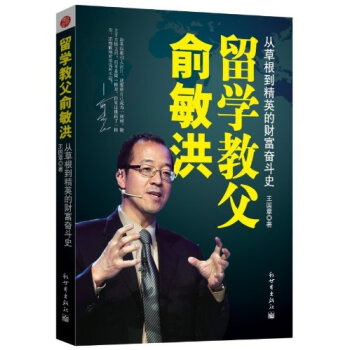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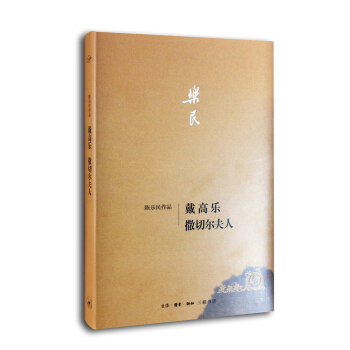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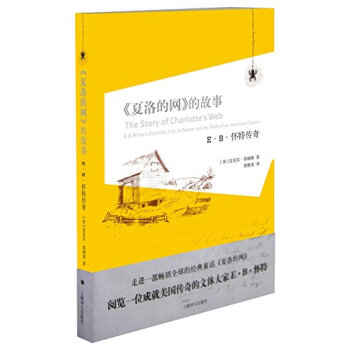
![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 [Albert Schweitzer Lesebuc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17714/5508eeb9Nd1a429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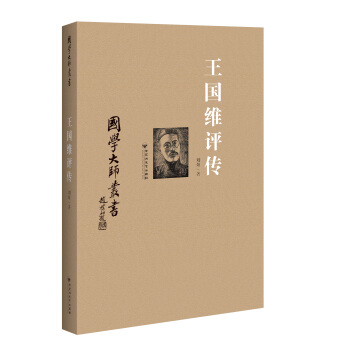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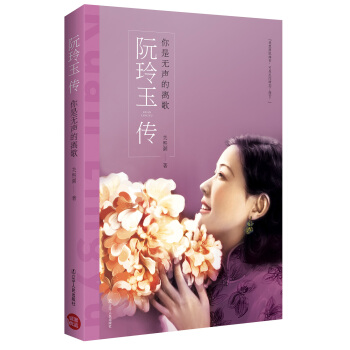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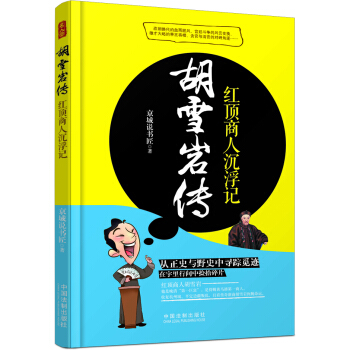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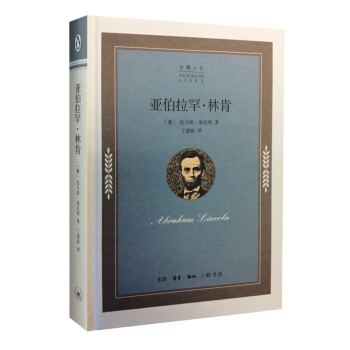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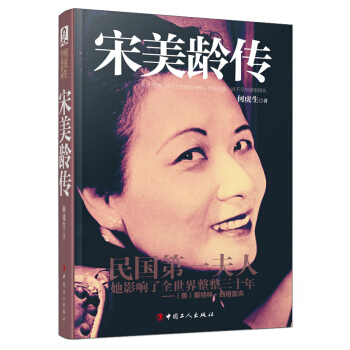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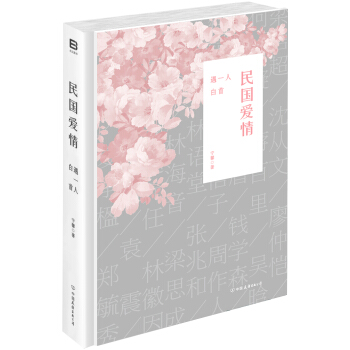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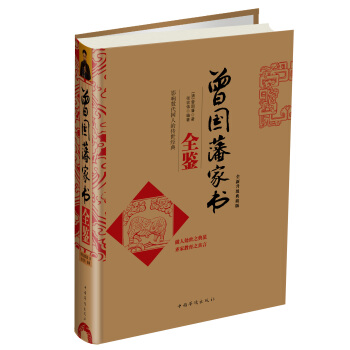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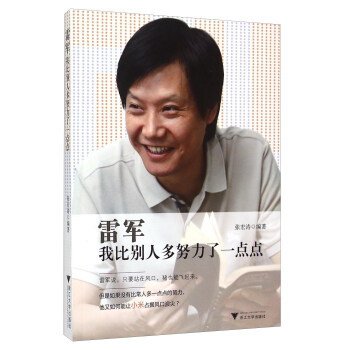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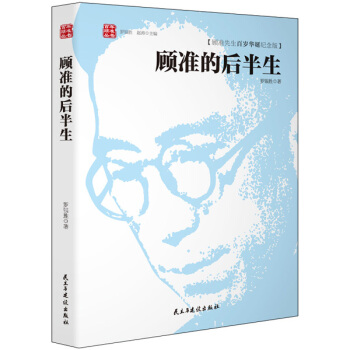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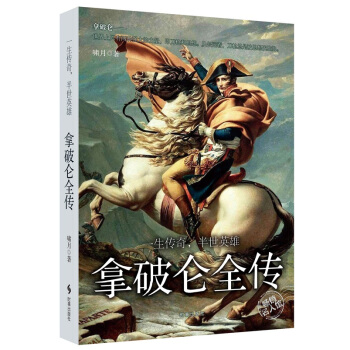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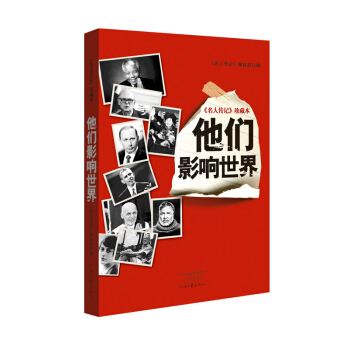
![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 [Anna May Wong: From Laundryman's Daughter To Holl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61347/56974644Nbc7cbe5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