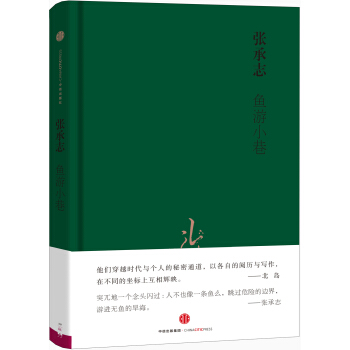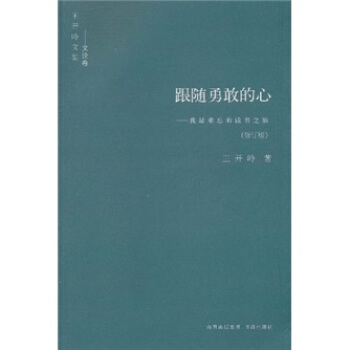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记住一些词,记住一些人和书的名字,会有助予生活。谨以此书纪念那些“透过眼前浓雾而看到了远方”的人。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闯进一个青年不眠的思想之夜:为反乌托邦咯血而死的奥威尔;战争中当逃兵的“德国良心”伯尔;苏军炮塔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稿纸的背后,是流亡、牢狱、枪声,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作者简介
王开岭,1969年生,祖籍山东,主要著作有《激动的舌头》《黑暗中的锐角》《精神自治》《跟随勇敢的心》《精神明亮的入》《古典之殇一纪念原配的世界》等,作品入选数百种中外选集、年鉴和教材。现居北京,历任央视《社会记录》《新闻会客厅》《24小时》《看见》等栏目指导。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他道路全都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的道德保险,它是我们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布罗茨基
目录
前言:这世界哭声太多三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乌托邦的变种
——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读乔治·奥威尔《1984》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关于伊凡·克里玛《我快乐的早晨》及其他
沸腾的生活一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地中海的儿子:置身苦难与阳光之间
——加缪《反抗者》阅读札记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
——读加缪《鼠疫》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白尔文论》之一
“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
——兼读海因里希·伯尔《伯尔文论》之二
爬满心墙的蔷薇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
——读爱伦堡保。《人·岁月·生活》
在羊毛和蓝天之间
——读契诃夫《草原》
“深水鱼”与“地下文学”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一
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
——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之二
“当你老了,头白了……”
——关于威·叶芝和茅特·冈
有毒的情人
——读玛格丽特·杜拉斯
迷途的潘多拉
——读米兰·昆德拉《搭车游戏》
最后的双人舞
——怀念邓肯和叶赛宁
精彩书摘
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狱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束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报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国度,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甚至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邻居。
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犹如父母对失散儿女的补偿,总觉欠之太多……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一甚至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母土,以最大的坚韧和牺牲,以坐牢、被监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虽然他们无意于此。
伊凡·克里玛,1931年生于布拉格,10岁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权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有20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一流亡——文学史。
……
前言/序言
这世界哭声太多王开岭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手,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世界哭声太多,你不懂。
——叶芝
勃兰兑斯在描述19世纪流亡作家时说:“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当有一天,我也站在了新世纪的清冷晨曦中,心不由得揪紧:历史其实何等相似120世纪的人之命运、思想之命运,哪一点不符合上述情景呢?甚至说,那段话更适于为20世纪的作家形骸和精神事业作注脚,像画外音,像一场大雪的旁白。
这是一个哭声最多的世纪;一个思想与行为最密集、最吊诡的世纪;一个物质与精神消耗最多的世纪;一个盛产最崇高和最卑鄙的政治的世纪……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的青春位于这个世纪。我的迷惘、疑问、挣扎、思想的饥饿,全和这个世纪有关。或许我已冲出来了,或许我和这个国家一样,半个身子仍卡在里面,仍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前夜”。
但不管怎样,时间上已天亮了,光线在增强,视力在恢复。
我想寻找那些被大雪吞没的“人”的影子,他们冷得发抖的工作,那僵紫得说不出话的嘴唇,那快要被遗忘、被“人工”打扫干净的生命辙印……
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
为了打捞和纪念,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其实更是荐书的方式,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与伟大的“他们”会师。
他们曾携着电,裹着雷,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他们曾那样震撼、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渴望破壳的灵魂。他们曾是我最饥饿年份里的光和盐。“他们”是——
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奥威尔;不停地扬筛尘土、终于捧上一朵“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伯尔;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布拉格精神”的伊凡·克里玛;见证俄罗斯伟大精神夜晚的巴纳耶夫;替生命辩护、与精神“鼠疫”殊死搏斗的加缪;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替百万亡灵起诉“古拉格”的索尔仁尼琴;孤独地讲述“人,岁月,生活”的爱伦堡;不顾“革命海燕”身份痛斥红色恐怖的高尔基……
恰达耶夫曾说:“请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但是,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
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刺头。是锐角,暗夜中最锋利、嘹亮的锐角。像矛刺、像号筒、像蒺藜,锋芒所向、剑气所指,无不乃黑夜中最阴、最毒、最凶险的方位……他们是诗人、作家,更是医生、战士和良心。是知识分子,更是伟大的精神保姆和人道主义者,是有史以来所有“人”的兄弟。
他们的笔总是寻着哭声而去,他们不仅同情天下的哭声,还发现了哭声的源头,那制造哭声的狰狞和恐吓。
对文学的使命和责任,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定义——
“他不能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去评论社会和同胞,他应该分担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所犯一切罪孽的结果。如果你国家的坦克曾在邻国首都的马路上进行屠杀,那永不褪色的血迹将喷在你的脸上。如果在一个深夜,那些信赖你的人中有人被从床上拉向绞架,那绞索必在你的手上留下勒痕。如果你国家的青年们懒惰而玩世不恭,甚至吸毒、绑架,那你的呼吸中也必搀杂污秽之气。谁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这个世界的弊病与我们无关?”(索尔仁尼琴)
在中国教科书上,它们没有“名著”的位置,甚至没有位置。由于特殊原因,它们长期被冷落成“另类”,被诬陷为“异端”,连户口都报不上。但它们是那样贵重、稀缺,它们完成的并非文学的单项成绩,而是理性、良知、人格、信仰、梦想、行动的全面成就。更有其来之不易、诞生的艰难和高昂成本,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它们也奠定了主人的苦难,稿纸的背后,往往是流亡、牢狱、枪声和铁丝网,是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
还有些重要的书,本打算谈的,比如索尔仁尼琴估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萧斯塔克维奇《见证》、茨威格《异端的权利》、扎米亚京《我们》、戈尔丁(<蝇王》,还有哈维尔、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还有顾准……因精力有限,暂不单列。事实上,它们已以气体和离子的方式弥漫在了我的文章里。
上述作品,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但较之它们的巨大意义,较之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出版物,实在太孤弱,太不成比例了……这是我的一个焦急,痛于此,虽自感非精识之人,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世纪之交,需要精神常识的普及,需要在自由空气中醒来的青年一代——他们应在真相和常识中生活。作为新人,他们首先应头脑合格,应在精神上脱胎换骨。
他们应比上一代人走得轻快,笔直。
除了沉痛、抑郁、忧患、理性,我也没忘记美、爱、自然和愉悦,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柔的东西,比如《草原》《金蔷薇》,比如杜拉斯、茅特·冈、邓肯……既是刻意平衡,也是心性使然。近年来,我惯于在某种对称格局中获得安慰和力量,否则,单极的事物会让人发狂,会对世界绝望。它们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一并掏予大家了。如果说,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那后者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在一个不易动情的物理时代,连雅致点的抒情和风花雪月也难觅了。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戗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布罗茨基)
……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2001年4月9日
用户评价
坦率地说,我原本对这种回顾性质的“读书之旅”题材并不抱太大期望,总觉得容易流于矫情或空泛。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固有印象。作者的叙事风格极其克制且富有张力,他没有用华丽辞藻堆砌,而是用一种近乎自白的真诚,构建起了一个个令人信服的阅读场景。特别是他提到某些作品如何在他人生低谷时提供了支撑,那种情感的真实性是具有强大穿透力的。我能感受到,每一次“难忘的读书之旅”,背后都对应着作者生命中一次重要的转型或顿悟。这种将阅读与生命体验紧密编织的写作手法,使得全书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它不再是单纯的书评合集,而是一部微型的生命史诗,只不过载体是文字而已。我欣赏作者敢于展示自己的脆弱与成长,这种坦诚让读者感到安全,敢于在自己的阅读世界里也进行同样的探索和审视。这本书就像一个可靠的向导,陪伴我重新审视我自己的阅读足迹,找出那些我曾经忽略的关键转折点。
评分我一直认为,最好的阅读分享,是能够激发听众主动去寻找和对话的欲望,而不是让他们盲目跟随。这本书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的文字像一股清泉,洗去了我心中对阅读“功利化”的杂念。他讲述的那些“难忘的旅程”,重点并不在于书籍本身的名气,而在于那个阅读瞬间如何与读者当时的内在需求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他对某本哲学著作的解读,平铺直叙中蕴含着巨大的智慧,让我领悟到,很多看似高深的理论,一旦与个人生活场景对接,便会立刻变得鲜活可感。这本书的修订版在语言上更加精炼,删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赘述,使得核心观点更加锐利。我特别喜欢它对“阅读疲劳期”的应对策略的探讨,这对于长期读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实用指导。读完全书,我感觉自己像是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大扫除”,清理了陈旧的偏见,为未来的阅读储备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坚定的信心。
评分读完这本新修订的版本,我简直是醍醐灌顶。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阅读记录集,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这些年来在精神世界里摸索前行的轨迹。作者的文笔细腻入微,对阅读体验的捕捉精准到位,仿佛能隔着书页感受到他当时的激动与困惑。尤其是他对于那些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那种洞察力令人赞叹。我特别喜欢他探讨“阅读的意义”那一部分,那段文字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己阅读习惯的欲望。我常常在想,我们究竟是在阅读书本,还是在阅读我们自己?这本书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方向。它教会我,每一次翻开书页,都是一次与过去和未来的自我对话,而那些“难忘的旅程”,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闪光的节点。这种由内而外的冲击力,让我在合上书本后,久久不能平静,只觉得胸中充满了新的能量,恨不得立刻再去翻开那些尘封已久的书籍,带着全新的视角去重新体验一番。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重新点燃了我对深度阅读的热情,让我明白,真正的阅读,永远是心与心之间的共振。
评分这本书的修订版,简直是为我这种“老读者”准备的一份惊喜大礼。我记得初版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但这次的增补和修改,明显让整体的逻辑更加流畅,情感的表达也更加老辣沉稳。作者在描述那些阅读瞬间时,那种画面感极强,让我仿佛也置身于他当时的阅读场景之中——也许是在一个阳光洒满的午后,也许是在一个灯火阑珊的深夜。他对于特定书籍带来的心境变化,描述得极其到位,那种从迷茫到豁然开朗的过程,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呈现。更让我佩服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推荐书单”层面,而是深入剖析了“为何是这本书,为何是此时此地”的哲学命题。这不仅仅是关于书的内容,更是关于时间、环境与个体精神需求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读罢,我立刻行动起来,按照他文中的指引,去寻找了几本我过去曾“错过”的经典,结果大有不同,收获远超预期。这本修订版,与其说是阅读指南,不如说是一份通往更深层次自我认知的地图。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它没有采用线性的时间轴,而是像一幅由不同光斑构成的星图,每一颗星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阅读体验。不同章节之间的跳跃和回溯,反而营造出一种记忆碎片重组的韵律感,非常符合我们真实记忆的运作方式。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对于阅读带来的“认知冲突”的描述。他没有回避阅读带来的不适感或挑战性,反而将其视为成长的必要代价。这种不回避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亲切。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太习惯于被动接受已经被消化好的“结论”,而这本书却在鼓励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发现问题”的初始阶段。这不仅仅是关于阅读的方法论,更是一种面对世界复杂性的勇气培养。我看完后,立刻给我身边几个热衷阅读的朋友强力推荐,并特别强调,这本书需要慢读,需要反复咀嚼,因为它所提供的回味空间,远比阅读本身要广阔得多。它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评分物流速度超级快,配送员态度杠杠的。
评分正版,很合适,已经买好几次了。
评分可以通过本书,了解世界上其他的好书,是一本不错的“好书索引”
评分跟随勇敢的心,感受大师的智慧
评分同事买的,很满意,包装也很好
评分好书,喜欢他的文笔
评分非常满意。。。。...
评分很不错的一本书
评分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夏洛克与亨利王子冒险系列·亨利王子4:玩偶屋的秘密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11119/55384902N4986d42c.jpg)

![孙悟空在我们村里 [6-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03283/5767a248N656a362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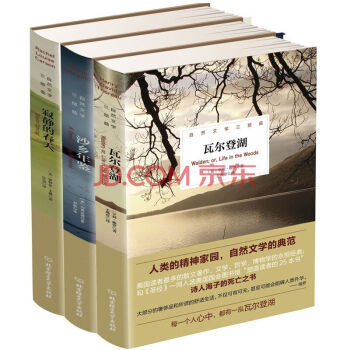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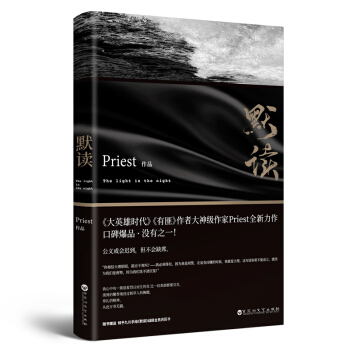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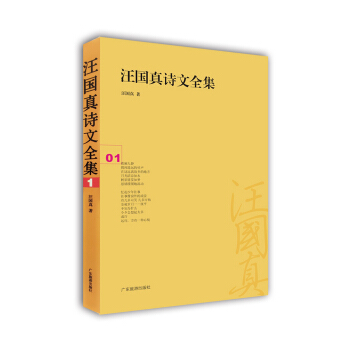
![七色狐丛书·我的快乐日记:一年级的小屁孩(注音读物) [6-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20496/5406851dN5d5e071e.jpg)
![大卫·少年幽默小说系列:臭臭先生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88849/rBEQWVE9qsMIAAAAAAPpCMZ1Pj8AAB5wAOP_5cAA-kg07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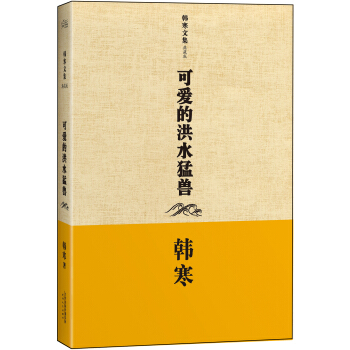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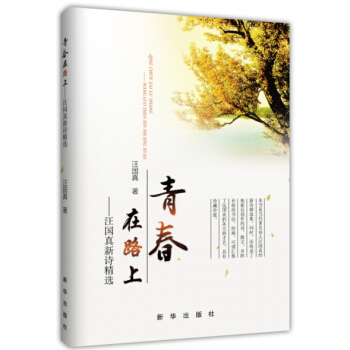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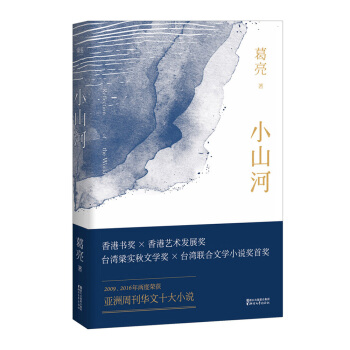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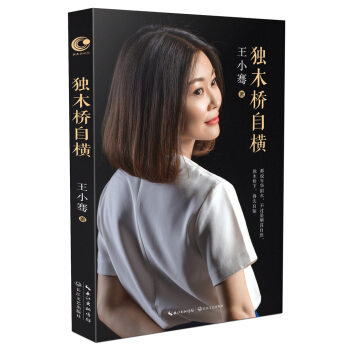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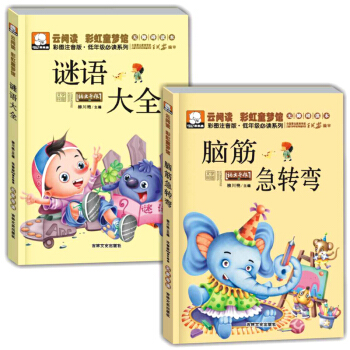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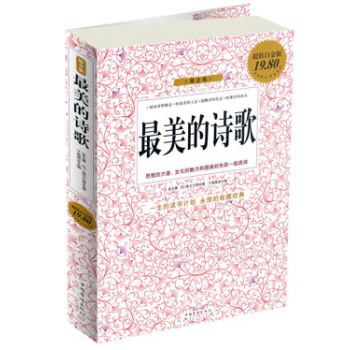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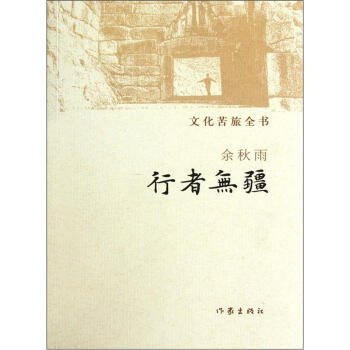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 [Refuge: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119911/rBEGF1CjYRkIAAAAAADaODS0gkQAAAgGwGoaf8AANpQ77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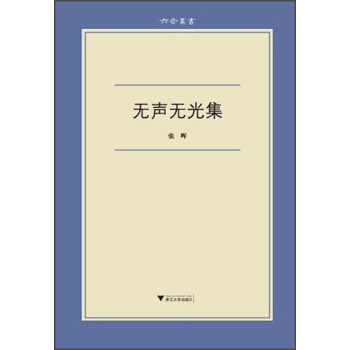
![曹文轩作品:跑偏的人我的儿子皮卡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6437/rBEhUlKdieAIAAAAAAJTRMNHqIMAAGSkQEKDc0AAlNc26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