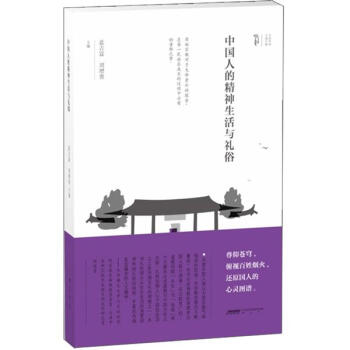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个国家教科书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的精神发育史。在近代中国输入新知的过程中,教科书是宣告黎明的朝霞。
内容简介
本著以中国近代教科书为焦点,从知识建构史的视角探察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教本,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诞生物,建构起近代中国人的常识体系,打造了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模型,其文化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晚清社会文化背景下近代教科书如何诞生,其编审制度怎样形成演变,以及它在塑造近代国民意识和培养科学观念上的贡献,是本研究着力考察的重心。作者简介
毕苑,女,籍贯山西。2001年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出站,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教育史。目录
序(郑师渠)建造常识:近代教科书的文化价值
第一章 传教士与教科书
一、从“教科书”一词说起
二、传教士·教会学校·教科书
第二章 欧美与东瀛:近代教科书的两次译介浪潮
一、“多译西国学堂功课书”
二、戊戌后翻译日本教科书的热潮
第三章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
一、师日浪潮中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
二、汉译日本教科书与近代知识体系的建立
三、汉译日本教科书与近代教育学的建立
四、汉译日本教科书的特点与影响
第四章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诞生和发展
一、近代教科书的萌芽
二、“蒙学教科书”:第一部中国近代教科书
三、开创“教科书时代”的商务版“最新教科书”
四、晚清教科书的出版和销售
五、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
第五章 近代教科书编审制度的演变
一、晚清教科书的编审
二、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审制度
第六章 从“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书中的国民塑形
一、经学和修身:道德教育的承接与开新
二、林纾和他的《修身讲义》:道德教育转型之一例
三、民初国民性改造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公民教育
第七章 斯巴达与中国:近代教科书里中国人的政体认识
一、“西洋史”中的斯巴达
二、国语文和体操课本中的斯巴达
三、中国人对斯巴达政体的认识
第八章 花鸟虫鱼看世界:博物教科书与近代自然教育的发端
一、中国博物教科书的诞生
二、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三、杜亚泉的博物学贡献及其“形而下”的自然哲学观
四、博物教科书与近代自然教育的开端
附录一 1877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总干事韦廉臣向委员会提交的学校用书表
附录二 1880年12月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大会记录所列学校教科用书表
附录三 1890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计划出版的中文教科书列表
附录四 189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执行委员皮彻博士(Dr.Pilcher)关于学校用书的纲要性设想
附录五 清末民初的汉译中小学用日本教科书(1890~1915)
附录六 民初“共和国”教科书与“新编中学共和国”教科书
附录七 民初“中华”教科书与“新制中华”教科书
附录八 杜亚泉编译校订的博物类教科书(共计52种)
引征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传教士与教科书中国的学校教育渊源甚早,《礼记》记载: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教材而论,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作为教材的典籍。《四书》、《五经》是对封建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献,可以称之为传统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教材。中国蒙童教材同样起源甚早,周时有《史籀篇》;汉魏有《仓颉篇》、《急就篇》;唐宋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更成为传统社会影响深远的童蒙教材。虽然以后历代稍有修改,但只是在内容上进行增减,教材的形式及施教对象没有什么变化。 教科书象所有传统时代的典籍一样,担负着接续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教化的职责。
然而,“教科书”这个名词并非是同中国教育共时发源的。在本章,我们将首先探究“教科书”一词的来源,从而讨论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
一,从“教科书”一词说起
与“教科书”意义相近或有相关联系的词语很多,比如“功课”、“课业”、“课本”、“教材”、“课程”、“读本”等等。传统社会中使用较多的是“功课”和“课业”等词,它们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学概念,比如“功课”是教师施教和学生学习内容的总称,也专指授课之后的作业;“课业”包含了功课和学业等含义。“课本”和“教材”等词,在使用上接近于俗语和泛称;“读本”一词的意义宽泛于正式教学用书;而“课程”一词更多地表达了教学科目和进程的含义。在“教科书”一词出现之前,这些词语已在各种官私文献中得到使用。那么,具有近代意义的“教科书”一词是何时、在何种情势下进入中国的呢?
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一词,按照通行的观点,是19世纪70年代末由基督教传教士首先使用的。学界认可的说法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可考。” “学堂教科书委员会”之名见于民国时期的文献,后人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它是学界公认的将“教科书”名称带入中国的机构。据上述说法,英文“Text Book”一词,在光绪二年即1876年就已传入中国。但是,西方传教士所使用的英文词语,如何被中国人接受为“教科书”的?探寻语言转换的脉络,对于理解“教科书”的近代意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人使用“Text Book”一词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较早有胸前佩挂之“明角书”(“hornbook”), “Text Book”是稍后才出现的词语。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正式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尽管传教士们使用了“Text Book”一词,但由于它的中文名字是“益智书会”,所以,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立即接受并使用“教科书”这个新名词。益智书会这一中文名字一方面说明传教士努力使其工作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西方传教士并没有将“教科书”这个名词传入中国的明晰念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虽然出版了各种作为在华教会学校教科书之用的书籍,但并没有在书名中使用“教科书”一词,而是大量使用诸如“读本”、“纲要”、“入门”、“基础”等词。在可见的晚清各种书目中,如徐维则的《东西学书目》、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以及江南制造局译书书目、同文馆所译西书等书目中,均未见到“教科书”一词。据可看到的英文资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所编辑出版学校用书的书名中也没有使用过“Text Book”一词,其原因可以用语言差异来解释。时人据原书名译为中文,自然不会出现“教科书”译词。虽然书名中没有使用“教科书”,但各书的凡例、编辑大意或序言之类仍有可能使用“教科书”一词。只是由于这部分书籍散轶不可考,我们无法获得清晰的结论。唯一存留的线索这样叙述:“光绪十九年,申江中西书院潘慎文、谢洪赉译《八线备旨》,由美华书馆活版印行。据潘慎文称系译以作中学堂程度之教科书云云。” 潘慎文牧师(Rev A. P. Parker)1887年1月成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1890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之后,他继续任职并发挥重要领导作用;谢洪赉同西方传教士多次合作翻译理化方面的教科书,成果丰硕。潘慎文牧师所称有可能在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这条叙述至少证实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传教士们事实上向中国人传输教科书的工作。
据此而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存在的19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还没有产生清晰的“教科书”概念。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逐渐产生了改良传统学校读物的要求,开始自行编译新式的学生读物。
考察“教科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0年之前,“教科书”一词首次出现,并开始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使用,但在清政府官方文牍中还未见使用该词。汪家熔认为,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772年),我国已经有以“学堂教科”字样出版的教学用课本,那就是清代蓝鼎元编写的《女学堂教科讲读启蒙》。但是汪家熔同样认为,这并不代表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出现。 光绪23年(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使用的教科书有《笔算教科书》一种,董瑞椿译《物算教科书》一种,张相文编《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二种。 这是可考的近代意义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另外,晚清时期思想家、毕生致力于教育改良事业的钟天纬曾编有《字义教科书》 ,钟天纬生于1840年,卒于1900年,也就是说,《字义教科书》的编写时间当在1900年之前。这说明至迟到戊戌维新时期,“教科书”一词就已开始流行了。
但是此时期,多数中国学者仍象梁启超一样,在文章中更多还是使用诸如“学堂功课之书”等词 来表达近似于“教科书”的意义。应该说,梁启超也是最早产生“教科书”概念之人。189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的一份奏折中讨论了“中学小学所读之书” ;同年盛宣怀在其奏折中介绍日本学校规则及“授读之书” ;清政府官方文牍中也使用类似的词语,如总理衙门在1898年上清帝的奏折中有“学堂功课书”之称,并奏称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 ;当年还有奏折称西国学堂皆有一定“功课书”,“有小学堂读本,有中学堂读本” ;清帝在同年的上谕中则使用“中学小学应读之书” ;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教科书成为教育改革讨论的一大热点。以后大量出现的具有近似于“教科书”意义的词汇充分说明了这一现象。
第二阶段从1901年至1911年,大致为清末新政时期。这一阶段“教科书”一词在官方文牍中出现,但仍与其他近意词相混用,只是使用频率逐渐增加。
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指出,统一的“教科之书”是西洋学校教学的一大优点 。如果不做机械限定,刘坤一、张之洞的此奏折可以视为清政府官方第一次使用“教科书”这个概念。同年5月,罗振玉在其主办的《教育世界》第一号中声明,该杂志将介绍日本各种“教科书”;在后续刊发的文章中,他大量译介日本各级学校令,介绍日本小学校“教科所用图书”和中学校“教科书”;此年末的《教育世界》连续登载了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夏谐复的长文,文章明确定义:“教科者,教育之标目;教科图书者,教育之材料” 。这可以代表中国人对于“教科书”的近代意义的理解。
戊戌以后,改革教育的呼声日见高涨,更多人注意到了改良教科书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中,“课本”、“学堂功课书”和“教科书”是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张謇因清政府的“新政”号召而上《变法平议》,他提出设文部负责编纂诸事,检查“授课之书”,小学堂、中学堂等次第编辑“课本”,并允许私家编拟“课程之书” 。当年两广总督陶模和广东巡抚德寿向清政府上奏提议“学中颁发应用书籍” 。罗振玉在1902年3月的《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使用了“课书”这一概念,并认为“课书”当分三类:师范用书(合行政法、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数者),教科书和参考书 。显然,从罗振玉的这个概念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其含义仅指学生用书而言,相当于通俗化的“课本”。这说明在20世纪初年,中国人还没有形成确定统一的“教科书”概念。
随着时间推移,表达“教科书”含义的词语在数量上逐渐减少,“教科书”与“课本”这两个概念呈现出并行同一的趋势。1902年5月,李宗棠在考察日本学校的日记中介绍日本的“教科书” 。7月,贵州巡抚邓华熙拟在贵州设立大学堂,在暂定章程中指出应由国家编订颁发“学堂功课” 。8月,袁世凯在拟定的直隶师范学堂和中学堂章程中使用了“教科书”和“教科图书”两词 。此年张之洞在上清政府的奏折以及写给学务大臣张冶秋的信中,全部使用“教科书”与“课本”二词 。刘坤一此年在向清政府汇报江南学堂情形的奏折中,全部使用了“课本”这个词 。这一年,梁启超在其《教育政策私议》中仅使用“教科书”一词。 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正式出台。在这份划时代的文件中,除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使用过一次“课本书”外,其余各级学堂章程均使用“课本”一词; 当年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则全部使用“课本”一词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一份比“壬寅学制”更全面、更具实践意义的文献。在它的各种学校章程之中,基本上只使用了“教科书”和“课本”二词,尤其在《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 。晚清学部在其设立前后的有关文牍中,亦多使用“教科书”与“课本”这两个词 。1906年,上海私塾改良会成立,其章程中亦只使用“教科书”与“学堂课本”这两个概念。这些文献中的名词使用情况表明,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一词已经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初步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和成立于1902年的文明书局,作为20世纪初中国两大书业巨擘,都是以编印出版教科书兴起并以之为重头戏的。它们编印出版了大量冠以“教科书”之名的学校用书。比如1903年以后,文明书局编印有诸如《蒙学体操教科书》等冠以“蒙学”二字的多种教科书;商务出版社编印出版有《数学教科书》、《矿质教科书》、《格致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最新教科书”等一批教科书。此时期纷呈出现的其他民间出版机构亦多从事于教科书的编印出版活动。例如1901年,中西译社编译、谢洪赉订定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化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3年,湖北中学教科书社纂译日人所著的《正则英文教科书》,由上海昌明公司发行;同年,上海作新社编印刊行有《中学教科书新编动物学》,宁波的新学会社编辑自刊了《理化博物教科书》,亚泉学馆编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4年,算学研究会编纂的《最新平面几何学教科书》由上海昌明公司出版;1905年,上海广智书局编辑出版有《中学用世界地理教课参考书》;1906年,上海会文编译社编辑印行了《初等女子修身教科书》和《教授书》,长沙三益社印行过《最近普通化学教科书》;1907年,上海的太谷求是书室编辑印行了《新译中等几何教科书》等等。如此繁琐地罗列众多例证是要说明,20世纪初,“教科书”在中国已不仅是名词的引进,中国人已经在这个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实绩。而且这一时期学部设立,作为清政府的官方机构,学部对于编辑审定“教科书”给予特别关注。在其奏折中,学部建议清政府确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以此原则指导教科书的编纂。此后学部还设立专门机构,筹划推出“部编教科书”。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虽然各种文献中,“教课书”和其他词语共用,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获得认可。
还应指出,从1901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大量汉译日本教科书。在这些翻译的著作中,基本都使用“教科书”字样。汉译日本教科书在时间上晚于西方传教士传输的教科书,也晚于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中使用“教科书”一词,笔者尚未发现证据能够证明“教科书”一词来自日本这一猜测。
第三个阶段是民国以后。在这个阶段里,“教科书”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成为官私行文中最经常使用的名词,“功课书”之类的概念不再有人使用,“课本”之类的概念使用减少,而且逐渐含有了非正式、口语化的使用意义。民国各种政府文件基本统一使用“教科书”这个概念,民间也同时接受其为正式用语。此后,“教科书”一直作为正式的通行用词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用户评价
评价二 阅读这本书的体验,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作者巧妙地将“教科书”这一看似静态的学术载体,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一宏大而动态的历史进程相结合,这种跨界叙事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些曾经印刻在泛黄纸页上的文字,是如何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成为塑造民族精神、引领社会思潮的关键力量。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探讨不同时期教科书的内容演变,例如,在晚清时期,教科书是如何开始引入西方科学知识和政治理念的?又或者,在民国时期,教科书在国民教育的推广和民族主义的构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分析教科书与社会精英、政治势力、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教科书引领了文化转型,还是文化转型反过来影响了教科书的内容编撰?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对于理解历史的复杂性至关重要。我设想,书中会引用大量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教材、教育政策、以及学者的论述,来支撑其观点。我希望这些史料能够生动而详实,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亲眼见证文化转型的阵痛与新生。总而言之,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让我能够从“教科书”这一独特的切入点,深入理解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从而获得一种更为全面和深刻的历史认识。
评分评价三 这本书的标题“建造常识”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它暗示了一种主动建构的过程,而非被动接受。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常识”正在被颠覆,新的“常识”也在被小心翼翼地建造。而教科书,作为教育的根本,无疑是这场“建造”工程的核心工具。我十分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以何种方式,被编撰进教科书中,从而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接受的“常识”?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新概念,是关于科学技术的新知识,还是关于社会组织的新规范?我期望作者能够深入挖掘这些教科书的内容细节,分析其背后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例如,在科学教育方面,教科书是如何介绍进化论、牛顿力学等概念的?在人文教育方面,教科书又是如何解读历史、塑造爱国情怀的?我更希望看到,作者能够将教科书的内容,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变革联系起来,展现教科书在其中扮演的催化剂或引导者的角色。比如,辛亥革命后,教科书的内容是如何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格局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教科书又是否受到了白话文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近代中国在思想启蒙、文化重塑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教科书所承担的独特而重要的使命。
评分评价九 “建造常识”——仅仅是这四个字,就足以引发我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无限遐想。一个古老的国度,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不得不审视自身,学习新知,并尝试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而教科书,作为教育的载体,无疑是这场“建造”工程的核心。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把精密的解剖刀,剖析近代中国教科书的“骨骼”与“血肉”。也就是说,它不仅仅要介绍教科书的内容,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政治诉求以及文化意图。 我对教科书的“形式”和“内容”都充满好奇。在形式上,它是否经历了从古籍装帧到现代印刷的转变?在内容上,又是如何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逐步转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新的政治理念的?我期望作者能够提供具体的例子,例如,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一本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解读中国古代史的?一本地理教科书又是如何描绘世界的?我希望通过这些具体的文本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教科书是如何在那个时代,扮演着“启蒙者”、“引导者”甚至“塑形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揭示,在教科书的“建造”过程中,是否存在着不同派别、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和争夺。例如,激进的改革派与保守的守旧派,他们各自的教育理念是如何体现在教科书中的?我期待这是一本能够让我深刻理解,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无数次的探索、尝试和调整,而教科书正是这场宏大转型中最生动、最直接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评分评价十 这本书的书名“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引子,让我对近代中国在剧烈变革时期,知识传播与文化塑造的复杂过程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我想,这本书的核心在于“建造”。在那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年代,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正在被动摇,新的思想和观念如同新生儿般呱呱坠地,需要被悉心呵护,并被赋予“常识”的地位,才能在社会上生根发芽。而教科书,无疑是承担这一“建造”重任的最重要媒介。我期待书中能够详细阐述,近代中国的教科书,是如何在吸收西方先进知识、批判传统文化弊端、以及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宏大叙事中,一步步完成其内容的建构和更新的。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教科书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呈现方式。比如,在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在科学教科书中,又是如何引入和传播西方科学理论,以期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对大量一手史料,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教科书文本的深入分析,来展现教科书在文化转型中的具体作用。这不仅仅是对知识内容的梳理,更是一种对思想的追踪,一种对价值的解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揭示,教科书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方向和进程。
评分评价四 当我看到“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个组合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无数个问号。教科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规范而理性的知识传递工具,但在近代中国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它们究竟扮演了怎样复杂的角色?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教科书的“变”与“不变”。“变”在于,它们如何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转向西学东渐,如何从帝王将相的歌颂转向民族国家的新叙事;“不变”在于,它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儒家文化的某些价值,或者在新的知识体系中,依然留有传统的痕迹?我尤其想了解,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教科书的内容是如何被争夺和改造的。例如,清末的改革派,民国的北洋政府,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他们各自的教育理念和政治诉求,是如何体现在当时的教科书中的?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详实的案例分析,比如对比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教科书,来展现这种变化。此外,我还会关注教科书的编撰者和使用者。这些教材是哪些人在编写?他们的思想背景是怎样的?而那些接受这些教科书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被影响和塑造的?这本书能否帮助我理解,正是通过这些看似平凡的教科书,一个古老的国家是如何试图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为下一代“建造”起一套全新的认知体系和文化认同?
评分评价一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给我一种朴实而又不失厚重的质感,深褐色的封底搭配烫金的标题,仿佛诉说着历史的沉淀。在翻开第一页之前,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些曾经陪伴我走过求学生涯的教科书,它们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时代印记的留存。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那些我依稀记得的插图,它们在我的记忆深处激起了涟漪。我希望作者能够带领我重温那些年的课堂时光,不仅仅是知识本身的记忆,更是当时学习的氛围,老师的教导,同学的讨论。更进一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理解这些教科书是如何孕育出我今日的思维方式,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然,我更渴望的是,能够从中看到一个更宏大的图景,那就是这些教科书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扮演角色的。是它们在传递新思想,是它们在挑战旧观念,还是它们在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民认同?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揭示这些教科书背后隐藏的复杂而迷人的故事,让我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曾经的“常识”,去理解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重量和意义。我期待的不仅仅是信息量的增长,更是一种智识上的启发,一种对文化变迁过程的深刻洞察,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从何而来。
评分评价五 这本书的标题,如同一个精心设计的谜语,让我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建造常识”——这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主动性和目的性。在近代中国,一个历经千年王朝更迭,如今又面临西方冲击的时代,知识的传递和观念的塑造,无疑是构建新国家、新社会的基石。而教科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其所承载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一代人的思想形成,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走向。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解析,近代中国的教科书是如何在“中体西用”的思潮下,在“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中,在“思想启蒙”的呼唤下,逐步完成其内容上的转型和功能上的演变的。 我特别好奇,在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讲述中国的过去,尤其是如何解释导致近代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构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在语文教科书中,又是否出现了新的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以取代旧的文言文传统?在科学教科书中,那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是如何被引入和解读的?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文本,挖掘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潜在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我期望作者能够将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与当时中国社会上层的教育政策、知识分子的论争、以及民间社会的反应联系起来,勾勒出一幅立体而真实的文化转型图景。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能理解,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在近代中国是如何被创造、被传播、被接受,甚至是被争夺的。
评分评价八 这本书的标题“建造常识”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许多观念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常识”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经过漫长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过程而逐渐形成的。而近代中国,恰恰是这样一个“常识”被剧烈冲击、解构和重建的时代。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教科书扮演的“建造者”角色,是如何具体的。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价值的塑造,一种世界观的构建。我希望作者能够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的教科书,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是如何选择性地吸收、改造和融合的。例如,科学知识的引入,是否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科学的批判?政治思想的传播,又是如何重塑“国家”、“公民”等概念的?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在不同时期,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和内容侧重点有何不同。是民族主义的崛起,还是共产主义的传播,抑或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思潮是如何在教科书中留下痕迹的?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史料考证,为我呈现一幅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教科书内容演变的生动图景。更进一步,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今天的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承载着那些由近代教科书所“建造”的“常识”,以及这些“常识”又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评分评价六 初次接触这本书的书名,我便被其所蕴含的深度所吸引。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教育史或文化史的书,更像是一次对我们自身认知根源的探寻。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许多“常识”,并非天生如此,而是经过历史的筛选、塑造和灌输。而近代中国,正是一个“常识”被剧烈颠覆和重塑的关键时期。我迫切地想知道,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建造者”角色。 是哪些思想家、教育家,以及政治力量,共同参与了这场“建造”?他们是如何挑选内容,设计体系,以期达到其预期的教育目标?我期待书中能够展现不同时期教科书在知识体系上的差异,例如,晚清时期引进的西学知识,民国时期强调的民族精神,以及抗战时期注入的爱国主义宣传,这些内容是如何在教科书中体现出来的?我希望作者能够细致地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文本,不仅仅是其表面的知识内容,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逻辑。此外,我还关注教科书的“生命力”。这些教科书是如何进入学校,如何被教师教授,又如何被学生吸收的?学生们又是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常识”的?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那些曾经被视为“真理”的教科书内容,在时代变迁中是如何被接受、被质疑,甚至是被遗忘的?我期待这是一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教科书作为一种隐形而强大的文化力量的深刻解读。
评分评价七 当我看到“建造常识”这个词时,我的脑海中立即闪过一个画面:一群人在一堆原材料旁边,小心翼翼地用各种工具,试图搭建起一座全新的、坚固的建筑。而这本书所说的“原材料”,很可能就是各种新的思想、知识和观念,而“工具”,则指向了近代的教科书。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旧有的思想体系如同摇摇欲坠的旧建筑,亟需被更新、被重建。而教科书,作为最直接、最广泛的教育媒介,无疑承担起了“建造”新“常识”的重任。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这群“建造者”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是如何从西方汲取养分的,又是如何融合本土文化的?教科书的内容,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被调整和修改的?例如,在国民革命时期,教科书是如何强调“三民主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教科书又是如何激扬民族精神的?我更希望看到,作者能够深入分析教科书在具体学科上的呈现方式。比如,地理教科书是如何描绘中国的疆域和世界的?历史教科书又是如何讲述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和民族复兴之路的?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丰富的实例,让我能够清晰地看到,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父辈甚至爷爷辈课本里的文字和图画,是如何一步步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又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面貌。
评分在重印民国老课本的过程中,出版社常常望文生义,影印当年的公民课本或者常识课本。但是,标题中有“公民”和“常识”,未必就和公民常识有关,有时恰恰相反。1922年,修身科被公民科替代。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本来推行于广东的党化教育推向全国。随后,中小学教育的“公民科”逐渐被“党义科”代替。……1932年,公民课程恢复,内容暗度陈仓,党义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再随后,“公民”又被“社会”取代。这种语言的政治学,后来奥威尔在《1984》里有过论述,即“新话”。
评分~~~~~~~~~~~~~~~~~~~~
评分xinao?ideology?
评分有一些新意,可供参考~~
评分希望不要在瞎扯
评分xinao?ideology?
评分关于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论文。有研究兴趣的还是可以看看,想看故事的可以直接闪人了。
评分东西收到了,一如既往的好,活动很给力,尝试了一下,和介绍描述的完全一致,质量很好,正品无疑,使用效果也很不错,很满意!首先感谢快递员小哥的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在最快的时间里将东西完好无损地送到手上,辛苦了!京东自营的商品总让人很放心,值得信赖,无论是订单处理,服务态度,物流速度还是售后流程都让人非常满意,真正做到了一条龙服务,必须点个赞!希望京东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在未来越做越好,带给大家更好更棒的商品!五星好评!
评分关于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论文。有研究兴趣的还是可以看看,想看故事的可以直接闪人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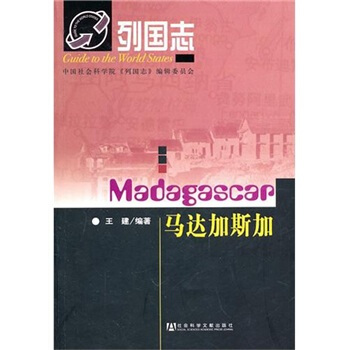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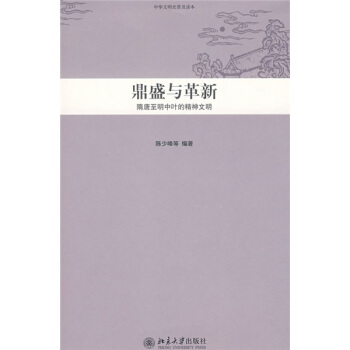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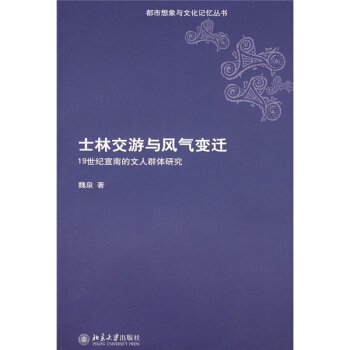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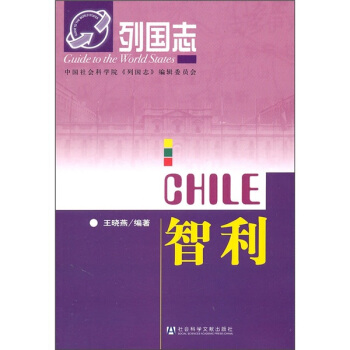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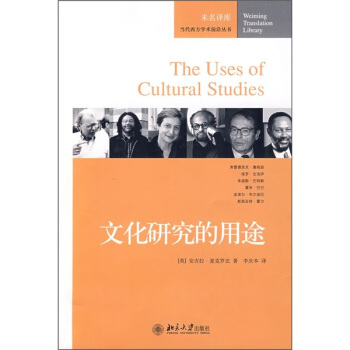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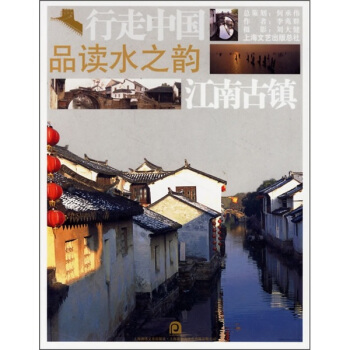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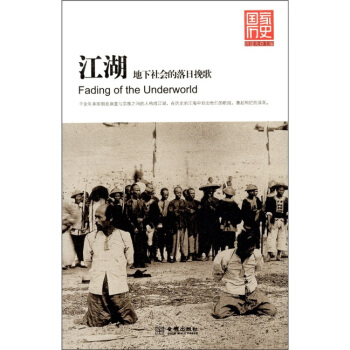


![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957422/64385184-7161-49c9-9002-a02a2aa1b6a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