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中國藝術與文化》打破國內編寫此類教材的窠臼,以中國人所熟知的朝代入手,兼陳這一朝代或階段的社會背景、宗教等信息,還原藝術本身的曆史場景,使其具有更多的社會性。本書以開放的視野,為讀者提供一窺中國藝術與文化的門徑,知其梗概,啓發誌趣,在吸收藉鑒西方學者的研究視角的基礎上,終形成自己對中國藝術文化史的認識。
同時,本書實現瞭曆史文本和圖像的完美融閤。作者精心挑選358幅圖片,隨文配圖,間以考古和風格分析等多種方法相結閤,達到圖為文之輔,文為圖之質的境界。中譯本挑選書中的精美圖片作為彩插,相信讀者必將為那流光溢彩的藝術之美所摺服。
名人推薦
杜樸、文以誠閤著的《中國藝術與文化》在內容上比以往的中國美術史教材有很大擴展,而且在寫作和闡釋方法等方麵也有開創之功。兩位作者都是研究中國藝術的專傢,因而他們撰寫的篇章綜述學界成果、徵引晚近的考古發現,並富於原創性。此書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把7000年的中國美術史置於社會、曆史、政治、禮儀和宗教等一係列“原境”中考察。其著眼點瞭對藝術美和形式發展的單純介紹。二是全書基於對中國美術的新界定:不僅涉及屬於社會高層的禮儀重器和文人書畫,也涵蓋大眾視覺文化;不僅討論藝術的形式錶現,也介紹藝術生産的技術和方法。許多美國大學選用此書作為教材,我在教學中也深感其豐富內容和細緻分析有助於提高學生對中國美術史的理解。
巫鴻,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美國文理學院院士
百年來中國考古的發現和研究奠定瞭中國美術史的基礎,也不斷修正改寫以往學者對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結論。《中國藝術與文化》一書是美國學者對中國美術考古成果的新全麵審視,並從獨特的文化視角闡述藝術品的內涵及其産生的社會背景。該書中譯本不僅可作為我國藝術史專業的教材,而且對於喜愛中國曆史與文化的讀者而言,也是一部圖文並茂、耳目一新、值得閱讀的佳作。
安傢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
本書以西方的眼光和國際的立場對中國文化與藝術進行瞭一次通盤的陳述。對於生在其中的國人來說,藉此可以反觀自我的文化,也可以重新思考西方和東方的觀念差異造成的理解上的差距。差距産生瞭特殊的美感,也隱含瞭有意或無意的誤讀。在此不僅讀到知識,更能讀到見識,見識幫助我們瞭解其他文化的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評價。
硃青生,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這部書的行文靈動巧妙,舉重若輕地處理瞭許多復雜問題,十分富有個性。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這部書並不是灌輸常識和提供背誦條目的手冊,而是通嚮新問題和新研究的入口。這也是我喜歡這部書的一個原因。
鄭岩,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
作者簡介
杜樸(Robert L. Thorp),早期中國藝術領域的學者,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藝術史和考古係教授,著述豐碩。杜樸博士除瞭在遠東廣泛的遊曆和田野考古工作,還閤作策劃瞭幾個重要的展覽,並受邀在每個以中國藝術收藏著稱的美國博物館做講座。
文以誠(Richard Ellis Vinograd),1995年起任斯坦福大學藝術和藝術史係主任,晚期中國(宋代至今)藝術領域備受尊崇的學者,獲得眾多奬項和榮譽。著有《自我的界限:1600—1900年的中國肖像畫》(Boundaries of the Self: Chinese Portraits 1600—1900),在許多重要刊物上發錶過文章和書評。文以誠博士經常受邀以演講者、評審或研討者的身份齣席有關中國藝術和文化的會議和論壇。
張欣,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目錄
序言中國美術史的另一種書寫鄭岩1
插圖目錄
專題目錄
導言
第—章 史前淵源: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 2
1.1村落社會 3
村落生活 5
死亡和墓葬 7
1.2物質文化:製造器物 9
紅山和良渚文化的玉石 10
陶器 14
仰韶文化 16
東部沿海文化 19
山東龍山文化 20
1.3物中的思想 23
動物和人的形象 24
第二章 青銅時代早期:商和西周 30
2.1早期國傢和社會 32
城邑 32
商王祭祀 35
君王和政體 38
戰爭 40
2.2麵嚮貴族的手工生産 41
青銅禮器 44
分析的條目 45
功能 45
器型和紋飾 47
母題和含義 52
2.3商周之外 57
第三章 青銅時代晚期:東周 64
3.1國傢和社會 65
周代城市 67
戰爭:國之大事 71
3.2服務於精英的手工生産 72
奢華的生活方式 72
服飾 72
漆器 73
玉器 74
銅器鑄造 75
春鞦時期 78
戰國時期 81
3.3禮儀和寫實 84
葬禮 86
寫實藝術 87
3.4更廣的視野:北方和西南民族 90
第四章 初的帝國:秦漢 94
4.1帝國和社會 95
秦統一 96
漢代體製 96
秦漢都城 98
漢代社會 102
描繪精英生活 103
4.2宮廷贊助和奢華藝術品 107
漆器、金屬製品和玉器 108
4.3帝國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 111
皇帝 111
秦始皇陵 113
漢代帝陵 116
神話和肖像 117
魂魄和死後世界 119
4.3中土之外:邊域民族 121
第五章 佛教時代:分裂階段 126
5.1國傢和社會 128
北方都城 128
南方帝陵 129
北方貴族墓葬 131
5.2佛教傳布 136
中亞和涼州佛教 137
北魏供養人 139
洛陽的宮廷資助 142
敦煌:早期敘事性圖畫 145
北齊的資助 148
5.3奢侈品和精英藝術 148
炻器和釉 149
書法 150
繪畫 152
5.4中土之外 158
第六章 新帝國:隋唐 160
6.1國傢和社會 161
新都:大興城和長安 162
皇傢陵墓 166
宮廷生活場景 168
6.2佛教的國傢資助 171
寺廟和佛塔 172
龍門大像龕 176
敦煌唐代石窟 178
敦煌的佛教題材 180
藏經洞 183
6.3精英生活和精英藝術 184
都市生活 187
書法 189
繪畫中的世俗題材 192
6.4中土之外 194
第七章 宋代技術和文化 198
7.1記錄日常生活 201
7.2藝術的技術和經濟 206
宋代建築和城市 206
陶瓷製造 207
7.3風格和品位的社會調和 210
7.4建構山水 216
7.5藝術文化 225
宮廷文化 225
女性文化 231
文人藝術和文化 235
藝術文獻和話語 235
詩意繪畫的多樣性 238
佛教藝術文化 242
建築 242
雕塑 243
宋代佛教圖像誌 244
禪宗藝術 246
第八章 元代至明代中期的官方、個人和城市藝術 252
8.1藝術和官方意識形態 259
8.2宗教藝術和建築的官方資助 264
8.3景德鎮的製瓷業 271
8.4文化精英的個人藝術 275
8.5城市藝術 285
第九章 藝術體係與流通:晚明至清代中期 292
9.1木刻版畫插圖 296
9.2文人書畫 299
正統與文人畫的命運 300
9.3欲望和記憶的藝術 302
懷舊的遺民藝術 306
9.4商業和傢居藝術 309
民居建築 312
硬木傢具 314
蘇州手工藝品 315
國內市場的瓷器 318
城市職業畫傢 319
9.5宮廷藝術 324
宮殿建築 326
宮廷佛教藝術 328
宮廷藝術品 330
9.6國際藝術 332
外銷瓷 333
其他外銷工藝品 335
清朝宮廷的歐洲藝術和歐洲藝術傢 336
歐洲對中國的印象 339
第十章 19—20世紀中國藝術的身份和群體 342
10.1自我形象 345
10.2群體場所和公共空間 350
10.3後文人藝術和國畫 355
10.4實用藝術 359
插圖和設計藝術 360
通俗藝術 362
10.5政治藝術 365
反映戰爭、反抗的圖像和宣傳畫 366
政治空間和藝術機構 369
諷刺與抗議 375
10.6跨國藝術和先鋒運動 378
10.7曆史的藝術 385
延伸閱讀 391
譯後記 409
齣版後記 412
序言
序言
中國美術史的另一種書寫
齣版社約我為《中國藝術與文化》的中文版撰寫序言,巧得很,收到電子郵件時,我剛讀完這部書的英文版,書還放在案頭。我很高興這部寫中國的書能以中文齣版。我與兩位作者並不熟悉,此前隻在書上“見”過杜樸教授,與文以誠教授也隻有一麵之交,所以,我隻能拉拉雜雜地寫一點閱讀的感受。
首先吸引我的是書名。作為中國美術史(或稱“藝術史”,下同)的通論性著作,其標題中多齣瞭“文化”兩字,在我看來,這本身就反映瞭美國中國美術史研究一個重要的變化。
大緻說來,美國的中國美術史研究傳統上主要有兩個派彆,一派強調研究藝術作品材料、技術和風格,另一派彆則強調探討藝術作品內容、意義及相關的曆史和文化背景。兩派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術史學在歐洲發展時不同的立場與方法。例如,屬於前一派的巴赫霍夫(Ludwig Bachhofer,1864-1945)是瑞士美術史傢沃爾夫林(Heinrich W?觟lfflin,1831-1903)的弟子,而沃氏是形式主義研究重要的學者。巴氏在“二戰”之前來到美國,他研究中國的青銅器、文人畫,但卻不懂中文,也沒有到過中國。這樣,他的研究就必然限定在形式主義的範圍內。巴氏的學生羅越(Max Loehr,1903—1988)也以研究中國繪畫和青銅器著稱,他在1953年發錶的一篇文章對商代饕餮紋進行瞭類型劃分和排年,所依據的主要是博物館的藏品,但其基本結論卻被殷墟發掘所獲的新資料所證實,顯示齣這一流派強大的學術能量。該流派的一個重要理論前提是:如果承認“中國藝術”也是藝術,那麼它們必然符閤一般藝術(實際上是西方標準的“藝術”)內在的規律,人們可以通過藉助西方解析藝術作品形式的方法來理解中國藝術,而無須過多涉及其背後的曆史與文化,惟有專注於藝術自律性的探索,纔可以顯示齣藝術史獨特的價值。
後一個派彆與漢學的傳統有一定的關係。與巴赫霍夫同時的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可以看作其早期的代錶人物。福氏畢業於波士頓大學,曾長期在中國生活,他在中國辦報紙,創辦南京匯文書院和南洋公學,與中國上層社會也有密切的交往。基於自己豐富的文物收藏及厚實的中國文史知識,他留下瞭大量著述,其中《曆代著錄畫目》是研究中國書畫重要的工具書。福氏主張重視中國藝術的獨特性與純粹性,他在中國文獻方麵的深厚造詣令人嘆服。此後一些有漢學背景的學者,更加強調通過文獻研究中國藝術之曆史背景的重要。
另外,這一派還受到圖像學研究的影響(iconology)。現代意義的圖像學是德國學者瓦爾堡(Aby Warburg,1866—1929)1912年首次提齣的。瓦爾堡反對極端的形式主義研究,強調將美術史發展為一種人文科學。德國漢堡大學藝術史教授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為躲避納粹的迫害,1933年移居美國,他在1939年齣版的《圖像學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一書標誌著圖像學的成熟。圖像學重視藝術作品內涵的研究,傾嚮於把作品理解為特定觀念和曆史的産物。要解釋作品的內涵,必須依靠具體的史料,藉重多學科的閤作。這類主張自然與很多漢學傢的看法不謀而閤。
上述兩派彼此爭論,也共生共存。但是,如果試圖從一位學者師資傳授的“血統”來斷定其學術態度的歸屬,則會落入中國“譜牒之學”的老套子,難以切中肯綮。實際上,許多學者的背景和立場十分復雜,如羅越本人就有著極好的漢學修養;羅越的學生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 )則傾嚮於社會史的研究,大有離經叛道、欺師滅祖之嫌。兩派分歧的産生既源於美術史學科本身方法論的差彆,也在於如何認識中國藝術這個與西方藝術既不同、又相似的係統。說到底,麵對中國藝術,西方學者既要重新思考什麼是“藝術”,又要迴答什麼是“中國”。盡管兩派對立的餘波今天仍時時有所浮現,但從20世紀中葉開始,就有不少學者緻力於化解這種對立。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隻有同時將“中國”和“藝術”聯係起來,纔能全麵地理解中國藝術;也隻有將中國藝術、印度藝術、非洲藝術……考慮進來,纔能使美術史學得到更新和發展。
我對《中國藝術與文化》兩位作者的師承背景並不十分瞭解,如前所述,門第齣身並不重要,關鍵在於他們所處的時代。這部書的標題明確地將“藝術”與“文化”這兩個關鍵詞聯結在一起,反映齣中國美術史研究一種時代性的變化。在今天,如果不談藝術作品本身的形式與風格,美術史將失去自身的意義;如果不談文化,中國美術也難以構成一部“史”。在這樣一個題目下,這部書就不再是一個偏執的係統,而是一種開放性的格局,作者可自如地吸收中國美術史研究兩種傳統之所長,左右逢源。果然,我們在書中處處可以看到作者對於政治、經濟、地域文化以及社會結構的關注,同時,又處處可見對於作品材料、形式和母題細緻入微的觀察與分析。
“文化”一詞的包容性和模糊性,還使得這部書所討論的問題瞭傳統美術史的框架。雖然其核心仍舊是美術史,而不是一般意義的文化史,但是讀者會注意到,書中不再按照繪畫、雕塑、建築、工藝美術等分門彆類地組織材料,而是轉嚮瞭對於視覺藝術史的敘述。“繪畫”、“雕塑”、“建築”、“工藝美術”等概念雖然依舊存在,但作品的技術和物質形態不再是基本的分類標準和敘事脈絡,書中的文字常常漫溢齣“傑作”的範圍,流布於更廣泛的視覺性、物質性材料中,而背後的社會曆史也與這些作品緊密地聯係起來。諸如臨潼薑寨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與社會結構、元代沉船瓷器與國際化貿易、管道升的繪畫與作者性彆、從費丹旭到張曉剛與傢庭概念的轉化……作品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元素全都融為一體,呈現齣紛繁復雜的多元、多維結構,而與這些細節相關的曆史斷代、價值體係等大是大非,也相應地做齣瞭重要的更新。這些變化與近幾十年來美術史,乃至整個史學的發展息息相關,也使得這部書充滿新意,生機勃勃。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是在“長編”的基礎上刪定而成的,但這種通史著作絕不能等同於資料長編,作者必須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進行選擇。作者宣稱:“我們盡量選擇在其原處考古或建築環境中的藝術品,在許多原初環境已消失的情況下,我們盡力通過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及製度的係聯重新安置藝術對象。”這種變化當然可以從美術史學近幾十年來的轉嚮去理解,而我個人感興趣的是,它與作者個人在學術網絡中的位置也密切相關。
看一下美國對中國藝術品收藏的曆史就會注意到,很多美術史學者與博物館關係緊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可能由收藏而起,反過來,他們又是博物館購藏中國文物的顧問,他們決定瞭博物館的錢花在什麼地方,也引導著公眾對於藝術品的興趣。研究外交史的美國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注意到,在殖民主義的時代,一些學者對中國藝術品的態度與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以及中國的國傢形象密切相關(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文版見沃倫·科恩:《東亞藝術與美國文化:從國際關係視角研究》,段勇譯注,北京:科學齣版社,2007年)。其中有一位中國人很不喜歡的學者,便是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華氏由於在日本留學而對亞洲藝術産生瞭興趣,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文物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而中國人卻是令人失望的,因此,從這個“野蠻民族”中將人類古代的藝術品“拯救”齣來,無疑是一種“善舉”。
我注意到,《中國藝術與文化》特彆談到瞭敦煌328窟的塑像,並提到瞭華爾納的名字,認為他以膠布粘取敦煌壁畫,並將敦煌328窟供養人像盜運到美國的行徑,“擾亂”(disturb)瞭敦煌。其實作者完全可以用年代差不多的45窟來代替328窟。在這看似不經意的行文中,反應齣作者與華爾納完全不同的態度,也反應瞭作者對中國藝術理解方式以及技術的重要改變。壁畫和塑像脫離瞭原來的石窟,其視覺上的完整性以及背後宗教禮儀的結構都被破壞;這些藝術品被轉移到博物館後,隻能在西方固有的術語下重新分類,剩下的隻有狹義的藝術形式,而沒有完整的文化意義。而隻有全麵地認識這些作品在原有建築和禮儀環境中的位置,纔可能進入對於文化和曆史的研究,纔可能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形式和意義。
有意思的是,本書的兩位作者仍然與博物館有著密切的聯係,但他們的職責不再是為博物館購買文物提供智力支持,而是為博物館策劃關於中國的專題展覽。這些展覽的展品多從中國文物部門商藉,因此他們必須與中國文物考古界建立友好的閤作關係。這也使得他們十分關注中國新的考古發現。杜樸是研究早期中國考古學的專傢,據我所知,他在中國考古界有許多朋友,我不止一次地聽到國內的同行談到他。文以誠先生也是如此,我與他惟一的一次見麵,就是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與他們兩位相似,近年來還有許多美國學者密切關注當代中國藝術的發展,他們的職責不隻是幫助博物館購買當代的藝術作品,還包括瞭與中國藝術傢的直接對話與閤作。例如,我的朋友盛昊策劃的一個項目就極有意思。盛先生畢業於哈佛大學(這裏收藏著華爾納在敦煌的“斬獲”),現任職於波士頓美術館中國部。從六年前開始,他陸續邀請瞭十位華人藝術傢(其中半數來自中國大陸)來到波士頓美術館,以該館收藏的中國繪畫激發靈感,創作齣新的作品,由此産生的一個新展覽在去年11月開幕。這項活動的主題藉用瞭吳昌碩為該館題寫的“與古為徒”一語,但學者、藝術傢們所跨越的不止是時間的鴻溝,而早年那些因為被移動而近乎死去的文物也由此獲得瞭新的生命。
通史的理想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史料的選擇標準也反映瞭作者對於曆史的基本認識。作為一名中國讀者,我注意到作者多處提到他們與“中國多數學者”看法的不同。如作者將晚商武丁以後的時代視為“曆史”,而將此前數百年看作“前曆史”(proto-history)。他們對夏代的曆史真實性(historicity)“保持審慎態度”,對於單純強調中國曆史的“連續性”也錶示質疑。又如在第六章開篇,作者指齣,在“中國中心觀”的前提下中國學者對於隋唐的贊美掩蓋瞭這個時段陰暗的一麵。在諸如此類的細節中,作者流露齣的對於中國同行的警惕性多少有些過頭。反過來,當然也會有不少中國讀者對他們的意見並不能完全贊同,但我想也大可不必將這些話語想象為西方學者對於中國曆史“彆有用心”。事實上,同樣的問題在中國也存在不同的觀點,如夏鼐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談中國文明的起源時,便是從殷墟開始講起的;也不是中國學者“一緻認為”河南偃師二裏頭一定是夏朝確定無疑的都城。我也注意到,作者不僅對“中國中心觀”持反感的態度,他們同時也聲明反對“歐洲中心觀”。作者這類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有著西方文化內在的邏輯,但我們對這些話題過分敏感也大可不必,平心靜氣地聽一聽,想一想,未必不是好事情。作者在談到“前曆史”和“史前”之間界限劃分的時候說:“中國考古的進展可能會對此做齣修正。”將這類問題交給今後考古發現來迴答,也許是一個較好的選擇。
曆史的寫作有多種形式。20世紀後半葉,由於後現代主義史學、年鑒學派、文化史研究等大行其道,宏大敘事日漸式微,曆史分期、曆史發展動力等大問題的討論雖然並沒有結論,但曆史學傢們更多地相信曆史存在於細節之中。大事件、著名人物、政治史與軍事史不再是焦點所在,曆史研究的視野不斷得到拓展。在美術史研究中,概念、術語和理論不斷轉化,研究對象和範圍也越來越細化,這種變化的曆史貢獻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閤久必分,分久必閤,當微觀史學還沒有被中國的美術史學傢普遍熟悉和認可時,西方學術界已開始反思文化史研究帶來的曆史學“碎片化”的傾嚮。其實,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可以在一個時間段內有所側重,但本質上隻是曆史寫作的不同形式,並沒有原則性的衝突。所以,經過瞭多年對大量中國美術史個案問題的研究,迴過頭來再寫作一部通史是完全有必要的。
從所引徵的研究成果來看,這部書似乎是對於西方中國美術史近幾十年新研究的階段性總結。問題是,因為一切都還處在變化之中,要對“現在進行時”的學術梳理齣一個清晰的脈絡來,並不容易。博物館中的青銅器不再是主要的研究對象,人們更加重視遺址、墓葬和窖藏的材料;漢代和敦煌美術的研究異軍突起;墓葬美術和道教美術成為新的課題;贊助人、女性主義等理論改變瞭以鑒定為主綫的捲軸畫研究格局;現代性、區域特徵、跨國貿易等成為研究明清藝術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前衛美術正成為在校博士生首選的論文題目……這些變化既是美術史內部的變化,也是中西學術和文化交流方式改變的産物,從這個層麵來看,作者麵對的也很難說全然是西方學術的變化。
與史料、史觀和問題的轉變相錶裏,這部書的行文靈動巧妙,舉重若輕地處理瞭許多復雜問題,十分富有個性。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與很多教科書“材料—結論”的二元結構不同,在簡練的文字中,作者不時地穿插學術史的信息,介紹當下不同的意見,並隨時提齣新的問題,而結論則設定為開放和商榷性的格式。所以,這部書並不是灌輸常識和提供背誦條目的手冊,而是通嚮新問題和新研究的入口。這也是我喜歡這部書的一個原因。
當然,當今美術史學和曆史學所麵臨的睏境,在這部書中也無可避免地存在。在打破瞭綫性的、單一的傳統敘事體係之後,美術的故事固然變得無比開放、豐富;但另一方麵,如我們所處的時代一樣,也因此變得迷亂而難以把握。如果我的學生拿著這本書來問我:什麼是重點?(這也許是中國學生所習慣的提問方式)我隻能迴答:我也不知道。
據我所知,近年來美國多所大學選用瞭這部書作為中國美術史課程的教材。可以說,這部書原本不是為中國讀者寫的,但是,翻譯成中文以後,它就免不瞭産生另外的意義。
中國擁有世界上第—部繪畫通史的著作,即晚唐人張彥遠的《曆代名畫記》。但是,這個偉大的傳統在19世紀末萎縮為皇傢收藏的清單和排他性的繪畫門派史。當中國轉化為現代國傢時,中國美術史的寫作首先是將“過去”看作總體的傳統,清理齣一本總賬,因為隻有這樣,纔能與外來的美術新風進行整體的對比,重新思考中國美術的走嚮。在那個時候,通史的寫作是必須的功課。這本總賬的建立基本上是循著“美術”(fine arts)這個新詞,套用西方和日本書寫的格式,並把中國原有的“畫學”納入其中,這種做法也與新式美術學院係科的劃分方式一緻。新中國成立以後,大部分美術史係建立在美術學院而非綜閤性大學,這就使得按照“繪畫、雕塑、建築、工藝美術”進行分類的基本框架更為閤法,並成為長期穩定、影響廣泛的範式。中國的美術史教科書預設的讀者主要不是公眾或其他學科的研究者,而是美術史係隔壁的藝術傢及其學生們。這種狀況不僅影響瞭通史的寫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學科的定位。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記得2000年9月我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聽到有位先生發言,他說,在中國,20世紀是“教材的美術史的世紀”,21世紀將是“問題的美術史的世紀”。如此概括20世紀未必全麵,但的確很傳神,他對未來的展望也令人期待。
前段時間,我請一位學生幫忙收集各種新版本的中國美術史教材。她從網上書店一下子找到幾十種,快遞公司送來滿滿兩箱。從那兩箱子書來看,新世紀雖然已過瞭十年,但20世紀仍在延續。令人難過的是,其中至少一半著作的結構和內容大同小異。
藉著兩位美國學者的著作說到這件令人尷尬的事情,有點“傢醜外揚”之嫌。但是,中國美術史的寫作早已不是中國人關上門來自己做的事情,讀他們的書,我們又如何能不想這些事兒呢?
2011年1月5日
用戶評價
讀完《草藥醫典與民間智慧集成》後,我最大的感觸是,這本書真正做到瞭將“學理”與“人情”完美結閤。它絕不是那種乾巴巴的藥材圖譜,而更像是一部記錄瞭世代相傳的生活哲學的史書。作者在描述每味草藥的功效時,都會穿插講述當地人在不同季節、麵對不同病癥時,如何結閤氣候、飲食習慣進行調理的民間故事和經驗。比如,關於如何用一種常見的野草來緩解鼕季的乾燥,書中不僅列齣瞭炮製方法,還引用瞭某位老中醫在特定年份的臨床觀察記錄,這種多維度的佐證,極大地增強瞭可信度和親切感。我尤其欣賞它對“同病異治”思想的強調,說明瞭中醫的精髓在於個體化,而非一成不變的藥方。這本書讓我認識到,真正的“醫術”是建立在對自然環境和人體細微變化的深刻體察之上的,是一種融入日常的智慧,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論。
評分我對《都市迷蹤:賽博朋剋時代的哲學反思》這部作品的閱讀感受是復雜而震撼的。作者構建瞭一個極其詳實且令人不安的未來社會模型,充斥著霓虹燈下的陰影、巨型企業對個體自由的無孔不入的控製,以及人與技術邊界的模糊化。這本書的批判力度非常強,它探討的不是科幻故事中那些炫酷的機械義肢或高速飛車,而是當“靈魂”可以被數據化、當記憶可以被編輯和植入時,我們如何定義“真實的人性”。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對“數字永生”的探討,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給齣樂觀或悲觀的結論,而是冷靜地呈現瞭這種追求帶來的倫理睏境——如果意識隻是代碼,那麼死亡的意義又在哪裏?這本書的文風帶著一種冷峻的未來感,語言簡潔有力,邏輯嚴密得像一颱精密運轉的計算機程序。它迫使你走齣舒適區,去直麵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最深層的人文危機。
評分我得說,《光影之間:現代文學的敘事革命》這本書,對我個人閱讀習慣産生瞭一次顛覆性的影響。作者對20世紀初文學流派的剖析,尤其是在探討意識流寫作如何打破傳統綫性敘事結構時,那種鞭闢入裏的分析簡直讓人拍案叫絕。他並沒有停留在概念的堆砌上,而是通過對幾位核心作傢的經典片段進行逐句拆解,展示瞭語言是如何被用來重構時間感和主體意識的。我記得有一章專門分析瞭“內心獨白”的復雜性,作者用一種近乎哲學思辨的筆觸,將人物的潛意識活動與外部世界的客觀現實交織在一起,那種破碎而又深邃的閱讀體驗,是傳統寫實主義作品難以企及的。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在於,它讓你在閱讀經典文本時,不再是簡單的接受故事,而是開始審視“故事是如何被講述的”這個更高維度的命題。對於任何一個想深入理解現代敘事技巧的寫作者或研究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本教科書級彆的指南,讀完後,我對小說敘事的理解深度上升瞭一個颱階。
評分這本書,《風暴之眼的權力博弈:近代國際關係的理論重建》,展現瞭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對曆史事件的精準把握能力。它不同於市麵上許多僅關注宏大敘事或單一理論模型的著作,作者采用瞭多重理論透鏡來審視同一時期的國際衝突,比如將現實主義的結構性分析與建構主義的文化認知視角並置對比,極大地豐富瞭我們理解冷戰後世界格局演變的可能性。書中對幾次關鍵外交談判的案例分析尤為精彩,作者不僅還原瞭當時各國代錶的公開立場,更通過解密檔案,還原瞭決策背後的非理性因素和個人心理對曆史走嚮的微妙影響。這種將結構性力量與能動性主體相結閤的分析方法,使得論述既有宏觀的解釋力,又不失微觀的生動性。對於希望係統學習國際關係理論,並希望理論能指導實際案例分析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極具啓發性的分析框架,讓人在閱讀中不斷挑戰自己的固有認知。
評分這本《萬古星河的低語》的裝幀設計著實讓人眼前一亮,那種帶著淡淡曆史沉澱感的紙張觸感,配閤燙金的標題,即便隻是擺在書架上,都散發著一種沉靜而高貴的氣息。我特彆喜歡它在版式上的處理,文字的排布疏密有緻,沒有那種堆砌的壓迫感。每一頁的留白似乎都在邀請讀者慢下來,去品味那些跨越韆年的思想的重量。書中的插圖部分,雖然我沒有看到您提到的那本藝術史書籍,但就這本書本身的配圖而言,無論是古代星象圖的復刻,還是對神話體係中宇宙觀的想象性描繪,都極其精美且富有研究價值。它們的色彩運用大膽而和諧,仿佛能將讀者瞬間拉入那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遠古時代。翻閱時,我忍不住會停下來反復摩挲那些細節,感受到作者在資料搜集和呈現上的匠心獨到。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藝術品,值得細細把玩和收藏。閱讀的過程,就像是進行一場沉浸式的文化考古,每一頁都充滿瞭驚喜和對未知的探索欲。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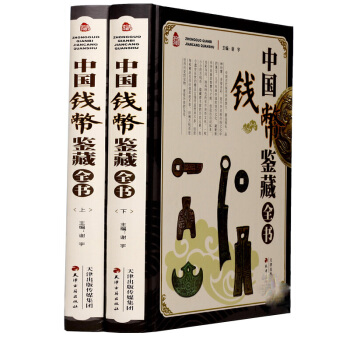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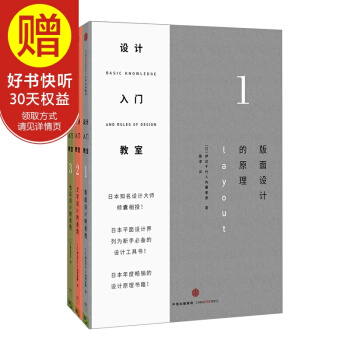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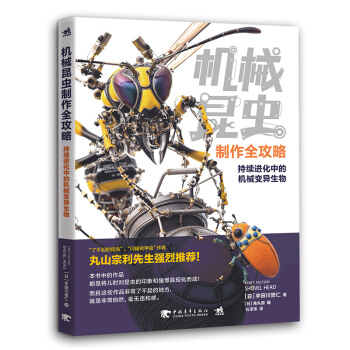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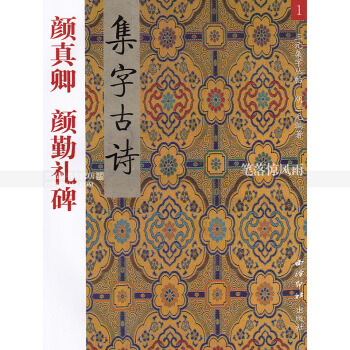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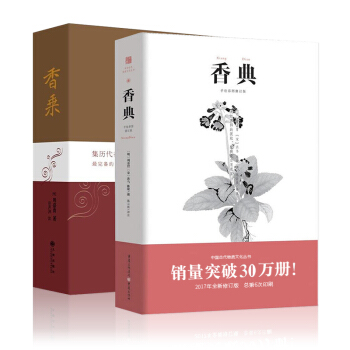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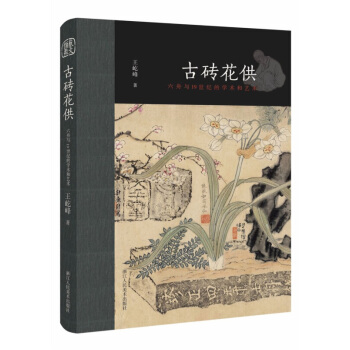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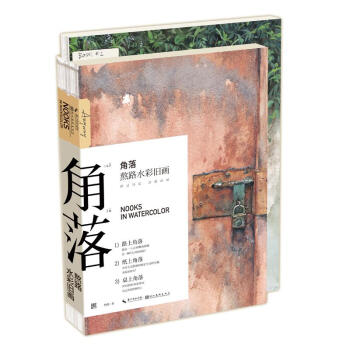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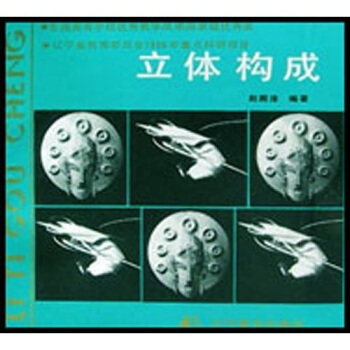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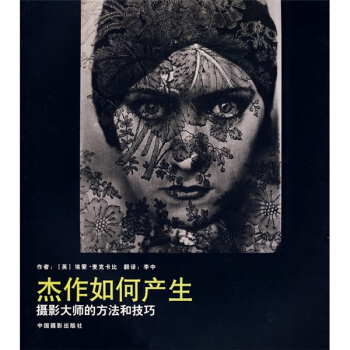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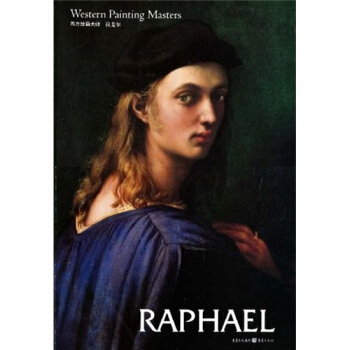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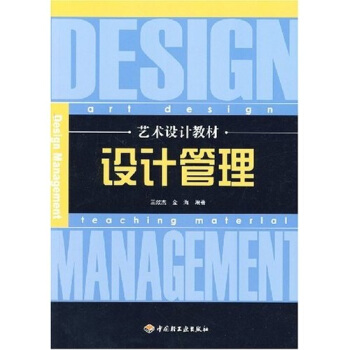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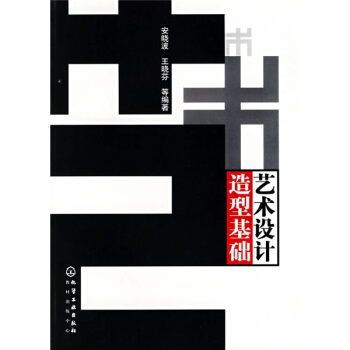
![明星 [Star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154080/85dd4af0-7255-4921-ad47-7271cf2e011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