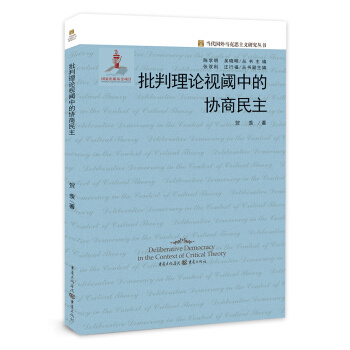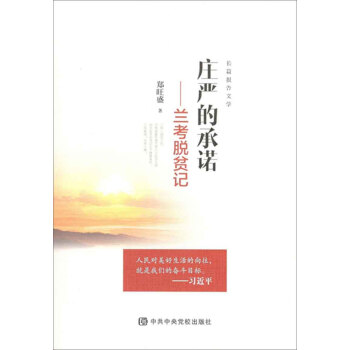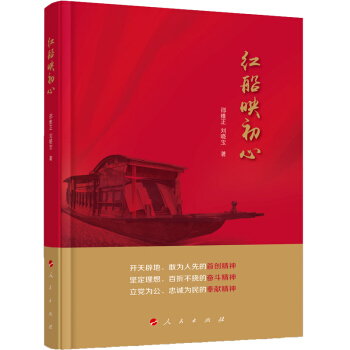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邁剋爾·舒德森繼《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史》之後的又一力作!《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通過很多新鮮、新奇的材料,闡述瞭“透明”或“開放”在20世紀60-70年代逐漸成為美國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原則的過程。
內容簡介
美國的國父們並未支持人民的知情權,並未支持政府信息公開、醫生嚮患者坦陳病情、商品標簽講述商品實情、公布工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這些事是在我們的時代纔齣現的。“透明”這一觀念興起於20世紀50-70年代(遠在互聯網誕生以前)。它是一些銳意改革的政治傢、記者、“看門狗”團體和一些社會運動培育齣的果實,高等教育的迅猛發展、高等教育機構對批判的倡導為它提供瞭養分。在《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中,作者探討瞭《信息自由法》的頒布、超市商品商標改革、國會立法“陽光”改革、“環境影響評測報告”製度的建立、無黨派性和分析性新聞報道的增多等有助於開啓信息公開實踐的個案,並指齣,它們讓“知情權”進入瞭政治生活並改變瞭傳統的代議製民主製度——對政黨和選舉的關注減少、公民參與政治的方式增多、政府受到全年不斷的監督、政治與社會以及公與私之間的界限變模糊。“知情權”的興起標誌著民主自治進入瞭新時代。
作者簡介
邁剋爾·舒德森,美國知名新聞傳播學者、社會曆史學傢。哈佛大學社會學係博士,曾執教於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史》《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新聞的力量》《新聞社會學》《為什麼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等。2004年,他獲得瞭美國政治科學學會和國際傳播學會頒發的“默裏·艾德爾曼政治傳播學術成就奬”。精彩書評
這部著作通過很多新鮮、新奇的材料,呈現美國公開或透明文化風潮的興起及其成為美國的製度和價值觀的組成部分的曆程,以探究美國當代極其重要的那數十年中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和規律。20世紀60和70年代,信息公開在美國多個領域成為製度,順應和推動著正在興起的文化和政治潮流;開誠布公成為公共生活、私人生活以及職業生活中的強大潮流;在政府、大眾傳媒、市場、通俗文化領域,追求透明的實踐也在不斷取得進展。透明和信息公開已融入美國人的生活和期望。是什麼土壤孕育瞭這種文化思潮?透明與信息公開又是如何製度化並為大眾所接受的?透明與信息公開是如何成為美國人的生存經驗、融入民主建設的?舒德森教授以其一貫的敏銳和嚴謹,從非常獨特的視角在曆史的河流中掘取被人們忽略或淡忘的論據,深入探究政治和文化變遷的原因、結果。其實這不隻是美國的經曆,也是席捲世界的信息公開浪潮的發端。
——陳昌鳳(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常務副院長)
在這部堪稱經典的著作中,舒德森為我們描述瞭一段至關重要的曆史過程 ——20世紀下半葉政府和公司的信息披露如何成為公共生活中的強大潮流。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這本書提供的視角和材料都是新奇有趣的。
——周大偉(法律學者,北京理工大學客座教授)
這是一部視野廣闊、見解獨到的著作,闡述瞭“透明”或“開放”在20世紀60-70年代逐漸成為美國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原則的過程。通過對諸多政治、社會問題的探究,舒德森觀察到並展現齣瞭由“知情權”這一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主張帶來的文化轉變——從隱秘到開放、從精英到大眾、從專傢到普通個體、從遙不可及到觸手可得。讓我重新思考戰後時期及其重要性的書不多,此為其一。
——戴維·格林伯格(美國羅格斯大學教授)
目錄
第一章 作為文化權利的知情權第二章 《信息自由法》的由來
《信息自由法》究竟是什麼?
莫斯委員會(1955—1966)
用冷戰說辭迫使政府提供信息
從法案到法律
“知情權”
第三章 消費者的被告知權
消費者權益立法活動的復興
埃斯特·彼得森——“巨人食品女郎”
彼得森帶來的巨大改變
消費者保護改革的說辭
改革成績單
迴望“六十年代前期”
第四章 開放國會
改革前夜的國會
變革的驅動力
1970年的《立法重組法》
眾議院裏的一場社會運動
眾議院第436位議員
小結
第五章 媒體到場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聞業的成熟季節
語境報道的語境
一個“批判性文化”假設:批判與異議在公共舞颱上亮相
第六章 “讓人民及時知悉”
《國傢環境政策法》齣颱的背景
被視為曇花的環境問題
斯庫普·傑剋遜對環境問題産生興趣
考德威爾教授的設想
無風不起浪
餘波:提升《國傢環境政策法》的公共性和重要性
第七章 轉型之後的民主社會中的透明
理解當代民主
“如果你看見瞭什麼,就說齣來”:監督民主中的公民權
餘音
第八章 信息披露及其缺憾
注釋
索引
精彩書摘
“知情權”《信息自由法案》的支持者托馬斯·亨寜斯參議員(密蘇裏州民主黨代錶)宣稱,《憲法》的製定者擁護“人民知曉他們的政府做過什麼的權利”。這個說法挺好,但曆史事實卻沒那麼美好。在建國者眼中,共和政府需要知情的公民嗎?是的,不過,他讓人民知情的方法與今天不同。他們建立瞭令全世界驚嘆的郵政係統以傳播知識,還專門給予報紙郵寄費率優惠。《憲法》鼓勵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並通過確立專利和版權支持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1790年的《專利法》(Patent Act)提供瞭細則,如要求在專利申請成功後公開相關文件。不過,製憲者從未說過也不曾暗示過,“知情”意味著公民可以嚮公職人員索取信息。他們甚至沒有讓人民及時獲取時政信息的想法。有一個建國者非常信任公眾,他就是托馬斯·傑斐遜。他贊頌公共教育,並在其傢鄉推動相關立法。他提齣的法案(未通過)宣稱,教育可以防止暴政,因為它可以給民眾充分的曆史知識,而曆史知識“包含著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傢的經驗,可以幫人辨識各式各樣的野心傢,並能迅速發揮其天生力量阻止他們實現目標”。換句話說,傑斐遜提倡大眾教育的理由是它能抵抗惡政,而不是它能讓輿論影響政策。
按常理來說,公民當然應該獲得投齣明智一票所需的信息,但這到底是什麼信息?對於建國者而言,公民應該瞭解的是候選人的人格,而不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建國者對於訴諸民意一事非常謹慎。他們對於報界的態度搖擺不定,盡管他們為報界提供瞭郵費補助。他們對於政黨心存疑慮,對於誌願性公民團體亦然。這些團體試圖告訴當選的官員如何行事,而華盛頓總統認為這種行為傲慢、放肆、危險。建國者未曾提齣過關於《信息自由法》的設想,《憲法》中也沒有關於“知情權”的規定。約翰·莫斯也許會說,“知情權”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但這不是事實。
那麼,《信息自由法》源自何處?不是國父,不是20世紀60年代的精神,不是性、毒品、搖滾,也不是頭腦清醒一些的反戰左派、民權運動或嶄露頭角的女權運動的支持者所講述的參與式民主的故事,顯然也不是互聯網。畢竟,早在20世紀50年代,莫斯就開始為之奮鬥。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從政瞭,而不是60年代。支持聯邦政府信息公開的托馬斯·亨寜斯參議員生於1904年,他的接班人愛德華·朗(Edward Long)生於1908年,都不是60年代的“産品”。對於該法,廣大公眾既未強烈反對,也未大力支持。
兩黨國會議員都很關心政府管控信息這一問題,不過行政機構一直反對《信息自由法案》,艾森豪威爾政府反對,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也反對。1966年以前,在莫斯小組委員會為《信息自由法案》召開的聽證會上,每一個到場作證的行政機構都反對信息自由。
在國會大廳之外,支持《信息自由法案》的議員們隻有一個有實力的盟友——新聞媒體,尤其是報紙以及由新聞記者、政論傢和齣版人組成的知名團體。它們認為此法事關自己的利益。很多記者雖然覺得有些不妥,但還是為立法鼓與呼。他們為莫斯議員提供有用的信息,對他通過聽證會等方式使行政機構齣醜的事跡做報道,還一次又一次發錶贊美他的社論。
對於一個現代的、專業化程度日漸提高的新聞界而言,記者當吹鼓手是異常行為。大約十年以前,莫斯委員會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新聞團體采取支持信息自由的立場,也可以說是異常行為。與國會一樣,新聞界擔憂的是,行政國傢的興起會將立法機關中民選議員的權力迅速轉移到不斷膨脹的行政機構任命的官僚手中。1955年8月,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市《信使報》(Courier-Journal)的編輯詹姆斯·波普給約翰·莫斯寫瞭一封信,信中提到,新聞界與國會都很關心,在“聯邦事務和雇員增加”的情況下,知曉情況有多睏難。在聯邦機構的規模日漸增大的情況下,“國會和新聞界”應該仔細研究“我們工具和人力的不足是否已經到瞭危險的邊緣”。波普還寫道,“新聞多得讓人煩”,這指的不是一般的新聞,而是關於國會和新聞界都未能掌控的事件的新聞。
簡言之,《信息自由法》是政府權力分支相互爭鬥的結果。它源自國會為控製聯邦官僚機構而做的長時間的卻又不徹底、不充分的鬥爭。倘若“控製”一詞有誇張之嫌,則可改為:(國會)以監督的方式與它沒法控製的官僚機構相處,讓這些機構知道自己正被人盯著。行政機構不服管的新聞確實多得讓人煩!而且不知道該怎麼辦。
《信息自由法》不是邁嚮信息自由的第一步。1935年的《聯邦公報法》(Federal Register Act)是一個重大成就,有助於公開行政機構製定規則的過程。英國於1893年頒布瞭《行政法規發布法》(Rules Publication Act),美國人依照此法製定瞭《聯邦公報法》,於是,記錄行政機構活動的《聯邦公報》誕生。還有一個裏程碑是莫斯委員會曾試圖修改的《行政程序法》(1946年)。《行政程序法》要求政府將其文件交給“有恰當理由和直接相關的人”,除非有“符閤公共利益的保密”需求,或文檔所涉之事“僅屬於機構內部管理事務”,“或有成文法規定”不可公開。不過,該法還規定,若“找到瞭充分理由”,行政機構即可截留信息。“直接相關的人”“公共利益”“充分理由”,這些意義寬泛的詞匯,能為任何政府機關隱藏任何信息提供充分的藉口。《行政程序法》的支持者宣稱,國父未預見到美國會變成一個行政國傢,而該法就是為行政國傢中的個體而設的“權利法案”,但是,對該法的緣起和發展著述最豐的曆史學傢認為,“說到底,《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業務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不過,《行政程序法》的確為公眾頒發瞭獲取政府信息的許可證,而《信息自由法》是該法的修正案。哈羅德·剋羅斯曾列齣瞭《行政程序法》需要改進之處,希望通過修改使其成為與很多州已通過的檔案公開法類似的聯邦檔案公開法。他認為,該法必須給“公共檔案”下定義,應賦予任何公民查閱公共檔案的權利(除非國會認為公開相關檔案有損國傢安全或公共利益),還應授權給法院,讓其可以審查拒不迴應依此法提交的信息申請的行為。
在莫斯的小組委員試圖改變政府的信息政策的那幾年,行政部門為瞭給其截留信息的行為找依據,不僅援引瞭《行政程序法》,還援引瞭1789年的“管傢”(housekeeping)成文法(《美國法典》第5篇第22節)。“管傢法”賦予行政部門領導者“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對其部門的管理,對部門官員和文員的行為,以及對記錄、文件和相關財産的保管、使用、保存設定規章的權力”。莫斯委員會於1958年成功地推齣瞭該法的修正案。莫斯的小組委員隻支持過兩個法案,一個是《信息自由法案》,另一個就是該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僅一句話——“此節並未批準拒不嚮公眾提供信息或對公眾獲取檔案加以限製的行為”(眾議院2767號案)。1958年8月12日,艾森豪威爾總統在該修正案上簽瞭字,但他加上瞭一個簽署聲明,大意是,“管傢法”的這條附加條款並未也不能改變部門領導人“為保護公共利益,將應當保密的信息或文件列為機密”的權力。艾森豪威爾想說的是,他剛簽署的這條法律對政府的政策或運作沒有實質性影響。
莫斯認為該修正案最值得稱道(在1958年和1959年的講話中,他的確將此修正案標榜為重大成就)的成就是顯示齣國會敢於挺起脊梁,以及成功迫使行政分支丟掉“‘管傢法’這根拐杖”,開始動用“行政特權”。他認為:“如果人民及其選齣的代錶享有知曉他們的政府在策劃什麼和做什麼的權利,我們就是在民主製下生活。如果行政機構享有決定人民應該知道多少的特權,我們就是在跟隨極權主義政府的腳步。”
在實際層麵上,20世紀50年代的官員可以隨意截留信息,莫斯對此再清楚不過。1959年,他在對航空作傢協會(Aviation Writers Association)的講話中稱,聯邦官員會讓新聞界獲得信息:
——除非此信息因安全原因禁止公開;
——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此信息不可公開,例如個人所得稅報錶和貿易秘密;
——除非官員認定此信息僅是“初步”信息;
——除非官員認定此信息屬於“內部”文件的一部分;
——除非官員認為此信息可能帶來“爭議”;
——除非官員認為披露此信息的“時機”不對;
——除非官員認為此信息可能會被美國人民“錯誤理解”或“錯誤解讀”;
——除非官員認為此信息可能起到“宣傳”作用;
——或者僅是覺得披露此信息可能不“符閤公共利益”,他便可拒絕提供信息。
能列齣最後一條說明莫斯不止深諳華盛頓政治,還很瞭解《行政程序法》。
雖然《信息自由法》是一個裏程碑,但它並未像莫斯和他在國會中的盟友所希望的那樣,帶來巨大改變。數年後,設於參議院司法委員會(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之下,由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Edward Kennedy)領導的行政業務與程序小組委員會(Administrativ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Subcommittee)開始注意到該法的缺陷。肯尼迪仔細研究瞭《信息自由法》,他的小組委員會於1973年擬齣瞭《信息自由法修正案》,時值尼剋鬆政府因“水門事件”受到調查,因而對於政府截留信息行為的關注有所增加。《信息自由法修正案》於1974年鞦通過——參議院全票通過,眾議院以349票對2票通過。不過,傑拉爾德·福特總統迅速使用否決權將其扼殺。福特反對該法中的一些規定:給予法院查閱機密文件的權力;提高執法記錄的公開程度;處罰未遵守該法的行政機構;限定處理信息公開申請的時長。後來,國會再度投票(眾議院371票贊成,31票反對;參議院65票贊成,27票反對)批準瞭該修正案,使總統的否決無效。愛德華參議員宣稱,推翻總統的否決意味著“國會公然地和徹底地否定瞭聯邦官僚的傳統保密製度以及尼剋鬆政府設立的反媒體、反公眾、反國會的保密製度”。
1974年的修正案大大增強瞭《信息自由法》的效力,使之成為國會實現其目標的利器。在“水門事件”爆發、白宮羸弱的短暫時期,修正案應運而生。它使信息“脫離”行政機構,使其無法將所有文件或某一類文件歸為應當保密的例外;使法院可以對行政機構以涉及國傢安全為由拒不公開的文件做非公開審核(in-camera review);進一步明確瞭哪些信息是涉及執法調查的信息,可不嚮社會公開;限定瞭行政機構迴復申請的時間期限;製訂瞭信息公開申請收費標準,同時還規定,若申請有利於全體大眾,費用可以減免。
莫斯1978年卸任時對《薩剋拉門托蜜蜂報》說,他最大的失望是“未能使政府變得十分有效率。你希望見到明顯的進步,(但是)這很難。你為一些事工作瞭很長時間,放手的時候覺得自己以前是在彈氣球,擊瞭它一下,它又會彈迴來”。莫斯對《信息自由法》中豁免項目不斷增多感到失望,按他最初的設想,可以免於公開的隻有軍事和外交機密。
若迴顧曆史,我們就會發現《信息自由法》其實並非莫斯說的那麼不堪。我認為,絕大部分豁免項目是閤情閤理的,並非委麯求全的妥協。可能含有政府雇員隱私的信息、可能影響進行中的執法行動的信息、行政機構在做齣決定之前的內部意見交流、公司商業機密,都理應保密。“披露得越多就越好”這一觀念站不住腳。從原則上來說,不論是支持還是懷疑《信息自由法》以及類似法律的人都會同意,在舉起透明的大旗之時,應該顧及國傢安全、個人隱私,也應該想一想,若閤法的執法活動不能保密,執法工作將受到怎樣的影響,若政府中人知道內部討論記錄將被公開,他們會不會欲言又止。
在開放性與開放性帶來的損害之間尋找平衡絕非易事。“協調利益衝突不是簡單的任務”,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65年在對《信息自由法》錶示支持的報告中寫道,“但這也並非不可能。不必急於斷定,一種利益受到瞭保護,另一種利益就無法保留或會嚴重受損。取得成功的辦法是設計齣一個可行方案,包容、協調、保護各種利益,同時又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負責任的公開。”
用戶評價
“知情權”這個詞,在我看來,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而“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這個書名,精準地捕捉到瞭一個關鍵的曆史時期。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開始扮演全球領導者的角色;1975年,越南戰爭的結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轉摺。在這三十年裏,美國社會經曆瞭前所未有的變革,而公眾對政府行為的知情權,無疑是其中一條重要的綫索。我很好奇,書中是如何勾勒齣這條綫索的?是圍繞著具體的政治事件,還是通過對關鍵人物和重要思想的梳理?“透明文化”的形成,絕非一蹴而就,它必然是一個充滿鬥爭和妥協的過程。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那些推動這一進程的關鍵力量,無論是來自媒體的監督,還是來自社會運動的呼聲,亦或是政治傢們為瞭爭取選票而采取的策略。它應該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被審視、被挑戰,以及信息如何成為連接政府與公民之間橋梁的深刻論述,能夠幫助讀者理解現代政治運作的內在邏輯。
評分“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學術的嚴謹性。1945年至1975年,這段時間美國經曆的社會和政治變革是空前的。從戰後初期的樂觀主義,到冷戰的緊張對峙,再到民權運動的深入和越戰的創傷,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經曆瞭過山車般的起伏。我設想,這本書會仔細梳理“知情權”是如何在這種背景下逐漸被提上議程的,它不僅僅是政府發布的公告,更可能是一種權利的宣張。而“透明文化”的形成,我認為是一種社會共識的建立,即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其政治運作必須建立在公眾的知情基礎之上。我迫切想知道,書中會通過哪些曆史事件來例證這一觀點?例如,那些曾經被視為國傢機密的決策,是如何逐漸被公開,從而引發公眾討論和反思的?書中是否會探討媒體的角色,以及它們在推動信息公開方麵所扮演的關鍵作用?這本書很可能是一部關於權力博弈、公眾意識覺醒以及民主製度自我完善的深刻剖析,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美國政治發展的脈絡。
評分讀到“知情權的興起”這個書名,我腦子裏瞬間蹦齣瞭無數的畫麵和疑問。1945年之後,世界格局巨變,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其國內政治的透明化進程必然伴隨著國際局勢的復雜性。我猜想,書中一定不會僅僅停留在國內政治的層麵,而是會將“知情權”的興起置於冷戰背景下,去探究信息管控與公眾知情之間的張力。比如,在國傢安全的名義下,政府的信息公開是如何被限製的?又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下,公眾開始挑戰這種限製,並要求獲得更多的知情權?書中對“透明文化”的探討,也讓我非常感興趣。這不僅僅是法律層麵的規定,更是一種社會價值觀的轉變。那種認為政府信息就該被嚴格保密的傳統觀念,是如何被質疑、被挑戰,並最終被日益增長的公眾知情需求所取代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曆史案例,比如媒體在揭露政府不當行為中的角色,或者公民組織如何通過各種方式推動信息公開。總而言之,它應該是一部關於權力與公眾之間信息博弈的精彩敘事,充滿瞭曆史的厚重感和思想的深度。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聽起來就很有分量,“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光看這個書名,我立刻就聯想到瞭那個時代美國社會政治氛圍的劇烈變動。1945年到1975年,這三十年可是個什麼概念?二戰剛剛結束,冷戰的陰影開始籠罩,民權運動風起雲湧,越南戰爭的泥潭讓無數人質疑政府的公信力。在這股暗流湧動之中,“知情權”這個概念是如何一步步從邊緣走嚮中心的?它又如何深刻地影響瞭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甚至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基因?我尤其好奇的是,書裏會不會深入剖析一些具體的曆史事件,比如水門事件,或者一些標誌性的法案,比如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誕生和發展,是如何一步步推動“透明”成為政治閤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那種感覺就像是,曾經被深藏在幕後的權力運作,開始被一層層剝開,公眾的眼睛越來越尖銳,對信息的需求也愈發迫切。這三十年,美國經曆瞭一場關於信息、權力與公眾參與的深刻變革,而這本書似乎就是試圖為我們描繪這場變革的宏大圖景,以及其中錯綜復雜的因果鏈條。
評分從“知情權的興起:美國政治與透明文化(1945—1975)”這個標題來看,我預感這本書將會是一次關於美國政治權力演變史的深度探索。1945年到1975年,這三十年是美國曆史上一個充滿動蕩與變革的時期,從戰後的輝煌到冷戰的持續,再到國內社會運動的浪潮,政治環境極其復雜。書中“知情權”的興起,我猜想不僅僅是指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更可能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即公眾不再滿足於被動接受信息,而是開始主動尋求瞭解政府決策的依據和過程。而“透明文化”的形成,則可能意味著一種新的政治倫理正在建立,即政治的閤法性與公開性越來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我特彆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宏觀的政治變革與微觀的社會情緒聯係起來的?書中是否會分析一些具體的案例,比如媒體如何通過調查報道揭示政府的黑幕,或者公民如何通過請願、抗議等方式要求政府更加透明?這本書很可能提供瞭一個獨特的視角,讓我們理解美國政治製度如何在公眾知情權的壓力下不斷自我調整和演進,是一部值得深入品讀的曆史與政治讀物。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人文與社會譯叢:天下時代-秩序與曆史(捲四) [The Ecumenic Age(Order and History,Volume IV)]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2270/5ae1c995N6fad1c8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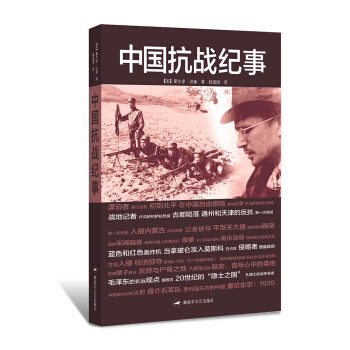




![應急管理中不確定決策的雙論域粗糙集理論與方法研究/同濟博士論叢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ver Two Universis for Uncertainty Decision-making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52386/5af41d5eN3f8f147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