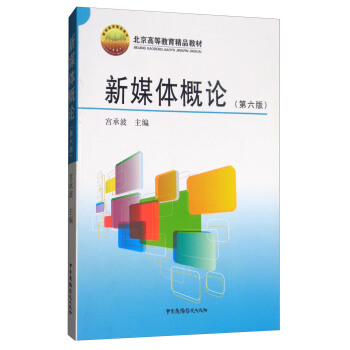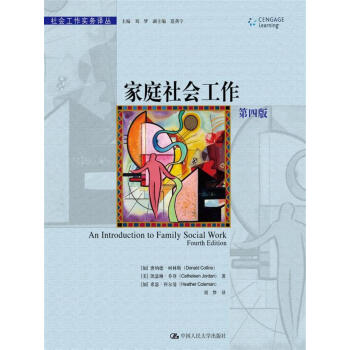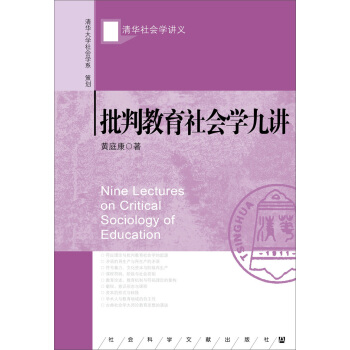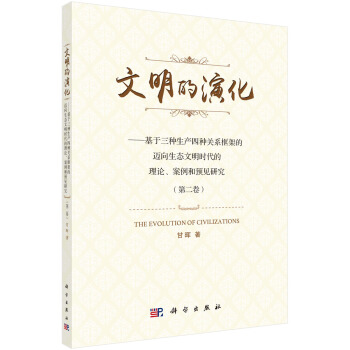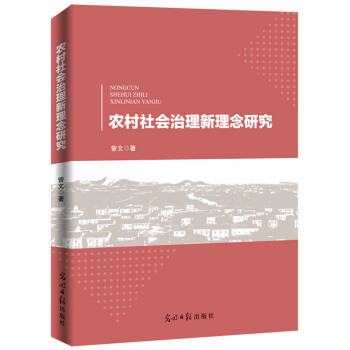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高校“双1流”建设启动后,大学教育改革牵动亿万家长学子的心,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条分缕析,解释了“大学之大”的核心价值观。
2.以民国教育为圭臬,为今日的莘莘学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成长套餐”。
3.作者深耕于民国领域的写作,著述多本,反响良好,《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一书更是被众多老师列为学生喜爱的书目予以推介。本书是作者民国著述的集大成之作,历经多年求索与磨砺,喜爱民国历史、关注中国教育的读者不容错过。
4.有趣与深刻完美融合,又充满青春气息和正能量。 这是编辑推荐
为什么民国教育*会让人津津乐道?
钱学森感慨:我们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培养的大师相比?
内容简介
本书从晚近以来海量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等一手资料中挖掘整理出众多民国时期学人、学子之趣闻轶事,以此梳理、搭建出一条民国大学的精神脉络,勾勒出一张民国大学精神图谱,并力图重现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年来及五四运动爆发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的“学统”,诠释大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核心要义。本书共分成两大部分,即“名师高徒”和“大学之大”。第一部分“名师高徒”共分成“争鸣”、“无名”、“会通”等十大主题,每一主题又分成“教师篇”和“学生篇”两大板块或者两个章节,从教师和学生两个角度分别叙述相关的故事,阐释相关的精神,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二部分“大学之大”分成“爱生”、“尊师”、“奉公”、“独立”四大篇章,从学校治理的宏观角度和微观细节再次阐述了民国大学精神*重要的内涵,并与前面的师生主体篇章形成呼应。全书教师、学生、学校“三位一体”,将有趣和深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又充满青春气息和正能量,是目前市场上难得一见而又让大众喜闻乐见的全面深入讲述民国教育的书。
作者简介
潘剑冰,青年学者。多年来致力于民国主题的写作,目前已经出版相关著作多部,其中《疯狂的科举》入选新华网和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办的“2013中国影响力图书”, 《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入选出版商务周报“2013中国风云图书”。作品以“幽默又优雅,深情且深刻”的风格,深受读者喜爱。精彩书评
NULL目录
目录第一部分 名师高徒
争鸣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_002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_014
狂傲
我就是风景!_025
二十不狂没志气_036
无名
大教授也“蹭课”_049
旁听生、偷听生、自绝生_060
风骨
民国教授“抗蒋”英雄传_072
壮哉,我中国少年!_083
嗜书
人书合一,臻于至境_098
唯有青春与书籍不可辜负_110
自由
大师讲学,就是这样!_121
原谅我放纵不羁爱自由_132
会通
学贯中西,汇参文理,熔铸古今_145
志汇中西归大海,学兼文理求天籁_156
亲爱
有一种亲情叫过去的老师_171
师之所存,道之所存_185
敬业
学者死于讲坛_199
求学是一场必经的修行_213
家国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_227
爱国是一种伟大的抉择_237
第二部分 大学之大
尊师
只有北大清华才“养得起”这么一群教授_250
爱生
维我母校,如我亲娘_264
奉公
大年初一,只剩下校长在上班_279
独立
得他这么个奖,叫我如何见人!_293
精彩书摘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以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了一代学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了这种理想的盛景,也不幸亲眼见证了这种理想的幻灭。对于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学人来说,他们对旧时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那种可以自由争鸣、独抒己见、无所顾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围之怀念。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如是说。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出蔡元培和他主导的北大,无需赞美已经立于云端。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梁漱溟和胡适都曾在北大的讲台上当众批评过一校之长,认为其学术观点不入格。据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锦回忆:
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北大六年琐忆》)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在旧学方面拥有极高的权威。而此时胡适刚留洋归来,初出茅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梁漱溟更是只有小学学历,因蔡元培看中了他写的一篇论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纪轻,一位学历低,且都刚刚登上北大讲坛,根基未稳就开始炮轰校长,好比破庙里的土地老儿叫板大雄宝殿上的如来佛,胆也够肥了。蔡元培居然不以为忤,不仅坚决捍卫两人批评的权利,还对他们的学问大加赞赏,后来梁漱溟要辞职他还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云:“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学术归学术,人际归人际,多么美好!回看民国,很多学林前辈交往的故事,常常让人惊叹于彼此的任性和单纯:
刘师培和崔适都是著名的经学家,但刘属于古文派,而崔则是今文派,好比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同派纷争,尤为激烈。两人在北大上课时经常互相抨击对方的观点,言辞相当火爆。碰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正好比邻而居,冤家路窄,每天都免不了狭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二位见面必然眼含杀气、怒目而视,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张中行《红楼点滴二》)
刘崔二位虽然学见不同,毕竟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在尚武的民国,知识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废名在北大教书时倾心于佛学研究,只是很少有人把他当回事,只有熊十力愿意跟他一起讨论,可惜两人观点迥异,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到最后甚至扭打成一团,不欢而散。不过,等到第二天废名再来找熊十力时,两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对此,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在《怀废名》中有过记述。
诗人梁宗岱热爱辩论,温源宁在《一知半解》里说,“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足、眼、身一起参加”,“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这不,在北大执教时,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因争论新诗节奏互不相让,导致上演全武行,多年后罗念生对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抗战时,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执教,又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大战三百回合,有在场的学生提供人证:“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将学术研讨转变为比武切磋,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国特色了。至少今天还从来没听说哪位名家如此不顾斯文,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德艺双馨。但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到当年学术论战的风气是何等兴盛,彼此之间毫无保留毫不掩饰,整个学术界重现八音齐奏的宏大交响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学术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国的流风余韵。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两位名师都以治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一为陈寅恪,一为岑仲勉。这二老一个目盲,一个耳聋,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时期的史学大家金毓黻认为当世治隋唐史首推陈岑二人,又常遗憾两人虽近在咫尺却“联系不够”。
岑仲勉半路出家,弃政从教,年近半百才正式走上学术道路,却厚积薄发,别开生面,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然而,岑仲勉却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而且总是毫不客气地在课上跟学生一一挑明,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之处,还公然宣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
遗憾的是,岑仲勉的名气和实力远远不及陈老,因此他对陈寅恪的批评在很多人眼里有一种“蚍蜉撼大树”的不自量力,招来了不少冷嘲热讽。对此,岑仲勉倒是十分坦然:“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对自己的非议,陈寅恪多有耳闻,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甚至还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多次引用了岑的学术成果。1956年,从中大历史系毕业的郑欣在拍毕业照时偶然看到陈岑二师见面时亲切握手的场景,不由回想起岑在课堂上对陈之抨击,因此,这一幕让他倍感疑惑。直到几十年后,郑欣读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后,方才恍然大悟。文中解答郑欣困惑的是这样一段话: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岑仲勉在学术上和陈寅恪划清界限,在陈寅恪受批判时,他却能不避嫌疑,当众为其叫屈。老岑死得早,没赶上“文革”,是不幸,也是大幸。当这一辈学人凋零已尽的时候,这一种任性与单纯也就成了空谷足音。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以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了一代学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了这种理想的盛景,也不幸亲眼见证了这种理想的幻灭。对于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学人来说,他们对旧时代的怀念,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那种可以自由争鸣、独抒己见、无所顾忌、快意恩仇的思想氛围之怀念。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费加罗的婚礼》中如是说。由此,我们也可以反推出蔡元培和他主导的北大,无需赞美已经立于云端。
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梁漱溟和胡适都曾在北大的讲台上当众批评过一校之长,认为其学术观点不入格。据1917年考入北大的田炯锦回忆:
梁漱溟先生教学时,对留欧美学者之见解,常有批评,甚至对全校拥护之蔡校长的论“仁”,曾有严刻的评议。蔡先生给“仁”的定义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梁谓这种定义叫人无可批评,但其价值亦仅止于无可批评。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认为是曹雪芹描写其家室与身世的一部小说,并批评蔡先生的考证,说:宝玉影射清廷某人,黛玉影射某人等等,是笨的猜谜,犹如有人猜“无边落木萧萧下”一般。蔡先生虽不同意梁、胡两位的意见,但对他们的学问非常赞许。(《北大六年琐忆》)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出身,在旧学方面拥有极高的权威。而此时胡适刚留洋归来,初出茅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梁漱溟更是只有小学学历,因蔡元培看中了他写的一篇论文,被破格聘入北大教席。此二人一位年纪轻,一位学历低,且都刚刚登上北大讲坛,根基未稳就开始炮轰校长,好比破庙里的土地老儿叫板大雄宝殿上的如来佛,胆也够肥了。蔡元培居然不以为忤,不仅坚决捍卫两人批评的权利,还对他们的学问大加赞赏,后来梁漱溟要辞职他还一再挽留。故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有云:“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学术归学术,人际归人际,多么美好!回看民国,很多学林前辈交往的故事,常常让人惊叹于彼此的任性和单纯:
刘师培和崔适都是著名的经学家,但刘属于古文派,而崔则是今文派,好比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同派纷争,尤为激烈。两人在北大上课时经常互相抨击对方的观点,言辞相当火爆。碰巧的是两人在北大正好比邻而居,冤家路窄,每天都免不了狭路相逢。不知情的人以为这二位见面必然眼含杀气、怒目而视,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张中行《红楼点滴二》)
刘崔二位虽然学见不同,毕竟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在尚武的民国,知识分子打架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废名在北大教书时倾心于佛学研究,只是很少有人把他当回事,只有熊十力愿意跟他一起讨论,可惜两人观点迥异,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到最后甚至扭打成一团,不欢而散。不过,等到第二天废名再来找熊十力时,两人又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对此,废名的老师周作人在《怀废名》中有过记述。
诗人梁宗岱热爱辩论,温源宁在《一知半解》里说,“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足、眼、身一起参加”,“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这不,在北大执教时,梁就曾跟自己的好友,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因争论新诗节奏互不相让,导致上演全武行,多年后罗念生对这一幕还记忆犹新:“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抗战时,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执教,又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大战三百回合,有在场的学生提供人证:“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将学术研讨转变为比武切磋,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大概也是民国特色了。至少今天还从来没听说哪位名家如此不顾斯文,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德艺双馨。但从一个侧面来说,也可以看到当年学术论战的风气是何等兴盛,彼此之间毫无保留毫不掩饰,整个学术界重现八音齐奏的宏大交响乐。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学术界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国的流风余韵。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两位名师都以治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一为陈寅恪,一为岑仲勉。这二老一个目盲,一个耳聋,形成有趣的搭配。同时期的史学大家金毓黻认为当世治隋唐史首推陈岑二人,又常遗憾两人虽近在咫尺却“联系不够”。
岑仲勉半路出家,弃政从教,年近半百才正式走上学术道路,却厚积薄发,别开生面,开拓了以碑证史的唐史研究路径,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的研究方向遥相呼应。然而,岑仲勉却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而且总是毫不客气地在课上跟学生一一挑明,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之处,还公然宣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
遗憾的是,岑仲勉的名气和实力远远不及陈老,因此他对陈寅恪的批评在很多人眼里有一种“蚍蜉撼大树”的不自量力,招来了不少冷嘲热讽。对此,岑仲勉倒是十分坦然:“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对自己的非议,陈寅恪多有耳闻,却从来不放在心上,甚至还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多次引用了岑的学术成果。1956年,从中大历史系毕业的郑欣在拍毕业照时偶然看到陈岑二师见面时亲切握手的场景,不由回想起岑在课堂上对陈之抨击,因此,这一幕让他倍感疑惑。直到几十年后,郑欣读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后,方才恍然大悟。文中解答郑欣困惑的是这样一段话:
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岑仲勉在学术上和陈寅恪划清界限,在陈寅恪受批判时,他却能不避嫌疑,当众为其叫屈。老岑死得早,没赶上“文革”,是不幸,也是大幸。当这一辈学人凋零已尽的时候,这一种任性与单纯也就成了空谷足音。
前言/序言
序 言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
为了写这本书,笔者又回头去将之前许多走马观花读过的的回忆录细细咀嚼
了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民国学子们对于母校感情之热烈与
执着,而且这种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红学家周汝昌在80岁时回忆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时说:“现在
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
校园。”(《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述》)历史学家何兹全85岁时写道:“掐指
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
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
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爱国一书
生》)何兆武先生则在《上学记》中深情告白:“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
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这样的信念不仅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会因空间的阻隔而遥远。
旅美史家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
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数学家陈省身和何炳棣一
样,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工作,但让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年轻时那段
“光辉岁月”,他晚年反复宣称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
II大学·大师·大时代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已经超出了信念的范围,而固化成一种人生信仰。
对于大学生涯的热爱,不仅仅是当年学子的集体情感,也是当年教师的普遍
价值。
历史学家蒋廷黻毕生最无法忘怀的就是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执教经历,他说:
“对我个人来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而诗人冯至,这位曾
经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则写下了这么一段不够诗意却很有诚意的文字:“如
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
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
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
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
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最可爱的是陈翰笙先生。这位比北大还大一岁的经济学家曾经接受蔡元培
的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到他107岁去世时,已经是北大最年长的教
授。北大百年校庆时,电视台记者采访101岁的陈翰笙,让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
话,陈老不假思索,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都觉
得不妥,教他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但老头子很任性,连说三遍,次次
都是“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绝不改口。(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
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很显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如果单从物质建设上来看,今
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一众名校,然而,它们却无法在学子心
中唤起那种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来的大学,同样无法因为物质建设的进步
获得同比例增加的归属感。
III
这就是笔者写作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于是,在我
们刚刚走进的这个年份,本书的写作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2017,正是蔡元培先
生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之际。
大学的起源也许要向上追溯千年,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则被公认为
是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将独立与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学的精神内
核,在帝制时代的尾声横空出世,也给一流大学的定义加上了一个“金标准”。
从此,大学走上了一条通衢大道。
国人历来热衷于寻根追祖,国内第一所大学的荣誉所归,至今还是个富有争
议的话题。据闻,有的大学已经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古代的书院。其实,这样
的争议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没有执掌北大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
大学。
1917年,曾经自费留德多年、深受德国现代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先生就任
北大校长,其后北大脱胎换骨,从一座“衙门”性质的封建官僚旧式学堂转变成
了追求科学新知的新式高等学府,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开天辟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了精神归位,也以一道霹雳在中国
的学术天空划出夺目的光亮。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现
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7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实在应该
共庆百年校庆。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长,再加上老北大连一个
统一的校园都没有,校舍四处分散、支离破碎,既无升旗仪式也无学年大会,甚
至连毕业典礼都没办法举行,难以形成集体意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因
如此,却使得学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长。清华则拥有庚子赔款的强大财力作为后
盾,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压制学校的手段在这里很难实现,经济独立支撑了精
序言
IV大学·大师·大时代
神独立,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因这两方面的因素汇聚清华园,他们的嶙峋风骨则进
一步推进了清华独立精神的涵育和发展。
于是,北大为代表的自由思想和清华为代表的独立精神遂成为中国大学的精
神双核,为中国大学的前进提供了连绵不绝的动力。同时,北大的激进与清华的
沉潜恰好又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如太极图式中的阴阳两仪,其他大学在其强大
的吸力之下,自觉形成了向心性,围绕着双核运转,如群星捧月、众壑朝宗。后
来,即使国民党政府极力扶持官方色彩更浓的中央大学为“最高学府”,也无法
撼动两校的地位。这并非北大清华多么优秀,而是由于真理的力量无可匹敌。
而在北大清华之外,民国的其他高校大都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哪个学
子毕业于哪个大学仿佛都贴上了标签,不会混淆;反过来,学子对于自己母校的
认同感也是惊人的强烈。不像我们现在,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还是牢骚不断。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盖因人文精神的缺位。
如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一个世纪的时光已经过去。尽管世事沧桑,风
流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民国大学高贵的精神却依然如头顶的星空一样熠熠生辉。
人类已经过去的历史中,知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奢侈品。在一篇好文章
都能引发“洛阳纸贵”的时代里,大多数人是无福享受教化之风的。大学的诞生
打破了少数人对于知识的垄断,也改变了无数底层民众的命运,功德无量。
然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至今日,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大学存在的意
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说很多院系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技术的
进步,完全可以让名师的课堂随着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脑桌面上一个图标的
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已经成年自立的学生,如果有足够的求
知欲望和毅力,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我的大学”。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欲
V
望和毅力,那么进了大学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收获。
世界上最顶尖的围棋选手已经在电脑面前败北,人工智能的压倒性胜利来得
比想象还早。至于更早被电脑降服的象棋界,重大比赛时防止大师们利用软件作
弊已经成了现在的主办方最为头疼的事情。人工智能这只“蝴蝶”还将在我们的
认知领域搅起怎样的飓风,或许会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假如未来有一天,
我们想学习某一项专业技术,身边马上就能有私人定制的无所不知而又不知疲倦
的机器大师的指导,那些天价的实验室也会成为基本的市政设施。再加上完善的
关于专业能力的评价手段、评价体系的建立,文凭只剩下象征意义,那么,我们
还有必要进大学学习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大学将会消失,因为现在很多大学不过是“劳动
力培训基地”,未来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大学不会消亡,只是会回归
其本来面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最初的大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只
是教会的附庸,最终,大学的成长壮大证明人类的信仰不仅可以来自于对神的膜
拜,也可以来自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宇宙自然的好奇与向往。
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这是对人类学会思考的恐惧。知识不但是一个谋生工具,更
应该是一种生存方式,而要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体验式”成长是不可或缺
的。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到达旅途的终点,而是观赏沿途的风景,
或修炼看风景的心情,求学亦复如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师友的碰撞融
合,学习中的喜怒哀乐,想象力、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之生发,进而整个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些都将使知识本身变成一种伟大的信仰,也是人
类超越机器的地方。同样的结果,由于过程的不一样,其深度和广度是大异其趣
的。有了这样的过程,大学的经历就将在我们的心海中升起一座精神岛屿,任凭
序言
VI大学·大师·大时代
浪潮拍打,却始终傲立于海平面上,永不沉没,如前面那些过来人的感怀一样。
天地广阔,山河浩荡,最令人留恋的还是校园中的大草坪和林荫道。我们曾
于此卧看云起,也曾执手走过落叶翩翩。惟有以此洁白纯净为底色,方可在人生
的画布上泼洒出大写意。
文明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作为一个群体就越强大,而作为一个个体则愈
脆弱。当技术到达特定的高度以后,人的存在感也必将跌入冰河期,这个时候,
唯有高擎人文精神的火把才能温暖僵硬麻木的躯体。未来的大学,必定从现在的
技术至上转向人本主义。归根到底,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法
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曰“人,诗
意的栖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人怎么活得像个人
是最大的课题,这或许也是未来大学最神圣的使命。
物理学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光电效应”,冷冰冰的金属在高频率光线的照
耀下,竟然也会激情四射,内部的电子被光子激发,脱离原子核的束缚跳出来并
形成电流。这样的变化也许肉眼看不见,但是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大学
之光照耀之处,必将解放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得我们的生命出现鸢飞鱼跃、
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这束光芒已经照亮了人类的过去,也必将照耀我们的未
来!序 言
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
为了写这本书,笔者又回头去将之前许多走马观花读过的的回忆录细细咀嚼
了一番,感慨良多。其中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民国学子们对于母校感情之热烈与
执着,而且这种情感往往持之一生,永不褪色。
红学家周汝昌在80岁时回忆自己早年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时说:“现在
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
校园。”(《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述》)历史学家何兹全85岁时写道:“掐指
算来,在北大读书已是60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有人问我:‘你这大半生中哪个时
期生活最幸福?最有意义?’我会毫不考虑地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
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爱国一书
生》)何兆武先生则在《上学记》中深情告白:“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
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这样的信念不仅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黯淡,亦不会因空间的阻隔而遥远。
旅美史家何炳棣晚年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
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的清华园。”数学家陈省身和何炳棣一
样,大半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生活工作,但让他魂牵梦萦的仍然是年轻时那段
“光辉岁月”,他晚年反复宣称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
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
II大学·大师·大时代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已经超出了信念的范围,而固化成一种人生信仰。
对于大学生涯的热爱,不仅仅是当年学子的集体情感,也是当年教师的普遍
价值。
历史学家蒋廷黻毕生最无法忘怀的就是自己在清华大学的执教经历,他说:
“对我个人来说,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而诗人冯至,这位曾
经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则写下了这么一段不够诗意却很有诚意的文字:“如
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
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
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
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
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最可爱的是陈翰笙先生。这位比北大还大一岁的经济学家曾经接受蔡元培
的聘任,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到他107岁去世时,已经是北大最年长的教
授。北大百年校庆时,电视台记者采访101岁的陈翰笙,让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
话,陈老不假思索,说:“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记者和家人都觉
得不妥,教他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但老头子很任性,连说三遍,次次
都是“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绝不改口。(潘维《跨越世纪的精神
薪火——忆先师陈翰笙》)
很显然,上述追念都是建立在精神层面上的。如果单从物质建设上来看,今
日很多不入流的大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一众名校,然而,它们却无法在学子心
中唤起那种深沉的情感。而那些一路走来的大学,同样无法因为物质建设的进步
获得同比例增加的归属感。
III
这就是笔者写作这本书的意义之所在——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于是,在我
们刚刚走进的这个年份,本书的写作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2017,正是蔡元培先
生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周年之际。
大学的起源也许要向上追溯千年,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则被公认为
是创立于1809年的柏林洪堡大学。洪堡将独立与自由的理念打造成大学的精神内
核,在帝制时代的尾声横空出世,也给一流大学的定义加上了一个“金标准”。
从此,大学走上了一条通衢大道。
国人历来热衷于寻根追祖,国内第一所大学的荣誉所归,至今还是个富有争
议的话题。据闻,有的大学已经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了古代的书院。其实,这样
的争议大可不必,在蔡元培先生没有执掌北大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
大学。
1917年,曾经自费留德多年、深受德国现代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先生就任
北大校长,其后北大脱胎换骨,从一座“衙门”性质的封建官僚旧式学堂转变成
了追求科学新知的新式高等学府,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开天辟地的。
蔡氏改革北大,使得徒具肉身的北大宣告了精神归位,也以一道霹雳在中国
的学术天空划出夺目的光亮。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现
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7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实在应该
共庆百年校庆。
北大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精神的哺育下迅速成长,再加上老北大连一个
统一的校园都没有,校舍四处分散、支离破碎,既无升旗仪式也无学年大会,甚
至连毕业典礼都没办法举行,难以形成集体意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因
如此,却使得学生的自由思想蓬勃生长。清华则拥有庚子赔款的强大财力作为后
盾,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压制学校的手段在这里很难实现,经济独立支撑了精
序言
IV大学·大师·大时代
神独立,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因这两方面的因素汇聚清华园,他们的嶙峋风骨则进
一步推进了清华独立精神的涵育和发展。
于是,北大为代表的自由思想和清华为代表的独立精神遂成为中国大学的精
神双核,为中国大学的前进提供了连绵不绝的动力。同时,北大的激进与清华的
沉潜恰好又形成了完美的互补,一如太极图式中的阴阳两仪,其他大学在其强大
的吸力之下,自觉形成了向心性,围绕着双核运转,如群星捧月、众壑朝宗。后
来,即使国民党政府极力扶持官方色彩更浓的中央大学为“最高学府”,也无法
撼动两校的地位。这并非北大清华多么优秀,而是由于真理的力量无可匹敌。
而在北大清华之外,民国的其他高校大都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哪个学
子毕业于哪个大学仿佛都贴上了标签,不会混淆;反过来,学子对于自己母校的
认同感也是惊人的强烈。不像我们现在,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还是牢骚不断。
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盖因人文精神的缺位。
如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一个世纪的时光已经过去。尽管世事沧桑,风
流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民国大学高贵的精神却依然如头顶的星空一样熠熠生辉。
人类已经过去的历史中,知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种奢侈品。在一篇好文章
都能引发“洛阳纸贵”的时代里,大多数人是无福享受教化之风的。大学的诞生
打破了少数人对于知识的垄断,也改变了无数底层民众的命运,功德无量。
然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至今日,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大学存在的意
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说很多院系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技术的
进步,完全可以让名师的课堂随着网络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脑桌面上一个图标的
背后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已经成年自立的学生,如果有足够的求
知欲望和毅力,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我的大学”。反之,如果没有这种欲
V
望和毅力,那么进了大学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收获。
世界上最顶尖的围棋选手已经在电脑面前败北,人工智能的压倒性胜利来得
比想象还早。至于更早被电脑降服的象棋界,重大比赛时防止大师们利用软件作
弊已经成了现在的主办方最为头疼的事情。人工智能这只“蝴蝶”还将在我们的
认知领域搅起怎样的飓风,或许会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假如未来有一天,
我们想学习某一项专业技术,身边马上就能有私人定制的无所不知而又不知疲倦
的机器大师的指导,那些天价的实验室也会成为基本的市政设施。再加上完善的
关于专业能力的评价手段、评价体系的建立,文凭只剩下象征意义,那么,我们
还有必要进大学学习吗?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大学将会消失,因为现在很多大学不过是“劳动
力培训基地”,未来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但真正的大学不会消亡,只是会回归
其本来面目,“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最初的大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度只
是教会的附庸,最终,大学的成长壮大证明人类的信仰不仅可以来自于对神的膜
拜,也可以来自于对知识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宇宙自然的好奇与向往。
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这是对人类学会思考的恐惧。知识不但是一个谋生工具,更
应该是一种生存方式,而要实现这样的终极目标,“体验式”成长是不可或缺
的。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到达旅途的终点,而是观赏沿途的风景,
或修炼看风景的心情,求学亦复如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师友的碰撞融
合,学习中的喜怒哀乐,想象力、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之生发,进而整个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些都将使知识本身变成一种伟大的信仰,也是人
类超越机器的地方。同样的结果,由于过程的不一样,其深度和广度是大异其趣
的。有了这样的过程,大学的经历就将在我们的心海中升起一座精神岛屿,任凭
序言
VI大学·大师·大时代
浪潮拍打,却始终傲立于海平面上,永不沉没,如前面那些过来人的感怀一样。
天地广阔,山河浩荡,最令人留恋的还是校园中的大草坪和林荫道。我们曾
于此卧看云起,也曾执手走过落叶翩翩。惟有以此洁白纯净为底色,方可在人生
的画布上泼洒出大写意。
文明越进步,科技越发达,人作为一个群体就越强大,而作为一个个体则愈
脆弱。当技术到达特定的高度以后,人的存在感也必将跌入冰河期,这个时候,
唯有高擎人文精神的火把才能温暖僵硬麻木的躯体。未来的大学,必定从现在的
技术至上转向人本主义。归根到底,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法
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曰“人,诗
意的栖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人怎么活得像个人
是最大的课题,这或许也是未来大学最神圣的使命。
物理学上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光电效应”,冷冰冰的金属在高频率光线的照
耀下,竟然也会激情四射,内部的电子被光子激发,脱离原子核的束缚跳出来并
形成电流。这样的变化也许肉眼看不见,但是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大学
之光照耀之处,必将解放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使得我们的生命出现鸢飞鱼跃、
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这束光芒已经照亮了人类的过去,也必将照耀我们的未
来!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高级文笔,但又完全没有学究气,读起来非常过瘾。它有一种沉稳而富有韵律感的节奏感,仿佛作者在用最精准的词语,雕刻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我欣赏它对“时代精神”的捕捉能力。作者没有将时代简单地标签化,而是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捕捉,让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空气、氛围,乃至知识精英们日常交流中的细微差别,都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书中描述某次学术会议的场景,通过对与会者衣着、眼神、甚至是茶歇时谈论的话题的描摹,我能真切感受到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文化氛围与价值取向的微妙变化。这种高度的现场感和氛围感,让阅读过程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而不是冷冰冰的信息接收,这种文字功力,绝对值得反复品味。
评分真正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本书在探讨学术成就的同时,并未回避那些光环背后的人性复杂面。作者以一种近乎冷静的克制,书写了大师们的争议、失误,甚至是性格上的缺陷。这种真实感,极大地拉近了读者与“神坛上人物”的距离。我们不再是膜拜者,而更像是理解者。书中对某位哲学家的晚年心境剖析,非常到位,既肯定了他思想的开创性,也坦诚地揭示了他在面对时代剧变时的彷徨与局限。这种不偏不倚、尊重历史原貌的态度,体现了作者极高的学术良知和人文关怀。它教会我们,真正的伟大,是建立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基础上的,这比起一味地歌颂,要深刻和有力量得多。这种批判性的继承,才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
评分翻开的每一页,都像是被邀请进入了一场知识的盛宴,但这场盛宴的菜单设计得极为精妙,绝非堆砌资料的粗暴展示。我特别留意到作者是如何处理不同学科大师之间的思想交汇与碰撞的。那些本来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思想体系,在作者的笔下,忽然间找到了某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跨学科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我原有的认知边界。比如,书中对于美学理论如何影响了某些社会学思潮的探讨,简直是醍醐灌顶。它不再将学术史视为一条条平行的铁轨,而是将其描绘成一张交织错综的巨网。这种结构化的梳理,使得原本零散的知识点,迅速被整合进一个更宏大、更有逻辑性的框架之中。读完特定章节后,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对着书本深思良久,因为那种“原来如此”的顿悟感,是久违的阅读快感,它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对许多既有理论的理解,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思维重塑。
评分从结构布局来看,这本书的处理方式非常巧妙,它避开了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采取了一种多维度、网状的叙事结构,使得不同大师之间的思想脉络能够相互映照,形成一种立体的知识景观。我发现,作者非常善于设置“锚点”,通过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或关键著作的深入解读,串联起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轨迹。每一次跳转到新的主题或人物,都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反而像是在迷宫中找到了另一条通往核心的路径。这种精心的编排,体现了作者对材料的驾驭能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不只是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识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影响世界的思维路径,对于渴望建立系统性知识体系的读者来说,这本“地图集”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评分这本书的开篇,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真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下去。作者在叙述中巧妙地将那些耳熟能详的学术巨匠,放置在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使得他们的思想光辉不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与那个特定时空紧密相连的产物。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描摹,那种身处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坚守与选择,读来令人唏嘘。比如,书中对某位物理学家的青年时期探索历程的刻画,不仅仅是科学发现的记录,更是一场关于信念与环境博弈的深刻剖析。文字的处理非常细腻,没有那种刻板的教科书腔调,而是充满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切。它引导我去思考,在宏大的“时代”面前,个体智慧究竟能发出多大的光芒,又会如何被时代的风向所塑造。这种将“人”置于“史”中的叙事手法,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让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参与了那段思想的激荡岁月,而非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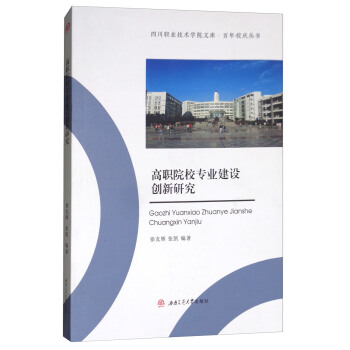
![国际可持续发展百科全书(第6卷):可持续性的度量、指标和研究方法 [Measurements,Indicators,and Reserach Methods for Sustainabil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77152/5a339579Nf79fb6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