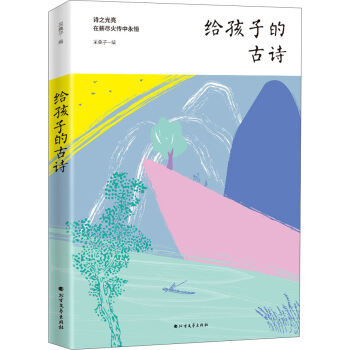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裘山山 非虚构新作尺牍飘零,串起山河岁月;见字如面,感悟世间亲情
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里的时代记忆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家裘山山的非虚构作品。作者从父母留下的几百封家书入手,在记忆回放中勾连起了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中的时代印记。在没有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年代,一封封书信将一个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成了一个整体,并在若干年后的重新检视中,发现了许多一度被忽视,却很重要的细节。作品图文并茂,配原汁原味的老照片若干,立体地展现了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庭历史,也以点带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色。
作者简介
裘山山,出身于军人知识分子家庭,18岁当兵,因喜欢写作成了作家。四川师大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0多万字。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现退休专职写作。其军旅文学的作品端庄而大气,社会题材的小说细腻而充满悲悯。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冰心散文奖等。其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等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和话剧,后者被称为“中国版《阿信》”。其短篇小说风格独特,曾六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我们这个家
1. 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
2. 母亲的第一封信,就将父亲彻底征服
3. 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那是1971年,我13岁
4. 1973年,第二封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也只有300多字
第二章 离开父母去当兵
1. 1977年,18岁的“后门兵”的忧虑
2. 熟记电话号码的通信女兵,非常愉快地给父母写信
3. “爸爸不必为此事再感到于心不安,我对这个问题(入党)没有一点儿怨言。”
4. “相比起入党,有件事更让我向往,就是上大学。”
第三章 我的1978年
1. “三八妇女节上午放假,中午加菜,下午女兵做游戏……我感到我们的确幸福。”
2. “陈慧莲都考上大学了。看看她,想想自己,不能不使我产生一些想法。”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一篇散文上了《重庆日报》,题目是《我们女战士》……”
4. 收到平生第一笔稿费: 七元。全部给连队图书室买了书
5. “这次年终总结,连里又给我报了一个营嘉奖。”
第四章 考大学
1. 一笔60元的“巨款”是怎样花掉的
2. 妈妈摘掉了“右派”帽子
3. 机房里间接参加西南边境保卫战
4. 终于争取到了考大学的名额
5. 高考上了分数线,体检却查出肺炎
第五章 校园生活
1. 富有时代特色的欢迎信:“欢迎你啊,可亲可爱的新战友,长征路上的好伙伴!”
2. 一下子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女生
3. 最喜欢的写作课反而得不了“优”
4. “我们2月9号放假,我最迟10号离开成都。不知妈妈几号返回?”
5. “我很希望能办一个刊物,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的作品,登出来……”
第六章 鲜活的1980年代
1. 麦乳精和鱼松里的同学情谊
2. 妈妈在信上指示我: 22岁了,可以考虑恋爱问题了
3. 1981年,从杭州、西安、成都分别向长沙聚拢的,四个人的春节
4.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散文,一篇小说。小说不理想。散文我把它投了,不知行否。”
5. “这几天除了复习英语,就是突击背古文。脑子都要背炸了。”
6. 暑假返校,坐了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火车: 68小时
第七章 狮子山往事
1. 写了50封家信的1981年: 平均每周一封
2. “妈妈,寄来的20元钱还没收到。高兴极了。因本人目前穷得叮当响。”
3. 寒假去长沙看父亲,竟然遇见了儿时的两个小伙伴
4. 我的24岁: 纠结考研。逃课和同学去卧龙玩。抽空写小说
5. “姐姐说她7月初就能到杭州。我现在常常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李双双》艺术特色’中抬起头来,盘算到杭州的种种。”
第八章 毕业歌
1. “我实在不想为分配的事去求别人。我相信我能凭自己的能力跳出来。爸爸你看呢?”
2. 在青神中学当了40多天实习老师,爱上了教书
3. 1983年春节,在杭州过年的一家四口: 妈妈的小屋挤不下四个成年人
4. “这是第四次退稿,我准备让他们退十次或者更多。”
5. 意外的“演艺生涯”: 被挑中演话剧中的女二号,一个性格古怪的大龄女生
6. 1983年7月8日,写了大学期间的最后两封家信
第九章 短暂的教师生涯
1. 从狮子山校园来到凤凰山教导队,挺符合我名字指出的道路: 山山
2. “有一件事可以使爸爸生日快乐: 我的小说要发表了,《昆仑》杂志。”
3. 年轻的教员想要“镇住”年长的学员
4. 心高气傲,为参加《昆仑》笔会与领导闹别扭
5. “火线”入党,竟然全票通过。庆幸遇到一个宽容的领导
6. 不辞而别的笔会: 再次遇到包容我的人
第十章 成家立业
1. 1984年,小说处女作《绿色的山洼》发表了
2. 384元稿费的去处: 爸妈的沙发、公婆的皮褥子以及亲友吃饭
3. 文凭热、全民经商时代的“河边湿鞋”
4. “最近一个多月,我笔不能动书不能翻,这怎么行?我的愿望是当作家而不是团长。”
5. “妈,我刚开会回来,一个教员表彰大会。说实话,我为自己的太顺利而感到不安……”
6. 大年初二,成都,27岁的婚礼
第十一章 离开凤凰山
1. 赶上了百万大裁军,是军内调动还是申请转业?纠结。
2. “我想进创作组,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就因为性别。”
3. “我被命运扔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沟。四面巍巍矗立着我的同胞们: 山。”
4. 到军区机关出公差: 迎来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
第十二章 走进北较场
1. “没想到我也当了编辑,这样爸爸妈妈的行当我算都干过了。”
2. 1986年春,赴北京约稿: 明明是去求人的,却不愿开口,亏你还姓“裘”
3. “刊物办得很艰难,不过邓小平给我们题写了刊名,在定编上又增加了一线希望。”
4. 巧合与纪念: 1977年3月14日,离家参军;十年后的同一天,儿子出生
5. 赴京参与报告文学写作: 想采访吴仪,她却带我去了燕山石化公司
6. 我的1988: 授衔落空,小说获奖
尾声: 没有结束
精彩书摘
第一章我们这个家1.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
我们家,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
特殊原因之一,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一辈子在部队,不说南征北战,也是一生漂泊无定。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于是乎,他和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总是聚少离多。父亲母亲谈恋爱的时间很长,因一直是“异地恋”。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一去三年。母亲一直等,等到朝鲜战争结束,才与父亲完婚。所以两人结婚时,都已经是28岁“高龄”了,生姐姐时29岁,生我时已32岁。父亲母亲是同年生人。
特殊原因之二,母亲是个职业女性。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可母亲是省报编辑,有自己的事业,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鹰厦线”的修建,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整整十年。
因为这个缘故,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可惜“文革”的时候都被销毁了,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在如履薄冰的年代,他们怕给已经“声名狼藉”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不敢保留。
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莫过于我的童年。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教书,而母亲因为被打成“右派”,不得已离开报社,就带着我和姐姐随军到了石家庄,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
这七年的生活,我在长篇小说《河之影》里,有大量描述。尽管期间经历了“文革”,但我们这个小家,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都非常疼爱,这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滋养着我。
好景不长,1970年,父亲又被调动,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依然相距遥远。那十几年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
如此,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分离。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而且这样一分为四的情形,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母亲被打成“右派”去浙江临安山区“劳动改造”,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一家四口天各一方,天涯零落。父亲探亲回家,一个月的假,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一岁半了。
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是1978年到1984年,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母亲“右派”平反回到杭州,在《浙江日报》工作;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我因当兵在重庆,后考上大学到了成都。
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是四个省份。那时我回家探亲,跟父亲当年一样,有时去杭州,有时去长沙,有时去西安。
幸运的是,那时的我和姐姐,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
我给爸爸写,给妈妈写,给姐姐写,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我们互相交织着写。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一封封的信,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妈妈当时曾戏言,我们家四个人,一个在华南(长沙),一个在东南(杭州),一个在西北(西安),一个在西南(成都),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就占领全国了。
自然是分久必合。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和母亲团聚,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和他们团聚。我虽然还在成都,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在杭州成立了。
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每年回家探亲。
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是1970年代初。
或者说写信这件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是1970年代初,我12岁。
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襄渝线,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所谓家属基地,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一层楼住八户人家,公用厕所,公用水龙头,两家合用一个厨房。
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没有文化,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就来找我妈帮忙。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文化人”(另几个“文化人”在外面单位上班)。身为“右派”的她,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她和阿姨们相处很好,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差异。
妈妈写信的时候,阿姨们总是围着看。
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让妈妈念,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我们家没有书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趴在木凳上写的。那个情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比如给邓阿姨写,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一般来说,是讲孩子的情况,或关心丈夫身体,鲜有感情表达。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加上“亲爱的我想你”,加上“你快回来看我吧”。
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依然很羞涩。这个时候,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我很喜欢这种时候,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
阿姨们排着队,一个写完了下一个。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比如,你要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什么的。然后读给她们听,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表示满意。
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父亲所在的29团,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丈夫来信,尽管一个字不认识,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而她们的丈夫,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跟文件一样有标配:最近工作很顺利,身体很好,不用担心。孩子们怎么样?你要注意身体。几乎回回如此。但等不到信的阿姨,就会焦急万分。真的是家书抵万金。
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老大是个儿子,比我小两岁,叫小明(不是段子里那个小明哦)。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你都读五年级了,认了那么多字儿了,还不能写信吗?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一封信,我就奖励你五毛钱。
1970年代初,五毛钱是巨款啊,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恨不能帮他写。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比如面壁思过,打手板心之类。若做了好事,也只是口头表扬。
但即使有写一封信五毛钱的重赏,小明仍不肯写。没办法,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不光是邓阿姨,王阿姨、曹阿姨都找我妈写。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右派”而歧视她,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
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比如曹阿姨问:徐大姐(我妈姓徐),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某某去世了,中(终)年76岁。这76岁还算中年吗?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王阿姨又问,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我妈就说,剑是刀剑的剑,英是英雄的英,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
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都非常诚恳。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是八一节》。
2.母亲的第一封信,就将父亲彻底征服
整理这些书信,让我感到最遗憾的是,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就是他们从恋爱到结婚,到“文革”前的信件。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包括1950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母亲被打成“右派”去劳改时,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
这些信一定是在“文革”时烧掉的。那时父母如履薄冰。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父亲被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母亲是“摘帽右派”,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现在留下的一包,仅仅是母亲平反后,到父亲1984年离休,他们团聚之前写的若干信。比之前面几十年,实在是很少一点点。
但母亲的第一封信,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
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
父亲和母亲,是经我们的二姨父介绍相识的。
我的二姨父,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好,姨父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并没有生出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出于礼貌,还是给母亲写了几句话,附在了姨父给姨妈的信里。
姨妈收到信,就拿去给母亲看,要母亲回一封。母亲便回了一封。信极短,却将父亲一下子“打倒”,彻底征服——一手漂亮的小楷,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要知道母亲只是小学毕业),直到晚年父亲仍能背出信的全文。可见其魅力。
采畴君:附在我姊夫函中之件悉。
你是我姊夫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间接的(地)也就是我的朋友。你愿我是你纯挚的友朋,当然我也希望你是我纯挚的朋友。
据姊夫来函云,贵校功课很忙,希望你能在忙中抽闲,多多的(地)给我指教。
再谈。祝
安好。
淑娟手泐
三,廿九
几十年后我和姐姐读到此信时,也是感慨不已,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母亲。那时母亲21岁,字好,文笔也好,态度不卑不亢。难怪父亲一辈子做了母亲的粉丝。信上面那个收到日期的字迹(194744收到),是父亲的。
最后那个“手泐”的“泐”,我和姐姐都不认识,只得请教一位书法家朋友,朋友告知,那个“泐”字读乐,四声,是旧时书信用语,手书的意思。
母亲这封信,应该是我们这个家所有家信的鼻祖。
此外,父亲还保留下三封与我有关的信,我读大学时他寄给了我,我猜想他在处理老信件时,实在舍不得,就留下了几封。我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可是其中一封还是被我藏得找不到了,甚是遗憾。好在另两封尚在。
找不到的那封,是我出生时母亲写给父亲的,1958年5月中旬。就半页纸,大意是说,女儿已出生,母女平安,还说女儿很好看,总之全是让父亲放心高兴的话。但我知道那半页纸对母亲来说有多么不易。她生我时难产,大出血,医院却因为她是“右派”置之不理。她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的。但她在给父亲的信上只字未提,只报平安。母亲真的很了不起。
找到的两封,是母亲写给父亲,专门讲我和姐姐趣事的。
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穿了件大衣,好像是大孩子了。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好像亏待了山山,我连忙过去看她,塞给她两颗糖。挺好,嘴里又说又唱,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了……山山现在活泼多了,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开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洗!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她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午后又及)
这封信没有日期,我只能分析,大约是写于我四岁左右,也就是1962年。我是1961年从乡下老家回到母亲身边的,一别三年,和母亲有些生分,别的孩子上幼儿园要哭,我是愿意去的。所以母亲特别讲了我的情况,想让父亲放心。
下面这封信更有趣,母亲语言的简洁生动可见一斑。
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地一翻一白,摊开两只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是大人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迫得我无话可答。
昨天我休息,幼儿园不放假,我进城处理一些事务,傍晚请她们回家玩儿。小白桦来和我谈时事。“妈妈,丁阿姨讲,坏蛋过几天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怕吗?”“不怕。我叫爸爸去打坏蛋,爸爸是解放军。还叫范家大哥哥也去打。范家大哥哥去年参军了,穿着一件新衣服,范家妈妈陪他去的。”这小家伙真有两下。范家的大孩子是去年参军的,记得吗?那时你也在杭州。这事我从未和孩子谈过,可是她却看在眼里,记在肚里了。……范家小儿子问她报了名没有?“怎么可以不报名呢?下半年没得书读。我们都先报名的。”一回家就找那些小哥哥谈论念书的事了。
(7月2日)
大约是1962年,母亲写给父亲的信。1961年母亲结束了三年的“劳动改造”,作为“摘帽右派”回到报社,也将我从乡下接回到身边。父亲那时远在福建修铁路,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抚养我和姐姐,还时常写信给父亲讲两个孩子的情况。这封信和另一封,都写得生动有趣,父亲费尽心思保留了下来。我上大学时他寄给了我。
从姐姐报名上学看,此信也是写于1962年夏天。信中所说“坏蛋要打过来了”,估计是那个时候台湾正在闹“反攻倒算”的事儿。人说三岁看老,也有几分道理,从信上看,三四岁的我就开始较真了,责怪妈妈没看好小乌龟。难怪成年后我总被人说“太好强”,活得累。
最重要的是,从这两封信看,母亲文笔真好,简简单单的叙述,就让我和姐姐的形象跃然纸上。看过的朋友无不夸赞。甚至说,比之我,母亲才应该成为作家。是的,母亲的文字充满灵性。
再摘录几段母亲晚年写给我的信:
最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
你爸最近鱼运亨通,钓鱼事业大有发展。设备方面,增添了海杆,成就方面,那天他一下子钓了拾柒条(大写,省得人家篡改)!他钓鱼我养花,我们相安无事。
我的阳台花园今年种植结构有所变化,主攻菊花和月季。不过眼下我的大叶海棠长得旺盛极了,开了成百朵花,丁零当啷,煞是好看。这海棠是曹老师(邻居)给我的。她给了我后,自己那株就夭折了。于是我还她一株。结果我留下的那株前年冬天一夜寒流袭击冻死了。来年春天她又给我一株,就是眼下开花这株。奇怪的是她自己的一株又在去年冬天冻死了。这是我们间的海棠缘。
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不管国家困难,一味白拿公家的东西,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来势不可挡,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最珍贵的资料。
我虽然受妈妈的影响喜爱文字表达,但对文字的感觉,实在是比妈妈差太远了,客观原因是成长环境不佳,一直闹革命,被“革命语言”裹挟;主观上,我也确实没妈妈聪明。父亲晚年曾说,你和姐姐加起来也顶不上妈妈的聪明。
我常想,母亲如果不遇上那倒霉的政治灾难,一定会成为大记者,或者大作家,写出不少精彩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我和姐姐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整箱旧信件,用旧报纸分类捆包着,其中我的最多,有500多封。
3.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那是1971年,我13岁
在这样一个有写信传统,或者说必须靠写信才能维系的家庭中长大,会写信是必须的。
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1971年,我13岁。
这封信能历时40多年保留到今天,连同那个印着“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信封,肯定是靠父亲这个严谨而又仔细的“档案管理员”。他不仅保存了我的第一封信,还保存了我写给他和母亲的所有的信件。
毋庸置疑,父亲也保存了自1979年以来他和母亲的所有信,他大女儿我姐姐写给他们的所有信,以及他和老朋友老战友之间的通信。总之在他看来值得留存的信件,全都留了下来,一一归类包好,摆放整齐。它们用发黄发脆的报纸包着,上面贴着小纸条,全部是父亲的字迹,如:山山87年4月到89年9月来信。
在一箱子信中,我的最多,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的缘故。从18岁当兵离家到父亲离世,我都远在部队。尤其在1995年前,电话不便,完全靠写信。我的那些信被父亲用报纸包好,捆好,注明了日期。
我数了一下,当兵两年多有20多封;大学时期最多,近150封。在教导队工作三年也多,近80封,调入机关后的头三年,也写了90多封。之后逐年减少。
一直到1997年以后,我还断断续续给父母写过信。多数是为了寄照片,或者寄剪报。因为其他事情,都打电话聊过了。父母也给我写过,也是为了寄剪报,照片,资料什么的。每年春节,我们还互相寄一张贺卡。
翻开父亲留下的一摞摞信件,竟然腾起了细小的灰尘,一时间我仿佛钻进了往事的大仓库,里面堆满了很久没有翻动过的过去了的日子。
这些信件不但按日期排列,还在每封信的信封上注明了收到的日期,父亲是个多么仔细的人。那些小字令我熟悉而又亲切。有一封信的背后还写着,这封信20天才收到。可见当时他和母亲盼望的心情。
父亲的字历来规矩,是长期画图纸写教案形成的,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潦草字,所以我若写潦草了,也常被他批评。“文革”期间,父亲被造反派叫去刻印传单,就是看上了他的字,说不上好,却很认真。他被迫天天去刻传单,以至于中指上磨出一个老茧。作为一个被打倒了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右派”的丈夫,他无法忤逆造反派。
我注意到有一个时期的信封,每一封都被剪了小方洞,显然是邮票被剪了。怎么回事,是父亲在集邮吗?后来我翻到一封自己的信,上面写着:“爸爸,把信封上的邮票寄还给我。”原来是我要求爸爸剪的!我已完全忘了,我自己并不集邮,显然是帮同学在集。父亲牢记在心,自此后,就把信封上的所有纪念邮票都剪下来寄给我了。
随便打开几封信看了看,发现我年轻时并无什么叛逆行为,凡事都告诉父亲母亲,也很顺从他们。除非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会暂时瞒着,等过去了也会告诉他们。同时还发现,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一直以为,自己从当兵后就经济独立了,没有再依靠父母了;从信里发现,在我当兵和上大学期间,我还是时不时地会从父母那里收到资助。婚后的头几年,也接受过父母的资助。一百,两百,在那个时候是很顶用的。除了钱,父母还给我寄过无数的包裹。等我反过来给父母寄钱,已是1984年了,也只寄了150元。到1990年代,我工资高一些了,稿费多一些了,才寄得多一些。但父母总是不愿意接受,总要我说很多理由才行。
重新翻看这些信件,过往的岁月一一从眼前掠过,那些艰难的却是快乐的日子,那些忙碌的却是充实的日子,铺成了我的来时路。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一直默默陪伴着我。内心的欢愉,无法言表。
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柏桦的这句诗。
我很庆幸那个时候给父母写了那么多信,我相信我的那些信还是给了父母很大安慰的(反之亦然)。尤其是在今天,在父亲走了之后,我不至于感到后悔。
信件整理过程中我发现,我写给父母的信,还是有不少缺失。从前后信的内容看,应该还要多。尤其是我当兵以后上大学以后,信写得很勤的。我猜测,那时父母不在一地,且经常搬家,丢失难免。
但就是这样,也已经非常丰富了。
先说第一封信吧。开头总是很重要。
这封信写于1971年,我13岁。读初二。
那时候父亲作为一名铁六师的工程师,在陕西紫阳县毛坝镇,参加修建襄渝线,谓之钻山沟。我和妈妈姐姐,住在部队家属基地重庆北碚。我进入重庆北碚的朝阳中学读初二。我们家是1970年从石家庄迁徙到重庆的。这个前面已交代。因为父亲在山里修路,一年才回来探亲一次,妈妈便要我给他写这封信。
1970年,作为“臭知识分子”的父亲,被当时的铁道兵学院革委会,带有惩罚性地分派到了在深山里修铁路的部队。父亲一到重庆,把我们母女三人撂在招待所就去工地了。半年后他回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我们母女三人都不认识他了,又黑又瘦,胡子拉碴的。直到父亲开口说话,我们才确定是他。可见铁道兵的生活有多艰苦。父亲虽然是地主的儿子,却非常能忍耐。他一句抱怨也没有,将我们搬到家属基地后,又回部队了。母亲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在突然被扔到人生地不熟的小镇后,依然带着两个女儿,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让丈夫安心。
这封信,就是我写给远在大山里的父亲的。虽然很简单,只有一页半纸,但背后的内容却很丰富。
从信的内容看,是因为邻居的杨叔叔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了,妈妈托他带姑姑寄来的一双布鞋给爸爸,顺便要我和姐姐每人给爸爸写一封信,汇报下家里的情况。
我的信全文如下:
爸爸你好:
今天我们上西南医院去了。妈妈晕车,不舒服,所以叫我来写这封信。
医院检查结果,姐姐身体恢复建(健)康,但还要注意。我也去了,医生说我肝和脾都有点儿大,但是检查肝功能正常。不知是什么道理。
上次王叔叔,就是跟你同房间的那个叔叔来过,托他带了手表,被里被面,荼(茶)叶,皮鞋油,收到了吗?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怕你生气,没带。
王洪昭叔叔也来看过我们了,还送给我们很多糖。
我去拉练从十五号出发于二十五号胜利归来了。脚也没有走拐,病也没有得,一切都很好,我的思想,身体,作风各方面都受到锻炼,收获(原文是错字)很大。
路过了嵊江、盐井、合川、云门、龙市、小沔、三汇、后丰台(岩)回北碚,路程大概是三百八十多里。我都坚持走了下来,一回车也没有坐。但是出去十多天我也有不够的地方,比方说,花了许多钱,妈妈给我带了两块钱,我光买吃的就用了一块多,这很不好,没有节约闹革命。还有出去才十天,我就经常想家,想妈妈,经不起艰苦生活的考验,这是由于多年跟在妈妈身边惯成的。出去后,我看到了许多农村的贫下中农生活都还很艰苦,我和他们比起来,差距很大,所以,我决心今后再不浪费了,要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将来工作了,才可以经受住各种艰苦生活的考验。
还有一件事,大姑姑给你和妈妈做了各(各做了)一双布鞋,这回同信一起托杨叔叔带给你。
现在妈妈以(已)经睡了,姐姐也准备睡了,我就暂时阁(搁)笔了。
上次来信你说我字体太潦草,这次我注意了些,但是还不够好,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把字写端正。好!
再见!
你的女儿,山山
(1971年)10月28日晚
……
前言/序言
缘起2013年8月,和我们相濡以沫50多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破碎了。很长时间,我都走不出内心的伤痛。
父亲走的时候87岁,也算高龄了,让我伤痛不已的不是他走得太早,而是太痛苦。眼看着癌症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们却束手无策。这让我一想起来,心里就刺痛。
父亲走了两年后,我和姐姐才去彻底整理他的房间。
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我们发现了满满一箱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贴着小纸条,注明了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全都是父亲的笔迹。
我从来都知道父亲是个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收藏的人。我常说他是我们家的档案管理员。他甚至收藏了我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所得的奖状,最早的一张是1965年的,薄如蝉翼,还是学校老师自己油印的。我发表作品的所有剪报,和关于我的各种消息,他也都一一剪下,归类放好。还有姐姐小时候画的画,姐姐当知青、当工人时得的各种奖状,姐姐发表每一篇文章的报纸和杂志……我们想找什么东西,总是会习惯性地开口问,爸,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样满满一箱信件时,内心还是被震撼了,很感动,也很悲伤。尤其是我,自当兵后,一直没和父母在一起,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全靠写信与父母交流,汇报情况,聆听教诲。因此我的信特别多,数了一下,有510封。
而且我还发现,保存我信件的,不只是父亲,还有母亲。因为有几年,父亲和母亲是不在一起的,我是分别给他们写信的。我写给母亲的信也全部都在。这对母亲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她自己的资料都靠父亲保管。
父亲和母亲,为我留下了这500多封家书。
我即刻拍了几张老信件的照片,发在朋友圈,不料引起了很大反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
有的说,他的父母也为他保留了早年的信件,只是没我那么多;
有的说,很遗憾自己的父母不会写信,从来没有收到过父母的信,很羡慕我;
还有的说,几乎没有和父母分开过,所以没有书信往来;
更多的朋友说,这些信太珍贵了,你应该整理出来,写本书。
起初我并没有这个念头,但说的人多了,心就动了。我想,也许父亲母亲那么仔细地留下这些信,就是希望我有一天会去整理它们。他们一定觉得,那会对我有用。
最后我终于下了决心,开始整理。
我想以此,来纪念我的父亲,感恩我的母亲。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本身就带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感,米黄色封皮像是旧相片褪色的边角,质地粗粝却又让人不忍放手。初读时,我被那种浓稠的笔触和近乎原始的情感深深吸引。文字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碎片,柴米油盐的琐碎,以及那些年轻人在时代洪流中摸索前进时的困惑与挣扎。那种青涩的、尚未被社会磨平的棱角,在字里行间跳跃出来,仿佛能嗅到信纸上墨水洇开的味道。它不是那种一蹴而就的成功学读物,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曾经历过的迷茫期。阅读过程中,我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情节跌宕,而是被某个瞬间的洞察力击中——那种关于“自我”与“原生家庭”之间永恒拉锯战的描述,精准得让人心疼。这书的魅力在于其克制,它把最激烈的情感包裹在最平静的叙述之下,留给读者自己去挖掘底下的暗流。
评分不同于市面上充斥的那些过度包装的“成长记录”,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近乎“考古学”的发掘体验。作者在信件中展现的思维路径,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新一代”如何与父辈的价值体系进行艰难的协商与重构。那些看似随意的家常,实则暗藏着深刻的代际冲突和文化变迁的张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期待”与“现实”落差时的笔法,那种既要尊重传统,又亟需冲破藩篱的矛盾心理,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它没有简单地将父母塑造成阻碍,也没有将自我浪漫化成唯一的先驱,而是呈现了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互相理解与误解的交织过程。这种复杂性,让这本书超越了简单的“家庭回忆录”范畴,上升到了对社会变迁中个体精神图景的描绘。
评分读完这本集结,最直接的感受是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信件中的语气、选择的词汇,甚至是某些表达习惯,都带有浓厚的那个年代印记,这对于年轻读者来说,是一种奇特的“时空旅行”。但令人惊叹的是,尽管背景是特定的,但其核心的人类情感——对被理解的渴望、对远方的憧憬、以及在异乡漂泊时的孤独感——却是高度普适的。我时常会代入到写信人的位置,思考如果是我,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我会如何向远方的父母描绘我的喜怒哀乐。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与父母的交流方式,思考我们是否因为现代生活的便捷,反而丧失了那种需要精心斟酌、字斟句酌才能传达完整心意的能力。这本书像是一剂慢性的“情感催化剂”,促使人去修复那些被时间冲淡的连接。
评分从文学性上讲,这本书展现了一种非常高级的“留白”艺术。作者很少直接去剖析自己的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恐惧或狂喜,而是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描摹、对他人言行的转述,巧妙地暗示了自己当时的情绪状态。例如,对天气变化的细致记录,往往映射着内心的起伏不定;对一顿饭食的简单评价,则可能隐藏着对生活质量的深切关怀。这种含蓄的力量,比直白的宣泄更具穿透力。它迫使我们这些习惯了直给信息的现代人,必须调动起想象力和共情力,去填补那些没有被写出来的部分。这种阅读体验是积极且富有挑战性的,它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之中,最终获得的满足感,是那种经过自己努力捕捉到的“真相”。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独特,它不是线性的、一气呵成的故事,而是散点式的、由无数个“当下”切片构成的拼图。每一封信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品,记录了某个特定时刻的困顿、顿悟或是对未来的憧憬。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读者可以随时中断、随时回归,且每一次重读,都能从不同的侧面捕捉到作者心境的微妙变化。我尤其喜欢那些夹杂在正式叙述中的一些“题外话”——可能是一段对某本书的粗浅评论,可能是一个关于室友的小八卦,正是这些“不重要”的细节,构筑了人物性格的立体感。这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阅读一个精心雕琢的文本,而是在偷窥一份真挚、未经修饰的内心独白。它要求读者付出更多的耐心,去拼凑出一个完整而鲜活的青年形象。
评分东西不错,正版真货价实,比较满意,继续合作
评分书写的很好,开本也大,值得推荐!
评分书很精致,包装完好,没有破损!满意!下次还来京东买书
评分非常感人肺腑的亲情之书!
评分东西不错,正版真货价实,比较满意,继续合作
评分东西不错,正版真货价实,比较满意,继续合作
评分书写的不错,书的质量不错,京东快递不错。满意。
评分书很精致,包装完好,没有破损!满意!下次还来京东买书
评分非常真诚温暖的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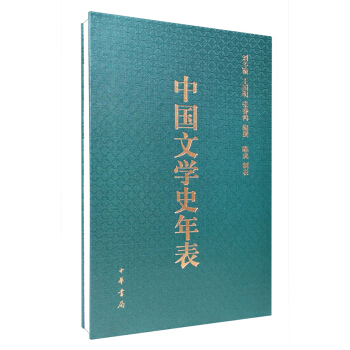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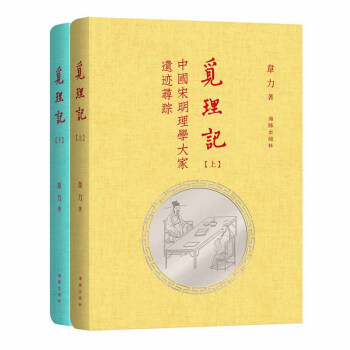

![叶赛宁诗选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Есенина]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32117/5a24eeffN6c0263b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