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第二版):汉学家柯律格对明代艺术的一种新诠释。内容简介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第二版):明代中国发展迅速,在经济领域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得益于这种传统的早期消费社会的模式,奢chi品消费者的数量激增,随之而来的是艺术领域的迅速发展。
图像是该时期主要的奢chi消费品之一,图像不仅以独立的图像环路的形式存在,还出现在墙壁、书籍、印刷品、地图、陶瓷制品、漆盒、纺织品,甚至是华丽的衣裙上,这些艺术品最初只包含一些规则的图形或动植物,后来扩展到描绘自然景观、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或者重要事件,以及与文学作品插图所构建出的世界密切相关的场景。
作者简介
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 ),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曾担任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长达十五年,并自1994年起先后任教于苏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06年,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他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他不仅博学多闻,对于中国传统典籍亦有深厚的造诣,同时经常观照西方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两者结合而提出新颖有洞察力的学术论述,学术成就广受国际学界的赞誉。目录
中译本前言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图绘的地位
第三章 三才天地人
第四章 视觉实践
第五章 木刻版画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第六章 对图像的恐惧
第七章 结论
前言/序言
中译本前言在把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同时,借此机会大概解释一下此书写作的缘起,我想会有所帮助。我同样希望能借此说明本书的某些特性,在中国读者看来,这些特性或许不同寻常,甚至有些让人困惑。十五年以前撰写此书之时,我刚刚放弃了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的工作,转而从事我的第二份工作,在大学里讲授艺术史。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美术馆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关于设计和装饰艺术的博物馆,该馆庞大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中充斥着陶瓷、玉器、漆器、家具、织物和其他此类的物品,在中文里,这些物品通常会被归入“工艺美术”这一宽泛的类别。该馆几乎未藏有任何中国绘画,亦无书法作品。那时我最熟悉的中国艺术作品因此大多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然而,我很了解书法和绘画作品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被赋予更高的地位,正如欧洲传统中作为“高雅艺术”的绘画、雕塑和建筑一样,我也热切希望我的学生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同样迫切希望向我自己和我的新同行们证明,我所研究的中国艺术品可以成为艺术史学科内部更大范围内的论争和交流的一部分。我想要证明这样的研究可以是艺术史主流研究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附加于一种狭隘的、欧洲中心的“艺术的故事(Story of Art)”(借用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爵士名著的标题)之上的“异国情调”的传统。我试图证明,事实上可以有多个故事,研究艺术史的学科如果不把它们考虑在内就会变得十分苍白贫弱。我试图证明,关于中国艺术的研究可以在艺术史学科内部进入更大范围的讨论。正因为如此,本书在某些方面着重针对以下读者群,即欧洲和北美的艺术史学家(例如,书中引用了很多1990年代在艺术史学家中很流行的理论家)。这一读者群体习惯纯粹以西方传统中的素材为基础对“艺术”“绘画”,或是“图画”进行概括性的阐述。我想向他们展示,如果这类综述不把图画制作在中国长久而复杂的历史考虑在内的话,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发现自己著书立说常常源于对另一位学者研究的不满。就本书的写作而言,最初引发了我思考的是出版于1983年的《视觉与绘画:观看的逻辑》(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书中的一段话,该书的著者是诺尔曼·布列逊。布列逊教授在英语世界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学者,该书曾广被(现在仍然如此)人们阅读。著者在书中宣称,在中国和欧洲的绘画传统二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完全的、绝对的差异。著者认为中国绘画始终都通过笔法来强调作画过程的可见性,而欧洲的绘画却始终在掩饰这一过程。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两幅绘画作品来证实这一绝对差异。如果我们精挑细选,把一幅董其昌的作品和一幅达·芬奇的作品放在一起,显而易见,第一幅画的笔触,即所谓“皴”或是“笔法”,非常突出,而第二幅画则并非如此。然而需要我们加以比较的是,比如说,明代宫廷画家边文进的一幅作品和伦勃朗的一幅作品,则并不能体现这种差异。绘画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从中欧同样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中产生的各类画作,都让我觉得进行这类概括是很不明智的。事实上,我要站出来直接表明,我认为“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这种二分法毫无用处。
我现在十分清楚,持有这种二元论看法的并非只有布列逊。在20世纪的中国,此类观点最直白的表达或许出自于大画家潘天寿,即其著名言论“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然而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一声明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来理解,它所传达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而只是在特定时期,面对一系列外来压力所提出的一种策略性需要,希望能为国画保留一个实实在在、至关重要的空间。我同样认为,艺术史学家需要更多地关注以往实际发生的各种绘画活动,关注这些实践活动远比艺术理论(在中国和欧洲皆是)的解读更能展示多样性。而且,即使是理论层面的多样性,也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例如,在17世纪的意大利,马可·博实尼曾说艺术家可见的笔触就是他们的风格所在。在17世纪的中国,当谢肇淛论及绘画中写实手法一贯的重要性时,亦称“古人善画者必能写真”。然而事实上我们却常常读到这类概论,即认为“笔法”是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赏鉴标准,或“写实主义”完全是西式的。我对这类概括表示怀疑,正如我不相信任何一味强调中国或西方绘画特殊性的言论。
本书写作之时,英语国家的艺术史学界正热衷于“视觉文化”的讨论。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围绕以下问题,即有哪些物品或哪一类图像,此前不被重视,而今却应纳入新近得到扩展的艺术史研究中去。因此,本书以“图绘(pictures)”这一范畴来连接绘画作品和印刷作品以及诸如陶瓷或漆器这类物品上的图像(images),这可视为是对那场论争的一个贡献。当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英国的艺术史研究大大拓展了对象范围,不同的群体对这一点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本人认为这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但我们也要继续研究那些经典(例如)绘画作品,把它们作为一个扩展了的领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这同样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研究漆器和瓷器,同样也要研究绘画,而非取而代之。
无可避免地,在回顾一部多年前写就的著作时,著者会发现其中有一些“硬伤”(对此我只能表示歉意),或是对某些段落如今已有不同看法。如果现在来写作此书,我大概不会再用“早期现代中国”来指称明代。这一说法的问题,正如现今很多人都意识到的那样,在于用一个在欧洲历史研究中生成的术语(大致相当于1400年至1800年间)来给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然而我在书中多次使用了这一说法,而且是有意为之,意在借此强迫欧洲学者关注中国的例子,而非只是以站不住脚的证据来断言欧洲的独到之处。如果本书题为《明代中国的图像与视觉文化》,那么欧洲艺术史学家很容易就会说,“这与我无关,我不需要关注它在说什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后悔使用了这个说法,虽然它必然会让中国的读者们感到奇怪。
我同样认为,在本书的结论中,我或许过于强调“图”和“画”二者之间的分别。更确切地说,我声称(我是这样向英国学生解释的)在明代,所有的画都可以归属于一个更大的图的范畴,而非所有的图都可以归属于画的范畴。这与画家龚贤的论述一致,即“古有图而无画”。我现在觉得,这一绝对的区别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持有一定保留态度的二元论。我越研究中国艺术传统的深度和广度——对此我仅有一知半解——就越觉得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做出这类概括性论述,或者是非常谨慎地接受我们在材料中读到的任何泛泛之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会获得一部更加丰富的艺术史。
柯律格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简直是另一个宝库。我留意到,作者在引用古代文献时,通常都会给出详尽的原文出处和版本对照,这为后续的交叉验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不仅仅是中文古籍,作者对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以及同时期其他区域的视觉交流资料的引用也相当全面,显示出扎实的跨文化研究功底。对于希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读者来说,这后面的“工具箱”部分尤为实用。我随手查阅了几个关键术语的注释,发现其注解清晰且信息密度极高,甚至不少注释本身就是一篇精彩的微型论文。这种对学术规范的极致追求,以及对读者后续研究的充分考虑,使得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真正做到了严谨与开放并存。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其实在于它对“研究方法论”的巧妙展示。很多艺术史书籍往往是直接呈现结论,而这本书却更像是一场关于如何“看”的教学实践。作者在分析具体的图像时,会不厌其烦地拆解他的观察步骤——他如何从图像的物质性入手,如何结合当时的社会语境进行文本互证,又如何审视观看者在特定历史场域中的接收方式。这种“展示工作台”的做法,对于我们这些希望提升自身分析能力的读者来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它不仅仅是告诉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教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从中学习到了如何跳脱出单纯的图像描述,进入到更深层的文化批判层面,这种方法论的传授,远比单纯的知识点罗列要宝贵得多。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封面那种沉稳又不失雅致的墨色调,搭配烫金的书名字体,初见便让人心生敬意。内页的纸张质感也挑不出毛病,触感温润,即便是长时间翻阅,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而且,我特别欣赏编辑团队在版式上的用心,文字的排布疏朗有致,大段的论述中穿插着恰到好处的留白,这让复杂的学术内容显得格外清晰易读。很多学术著作的图版往往因为印刷质量差而大打折扣,但这本书不同,那些历史图像的色彩还原度极高,细节纤毫毕现,仿佛能透过纸张触摸到当时的绢帛或石刻,这对于研究视觉文化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装订方式也很扎实,即便是经常翻阅,书脊也不会轻易松散,足见其制作工艺的精良。可以说,光是把它放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体现了出版方对知识载体本身价值的尊重。
评分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过去在接触明代图像时,常常感到资料分散,且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来整合碎片化的信息。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提供了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的图像——比如仅仅是绘画或雕塑——而是以一种非常宏观的视角,将明代的肖像、版画、建筑装饰乃至日常器物上的视觉符号都纳入了考察范围。这种跨媒介、跨门类的整合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打破了我以往将“艺术”与“生活”割裂开的固有思维,让我意识到,在那个时代,视觉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是如何深刻地编织进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极大地拓宽了我对那个时代的认知边界,构建起了一个更为立体和立体的明代视觉生态系统。
评分我最近阅读了市面上好几本关于明代艺术史的著作,但坦白说,很多作品在叙事的流畅性和论证的逻辑性上总有些瑕疵。然而,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却让人耳目一新。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将枯燥的史料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他构建的论述框架极其稳固,每提出一个观点,都能迅速地引出扎实的旁证,层层递进,逻辑链条几乎找不到断点。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概念时所采取的那种克制而精准的笔法,既不流于空泛的理论堆砌,也避免了陷入碎片的细节泥沼。读起来就像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越层层迷雾,最终到达清晰明朗的洞察之地。这种行文的节奏感和结构上的平衡感,使得即便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也能轻松跟上其深邃的思考,而资深研究者则能从中品味到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评分东亚“儒学文化圈”内部政治、社会和思想的互动,以及近代其与西洋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变化。
评分京东购物,体验很不错。
评分早就想看了,可是定价高的吓人,于是只好的报告打折~
评分这次在京东的购物经历很不错,书是正版的,价格上还算比较实惠,而且品相上还是不错的。此外在送货上,物流比较快,比较及时。因为这个书有时候购买下来有时效的需要,送的及时了,对于使用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综上来说,这次还是挺好的,以后也会继续在京东购买。
评分说不错,明代的影响的一个记录
评分嗯哼
评分经典作品,无损快速送货!
评分¥53.50
评分穗嵇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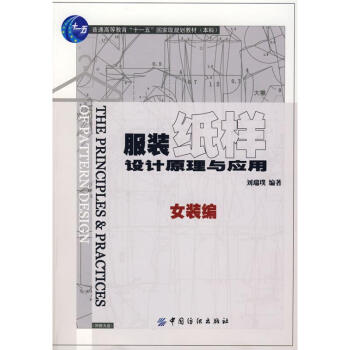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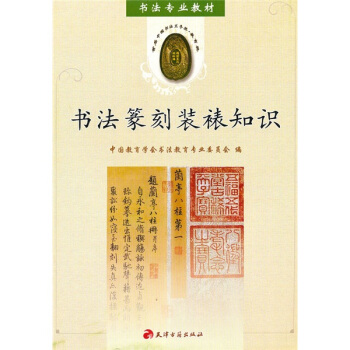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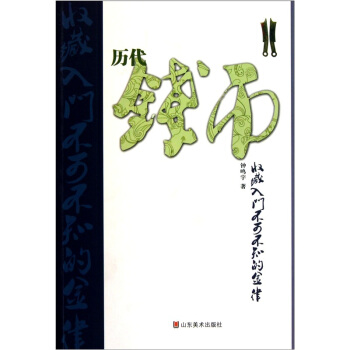


![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程:英语电影视听说(附光盘) [English Movies:Viewing, Listening, Speak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67602/rBEhV1Hc6_0IAAAAAAWmdft48fEAAA7EgJqNZgABaaN49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