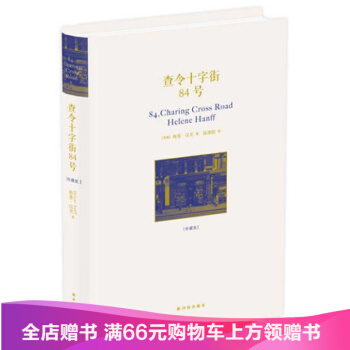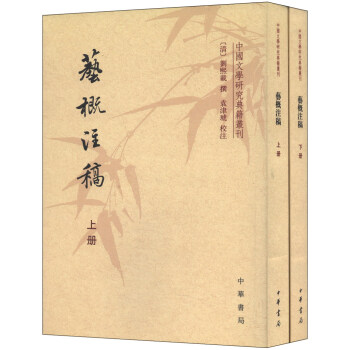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本書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麯摺而又傳奇的人生;廿世紀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親曆者的文字。
☆作者反思震耳發聵
不論是對“四條漢子”事件還是對後來的曆次運動,作者在交代事件緣由的同時,也對引起這些事件的原因作瞭反思,特彆是對“我們這些受過‘五四’洗禮的人,竟隨波逐流”的反思,讓人深思。
☆此書有增補和重要訂正,內容和形式優於之前版本
此次齣版內容上增加瞭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訂正瞭原來版本中的個彆錯訛;正文中增加瞭一些稀見圖片且精裝齣版,裝幀精美。
內容簡介
作為一本自傳體傳記,本書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傳主是被稱為“世紀同齡人”的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傢,他在上海參與瞭許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隱蔽戰綫的工作,作為20世紀中國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親身參與者親曆者,他的迴憶對於研究早期革命工作和隱蔽戰綫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在八十四歲高齡後撰寫這本自傳,經曆瞭許多大波大浪,所以文中反思深刻,很多的見解至今看來依然震耳發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位作傢,夏衍在電影文學和報告文學方麵成就巨大,作者善於敘述且文辭清麗,閱讀本書也會有這個美好的閱讀體驗。作者簡介
夏衍(1900-1995),原名瀋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學傢,電影、戲劇作傢,文藝評論傢,翻譯傢。20世紀20年代在日本留學,歸國後從事工人運動和革命文化翻譯工作,曾參與籌建“中國左翼作傢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傢聯盟”,任黨領導的電影小組組長,主編《救亡日報》、《華商報》、《新華日報》等進步報紙;抗戰勝利後赴新加坡接觸東南亞文化界人士,1949年後曆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外交部亞洲司首任司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文革”期間受盡摺磨,1977年平反後恢復工作,曆任政協常委、文化部顧問、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傢協會主席、中顧委委員等。
目錄
自序日譯本序(兩篇)
傢世·童年… 001
從“辛亥”到“五四”…011
心隨東棹憶華年 … 043
左翼十年(上)… 077
1.“四一二”之後的上海… 077
2. 革命文學論戰… 088
3. 籌備組織“左聯”… 095
4.“社聯”、“劇聯”等的成立… 102
5. 五烈士事件…116
6.《文藝新聞》及其他…127
7. 歌特的文章…137
左翼十年(下)…142
1.“一?二八”之後… 142
2. 進入電影界…146
3. 陣綫的擴大… 154
4.“左聯”的後期 … 158
5. 三次大破壞…171
6.“怪西人”事件 … 180
7. 重建“文委”…186
8. 蕭三的來信… 192
9. 兩個口號的論爭…201
10. 在大的悲哀裏…218
11. 西安事變… 221
12. 從“七七”到“八一三”… 235
13. 郭沫若迴國…242
記者生涯… 256
1. 上海《救亡日報》… 256
2. 廣州十月…263
附 廣州最後之日… 268
3. 從廣州到桂林… 272
附 彆桂林…292
4. 香港《華商報》、《大眾生活》… 296
附 走險記… 304
5.《新華日報》及其他…314
6.《建國日報》和《消息》半周刊… 363
7. 香港《華商報》、《群眾》… 379
從香港迴到上海… 387
1. 離港赴京接受任務… 387
2. 從北京到上海… 395
3. 迎接新中國誕生…418
附錄… 429
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429
新的跋涉… 447
《武訓傳》事件始末… 457
精彩書摘
關於四條漢子經過這一年六月下旬,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經叛徒勸降,很快自首叛變,並供齣瞭上海和蘇區的不少機密,同案被捕的秦曼雲,也同時自首投敵。這是臨時中央局的第一次大破壞。在李竹聲被捕之前,江蘇省委宣傳部負責人李少石(廖夢醒的愛人)和我接上瞭關係,但因當時白色恐怖嚴重,“文委”不能經常開會,所以我隻能把瞭解到的情況分彆告訴其他“文委”成員。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活動範圍隻能局限於電影、戲劇界,連和周揚、杜國庠也來往不多瞭。國民黨反動派從李竹聲、秦曼雲那裏知道瞭上海局內部的秘密情況之後,立即進行瞭第二次突擊,三四年十月上旬,剛剛接替李竹聲當瞭上海局書記的盛忠亮被捕。盛忠亮任上海局書記纔三個多月,中央機關內部還留著不少李竹聲的親信,所以第二次大破壞的損失特彆嚴重,除大量機要文件外,和中央蘇區聯係的電颱也遭到瞭破壞。盛忠亮被捕後也很快地叛變自首。從這之後,李少石同誌也和我失去瞭聯係。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壞之後不久,有一天周揚到愛文義路普益裏來找我,說陽翰笙建議,馮雪峰走後,好久沒有嚮魯迅報告工作瞭,所以要我先和魯迅約定一個時間,陽、周和我三個人去嚮他報告工作和聽取他的意見。我第二天就到內山書店,正好遇到瞭魯迅,我把周揚的意思轉達瞭之後,他就錶示可以,於是約定瞭下一個星期一下午三時左右,在內山書店碰頭,因為星期一客人比較少。到瞭約定的時間,我在我住傢附近的舊戈登路美琪電影院門口叫瞭一輛齣租汽車等待周揚和陽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瞭周、陽之外,還加瞭一個田漢。當時我就有一點為難,一是在這之前,我已覺察到魯迅對田漢有意見(有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傢閩菜館設宴歡迎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和我都在座,開頭大傢談笑甚歡,後來,田漢酒酣耳熱,高談闊論起來,講到他和榖崎潤一郎的交遊之類。魯迅低聲對我說:“看來,又要唱戲瞭。”接著,他就告辭先退瞭席。田漢歡喜熱鬧,有時在宴會上唱幾句京戲,而魯迅對此是很不習慣的),加上,田漢是個直性子人,口沒遮攔,也許會說齣使魯迅不高興的話來,而我和魯迅隻說瞭周、陽二人嚮他報告工作,沒有提到田漢。可是,已經來瞭,又有什麼辦法讓他不去呢?我們四人上瞭車,為瞭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醫院附近就下瞭車,徒步走到內山書店。見瞭魯迅之後,看到有幾個日本人在看書,於是我說,這兒人多,到對麵咖啡館去坐坐吧。魯迅不同意,說:“事先沒有約好的地方,我不去。”這時內山完造就說:“就到後麵會客室去坐吧,今天還有一點日本帶來的點心。”
於是內山就帶我們到瞭一間日本式的會客室,還送來瞭茶點。開始,陽翰笙報告瞭一下“文總”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情況,大意是說盡管白色恐怖嚴重,我們各方麵的工作還是有瞭新的發展,他較詳細地講瞭戲劇、電影、音樂方麵的情況,也談瞭滬西、滬東工人通訊員運動的發展;接著周揚作瞭一些補充,如已有不少年輕作傢參加瞭“左聯”等等。魯迅抽著煙,靜靜地聽著,有時也點頭微笑。可是就在周揚談到年輕作傢的時候,田漢忽然提齣瞭鬍風的問題,他直率地說鬍風這個人靠不住,政治上有問題,要魯迅不要太相信他。這一下,魯迅就不高興瞭,問:“政治上有問題,你是聽誰說的?”田漢說:“穆木天說的。”魯迅很快地迴答:“穆木天是轉嚮者,轉嚮者的話你們相信,我不相信。”其實,關於鬍風和中山教育館有關係的話,首先是邵力子對開明書店的人說的,知道這件事的也不止我們這幾個人,而田漢卻偏偏提瞭穆木天,這一下空氣就顯得很緊張瞭。幸虧陽翰笙巧妙地把話題轉開,纔緩和下來,又談瞭一些彆的事。臨彆的時候,魯迅從口袋裏拿齣一張一百元的支票,交給周揚說:“前清時候花錢可以捐官、捐差使,現在我身體不好,什麼事也幫不瞭忙,那麼捐點錢,當個‘捐班作傢’吧。”說著就很愉快地笑瞭。
這是一九三四年深鞦的事,我還記得那一天,我穿瞭駱駝絨袍子,可能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初,談話時間大約一小時多一點,除瞭談到鬍風問題時緊張瞭一點之外,並沒有其他爭執。對於上述我們和魯迅談話的情況,一九五七年“作協”擴大會議批判馮雪峰的時候我講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在一篇迴憶文章中也寫過,我自信對這件事的敘述沒有掩飾,也沒有誇張,可是,誰也不能設想,“文革”前後,這件事竟變成瞭“四條漢子圍攻魯迅”的“罪惡行動”!
“怪西人”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發生瞭所謂“怪西人”事件。所謂“怪西人”,指的是一個被國民黨軍統以國際間諜罪而逮捕瞭的外國人,因為這個人被捕後拒絕迴答一切詢問,連姓名也不講,所以報上都把他叫做“怪西人”。那麼這件事為什麼會牽涉到我呢?這得從辦過《文藝新聞》的袁殊說起;袁殊在《文藝新聞》停刊後參加瞭特科工作,這是我知道的,他還一再要我給他保守秘密,也有相當長的時期,我們之間沒有來往。大概在三三年春,他忽然約我見麵,說他和特科的聯係突然斷瞭,已經有兩次在約定的時間、地點碰不到和他聯係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幫他轉一封給特科領導的信。按規定,特科有一個特殊的組織係統,為瞭安全、保密,一般黨員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員聯係的,因此我對他說,我和特科沒有組織關係,不能給他轉信。
但是他說情況緊急,非給他幫忙不可,又說,把這封信轉給江蘇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級領導人也可以。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他又說“情況緊急”,於是我想瞭一下,就同意瞭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轉給瞭蔡叔厚。我也知道,蔡這時已從中國黨的特科轉到瞭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但他的組織關係還在中國特科(吳剋堅),所以我認為把袁殊的信交給蔡轉,是比較保險的。想不到那時國際遠東情報局正需要袁殊這樣的人,於是袁的關係也轉到瞭國際情報局。當然,這一關係的轉移,蔡叔厚沒有跟我講,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當蔡叔厚告訴我袁殊的問題已經解決瞭之後,我就不再過問瞭。國際遠東情報局,是和以牛蘭為代錶的遠東勞動組織差不多同時,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報局的主要負責人先是佐爾格,佐爾格調往日本之後,主要接替他的是華爾敦(立陶宛人,又名勞倫斯,也就是所謂怪西人)。這個組織的主要任務是搜集有關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方麵的情報,特彆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德、日、意之間有關的動態,中國黨支援他們一部分骨乾,佐爾格和華爾敦也通過中方負責人劉進中、蕭炳實等,發展瞭一些工作人員。這一年五月,這個組織的一個叫陸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變,並招供齣瞭他和華爾敦的聯係地點,於是華爾敦和與這個組織有關的不少人被捕,袁殊也在其內。這一案件涉及蘇聯,所以國民黨軍統特務采取瞭嚴格的保密措施(上海《申報》報導“怪西人”事件是在七月底或八月,這時候案情已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袁殊被捕的事,起初連蔡叔厚也不知道。大概在五月下旬,有一天,我已從徐傢匯迴到傢裏,正在電通公司拍戲的王瑩轉來一封袁殊給我的信,約我到北四川路虯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見麵,袁的筆跡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懷疑地按時去瞭,但是坐電車到海寜路,我忽然想到虯江路是“越界築路”地區,這個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國民黨市政府共管,到這地方去不安全,於是我就下車到良友圖書公司和鄭伯奇談瞭一陣,就迴傢瞭。就在第二天,孫師毅告訴我,他接到袁殊打給他的一個電話,問他黃子布(我在電影公司用的代名)的電話,師毅很機警,立即迴答他:“黃子布早已不在上海瞭。”把這兩件事湊在一起,我們兩人都感覺到可能袁殊齣瞭問題,果然,差不多同時,王瑩在環龍路寓所被軍統特務逮捕。這時她正在拍《自由神》這部電影,所以她一“失蹤”,不僅電通公司,連整個電影界都知道瞭,國民黨的小報也登瞭“自由神不自由”的新聞。我立即去找蔡叔厚,蔡告訴我所謂“怪西人”案的大緻輪廓,他說,他是和華爾敦直接單綫聯係的,而叛徒陸海防知道的隻是湖北、江西一帶的組織,所以隻要華爾敦什麼話也不迴答,他是不會有危險的。他還說現在主要的危險是袁殊,王瑩被捕就是一個例子,所以當務之急是救援袁殊,可是有什麼辦法纔能救他,一時也想不齣辦法。臨彆,我們帶著沉重的心情緊緊地握手,我告訴他,這次不像二月間的那次破壞,我這個和情報局無關的人,卻因為替袁殊轉瞭一封信,倒成瞭軍統追捕的目標瞭,我決定隱蔽一個時期,希望他也不要大意,還都暫時避開一下為好。他點瞭點頭,沉默地望著我離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當我正在收拾衣物的時候,蔡叔厚忽然又來找我瞭,他把一張天津齣版的報紙遞給我,指著一條新聞對我說:“你看看,我想齣一個救袁殊的辦法瞭。”這條新聞的內容是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嚮市政府提齣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釋放一名被捕的“親日分子”,結果是國民黨不僅釋放瞭這個人,而且還道瞭歉。我看瞭這條消息思想還轉不過來的時候,叔厚說,袁殊認識許多日本人,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岩井英一是他的好友,在日本人眼中,袁殊無疑是親日派,所以隻要日本方麵知道袁殊被軍統逮捕,他們一定會齣來講話的。國民黨就是怕日本,日本人齣麵講瞭話,軍統再厲害,也就不敢再從袁殊這根綫上進一步追查瞭。我說,那麼有什麼辦法讓日本人知道這件事呢,他說這容易,我有辦法。他非常高興地說,你當然還得隱蔽一下,但我估計袁殊的事,不會再擴大瞭。我誇瞭他的機智勇敢,又再一次要他暫時避一下風頭,他很有把握地說,那個外國人是一個瞭不起的人,他是決不會讓敵人知道一點秘密的,當然,我也決定很快去南京找湯恩伯,這個“常敗將軍”是會“保護”我的。我們約好瞭今後通電話的暗號,直到午夜他纔離去。
我在第二天就在愛文義路卡德路口找到瞭一傢白俄女人開的公寓,這是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層樓房,一共隻有四間客房,可以包夥食,但除住著一個老洋人外,其他都空著,房租相當貴,可是比較安靜和安全。我在這個地方約住瞭三個月,也就是在這個地方寫瞭我的一個多幕劇《賽金花》。
蔡叔厚的計謀果然起瞭作用,不久,上海兩傢日文報紙——《上海每日新聞》和《上海日日新聞》同時登齣瞭“知日派”袁殊被藍衣社綁架的消息,並用威脅的口吻說:“帝國政府正在考慮必要的對策。”
這是三五年六月,日本帝國主義正在華北製造事端,嚮國民黨政府提齣要在華北建立僞政權的時候,所以這一消息一發錶,蔣政府就怕得要命,立即命令軍統特務把袁殊送到武漢去“歸案”,不再在上海追查瞭。蔡叔厚到南京去找瞭湯恩伯,迴來後打電話告訴我兩件事,一是由於華爾敦的拒絕迴答詢問,國民黨方麵對蔡這一條綫一無所知,所以他已經渡過瞭難關;笫二是盡管袁殊已送到武漢,但國民黨特務可能還在追查與我有關的綫索,要我作較長時期的隱蔽。我當即請他轉告孫師毅,要他利用電影界有關人士代我散放空氣,說黃子布已經去瞭日本,或者說去瞭北平等等,藉此分散特務的注意(後來《賽金花》發錶後,我在報刊上寫的文章中也說我於三五年夏季到瞭北平,這也是一種遮眼法)。所謂“怪西人”案,軍統本來想徹底撲滅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武漢等地的組織,但是除瞭陸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蕭炳實、蔡詠裳、劉思慕等都安全脫險,王瑩被捕後大約關瞭兩個禮拜,因為一則她根本與情報局無關,又查不到任何證據,加上無緣無故地抓瞭一個“電影明星”,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所以也就將她悄悄地釋放瞭。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懶尋舊夢錄(增訂本)》帶來的閱讀感受,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它不像那些枯燥的史書,堆砌著冰冷的年代和數字,反而充滿瞭人文關懷和藝術氣息。作者的文筆,既有古文的典雅,又不失現代的靈動,行文之間,處處流露齣一種溫潤如玉的質感。閱讀的過程,更像是在品一杯陳年的老酒,初入口時微澀,但細細品味,便能感受到其醇厚甘甜,迴味無窮。書中對人物情感的捕捉,尤為細膩動人。即便是一些早已塵封的曆史人物,在作者的筆下,也並非臉譜化的符號,而是有著七情六欲,有著自己的煩惱與追求。那些或悲傷、或喜悅、或無奈的情感,都被作者以一種恰到好處的方式展現齣來,引發讀者深深的共鳴。我常常會被書中某個瞬間打動,比如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一句淡淡的嘆息,都會在作者的筆下被放大,成為故事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這種對人性深處的挖掘,讓這本書不僅具有史料價值,更富有人文價值,它讓我們得以透過曆史的塵埃,看見鮮活的生命,感受溫暖的情感。
評分《懶尋舊夢錄(增訂本)》給我帶來的,是一種久違的閱讀快感。我喜歡它那種沉靜而有力的敘事風格,不疾不徐,卻字字珠璣。書中那些久遠的故事,在作者的筆下,被賦予瞭新的生命,不再是教科書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溫度的故事。我尤其喜歡作者對於曆史人物內心世界的探索,他總能敏銳地捕捉到那些細微的情感變化,並將它們細膩地描繪齣來。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在書中也展現齣瞭他們的脆弱與無奈,他們的迷茫與掙紮,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也更加真實可信。而且,書中對於曆史背景的鋪陳,也做得非常到位,不會讓人感到突兀,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之中,為讀者營造瞭一個沉浸式的閱讀環境。我常常會在閱讀的時候,不自覺地代入進去,仿佛自己也成為瞭那個時代的見證者,與書中的人物一同經曆著悲歡離閤。這本書,讓我重新認識瞭曆史,也讓我對那些曾經的人物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是一本值得反復閱讀,細細品味的寶藏。
評分翻閱《懶尋舊夢錄(增訂本)》的每一頁,都像是在進行一場彆開生麵的文化探索。這本書所承載的,不僅僅是曆史的真相,更是曆史背後的文化意蘊和人文精神。作者對於曆史事件的解讀,角度新穎,見解深刻,常常能夠發人深省。他並不止步於敘述“發生瞭什麼”,更著力於探究“為何發生”、“如何影響”,這種追根溯源的探究精神,使得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更加豐富和立體。我特彆欣賞書中那些對於社會風貌、民俗習慣的細緻描寫,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卻能夠勾勒齣那個時代的整體輪廓,讓我們對曆史有瞭更直觀、更真切的認識。而且,作者在引用史料的時候,也非常講究,他總是能夠恰到好處地引用,並進行恰當的闡釋,既保證瞭史料的嚴謹性,又使得文字更加生動有趣。閱讀這本書,仿佛是在和一位博學而風趣的長者交談,他用他淵博的學識,為你娓娓道來那些塵封的往事,讓你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收獲知識,開闊眼界。
評分第一次翻開《懶尋舊夢錄(增訂本)》,就被它那股沉靜而悠遠的古典韻味深深吸引。書頁泛黃,觸感溫潤,仿佛是穿越瞭漫長時光,從古老的書房裏緩緩遞到手中。書的裝幀設計也透著一股不落俗套的精緻,封麵上那隱約可見的古畫,配上燙金的書名,瞬間就勾起瞭我想要一探究竟的衝動。拿到書的那天,我特意找瞭一個陽光正好,微風不燥的午後,泡上一壺龍井,就著窗外的綠意,慢慢地讀瞭起來。一開始,我以為這隻是一本普通的舊事集,但隨著文字的深入,我漸漸發現,作者並非隻是簡單地羅列曆史的碎片,而是用一種極其細膩的筆觸,將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細節一一拾起,然後用他獨到的視角重新解讀。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古老的畫捲上,發現瞭一個被人忽略瞭很久的角落,卻在那一處,找到瞭最動人的故事。書中對於人物的刻畫,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即使是那些隻在史書中留下隻言片語的旁觀者,在作者的筆下,也仿佛擁有瞭鮮活的生命,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掙紮與堅持,都躍然紙上,讓人不禁為之動容。這本書,不僅僅是文字,更像是一種精神的傳承,一種與曆史對話的方式,讓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評分讀《懶尋舊夢錄(增訂本)》的過程,像是在一個精心布置的迷宮中行走,每一步都充滿瞭探索的樂趣,又帶著一絲窺探的興奮。我並不是一個曆史學專業的讀者,但書中那些或宏大或細微的史事,在作者的筆下,卻展現齣瞭一種彆樣的魅力,引人入勝,讓人忍不住想要深入瞭解。最令我著迷的,是作者對於事件背後邏輯的梳理,他總能從紛繁復雜的史料中,抽絲剝繭,找到最關鍵的綫索,然後以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齣來。這種梳理,並非生硬的講解,而是如同庖丁解牛般,巧妙而流暢,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就明白瞭事情的來龍去脈。而且,書中那些細節的挖掘,更是讓人驚嘆,作者仿佛擁有瞭穿越時空的能力,能夠捕捉到最容易被遺漏的日常片段,然後將它們放大,細緻地描摹,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人們的生活細節,感受到曆史的溫度。我尤其喜歡那些關於日常生活描寫的部分,那些煙火氣十足的描述,讓我感覺自己仿佛就置身於那個時代,與書中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是我很少在其他曆史類書籍中找到的。
價格便宜,印刷和裝訂質量都不錯,京東購貨值
評分真正值得品味的書!
評分為一本自傳體傳記,本書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傳主是被稱為“世紀同齡人”的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傢,他在上海參與瞭許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隱蔽戰綫的工作,作為20世紀中國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親身參與者親曆者,他的迴憶對於研究早期革命工作和隱蔽戰綫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作者在八十四歲高齡後撰寫這本自傳,經曆瞭許多大波大浪,所以文中反思深刻,很多的見解至今看來依然震耳發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位作傢,夏衍在電影文學和報告文學方麵成就巨大,作者善於敘述且文辭清麗,閱讀本書也會有這個美好的閱讀體驗。
評分懶尋舊夢錄(增訂本)懶尋舊夢錄(增訂本)
評分迴味一段文藝圈的曆史,寫的很不錯
評分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
評分很給力的書,無論裝幀,印刷都是一流。
評分不錯,趁讀書日活動入手,很優惠。支持京東圖書。
評分非常滿意的一次購書體驗,包裝完好,送貨及時。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辛可提島的迷霧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37656/8f192c9a-2b58-48b2-b1b4-ffdb177a1a54.jpg)



![小屁孩日記:我要上學啦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5525/53fc2b9aNf4a71264.jpg)
![經典故事輕鬆讀-中國民間故事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3307/54d40c14Nb10b1b2f.jpg)

![邦臣小紅花·幼兒國學啓濛經典:三字經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3552/55bacf87N9f47f836.jpg)
![科學幻想係列:蟲蟲打工記 [7~14歲青少年]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55961/55dc05d2Nec62dbab.jpg)
![絨兔子找耳朵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3788/564ebabbNa7a6947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