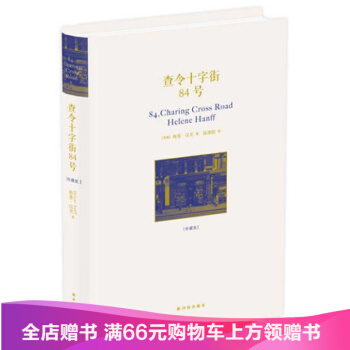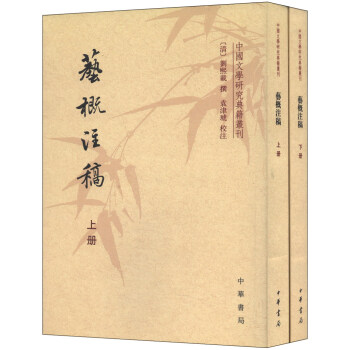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本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廿世纪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亲历者的文字。
☆作者反思震耳发聩
不论是对“四条汉子”事件还是对后来的历次运动,作者在交代事件缘由的同时,也对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作了反思,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的反思,让人深思。
☆此书有增补和重要订正,内容和形式优于之前版本
此次出版内容上增加了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订正了原来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正文中增加了一些稀见图片且精装出版,装帧精美。
内容简介
作为一本自传体传记,本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传主是被称为“世纪同龄人”的夏衍,他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革命家,他在上海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工作,有的甚至是隐蔽战线的工作,作为20世纪中国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亲身参与者亲历者,他的回忆对于研究早期革命工作和隐蔽战线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在八十四岁高龄后撰写这本自传,经历了许多大波大浪,所以文中反思深刻,很多的见解至今看来依然震耳发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位作家,夏衍在电影文学和报告文学方面成就巨大,作者善于叙述且文辞清丽,阅读本书也会有这个美好的阅读体验。作者简介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革命文化翻译工作,曾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党领导的电影小组组长,主编《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纸;抗战胜利后赴新加坡接触东南亚文化界人士,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首任司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等,“文革”期间受尽折磨,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历任政协常委、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目录
自序日译本序(两篇)
家世·童年… 001
从“辛亥”到“五四”…011
心随东棹忆华年 … 043
左翼十年(上)… 077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077
2. 革命文学论战… 088
3. 筹备组织“左联”… 095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102
5. 五烈士事件…116
6.《文艺新闻》及其他…127
7. 歌特的文章…137
左翼十年(下)…142
1.“一?二八”之后… 142
2. 进入电影界…146
3. 阵线的扩大… 154
4.“左联”的后期 … 158
5. 三次大破坏…171
6.“怪西人”事件 … 180
7. 重建“文委”…186
8. 萧三的来信… 192
9. 两个口号的论争…201
10. 在大的悲哀里…218
11. 西安事变… 221
12. 从“七七”到“八一三”… 235
13. 郭沫若回国…242
记者生涯… 256
1. 上海《救亡日报》… 256
2. 广州十月…263
附 广州最后之日… 268
3. 从广州到桂林… 272
附 别桂林…292
4. 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296
附 走险记… 304
5.《新华日报》及其他…314
6.《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363
7. 香港《华商报》、《群众》… 379
从香港回到上海… 387
1. 离港赴京接受任务… 387
2. 从北京到上海… 395
3. 迎接新中国诞生…418
附录… 429
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429
新的跋涉… 447
《武训传》事件始末… 457
精彩书摘
关于四条汉子经过这一年六月下旬,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经叛徒劝降,很快自首叛变,并供出了上海和苏区的不少机密,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同时自首投敌。这是临时中央局的第一次大破坏。在李竹声被捕之前,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少石(廖梦醒的爱人)和我接上了关系,但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文委”不能经常开会,所以我只能把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告诉其他“文委”成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于电影、戏剧界,连和周扬、杜国庠也来往不多了。国民党反动派从李竹声、秦曼云那里知道了上海局内部的秘密情况之后,立即进行了第二次突击,三四年十月上旬,刚刚接替李竹声当了上海局书记的盛忠亮被捕。盛忠亮任上海局书记才三个多月,中央机关内部还留着不少李竹声的亲信,所以第二次大破坏的损失特别严重,除大量机要文件外,和中央苏区联系的电台也遭到了破坏。盛忠亮被捕后也很快地叛变自首。从这之后,李少石同志也和我失去了联系。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之后不久,有一天周扬到爱文义路普益里来找我,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我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了鲁迅,我把周扬的意思转达了之后,他就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一个星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人比较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在我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了周、阳之外,还加了一个田汉。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座,开头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先退了席。田汉欢喜热闹,有时在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去呢?我们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看书,于是我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室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
于是内山就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室,还送来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其实,关于胡风和中山教育馆有关系的话,首先是邵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知道这件事的也不止我们这几个人,而田汉却偏偏提了穆木天,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幸亏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些别的事。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着就很愉快地笑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深秋的事,我还记得那一天,我穿了骆驼绒袍子,可能是十月下旬或十一月初,谈话时间大约一小时多一点,除了谈到胡风问题时紧张了一点之外,并没有其他争执。对于上述我们和鲁迅谈话的情况,一九五七年“作协”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时候我讲过,“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写过,我自信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掩饰,也没有夸张,可是,谁也不能设想,“文革”前后,这件事竟变成了“四条汉子围攻鲁迅”的“罪恶行动”!
“怪西人”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发生了所谓“怪西人”事件。所谓“怪西人”,指的是一个被国民党军统以国际间谍罪而逮捕了的外国人,因为这个人被捕后拒绝回答一切询问,连姓名也不讲,所以报上都把他叫做“怪西人”。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会牵涉到我呢?这得从办过《文艺新闻》的袁殊说起;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工作,这是我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间没有来往。大概在三三年春,他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经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
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吴克坚),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诉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国际远东情报局,是和以牛兰为代表的远东劳动组织差不多同时,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建立的。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先是佐尔格,佐尔格调往日本之后,主要接替他的是华尔敦(立陶宛人,又名劳伦斯,也就是所谓怪西人)。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德、日、意之间有关的动态,中国党支援他们一部分骨干,佐尔格和华尔敦也通过中方负责人刘进中、萧炳实等,发展了一些工作人员。这一年五月,这个组织的一个叫陆海防的人在上海被捕叛变,并招供出了他和华尔敦的联系地点,于是华尔敦和与这个组织有关的不少人被捕,袁殊也在其内。这一案件涉及苏联,所以国民党军统特务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上海《申报》报导“怪西人”事件是在七月底或八月,这时候案情已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袁殊被捕的事,起初连蔡叔厚也不知道。大概在五月下旬,有一天,我已从徐家汇回到家里,正在电通公司拍戏的王莹转来一封袁殊给我的信,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新雅茶室和他见面,袁的笔迹我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毫不怀疑地按时去了,但是坐电车到海宁路,我忽然想到虬江路是“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方由租界工部局和国民党市政府共管,到这地方去不安全,于是我就下车到良友图书公司和郑伯奇谈了一阵,就回家了。就在第二天,孙师毅告诉我,他接到袁殊打给他的一个电话,问他黄子布(我在电影公司用的代名)的电话,师毅很机警,立即回答他:“黄子布早已不在上海了。”把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我们两人都感觉到可能袁殊出了问题,果然,差不多同时,王莹在环龙路寓所被军统特务逮捕。这时她正在拍《自由神》这部电影,所以她一“失踪”,不仅电通公司,连整个电影界都知道了,国民党的小报也登了“自由神不自由”的新闻。我立即去找蔡叔厚,蔡告诉我所谓“怪西人”案的大致轮廓,他说,他是和华尔敦直接单线联系的,而叛徒陆海防知道的只是湖北、江西一带的组织,所以只要华尔敦什么话也不回答,他是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袁殊,王莹被捕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当务之急是救援袁殊,可是有什么办法才能救他,一时也想不出办法。临别,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紧紧地握手,我告诉他,这次不像二月间的那次破坏,我这个和情报局无关的人,却因为替袁殊转了一封信,倒成了军统追捕的目标了,我决定隐蔽一个时期,希望他也不要大意,还都暂时避开一下为好。他点了点头,沉默地望着我离去。
就在第二天晚上,当我正在收拾衣物的时候,蔡叔厚忽然又来找我了,他把一张天津出版的报纸递给我,指着一条新闻对我说:“你看看,我想出一个救袁殊的办法了。”这条新闻的内容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名被捕的“亲日分子”,结果是国民党不仅释放了这个人,而且还道了歉。我看了这条消息思想还转不过来的时候,叔厚说,袁殊认识许多日本人,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是他的好友,在日本人眼中,袁殊无疑是亲日派,所以只要日本方面知道袁殊被军统逮捕,他们一定会出来讲话的。国民党就是怕日本,日本人出面讲了话,军统再厉害,也就不敢再从袁殊这根线上进一步追查了。我说,那么有什么办法让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呢,他说这容易,我有办法。他非常高兴地说,你当然还得隐蔽一下,但我估计袁殊的事,不会再扩大了。我夸了他的机智勇敢,又再一次要他暂时避一下风头,他很有把握地说,那个外国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决不会让敌人知道一点秘密的,当然,我也决定很快去南京找汤恩伯,这个“常败将军”是会“保护”我的。我们约好了今后通电话的暗号,直到午夜他才离去。
我在第二天就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找到了一家白俄女人开的公寓,这是一座古老的西式二层楼房,一共只有四间客房,可以包伙食,但除住着一个老洋人外,其他都空着,房租相当贵,可是比较安静和安全。我在这个地方约住了三个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写了我的一个多幕剧《赛金花》。
蔡叔厚的计谋果然起了作用,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和《上海日日新闻》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用威胁的口吻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
这是三五年六月,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在华北建立伪政权的时候,所以这一消息一发表,蒋政府就怕得要命,立即命令军统特务把袁殊送到武汉去“归案”,不再在上海追查了。蔡叔厚到南京去找了汤恩伯,回来后打电话告诉我两件事,一是由于华尔敦的拒绝回答询问,国民党方面对蔡这一条线一无所知,所以他已经渡过了难关;笫二是尽管袁殊已送到武汉,但国民党特务可能还在追查与我有关的线索,要我作较长时期的隐蔽。我当即请他转告孙师毅,要他利用电影界有关人士代我散放空气,说黄子布已经去了日本,或者说去了北平等等,借此分散特务的注意(后来《赛金花》发表后,我在报刊上写的文章中也说我于三五年夏季到了北平,这也是一种遮眼法)。所谓“怪西人”案,军统本来想彻底扑灭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武汉等地的组织,但是除了陆海防、袁殊及一些不很重要的人之外,萧炳实、蔡咏裳、刘思慕等都安全脱险,王莹被捕后大约关了两个礼拜,因为一则她根本与情报局无关,又查不到任何证据,加上无缘无故地抓了一个“电影明星”,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也就将她悄悄地释放了。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翻阅《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的每一页,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探索。这本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真相,更是历史背后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角度新颖,见解深刻,常常能够发人深省。他并不止步于叙述“发生了什么”,更着力于探究“为何发生”、“如何影响”,这种追根溯源的探究精神,使得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加丰富和立体。我特别欣赏书中那些对于社会风貌、民俗习惯的细致描写,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能够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整体轮廓,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直观、更真切的认识。而且,作者在引用史料的时候,也非常讲究,他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引用,并进行恰当的阐释,既保证了史料的严谨性,又使得文字更加生动有趣。阅读这本书,仿佛是在和一位博学而风趣的长者交谈,他用他渊博的学识,为你娓娓道来那些尘封的往事,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开阔眼界。
评分第一次翻开《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就被它那股沉静而悠远的古典韵味深深吸引。书页泛黄,触感温润,仿佛是穿越了漫长时光,从古老的书房里缓缓递到手中。书的装帧设计也透着一股不落俗套的精致,封面上那隐约可见的古画,配上烫金的书名,瞬间就勾起了我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拿到书的那天,我特意找了一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午后,泡上一壶龙井,就着窗外的绿意,慢慢地读了起来。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一本普通的旧事集,但随着文字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作者并非只是简单地罗列历史的碎片,而是用一种极其细腻的笔触,将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细节一一拾起,然后用他独到的视角重新解读。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古老的画卷上,发现了一个被人忽略了很久的角落,却在那一处,找到了最动人的故事。书中对于人物的刻画,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即使是那些只在史书中留下只言片语的旁观者,在作者的笔下,也仿佛拥有了鲜活的生命,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坚持,都跃然纸上,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字,更像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让我沉醉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评分读《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的过程,像是在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中行走,每一步都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又带着一丝窥探的兴奋。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学专业的读者,但书中那些或宏大或细微的史事,在作者的笔下,却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魅力,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要深入了解。最令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事件背后逻辑的梳理,他总能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到最关键的线索,然后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梳理,并非生硬的讲解,而是如同庖丁解牛般,巧妙而流畅,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书中那些细节的挖掘,更是让人惊叹,作者仿佛拥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能够捕捉到最容易被遗漏的日常片段,然后将它们放大,细致地描摹,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细节,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我尤其喜欢那些关于日常生活描写的部分,那些烟火气十足的描述,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就置身于那个时代,与书中人物一同呼吸,一同感受。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是我很少在其他历史类书籍中找到的。
评分《懒寻旧梦录(增订本)》带来的阅读感受,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它不像那些枯燥的史书,堆砌着冰冷的年代和数字,反而充满了人文关怀和艺术气息。作者的文笔,既有古文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灵动,行文之间,处处流露出一种温润如玉的质感。阅读的过程,更像是在品一杯陈年的老酒,初入口时微涩,但细细品味,便能感受到其醇厚甘甜,回味无穷。书中对人物情感的捕捉,尤为细腻动人。即便是一些早已尘封的历史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也并非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着七情六欲,有着自己的烦恼与追求。那些或悲伤、或喜悦、或无奈的情感,都被作者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展现出来,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我常常会被书中某个瞬间打动,比如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淡淡的叹息,都会在作者的笔下被放大,成为故事中最具感染力的部分。这种对人性深处的挖掘,让这本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富有人文价值,它让我们得以透过历史的尘埃,看见鲜活的生命,感受温暖的情感。
评分《懒寻旧梦录(增订本)》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我喜欢它那种沉静而有力的叙事风格,不疾不徐,却字字珠玑。书中那些久远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有温度的故事。我尤其喜欢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并将它们细腻地描绘出来。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书中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脆弱与无奈,他们的迷茫与挣扎,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更加真实可信。而且,书中对于历史背景的铺陈,也做得非常到位,不会让人感到突兀,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之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的阅读环境。我常常会在阅读的时候,不自觉地代入进去,仿佛自己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与书中的人物一同经历着悲欢离合。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历史,也让我对那些曾经的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细细品味的宝藏。
评分回味一段文艺圈的历史,写的很不错
评分那一辈的文人真惨,哎。
评分想买很久了,一直在京东买书,活动很给力,物流质量高,不错,很喜欢。。。。
评分精致的书,很好
评分不错很好 质量没问题 非常满意
评分本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廿世纪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亲历者的文字。 ☆作者反思震耳发聩 不论是对“四条汉子”事件还是对后来的历次运动,作者在交代事件缘由的同时,也对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作了反思,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的反思,让人深思。 ☆此书有增补和重要订正,内容和形式优于之前版本 此次出版内容上增加了日文版序言和多篇附文,订正了原来版本中的个别错讹;正文中增加了一些稀见图片且精装出版,装帧精美。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买的东西太多。不能一一评论。在这里统一回复,东西不错,是我所需要的。
评分西汉马王堆《帛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辛可提岛的迷雾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37656/8f192c9a-2b58-48b2-b1b4-ffdb177a1a54.jpg)



![小屁孩日记:我要上学啦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5525/53fc2b9aNf4a71264.jpg)
![经典故事轻松读-中国民间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3307/54d40c14Nb10b1b2f.jpg)

![邦臣小红花·幼儿国学启蒙经典:三字经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3552/55bacf87N9f47f836.jpg)
![科学幻想系列:虫虫打工记 [7~14岁青少年]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55961/55dc05d2Nec62dbab.jpg)
![绒兔子找耳朵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3788/564ebabbNa7a6947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