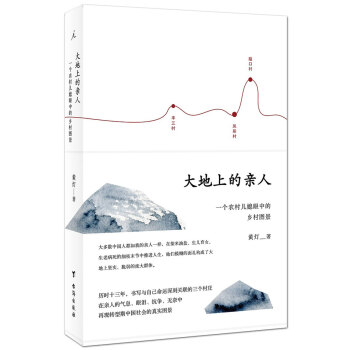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全面专业的周氏文集。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1。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内容简介
《周作人自编集:药堂语录》收入周作人一九四○年前后所作文章五十篇,是其散文创作文体的一种新尝试,同《书房一角》为一类,文章篇幅短小,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作者自述为文经过是一部书“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药堂语录》就是其中一部分。题曰“语录”并不是想效仿儒释,记录自身言行以传世,而取其“说的更简要”,择取一点切入,抓住思想的某种闪现。书中所“抄”所谈之书都是中国古籍,其中又以笔记为多。作者自称这些文章意不在针砭,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摆列点药”,但行文处处透着“疾虚妄”“爱真实”的精神。以《女人三护》为例,文章从《茶香室三钞》中女人三护一条,谈及佛家三护与儒家三从之不同,进而深及到对佛道儒的讨论,可谓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点评式梳理。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内页插图
目录
序太上感应篇
文海披沙
科目之蔽
女人三护
习苦斋画絮
鼠数钱
琐事闲录
跨鹤吹笙谱
九烟遗集
如梦录
存拙斋札疏
姚镜塘集
汴宋竹枝词
五祖肉身
七修类稿
辛卯侍行记
舌华录
夷坚志
麻团胜会
划水仙
张天翁
洞灵小志
耳食录
洪幼怀
药酒
落花生
入都日记
许敬宗语
销夏之书
绕竹山房诗稿
宋琐语
南园记
郢人
燕窗闲话
七夕
朱詹
澹盦文存
松崖诗钞
武藏无山
指画
如梦记
日本国志
钱名世序文
曲词秽亵
读诗管见
曾衍东诗
右台仙馆笔记
方晓卿蠹存
夜光珠
中秋的月亮
后记
精彩书摘
太上感应篇近来买几种天津的总集,得到郭师泰编《津门古文所见录》四卷,亦颇可喜。卷一有董梧侯著《重修天津文昌庙碑记》,中有云,世所传《帝君阴骘文》,大者皆六经之渣滓,微者如老妇之行仁,报应多端,义利所不能析也。编者注曰,吾见败德之人,妄希福泽,曰吾能诵《阴骘文》数百遍矣,曰吾能施《阴骘文》几百本矣,此记正为吾辈当头棒喝。案《轩语》卷一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条,云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此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诃而麾去之。此诸人意见皆明白难得,读书人志切科名,往往迷惑,所尊奉者在世俗所谓四书五经外,又有《感应》《阴骘》《明圣》三书,如惠定宇且不免,他可知矣,董君以为文昌可祀,而文不必诵,其有识盖不亚于张香涛也。唯鄙人重读《太上感应篇》一过,却亦不无恕词,觉得其乌烟瘴气处尚不甚多。篇中列举众善,能行者是为善人,其利益中只有福禄随之一句稍足动俗人歆羡,而归结于神仙可冀,即说欲求天仙或地仙者立若干善,为恶的罚则是夺算。由是可知此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科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鄙人素无求仙的兴趣,但从人情上说,见人拜北斗,求延年,此正可谅解,若或以此希冀升官,自不免看不入眼,至于照原来说法北斗本不管铨叙事务,那还是别一件事也。
文海披沙
《文海披沙》八卷,明谢在杭撰,有《申报》光绪丁丑活字本,今尚易得。《申报馆续书目》,《文海披沙》项下云,惟闻先生脱稿后并未问世,继乃流入东瀛,得寿梨枣,近始重返中华。案活字本有万历辛亥焦竑序,宝历己卯幡文华及宽延庚午鱼目道人二序,焦序中有诸子取《文海披沙》刻之南中之语,故并未问世,殊非事实,唯中土传本罕见,申报馆乃据日本刻本而重印之耳。寒斋所有日本刻本无幡文华序,而别多万历己酉陈五昌序文一篇,卷末墨笔书曰,天明丙午岁八月二十八日,则是购藏者题记也。计宽延庚午为清乾隆十五年,宝历己卯是二十四年,天明丙午则五十一年矣。鱼目道人不知为谁,序中有云,校先师遗书,载宁馨儿,引《文海》说。查伊藤东涯著《秉烛谈》卷三,宁馨条下引有《文海披沙》语。然则当是东涯之弟子也。序文又云,“余喜在杭者,盖喜其气象耳。夫训诂文辞可以工致,微言妙语可以深造自得,唯是气象自然佳处难以力致耳。”此语甚有理解,在杭见识思想并不一定高超,《诗话》之谈文学,《麈余》之记因果,尤多陋见,唯《五杂组》《文海披沙》故自可读,正因其气象可喜,明末有些文人多是如此,鱼目道人之言可谓读书得间,殊有启发的价值也。
科目之蔽
《复堂日记补录》,同治七年十二月下云: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案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余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以求冥佑,卑鄙已甚,真足为人心世道之害也。凡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虽是谈酒色财气,作市井语,亦总尚胜一筹耳。余尝谓读书人笥中不妨有淫书,但案头不可有《阴骘文》,《棘闱夺命录》一类善书,盖好色尚是人情,只须戒邪淫便是合法,若归依道士教,已止去白莲教一间,无以愈于吃菜事魔人矣。孔子论人事只讲仁恕,正是儒家的本色,孟子说义,便已渐近法家了,老庄觉得仁恕也济不得事,凡事想到底自都不免消极。总之古来圣人何尝说及那些怪语,而后来士人津津乐道,此正是儒之道士化,盖历汉唐宋明而遂完成,其源流不自外来,其影响亦不及于外国,与女人缠足的历史很有点相像,此一节亦甚可注意者也。
女人三护
《茶香室三钞》卷五女人三护一条云:“唐沙门慧苑《华严经音义》卷四云:女人志弱,故藉三护,幼小父母护,适人夫婿护,老迈儿子护。案儒书所谓三从,佛书谓之三护。”曲园先生谓三护即三从,形迹虽似,精神却实甚不同。印度女子的地位在社会上本甚低微,未必能比中国更好,在宗教上被视为秽恶,读有些佛教经传,几乎疑心最澈底的憎女家是在这里了。但是佛教的慈悲的精神有时把她们当做人类来看,对于人或物又总想怎么去利济他,那么其时便很不同,三护可以算作一个例。这里所谓护正是出于慈悲,是利他的,《庄子》里述尧的话,嘉孺子而哀妇人,可说是同一气息,此外我竟有点想不起来了。中国的三从出于《仪礼》,本是规定妇人的义务,一面即是男子的权利,所以从男人的立场说这是利己的,与印度的正是对蹠的态度。我常觉得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合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信如吾言,则我所佩服的尧的话大抵当出于道家,而黄老之学乃为中国最古老的传说,很可尊重。佛道至今称为二氏,唯其好处颇不少,足补正儒家之缺失,识者当不以为妄言也。
中秋的月亮
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云,“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此记作于四十年前,至今风俗似无甚变更,虽民生凋敝,百物较二年前超过五倍,但中秋吃月饼恐怕还不肯放弃,至于赏月则未必有此兴趣了罢。本来举杯邀月这只是文人的雅兴,秋高气爽,月色分外光明,更觉得有意思,特别定这日为佳节,若在民间不见得有多大兴味,大抵就是算账要紧,月饼尚在其次。我回想乡间一般对于月亮的意见,觉得这与文人学者的颇不相同。普通称月曰月亮婆婆,中秋供素月饼水果及老南瓜,又凉水一碗,妇孺拜毕,以指蘸水涂目,祝曰眼目清凉。相信月中有娑婆树,中秋夜有一枝落下人间,此亦似即所谓月华,但不幸如落在人身上,必成奇疾,或头大如斗,必须斲开,乃能取出宝物也。月亮在天文中本是一种怪物,忽圆忽缺,诸多变异,潮水受他的呼唤,古人又相信其与女人生活有关。更奇的是与精神病者也有微妙的关系,拉丁文便称此病曰月光病,仿佛与日射病可以对比似的。这说法现代医家当然是不承认了,但是我还有点相信,不是说其间隔发作的类似,实在觉得月亮有其可怕的一面,患怔忡的人见了会生影响,正是可能的事罢。好多年前夜间从东城回家来,路上望见在昏黑的天上挂着一钩深黄的残月,看去很是凄惨,我想我们现代都市人尚且如此感觉,古时原始生活的人当更如何?住在岩窟之下,遇见这种情景,听着豺狼嗥叫,夜鸟飞鸣,大约没有什么好的心情,——不,即使并无这些禽兽骚扰,单是那月亮的威吓也就够了,他简直是一个妖怪,别的种种异物喜欢在月夜出现,这也只是风云之会,不过跑龙套罢了。等到月亮渐渐的圆了起来,他的形相也渐和善了,望前后的三天光景几乎是一位富翁的脸,难怪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喜悦,可是总是有一股冷气,无论如何还是去不掉的。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东坡这句词很能写出明月的精神来,向来传说的忠爱之意究竟是否寄托在内,现在不关重要,可以姑且不谈。总之我于赏月无甚趣味,赏雪赏雨也是一样,因为对于自然还是畏过于爱,自己不敢相信已能克服了自然,所以有些文明人的享乐是于我颇少缘分的。中秋的意义,在我个人看来,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看月亮,而还账又过于吃月饼,然则我诚犹未免为乡人也。
……
前言/序言
关于《药堂语录》止 庵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下午整理《庸报》旧稿。”此即《药堂语录》,一九四一年五月由天津庸报社出版。集中五十篇文章,大部分发表于一九四○年,个别篇目(《药酒》、《洪幼怀》、《张天翁》和《洞灵小志》)则前此一年问世,写作大约就在这时,抑或更早一些。在《庸报》连载时,曾用“药草堂随笔”及“药草堂语录”作为总的题目,《序》(该篇最初发表即名为“药草堂语录”)中所谓“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云云,即此之谓也。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氏在《自己所能做的》中说:“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写笔记。”将近五年之后为《药味集》作序,也说:“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所说“笔记”均有特指,即《药堂语录》及《书房一角》,在周氏散文创作历程中,是为文体上一种新的变化。正如《书房一角原序》所说:“现在文章更琐屑了,往往写不到五六百字,但我想或者有时说的更简要亦未可知。”笔记与此前的“文抄公”之作都是“披沙拣金”式的摘录,区别在于文章的切入点和感受范围,二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说的更简要”的确意味着一种新的切入方式,就对象而言,是只择取或优或劣的一点;就主体而言,也仅仅把握思想的某种闪现,或者说是记录彼此间一次碰撞,而舍弃了通常构成随笔主体的那个思想过程。虽然切入点和感受范围都小了,背后的意蕴仍相当广阔深厚。即便是《郢人》和《中秋的月亮》这样一时感兴之作,作者的感受也很敏锐丰富,更不要说以“疾虚妄”与“爱真实”为主旨的各篇了。笔记以关乎中国古籍(尤其是笔记作品)者为多,《药堂语录》几乎全数如此,所以虽然篇幅远逊《书房一角》,却显得更纯粹些。《书房一角原序》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用在这里更为恰当。
《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在形式上与中国古代之笔记和题跋颇有相似之处。周氏对古人此类作品一向留意,可谓烂熟于心,然而此番大规模写作之前,尚做过认真而系统的准备工作,见《一蒉轩笔记序》(载《风雨谈》杂志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丁丑(按即一九三七年)秋冬间翻阅古人笔记消遣,一总看了清代的六十二部,共六百六十二卷,坐旁置一簿子,记录看过中意的篇名,计六百五十八则,分配起来一卷不及一条,有好些书其实是全部不中选的。”其间自有一副鉴别取舍的眼光,即:“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这涉及文章与思想两方面,如果说有所承继,也是承继了这样一路,具体说来,与所提到的刘献廷、俞正燮、郝懿行、王侃、李元复、玉书、马时芳等人作品关系可能更大一些。《后记》又讲“此种文字新陈两非”,虽是谦辞,文白夹杂而又和谐一体,确是周氏散文新的语言特色,而且除《药堂语录》、《书房一角》外,此后一段时间所作随笔也往往如此。作者在《药堂杂文序》中所说,可以代表他的用意:“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人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以其学养胸襟,最大限度地汲取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有益养分。而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前一方面是进一步拓展现代散文的体式,同时赋予笔记和题跋以新的生命;后一方面则对于现代散文语言之丰富完善,更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了。
周作人写的笔记原不止《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这些。一九四五年五月下旬的日记中,多有写作笔记的记载,六月四日云:“下午写笔记,成一卷,共约三万三千字。”八月三日云:“收亢德寄还笔记稿廿页,即寄读书出版社。”此书未能出版,或已亡佚。一九四九年后在《亦报》、《大报》发表的七百余篇短文,其实也近乎笔记之作。
此次据庸报社一九四一年五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为“著者周作人先生之近影”,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一百一十页。“序”原作“药堂语录序”,目次中亦如此。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对于一个习惯了现代快节奏、碎片化信息输入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但也是一种享受。它要求你慢下来,去品味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温润的词句。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近乎“犬儒”的超脱感,他似乎总能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审视世间的喧嚣与沉浮。比如在谈论某个社会现象时,他从不直接抨击,而是用一些看似不相干的典故或民间故事来旁敲侧击,这种“言外之意”的表达技巧,真是高妙。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其中一些关于“中庸之道”的论述,初读时觉得有些圆滑甚至世故,但多读几遍后,才明白那其实是一种在乱世中寻求个体存续的智慧——不是妥协,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持自我精神的完整性。这本书里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热血的沸腾,只有沉静的思考和对人性幽微之处的洞察,这对于当下这个急躁的社会来说,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心灵庇护所。
评分坦白讲,我对周作人的了解一直很肤浅,大多停留在教科书上那几个被简化了的标签上。然而,这本“自编集”的装帧和选篇,明显经过了编者的精心考量,它试图展现一个更立体、更具生活气息的周作人。里面的散文,尤其是那些记录日常生活点滴的文字,充满了浓郁的“京味儿”和浓厚的“人情味”。比如描述他如何为了一碟小菜而辗转寻觅,或是记录某个冬日午后,阳光如何斜斜地洒在书桌上,以及他与友人之间那种不着痕迹的寒暄往来。这些细节的描摹,让我感到非常亲切,仿佛隔着厚厚的历史尘埃,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温润如玉的文人气象。比起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文章,这些“烟火气”十足的文字反而更能打动人心,让人认识到,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同样要面对柴米油盐和人际的微妙,这种真实感,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所在。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初闻不觉惊艳,但细品之下,醇厚的回甘便在唇齿间弥漫开来。它使用的词汇,有些现在看来已是生僻,但作者的遣词造句却又是那样自然贴切,不显矫揉造作。我尤其留意了他在描述自然景象时的笔法,那份细腻程度,简直可以与古代的山水游记媲美,但他又融入了一种近代的审视视角,使得景物描写不再是单纯的抒情,而带上了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感伤。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时地需要查阅一些背景资料,来理解他所引用的典故,这反而成了一种有趣的“学习过程”。这表明,作者并非在故作高深,而是他所处的时代文化底蕴太过丰厚,自然而然地流淌在了文字之中。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度,更在于其语言艺术的典范性,它提醒着我们,汉语的美感和表现力,可以达到何种高度。
评分这本书,说实话,拿到手里沉甸甸的,封面设计得很有年代感,那种淡淡的墨香,让人瞬间仿佛穿越回了上世纪的某个文人书房。我原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读物,毕竟是周作人先生的“自编集”,但翻开后才发现,里面的文字风格真是独树一帜。他那种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暗藏机锋的叙事方式,让人不得不停下来细细咀嚼每一个字背后的深意。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关于“闲适”的篇章,他没有高谈阔论什么人生哲学,只是娓娓道来自己如何在一间小小的书斋里,伴着猫儿和旧书度过一个下午。那种对日常细节的捕捉和对生活诗意的营造,简直是神来之笔。读着读着,我常常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那些疾呼呐喊的形象,再看周先生这边的从容不迫,便更觉出两位大家在精神气质上的巨大分野,而这种分野,恰恰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丰富性。这本书,与其说是文字的堆砌,不如说是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复杂而真实的旧日文人内心世界的一隅。
评分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去读”的作品,绝不适合用来消磨时间,而更适合用来“充实时间”。如果期待在其中找到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或者振聋发聩的论断,恐怕会失望。它更像是一次与一位睿智长者的深夜长谈,话题从一朵花开到一片雪落,从邻里的琐事谈到历史的兴亡,看似散漫,实则条理清晰,暗合着作者内心构建的某种秩序。我最欣赏的是他处理“矛盾”的方式——他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将矛盾双方并置,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张力。这种留白的处理,既是对读者智识的尊重,也是一种高明的写作策略。读完全书,我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有一种出奇的平静,仿佛洗涤了心灵上的浮躁。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从容与节制,非常值得一读再读。
评分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评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
评分好书
评分周作人的散文是一流的。。。。。。。。
评分自编辑必收书,开本适合阅读
评分很好很完美,很喜欢!!
评分整体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继承了诗经、六朝和晚明文学的内蕴,充满着平淡如水、自然如风的语言色彩。其冲淡平和的散文风格展现出空灵的人生境界,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评分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评分周作人《药堂语录》中《麻团胜会》之末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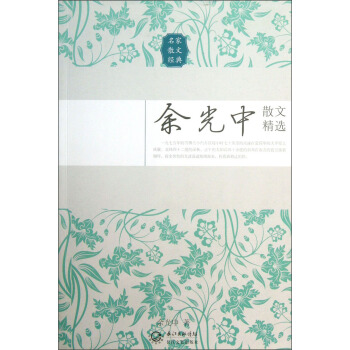

![小屁孩日记:我要上学啦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5525/53fc2b9aNf4a71264.jpg)
![经典故事轻松读-中国民间故事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3307/54d40c14Nb10b1b2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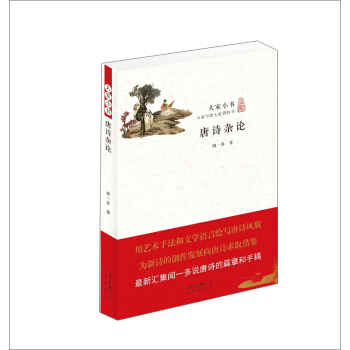
![邦臣小红花·幼儿国学启蒙经典:三字经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3552/55bacf87N9f47f836.jpg)
![科学幻想系列:虫虫打工记 [7~14岁青少年]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55961/55dc05d2Nec62dbab.jpg)
![绒兔子找耳朵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03788/564ebabbNa7a6947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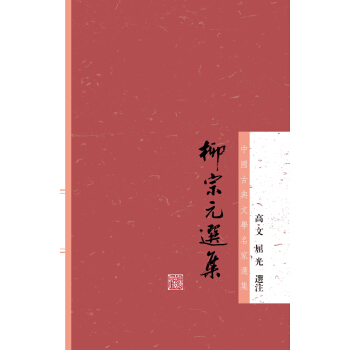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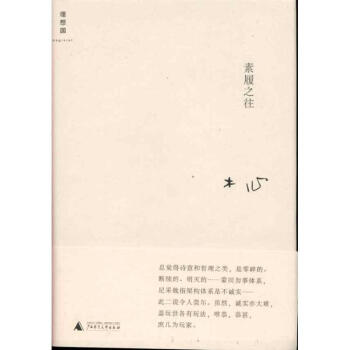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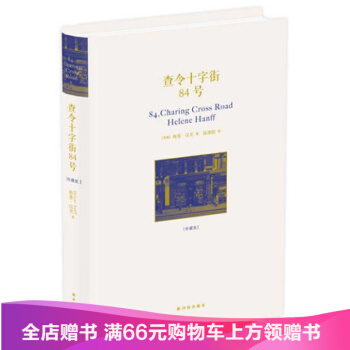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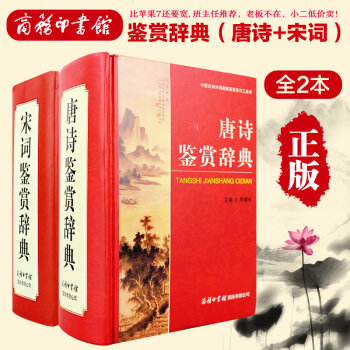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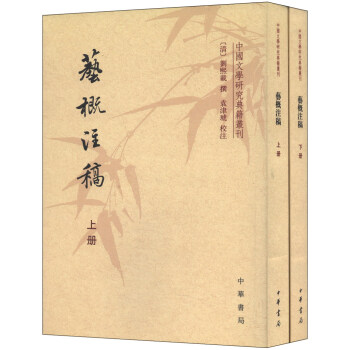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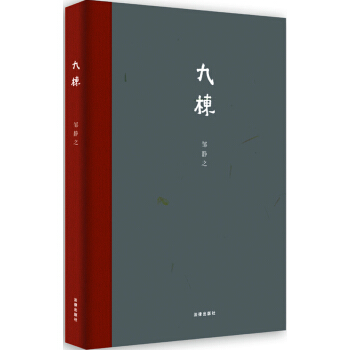
![世界名家手绘经典童话:匹诺曹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32173/55a8ab0aNcc618ac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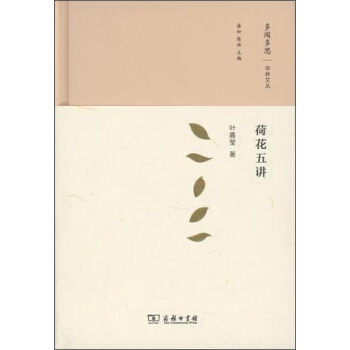
![艰难时代 [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07375/58467d8bN2435a87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