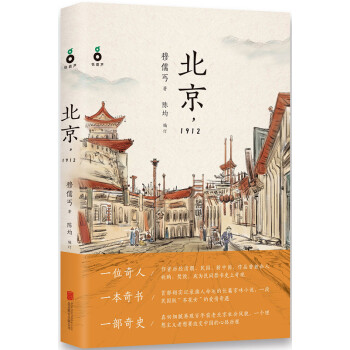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作者是一位奇人: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作品曾被私人收购、焚毁,成为民间禁书史上奇观。
本书是一本奇书:首部翔实记录旗人命运的长篇京味小说,一段民国版“茶花女”的爱情奇遇。
本书记载的是一部奇史:书里真切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老北京的社会风貌,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改变中国的心路历程。
正如本书编者陈均所言:这本书写的是世相(社会小说),但探寻的依然是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之寄托: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而且还将堕落下去?理想的社会到底在哪里?
内容简介
《北京,1912》内容简介:
满族青年宁伯雍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遇上辛亥革命,听说老同学在前门外经营《大华日报》,便去求职,成为记者。
从京郊到城里后,宁伯雍看到了一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他在龙泉寺认识了梆子小花旦白牡丹,并与沛上逸民等人组织团体捧白牡丹。从此白牡丹渐渐走红,后被维二爷独占,厌弃宁伯雍等人。宁伯雍又认识了妓女秀卿。秀卿对高官富商冷眼冷语,对宁伯雍却另眼相待,两人渐生情愫。秀卿不幸患病,临死前将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宁伯雍……
作者简介
穆儒丐:中国现代史上早期的白话小说家和享誉一时的剧评家。1884年(也有一说为1883年)生于北京西郊香山的旗人家庭。190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1916年至沈阳。1945年返回北京,先后从事秘书、教师、报纸编辑等职业。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2月15日逝世。著有数量众多的小说、随笔、戏曲评论和岔曲作品,但因其特殊的经历,被后人所忽略。
陈均: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编订朱英诞、穆儒丐、顾随等作家的作品及京昆史料文献多种。出版有专著《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京都聆曲录》及诗集《亮光集》、小说《亨亨的奇妙旅程》等。
目录
第一章 021
第二章 040
第三章 069
第四章 084
第五章 107
第六章 130
第七章 153
第八章 164
第九章 176
第十章 194
第十一章 206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52
第十五章 278
原书序跋 283
精彩书摘
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 青龙桥:位于今颐和园北宫门外,为明清以来由西山通往海淀的交通要道。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太后即经由此桥出京,仓皇逃往山西。]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 王石谷,即王翚(1632─1717),常熟人,被称作“清初画圣”,与王鉴、王时敏、王原祁合称山水画家“四王”。]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
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 指造就出很好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伯雍因为在家白闲着,终归是闲不起,没法子只得受了人家聘书。好在做幕的勾当,名义上还清高一点。当下禀明父母,择个日子,到军营里给人家做书记去了。他以为这些军官,除了同乡就是同学,自然容易处的。谁知这些老爷大人们,在军营里染了满身骄傲脾气,动不动以阶级压人。伯雍初到营时,多少还受点礼遇,过了二十天一个月的,也就不拿伯雍当事。有时大家一起闲谈,还指桑说槐的,把书呆子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说念书好一点的,总要带一贴[ 一贴:量词,一张/一块。]酸狂样子,看不起人,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可是如今看不起人的穷酸,要想当个司书生,都没人要。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如今倒大马长刀,当了营长、团长,还有当旅长的,这不上天睁开眼睛,无形中惩治他们一下子吗?说到这里,许多老爷大人总要哈哈大笑,并且有的说:“这些穷酸也不能办什么大事!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不致饿死,也够他们享受的了!”
伯雍听了这些话,自然有些不愿意。虽然目下念书的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作践。何况当初都是村学房圣人龛下一同长起来的,便是如今所业不同,有幸不幸之分,也不可因为自己地位一时比人家强,便这样肆口奚落,未免使人太难堪了。从此伯雍不愿在军营里做那会使笔的奴隶。有一天,他给营长留下一张辞呈,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次日营长回营,知道伯雍已然辞了差使,还打发副官到伯雍家里挽留一次。伯雍婉言谢绝说:“贱质不惯于军营生活,诸君抬爱,异日再补报吧!”副官无法,回复营长另聘高明去了。
这是还没改民国那一两个月内的事。转过年来,便是民国元年,伯雍依然在家赋闲。假如他有相当的不动产,丁[ 丁:遭逢。]此大革特革时代,他一定不会出来的。在山里头侍奉父母,闭户读书,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山农,也就够了。无奈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不能不另谋生计,长此家居,终非了局。可巧这时有同窗友人,在前门外开了一家报馆,定名《大华日报》。两个经理,正经理白歆仁[ 白歆仁:为穆儒丐友人乌泽声在小说中的化名,详情另述。],副经理常守文,都是新被选的众院议员,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进步党,当初他们都是很有志气的青年,如今荣膺民国代表,在议会里很占一部分势力,由党部支了一笔补助费,开张了这家报馆。伯雍听说他们的报销路还不坏,打算在他们报馆里卖文为生,或者充任一员编辑亦可。于是他给歆仁去了一封信,说明所以。歆仁素日很知道伯雍的笔墨有两下子,假如得他来帮忙,于报纸声价不无小补。而且伯雍为人狷介,最不爱提钱字,较比他人,容易打发,一举两得,有何不可?何况他来求我,我没去邀他,日后的薪金大小,他不能与我争执了。主意拿定,便给伯雍去了一封信说:“你命令我的事,已然和同人说好了,请你赶快到馆,襄助一切。”伯雍见字,收拾进城。前面所述,正是他雇了驴子,进城上报馆的那一天。
伯雍一边催促着驴,一边看那山村景色,不知不觉,已然到了万寿山[ 万寿山:燕山余脉,颐和园内,昆明湖前。]。他由驴上下来,付了驴钱,招呼了一辆车,言明雇到新街口,二十五枚铜元。到了新街口,他多给拉车的五枚,说:“我多着一件行李,这五枚给你打酒喝吧!”拉车的道声谢,接了钱,用条破手巾,不住擦他脸上的汗。伯雍在一旁看着,老大不忍,暗道:“小二十里路,给他三十铜子,还很高兴。可见出汗赚钱,过于不易了。”这时伯雍方要再呼一车,到宣武门外去。那拉车的见伯雍还要出城,又知他肯多花钱,便说:“先生!不必另雇车了,我送你去就完了。”伯雍说:“你已然出了一身汗,跑了二十来里路,再到南城恐怕你的力气来不及。”这时那车夫已然把汗擦干,喘息定了,连说:“行行!三四十里算什么,我就怕不挣钱!道路多跑,倒不在乎。先生,你上车吧!”伯雍说:“你既然愿意去,我仍坐你车去吧,省得费事。”当下告诉他什么地名。伯雍方要上车,这时在街心上,早拥来许多辆车,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先生别坐他的车了,他已然跑不动了。”这个拉车的见大众车夫抢他买卖,便大声说道:“谁跑不动!有敢跟我赛赛的么?”还是伯雍排解了几句,别的拉车的才散了。当下上了车,那车夫拉起来便跑。伯雍说:“你倒不必快跑,我最不喜欢拉车的赌气赛跑,你只管自由着走便了。”车夫见说,果然把脚步放慢了些。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 固赛呢亚拉玛:旗人。此为满语汉译之词。]。”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
善扑营:清代禁卫军之一。“善”即“擅”之意。擅长相扑的人编为军营,即善扑营。清亡后,善扑营解散,扑户们无以为生,或设馆教授摔跤,或设场卖药,或拉人力车,或卖苦力,或流浪街头。]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 攀腿禄:清末善扑营扑户名单中有“搬腿禄”。],你认识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岁,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 自要: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做。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觍着脸活着呢。”这时德三已然把脚步放快,他们二人已无暇谈话。伯雍抬头看时,已然到了西四牌楼。只见当街牌楼,焦炭一般,兀自倒在地下,两面铺户,烧了不少,至今还没修复起来。这正是正月十二那天,三镇兵士焚掠北京的遗迹。
伯雍看了这些烧残的废址,他很害怕地起了一种感想:“这北京城自从明末甲申那年,遭了流贼李自成一个特别的蹂躏,三百来年,还没见有照李自成那样悍匪,把北京打破了,坐几天老子皇帝。便是洪杨那样厉害,也没打入北京。不过狡猾的外洋鬼子,乘着中国有内乱,把北京打破了两次,未久也就复原了。北京究竟还是北京。如今却不然了,烧北京打北京的,也不是流贼,也不是外寇,他们却比流贼外寇还厉害!那就是中国的陆军,当过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如今推倒清室,忝为民国元首,项城袁世凯的亲兵。项城先生是北洋派的领袖,国家陆军多半与他有关系。如今他的兵,在他脚底下,居然敢大肆焚掠,流贼一般的饱载而去。此例一开,北京还有个幸免吗?哎呀!目下不过是民国元年,大概二年上就好了,二年不好再等三年,三年不好,再等四年。四年不好,再等五年。五年不好,再等六年。六年不好,再等七年、八年、九年……若仍见不出一个新兴国家样子,那也就算完了。”伯雍一边感想着,一边替未来的北京发愁。他总想北京的运命,一天不如一天。他终疑北京是个祸患的症结,未来惨象比眼前的烧迹废址,还要害怕得多。他终以北京是不可居的,还是在西山寻个无人所在,韬晦起来,较着平安。但是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都得现抓。为饥所驱,遂把伯雍一个志行高洁、有意山林的青年,仿佛用鞭子赶到猪圈里去。他明知道一入北京,人也得坏,身子也得坏,耳目所接,一定不如涧边清风、山间明月,但是无论怎样与志相违,终是不能不到北京城里去,他的境遇也就很可怜了。
伯雍在车上不住感想,车夫德三在马路上不住飞跑。少时已出了宣武门,进了西茶仓胡同,伯雍才把他的思潮打住。又走了半里多路,进了一条僻巷,早见一个如意门,两边青灰墙上,写着老大白字:大华日报社。伯雍教车站住,下了车,教车夫把行李搬到门洞内,然后递给德三一张五吊钱的票儿,德三千恩万谢去了。伯雍来到门房,只见有三四名馆役,正在炕上躺着睡觉。伯雍叫了几声“借光”,才有一个由炕上爬起来,蒙眬着眼睛,懒恹恹地问伯雍说:“你是做什么的?”伯雍当时取出一张名片说:“烦劳通禀白先生一声,就说鄙人求见。”那馆役此时仍是懒洋洋的,仿佛再睡一会儿才好呢,所以他很愿意来客赶紧就去了,他好再睡。只听他打着呵欠说道:“你要见总理么?总理没在报馆。”说罢似仍然要去睡觉。伯雍见这馆役的神气,待理不理的,知他为睡魔所困,想是昨夜不曾睡觉,也不嗔怪于他,只得把自己来历说了一番,并不是寻常拜访,特来到社做编辑的。那馆役见说,少微[ 少微:稍微。]把精神一振,说:“你先生在此等一等,我去回一回账房的经理。”当下他拿了伯雍的名片进去了。不多时出来,和伯雍说:“请进去吧。”伯雍随他进去,走入一个木板屏门里面,却是坐西五间正房,南北各有两间厢房,院子没有一把掌[ 把掌:巴掌。]大,被四面房屋欺得连太阳光也得不着。馆役把伯雍让到南厢房里,里面也有几件木器,最重要的是一个铁柜,证明此处是报社的“财政部”。随墙放着一张木床,上面放着烟具。早有一个极瘦的人,由床上站起来,向伯雍一拱手,做出笑脸来说:“伯雍先生请坐请坐,我常听我们总理提你先生,兄弟很是久仰的,头几天总理跟我们说,已然把你先生约来帮忙。好极了!活该我们的报纸应该发达!”这时伯雍一边还礼,一边问那瘦人说:“阁下贵姓?”那人说:“贱姓吕,草字子仙。”伯雍说:“久仰久仰。”于是二人就木床上对面坐下,彼此周旋几句。吕子仙烟瘾未足,仍旧躺下吸烟。吸了两口,问伯雍说:“伯雍兄于此怎么样?”伯雍说:“倒是喜爱,还没尝试过。”子仙说:“不吃甚好。兄弟一生事业,便为这东西给耽误了。假若我不吃烟,内阁总理也敢去做。”伯雍说:“现在阔人,谁不吃烟?皆因吃烟才能做总理。照我们不吃烟的,也无非给人家卖卖胳膊[ 卖卖胳膊:靠体力劳动为生。]。自目下看起来,究竟是没出息的人,吃大烟才能表示有做阔事的资格。”吕子仙见说,不禁大笑说:“伯雍你这样一个人,还会说笑话。如此看来,我这烟倒得足吸一气。”他又连吸了五六口,精神比从前大了些儿。伯雍细看他时,虽然瘦得不成样儿,眼睛里却含着机警的神气。歆仁既然用他当账房经理,想必是歆仁的心腹,可以无疑了。
此时外面已有午后四五点钟,伯雍一个山居的人,起得绝早,自然早晚饭也早些。他此时因为行了三十多里路,虽然骑驴坐车,未免有些劳乏,肚子里尤觉饥饿,可是报馆里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厨房里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吕子仙把烟吃完,才叫馆役打水,漱口净面,原来他才起床不大会儿。伯雍无法,初来乍到,也不能便要饭吃,只得向吕子仙说:“兄弟下榻地方,想是预备出来了?”子仙道:“头几天便预备好了。”说着叫来一个馆役,把伯雍带到寝室,却是那五间上房,南套间里。伯雍到了套间一看,沿窗放着一张书案,案面上蒙的绿呢,已然看不出本色,一块黑、一块黄、一块红的,还有一圈一圈的茶污。那纸烟的烧迹,比马蜂窝还密。案头沿墙去处,放着一个书架,尘土积得有一钱多厚。挨着后檐墙,两条长凳,架着一张藤织床面。他的行李,已被馆役堆在床屉上头。此外别无陈设。惟有那墙上,因为潮湿,把糊纸霉得都变了颜色,一块一块的霉湿阴晕,蔽满了四壁,隐隐现现的,好似郭河阳[ 郭河阳:即郭熙,北宋著名山水画家,有《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幽谷图》等传世,其画山石多用卷云或鬼脸皴。]云山的蓝本。
伯雍一见这屋子,也就明白他后来的运命了。他没法子,把行李打开,向馆役要了一把掸子,把案子和书架打扫打扫,把自己带来的几本破书,放在书架上,然后把铺盖就床上叠起来。他略微休息休息,又到外屋去看一看。外头四间,却隔成两间。堂屋临窗,也是一个大书案,上面放着文具,它那墨污的程度,比套间那张还厉害。挨着西墙,放着一张榆木擦漆的方桌,一边放一把旧式大椅。此外有许多报夹子,架着那些交换报。伯雍暗道:“这间一定是编辑部了。”那北屋屋门上,挂着一张青布帘,下面犄角不知被什么烧去半边。上面的污垢,与书案上的绿呢面,可称双绝。此时伯雍知道屋里必然无人,因为过于寂静了,他遂把门帘揭起,到这屋里一看。两张床上,都放着油污的寝具,大概是底下人的。他一想:“不能,底下人自有下房,这里明明是上房,怎能住底下人呢?一定是编辑先生卧榻了。”这屋窗前,也一样放一张书案,文具倒很齐备。伯雍把各屋参观已毕,他的感想,也不知是喜是伤。
只见他点点头,仍回到自己屋中。他此时饿极了,听一听厨房那里还没信,也没人来问他开饭不开饭。他暗想道:“大概饭时还早,别教老肚埋怨我了,应当吃点什么才对。”想罢,取出二十枚铜子,喊了两声“来人”,却不见有人答应。他不由暗想道:“我叫‘来人’,他们或者不愿意,叫他们一声‘馆役’试一试。”也不见答应。伯雍无法,又叫一声伙家,就短叫大哥、先生了,却仍不见有人答应,气得伯雍无法,暗道:“他们真会欺负人。我新来的人,就不配使令你们么?我自己有腿,会外头去吃饭。”当下要出去吃饭。只听厢房里吕子仙喊了一声“来人”,遂听门房那边四五个人一齐答应了一群:“是。”随着就听有一个人,连忙跑过去。只听吕子仙和那人嚷道:“你们都干什么来着?上屋叫半天人,怎么一个答应的也没有,快过去问问什么事!”没一会儿,果见一个馆役,到伯雍屋里问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伯雍本来有着气,要出去吃饭,如今见一个馆役跑了过来,当时把气减了许多。及见那馆役问说:“有什么事吗?”只得把那二十枚铜子交给那馆役,说:“求你到外头给我烙一斤饼,买一吊钱酱肘子来。”那馆役见说,接钱去了。此时伯雍倒不禁好笑起来,暗道:“这些馆役,怎这样不知自爱?我叫了半天,却一个答应的没有。账房经理不过哼了一声,五六个人,一齐答应。不用说他们心里就知有总理、经理,把别的先生自然看不到眼里。小人常态,大抵如此,姑且不必与他计较。等日后手内富裕,给他们几个零钱花,也就不能呼应不灵了。”
正自想着,那馆役已然把饼烙来,伯雍趁热,卷了酱肘子,饱餐一顿。因为他饿极了,在乡下时,哪里这晚[ 这晚:这么晚。]吃过饭?他吃完了,电灯早来了,俗语说得好:吃饼,离不开井[ 北京土语,意为饼吃多了口渴。]。他此时已然不敢教馆役替他泡茶,生恐碰钉子。幸亏他还明白,仍跑到吕子仙屋中。子仙一见他,便说:“你自己买饭吃做什么?咱们馆里有的是厨子,饿了自管分付[ 分付:吩咐。
]他。”伯雍说:“为我一个人,也没有开饭的道理。再说饭时未到,不可破例,此时我倒很渴的了。大哥!你教他们给弄壶水来喝。”子仙说:“那容易。”只听他沉着声音叫声“来人”,门房那边又“嗡”的一声,有五六个人答应起来,比司令官的命令还有效呢。随即有个年青的馆役,年约十八九岁,面皮挺俏皮的,跑过来问有什么事。子仙说:“你去给泡壶茶来,拿好叶子。”那馆役见说,由一张抽屉柜内取出两罐茶叶,问用哪个。子仙说:“糊涂!拿一包给总理喝的。”那个馆役又由别的抽屉内,取了一包茶叶,拿了茶壶去了。少时,把茶泡来,给伯雍和子仙,每人斟了一碗,却站在一旁。这时子仙又躺在床上,弄他的大烟。伯雍乏了,也躺在对面,因问子仙说:“馆里什么时候办事?怎么这时候编辑部里还冷清清的?”子仙说:“每日吃完晚饭才办事呢。这时候稿子也不能来,所以他们吃了早饭,便都出去瞎跑,有听戏的,也有看朋友的,待一会儿,就热闹了。串门子的也都晚上来,完了事,还可出去逛逛胡同,打八圈麻将什么的。你如今入了报馆很好,究竟比你老在乡下强得多。”伯雍一听,便有些害怕,暗道:“晚间办事,已然是没益处了。办完事,还打麻将逛窑子,那一夜还有睡觉的时候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忽然闯入了一个旧时的画卷,色彩斑驳却又异常清晰。作者对那个时代社会百态的描摹,细腻得令人心惊。街头巷尾的吆喝声、腐朽衙门的昏暗光线、乃至上流社会那些不动声色的权力角逐,都被他用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触刻画出来。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捕捉,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个体,他们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犹豫,都带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有的沉重与无奈。我仿佛能闻到旧北京特有的尘土味和煤烟味,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让我忍不住一页一页地往下翻,想要探究每一个人物最终的命运。它不是那种轻快的消遣读物,更像是一面打磨得锃亮的镜子,映照出历史深处那些复杂的人性与纠葛。读完合上书的那一刻,我甚至需要几分钟来重新适应现代的节奏,足见其强大的代入感。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享受。它不像当代小说那样追求快速、直接的表达,而是带着一种古典的韵味和节制的美感。每一个句子都像经过精心打磨的玉石,圆润、光泽,掷地有声。作者对于景物的描写,并非简单的堆砌形容词,而是巧妙地将环境氛围融入人物的情绪之中。比如描写一个寒冷的冬夜,那份寒意不仅仅是温度的下降,更像是人物心中绝望的具象化。这种文学性的追求,让阅读过程充满了仪式感。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降低了阅读速度,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措辞的妙处。这绝对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每一次重读,都会因为心境的不同,而挖掘出先前未曾察觉的深层意蕴。对于追求文字美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场盛宴。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对“选择的代价”这一主题的探讨,处理得极其深刻且不落俗套。它没有简单地将角色划分为好人与坏人,更多的是展现了人在极端压力下,为了生存或理想,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与牺牲。那些看似光彩夺目的成功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道德困境和情感上的巨大割裂。作者并没有急于评判,而是将这些复杂的内心挣扎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将判断的权利交给了我们。这种开放式的呈现方式,使得故事的余韵非常悠长。合上书后,我依旧会思考:如果是我处于那个境地,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强烈的代入感和反思性,让这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小说范畴,更像是一部关于人性边界的哲学探讨。它提醒着我们,历史是由无数个艰难抉择累积而成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重量。
评分我通常不太喜欢情节过于曲折离奇的故事,总觉得那样容易显得虚假。然而,这本书的“曲折”却让人信服,因为它根植于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荒谬与不公之上。人物之间的关系网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作者处理这些复杂性时,却展现出一种极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让你始终能跟上故事的发展,而不是迷失其中。更吸引我的是那种暗流涌动的张力。很多矛盾和冲突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大张旗鼓的爆发,却在平静的表象下酝酿着巨大的能量。你看着人物在做看似平静的选择,却知道这些选择将如何不可逆转地改变他们的未来。这种对“宿命感”的把握,让整个阅读体验充满了张力和悬念,让人忍不住猜测接下来的走向,即使知道历史的大方向,也为书中人物的小命运捏一把汗。
评分老实说,我一开始对这种历史背景的小说抱持着怀疑态度,总怕它会变成枯燥的说教或者堆砌史料。但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它的叙事节奏掌握得极为精妙,像老中医把脉一样,时而平稳叙述,时而忽然加重力道,抛出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情节转折。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体之间的平衡艺术。你可以看到国家层面的风云变幻,但所有的变革最终都落脚到了某个特定家庭、某个特定人物的命运之上。这种“大背景下的小悲欢”的处理方式,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线,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一些女性角色的塑造,她们的智慧与隐忍,在那个男权至上的年代里,闪烁着不易察觉却又光芒万丈的生命力,让人读来感慨万千,甚至会开始反思我们今天所享有的自由是多么来之不易。
评分领导让帮忙买的书!
评分揭露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
评分好书
评分民国之初,袁世凯称帝前的北京乱象。主人公伯雍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北京西山的旗人,在日本早稻田留过学,在南城作报纸编辑,也写小说养活一家老小。接触到“八大胡同”(当时号称“议员俱乐部”,有些妓女被议员们娶作姨太太,时称“窑变”)和伶界(书中写到初出道时的荀慧生/白牡丹,后写书《梅兰芳》因涉及“相公堂子”旧史被焚)。穆儒丐在中国文学界的边缘地位据说与他在“伪满洲国”任职的经历也有关。本书中可看出他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对“共和”后的北京乱状不满,又无法施展救国情怀。偶有“满清遗少”的怀旧情怀。说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有《水浒》、《儒林外史》、文康《儿女英雄传》,国外作家则喜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尽管作者并非很喜欢《红楼梦》,书中时见其影响的痕迹。
评分内容符合实际,还是值得推荐的
评分不错
评分有难度。不太容易读懂。
评分比较传奇,慢慢看。
评分我很喜欢这本书,而且我为了买这本书等了好久好久。多做点活动吧,还要继续多买一些。内容还在看,下次来评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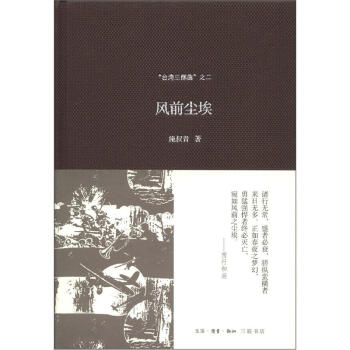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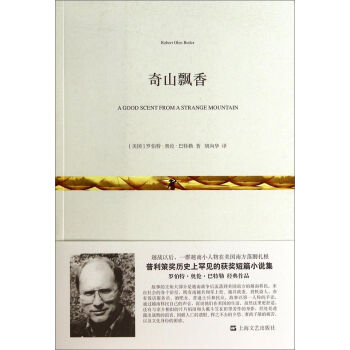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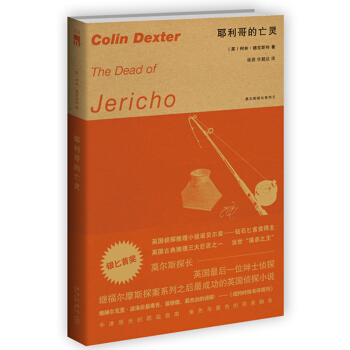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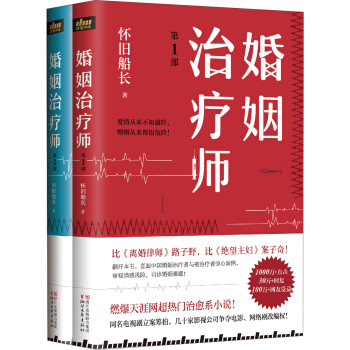
![简爱 [Jane Eyr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83698/586f4c14Nd34a5f6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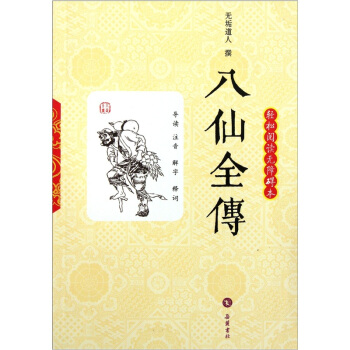
![金钱:绝命书 [Money, A Suicide Not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6644/5400162cN813803ac.jpg)
![译文名著精选: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35615/554c979eNf87f7bd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