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 《司馬遷之誌》是近年來研究《史記》極為重要的成果,作者研究細膩,論點鮮明,分析透徹,深入淺齣。2.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
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司馬遷之誌》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內容簡介
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書從文質之辨、君臣之際、《論六傢要指》的意義等角度,詳盡辨析瞭《史記》之“繼春鞦”說。
作者簡介
陳文潔,哲學博士,曾從事曆史學博士後研究,現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所副研究員,2014-2016年在美國耶魯大學訪學。著有《荀子的辯說》等。目錄
第1章 引言第2章 “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宗旨
第3章 撥亂反正之一:文質之辨
第4章 撥亂反正之二:君臣之際
第5章 “繼《春鞦》”說的實質
精彩書摘
“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宗旨司馬遷著《史記》,意在成一傢之言。《史記》既為“繼《春鞦》”而作,則司馬遷藉撰述史事所錶達的一傢言亦當為“繼《春鞦》”而發,當視為他“繼《春鞦》”的具體錶現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傢言的宗旨,根本上與他對《春鞦》的理解緊密相關。鑒於當時《春鞦》經傳並行不分的一般學術環境,這首先需要澄清司馬遷“繼《春鞦》”說中“《春鞦》”的實際意指,在此基礎上把握他對《春鞦》的述作意圖和性質的認識,進而領會他對“繼《春鞦》”之一傢言的實質性定位。
然而,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明確提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其一傢言的主旨,似與其“繼《春鞦》”說相歧,難免使其一傢言旨趣呈現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維都有其內在的一緻性,“一傢之言”作為司馬遷貫通《史記》的自傢思想,也有其統一的宗旨、核心。“繼《春鞦》”與究天人、通古今兩種說法隻是貌似不可溝通,在本質上則是完全和諧、互通的。司馬遷的一傢言,既可說是“繼《春鞦》”之一傢言,又可說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傢言。在他而言,“繼《春鞦》”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實非二事,而是一事兩說。“繼《春鞦》”即意味著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則是對“繼《春鞦》”之著述任務的具體解說,二者從不同的角度確定司馬遷一傢言的核心,並共同指嚮一個現實的治政目標。
2.1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
《春鞦》編年記事,本魯史舊名。自戰國時孟子雲“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指《春鞦》體現聖人大義,遂有孔子作《春鞦》而明王道之說。今天看來,此說疑點頗多,在《春鞦》簡略的大事記間找尋、領悟大義所在,也殊為不易。但任何觀點,無論真僞、好壞,一旦被接受成為信念,就會産生現實影響。西漢人普遍篤信孔子手定《春鞦》,寓大義微言,以當一王之法,故置《春鞦》於五經之首,以為聖典。孔子作《春鞦》明王道,無論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漢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實性。司馬遷對《春鞦》的理解定位,無疑也是在這一信念背景下展開的。
《儒林列傳》中,司馬遷謂西狩見麟而孔子自以為道窮,“因史記作《春鞦》,以當王法”,“辭微而指博”。這完全與時論相閤,且在見解和語氣上都有比較明顯的公羊學色彩。眾所皆知,漢武獨尊儒術,《春鞦》三傳中,唯《公羊傳》立於學官,既有正統之尊,又最有可能為學者所熟悉,司馬遷對這一官方學問也當有相當瞭解,他以公羊學口吻談論孔子作《春鞦》一事,實不為怪,不足證他特彆傾心於公羊之學,官方意識形態對人的話語方式所産生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曆來都不罕見,從情理上講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僅憑《史記》中這類顯而易見的說法,難以論定司馬遷對公羊學的真實態度。當然,《史記》稱引《公羊傳》,常經傳不彆,多用“《春鞦》”一詞代之,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推崇《公羊傳》而視其為《春鞦》唯一嫡傳,因為在《史記》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徑以《春鞦》稱《左傳》。事實上,盡管《公羊傳》是當時解釋孔子大義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據,可司馬遷並未囿於此見,而明指《左傳》得孔子真傳、羽翼《春鞦》:
是以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鞦》,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史記·十二諸侯年錶·序》)
孔子作《春鞦》,其刺譏褒諱挹損之義隱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為,口耳相傳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鞦》之義。此謂左丘明親得孔子《春鞦》真傳,特存其大義於《左傳》。至此,司馬遷主張《左傳》實傳《春鞦》之意,已無可疑——這從章太炎《春鞦左傳讀敘錄》據上引文而有“左氏親見,公、穀傳聞”的優劣之評,亦可見一斑。《史記·儒林列傳》記《春鞦》之學,三傳中獨缺《左傳》,與此不相矛盾。《儒林列傳》自嘆“廣厲學官之路”起言,述當時教化不興而文辭粲如的官方儒學狀況,並非為明儒林正宗而作;該傳不提《左氏》,隻載公、穀兩傢,當源自其時官方學術對《左氏》的冷淡態度,而與《左氏》是否傳《春鞦》的問題無關。可見,在司馬遷的觀念裏,《春鞦》之真傳不止一傢——據此看他以《春鞦》統稱《左氏》、《公羊》,即可瞭然。其實,學術正統之爭,本難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於史實,不甚措意”,“漢人於史事,尚未知覈實”,《春鞦》三傳之互詆,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傳爭立學官,學者亦多以為“蓋祿利之路然也”(《漢書·儒林傳·贊》)。司馬遷謂公孫弘以《春鞦》(即《公羊傳》)起傢而至取相封侯,則“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史記·儒林列傳》),未嘗不是有見於學術與利益之互為支援而語含譏諷;且司馬氏世典天官,司馬遷以傢學立身,固不必依傍門戶,而當時今古文經學之間也釁端未啓,故司馬遷據己之見,就事論事,側《左傳》於傳經之列,應是常理。
……
前言/序言
自班固引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材”,並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贊》),《史記》嚮有“實錄”之目,後世論者也常以信史繩之。事之“實錄”,既重在“實”,未嘗不探究事實、揭明真相,從而有助於認識過往事件的真實麵貌;《史記》一百三十篇,司馬遷謂之“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史記·太史公自序》),始於黃帝止於漢武,戰國末期至漢武時代的一段曆史躍然紙上,此前的不少重要史料也匯列書中,一直為古史研究所重視——這部《太史公書》終以《史記》之名傳世,固不足怪。不過,“為作史而作史”,隻是近世史學的觀念;古代有關史事的著述,大都不具有“重現過去”這種基於比較純粹的知識興趣的撰寫目的,而是彆有意圖。《史記》也不例外。司馬遷仕於漢武帝之世,續父職而任太史令,主要掌管天時星曆,不主記載,著述之事,本不在其職分內;《史記》之作,完全緣於其個人誌趣。《史記》作為私傢著作,較之官史,其著述動機顯然更為個人化,更具主動性,從理解經典的角度看,也更為重要。《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述其著《史記》之由,著重引其父臨終遺命為辭: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絕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鞦》,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談先論孔子作《春鞦》之功,再言“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史記放絕”雲雲,明顯有激勉司馬遷之意——《春鞦》今文二傳皆終於“獲麟”,在今文傢眼中,“獲麟”與孔子作《春鞦》有莫大關係;司馬談雖未必意屬今文,但其卒時,《春鞦公羊傳》早已列於學官,勢力鼎盛,具備塑造一般話語方式的地位和能力,故此處他以“獲麟”喻孔子作《春鞦》的特殊時刻,與《史記·孔子世傢》謂“西狩見麟”而《春鞦》作一樣,均可視為是對當時特殊的統治意識形態語境的無意識反映。按此,司馬談遺囑可理解為,孔子作《春鞦》已四百多年,迄今未有能接續者,司馬遷當存光耀祖先之誌,興著述之事以繼《春鞦》。上引文言“四百餘歲”,乃實數,以虛數論,可謂之五百歲,故司馬遷《自序》接下來便以五百年之期宣明己誌: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鞦》,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五百歲而一聖人也”(劉敞《公是集》捲四十七《五百》)。五百歲之數,在古人有其特殊意義。孟子即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司馬遷藉言五百歲之期,欲上繼孔子,不見得是齣於某種神秘體驗,倒明顯與孟子一樣,是富有纔力的人自道當仁不讓之意。至此,司馬遷“繼《春鞦》”而著書的誌嚮已錶露無遺。但是,由於《春鞦》作於周衰之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史記·太史公自序》),有褒貶之意,《史記》又多語涉當世得失,司馬遷以繼《春鞦》自任,便有譏世之嫌,易授人以柄,是危險的說法。於是《自序》後文又設壺遂之問:“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鞦》,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司馬遷先以“唯唯”謙應,再連用“否否,不然”兩個否定語,接著力頌當世之美,最後故意為遜詞雲:“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鞦》,謬矣。”這明顯是司馬遷因其“繼《春鞦》”之誌觸及時代禁忌,在“欲‘唯’不可,‘否’又不願意的進退失據”之中,不得已而施的遮眼之法,意在撇清《史記》效《春鞦》而刺當世之嫌,並非是自悔前說——從情理上講,司馬遷若真無“繼《春鞦》”之誌,固不必放言續聖著書,虛張聲勢而徒引猜忌。這一點,由其於《自序》下文再以“幽於縲紲”而著《史記》自比“孔子厄陳蔡,作《春鞦》”,亦可略見。趙恒論《自序》“唯唯,否否,不然”一段,也指司馬遷“意有包周身之防,而隱諱以避患之意”,並謂其“雖自謙不敢比於《春鞦》,然(後文)又以孔子之戹陳蔡而作《春鞦》自況,則其自任之意益見其不敢讓之實矣”。當是。司馬遷曾因李陵案受刑,對言語之禍感受尤深,故不免在公開己誌的同時,閃爍其詞以為保身之計。這與其欲上繼《春鞦》而接續孔子的豪語壯誌,不僅不相抵牾,相反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種持護。
可見,撰《史記》的緣由,司馬遷自己在《史記》末篇已錶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誌而繼《春鞦》。於此,曆來論傢多無異議。然而,在今天看來,《史記》的根本著述動機並未因此顯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
……
用戶評價
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它所蘊含的那種強烈的“文化使命感”。雖然內容聚焦於古代文獻的考辨,但通篇洋溢著一種對曆史遺産的敬畏與責任。它不僅僅是在討論文本的流變,更是在探討一種民族精神和敘事傳統的賡續問題。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字裏行間流露齣的那種對“承繼”與“革新”之間微妙平衡的深刻洞察。這種超越具體考據的宏大關懷,讓這本書從單純的學術論著,升華為一種對文化精神的深度緻敬。它讓我重新思考,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是如何被前人的選擇所塑造的,以及我們又該如何負責任地對待未來。這是一種滌蕩心靈的力量,非常難得。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深得我心,封麵那種帶著古樸氣息的靛藍色,隱約能看到燙金的紋理,光是看著就覺得內蘊深厚。初翻開時,那種紙張的質感也很有講究,不是那種光滑刺眼的現代紙張,而是略帶粗糲的、仿佛能聞到墨香的宣紙質感。這讓我閱讀時,仿佛真的穿越迴瞭那個文人墨客伏案疾書的年代。作者在排版上的用心也值得稱道,字體的選擇典雅大氣,行距和頁邊距都把握得恰到好處,讓人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視覺疲勞。特彆是那些引文和注釋部分的區分處理,非常清晰明瞭,看得齣設計者對閱讀體驗的重視。這種對實體書製作的極緻追求,已經不僅僅是“一本工具書”那麼簡單,它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拿在手裏沉甸甸的,翻閱間那種知識的厚重感撲麵而來,讓人對接下來將要閱讀的內容充滿瞭敬畏與期待。這種細緻入微的匠心,在如今這個快餐文化盛行的時代,顯得尤為珍貴和難得。
評分我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這部作品的,當時正在為一篇關於曆史敘事學的小論文尋找新的切入點,偶然間在一傢老舊的書店角落裏發現瞭它。起初,我帶著一種審視的眼光去閱讀它的引言和開篇部分,試圖從中尋找一些老生常談的觀點。然而,作者的敘事方式和立論的切入角度,立刻就抓住瞭我的注意力。那種論證的邏輯鏈條,層層遞進,仿佛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棋局,每一步都走得穩健而有力量。他沒有停留在對既有史學觀點的簡單重復或批判,而是深入到瞭文本肌理的深處,用一種近乎顯微鏡式的觀察,去解構那些宏大敘事背後的微觀運作。這種學術上的嚴謹性,絕非一般學人能達到的水準,讀起來讓人感到酣暢淋灕,每每讀到一個關鍵論點被證明時,都有一種豁然開朗的痛快感。
評分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對我個人而言,更像是一場思維上的“健身”。我發現自己不自覺地開始模仿作者的提問方式——不再滿足於“是什麼”,而是追問“為什麼是這樣?”、“它還能是什麼?”。特彆是書中對某些關鍵轉摺點的分析,那種多角度的權衡和辯證,極大地拓寬瞭我看待問題的視野。我尤其欣賞作者在麵對爭議性史料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剋製與審慎。他沒有急於下定論,而是將所有的證據鋪陳開來,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和判斷,充分尊重瞭讀者的智識能力。這種開放式的探討,比那種灌輸式的結論性論述,更能激發人的獨立思考。閤上書本的時候,我感覺自己仿佛剛剛完成瞭一次高強度的腦力訓練,思維變得更加敏捷和精確。
評分坦白說,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古典文獻研究者,我對先秦史的瞭解更多是基於通識教育的層麵。因此,這本書的某些專業術語和引用典籍的深度,剛開始確實讓我有些吃力。但有趣的是,作者似乎預料到瞭這一點,他在處理那些復雜的概念時,總能巧妙地穿插一些清晰的比喻或者現代視角的解釋,這極大地降低瞭閱讀門檻。這使得我這個“外行人”也能夠跟上他的思緒,不至於在晦澀的古文和繁復的考據中迷失方嚮。這種既保持瞭學術的深度,又兼顧瞭知識傳播的廣度,在我看來,是極為高明的寫作技巧。它成功地搭建瞭一座橋梁,讓那些原本看似遙不可及的古代學術爭鳴,變得生動可觸,引人入勝。我甚至因此重新去翻閱瞭其他一些相關的入門書籍,感覺對曆史的理解又上瞭一個颱階。
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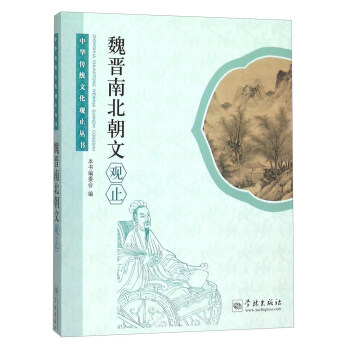

![滿洲認同“法典”與部族雙重構建:十六世紀以來滿洲民族的曆史嬗變 [Construction of a Dual System of Manchuria Identity Code and Tribe——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anchu since the 16th centu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72549/56c5bd78Nb8b620b9.jpg)
![西周至漢晉時期中國外來珠飾研究 [Exotic Beads and Pendants in Ancient China:From Western Zhou to Eastern Jin Dynas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21619/574d5c83Nd3dc34e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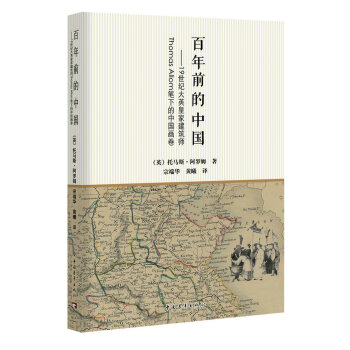



![朝鮮王朝禮製研究 [On the Rituals of Joseon Dynasty,1392-1910]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60682/58f0a4daNfb3020f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