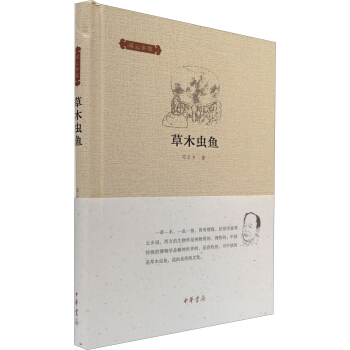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一草一木,一虫一鱼,皆有情致。民俗学家邓云乡说,西方的生物学是纯物质的,理性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是精神世界的,是诗性的。书中谈的是草木虫鱼,说的是传统文化。内容简介
《邓云乡集》十七种之一。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所写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看似专注于草木虫鱼,实际上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借草木虫鱼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富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情趣。
作者简介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目录
前言草木虫鱼知识
话兰
荷与莲
菊有黄花
寒梅
海棠
牵牛?凤仙
芍药
牡丹
茉莉
桂花桂树
毒草
罂粟
烟草
水烟?纸烟
竹
树之以桑
梧桐
银杏王
白果树故事
古槐
槐荫文化
故园草木(之一)
故园草木(之二)
寒窗花草
蟋蟀
斗蛐蛐?听蝈蝈
虫趣话蜗牛
萤火虫
蝉与蛙声
苍蝇(之一)
苍蝇(之二)
虱子(之一)
虱子(之二)
龟寿
蝙蝠
鹦鹉
燕子?麻雀
小金鱼
鱼之乐
种鱼术
弄虫蚁(上)
弄虫蚁(下)
草木虫鱼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草木虫鱼知识韩愈诗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诗题很长,在此不必全引,只是这两句话,就似乎已看出这位“文起八代之衰”,以“圣人”自命的韩文公的思想状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总觉得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应以经邦济世为主的,总是与政治分不开的,最高的理想是王佐之才,澄清天下之志,舍此之外,似乎再无学问。扬雄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连一些才子自命不凡的诗词歌赋都认为是“雕虫小技”,况等而下之为草木虫鱼作注释者乎?不过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圣贤之志,以及大量表面讲圣道、胸怀窃国志的“英雄”们的口头禅,而并非凡人所能想象的。一般凡人,靠自己双手做工种田,或手脑并用,爬格子乞讨稿费的人的想法则是另一种的,说的更具体些,就是更接近生活,更实际一些,也就更有情趣些。
生活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物质是自然界给予的,又是在生活中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没有自然界的给予,不可能有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物质;没有智慧和劳动的创造,人类也不能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只能像动物一样向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原始物质。所以细想想,人类的学问,还是从最早认识自然一草一木开始的。因而草木虫鱼本身就是很重要复杂的学问。等到圣人们讲仁政、霸道等等大学问的时候,自然远在初步认识草木虫鱼之后了。
不过中国圣人讲大学问,却也有其独特的特征,就是不讲上帝,不讲神灵,而只讲人,或者说只讲圣人。比如说火,首先想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这是《韩非子》中记载的;他是王天下的圣人。其次是祝融、阏伯,被人尊为“火祖”,享祀南岳,是《汉书?五行志》记载的。至于说所谓“火神”,这是因崇拜火神的波斯索罗亚斯德教的传入而流行开的,这是唐朝的事,远在燧人氏和祝融、阏伯等“火祖”之后了。至于那位偷窃上帝火种给予人间的天使,那是出于希腊神话上的外国故事,传入中国,为人所知,更是近代的事。比之于古老的燧人氏,那更是不成比例的晚生后辈了。就从此一例的分析上,也还可以看出中国人历来相信,生活知识进而至于全民文化,最早都是人教的,而非神赐的。谁能说中国人迷信呢?
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螺祖教民养蚕缫丝……最早的圣人们似乎都是以生活的知识和手段来教民的,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头以后,那情况就完全两样。那“钻木”、“构木”、“尝百草”,等等,都是“草木虫鱼”的雕虫小技了。不过虽然圣人不提倡,而老百姓还是十分爱好此道的,生活的观察越来越细致,劳动的创造越来越辛勤,知识的积累和传授、继承也越来越丰富,这样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握也越来越深刻了。到了中国文化典籍从无到有,孕育成熟,一一问世,集大成的时代,那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已经十分完备,而且载入典籍,以垂永久了。自然这是众多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而非出于某一个神人、圣人的恩赐与教导。但是在众多的人中,智慧超群的人也是不断涌现的,自然他们在获得、创造这些知识中是起了更大作用的。
鲁迅曾经说过第一个懂得吃螃蟹的人,一定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其实他这个笑话想得未免简单些,因为这“第一个”恐怕是很难选出的。先民生活生存,想来是群居的多,不要说当时还没有文字纪录,纵然有,恐怕也无法分第一第二。再有纵然找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恐怕也还是生吃的,不会蒸熟了,剥开来蘸着姜末、镇江醋,佐以绍兴老酒,悠悠然地吃。所以好多事,好多话,不细想尚可,一细想便不免有许多问题,纵然是被崇拜为“神人”的人,他们的话也还是值得推敲的。《韩非子?五蠹》中说得好,他道: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看来这位法家的话说的还是没有太大漏洞的。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自然是生吃,这些或者包括螃蟹在内,最早吃它,恐怕并非贪九雌十雄的美味,当然更并无持螯对菊的雅兴,而只是肚子饿得恐慌,捉来能吃的各种植物、动物充饥,野果、野瓜、鱼类、蚌类,等等。大概懂得吃种子,还在懂吃野果、野瓜之后;懂得取火、熟吃,更在此后。懂得钻燧取火,自然也是智慧出众的有心人,这就是古代的“圣人”。自然人类由因饥饿而寻找食物,由生吃而熟食;由向大地自然界寻找野生植物、动物充饥,到懂得种植谷物、饲养家畜;由单一认识动、植、矿物的区别,到分出不同大类,不同小类,单一名称,各自特征……这中间经过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十分漫长的岁月,其间不知经过多少智慧超群的有心人的仔细观察、比较研究,传授给众人,这样创造了最早的文化,也可以说是草木虫鱼,自然也包括鸟兽的早期的知识、学问,完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万物的初级阶段。关于这点知识的获得过程,我想中外大概是一样的。
这种认识,又历多少世、多少劫之后,那就是花柳含情、草木生春,虫鱼亦通人性了。读近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有一段以虫比人的文字,小有情趣,现引于后,以见人类对草木虫鱼认识的升华吧。原文如下:
以虫比人,蚕是鸿哲大儒,吐其丝纶,衣被天下。蜂为名将相,部勒有法,赏罚严明;酿花成蜜,犹之造福地方也。蝶是名士,爱花嗜酒,倜傥风流。蝉乃高人,吸风引露,抱叶孤吟。蟋蟀,闺妇也;蜻蜓,江湖游食之人也;蜘蛛,土豪也;蚊蚋,马贼;蚤虫,鼠窃也;苍蝇,依附势力之小人也。螬蠹,猾胥狡吏也;臭虫,奄宦及恶丁劣役也;粪中蛆,乃纨绔子弟及持禄保位之公卿也。惟蝼蚁确是务本业安分守己之善良百姓。
试问读者,感觉他的比喻如何呢?
……
前言/序言
说起“草木虫鱼”,首先就想起了《骆驼草》,前不久买了一本影印的《骆驼草》合订本。这已是整整六十年前的刊物了,好在是影印本,还如看到当年的刊物一样,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虽然当此刊物出版时,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要上学读书的孩子,但毕竟它的出世晚于我,也算是我经历过的事了。在此合订本的一七八页上,刊有一篇岂明写的《草木虫鱼小引》,这是他所写《专斋随笔》的第六篇。文章开头先引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的话,然后从“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二语,发挥开来,阐述写文章的道理。结尾处归结云:
——话虽如此,文章还是可以写,想写,关键只在这一点,即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作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可以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只怕此事亦大难,还须得试试来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选择一下再说,现在便姑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十九年旧中秋。
中国文人照例是小题大作的,香草美人都要联系到国家大事,《红楼梦》中吃完螃蟹,宝钗姑娘写有一首意存讽刺的诗,别人还称赞道:“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由于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写的人、读的人有时都变成神经质的人了,明明是普普通通一草一木,却要把它拟人化一番,要写出微言大义来。如果有哪位说草就是草,说木就是木,并没有指桑骂槐,这样看的人就感到不满足,在字里行间,还想找出点这个或那个来,或者说好,或者说坏,比如《诗经》“关关雎鸠”的诗篇,一定要被解释作“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化之端也”。反正原来编这首诗歌的人不知是谁,况且又是死了几千年的古人,死无对证,如何解释,也没有人分辩了。因为是“经”,就要说的特别好些,引申而又引申,那样任何说到草木虫鱼的具体文字,都可以辗转引申成为至高无上的称颂;或者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延展,变成大逆不道的诅咒了。
岂明说“草木虫鱼”,原因第一、第二之间,看似“好说”、“想说”,实际也不尽然。原因之一是“我所喜欢”,这就大成问题,别的不喜欢,为什么单喜欢“草木虫鱼”呢?从传统的观点来评价,一顶“玩物丧志”的帽子便可轻轻地扣到头上。从新的伟大的观点来评价,最轻的评语也可以说是“无聊”、“落后”。如用最新的“经济效益”的观点看,草木虫鱼如能赚钞票,便可欢喜;如不能赚钞票,欢喜这些就是寿头,那是一切以钞票为准星的标准。因此岂明认为草木虫鱼可说的第一原因并不一定能成立,或者还待商榷。
第二原因他说草木虫鱼是生物,又是异类,既与人类有关系,却又因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些说法如仔细思量,却有时也觉得难说。苏东坡《赤壁赋》说:“宇宙之内,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就似乎告诉我们,草木虫鱼,等等,也是各有其主的。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异类”纵然可让你随便说它,那这些“异类”的主人也不见得让你随便乱说。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无主的“草木虫鱼”,似乎可以随便说说,但能说的、说得来的、想说的、有兴趣说的,实际也并不多。视野有限,不能周游天下,也不能像神农氏那样尝百草,无法活到银杏树般的寿命,无法变成蚯蚓钻进泥土中,无法潜入海底与鲨鱼交朋友,无法像庄周那样化为蝴蝶,无法像跳蚤那样一跳超过自身高度几百倍……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比之草木虫鱼之同为生物,究竟高明多少呢?万物之灵的人,对草木虫鱼知道又有多少呢?既不高明又无知,这样来讲说草木虫鱼,岂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似乎人有感情,比草木高明得多。其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某种程度上,草木似乎更守信义、有生机、顺自然,这似乎是更高超的感情。自然它不会有尔虞我诈、种种骗人欺人的伎俩。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蒙庄虽然用“子非我,又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驳倒惠施,实际也似乎是在玩弄诡辩哲学,他是否真知鱼,则大成问题。当一条泼剌剌的活鱼被从水里钓上来,放在砧板上,开膛破肚刮鳞,“哗啦”一声,放入滚开的油锅,这时他只闻着香,馋涎欲滴了……哪里还会想到鱼乐呢?河南馆子,爱以“梁园酒家”命名,名菜是糖醋瓦块,正是蒙庄的家乡菜,难道庄子不吃鱼吗?这是不可能的,这正像口头上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孟轲一样,同样是假正经。“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他连熊掌都能吃,何况鱼和红烧牛肉呢?所以庄子、孟子以及其他圣人、凡人都一样。从“草木虫鱼”的立场来看人,那太可怕了,太残忍了,他们笑嘻嘻地就把草锄了,割了;木砍了,锯了;虫灭了,除了;鱼杀了,烹了……用岂明前面的话道:“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这话明称“异类”,便生杀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想多么可怕呢!如只想着冲淡的散文是多么和平典雅,那就忽略了另一面了。当然,我这里不是针对岂明而加以批判,只是借他的话来说明一点世情而已。
如上所云:难道真像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所引白石生辟谷默坐时回答别人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吗?“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既无一可言,为什么还回答人两句话呢?“花如解语诚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或者说:一言不发才是最可爱的。但鲁迅又说过:最大的轻蔑是无言。因而一言不发的人,如遇到鲁迅,那就要恼怒你是对他轻蔑了……这又要学会说天气哈哈,或跟着喊打倒以及三呼万岁,等等。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看来人注定是要受“口”——这个不可少的五官之一之累的。奈何!奈何!
世界上哑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父母给了一张“口”,是既能吃饭,又会说话的。“少说话,多磕头”的教训是要牢牢铭记在心的。不过“少说”,并不等于不说,说还是要说的。只不过不要认真,要讲求一点处世的艺术,讲求一点语言的艺术,这样就要注意一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讲什么有意思,而又比较少麻烦,说来说去,又回到“草木虫鱼”上来了。
草木虫鱼可说乎?曰可说,不过也要有几个条件。比如说:草木虫鱼的范围那么大,联系那么广,知识有限,见闻有限,又如何能说得广,说得全,说得深,这也只能就有所知者说之,就有趣者说之,尽量就不会惹麻烦者说之……这样一限制,实际能说的也就不多了。
先此声明,以免贻笑于读者,是为“小引”。
用户评价
从整体的阅读感受来看,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一种久违的“踏实感”。这里的“踏实”并非指内容上的简单易懂,而是指作者对所描绘对象的尊重与热爱所带来的充实感。他似乎用尽了毕生的积累去描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度,都经过了反复的揣摩和验证。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所描绘的那个世界观感变得更为丰满和立体,好像亲身经历了一段旅程,接收到了大量的鲜活信息和感性认知。这是一种非常充实且有分量的阅读体验,它不像某些流行读物那样读完即忘,而是会成为认知结构中一部分坚实的基础,让人在日后的生活中,也更容易以一种更具洞察力、更富有人文关怀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知识与情感的投资。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巧妙,张弛有度,丝毫没有拖沓之感,却又留足了让读者回味的空间。开篇的铺陈自然而然,像是春日里缓缓融化的冰雪,逐渐展现出故事的全貌和人物的性格底色。中段的情节推进紧凑,高潮迭起,引人入胜,常常让人在夜深人静时也忍不住想再多读几章,去探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到了收尾之处,作者的处理又显得那样收敛和含蓄,不落俗套,留给读者的解读空间非常大,读完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留下的思考余韵比故事本身更值得玩味。这种流畅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无疑是建立在一流的文学素养之上的,让人由衷佩服作者对整体布局的掌控力。
评分这本书所蕴含的思想深度,远超乎我最初的想象。它绝非是肤浅的记录或简单的叙事,而是在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篇章背后,都隐藏着对人情世故、自然哲理的深刻洞察。作者似乎拥有穿透表象的能力,能够直达事物的本质,并在不经意间将那些宏大而严肃的议题,巧妙地融入到细微的生活片段中。我时常会因为某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议论而停下来,反复咀嚼,体会其中蕴含的智慧和人生的况味。它像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社会百态,更引发了我对自身存在和价值的重新审视,这种由内而外的触动,是任何快餐式阅读都无法提供的精神滋养。
评分作者的文字功底简直是炉火纯青,笔触细腻入微,观察事物极其敏锐。阅读过程中,我被他描绘的那些日常场景深深吸引,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细节,经过他的笔尖一加工,立刻鲜活了起来,仿佛拥有了生命和呼吸。他似乎总能捕捉到藏在生活肌理中的那些微妙的情绪波动,无论是喜悦的瞬间,还是稍纵即逝的失落,都被他精准地捕捉并用极富画面感的语言呈现出来。阅读体验就像是跟着一位高明的导游,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这种文字的魔力,让人不禁放慢了翻页的速度,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妙的比喻或是那如珠玑般闪光的词句,让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文字本身的力量与美感。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拿到手中便能感受到一种朴素而又精致的韵味。封面采用的纸张质地细腻,触感温润,那种微微泛黄的色调,仿佛带着岁月的沉淀感,让人联想到旧时的书卷气。排版上,字体的选择也十分考究,疏密得当,阅读起来极为舒适,即使长时间沉浸其中,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装订工艺扎实牢固,侧边翻阅时,能清晰地看到书页间严丝合缝的纹理,体现了制作者的匠心。整体而言,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将传统的美学与现代的制作技术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光是摆在书架上,就足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人忍不住想时常拿出来摩挲一番,感受那份独有的书香气息。
评分好书推荐给大家分享一下正品特价
评分邓云乡集:草木虫鱼邓云乡集:草木虫鱼
评分这次出版,将《石头记》正文、批语和评点用不同的颜色分别印刷,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对各部分的内容一目了然。同时也使得本书独具特色,成为当下同类书中别具一格的特例。
评分听邓先生通过草木虫鱼讲诉传统文化.
评分很实惠,看着不错。内容很有趣。
评分感谢中华书局,要是布面精装就更好了
评分感谢中华书局,要是布面精装就更好了
评分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邓云乡先生所写关于草木虫鱼的知识。看似专注于草木虫鱼,实际上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借草木虫鱼讲述中国传统文化,富有浓烈的中国文化情趣。一草一木,一虫一鱼,皆有情致。民俗学家邓云乡说,西方的生物学是纯物质的,理性的;中国传统的博物学是精神世界的,是诗性的。书中谈的是草木虫鱼,说的是传统文化。
评分帮同学买的,赶上活动,很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本站所有链接都为正版商品购买链接。
© 2026 windowsfron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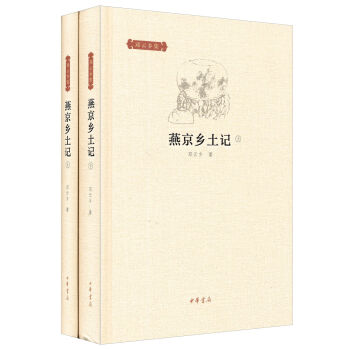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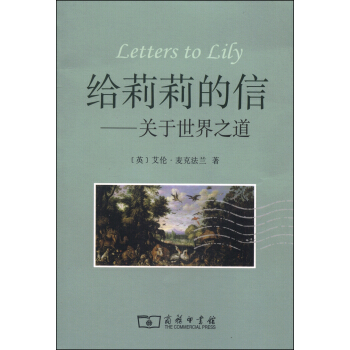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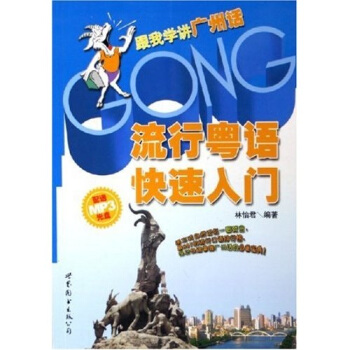








![常青藤好老师教学策略系列:快速改善课堂纪律的75个方法(白金版) [75 Quick and Easy Solutions to Classroom Disrupt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80231/rBEhVlHt2CsIAAAAAADGptW6_h8AABVGwCZVg0AAMa-46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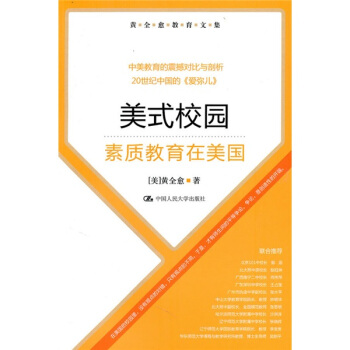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 [Future Wise: Educating Our Children for A Chang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7836/55c30935N0c64263b.jpg)